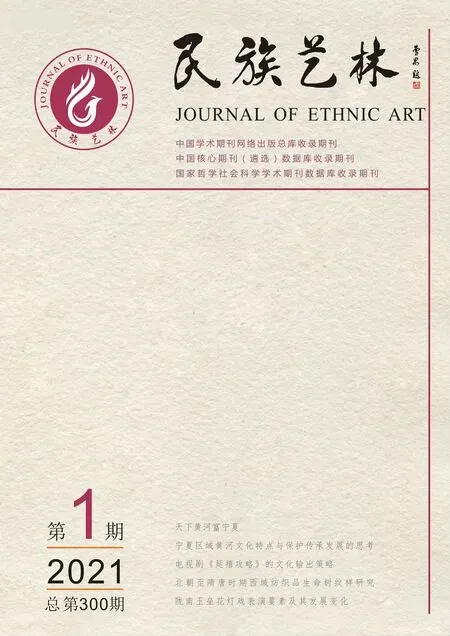云南彝族再生神话特征论析
——兼与东北满族等民族神话《尼桑萨满》比较
2021-12-07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中国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人口达870 多万,位居全国第七位,是西南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之一。马学良曾说:“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生活的渊源,研究他们的神话,是最直接的材料。”[1]作为人类文化和文学的重要组成,神话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云南彝族神话是中国西南彝族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外界认识云南彝族思想和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彝族再生神话定义及内涵
按照彝族神话的演述逻辑,灾难发生之后会出现人的死亡。在“灵魂不灭”观念影响下,亡人的灵魂经过毕摩①指路回到彝族的发源地,又与祖先相聚,并化生为祖先神,进而庇佑后人并受到人们的祭拜。因此,人的死亡、亡灵的超度、人的再生是彝族死亡认知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再生神话是彝族人关于死亡和指路为内容的神圣叙事。按照神话文本内容来分类,云南彝族再生神话可分为死亡认识神话、死亡发生神话和再生神话三类。死亡认识神话以“死亡是什么”为主要叙事线索;死亡发生神话则以“人为什么会死”为主题叙事;再生神话以毕摩为亡灵指路实现再生为主题叙事。彝族人认为,人生病或死亡是因为灵魂丢失所致。人的灵魂一旦被阴曹地府的阴兵抓去,人必然生病甚至死亡。人死有三魂:一魂在家中祖灵排位处,一魂在墓地处保佑,一魂经毕摩的指路回到了族群发源地,与祖先团聚。这是彝族先民对死亡观的一种独特认识,并深刻影响着彝族再生神话。
云南彝族神话史诗《梅葛》讲道:“天王撒下活种子,天王撒下死种子。活的种子撒一把,死的种子撒三把。死种撒出去,会让的就能活在世上,不会让的就死亡。”[2]天神撒下死种,人类就有了死亡,生死由天神控制,这是彝族人朴素的死亡认识。在彝族神话中,死亡就像种子,天神撒下一把,哪里就有死亡;天神撒向哪里,哪里就有人死。由诸神组成的神灵体系,等级森严,天神作为最高统治者,权力无限,掌管人间的生老病死。因此,在“天命观”影响下形成的云南彝族死亡观具有如下两方面的重要内涵。
第一,直面死亡。《逃病逃死》经文说:“老死逃不脱,病死躲不了。死临学阿龙,沉疴学阿龙,阿龙躲棺中,烂在棺材里,化在棺材内。”经文以一问一答形式,向亲属讲述了人必有一死的道理。老极必死,病极必死,是人生无法逃避的现实命题,要像英雄支格阿龙一样直面死亡之神。在死亡神话中,讲述者从不回避死亡命题,且在死亡的现实面前,表达主动勇敢面对死亡:一方面体现出天神宿命论,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彝族人豁达的死亡观,不畏惧死亡、善待死亡的人生态度。
第二,从死而生。《死亡》经文吟诵道:“狐狸平路场,兔子山包死,没有不死物,没有不损物。是碗就会缺,是石就会碎,是叶就会落,是果就会坠。……他也会致病,他也有一死。无不死男人,无不死女人。”[3]彝族死亡神话不仅讲述死亡何为,死亡如何发生,还重点叙述死后何为的哲学问题,即从死而生。彝族“灵魂不灭”及“人有三魂”的灵魂文化观认为,人死得到永生,即升天成神,并以祖先神灵的方式保佑后代平安吉祥、人丁兴旺。
二、云南彝族再生观
彝族人认为,逝者去往阴间时,往往会因迷失方向而受魔鬼阻拦,不得超度,所以人死后都要请毕摩念诵《指路经》。《指路经》是“以彝族迁徙史为依据,以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观念为依托,以祖先崇拜观念为支撑的典籍”[4]。指路内容大多涉及死者的列祖列宗从何而来、本人生平情况,以及如何去阴间,等等。可以说,毕摩指路的内容就是一个形象、生动、完整的彝族再生神话,指路为再生服务,再生建构了彝族再生文化。云南彝族再生观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宣扬积德行善方能再生的教化思想。《彝族教典·人生哲理篇》:“世间的人类,死后变牲畜,死后变禽鸟,死后变野兽,十变方成人。”[5]毕摩经中讲道,人要生前多做善事、多积德,死后才能变为人。由此可见,在彝族人的信仰体系中,人死后化生是一个基本认识。人死必化生,而化生为何物,要根据生前的德和善的积淀来决定。《投生》吟诵道:“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轮回去投生。投生变什么?投生莫做牛。……投生变作猫,可以上房梁,灶头任意睡,美味和佳肴,任尔尽情享。投生变什么?变成咕咕鸟,变成布谷鸟,变成鸥乌鸟,变成此三鸟。每年二三月,房屋背后树,枝头去栖息,催促儿做活。”这则经文讲述逝者如何选择投胎转世的故事。若不能转世为人,最好投生为催生鸟,以便于催促儿子勤劳持家。在彝族民间,父母临终前,若有孩儿尚未成家,往往会异常惦记,转世到阴间也会督促孩子成家立业。他们认为,成家立业之后才能更好地积善行德,人只有积累到更多的德与善,今后才能更好地实现再生。
第二,再生形态的生活化。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看,毕摩经典以及口传文本鲜有关于如何转世及再生的具体叙事。笔者以为,这是毕摩将“阴间叙事”视为非正宗、经典的祭祀内容,认为那是苏尼所作所为,不应该列入毕摩经典记载范围,因而未收录和传抄下来。在彝族社区,毕摩与苏尼的职责确有分工,且界限相对明晰。苏尼是彝族传统社会的巫师,虽不懂经文,但也经常施巫术驱鬼治病,被彝族人认为苏尼常与阴间打交道。当然,二者也有相通之处,他们在原始社会早期都是巫师,一个是受原始巫术思想支配而施术的巫师,一个是祈祷祭献的祭司。随着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毕摩的祭祀礼仪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巫术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减弱,苏尼的地位从而下降。笔者故将再生神话放置在彝族日常生活中去讨论。以笔者田野调查点为例,楚雄州禄丰县高峰乡彝族格苏颇支系的成年男性去世后,出殡第二天上午由毕摩带领孝子到山上竹丛中找祖灵竹。毕摩念经后,孝子大叫三声“阿爹”,最先摇动的竹子即被视为祖魂依附。孝子将竹连根挖出捧回祭场,由毕摩用刀刻成人形,以银子点上眼鼻裹上五色布即成祖灵。彝族人在家中设香炉,插竹灵牌位,即成为祖灵堂位,受后人祭拜,寓意祖先与家人常在。由此可见,云南彝族再生观以生活化、活态化存在于民众的日常实践之中。
三、云南彝族再生神话特征
为更好地总结云南彝族再生神话特征,笔者选取一则广泛流传的满族《尼桑萨满》②与之进行对比分析。现转引满族再生神话《尼桑萨满》的主要情节:
A.1.巴彦夫妇中年时,其子15 岁上山打围而死(又说10 岁病死)。2.50 岁时,又生一子塞尔古岱·费扬古,15 岁时上山打围又死。3.办丧事时,一神人指点让他们去请尼山萨满起死回生(又说来一道士指点)。4.尼山萨满答应,并请二神纳里·费扬古帮忙。B.5.尼山萨满渡二道河,闯三道关到了阴间,得到了塞尔古岱·费扬古的灵魂。6.尼山萨满给蒙古尔岱舅舅鸡、狗、酱等,使塞尔古岱·费扬古有了90 岁的寿限。7.尼山萨满碰上死去丈夫的纠缠,将其抛入丰都城,让他永远不能转世。8.尼山萨满见到了子孙娘娘,看到了各种刑惩。C.9.尼山萨满回到阳间救活了塞尔古岱·费扬古,得到巴彦员外的赏钱和财产。10.赛尔古岱·费扬古娶妻,夫妻活到90 岁。11.婆婆得知尼山萨满没有救她的丈夫,告与皇帝。12.皇帝大怒,将尼山萨满拴在井里。13.尼山萨满成为萨满的创始人。[6]
我们从作者划分的A、B、C 三个大情节和13个小情节来看,在《尼桑萨满》关于人死而复生的神圣叙事中,萨满起到了赴阴间为人救命的关键作用。
而在彝族文献典籍《唐王游地府》中,讲述的是毕摩假借唐王的名义赴阴间游玩,让阎王增改生死簿的有趣故事:
拿上生死簿,呈给阎王看。阎王见唐王,阳寿三十三,皇位十三年,就对判官说:“唐王寿面数,再加二十年!”金口出玉言,正合判官意。阴间冲判官,拿起生死簿,删去四页书,重修六页满。阎王接着说:“然后带着他,阴曹地府中,三十六河边,让他看一看;七十二种刑,让他瞧一瞧;美丑和善恶,让他辨一辨。回到阳间后,让他去教导那些行恶人。”阎王吩咐毕,阴君阎罗王,送出唐王来。[7]
这个故事表达了彝族人的再生观,告诫人们多多行善,延年增寿,死后才可轮回转世。这部出自毕摩之手的经书,从文本内容来看,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部彝族传统经籍文学,其神圣性荡然无存,而幽默、风趣的情节增加不少。这部经文,应该是唐朝以后彝族毕摩学习和借鉴汉族文化而不断增补修订完善的整理本,它既不同于古代的唐王故事,也不是单纯的毕摩经文,而是一种内化了彝族再生思想和汉文化交融的毕摩文献。
满族萨满信仰与彝族毕摩信仰比较,都是原始性信仰,表达的是人类生死、宇宙起源和万物变化的认识观和世界观。萨满有男有女,也唱萨满神歌。而彝族毕摩则全为男性,以念诵毕摩祭经为重要内容。同时,《尼桑萨满》神话不仅流传在满族,在达斡尔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东北人口较少民族中也广为流传,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重要口头文学代表,体现出北方少数民族的死后再生的观念。萨满直接进入了阴间,帮助亡者找回灵魂,实现人的复活和再生。而毕摩则以指路方式帮助亡灵回到祖先的居住地,没有走丢迷路,与祖先相聚,不成为孤魂野鬼,方能实现再生。从《唐王游地府》的情节来看,创作主体已假借历史上的人物之名进入阴间。从在阳间吟诵经文指路到游玩阴间,可以说是一种空间的超越。阳、阴空间的转换,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移动,而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云南彝族文化与中华汉文化交流交往早已有之,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改土归流”,推动了彝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融进程。毕摩的指路融会了唐王故事,从而形成了彝族特有的唐王游地府的毕摩叙事。满汉文化的交融也会影响到西南边地的彝族文化。相比满族的萨满,彝族毕摩的职责和功能均有所不同。毕摩被视为神的化身,具有神性,阴间的鬼等诸类畏惧毕摩的威力。毕摩是人,是彝族民间的知识分子,毕摩不参与阴间或鬼之类的祭祀活动。苏尼,如前所述,类似于汉族社会的“巫师”或“端公”,也与北方民族的“萨满”具有相似性。但在彝族传统社会,毕摩的社会地位较高,尤其在氏族和部落时代,毕摩就是统治者,“他们是彝族最早的自发的公众领袖即酋长”[8]。而苏尼的社会地位较低。因此,我们通过彝族再生神话也看到彝族民间的地方性知识。毕摩指路是引导亡灵回归故里,回到祖先发源地,“不忘来时路”,才能更好地实现再生。
综上所述,我们试图对云南彝族再生神话的特征作如下总结。
第一,再生神话是毕摩及仪式文化的综合体。云南彝族再生神话借用毕摩吟诵和指路,实现亡者的再生。纵观而论,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毕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再生神话也是仪式神话,它强调仪式性,即再生神话伴随毕摩祭祀仪式而产生,毕摩成为再生神话的主要演述者和推动者,亡灵的回归、逝者的再生、祖先成神等一系列愿望,均在毕摩的指路和祭祀中得以实现。毕摩作为人与神之间的使者,既具有神的力量,又具有人的特性,俨然成为神性人物。这正与马学良在《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一文中揭示的论断相符:神巫呗耄天上来。毕摩从天而来的情节叙事在云南彝族神话中并不少见,在贵州彝族甚至将彝族人文始祖支嘎阿鲁形塑为毕摩始祖。这些在地化的神圣叙事,旨在表达彝族毕摩神圣化的事实。作为人和神的中介,具有人性的毕摩被神圣化的形塑过程,其实也是彝族人表达死后成神,死而再生的美好祈愿的一种独特方式。毕摩手持经书,面对逝者念诵《指路经》,经文指引的方向是祖先居住的地方,在毕摩祭祀的演述场域中,祖先也是经毕摩指路而再生,乃至神化后的人物。因此,离开毕摩祈祷和献祭仪式,再生神话无从叙事。
第二,再生神话叙事的多形态化。在云南彝族社区,人神同在的思想不仅集中体现于丧葬祭祀活动,在火把节活动中也有所体现。高峰乡彝族人每年欢度盛大的火把节,节日从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起至二十七日结束,历时四天。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各家各户进行叫魂、祭祖活动;二十五日进行开光、祭天等祭祀活动。开光即用大红公鸡的冠子血为祭火所用的主、副傩神面具及龙、虎、凤旗点眼,祈求大神大将降临,使其显神灵;二十六日全天和二十七日上午,逐家逐户进行扫邪驱魔活动。彝族人认为家中有病人,是被视为有鬼邪祸害,需认真扫邪;二十七日下午进行送火仪式。据笔者观察和分析,火把节祭祀活动中有两个主要仪式,即驱鬼逐疫和送火把,均内含再生叙事,属于彝族再生神话。在毕摩的指路叙事中,指路不再局限于丧葬祭祀情境中的亡者指路,我们可理解为广义上的指路,即献祭祈福。虽然没有看到字面意义上的复活字样,但背后却隐藏着相应的意涵。毕摩带领村民延请祖先神庇佑人们,祈愿人畜平安吉祥、国泰民安。该地彝族民间故事讲道,三大面具代表三位大神,分别代表彝族首领孟获、孟优、孟亮三兄弟。他们均是身经百战,白天战死沙场,夜里却能复活再生的英雄。他们的军队、军旗、战刀,都被彝族后人保留和传承下来。因此,火把节演绎彝族英雄祖先的征战仪式,再现战斗的实物和场景,构成了具有复活功能的神圣叙事场域,成为典型的彝族再生神话。可见,云南彝族再生神话的叙事不仅存在于丧葬中的亡灵复活,也呈现在节日祭祀甚至日常仪式,叙事具有多形态化。
第三,人神共美理念是再生神话的追求。云南彝族再生神话植根于彝族人的民俗和信仰体系之中,它以仪式为活态存在方式,以毕摩为中介,以期实现人与神的共生和共存。它通过毕摩献祭取乐于神,让诸神庇佑后人,最终实现人神共美、美美与共。“人类要好好生活,不但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还要处理人与自然、人与鬼魅的关系”[9]。人与祖先、人与神是云南彝族再生神话中极为关键的两组关系。高峰彝族火把节祭祀仪式上摆放着三个大神面具,寓意土主、人祖、天神。彝族人把祖先神在节日中加以祭拜,既强化祖先和英雄崇拜意识,也体现出人神共生、共存和共美的理想追求。
总之,云南彝族再生神话是基于死亡观和再生观形成的一种较为独特的神话类型。它以直面死亡、向死而生的死亡观,以及积善再生、生活化再生的再生观为丰富内涵,具有毕摩及仪式文化的综合体、多形态化再生叙事,以及人神共美理念追求的显著特征,是云南彝族思想和生活的重要象征和符号,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注释
①毕摩是彝语音译,因各地区彝语方言不同,也称为“贝玛”“布摩”“腊摩”“朵觋”“鬼主”等,目前彝学界通译、通称为“毕摩”。“毕”即念诵,“摩”即长者,毕摩是彝族宗教祭祀活动的主持人,是彝族文化的集大成者。
②《尼桑萨满》,又称《尼山萨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