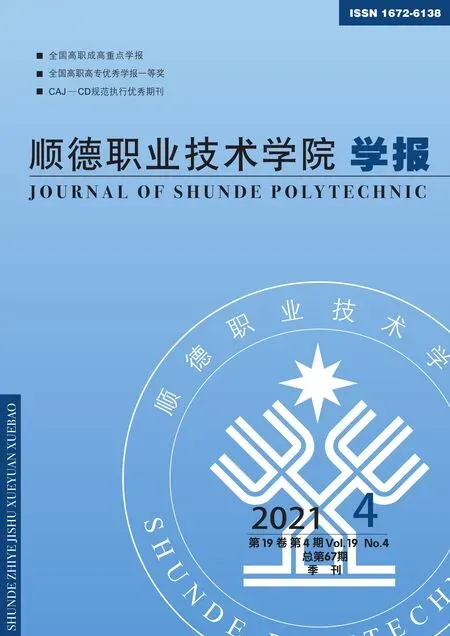唐小说中的山神形象变异研究
——以华山神为例
2021-12-06杨媛媛
杨媛媛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作为一种古老的自然崇拜,山岳崇拜起源久远,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能找到这种崇拜的影响痕迹。而在中国,最突出的山岳崇拜要数五岳崇拜。其中,华山作为五岳之一的西岳,历来享有崇高的地位,特别是在唐代,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更是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被纳入国家祀典的范围。然而与之相对的,却是中晚唐小说中屡次出现的华山神作恶故事,其中的华山神形象极度恶化,成为致人于死的邪恶神灵。这些故事情节固定、人物形象鲜明,细究下来,有着超越文字层面的深层文化内涵。
1 唐前文献中的山神形象
像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国先民也很早出现了对山岳的崇拜,并在不断的演化发展中,完成了山岳崇拜的人格化核心:山神崇拜。考察我国山岳信仰及山神崇拜的形成,可发现一条明显的演化痕迹:即由最初的山体崇拜过渡到山精(山鬼)崇拜,最后成熟和定型为山神崇拜[1-2]。其中,山神崇拜又可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短暂地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女性山神崇拜,后期则主要是以男性山神为主。
一般来说,最早的女性山神形象可追溯到屈原的《山鬼》篇。此篇虽名为“山鬼”,但通过郭沫若等众多学者的考证,现在普遍认为是战国时期楚国祭神的歌曲,实乃《九歌》的“尾声”部分。从其中内容的描写来看,整篇充斥着一股淡淡的忧愁气息,而篇首对“山鬼”的描写:“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3]24,一个美好、多情、善感的女性山神形象分明跃然于纸上。至于后来宋玉在《高唐赋》中所描写的“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3]95的巫山神女,更是十分确定为定居巫山的女神。
然而要注意的是,我国古代毕竟还是一个长期封建的男权社会,也因此,女性山神存在的时间十分之短,很快就被男性山神所取代,占据了历史的舞台。两汉以后文献中记载的山神形象基本以男性为主,其中又以五岳神为山神中的最高代表。所谓“五岳”,东汉的《白虎通德论》中引《尚书大传》的说法,称:“五岳,谓岱山、霍山、华山、衡山、嵩山也。”就笔者目前检索到的资料来看,唐代以前关于五岳山神的记录和描写基本都偏向于正面,兹举几例以作说明:如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中就记载了霍山神与赵襄子之间的一场“合作”,说霍山神传书给赵襄子,称:“赵毋恤,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4]1795在这里,霍山神答应帮助赵襄子取得战争的胜利,条件是要求赵襄子为他建立百邑进行祭祀。很显然,此处的霍山神是以战争辅助神的形象出现的,可以决定战争的成败和获得土地的多少。此外,曹丕的《列异传·蔡支》中又记载一条有关泰山神的故事,称一个叫蔡支的县吏途中迷路,行到泰山脚下,“见如城郭,遂入致书。见一官,仪卫甚严,具如太守。”[5]170这位形象如人间太守的“官员”其实就是泰山神,他在与凡人蔡支的交往中,彬彬有礼,温润谦和,不仅设席款待,还十分信任他,请求他为自己送信给天帝。于是,蔡支在山神的引介下,又去到天界认识了天帝,从而获得天帝敕命,使已故的妻子由死转生。同样的,在干宝的《搜神记》一书中,《张璞》[6]49故事里的庐山神也被刻画成一位充满人情味的山神形象。在此故事中,太守张璞家的婢女不敬神明,指着庙中的神像与小姐作配,这在古代的民间信仰中,无疑可视作对神明的一种“口头承诺”。于是,张家人不得不将小姐投入水中祭神。而此时,作为被凡人“戏弄”的庐山神却没有理所当然的享受祭品,而是派人将两位小姐送还阳间,展现出山神性格中充满的人情味与正义感的一面。
以上数例都涉及唐前文献中对华山以外其他山神形象的刻画。我们发现,在这些山神中,无论是轻盈美好、感情细腻的女性山神,还是仪态威严、气势肃穆的男性山神,其神格要么是中性的,要么是偏向于善良、正义的一方,比较符合传统思维中对神灵形象的构设。下面具体分析五岳中的华山神形象及其演变过程。
2 华山神形象在唐代的新变
作为五岳中的西岳,华山受到的关注直到唐代以后才猛然增多,在此之前能读到的记录非常少,有《后汉书》中记载的一条,称“昔秦之将衰,华山神操璧以授郑客,曰:‘今年祖龙死。’”[7]1078在这里,虽然出现了华山神这一形象,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体现山神预知生死的能力,并没有对山神性格进行善恶方面的刻画。而进入唐代以后,由于华山地近长安的特殊地理位置,常常出现在其时的文学描写中,如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都曾以此为题,留下许多传世的精彩诗篇。至于小说中,华山神的形象也逐渐变得多样、复杂起来,时间上大致以中唐为界,表现出前后两个阶段的明显变化。
中唐以前,小说中对华山神的刻画依然较少,并且依循传统,主要展现山神形象威严、正义的一面。如唐初王度所作《古镜记》中,就写狸妖变幻人形,逃窜人间作恶,伏法时自称:“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大行变惑,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8]2此处的“老狸”可视作狐妖一类的精怪,在中国古代精怪小说中,狐妖、老狸因擅长魅惑、变换之术,往往为祸人间,凡人深受其害。于是在《古镜记》中,这位“老狸”果然因此受到华山府君(即华山神)的追捕,四处逃逸,最终流落至河渭地区。可以看出,此处出现的华山神依旧是崇高、正义的,在整个故事的发展中,他显然是站在人类的一方,从护佑人类的角度着想,才四处搜捕逃亡人间的精怪。
出乎意料的是,到了中唐以后,小说描写中不仅高频出现华山神这一形象,更有甚者,华山神的神格干脆由善转恶,成为一位远近闻名的“恶神”。在这些山神作恶故事中,山神往往以强抢人妻、强召人魂的形象而出现,且多表现出放荡、轻浮的一面。考察具体细节,其中明确提及作恶者为华山神的有三则,见表1。

表1 唐小说中几篇华山神作恶故事概况
表中所举虽仅有三则,但在当时流传的范围应是十分之广,以致于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一般而言,出场的人物总是四个:作恶的山神,被召的人间女子,人间女子的丈夫,救人的道士。且这些人物都各自有明显的特征,如被抢的女子或是有才,或是有貌,或是才貌双全者,某天突然猝死,灵魂离体而去;而实施抢人行为的通常都是山神,更准确地说是华山神,横行一方、肆无忌惮;至于女子的丈夫,地位都比较低下,只是人间的低级官吏;至于故事的最后,总会安排一个救助者角色的道士出场,道士法力高超强,通过“书符”的方式救人,且每次都能成功救回。
此处重点说说几则故事中展现出的华山神形象:爱色享乐、放荡纵情、无视法度。首先,从华山神的表现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喜爱美色、沉迷享乐的人,如《广异记·河东县尉妻》中,王氏就是一个“有美色,著称三辅”的绝世美人,她被召至华山时,华山府君正“列供帐于山椒,与其徒数人欢饮”;至如《逸史·李主簿妻》中,华山神则是在女主人公拜神时见色起意,直呼“好夫人!”,下令左右扶归院。种种情形表明,华山神作恶的原因,正在于其对美色和享乐的追求。其次,小说中的华山神又表现出放荡纵情、轻浮狂肆的一面。《河东县尉妻》中称其“宴乐毕,方申缱绻”;《仇嘉福》中称“王见喜,方欲结欢”。两则故事中的华山神都表现出一副急不可耐的昏聩模样,轻狂、浮薄,神明的威严一扫尽。最后,唐代小说中的华山神还无视法度,不仅轻易拘役凡人的魂魄,更是在明知有错的情况下依旧不知悔改,试图逃开惩罚。几篇故事中都插入了道士“书符救人”的情节,但无一例外,华山神都要对此进行一番抵抗,以《河东县尉妻》为例,华山神在面对第一次责问时,尚“犹从容,请俟毕会”,一点都不慌忙;直到第二次,受到太一神的怒骂后,才“大惶惧,便令送至家”。由此看来,在这一系列的山神故事中,华山神的形象是彻底地由善转恶了,成为一位劣迹斑斑的恶神。
更有甚者,这类故事发展到后期,又影响及其他山神,使其他山神也随之产生作恶行为,只是统计下来,数量毕竟不如华山神的多。如戴孚《广异记》中就有一则《赵州参军妻》[8]450,叙事模式和上述几则一脉相承,只是将作恶的山神由“华山神”转嫁到了“泰山神”身上。然而从故事内容及细节来看,此则故事中不仅增加了人物心理描写,在道士与山神的斗法中更是进行了戏剧化处理,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情节更加生动。以此而言,此故事很可能是在上述“华山神”故事基础上所做的加工和完善,与其说是泰山神作恶,不如说是“华山神作恶“的衍生,由“泰山神”代“华山神”受过了而已。
以上只是就山神本人作恶而言,此外,受华山神影响,甚至连唐代小说中的华岳系神灵也变得恶劣起来。如《广异记·三卫》[8]453中载北海仙女嫁华岳神第三子为妇,夫婿极恶,不堪受辱,于是向家中报信请求援助一事;而同书《李湜》[8]458中又载,开元中,赵郡人李湜过华岳庙,为岳神家中的三位女眷所迷,致使身带邪气,差点危及性命的故事。在这里,不仅是华山神本人,就连他的亲属也面目可憎、行为恶劣,失去了以往神明的威严、庄重。只是限于本文篇幅,不再作详细讨论。
综上,在唐代小说中,华山神的形象发生过一次“变异”,原本的宗教正神应有的威严在此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世俗性的人格特征,此时的山神形象及其行为举止明显偏向恶的一方,表现为一位劣迹斑斑的恶神。这一现象可谓是唐代小说中十分难得的一例,理应受到关注和重视。
3 唐代山神形象“变异”考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唐代华山神形象的恶化?山神作恶故事又为何数量如此之多,流传如此之广?可以肯定的是,在小说发展史上,任何故事类型的产生都不是无根之萍,总能在相应的社会背景及文化思潮中找到依据。关于唐代华山神形象的变异,经考证,或许有以下原因。
1)“影射玄宗”说。考察中国古代典籍与文化,历来有研究者注意到华山和玄宗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本命”说。本命之说源于《旧唐书·礼仪志》中记载:“玄宗乙酉岁生,以华岳当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华岳神为金天王。”[9]904究其根本,是因为“十二支中,酉当西方,而在五岳中华山为西岳。”[10]正因为玄宗与华山之间存在这样隐晦的联系,而其在位期间又发生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导致唐帝国由盛转衰,难免会引来不少明嘲暗讽。其中,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又向来被文人视为亡国的原因之一,在文学作品中多有暗示,而杨贵妃入宫之前的身份也较为敏感,常被人拿来大做文章。这种微妙的关系流传到民间,或许就被当时人吸收改造,投放到华山神故事中来,塑造了华山神强抢民女、霸占人妻的邪恶形象。故而,学者贾海建提出此类小说乃“影射玄宗”的说法,认为:“收录记载这些华山神及其子女劣迹故事的小说集如《广异记》《宣室志》《异闻集》等都产生在玄宗朝之后……因此,唐代出现的大量华山神及其亲属的劣迹故事不无对唐玄宗的影射,至少是含有对当时统治阶层的批判。”[11]
2)对社会风气的反映。避开玄宗的影响不谈,如果把目光放宽,顺便考察一下唐代的野史笔记,我们会发现,其中记载了大量类似华山神欺男霸女的夺妻、夺妾事件。如同样是在中晚唐成书的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中,就记载了当时王公贵族夺人之妻的故事:“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12]1239
此外,还有上级官吏掠夺下级僚属宠妓的故事,如:“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晋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饯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12]1240
梳理这些被掠夺女子的特征,都是有色有貌,有才有艺的绝色美人,而她们被掠夺去的目的,也多是为了陪伴男性欢会饮酒、歌舞取乐。结合上述几则山神故事,美人和才艺、宴会联系在一起,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唐代的饮妓文化。
赵睿才在《唐诗与民俗关系研究》中认为,自天宝末年起,宴乐之风“便逐步席卷了社会各阶层。以酒筵为媒介,歌舞伎艺蓬勃发展,成为中晚唐文化的一大特点。”[13]126甚至在正史当中,也有对这种风气的记载,如《旧唐书·穆宗本纪》言:“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而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9]485对比唐代都市中饮酒风俗的盛行与华山神作恶故事产生的时间,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许可认为,唐小说中此类华山神作恶故事的产生与山神形象的恶化正是对中晚唐时期社会风俗变化的反映,同时也含有对当时社会黑暗现象及官场腐败的批判。
3)受传统民间造神思维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恶神的存在古来有之,不只是在唐朝,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许多民间神:麻姑、丁姑以及厕神等,都有过作恶甚至致人于死的行为。如干宝《搜神记》中所载“丁姑”求渡的故事:“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即当相渡也。’丁妪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6]61
因为被两个凡人调戏冒犯,丁姑发怒,干脆就通过夺去两人的性命以示惩戒,使用的手段虽偏激,但也见出神灵对普通人所行使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在这里,神灵杀人害人的行为似乎只是随心所欲,并不受到任何约束。由此看来,神灵发威发怒,导致普通人受到损害的故事在民间传说中并不罕见。也因此,唐代华山神形象的恶化就不再出人意料,而可看作是受民间造神思维的多样性及不确定性的影响。毕竟,神本来就是人造的产物,人既然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抬高神的地位,自然也可以把种种恶行加诸他们身上,降低其神格。这点可通过古代民间祭祀的目的体现出来。历来的民间祭祀,无外乎两个目的:一为祈福,二为禳灾。所谓禳灾,就是通过种种祭祀手段讨好神灵,不求神灵护佑,至少也祈祷神灵不要加害自己,最好能远离人类的正常生活。
4 结语
从历代山神故事的研究来看,唐小说中的华山神形象作为一个特例,表现出有别于其他山神的独特文化内涵。在这里,一系列的山神故事并非只是对神明作恶的简单书写,其发生与流传已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当时的客观环境及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在考察这类故事时,就不得不深入到历史的厚度及当时的文化内层,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