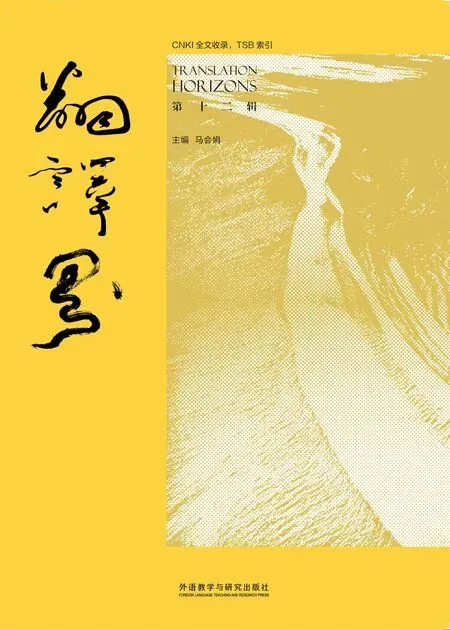清初旗学中的翻译教育及其变化过程
——清初旗学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研究*
2021-12-06宋以丰
宋以丰
湖南理工学院
1 引言
清军入关统治中原后,如何既能保持满族的民族特色,又能与汉人交流,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乃是清政府统治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设置旗学,教授满语、骑射,并推动翻译教育,乃是清政府因应时势之举。顺治初年,清廷循汉族国子监之例创设旗学,开清代官学教育之先河,专供旗人学习语言、骑射与翻译。顺治朝以后,旗学教育屡经调整与改革,不仅在特定区域设学,而且使旗学教育逐渐平民化、普遍化,这样既稳定了生源,又规范了教习的拣选和稽核。清政府还适时调整旗学机构的设置,以及教学内容与考核方式,确保了旗人的学习品质。由于清政府办理旗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翻译人才和具备多语种能力的治国之才,故旗学中的教学和学习用书多为汉籍译本,其中多数为满文译本,另有部分为蒙文译本或者满汉、满蒙合璧本。虽然乾隆朝尤其是乾隆中期以后,旗学教育多有弊病,比如,旗学制度流于形式,章程管理日渐松弛,加上旗人子弟仕宦心态突出,致使学习不勤不精,但在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要求与支持下,以及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旗学制度仍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治理之才和翻译专才。
2 旗学的翻译使命
满族统治阶级建立的清朝,为维护满族的民族特质以及少数族裔的统治优势,一向提倡旗、民分治,要求旗人保持民族特质、习满语、专骑射,以维护国家根本。然而,为确保国家治理行之有效和国家长治久安,旗人亦必须兼通满、汉,与汉人沟通交往,以便学习其典章制度与执政经验。顺治朝以后,旗学教育逐渐兴起,除国子监八旗官学、顺天和奉天府学外,还有咸安宫和景山官学、宗人府宗学和觉罗学,以及各地八旗官学、义学和清文学等。这些官学成为清代兴贤育才、教养备至的重要场所。对于旗人而言,只有接受旗学教育、熟读经史、掌握翻译、练习骑射,才能符合清政府的人才标准和要求,为进身入仕觅得正途。清统治者重视满、汉语的学习以及翻译能力的培养,乃是国家行政和治理的需要。众所周知,国初之际,官员的日常行政广泛使用满文,政务的推动离不开翻译。《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朝)》中说,清初以来,皇帝颁发满、汉文谕旨时,往往先由内阁进行翻译,或将清字(即满语)译汉,或将汉文翻清,如此才能上传下达,确保政令畅通。各部院衙门撰写本章时,虽然兼用清、汉双语,但直省本章中不使用清字者较为常见,这种情况下往往由通政司将本章咨送内阁,再由后者送交汉本房进行翻译,事毕之后由满本房誊写(允祹等,1983)。各省驻防将军、副都统等遇奏事之时也只使用满语,因而旗籍官员中办理文书业务者也必须娴熟翻译(曹振镛,1986)。至清末之际,虽然旗学中清语荒废的情形日益严重,学生的翻译能力每况愈下,但国家对于翻译人才的需求并没有完全消失。
然而,有清一代,旗学教育到底兴于何时,旗学中培养的翻译人才究竟几何等等问题仍存争议。比如,以宗学的设置时间为例,不同文献的记载便不相同。如《八旗通志·初集》和《钦定八旗通志》都载有顺、康年间宗学变化之事,但《大清会典(雍正朝)》却未见此段史实,反而将宗学之设归于雍正二年(鄂尔泰等,1986;铁保等,1983;允禄等,1995)。虽然如此,有两点却可肯定。其一,不论雍正二年办理的宗室之学是“复开”还是“创设”,其中原因确与康熙朝晚期的皇子夺嫡事件有关。《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中对此已有说法。
朕惟睦族敦宗,务先教化。尝见宗室中,习气未善,各怀私心,互相倾轧,竝无扶持爱护之意,惟知宠厚妻党姻娅,其于本支骨肉,视若仇敌,殊为悖谬。或因祖父昔日微嫌,追念旧恶,必图报复,……诚恐朕之宗室,日流日下,不知前鉴,深用为忧,是以亟筹保全之道。若非立学设教,鼓舞振兴,循循善诱,安能使之改过迁善,望其有成。(鄂尔泰等,1985a:310)
上谕中,雍正帝明确阐述了设立宗学的前因后果,将其当作鼓舞人心、劝善惩恶的手段。其二,清代的旗学教育名目繁多,机构林立,其中不少仅教习满语、骑射等维护民族特质的科目,但教习满、汉翻译或者满、蒙翻译者也有不少,为国家培养了不少语言人才。
清廷创设八旗官学,令八旗弟子学习语言(满文、蒙文和汉文)、翻译和骑射等,此举既不失满族特色,又增进民族交流,对呈现满族特色的统治特征、扩大政权的参与基础等皆有意义。众所周知,顺治时期,虽然清军已经入关,清王朝渐趋形成,但有碍统治的许多问题仍未解决,如溃散以后的李自成余党、盘踞各地的地方势力、南明政权的继续存在以及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种种难题使得清政府统治者不得不与汉人合作,与汉人共同进行国家治理与制度重构。为此,清政府便需要八旗人等具备多语种能力,一则为沟通政事,二则为学习汉制,这一点与官学的功能高度契合。加之康熙中期以前,汉族知识分子中对于异族政权无法释怀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具有明确的使命感,虽然表面上对清政府采取合作态度,心中却希望在统治者的支持下维护、发扬汉族文化。而清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虽然不得已在满、汉之间寻找平衡点,考量汉族士子和汉民利益,以免因失去民心危及政权稳定,但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特殊地位,又不得不牺牲汉人利益,而旗、民分治,创办官学,倡导满语、骑射,正可以保持满族人的民族特质,抵御汉文化的冲击。总之,旗学之兴,乃是睦族敦宗、加恩八旗之举,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流,为清廷广育人才。
3 顺治以前的翻译人才培养与使用
清太祖、太宗年间,朝中通晓满、蒙、汉语者不乏其人,如达海、额尔德尼和希福。这些人多来自归附的海西女真,即扈伦四部(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民族互动频密,这些人养成了多语种能力,多数在朝廷充任翻译、文书、外交之职。比如,来自扈伦哈达部的硕色和希福兄弟,因兼通满、蒙、汉文字,一个奉命在文馆行走,另一个奉命出使蒙古诸国。硕色的长子索尼也因早承家学,兼通满、蒙、汉文字,在文馆办事。
随着国家政权的逐步扩大、内政外交的日益繁复,翻译与文书工作大幅增加,仅仅依靠归附者群体中的语言人才已然不够,自行培养势在必行。于是,天聪年间,清廷规定八旗子弟循例读书,并令汉人中的儒生俊秀入文馆肄业。即便如此,因文馆官员政事冗繁,管理不善,八旗笔帖式及文馆臣僚中,通晓翻译者仍不敷任用。比如,天聪六年九月,书房(即文馆)秀才王文奎奏称:“至若翻译之笔帖式,在书房之通文理者,止恩国太一人”(罗振玉,1989:329-330)。礼部汉官王舜也以翻译人才不济为由,奏请“尽搜国中识汉字者”,“考其识见才调”,并“拣选实学秀才,朝夕讲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今日之小榜什(笔帖式,笔者注)”成为“后日之大榜什(巴克什,笔者注)矣”(同上:338)。为满足国家政务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清太宗于天聪八年晓谕礼部考取举人十六名,从事满书、汉书、蒙古书的学习。崇德三年、六年,清廷又两次考取举人十七人、生员一百零五人。此两次考试虽系满族、蒙古、汉军“同为一榜”,但内容上却是“互考汉文、满文”,其取士额数虽少,却是清廷招募翻译、文书人员的重要来源。以《辽史》《金史》《元史》的翻译为例,三书的满文译本于顺治元年进呈,因此而受赏者达十六人。《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中,对此事的记载如下。
赐大学士希福鞍马一匹、银四十两;学士胡球、查布海、王文奎、员外郎刘弘遇、他赤哈笔帖式能图、叶成格(又名宜成格,笔者注)马各一匹、银三十两;铿特、卜尔凯、卦尔察银各四十两;卞为凤、科尔科代、尼满银各三十两;硕尔格、刘朝卿、李允昌银各二十两。(鄂尔泰等,1985b:49)
上述十六人中,出身举人、生员者七人。其中,查布海为天聪八年举人,胡球和王文奎为崇德三年举人,卞为凤为崇德六年举人,铿特为崇德三年生员(列二等),叶成格和科尔科代则为崇德六年生员,分列三等和一等。由于汉书翻译向来任重道远,清廷格外重视,因而一部书籍译成之后,受赏者往往众多。比如,《洪武宝训》于顺治三年译成之后,受赏者更是多达一百零九人,受赏对象从大学士、学士、侍读,到笔帖式、他赤哈哈番、中书舍人,再到编修、检讨和誊录官不等,可见翻译职责之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9)。
清军入关后,清廷对翻译人员或者兼通满、汉文的官吏的需求显著增加,旗人教化刻不容缓。为此,清政府既允许宗室、大臣子弟在家读书,也鼓励其入国子监八旗官学肄业。然而,旗学教育虽系正途,但国家方举,用人之事如同在弦之箭,通过旗学培养翻译人才,缓不济急。在此情形下,清廷又允许八旗士子以荫生、监生等资格参加各部院衙门组织的职缺考试,如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中书、库使等。顺治朝以后,清廷更加重视旗人教育。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布圣谕,令京城满族八旗各觅空房,立为书院,翌年又令四品以上京畿官员,以及在外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国子监读书,并于九年设立宗学,教养宗室子弟。旗人读书风气日盛,知识储备渐趋完善,可充任用者随之增多,因而考试选才不可避免。顺治八年,经礼部议准,清廷规定嗣后凡遇应考之年,均由内院会同礼部办理,分童试、乡试、会试,定生员额数一百八十人(满族一百二十、蒙古六十),举人额数一百二十人(满族五十、汉军五十、蒙古二十),进士额数六十人(满族二十五、汉军二十五、蒙古十),并另由顺天府学政考取汉军生员一百二十人。在考试内容上,无论乡试、会试,满族、蒙古中的识汉字者均以翻译考试为主,即翻译汉字文一篇(鄂尔泰等,1985b)。虽然本次办理的翻译考试并非后来的翻译科考,但却是清初以来首次通过考试翻译选拔旗人官员,为旗人提供了另一条进身入仕之途。鉴于政权的性质和政治的现实,对旗人而言,无论是八旗满族,还是八旗蒙古,要想留任京畿官职,往往必须兼通满、汉或者满、蒙,以充翻译、缮写文书之用,这一点正是乡、会二试中考试翻译的缘由所在。
顺治九年,礼部议准办理壬辰科会试,通过翻译考试的满族、蒙古进士共计五十人,这些人比照汉人科举之例,被分别授予修撰、编修等职。同年四月,吏科给事中高辛允具折,建议朝廷慎选庶吉士(翻译职官之一),以重名器。此事经内院议覆并奏准,决定从进士及第者中拔取汉人四十名、满族与蒙古各二名以及汉军四名,一体入“馆”(内弘文院庶常馆)读书。其中,汉进士中的部分学生被要求学习清文(即满文)、清书(即满书),满族、蒙古进士则需要学习汉书、汉语,其目的是为了应对“奏对讲读”,以及在兼晓满、蒙、汉文字之后提升翻译能力。在顺治朝两科翻译考试(八年、十一年乡试以及九年、十二年会试)中,虽然出身旗学的举人和进士人数已无从详考,但中式者中确有供职于各部院衙门,职掌翻译和处理满、汉文书者,如乙未科满族进士伊桑阿,初由礼部六品笔帖式授主事,后于康熙年间累迁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与清太祖、清太宗时期一样,顺治年间统治者亟需了解汉族文化,汲取治国理政经验,同时安抚汉族民众,伊桑阿等经考试翻译获得进身者往往被分派至内三院或其后改制的内阁与翰林院,或经皇帝钦定,或由部院议决,担任翻译汉籍的工作。比如,顺治十一年十月,大学士宁完我进呈洪武《大诰》,世祖遂命内院诸臣翻译进览。又如,顺治十五年五月,“九卿”等会同议决国子监书籍一事,要求将“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各印一部,收藏于国子监内,并要求将其“俱翻译清书,以昭同文之盛”(同上:915),虽然此二者的翻译在动因上明显不同,但由此可知清廷对于翻译之重视。
4 康熙年间的译才取用与汉书翻译
有清一代,由于“翻译之事,大有关系”,统治者都很重视(马齐等,1985:275)。比如,康熙帝认为,旗人供职于各部院衙门,如兼通满、汉文义,精通翻译,则料理部院事务时,便无不能。而挑选内阁、翰林院官员,也需“博通汉文,善于翻译之人,方为有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9:1297,1329)。翻译公文尚且如此,翻译汉籍更毋庸说。又如,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圣祖对《清太宗实录》纂修过程中朝鲜表文的翻译颇为不满,认为其满、汉文义皆不相符,因而差员苦心寻释,两年后终于“将文义完美”(马齐等,1985:275)。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圣祖再次提及此事,“昔太宗皇帝时,朝鲜国进表,原无不恭之语,翻译官意欲起衅,故将表文翻错,以致问罪往征。后纂修《实录》,见彼表内汉文,与所翻满文,大不相同,始知当时翻译有弊”(同上:470)。
康熙时期的汉书翻译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是整理、刊行前朝译本。其二则是新译其他汉籍。康熙帝对旗人教育以及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视更是超越前人。康熙年间,清廷设立的旗学颇多,不仅有康熙二十五年设立的景山官学,也有分设于不同时期的各地官学与义学。康熙三十年,圣祖御设八旗义学,其后又将义学的设学地域不断扩大,并出台章程制度,规范义学的生员、教习、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等。翻译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是八旗义学的重要内容,义学中常设翻译教习,主要由笔帖式和翻译生员等担任。乾隆时期更对义学翻译教习的考选方式予以明确规定,要求考取八旗义学翻译教习,“由该旗将举、贡生员咨送”(昆冈等,1963:23),并要求“择其年逾三旬,行无匪僻者”(柳海松,2017:24)。学生学习的内容,既有语言课程,也有文化课程,汉文典籍的满文、蒙文译本也是必学内容,如《四书解义》《性理精义》等。此外,学生有时也需要翻译经义。康熙三十四年,应黑龙江将军萨布索奏请,圣祖同意在墨尔根设立旗学,从现任笔帖式中考选翻译明通、品行端方者,充当教习。由于清廷对于东北旗学向来格外重视,要求其确保民族特色,因而清语、骑射尤为重要。但即便如此,黑龙江八旗义学仍以翻译笔帖式教习汉书、汉字,由此可见旗学中翻译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普遍性。
虽然康熙中期以前,旗学学生的清语能力普遍较好,但欲使其精通翻译以堪翻译汉籍资用,不能只是加强汉语能力,而令满语能力废弛。康熙中期以来,随着民族交流显著增多,旗人子弟习汉书的风气日盛,不仅妨碍了其习清书的意愿,而且也因其清语能力的消退影响了翻译。事实上,早在康熙十二年四月,圣祖便常常告诫侍臣,表达对于旗人学习清语的忧虑。圣祖所担心的并非此时的满族人不知清语,而是嗣后因为满族人渐习汉语,可能会将满语遗忘。圣祖认为,满、汉文义不乏相似,即便照字翻译,可通用者仍然很多,因而不致给今天的译者造成困难,但随着世易时移,后世子弟未必知晓,“差失大意”“言语欠当”或许在所难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9:93)。康熙的担心到了晚期以后得到应验,此时的八旗子弟清语能力普遍下降。不仅后生子弟“竟忘满语”,“老成旧耆”者也有语音不正、字句失落的情况,导致翻译中误译、错译丛生,与“先年老人所翻之语不独恰当,真有奇处”(张玉书、允禄等,198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9:2271)的局面,已不可比拟。
5 雍、乾二朝关于翻译人才培养的调整与改革
雍正朝初期,礼部遵圣谕拟调整旗学的办学方针,强化学生的满、汉语等多语种能力,可谓是因应时势之举。《大清会典(雍正朝)》中说,雍正二年,清廷对国子监八旗官学的管理进行改革,要求依学生的学习科目,调整其学习重点。具体来说便是,习满文者,以书写本折字画为主;习文章者,以讲论圣贤经传为主;习翻译者,则以熟翻《古文渊鉴》《大学衍义》等书为主。教育方式的分流发展,既可以令培养目标更趋明确,也可以强化培养的专业性与针对性。然而,鉴于翻译科目自身的特殊性,学习者不宜为“幼稚之人”,而必须是年龄稍长且资性聪敏者,如此才能保证学习效果。于是,经国子监祭酒孙嘉淦条奏,并经康亲王崇安、果郡王允礼议覆,清廷决定嗣后选取官学生需以年龄区隔,令年幼者学满文,年龄稍长者学汉文。随后,清廷又规定官学生中如有愿习清书者,可由助教视其年岁稍长,且文义粗通,准其改学翻译,但若要拨入翻译馆,则必须“读过汉书”(铁保等,1983:16)。乾隆年间,清廷进一步调整国子监八旗官学的培养方式,明确将其分为清、汉两途。《钦定八旗通志》中说,八旗子弟选入国子监八旗官学后,前三年并不分途,而是一体专习经书,朝夕讲课。三年后,经监臣稽考,“材质聪颖、有志力学者”归入汉文班,分隶教习,而“年齿已长,愿学翻译者”(同上:10)则归入满文班,分隶助教,以专习翻译。
国子监八旗官学的清、汉分途教学固然有其影响,但就清代旗学整体的翻译人才培养而言,亦谈不上冲击。然而,乾隆帝接受孙嘉淦的奏议,同意改变官学之旧例,即官学中研习翻译者往往只是应考笔帖式,允许八旗官学生之归入汉文班者,不必专习“四书”,也可讲求经、史等有用之学,并每三年一次对其进行考试,“取其明通者,授为监生,由官学而升之太学”(同上:10-11)。这一做法虽然可以拔擢旗学汉文班中的秀异者,使其获得入国子监深造的机会,却与旗学设立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相悖。《大清会典(雍正朝)》中说,八旗官学之设,“原欲清、汉兼优,精通翻译,备部院衙门补用,可任职事”(叶高树,2012:141-142),而孙嘉淦所奏不仅会造成旗学教育资源的浪费,而且会造成国家教育的制度扞格,容易诱使官学学生竞相钻研汉文,从而背离旗人根本。
与放宽八旗官学生学习汉书不同,乾隆时期对于八旗清文学学习翻译之事,则提高了要求。清文学专以汉军为对象,主要教授清书、骑射和伦理,它的开设是衡量旗学教育普及程度的重要参数。雍正十二年,为了对清文学教习从严管理与考核,以形成教学压力,督促汉军子弟更好地学习清文和翻译,经部议准,出台了满教习考核之规定。满教习的考核以三年为限,有头等、二等、三等之分,考核标准主要与教习子弟的考课有关。乾隆三年,清廷对现行标准进行修订,出台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以“头等”为例,在雍正十二年的考核标准中,但凡子弟能考中翻译外郎、笔帖式者,其清书教习便能位列头等,其奖励方式与内容交部议叙。至乾隆时期,头等的考核标准在先有的基础上增加了“翻译生员”一项,但奖惩规定不变,仍为“交部议叙”。雍正年间关于“二等”清书教习的考核标准明显低于“头等”,其具体规定是“子弟虽未有考试之人,有能写清字楷书,并粗通翻译者”,其奖励则是“再留学三年”。但同样的是,这一标准经乾隆三年的修订之后,变成了“虽无考中之人,尚有能写清字楷书,并粗通翻译,及通晓清话者”(同上:143)。二者对比,增加了“通晓清话”的内容,明显较之雍正朝更严。如果说雍、乾两朝关于“头等”“二等”的考核标准只是些微调整的话,那么关于“三等”的考核标准则存在明显不同。其中,雍正朝的说法是“子弟止能写清字,并粗通清语者”,到了乾隆年间则成了“子弟并无粗晓翻译、清话,又不能缮写清字楷书”(同上:143),后者再次凸显了对于翻译的重视。关于“三等”清书教习的奖惩规定也有明显不同,其中雍正年间的规定只是轻描淡写的“拨回原处”,而乾隆时期则是“系现任笔帖式、闲散官充当者,即时交部查议,系废员充当者,即时驳回,永不叙用”,后者的惩处力度显然更大(同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关于清书教习的考核标准及奖惩规定等,在雍、乾两朝的适用性并不一致。其中,雍正朝时期的办法是清文学教习一体适用,乾隆朝时期则特别针对汉军清文教习,其中原因与汉军清语能力普遍低下有关。乾隆帝对待八旗官学和清文学的态度明显不同,他鼓励前者学习汉文,却要求后者保持满族的民族特质,这种政策的两面性说明统治者在旗学的问题上尚未真正做到通盘考虑,因而政策缺乏一致性。
但作为“夙善国语,于翻译深所讲习”的“十全”皇帝,乾隆帝既能洞悉旗学教育的不足,又能从落实清语与翻译教学的立场出发,对旗学教育的方针进行修改与完善。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高宗御阅宗学试卷,发现汉文教习宗室子弟虽然已历数年,但“翻译卷亦属平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8a:827)。乾隆十七年,上谕敕设世职官学,原因即是八旗世袭官荒怠清语和骑射。为了落实旗学设立之初衷,即以“清、汉兼优,精通翻译”为要,清廷调整了部分旗学的教学重点,如乾隆二十一年裁减宗学汉教习九人,改设为翻译教习,并从翻译生员中选取适任者,担任圆明园学教习(铁保等,1983;托津等,1994)。乾隆三十一年,朝廷在议准八旗官学的修业年限时,一并对官学生的考课做了要求,规定习翻译和清语者如不能在学习期满时,考取中书、库使、笔帖式等,都必须咨回本旗,并另挑差使(铁保等,1983)。至于学习的具体年限,则规定十八岁以下者以十年为期,这一规定为嗣后沿用。
乾隆朝关于旗学教育的另一项改革便是“进学”。所谓“进学”是指旗学中的汉文班官学生经过一定的稽核或者考试之后,成绩优异者可升入国子监的办法。毫无疑问,“进学”办法的出台与清廷一贯强调民族特质的政策颇有龃龉,其所以成行与统治者放宽八旗大臣子弟参加科试不无关系。比如,乾隆三十年,上谕内阁,指出八旗三品以上大臣子弟如清语娴熟,练习弓马,则遇考试之期时,可由其父兄自行奏明,一体入闱考试。但上谕同时规定,如果他们不潜心力学,于清语、骑射又不专攻娴习,自然不如兼习文艺,兼收并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8a)。换言之,在旗人学习清语、骑射的意愿低下时,清廷采取“进学”的办法,希望旗人通过兼习文艺而“犹可为造就之资”(同上:568)。朝中尚且如此,驻防自不待言。比如,乾隆四十至四十一年间,西安将军傅良条奏,指出满营官员内,熟练稿案且兼通满、汉文义者,已“甚难其人”(同上:140)。乾隆年间,清军入关日久,满汉交流频密,旗人使用汉语阅读汉书的机会大增,使用清语的场合自然减少,这一点自会影响其学习清语和翻译的意愿。
6 嘉、道以后翻译人才培养的颓废
嘉庆以后,有关旗学教育的许多做法都是沿袭前朝规定。比如,在有关官学生肄业的具体年限上,嘉庆便接续了乾隆三十一年的要求,规定年龄在十八岁以下者,仍须以十年为限,并将这一规定应用至咸安宫官学和景山官学。《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中对此事的记载如下。
咸安宫官学成材者众,体制较优,……嗣后凡由官学生及闲散人等挑选者,定以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内入学,至十年限满,不能考中生员, 即行出学。如由举、贡、监生挑选者,亦以十年为率,核计已经正科三届乡、会试不能取中者,一并出学。其景山官学,……即照八旗官学之例,将十岁以上十八岁以下者入学肄业,至十年限满无成者,拨回本旗,另行挑差。(昆冈等,1963:273)
道光年间,官学生的学习仍以十年为限,一方面是为了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更重要的是为了体现朝廷对旗学教育质量的重视。比如,道光三年,礼部议准:
嗣后八旗官学生留学,亦以十年为断。其有考取文生员、翻译生员者,以考中之日为始,留学十年。如再考中副榜、拔贡、优贡等项,复以中式之日为始,扣满十年,俾得底于有成。如中式举人,则以有铨选之路,不得再行留学。(同上:288-289)
由上可知,所谓十年的年限适用于所有八旗官学生,不论其考取文生员还是翻译生员,皆是如此。即便是考取副榜、拔贡和优贡等,也是从其中式之日起,计满十年。这么做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学有所成。
与此同时,由于乾隆后期推行“讲学”制度,八旗子弟学习清语和翻译的意愿明显减退,对嘉、道年间的旗学教育也产生了影响。如嘉庆十三年闰五月,仁宗曾颇有感慨地对大臣说,开国之初,风气淳朴,朝中满洲大臣教诫八旗,因而“如清语、骑射,尚能勤加练习,远胜今日”(曹振镛等,1986:601)。又说:“从前满洲,尽皆通晓清文,是以尚能将小说、古词翻译成编”,而“今满洲非惟不能翻译,甚至清话生疏,不识清字。其粗晓汉文者,又以经、史正文,词义深奥,难于诵习,专取各种无稽小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0:370)。由是观之,前文中傅良所奏并非虚言。虽然乾、嘉年间旗人的清语能力普遍衰退,翻译能力普遍欠佳,但清廷中仍不乏精通翻译之才。比如,笔帖式出身并累迁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舒赫德,便向来以“善译”出名。《钦定翻译五经四书》也“皆八旗精翻译者所成”(铁保等,1983:4)。在政府组织大规模翻译工程时,包含翻译官、誊录、纂修在内的各种参与人员,也都是从国子监八旗官学以及八旗各学学生中考选。各部院衙门中兼事翻译、文书的笔帖式、中书、库使等也多由旗人构成。凡此种种,只能说明满族人的清语学习出现了部分问题,而非全部。但问题既已造成,必须加以解决。因而嘉庆六年三月,原礼部主事尹壮图奏请将十五、六岁前的满族子弟专读经书,待心性成熟、精力完固之后,再学习骑射与翻译。尹壮图的本意是为了提振满族人学习骑射与翻译的效率,但由于他本末倒置,将翻译学习建立在汉族经史而不是满文学习之上,无异于戕害清初以来历代君主倡导的满族主体性,自然无法获得嘉庆帝的认可。尹壮图所奏是否合理暂且不论,但事实是道光以后,旗人清语、翻译荒废的情形日益严重。比如,道光十五年六月,宣宗敕令满族五品以上至侍郎以下京堂,分日考试清文。令道光帝所料未及的是,本次考试中翻译通顺以及尚能翻译但偶有讹错者,也只不过在十分之三、四之间,其中半数甚至不能落笔。为此,道光帝特降旨训诫,强调清语乃满族根本,无论出身如何,满族人皆应熟习。道光帝尤其针对宗室、觉罗子弟做出训诫,令其务必勤修本业,勉绍家声,断不可因不晓清语、不识清字,而辜负了朝廷“务本成全”(穆彰阿等,1986:109)的用意。至清末年间,旗人清语、翻译能力的衰退一如既往,甚至出现了国子监课士官不知清语的怪异现象。比如,咸丰四年,苏勒布因新授国子监满洲司业具折谢恩,但皇帝在御览此折时,发现其竟不能用清语缮写自己名字,更不用说讲解折内字句,于是饬令将其降为编修,以示惩戒。为了使八旗人等一体加强清语、翻译的训练,咸丰帝降旨:
八旗人员,骑射、清文是其本务,即使于清文义理不能精通,亦岂有不晓清语、不识清字,遂得自命为旗人之理?道光年间特奉谕旨,停止驻防文试,专考翻译,原期返朴还淳,俾我八旗子弟咸知本业。乃近日八旗人员,仍有专习汉文,于清语、清字全不讲求,沾染习气,徒务虚文,实堪痛恨。嗣后无论何项出身人员,均宜练习清文,通晓讲解,即由文乡、会试入仕之员及兵丁子弟,亦应一体练习,不准怠惰偷安,以务根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8b:89)虽然咸丰帝对于部院衙门僚属以及八旗官员荒废清文、不能翻译的情形忧心忡忡,或循循善诱,或严词斥责,但无论何种,终究未能阻止旗人清语和翻译能力的废弛。清末之际,虽然清廷仍规定各地官员遇有奏事折件时,采用满汉合璧的形式,由此说明满语仍占一定地位,且旗学培养语言人才的功能并未完全消失,但随着时势推移,民族融合日盛,旗人清语荒疏的情形已不可逆,翻译能力随之凋敝。
7 结语
清代旗学是统治阶级共享政治利益的特殊体制,既面向八旗设学,又面向皇族和宗室设学,虽然客观上振兴了文教,养育了人才,促进了民族融合,主观上却是统治者用以巩固统治的保全之道。为教育旗人,改善治理,政府从初级而进阶,由贵族而惠及弱势,依次推进旗学教育,设想不可谓不周,成效不可谓不甚。有清一代,促成旗学兴起、改革、发展与完善的因素颇多,其中既有皇帝个人的支持与投入,也有满汉族官员的鼓吹,另有清朝大儒的力倡,使得旗人读书渐成风尚。而旗学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依其名目主要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其一为普通旗学中的翻译教育。其二为翻译官学、翻译义学等专门机构。上述机构在办理翻译教育、培养翻译人才时,往往皆有详细具体的典章制度,其内容涉及教习的延聘、学生的录取、教材的选用、课业的形式、考课的评定以及奖惩的规定等,使翻译办学合乎规范。翻译教学在旗学教育中并非权宜之计,而是着眼长远的高瞻之举,其目的是培养德行纯正、谙悉汉书、兼通满汉双语的语言人才,以飨治国理政之需。事实上,旗学中培养的翻译人才也的确成为嗣后处理文书、办理翻译的重要来源与支柱。虽然旗学的初衷是为了教导旗人崇实黜华、专心向学、固守民族根本,但实际操作中亦不乏与民族特质龃龉者,比如,“进学”政策即属此类,最终导致旗人学习意愿低下,旗学教育废弛,并殃及旗人的翻译能力与翻译人才培养,以致翻译之事难观其成,译才培养几近废置,与“开国之初,风气淳朴,……从前满洲,……尚能将小说、古词翻译成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0:370)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