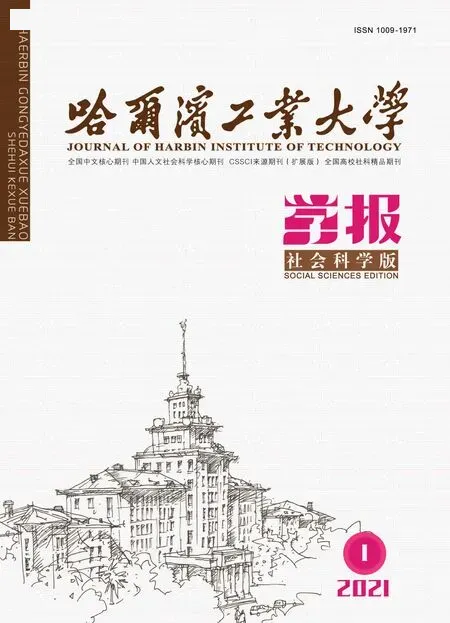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关系考辨
2021-12-06马莉娜
杭 勇 ,马莉娜
(1.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文学院,西安 710100;2.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710119)
关于陈与义和江西诗派的关系,从南宋到现在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宋代的严羽认为他是江西诗派,诗风又与江西诗派有一定的差异。宋末元初的方回也认为陈与义属于江西诗派,并将其列入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南宋的杨万里、刘克庄和明清的很多诗论家反对将陈与义划入江西诗派。当代大多学者延续了严羽、方回等人的观点,事实上陈与义并不属于江西诗派。弄清陈与义是否属于江西诗派,不仅关系到对陈与义诗歌风貌及其在宋诗史上地位的认识,亦有助于厘清两宋之交乃至宋代诗歌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问题的由来
江西诗派的提法始于两宋之交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后来不断地被扩大,不同的论家划分江西诗派的依据不尽相同。这是论家争论陈与义是否属于江西诗派的症结所在。
从现存的资料看,吕本中界定江西诗派的标准有两点:一是认为派中二十五位诗人“源流皆出豫章也”,是黄庭坚的“法嗣”;二是“同作并和”[1]327,强调派中诗人之间密切的创作交往。南宋开始,诗派的成员被不断增补,关于江西诗派立派的标准也逐渐变得混乱。江西诗派后期领军人物曾几就说:“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于元渤》)曾几第一个将江西诗派的诗学渊源追溯到了杜甫,提出了“祖宗”的说法,对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仔也认为“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1]332。刘克庄以学杜标准,将吕本中、曾几、杨万里纳入了江西诗派。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说江西诗派“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以味不以形也”[2]。他与吕本中等人一样认同诗派的门户传承,不同的是他强调诗派的艺术风格的趋同性。
最早将陈与义列入江西宗派的是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从诗史的角度,划出了“东坡体”“山谷体”和“陈简斋体”等六体,认为苏轼、黄庭坚、陈与义等六人分别代表了宋诗发展的六个阶段,他认为从诗歌风貌看陈与义“亦江西之派而小异”[3]。 方回以学杜和“嗣黄陈”[4]42为依据,把陈与义划入了江西诗派。并将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列为“古今诗人”之“一祖三宗”[4]1148。确定了陈与义在江西诗派中的地位。清代四库馆臣基本承袭了方回的说法,认为陈与义“诗虽源出豫章”,而又“能卓然自辟蹊径”自成一家。批评方回将陈与义划入江西诗派是“一家门户之论”[5],认为就江西诗派中而言,陈与义位置应该在陈师道之上。
综上所述,论家将陈与义划入江西诗派的依据不外乎三点:一是认为陈与义推重黄、陈,创作上属于黄、陈的法嗣;二是陈与义和江西诗派都主张学杜,有相同的诗学渊源;三是陈与义的诗风与江西诗派相同或相近。现在学界多数论家承袭了方回等人的看法,亦有学者认为陈与义诗风和江西诗派有很大不同,反对将陈与义划入江西诗派,但未能推翻对立派的另外两方面依据。因此,陈与义属于江西诗派的观点仍然是学界的主流看法。事实上,论家将陈与义划入江西诗派的三个依据都很难成立,下文将逐一考辨。
二、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创作关系考索
总观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诗人,黄庭坚与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领军人物,对诗派中多人有过重要指导,也是江西后学的师法对象。派中其余成员,大多比黄庭坚小20多岁,比陈师道小15岁左右,属于黄陈的晚辈。从诗学传承的角度看,他们都是苏门诗人的后学,与苏门诗人交往频繁[6]153-156。曾师从苏轼学诗者有王直方、何颙等6人;从黄庭坚者有三洪、徐俯等11人等;从陈师道的有吕本中等5人;也有一些人曾师从秦观、张耒;诗派中成员在诗歌创作上都受到黄陈的影响和栽培,黄庭坚常以导师的身份自居。他在《书倦殻轩诗后》中说:“潘邠老蚤得诗津于东坡,盖天下奇才也。予因邠老故识二何。二何尝从吾友陈无已学问,此其渊源深远矣。”将其和江西宗派诗人的交往说得尤为明了。黄庭坚还经常以书信对徐俯、韩驹等人的创作进行指导。这一点莫砺锋在《江西诗派研究》中有很好的论析,这里不再赘述。由此可以看出江西诗派的诗学渊源并不限于黄陈,朱熹就说:“舍丈人(吕本中)所著《童蒙训》则极论诗文必以苏黄为法。”[7]论家舍去其他不论,单言黄陈很值得思考。
江西诗派诗人相互之间的创作交流亦非常密切。上文所引黄庭坚《书倦殻轩诗后》就是黄庭坚为四洪、徐俯等人在元祐四、五年一次唱和诗集后的鼓励之言。黄陈去世之后,江西宗派诗人间交往更为密切,形成了几个集中的创作中心:一是以三洪、徐俯为主导的南昌;二是以二谢、王革为中心的临川;三是以二潘、二何为主导的黄冈。此外,京城王直方家也是他们重要的聚会唱和之地。几个地方的诗人频繁唱和,一次唱和常常往复十几次[6]153-156。
另外,江西诗派成员之间还有极强的学术渊源关系与血缘伦理关系。从学术渊源看,派中很多人是北宋末年主要理学传人程颐、吕希哲、陈瓘、晁说之和杨时等理学家的门下。清人全祖望说:“山谷之学出于孙莘老,心折于范正献公醇夫。”[8]陈师道曾对吕希哲“拜揖如亲弟子”[9]。宋代吕祖谦也说谢无逸、汪信民、饶德操等人对吕希哲“奉几杖侍左右,如子侄”[10]。派中诗人不仅是元祐诗学的传承者,也是元祐学术的传承者。再者,派中诗人群禅学上也有师友关系。据周裕锴在《文字禅与宋代是学》中考证,黄庭坚和徐俯、李彭等人在禅宗黄龙派中也是师侄关系。此外,派中成员有着共同的地域生活,这些诗人主要来自临川、淮南、南昌等地,很多人还有亲缘关系。黄庭坚与徐俯、三洪是甥舅关系,李彭的父亲是黄庭坚的舅父,曾几的舅父“清江三孔”也与苏门诗人的关系密切。他们中一些人的家族之间还有联姻关系,韦海英在《江西诗派诸家考论》中有详考辨,这里不再赘述。
江西诗派成员之间具有广泛的师友关系,但陈与义和派中诗人根本没有以上关系。就年龄看,他比黄庭坚小45岁,比陈师道小38岁,与黄陈则属于隔代人。陈与义与江西诗派中人大多相差20岁以上,是相邻的两代人。就创作实践看,黄陈的创作高峰在神宗元丰到哲宗元祐年间,陈与义出生时,黄庭坚远谪西南,陈师道寓居徐州、曹州等地,他们的后学活跃于江西,此时陈与义基本生活在京洛一带,根本没有交往的机会。徽宗政和三年陈与义登上诗坛时,陈师道已辞世14年,黄庭坚已离世8年,他们传人的创作巅峰(大观年间)也即将过去。当南渡前后陈与义创作进入高峰时,江西诗派的主要成员已大部分离世。因此,陈与义与派中人唱和也极少,据全宋诗考证,陈与义只有一首与吕本中的唱和诗,还是创作于南渡以后。
再者,在对待黄庭坚的态度上,陈与义与派中诗人也有巨大差异。派中诗人奉黄庭坚为圭臬,而陈与义对黄庭坚却颇有微词,批评苏轼诗过于放纵,黄庭坚又过分拘泥于规矩,“要必识苏黄之所不为,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矣”[11]2。陈与义表现出要在苏黄之外另辟蹊径的创作主张,可见陈与义并不像江西诗派中人那样推重黄庭坚。
至于江西诗派诗人之间所具有的理学渊源、禅学渊源关系,陈与义更不具备。因此,以黄陈的法嗣为标准将陈与义列入江西诗派是不能成立的。江西诗派中无人学过陈与义,将其列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中,把一个后辈诗人列为过世前辈作“祖宗”,更是无稽之谈。
三、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学杜考异
陈与义和江西诗派一样主张效法杜甫,是论家将其划入江西诗派的又一重要依据。学杜被方回视为江西诗派开宗立派的不二法门,他认为黄庭坚诗法杜甫,陈师道通过学黄学杜,“遂名黄陈,号江西派”,“老杜实初祖也”[4]18。 “黄、陈学老杜者也,嗣黄陈而恢张悲壮者,陈简斋也。”[4]42“简斋诗即老杜诗也。”[4]42后世的很多论家和方回一样,认为学杜集中地反映出陈与义和黄陈等人的诗学主张和诗学渊源。但事实上陈与义和江西诗派学杜有着本质的差异。
江西诗派学杜集中体现在黄庭坚和陈师道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中,江西诗派的后学们主要是通过黄陈间接学杜。黄庭坚在早年的《老杜浣花溪图引》等作品中称赞杜甫在颠沛流离中不忘忧国的情怀,《流民谈》和《按田》等作品都体现了与杜诗相类似的忧国爱民情怀。但他中年进入创作高峰期后的诗歌却没有了杜诗那种浓郁的忧国忧民情怀。同时,他的诗学思想也有了重大变化,他在《书王知载胊山杂咏后》中说:“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他认为诗本质是抒情,且诗歌抒发的情感应该受理性约束,含蓄而不怒张,不能把诗歌当作讽谏的政治工具。他强调诗“闻者亦有所劝勉”的感化功能,还有诗“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的审美功能。在创作上黄庭坚强调从内心和书本去发掘创作素材,与杜诗现实精神存在极大差异。他指导后学时反复强调:“但须勤读书……根本若深,不患枝叶不茂也。”(《与济川侄帖》)“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论作诗文》)黄庭坚重视以读书来提高诗人的心性与品格修养和学术修养,认为杜甫和韩愈的创作“无一字无来处”。他批评江西诗派的晚辈诗意不高的主要问题在于“读书未精博”(《与王观复书》),指点江西诗派的后学在诗歌创作中应该“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这些都体现了黄庭坚的诗学主张。
黄庭坚主张学习杜甫晚年夔州后诗歌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精妙诗法。他在《与王观复书》中说:“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并称赞杜夔州后的诗歌“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达到了“平淡而山高水深”的纯熟老成的境界。可见,黄重点强调学习杜甫夔州后诗歌醇熟的技法,以达到“不烦绳削而自合”“平淡而山高水深”“大巧”的老成境界。“黄庭坚的诗在艺术上往往得到杜诗的精髓,但缺少像杜诗那样深厚的思想内容。”[12]所以,黄庭坚创作进入高峰期以后的诗歌总体上和杜甫晚年诗作那种技法纯熟、但“格调气韵渐趋衰敝”“诗歌题材的琐细、诗歌意象的衰飒”[13]的风貌十分相近。
陈师道推重黄庭坚,在学杜方面和黄庭坚大致相同。他认为:“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14]1019而王安石 、苏轼、黄庭坚各执其一端。陈师道认为杜诗“有规矩故可学”,在学杜诗的具体方法上,他主张要从黄庭坚和韩愈入手,认为“不由黄韩而为老杜,则失之拙易矣”[14]1017。具体内容也是学习杜甫的诗法技巧,摆脱有意为工,达到超越法度的无意为工。
江西诗派其他成员作为黄陈的法嗣,主要是通过黄陈间接学杜,也侧重于学习杜甫的创作技巧。吕本中和曾几等江西诗派代表人物,论诗多从字法和句法着眼。吕本中著名的“活法”显然承接了黄庭坚“点铁成金”的诗法而来。曾几学杜也主要从句法、格律入手。他认为陈师道的诗格律严,“豫章乃其师,工部以为祖”(《次陈少卿见赠韵》)。他在《李商叟秀才求斋于元渤,以“养源”名之,求诗》中说自己“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列江西”。也可以看出,其所推崇老杜的也正是句法、句律等艺术技巧。
陈与义学杜与江西诗派有很大不同。他在南渡前并不看重杜甫,南渡后才真正开始学杜,且主要学习其安史之乱期间的现实主义作品。
陈与义前期对杜甫与杜诗的认识并不深刻,对杜甫的执着的人生态度表示质疑,他在《杂书示陈国佐胡元茂》一诗中感慨“冥冥云表雁,时节自往还。绝胜杜拾遗,一饱常间关。晚知儒冠误,犹恋终南山。”在《冬至》一诗中也说“人生本是客,杜叟顾未知”。他认为官场险恶、俸禄微薄,不可学杜甫抑郁不得志,还要执着于官场,批评杜甫不解人生之道。所以,陈与义在南渡前的诗中写道:“堂堂李杜坛,谁敢蹑其址。”(《再赋》)称赞杜甫在唐代诗坛上绝高的地位,但在创作过程中主要大量化用杜诗的词句,学习杜诗的技法,与江西诗派相类。这一点论家有充分的论析,这里不再赘述。
靖康之难后,面对国家和社稷的严重危机,陈与义才真正理解了杜诗的真谛,开始认识到杜诗现实主义的深刻价值。“年华入危涕,世事本前期。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发商水道中》)“避兵连三年,行半天四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正月十二日自房州遇金兵》),在这些诗句中表达了自己为曾经忽视杜诗而懊悔。钱钟书说陈与义“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才认识到他是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诗人要抒写家国之恨,就常常自然效法杜甫这类悲壮苍凉的作品。”[15]陈与义南渡逃难过程中创作的很多诗作,如《伤春》《邓州西轩书事十首》和《牡丹》等,都继承了杜诗的风雅精神,可谓是学杜而得杜诗之精神者,在艺术精神上逼近老杜,一些作品纳入老杜集中亦不见逊色,也是历代论家评价很高的作品。吴子良就说:“盖建炎乱离奔走之际,犹庶几少陵不忘君之意而。”[16]胡稚也说:“其忧国忧民之意,又与少陵无间。”[11]2不约而同称赞陈与义诗歌对杜甫忧国忧民情怀的继承。
同时,陈与义明确提出反对江西诗派雕章镂句式的学杜。“唐人作诗皆苦思……造语皆工,得句皆奇,但韵格不高。故不能参少陵之逸步。”[17]陈与义认为晚唐以来的诗人学杜但没能学到杜诗内在的精髓,他所反对以追求工、奇等方式学习杜诗,正是上文所论江西诗派学杜的基本路径。
要而言之,陈与义和江西诗派学杜最大的差别主要就在于:陈与义则更侧重于学习老杜在“安史之乱”中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而江西诗派注重学习杜甫夔州以后诗歌对诗歌技法精深的锻炼。陈与义的诗歌创作在艺术精神上已逼近老杜,得杜甫诗沉郁之精髓,江西诗派的诗有老杜诗歌的顿挫而没有老杜的沉郁。
再者,在诗学渊源上只强调学杜,也有以偏概全之嫌。杜甫也不是黄庭坚等江西诗人和陈与义唯一的诗学渊源。黄庭坚的诗学渊源就非常广泛,他对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刘禹锡、梅尧臣、苏轼、王安石等人的诗歌艺术给予广泛的吸纳。陈与义示范的对象也包括曹植、刘桢、陶渊明、谢灵运、杜甫、王维、柳宗元、刘禹锡、韦应物等人。论家舍弃其他不论也很值得深思。对此本人曾有专文论析[18],这里不再重复。
因此,简单地以学杜为依据将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也难以立足。
四、陈与义与江西诗派诗风之差异
论家以陈与义诗风与江西诗派诗风相同或相近将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的说法也不符合陈与义的创作实际。陈与义南渡前的诗风的确与江西诗风相近,但代表其主导风格的南渡后诗风与江西诗风有很大差异。
江西诗派的诗风主要承袭了黄陈后期的诗风,内容狭窄,“诗歌的表现范围由社会转向个人,由外界转向内心,由生活转向书卷”[19]。其诗歌主要反映他们穷居末世的消极颓废心态,以及贫寒自守中对高洁耿介、淡泊超脱精神的发现和追求。在艺术上讲求用典,语言朴拙而生新,句法结构曲折,风格奇崛料峭。由于才学和艺术修养不及黄庭坚,因此生新瘦硬程度不及黄庭坚。
陈与义南渡前的诗歌内容与江西诗派基本相同,强调技巧,大量使用典故,颇有逞才斗巧之嫌疑,南渡前的作品大多是和诗友的唱和之作,这类作品也最能体现他此时的创作特点,《目疾》《次韵张矩臣迪功见示建除体》等作品几乎句句用典,字字有出处,很多典故还有生造之嫌疑,如“李逺棊”“圆规尘”“汉帝河”和“灵运屐”等,在人名或人称代词前加上一个事物名词,缺少审美的韵味,也使诗意艰涩难懂。宋人楼钥就说陈与义南渡前的诗“用事深隐处,读者抚卷茫然”[11]1。冯班评价陈与义《目疾》说:“太堆砌”,批评陈与义这样用典是“假借扭合”“不可通”“不本古法”“杜撰”“都是江西恶派乱谈”[4]1596。 可见,陈与义南渡前诗风总体上和江西诗派诗人创作十分相近。
靖康之难后,随着环境和个人生活的变化,陈与义的诗风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为逃避战乱,五年时间里,陈与义历经河南、两湖、浙江等地,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国家和个人磨难深深地触动了诗人的心灵,创作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内容上由关注个人穷愁转向关注国家磨难和自己苦难的人生遭际。感事伤时,描写逃难生活的痛苦以及漂泊异地的思乡之情成了他诗歌最重要的主题,大大突破了其南渡前的创作范围。其中感伤国难是陈与义南渡后创作最突出的主题,如《伤春》就抓住了国家面临的战乱、朝廷御敌无策、天子蒙羞逃难、沉重的岁币和军队抵抗无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写出了在国难面前的愁苦、感愤与无奈。感伤中带有尖锐的批判,显示了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士大夫的使命感,类似的作品还有近30首。面对国难,作为一个具有良知的士大夫,陈与义的不少作品表现出积极的救国热情。“中兴天子要人才,当使生擒颉利来。正当吾曹红摸额,不须辛苦学颜回。”(《题继祖蟠室》)其大有投笔从戎、慷慨赴国的气慨,表现出诗人强烈的责任感和中兴热望,被白敦仁称为“充满爱国激情的战歌”[20]2。
抒写个人在战乱中历经艰险和对故国家园的思念也是陈与义此时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今年奔户州,铁马背后驰。造物亦恶剧,脱命真毫厘。”(《正月十二日自房州遇金兵》)作品写诗人长期逃难的漂泊之苦和死里逃生的艰辛,深刻而真切地写出了诗人历经战乱生死考验和长期逃难的痛苦。刘辰翁在评点时说:“隔世读此,如对当日避世,常有此不能语。”[20]502再如《牡丹》:“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该诗把作者的漂泊之感和思乡之情写得淋漓尽致。这些作品不仅在内容上大大突破了他前期诗歌,在艺术手法和审美风格上也和前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中很少用典,化用前人诗句亦极自然,语言凝炼,简洁自然又不失工切,语言看似浅近却极具有表现力,达到了以短语述无限的艺术效果。在审美风格上,陈与义后期的诗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有类似《伤春》这样雄浑悲壮者,也有类似《牡丹》这样沉郁低回者,还有上文没有提到的一些清淡自然的山水田园之作。这不仅是他前期所没有的,也是北宋末年的江西诗派诗人所没有的。
更为重要的是陈与义的诗在艺术表达上,明显地表现出融合唐宋诗风的倾向。那些感时伤时之作,对社会批判的见解深刻而富有理性,议论化倾向明显,表现出宋诗重意、重思理的特点。唱和之作用典繁复与江西诗风相近,有逞才弄学之嫌,属于典型的宋诗。而他的写景抒怀诗和山水诗,又明显地走的是唐诗重意象、意境营造的路子,显得情韵皆胜。如《登岳阳楼》将洞庭湖秋日傍晚凄凉壮阔的景象和诗人在战乱中凄凉的情怀融为一体,营造出一种韵味无穷的审美意境,具有唐诗的审美意蕴。张嵲就曾指出陈与义的诗:“上下陶、谢、韦、柳之间。”[11]5胡稚也说:“其正始之源,出《风》、《骚》,达于陶、谢,放于王、孟,流于韦柳,而集于今简斋陈公。”[11]6近代陈衍也说:“宋人罕有学韦柳者,有之,以简斋为最。”[21]这些论段都指出了陈与义和王、孟等人的诗学传承关系和风格上的相同之处,还有很多论家也一再强调这一点。宋代刘辰翁就说陈与义的一些作品写得近王维的“辋川”诗,冯舒评他的《晚晴野望》说:“此亦不减唐人。”[20]524这也是陈与义诗歌不同于江西诗风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对改变北宋末年宋诗渐已僵化的格局,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路子,具有重大的诗史意义。
五、将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的谬误根源
通过以上论析可以看出,持论陈与义属于江西诗派的观点有很大的偏颇。论家在陈与义与江西诗派的创作实践、诗学渊源和审美风格上,为什么舍去那么多的不同不论,而单要笼统地说其相同之处,非常值得深思。笔者以为,南宋以来,诗坛的门户之争是造成这种偏差的最主要原因。
南宋中后期,诗坛派系之争激烈,唐宋诗之争就是当时诗坛争论的重要话题,当时重要的诗人和诗论家刘克庄、杨万里、严羽、方回等大多卷入了派别争论之中[22]4-8。在激烈的争论中,界定间隙诗派的标准也比较混乱,江西宗派不断被泛化。吕本中的《宗派图序》就表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倾向,他贬低李、杜之后到黄庭坚之前的诗人,隐约可以看出他尊崇宋诗的倾向[22]1。他以黄为诗派之“宗”,认为宗派中诗人在渊源上都出自黄庭坚,表现出重统序的思想。杨万里以“味”论诗,将曾纮、曾思父子续入江西诗派。严羽宗唐黜宋,以“兴趣”论诗,推崇汉魏至盛唐的诗歌,对唐代大历以后和宋代诗人不加深考一概否定,将陈与义划入江西宗派。方回论诗倾向宗宋[22]6,力主学杜,把赵章泉、韩涧泉和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几人以不同于吕本中的标准,扩大了江西宗派。
这些主江西诗派者以及江西籍学者(严羽除外),把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的目的就是为扩大门派的影响。谢薖之孙刻江西宗派诗人作品的目的就是“将以兴发江西山章之秀,激扬江西人物之美,鼓励骚人国风之盛”。他邀请杨万里为其作序的信中写道:“子江西人也,非乎?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将焉在?”[2]陆九渊赞程帅刻宗派作品之举为盛事,并说:“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宠。”[23]这些言行明显是标榜乡学前辈。方回建立所谓的“正脉”统序,并将陈与义纳入派中,也是为自己标榜的诗派壮大声势。不同论家立派标准也各不相同,或强调派中诗人诗学渊源的相同性,或艺术风格上的趋同性,与吕本中强调派中诗人学黄与密切的创作交往,大相径庭,这就淡化派中诗人之间基于多方面的师友关系。清人张泰来就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吕本中索索的江西诗社宗派:“意实不专主诗……后人舍立身行己不论”单纯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看待他做划定的江西诗派,“几何不以吕公论世尚友之旨大相径庭也哉!”[24]在这种情况下,论家对陈与义是否属于江西诗派自然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从根本上说,方回等人把诗人的渊源关系看作决定作家风格的主导因素,忽略了时代环境对作家创作带来的差异。他以学杜和推重黄陈为由将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的依据,违背了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基本规律,忽略了诗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对其诗歌创作的决定作用。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5]清代著名诗人与诗论家王夫之也曾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26]这些精辟的论断都道出了作家所生活的时代环境才是决定作家艺术风貌的最根本因素,从根本上讲,陈与义南渡前诗风与江西诗派大致相近,是他们都生活在相同的时代和相似的人生经历所造成的。陈与义南渡后诗风发生了不同于江西诗派的变化,也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江西诗派诗人所生活的北宋末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钱钟书在《宋诗选》中批评方回错将陈与义划入江西诗派,“从此淆惑了后世文学史家的耳目”[15]133。 其确是非常有见地的论断。
关于陈与义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南宋刘克庄曾作过精辟的论析,他说:“元祐后诗人迭起……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并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桥,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优爱,以简洁扫繁褥,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27]。刘克庄明确地指出了陈与义与苏黄生活年代的差异对其诗风的影响,找到了陈与义南渡诗风改变的根本原因。他充分肯定了陈与义要在苏黄之外另辟蹊径的诗歌创作追求,同时也指出陈与义跨越苏黄,直承老杜,道出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在诗学渊源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南渡后的创作才是陈与义创作的成熟期与风格的代表期,视陈与义为元祐以后诗人之冠,准确地道出了陈与义在当时诗坛上突出的成就与地位。此外,杨万里也曾增补过江西诗派成员的名单,并对陈与义的诗有很高的评价,他在《跋陈简斋奏章》说“诗宗已上少陵坛”[2],但没有把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论调和刘克庄大体一致。
综上所述,陈与义并不属于江西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