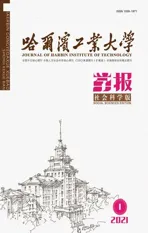李渔戏曲创作理论和写作实践的矛盾性刍议
2021-12-06袁楚林魏琛琳
袁楚林,魏琛琳
(1.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香港999077;2.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西安710049)
引 言
《闲情偶寄》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领域难能可贵的集大成之作。“观人有别言,论事有别见,行文有别肠”[1]的李渔将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写作建议集中写在了“词曲部”和“演习部”中,系统、全面地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等角度为戏曲创作方式“立法”,以期“为大众慈航”。琴隐翁在《审音鉴古录序》中称此书“可谓梨园之圭臬矣”[2],后世研究者游友基称“李渔的《闲情偶寄》,是我国古典戏剧美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论著……在阐述戏剧创作的规律和总结戏剧创作的经验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代以及同时代的戏剧美学著作,在探讨中国古典戏曲的审美特性上,又有别于欧洲的戏剧理论,而闪耀出特有的光彩。”[3]目前,《闲情偶寄》已经在海内外出现50多个版本,此亦佐证其受时人和后人推重之景况。然当我们将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的理论与其具体的创作实践进行对比,会发现其创作并未完全遵循《闲情偶寄·词曲部》中的主张,甚至多有矛盾。这与明末的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
明末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市民队伍的壮大等都激发着启蒙思潮在市民阶层中的兴起。王阳明的心学为人性解放打开了一个缺口,而泰州学派更是将“道”与百姓日用联系起来,肯定世俗生活中人的物质欲望。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社会中的日常生活,还是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风貌。苗玲玲指出:“晚明时期,市民文化以肯定世俗生活、歌颂人世欢乐为主要特点。因此,反映世态人情、人的自然欲望的作品自然会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这一风尚引导了文人创作的世俗化。”[4]蓝天指出李渔“深深懂得作品内容的通俗性事关作品的艺术生命和观众接受的效果”[5]。这种社会的“变化”作用在兼具文人和商人两重身份的李渔身上便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他一方面不自觉地流露出传统文人对创作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体现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学养;另一方面努力经营自己在市井之中的生活,根据普通市民大众在娱乐、休闲和观赏方面的需求,进行市场化的写作,卖文为生。其“矛盾”离不开“士”和“民”双重身份及价值属性的重叠和冲突,更展现出传统士人精神在世俗环境下的独特风貌——所以他既是“风雅功臣”又是“红裙知己”;既期待作品规正风俗、警惕人心,又无法避免作品中出现为市民喜闻乐见的荒唐情节和低俗的恶趣味;既要求戒除对陈言旧集的剽窃网罗,又不能削减自己对前人有趣情节的蹈袭模仿。
以往的研究成果多重视探讨李渔戏曲理论与创作的一致性,如郭玉坤《雅中带俗活处寓板——谈李渔的喜剧理论与实践》、李雪《“重机趣”的理论、实践及其影响》等。也有些研究成果注意到李渔戏曲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差异,但涵盖面存在局限。如陈阳雪《论李渔曲学理论与实际创作的出入和统一——以〈怜香伴〉为例》,其讨论范围仅局限于《怜香伴》这一个作品。许莉莉《李渔剧作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感”及其成因探讨》关注到李渔多个戏曲作品,然而没有认识到李渔的小说作品与戏曲是“事迹相类”的,因而也同样应该被纳入考量。李小慧《李渔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的背离性》分析了李渔戏曲创作实践与戏曲理论呈现出的思想矛盾和不同目的,但仍有深入阐述的空间。本文的研究以“矛盾”为关键词切入,从各方面比较李渔的戏剧理论和创作实践,发掘了探索《闲情偶寄》和李渔小说、戏曲创作的新视野。笔者拟对比李渔的创作理论和写作实践,指出其中的矛盾,①与戏曲理论相对应的“写作实践”并不仅限于李渔的传奇剧创作,而是将其戏曲和小说共同纳入考量——毕竟戏曲和小说“事迹相类”。胡应麟在其《庄嶽委谭下》中就曾对这一点进行论述:“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铏所撰……其书颇事藻绘而体气俳弱,盖晚唐文类耳,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或以中事迹相类,后人取为戏剧张本,因展转为此称不可知。”(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424页)可见传奇和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讲故事。《绣像合锦回文传》评点者素轩曾提出“稗官为传奇蓝本”(李渔全集:第九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326页)李渔也有过类似主张,如在《十二楼·拂云楼》第四回的结尾处写下“各洗尊眸,看演这本无声戏。”(李渔全集:第九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176页)将小说比作无声戏。因此本文将小说和戏曲视为一个整体,用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的创作理论关照其小说和戏曲的创作实践,论证李渔的矛盾性。并对此类“矛盾”的成因进行探索,旁涉明末清初社会的时代氛围、文化风气和士人心态。
一、避犯佻达之嫌的“戒淫亵”与不忌淫词秽语的“恶趣味”
在《闲情偶寄》的“语求肖似”一节,李渔提出要对创作的主题内容有所拣选:“稍欠和平,略施纵送,即谓失风人之旨,犯佻达之嫌”[6]47;也在“戒淫亵”一节写下戏曲创作的标准:“人间戏语尽多,何必专谈欲事?即谈欲事,亦有‘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之法,何必以口代笔,画出一幅春意图,始为善谈欲事者哉?”[6]56意在强调尽量不要过分言及男女之事,“如讲最亵之话虑人触耳者,则借他事喻之”[6]56。但另一方面在具体写作实践时,他却仍然淫词秽语毫无避忌,为夺人眼球无所不用其极。
《夏宜楼》中,李渔以“西洋千里镜”充当瞿吉人和詹娴娴相识相恋的媒人,情节设置新颖别致。但有一幕是侍女们因在荷花池嬉戏被瞿吉人看到裸体,因而“只有娴娴小姐的尊躯,直到做亲之后才能畅览;其余那些女伴,都是当年现体之人,不须解带宽裳,尽可穷其底里。吉人瞒着小姐与他背后调情,说着下身的事,一毫不错……既已出乖露丑,少不得把‘灵犀一点’托付与他。吉人既占花王,又收尽了群芳众艳,当初刻意求亲,也就为此,不是单羡牡丹,置水面荷花于不问也”[7]97。这样的内容格调并不高,且多少有伤风化。
同样有悖于公序良俗的还有《萃雅楼》中描绘权汝修被软禁在严府、留在后庭相见的场面。东楼形容权汝修“肌滑如油,豚白于雪,虽是两夫之妇,竟与处子一般”[7]139。而东楼自然“心上爱他不过,定要相留。这三夜之中,不知费了几许调停,指望把‘温柔软款’四个字买他身子过来”[7]139。 对于好男风的宠狎行为毫不避忌;《拂云楼》中也是如此,重阳节时男男女女都到西湖看赛龙舟,不想狂风大作,浪声如雷下起大雨来。少年们便借机窥视,发现此中“独有两位佳人,年纪在二八上下,生得奇娇异艳,光彩夺人,被几层湿透的罗衫粘在裸体之上,把两个丰似多肌、柔若无骨的身子透露得明明白白,连那酥胸玉乳也不在若隐若现之间”[7]156。将女性的身体和形态毫不避忌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并未脱佻达之嫌。类似的场景在裴七郎和韦小姐、能红成亲之日也有着墨。
《十卺楼》更是把李渔对于床第之事的恶趣味展现到了极致。其中对石女以及新婚当夜的描写,十分秽亵露骨。“好事太稀奇!望巫山,路早迷,偏寻没块携云地。玉峰太巍,玉沟欠低,五丁惜却些儿费。 漫惊疑,磨盘山好,何事不生脐!”[7]193把石女的生理特点和身体缺陷不遗余力地描述出来。后面还叙述了夫妻之间的“舍前趋后”之事、新妇“怎肯爱惜此豚,不为阳货之献”等一系列行为。后来又描写了石女的妹妹夜间遗小便之事,最后在第十次成亲换回石女之后,描述夫妻两口搂作一团,借毒疮摩疼擦痒,享“肆意销魂之乐”。小说中对夫妻私密生活进行大胆暴露、并不厌其烦地加以渲染,甚至描绘了一些让人作呕的情节(如锦衾绣幔之中让人难以忍受的秽气),并未带给人感官享受、引发人的审美愉悦。在《人宿妓穷鬼诉嫖冤》中,对床事的描写同样是丝毫不加以掩饰。
除以上几篇作品中的大肆提及,其他篇目中对这类行为也均有涉及,《合影楼》中有珍生张开双手试图搂抱玉娟的桥段,《鹤归楼》中段玉初和绕翠多年之后重逢时的恩爱画面,《风筝误》中好淫的戚有先从墙外对女性身体进行窥视、垂涎淑娟的美色……这类涉及夫妻生活、阉割场景、女性体态、亵狎之事的描写在李渔的笔下出现频率相当高,只是露骨的程度略有区别。还有一些“恶趣味”的情节,如《怜香伴》中没有真才实学的周公梦为顺利通过科举考试,竟然制作出来小抄藏在粪门之中,戏谑的同时亦较为粗鄙。《意中缘》中第六出“奸囮”中是空和尚称黄天监“只因嫖兴太高,惹了一身梅花疮,刚刚在那话上面结了一个肿毒,齐根烂得精光”[8]337-338。 污言秽语径直进入读者眼帘,并不符合李渔曲论中“戒淫邪”之说。这些都是李渔与同时期精英文人的不同之处,是其作品吸引市民大众、在不同阶层读者群中得到广泛传播的缘由,但同时也是李渔在创作实践中对自己理论主张的背离。
二、求诸日常见闻的“戒荒唐”与“无奇不传”的大胆虚构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多次论及创新求奇的重要性,在词曲部中明确提出“无奇不传”的创作理念,但亦强调要“有奇事,方有奇文”[6]4。 在“戒荒唐”一节中,李渔也明确提出,传奇要“说人情物理”,而且“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6]13-14。 由此可见,他虽然求奇,但求的是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但尚未被别人发现或记载的“奇特之事”。与此相反,他在“语求肖似”一节又提出作家也可以不拘泥于事实,大胆进行艺术想象:“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籛之上。”[6]47称作家创作时可以超出寻常见闻之外,任文字、情节随思绪飞扬。那么,“大胆虚构”和“不当索诸见闻之外”之间的界限就很模糊了,这两种并存的创作理念有时是自相矛盾的。
以《蜃中楼》为例,这部虚构的传奇剧描写了人间才子与海中龙女的奇幻姻缘。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姻缘是“天定”的,因龙王过寿,久居龙宫的龙女姐妹二人相遇,相约去海面游玩,他们的父亲为了保护他们而让虾兵蟹将“嘘气成云,吐涎作雾”结起一座蜃楼。这座蜃楼不再是现在谈及的光学现象,而是靠虾兵蟹将“吹得上气不接下气,口涎连着鼻涕”结成的;后柳毅之所以能走到蜃楼上与龙女们交谈,又是靠东华上仙“掷杖成桥”;不仅如此,甚至连玉帝都参与进来。这些情节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可能发生,都是基于李渔的想象和虚构,可谓“索诸见闻之外”的“荒唐”。当张生带着金钗去洞庭湖报信,“金钗一响,潮水忽然分开”[8]275。连主人公自己都说:“每读齐谐眼倦开,怪将诧事费疑猜。从今莫笑荒唐史,亲向荒唐会里来。”[8]229最后的试术、煮水等情节更是离奇,几乎全部情节都建基于奇幻、想象和虚构,与《闲情偶寄》中的“戒荒唐”自相矛盾。
此外,李渔亦曾明确指出创作传奇应尽量少论及鬼神:“殷俗尚鬼,犹不闻以怪诞不经之事被诸声乐,奏于庙堂,矧辟谬崇真之盛世乎”[6]13,指出有尚鬼风俗的殷代都没有在演奏宫廷音乐时加入荒诞不经之事,现在这个剔除谬误、崇尚真实的社会就更不应该这样做了。更何况“活人见鬼,其兆不详,矧有吉事之家,动出魑魅魍魉为寿乎?”[6]13但反观其个人创作,李渔并未按照自己的理论主张去做,反常借鬼神之力推进故事情节发展。
以《无声戏》为例,十二回中有五回涉及鬼神显灵,所占比重接近二分之一,不可谓不高。具体来说:第二回“改八字苦尽甘来”中,蒋成一直时运不济,直到“活神仙”华阳山人替他改了八字,才逐渐发家致富、官运亨通;第七回“人宿妓穷鬼诉嫖冤”中,王四在受到雪娘与妈儿的算计和欺辱后申冤无门,终靠魂魄现作人身,向与雪娘同宿的运官伸冤才拿回自己的钱财;第八回“鬼输钱活人还赌债”中,竺生受骗致使家产尽失,母亲病亡,其父化身为鬼惩治恶人,终使因果得报。第九回“变女为儿菩萨巧”也是如此,先以三个举子一起求梦且梦兆得现的例子,指出“鬼神的聪明,不是显而易见的,须要深心体认一番,方才描摩得出”[9]176。后又用施达卿停止施舍财产为自己赎罪,菩萨赐给他一个“逃于阴阳之外,介乎男女之间”的孩子。当菩萨再次显灵,原本不男不女的孩子竟然奇迹般变为儿子,菩萨神力可见一斑。第十回“移妻换妾鬼神奇”中正妻杨氏被善妒的小妾阴谋算计陷害,差点被丈夫休出家门,最后靠神鬼之功才沉冤得雪,使小说结局朝着理想方向发展。以上诸例中,鬼神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与李渔本人提出的创作理念自相矛盾。
其他诸如此类“事涉荒唐”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比目鱼》中谭楚玉和刘藐姑两人双双化作比目鱼,后来又幻化回人形。《十卺楼》中,主人公姚子穀的婚姻经历完全印证了郭酒痴“请仙办事”得到的题咏,奇则奇矣,然颇为荒唐,与李渔自己提出的创作理论不符。不过,李渔也曾以“从来不演荒唐戏,当不得座上宾朋尽好奇。只得在野豆棚中说了一场贞义鬼”[8]313的理由为自己辩解。这种观众“好奇”的审美需要制约、影响李渔写作实践的情况会在后文着重分析。
三、力倡“无我之境”与作者主观色彩的介入
李渔在“词曲部”中强调追求“无我之境”:“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辟之思。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之绝技。”[6]47-48主张创作时要设身处地把自己当成作品主人公进行表达和言说,让作品中人物的语言、行为等都符合人物的处境、身份和心理,尽量减少作者的主观介入。①这其实类似于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都是为了让作品人物以尽量独立、客观的面貌呈现于读者面前,不让作家的主观态度和情绪影响读者的阅读效果。这样一来,作品便距离读者更近,具有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读者亦有了更多的理解维度。值得注意的是,罗兰·巴特出生于1915年,提出“零度写作”这一概念是在1953年,而生活于1610—1680年的李渔早于其200多年就在《闭情偶寄》中对作者的参与程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得不说,在作者如何客观地塑造作品人物这一问题上,李渔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和指导性。但在实际创作时,李渔却时不时插入自己的主观叙述,入话、结尾处的劝诚更是屡见不鲜。这些导致他的作品有非常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抒情性,明显带有创作者的主观色彩,其“说话者”身份和“创作主体”地位不断得到彰显。
如《怜香伴》开头的“破题”:“真色何曾忌色,真才始解怜才。物非同类自相猜,理本如斯奚怪。”[8]7与其说是为了引入下文而进行的“破题”,倒不如说是创作者主观态度的表达。又如《凰求凤》收场诗:“倩谁潜挽世风偷?旋作新词付小优。欲扮宋儒谈理学,先妆晋客演风流。由邪引入周行路,借筏权为浪荡舟。莫道词人无小补,也将弱管助皇猷。”[8]521传达了作者寓教于乐的态度,有强烈的主观表达意愿。再如《鬼输钱活人还赌债》入话,宣扬了作者赌博败家的观点。《合影楼》中更为明显:“我今日这回小说,总是要使齐家之人,知道防微杜渐,非但不可露形,亦且不可露影,不是单阐风情,又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条相思路也。”[7]15使用“我”进行主观表态,抒劝惩之意。作者甚至会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态度和主张。例如《比目鱼》中的女主人公义正辞严:“自古道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妇。你在明中夺人的妻子,焉知你的妻子,不在暗中被人夺去?”[10]157《凰求风》中男主人公就因果得报发表评论[8]426;《慎鸾交》也借主人公华秀之口讲述对学士、文人的期待[10]424。这都是创作者抒发个人观点的表现,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此外,若仔细分析李渔笔下的男主人公,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或多或少带有李渔本人的某些特征——或是相似的性格特点,或是相似的业余爱好,或是风流自赏的审美情趣,或是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等。如《三与楼》的男主人公虞素臣不仅和李渔本人一样绝意功名、寄情诗酒,而且非常喜欢盖楼。在盖楼的过程中,他也同样是穷极精雅,后来还和李渔一样迫不得已卖楼。孙楷第先生就曾指出“文中虞素臣,即是李渔自寓。”[11]52《闻过楼》中的顾呆叟更是避时逃名,三十多岁就放弃了功名,十分恬淡脱俗,隐居在去城四十余里的荆溪之南,还计划将自己的居处安排得高雅脱俗,不仅生活方式与李渔如出一辙,作者在塑造顾呆叟形象时更是将自己对园林建设的心得“移植到他的身上”。孙楷第先生亦指出:“我们稍知笠翁生平,便知道这一篇小说是签翁自己的梦。”[11]60他又称:“我们认识了《闻过楼》中的顾呆叟,便认识笠翁了。”[11]64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徐保卫曾指出“襁褓识之无,曾噪神童之誉;髫龄游泮水,便腾国瑞之名”[10]112的谭楚玉身上,明显打上了李渔本人青少年生活的印记。总之,李渔笔下的许多主人公都和他本人有着极为相似的性格志趣、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
李渔作品中的“有我之境”还表现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掺入自己对于社会、时事、官场等的态度和看法。如《蜃中楼》中,作为东海龙王的兵将,鱼、虾、蟹、鳖在收到“结蜃”指令后互相推脱,谁都不愿意先来,可当听到“蜃楼结成了,大家都去报功”之后,鳖便立刻伸头高叫“让我先走”。遭到大家取笑时还振振有词:“列位不要见笑,出征的时节缩进头去,报功的时节伸出头来,是我们做将官的常事,不足为奇”[8]223。 《怜香伴》中也多借宗师岁考、副净之口讽刺官场上贿荐卖官的丑恶现象,申明自己的态度。
同样掺入作者主观意愿的例子还表现在作者对妒妇形象的塑造上。李渔认为女性不应善妒,他曾经驱逐家中一个善妒、生事的姬妾,而对自己宽容大度、明理包容、照顾姬妾的正妻颇为感激,还不止一次提及对妒妇的厌恶,如《闲情偶寄》中的“女德莫过于贞,妇愆无甚于妒”[6]14等。 这种态度同样在其塑造作品人物形象时有所体现。在《移妻换妾鬼神奇》中,小妾陈氏多次设计陷害杨氏,并伺机制造杨氏与丈夫之间的矛盾和误会。但李渔安排了陈氏遭到上天惩罚,不仅如疯子般披头散发在猪圈之中搂着癞猪同睡,还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讲出了以往陷害杨氏的所有阴谋。此外,陈氏还因为与猪同睡染上癞疮,再也无法与丈夫同床。而不会吃醋的杨夫人却得神明帮衬,享了一生忠厚之福。又如《凰求凤》中李渔让才貌双全的许仙俦和曹婉淑先行得到意中人并顺利成婚,却使善妒的乔小姐和吕哉生的婚约一波三折。由此可见,李渔为小说中人物设置的结局其实正是他自己对妒妇态度的真实再现。不仅如此,李渔还在小说的结尾强调,吃醋这件事“无论新陈,总是不吃的妙”,认为世间的醋“不但不该吃,也尽不必吃”[9]206,使得整篇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完全成为作者主观态度的“传声筒”。
可是,按照李渔曲论中的“舍经从权”“心曲隐微”之说,作品人物的思想感情、意志情趣、个人选择怎么能是作家自身人格的呈现和主观意愿的表达呢?这些都与他自己提出的“无我之境”艺术追求自相矛盾。
四、“好为矫异”的创新求奇主张与结构安排的重复
李渔还在《闲情偶寄》中多次强调创新、求奇的重要性,如“若人人如是、事事皆然,则彼未演出而我先知之”[6]102等说法,称自己“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6]156,得意夸口自己的作品“不肖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12]等。但是当我们对李渔的作品加以细读便会发现,他虽在情节设置等方面有出其不意、令人耳目一新之处,但绝不是“不肖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的。傅承洲就曾在其《李渔话本研究》一书中指出李渔对前人的效仿和因袭,如《无声戏》第二回《美男子避祸反生疑》对朱素臣《十五贯》的模仿;十一回《儿孙弃骸骨童仆奔丧》对《徐老仆义愤成家》的因袭;十二回《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对《警世通言》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参考……更不要提《十二楼》之《奉先楼》与《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六《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两者间的相似;《连城璧》第七回《妒妇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与冯梦龙的传奇《万事足》之类同,又有诸如《无声戏》第七回《人宿妓穷鬼诉嫖冤》对《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加工和改写,《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阙里侯为娶到漂亮妻子而行的“偷天换日”之举与《钱秀才错占风凰俦》中的颜俊央人替自己相亲的处理方式如出一辙[13]。诸如此类都可以说明李渔虽大力标榜创新,但其具体的写作实践与其创作要求自相矛盾。
李渔曾在“脱窠白”一节明确表达对“拼凑”的反对,“吾观近日之剧,非新剧也,即是一种‘传奇’,但有耳所未闻之姓名,从无目不经见之事实。语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以此赞时人新剧……若是则何以原本不传,而传其抄本也?窠臼不脱,难语填词”[6]10,认为这样拼合而成的所谓“传奇”只会“枉费辛勤,徒作效颦之妇”[6]10。李渔虽然从理论上对时下创作弊病进行了抨击,但他自己创作的《蜃中楼》却完全违背了这一指导理念,直接由唐代传奇文《柳毅传书》和元代杂剧《张生煮海》两个故事拼接而成,与他抨击的其他作品并无区别。
李渔在推动情节进展时也广泛使用了前人创作中经常采取的误会、反差、巧合等创作方法,并未做到“脱窠臼”。如《丑郎君怕娇偏得艳》《风筝误》《美男子避祸反生疑》《失千金福因祸至》《奉先楼》《生我楼》等都明显使用了误会和巧合的创作手法。如《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的主人公阙不全“五官四肢,都带些毛病,件件都阙,件件都不全阙”[9]8。 可他却恰巧应了“福在丑人边”的说法,娶回来的妻子都是才貌双全。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巧合,让故事一步步走向了高潮。《风筝误》更是如此,从题目就能看出整个故事基于“误会”。书生韩世勋题诗风筝上,纨绔弟子戚施拿着这只风筝去放,不料线断。飘走的风筝恰巧被詹府才貌双全的二小姐淑娟捡到,之后便倾慕于题词者的才情。当韩世勋第二次放风筝时,风筝却意外被爱娟捡到。就这样,韩世勋、戚施、淑娟、爱娟四人的命运被阴错阳差地联系到一起,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误会和巧合,四人之间扑朔迷离的错配关系终于水落石出,结局皆大欢喜。《美男子避祸反生疑》亦是如此,蒋瑜和何氏因为移房之事引起赵玉吾夫妇的误会,之后老鼠衔扇坠的巧合更让故事的冲突发展到高潮。《奉先楼》和《生我楼》亦是如此,主人公在乱世中没有孤单飘零,反倒是经过种种巧合最终一家团圆……可以发现,在李渔笔下的故事中,误会和巧合常常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促进和推动情节发展,从创作方法的角度而言并没有做到“一篇有一篇的新境界”。以上这些都可看出李渔写作实践对自己提出的创作理论的背离,可谓自相矛盾。也正因为此,李渔获得的评价也是非常矛盾的,既有人对其表示认可,称赞他的作品“位置、脚色之工,开合、排场之妙,科白、打诨之宛转入神,不独时贤罕与颉颃,即元、明人亦所不及,宜享其重名也”[14],同时也有人评价其作品“全以关目转折,遮伧父之眼,不足数矣”[15]。但无论评价如何,双方都不会否认李渔作品和其戏曲理论之间的显著矛盾。
小 结
作为明末清初学养深厚、涉猎广泛、才华横溢的名士,李渔凭借自己独特而又新奇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作品受到大众购买者的狂热追捧,不仅“十曲初出,纸贵一时”,更为他带来了“日食五候之鲭,夜宴三公之府”的机会。道光年间的曲论家支丰宜在《曲目新编题词》中谈到对清代戏曲的总体看法时十分推重李渔,称:“今古才人聚一编,尤、吴、李、蒋最堪怜,世人莫认为儿戏,不比《桃花》《燕子笺》。尤西堂、吴梅村、李笠翁、蒋莘畬四家所制词曲,为本朝第一。”[16]将李渔与尤侗、吴伟业、蒋士铨四位并列为他最欣赏的清代传奇剧作家,持类似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虽亦有研究者评价李渔时贬大于褒,但不妨碍李渔凭借着自己的作品跻身当时最为流行的创作者行列,在清代众多杰出戏曲家中居于显著地位。其最令人称道之处在于其对戏曲理论亦进行了明确、精辟的探索和论述。康熙十年,他撰写并出版了《闲情偶寄》,其中的“词曲部”既是根据自身经历对戏剧创作经验进行的理论总结,又是对读者和后人提出的创作建议和写作准则。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理论著作,李渔向读者呈现了其新奇而广阔的戏曲理论体系,以难能可贵的开创性和精辟独到的论述为后世所推重。
虽然《闲情偶寄》在戏剧理论史上得到的评价颇高,但本文发现,《闲情偶寄》中提出的戏曲理论和李渔具体的创作实践存在诸多矛盾。如理论上的“戒淫邪”和实际创作中的“恶趣味”;理论中的“戒荒唐”和创作中不时出现的鬼神之事、不合常情常理的情节;号召创作应追求“无我之境”,然而作者的身影、声音和态度却贯穿在许多作品的字里行间;又如虽在理论上强调情节结构上的“创新求奇”,然而具体创作时却不乏蹈袭窠臼、缺乏新意的情节、结构和手法……这些均是李渔写作实践对其创作理念的背离和矛盾。对此类“背离”和“矛盾”的关注,给予研究者重新观照和审视《闲情偶寄》的可能,也启发着笔者思考与形成此类“矛盾”相关的社会阶层、文化心态等问题。
李渔在其创作理论和写作实践方面呈现出的矛盾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试图延续学人传统与明清之际特殊时代风貌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是明清之际市井之人的审美情趣和中国传统士人创作理念的碰撞和交融,是中下层文人在与社会接轨后将创作理念与市民大众审美需求相融合的产物。而在这些矛盾的背后,潜藏着明清之际在政治和经济上丧失了优势地位、只能转向卖文为生,处境尴尬却仍旧怀有传统文化精神和理想的中下层文人所共同秉持的生存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