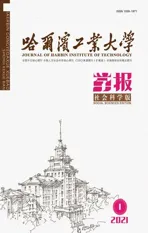论程煐《龙沙剑传奇》的文人化色彩
2021-12-06陈才训王一夫
陈才训,王一夫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150080)
相较于此前的顺、康、雍各朝,乾隆时期文网日密,文祸频起。乾隆四十四年(1779),安徽天长县贡生程树榴为其友人王沅《爱竹轩诗稿》作序,并出资刊印该书,因其序文中有“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之语而被仇人王廷赞告发,诬称此乃“隐喻讪谤”当今皇帝。乾隆帝阅程树榴序文,怒斥其“牢骚肆愤,怨谤上苍,实属丧尽天良”[1]。 于是,程树榴被“律以大逆”而罹祸,其子程煐则在被关押了十几年后,于嘉庆戊午年(1798)被流戍至黑龙江卜奎(今齐齐哈尔)。 程煐(1746—1812),字瑞屏,一字星华,号珂雪头陀,又自称瑞头陀;邑廪生。在流戍卜奎期间,程煐创作了黑龙江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戏曲作品《龙沙剑传奇》,这也是清代东北流人创作的唯一一部戏曲著作。目前,《龙沙剑传奇》仅有“世瑞堂珍本”传世,因其20世纪80年代末才被发现,故这部长达三十出的戏曲作品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为数不多的几篇相关论文或对程煐生平及该剧情节内容予以简单介绍,或对其主旨加以阐发;至于其创作特色则鲜有论及,更无人将该剧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探讨其最为突出的“文人化”特色①目前,研究《龙沙剑传奇》的代表性论文是张福海《流人的戏剧:〈龙沙剑传奇〉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清代流人戏剧研究——兼论程煐及其〈龙沙剑传奇〉》(《曲学》2013年刊),前文主要介绍程煐的生平及《龙沙剑传奇》剧情内容,在论及该剧艺术特色时只强调了其“象征精神”;后文“兼论”《龙沙剑传奇》的部分,实际上重复的仍是前文内容。其他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以对《龙沙剑传奇》的宏观介绍为主,研究深度明显不够。可以说,学界对《龙沙剑传奇》的创作特色关注甚少,更未论及该剧所体现的“文人化”这一最为突出的艺术特征。。实际上,缘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及程煐特殊的人生遭际,《龙沙剑传奇》已成为清代戏曲创作文人化的代表性作品。
一、借镜八股,以文为曲
清代,随着八股取士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成熟,几乎所有文人都经历过长期而严格的八股文训练,因为“举业既属士子唯一出路,八股文自为必读必习之艺”[2]。清代著名文人戴名世曾谈到当时读书人研习八股制艺的普遍现象:“以四子之书,幼而读之即学为举业之文,父兄之所劝勉,朋友之所讲习,而又动之以富贵利达,非是途也则无以为进取之资,使其精神意思毕注于此,而鼓舞踊跃以赴之。而人之学之者,自少而壮而老,终身钻研于其中,吟哦讽诵,揣摩熟习,相与扬眉瞬目,以求得当于场屋。”[3]自然,身处其时的清代戏曲作家也不能例外,他们由此形成顽固的八股思维定式,正所谓“工于八比者”,“惟其始也以八比入,其终也欲摆脱八比气息,卒不易得耳”[4]。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八股文作为一种强势文体对清代传奇戏曲的渗透至为显著,使晚明以来“以时文为南曲”[5]的创作传统大行其道,以致出现举世“以文为曲”[6]的创作倾向。例如,工于八股文的张雍敬认为“制艺之于传奇,均文类”,强调“作文之法,其妙悉于传奇”,传奇戏曲也需像八股文一样讲究“埋伏有根、照应有法、线索必贯、收拾必完”[7]1661-1666。 而陈栋竟称:“传奇虽小道,要是作者有许多文法,借此发泄,不理会他文法,但作词曲看,便是买椟还珠。”[8]可见,熟谙八股文法的清代戏曲作家自然而然地将八股技法融入戏曲编创,以八股文之结构布局取代戏曲的关目排场,以致“使编剧法成为文法的一个分支,丧失了自身作为一种艺术写作方法的独立特征”[9]。
廪生出身的程煐具有深厚的八股文素养,他是“以文为曲”观念的积极践行者。族弟程屺山在《龙沙剑传奇跋》中称赞程煐的八股文“率天骨开张,雄才拔俗”[10]141,认为八股“余技”乃是程煐编创这部传奇戏曲的重要凭借。从弟程虞卿也认为程煐以八股之才即以“勃窣文心”运于《龙沙剑传奇》,从而使“读者只便于时艺”[10]142,这里所谓“时艺”,即指八股文法。嘉庆壬戌(1802),《龙沙剑传奇》的评点者“浙西二吾居士”在为该剧所作序文中指出:《龙沙剑传奇》“非传奇也,天下之妙文”,“戏者见之谓之戏,文者见之谓之文”[10]141。 他认为程煐以八股“文法”取代了传奇“戏法”,而这恰是赋予《龙沙剑传奇》以显著文人化特征的重要原因。
首先,程煐对八股密合结构的伏应技法有着自觉而成功的运用。八股文讲究结构严密,前后照应,故倪士毅认为作文须“有开必有合,有唤必有应,首尾当照应”,“一篇之中,逐段、逐节、逐句、逐字,皆不可以不密也”,“要是下笔之时,说得首尾照映,串得针线细密”[11]。以八股文法从事戏曲创作的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中提出的“密针线”理论即由此而出。同样深谙此道的程煐也将这种八股构文之法用于戏曲创作,他在《读曲偶评》中不无自诩地称自己的《龙沙剑传奇》“贯穿排比,俨成无缝之衣”[10]13。 对此,作为《龙沙剑传奇》的评点者,“江西梦熊子”在为该剧所作序文中亦大加赞赏:“结构严密,绝不似则诚之渗漏,洵乎美锦之无类,白璧之无瑕也。”[10]9他认为《龙沙剑传奇》在结构的严密性上超过“传奇之祖”《琵琶记》,此等褒奖之语虽不无过誉之嫌,但也决非虚言。例如,传奇戏曲往往先由副末开场,交代剧情概要、创作意图,同时肃静剧场,迎候观众,此后副末便完成使命,不再出现在剧中。然而,为了使《龙沙剑传奇》做到前后照应,结构严密,程煐打破了这种结构惯例,他安排副末太白星君在最后的第三十出再次登场,以照应“家门”部分,对此梦熊钓叟与浙西二吾居士评云:“开场用末,乃传奇定例。然不过表明通部大意,无穿入关目者,此却用做起结,弥见气脉贯通,结构紧密。”[10]18再如,“龙沙剑”作为道具在剧中出现照样起着勾连情节、密合结构的艺术功能,如第四出《说剑》的安排便体现了这种意图,故梦熊钓叟与浙西二吾居士评云:“标目是说剑,自应结到剑上。 此作文一定之法。”[10]36显然,评者认为程煐是以“作文之法”来安排戏曲结构。可以说,正是得益于程煐对八股结构技法的娴熟运用,才使《龙沙剑传奇》结构严谨而“血脉无处不贯通”(梦熊钓叟、二吾居士评语)[10]104。
其次,程煐还将八股文写作中经常运用的“虚实相间”之法用于戏曲创作。八股文家向来重视行文布局的虚实相生,武之望《新刻官版举业卮言》将“趣”作为八股衡文标准之一,他释“趣”为“意之所不尽而有余者是也”,而他指出要使文章有“趣”,须注意行文的“虚实之法”:“实不着相,虚不落空”,“有用实意发挥者,亦有用虚意游行者;有用实语衬贴者,亦有用虚语点缀者。”[12]很明显,文家之所以推崇虚实相间之法,是因为它可以使文章行文避免呆板僵滞,并能收到“意之所不尽而有余”的艺术效果。程煐对此心领神会,所以他才在剧作中对此加以巧妙利用。如第八出“投店”中【前腔】写女主人公萧绛云死里逃生后的境况,第一、二、四句直接写她落水后的窘迫情状,第三句则从周围“响凄凄飐不定的芦花”来间接衬托其凄冷感受,这就是对“虚实相间”之法的成功运用,故梦熊钓叟、二吾居士指出:“第一、第二、第四语俱从身上实写,第三语却空写一句芦花,并前后三语俱觉灵活”,认为“若板板排写四句,便无意味,于此可悟作文虚实相间之法”[10]50。这里评者认为虚实相间之法使行文“俱觉灵活”而耐人寻味;否则“若板板排写”,“便无意味”,并明确指出作者此法乃借鉴自“作文虚实相间之法”。
最后,程煐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对八股代言技巧也有所借鉴。代圣贤立言是八股文的根本任务,而戏曲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离不开代人物“立言”,即通过个性化语言来刻画人物,正是基于二者的相通性,清代许多戏曲评论家才喜欢用“立言”“声口”“口气”“口角”等八股代言术语来分析戏曲人物形象的声情口吻。李渔《闲情偶寄》“语求肖似”中所提出的“立心”说;张雍敬在论及戏曲人物塑造时所谓“夫文章至于肖其神情,肖其口角,而可喜可怒,可歌可哭,则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制艺之法,亦若是焉已矣”[7]1661,皆主张以八股代言技巧设身处地地悬揣戏曲人物心理,逼真形象地代人立言。这对于熟谙八股代言技巧的程煐并非难事,其《龙沙剑传奇》真正做到了为人物代言的个性化,例如,第五出《孽兴》中写妖蛟大王的张狂自大,其语言完全“是孽物口角”(梦熊钓叟、二吾居士评)[10]39。 第九出《妖宴》中【驮环着】写妖蛟与鱷鱼精狂妄自负、“夜郎自大,全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口吐狂言,完全是“一派妖魔口气”(梦熊钓叟、二吾居士评语)[10]55;【中吕过曲】是鱷鱼大王“闷来时,横吹噫吷;喜来时,头摇尾撇”一段唱词,作者紧扣其鱼性、妖性及人性,“活画出一鱼来”(梦熊钓叟、二吾居士评)[10]54。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八股文乃清代文人习用文体,其文人化特征自不待言,而举世“以文为曲”的戏曲观念促使程煐以八股“文法”取代传奇“戏法”,这自然使其《龙沙剑传奇》呈现出显著的文人化特征。
二、比兴象征,寄意遥深
因文字狱而罹祸的程煐内心必积聚一股抑郁不平之气,但对严酷文祸的深切感受、敏感的流人身份,都使他有所感触而不敢放胆直言,于是他只能以比兴寄托手法来隐晦曲折地表情达意。程煐在《读曲偶评》中自称其《龙沙剑传奇》是他“戊午年(1798)孟冬望,初到边城,侘傺无聊,饥寒交迫,偶拈许旌阳除妖及湘媪、李鹬之事合为一传,谱以九宫,不浃旬而三十出成焉”[10]12。程煐由江南流徙至陌生的荒寒之地,其特殊的身份、特定的创作心态,促使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不浃旬”)完成长达三十出的《龙沙剑传奇》,这些都意味着该剧绝非消遣之作。程煐从弟程虞卿深知其创作底里,他说:“(程煐)命途多蹇,侘傺无聊,触境兴怀,寤言不寐。身已投于有北,情犹协夫以南。寄怀优孟之场,略举神仙之事。”[10]142显然《龙沙剑传奇》是程煐“触境兴怀”、“寄怀优孟之场”之作,其中必有寄寓。嘉庆七年(1802),“浙西二吾居士”在为《龙沙剑传奇》作序时也指出,程煐因“其志悲”而“托于头陀,人莫之怜;托于传奇,人莫之赏;托于仙怪,人莫之省”[10]11,正因作者别有怀抱,寄托遥深,乃至评者遂有知音难觅之叹。崔恒宁《龙沙剑传奇》题词云:“读君所作龙沙剑,不作寻常艳曲看。”[10]60仍视该剧为别有寄托之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流戍卜奎的程煐与清初著名流人吕留良的后人交往密切,而吕氏后裔还为《龙沙剑传奇》题词,由此也可获知该剧的确寄托遥深。署名为“浙西吕肯堂”的《龙沙剑传奇题词》云:“李杜韩欧至诣深,忽从歌曲写幽襟。……一曲阳春谁解听,锦囊什袭待周郎。”[10]144他认为该剧因作者自写“幽襟”而“诣深”,有待索解。署名“浙西吕尚贤”的《龙沙剑传奇题词》亦云:“高山流水知音少,不是钟期漫与听。”[10]145他也将该剧视为寄怀幽微之作。 需要特别说明,这两位吕姓题词者乃吕留良后裔,这从两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首先,吕氏籍贯浙江嘉兴府隶属浙西,因此二人为《龙沙剑传奇》题词时便在名号前自署“浙西”。其次,判定二吕为吕氏后人是有文献可征的,据《吕氏宗谱叙》云:“晚村公之曾孙九房名耀先,谱名赞先,字肯堂,号凤台,书于讲习堂之南窗。”[13]由此可知,吕肯堂乃吕留良曾孙。嘉庆至道光间,吕氏后裔吕景儒在卜奎修建住宅,其中东屋两间即为吕氏讲习堂所在,《吕氏宗谱》即续修于此。雍正六年(1728)吕留良文字狱事发后,吕氏子孙共有四个支族三十余人被流徙卜奎,①参考《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百六十九、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四,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而吕氏后人遣戍卜奎后,“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末尝自屈也”[14],因此作为流人的程煐是有机会结识吕氏后人的。除吕肯堂外,吕景儒也“与程瑛相友善”[15]。据此,笔者认为吕景儒很可能就是吕尚贤;而评点者“浙西二吾居士”有可能就是吕留良后人,且不排除为吕肯堂、吕尚贤二人的可能性。早在程煐之前,吕氏后人因文字狱而被流戍至宁古塔,其后部分族人又流落至卜奎,他们与程煐罹祸原因相同且交谊深厚,应对程煐的创作心态有所了解,因此由他们的“题词”看,程煐借曲抒怀的创作动机毋庸置疑。
在戏曲观念上,程煐反对“直白语”,并对《桃花扇》“爽而伤直”(《读曲偶评》)[10]12的创作特色提出批评。从《龙沙剑传奇》本身看,程煐确实隐晦曲折地抒发了其作为流人的复杂心态。例如,第九出妖蛟的唱词确实耐人寻味:
【驮还著】笑书生怯怯,笑书生怯怯,怎一个童娃,撞入天罗,来探地穴,被缚何须多说。速将他脱尽皮毛,赤精精肢体割裂,砍骷髅、当馒头粉捏,抉眼珠、算荔枝果碟。
【驮环着】把华筵摆设,把华筵摆设,有的是美女芳心、文士柔肠、英雄热血:一例燔炰煎炙,海错山珍,霎时间杯盘罗列。也不管乾坤许大,也不论江山几叠、吹横沙、奋长鬣,甚西海瑶池、东皇贝阙。[10]55-56
这两支曲中的唱词都具有隐喻意义,故评者江右梦熊钓叟、浙西二吾居士皆以“警绝”“妙绝”[10]55提醒读者。其中的“书生”即指男主人公李鹬,这一人物形象带有作者自况的意味,所谓“天罗”“文士柔肠”云云,不禁使人联想到清代严酷的文化政策,可以说这是作者以隐晦曲折的比兴寄托手法,对当时文字狱背景下的文人生活情状作了真实反映。
程煐因被流徙荒寒之地而产生的虚幻心态和孤寂落寞情怀也寄寓剧中。浙西二吾居士《龙沙剑传奇序》在论及程煐当时的处境及其创作心态时说:“知之者奴之,不知者儒之。儒其名,奴其实也。名不敢居,实不可道,名实两忘,逃诸虚空,则曰头陀而已尔。 其境幻,其志悲矣!”[10]11流人的生活处境使“志悲”的程煐“逃诸虚空”而以头陀自居,自然剧中“境幻”之处不可避免。因此,程煐在剧作结尾自称“江左词人程瑞屏,廿年书剑叹飘零”,认为自己是“黑龙江上老奴星”;而该剧以悲剧结局,男女主人公在历经坎坷磨难后,没有走向清代传奇戏曲惯用的大团圆俗套,而是以遁入空门为结,这更是作者悲凉虚幻心境的曲折反映。再以第十一出《思夫》为例,肖绛云独自寄居樊夫人酒店,她在【越调过曲】中唱到:“则俺这未亡人如梦夫如醒,夜悠悠漏长人静。原来是走踈檐铁马弄冬丁,一星星西风送冷。伤感煞背乡离井,望中何处也,陇山青。兀自掩柴荆。”【尾声】:“听遥遥茅店声,一弄儿霜华月影。我就去拥孤衾,也只是常独醒。”所谓“未亡人”“背乡离井”“拥孤衾”“常独醒”都契合程煐的身世遭际,可见这两支曲都是他自道心曲之处,是其流寓北国之孤寂心境的真实写照。而【小桃红】一曲也值得玩味:“咱一个断肠人,无处不伤情,说不出心中病。”显然这些话也是作者的夫子自道,故评者江右梦熊钓叟、浙西二吾居士指出该剧“深深郁郁”[10]60,此可谓中的之语。
戏曲、小说一般被视为通俗文学,其实并不尽然。俗文学一般以读者为中心,尽量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文学作品作为文化商品的属性更为显著,其娱乐性、故事性比较突出;而雅文学则以作者为中心,意在抒情写意,其主体抒发色彩浓重。以此衡之,《龙沙剑传奇》应属于具有显著文人化特征的雅文学,因为身为流人的程煐在剧中有着强烈的主体抒发意识,乃属“有为而作”。
三、师古崇雅,用语典丽
传奇戏曲发展至清代,表现出明显的雅化倾向,而创作主体的变化是主要原因。戏曲本是市井通俗文化的产物,其早期语言以“本色”为主,故王骥德《曲律》“论家数”指出,“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观《琵琶》、《拜月》二记可见”[16]53。 以元杂剧为例,其创作队伍多为书会才人,混迹于勾栏瓦肆的剧作家为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追求戏曲语言的直白通俗,自然朴质而绝少雕饰,因此王国维称“元人以本色为长”[17]。可是,随着创作队伍的文人化,戏曲语言上的藻饰繁丽便取代了早期的质朴本色,正如王骥德所言,及至戏曲作家“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他认为戏曲“一涉藻绘,便蔽本来,然文人学士,积习未忘,不胜其靡,此体遂不能废”[16]61。的确,讲究藻饰的文人学士的介入使戏曲创作由本色而逐渐走向雅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用语典雅,辞采华美。《龙沙剑传奇》之所以表现出鲜明的文人化特色,正与程煐所秉持的师古崇雅之戏曲观念息息相关。程煐《读曲偶评》云:“王实甫《北西厢》圣矣,则诚中行,若士狂,石渠狷,其贤矣乎!”对王实甫、高明、汤显祖、吴炳等以“词采”见长的戏曲家大加赞赏,并自称要“望玉茗之雄丽”“步石渠之清华”[10]12,显然他推崇、师法的是“文采派”戏曲作家。同时,程煐《读曲偶评》在肯定《荆钗记》《拜月亭》“音律极严”的同时,却批评它们“以直白语为本色,如不文何!”[10]12这表明他不赞赏戏曲语言的直白浅俗而崇尚典雅绮丽的语体风格。
为此,程煐在剧中频繁使事用典,尽量避免浅白俚俗之语,这也使其戏曲语言表现出淳厚古雅的文人化特色。乾嘉时期,朴学大盛,与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人一样,程煐也具有深厚的学识,故其从弟程虞卿称他“骚情雅思,经熔史铸”[10]142,这为其在剧中大量用典使事提供了便利。如第十八出中女主人公萧绛云所唱【好姐姐】:“使君虽好,我罗敷本自有郎。心悲怆,做个绿珠投阁惭孙秀,乌鹊双飞愧宋王。”这支曲共有三处用典:“使君”句典出汉乐府《陌上桑》,“绿珠投阁”句典出宋乐史《绿珠传》,“乌鹊双飞”句典出干宝《搜神记》中的“韩平夫妇”。这些典故运用得巧妙自然,不仅切合了人物的身份与处境,更使戏曲语言文雅蕴藉。类似例子在剧中仍多,故梦熊钓叟、二吾居士在评点中对该剧语言之典雅多有称赞,像“一切典故韵脚自然奔凑”[10]71,“用事皆工稳熨帖之至”[10]90,“故知作佳文,原不在用僻典也”[10]131,等等,都是对《龙沙剑传奇》古雅曲辞的称赞。
程煐师法“文采派”,对《龙沙剑传奇》词采之华赡充满信心,故有“知文者赏其词”(《读曲偶评》)[10]12之谓。 江西梦熊子《龙沙剑传奇序》也称赞“是书高华雄丽,兼实甫、若士之长”[10]9,认为该剧兼有王实甫、汤显祖二位“文采派”大家戏曲语言之美。《龙沙剑传奇》文采斐然之处甚多,像第二十八出《拜章》中的【前腔】:“孤鹜落霞纤,秋水长天滟。腾阁敞晶帘,匡庐碧染。扑地闾阎,从此无危险,喜看他万井和风扬酒帘。”这里作者熔铸诗词韵语,可谓“笔歌墨舞,姿态横生”(梦熊钓叟、二吾居士评语)[10]9。 再如第十三出《探穴》中的【仙吕入双调过曲】:“五老峰头耸,千山伏处低。洞天真觉匡庐异,飞泉上接银河际,轻烟袅出香炉气。”其词语雄丽,情韵俱佳,与诗词无异,故评者以“雄健明丽,天骨开张,不减太白诗”[10]67赞之。无疑,华茂丰赡的词采进一步增强了《龙沙剑传奇》的文人化色彩。
说到底,程煐在《龙沙剑传奇》中频繁使事用典、追求词采华茂的创作倾向体现了乾嘉时期文人传奇的时代特色。焦循在《花部农谭》中指出,当时传奇戏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反不如花部“其词质直,虽妇孺亦能解”;他认为传奇戏曲“若徒逞其博洽,使闻者不知为何语”,则与“对驴而弹琴”[18]无异。焦循之言虽非专门针对程煐及其《龙沙剑传奇》而发,但从程煐对其他曲家“以直白语为本色”的贬斥态度看,其戏曲创作显然遵循的是“雅部”传统。如上所论,《龙沙剑传奇》带有显著的雅化特征,程煐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明显的炫才意识,而这正是导致这部传奇戏曲具有典型文人化特征的原因所在。
《龙沙剑传奇》实属“案头之作”而非“场上之曲”,其文学性超过了戏剧性,这也必然导致其显著的文人化特征。程煐初到卜奎时,当地戏剧演出活动不盛,这从署名为“乐城范毓祥”的《龙沙剑传奇题词》即可获知:“山歌野调满边城,谁识苏门鸾凤清;安得龟年来绝域,试将檀板按新声。”[10]144正因当时塞外不具备戏剧演出的条件,所以《龙沙剑传奇》没有被搬演的机会,仅以案头之作的形式在极少数人中间传播。换句话说,程煐在创作之初,就将《龙沙剑传奇》预设为“案头之作”而非“场上之曲”,他仅仅是为寄托自己的幽怀深衷而作。戏曲本应适合舞台演出,即“填词之设,专为登场”[19],但乾嘉时期,戏曲创作领域却出现了明显的“反剧场化”倾向,如王懋昭《三星圆》“例言”即云“兹集却不徒为梨园演唱起见”[20],这正是戏曲发展走向雅化而成为案头之作的结果,而程煐的《龙沙剑传奇》恰创作于这一特定时期。实际上,“以文为曲”的创作倾向也必然导致《龙沙剑传奇》和当时其他戏曲一样,最终演变为“案头文章,非场中剧本”[21]。戏曲以舞台性为基本文体特征,它一旦成为文人的案头之作,必然会趋向雅化而体现文人的审美趣味。
总之,程煐秉承了“以文为曲”的创作传统,以比兴寄托的方式来抒发其幽怀深衷,并坚持师古崇雅的戏曲观念,这些都导致《龙沙剑传奇》在艺术志趣上表现出显著的文人化特征。无疑,只有将《龙沙剑传奇》置于真实的历史语境,并切实联系作者特殊的人生遭际,才能正确把握其所体现的“文人化”这一最为显著的创作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