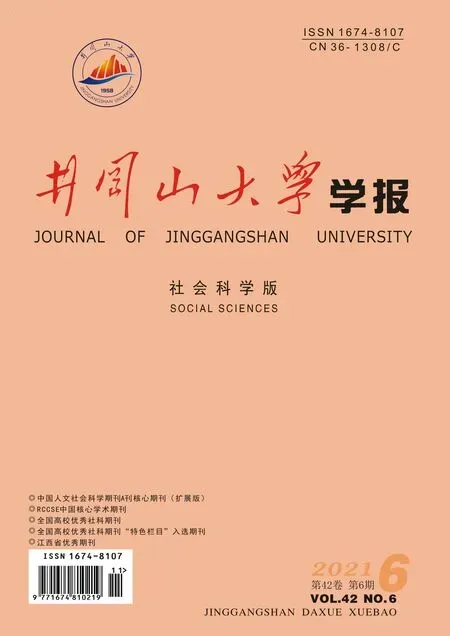白鹭洲书院的办学及其影响
2021-12-06邱炜耀
邱炜耀
(井冈山大学图书馆,江西 吉安 343009)
白鹭洲书院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古称庐陵郡、吉州、吉安府)城东赣江中流的白鹭洲上,南宋淳祐元年(1241)吉州知州江万里始创,此后千年弦歌不辍。书院践行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了文天祥、邓光荐、刘辰翁等大批爱国志士,同时引领庐陵士风,实施社会教化。作为区域文化教育高地,白鹭洲书院从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社会教化等方面影响了庐陵地区,培育了文章节义、崇文重教的庐陵文化精神。
一、教育理念及其影响
中国书院教育始于唐代,兴于两宋,盛于明清,在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书院作为一种教育机制,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文化与社会的演变。就办学理念而言,白鹭洲书院创办人江万里曾受业于白鹿洞书院,首任山长欧阳守道曾担任岳麓书院副山长,因此白鹭洲书院兴办之初,借鉴过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的办学理念,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办学特色。白鹭洲书院是一个集人才培养、学术创新为一体的文化组织,是以学者私人讲学为主,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教育机构。其办学理念彰显平民化,注重德育,突显学术性等特色,作为理学传播的重要阵地,对庐陵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书院教育的平民化
白鹭洲书院继承儒家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官学垄断,向下层社会生徒开放,打通了官学与民间教育的鸿沟,让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共同接受教育。首任山长欧阳守道说:“三代国都乡党之学无所与于岩穴之士,后世山中之教不出于上之人主张,而今日兼之,我宋文风于是最盛矣。”[1](P99)他认为平民化教育是宋代文教兴盛的重要标志。白鹭洲书院的教育对象广泛,市井樵夫子弟,也在其列,为解决平民生徒的学费问题,在书院创建之初,江万里就“置田租八百石有奇,绕城壕池,岁入租银五十两赡学”[1](P10)。《罗太守馆规十三则》其一《供给》亦说:“长住房舍朝夕不离者,本府量助供给,各人每月给钱三百文,给米一斛,按期给发。”[2]
白鹭洲书院教育的平民化,又体现于师生民主和教学民主。欧阳守道《白鹭洲书院山长厅记》回忆学院初立时,“山长未有人,先生(江万里)亲为诸生讲授,载色载笑,与从容水竹间,忘其为太守、古诸侯。”在日常教学研讨中,书院不将入师门先后作为论资排辈标准,而是能者为师,凡品学兼优者都有机会参与教学。白鹭洲书院的教育平民化,也体现于学生来去自由,自主择师,师生耕读相兼,共同创建书院,开办校舍,置办田租等。师生之间还相互协作,刊印书籍等。[3]
受白鹭洲书院平民化教育的影响,庐陵地区书院教育迅速繁荣起来,发展成为三级教育构成的多层次体系。据元末史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4]统计,吉安有名可循的书院有408所,大都出现在南宋之后。宋代庐陵书院的发展明显超越官学,这些书院大都分布在乡村,由乡绅乡民集资创办,都向社会下层民众开放,书院学习没有固定年限,生源没有年龄和地域的限制。各县乡书院为保障平民子弟的受教育权利,纷纷设立义塾,提供生徒食宿费用,并且减免家境困难者学费。元人欧阳玄说:“义塾既作,一乡之士患不志于学,不患无从师之资;一塾之师不患学者之不勤,不患供亿之不继。 ”[5](P145)
(二)书院教育的德育观
白鹭洲书院的办学,特别注重道德品德教育。其道德教育也曾借鉴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的经验,保持理学教育的特色。江万里曾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张贴在白鹭洲道心堂,作为书院办学指导思想。后来又根据书院自身实际,不断细化优化德育馆规。白鹭洲书院完备的德育体系,逐渐形成自身办学的鲜明特点。其德育课程设置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历史典籍为补充。基本教材是《四书》《五经》,同时辅以历史典籍。以史学教材作为镜子,鉴古知今,有助于生徒的开拓视野,涵养儒家人伦道德的品性。白鹭洲书院生徒学习的历史典籍主要有《左传》、《尚书》、《汉书》等。
其德育课程设置又一原则,是重理学、明人伦。欧阳守道说:“世道以人心为主,读书为士,不得不以世道为己任”[6],强调弟子首先要懂得做人的道理,明人伦是一个人立身处事的根本,是古圣先贤教育人一脉相承的传统。白鹭洲书院先后建筑文宣王(孔子)殿、棂星门、云章阁(藏书楼)、道心堂、万竹堂、风月楼、浴沂亭、斋舍、庖廪和六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朱熹等理学名儒)祠等,以先哲先贤建树人伦道德典范。又通过理学课程传授人伦之至的道理,敦促生徒尊德性,明人伦,以达到圣贤教育之目标。
白鹭洲书院的德育教育体系中,也注重个体的因材施教,随人指授,日常考核等原则,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教师常常根据学生的爱好和特长组织教学,并且实行分年教育,把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坚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汪可受说:“诸生各立日课簿,每日将用过功夫登进簿内,诸生各随意力量,但要日有日功,月不忘之。本府将无时抽签稽查。”[7]书院对学生的德育考评,实行簿书制度,簿书详列其目,简而不略,要而易遵,由书院各级负责人纠察生徒的品行善过而登记之。
白鹭洲书院德育课程的开设,以史为鉴,明人伦,尊德性,“崇祀”展礼等德育培育手段,对庐陵各县乡书院教学有示范作用。庐陵各级书院的德育观,对生徒爱国主义观念的形成,理学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促进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书院教育的学术性
白鹭洲书院办学特别注重学术性。白鹭洲既是学习的地方,又是理论研讨的场所。创办人江万里是朱熹门人林夔孙的弟子,书院继承了朱熹的教学理念,鼓励百家争鸣,倡行包容精神。白鹭洲书院曾是朱熹和二程的过化之地,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但几人师承不同,具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书院曾对诸多问题开展会讲,范伯崇曾为其陪侍的学生,记述“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书院实行开放教学,硕学鸿儒在不同的书院进行巡回讲学,而在书院内部,书院的领导者也倡导思想独立的学术观点,据苗春德的《宋代教育》一书记载,白鹭洲书院平日教学以自学为主,生员每人各自立日课,强调生员自学,自行理会,相互切磋,彼此质疑问难更是师生群居间的日课,形成白鹭洲书院教学民主与学术氛围浓厚的鲜明特色。[8]
在中国书院史上,白鹭洲书院讲会制度名闻遐迩。讲会制度是书院彰显学术性的重要方式,书院讲会不仅有师生参加,还有社会名士参与。白鹭洲书院的讲会是定期举行的一种聚会讲学,是一种长期稳定、制度化的教学形式。讲会中还有一种“会讲”的方式,大多由著名大师和大儒聚会发起,书院为不同学派和不同观点自由辩论和探讨提供良好的平台。明清时期,白鹭洲书院主办过各种讲学活动,邹元标、王时槐、贺沚等理学名家,先后在白鹭洲讲会或辩论,探讨程朱理学与王门心学,各种思潮在此交融碰撞,成为江西学术史上的盛事。白鹭洲书院讲会最典型的是施闰章主持的白鹭洲辩论。康熙初年,湖南儒士杨洪才率徒数人专程到白鹭洲书院讲授阳明心学,施闰章邀请退居崇仁的原白鹭洲书院山长毛奇龄与杨氏辩论三天,施闰章和乡绅学士张贞生、张自勋也讲学其中。施闰章将辩论内容做了记录,毛奇龄又据施氏记录中涉及《诗经》部分的内容,辑为《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白鹭洲书院的讲会不仅丰富教学内容,活跃学术空气,而且有利于扩大书院的影响,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大展其才。
书院的基本功能,除讲学外还有藏书。白鹭洲书院云章阁本为藏书楼。据《白鹭洲书院志》卷二《书籍》记载,清代白鹭洲书院藏书“有明八家、四家外,其诸名家选本及专稿不可枚举。”从其列举经、史、子、集篇目,有一百余种。然而,到同治十年(1871)刘绎编《白鹭洲书院志》时“存者不过十之一”,他由此感慨说:“典守者谁?不得辞其责矣!”白鹭洲书院的印书业也曾引人注目,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白鹭洲书院刻印《汉书集注》100卷、《后汉书》90卷、《志注补》30卷,被刻书界奉为“圣本”。
二、人才培养及其影响
白鹭洲书院的办学始终将人才培养置于首位,又以培养文章节义之士而闻名于世,它培养了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邹元标、杨邦等一大批爱国志士,其中以文天祥最为著名。文天祥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尽管他在白鹭洲书院求学时间只有一年,但其思想的形成与白鹭洲书院息息相关。白鹭洲书院的教育造就了后来的文天祥,文天祥用自己的言行扩大了白鹭洲书院的声誉。正是由于培养出了文天祥、邓光荐、刘辰翁等爱国志士,白鹭洲书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才培养特色,即三个注重:注重气节,注重立志,注重人格。
(一)注重气节
气节是人的志气和节操,指坚持正义,在敌人或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品质。白鹭洲书院的人才培养注重气节教育,书院创始者江万里一生风节自持,在民族危亡之时,以身殉国,率领全家投水自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夫效忠而忘其身,是固臣子大义。”[9]江万里也非常重视书院生徒的气节教养,气节教养贯穿于白鹭洲书院的日常教学与管理,并长期坚持,蔚为书院风气。刘辰翁《白鹭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说:“自鹭洲兴而后,斯人宿于义理,自鹭洲兴而后,言义理者畅,……而后立身名节,一以先生台谏为风采,推论人物,长育之。”[10](P154)
欧阳守道也认为,人之气节由养以成。其《三勿堂秘》指出:“浩然也者,盖人人所同有。惟其有之,故可养也。”[11](P154)气节是一个不断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个人持之以恒的自我磨练。他认为君子要在贫穷面前保持气节,对待功名要以大义为重,名节重于泰山,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之际的紧要关头,要践行孔孟杀生成仁的理想。其《代贺王师遂啓》云:“皦乎白日,孤忠结明主之知;凛然清风,气节激懦夫之立。”[12](P151)表达心系南宋朝廷的孤忠气节。在欧阳守道倡导下,白鹭洲书院将气节教育作为书院教学的重点,认为浩然之气根植于人性,培养崇高的气节应当顺应自然。主张自强不息,不断磨练以保持崇高气节。正是由于江万里、欧阳守道等书院名师的率先垂范,才有了文天祥后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有了“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崇高气节。
白鹭洲书院的气节教育,增强了庐陵地区士人的爱国情怀,增强了庐陵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对庐陵士人弘扬正气,坚持真理,追求公平正义,产生了广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注重立志
白鹭洲书院继承了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十分关心生徒的志向和抱负,认为远大的志向来自远大的理想,人在青年时期就应该树立远大的抱负。欧阳守道强调弟子成材务必立志,其《张南轩回周益公书》说“若志不先立,即为自弃,尚何所进哉!”[13](P141)其《送彭士安序》又强调弟子们养气必先立志。立何种志?他主张应当学习圣贤,以天下为己任,说:“贵立志,非志富贵也,信圣贤之言而期于有立,不以贫厄更所守,斯之谓志。”[14](P151)正是这种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少年文天祥出入学宫,仰慕四忠一节,说道:“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也正是因为书院对学生的这种励志教育,才形成了文天祥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才使得文天祥成为了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
历代白鹭洲书院院规,都强调办学目的并非为科举功名。明万历间知府汪可受《馆例》说:“本府所属望诸生,不独以文章取科第而已,愿以行己有耻为士人第一义。”[7](P142)清康熙年间,知府罗京制定的《馆规》也重申:“本府属望诸生,不独以文章取科名而已,愿以行己有耻为士人第一义。”历代讲师也都立志圣贤之学,做道德高尚之人。《白鹭洲书院志》施闰章《书院讲义》开章说:“学者首辨志,志必向道。”《孔山长学说四则》其一也说:“学莫先于立志。志圣贤之志,方为学圣贤之学。”[15](P151)可见立德重于立功与立言,人品高于文品,这是历代白鹭洲书院的办学主旨。七百余年来,这种办学理念从未偏离。
白鹭洲书院的立志教育为社会树立了道德楷模,提供了道德实践的行为模式,所数百年间为庐陵地区书院所效仿。白鹭洲书院把立志教育放在首位,影响了吉安的各县书院。书院的励志教育非常重视人文关怀,反复宣传天理人心,这种教育对庐陵地区的士子树立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三)注重人格
白鹭洲书院继承历代先哲的教育传统,崇尚人格塑造,把人格作为道德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书院教育体系。人格修养是一个自我选择、自我负责、自我支配的过程,白鹭洲书院继承并强化朱熹的居敬理念。书院创办人江万里以为居敬为万善之根本,是人格修养的前提;其次是涵养,是修养心性的重要方法;再次是省察,即自我反省,是最终成就圣贤人格的关键。
历代白鹭洲书院之师长,都坚持言传身教并重。书院创建之初,江万里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亲自为生徒授课。在生命最后时刻,拒绝降元,将舍生取义融入理想人格当中。欧阳守道亦是生徒的学师行范,文天祥在《巽斋先生像赞》中称其“横经论道,一世宗师”其书简《与刘吉州汉传》亦说:“先生之风,可使懦夫立也”[16](P155),《回秘书巽斋欧阳先生》自称受益终生,欧阳守道对自己立身处世的影响是“后生从政,未知向风,惟先生终教之耳”。清乾隆间庐陵知县周作哲《白鹭洲书院志序》也说道:“书院每月三课,余参襄一次,见多士争自濯磨,惴惴焉惧辜贤大夫雅望。”[17]P155)而每逢节令的祭祀活动,亦是白鹭洲书院人格养成的重要手段。书院设立的文宣王庙、道心堂、六君子祠,能让学子近距离看到圣贤形象,对其人格产生强烈震撼。白鹭洲书院的教育,对文天祥、邓光荐、刘辰翁、邹元标等忠节志士的人格修养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可见在书院师长言传身教下,学子们以浩然正气的师长、先哲为楷模,养成其高尚之人格。
白鹭洲书院的人格教育,对庐陵地区士子人格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白鹭洲书院的人格教育的核心内涵,它深刻地影响了王守仁、邹守益、聂豹、欧阳德、罗洪先等“阳明书院”五贤,还广泛地影响了庐陵各县乡书院的学子,这些学子不乏人格高尚的爱国志士,如泰和的杨士奇、郭子章,吉水的王艮、邹元标等,龙泉的张彦方。白鹭洲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庐陵地区各级书院的气节教育、立志教育、人格教育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庐陵地区节义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三、社会教化及其影响
社会教化是我国古代一种上对下的意识形态宣教,它通过一定的途径对百姓进行教育感化,其内容是政治化的伦理道德,目的是使全社会形成良好风尚,使社会成员按照社会管理者拟定的规范行事,最终达成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古代书院生徒的出路,一部分通过科举考入仕途,挤进社会官僚系统,更多的则是回到民间,成为乡绅。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乡村基本上由乡绅自治,回乡的书院生徒,往往是农村社会的中坚分子,也是社会教化的中坚力量。因此书院办学与社会教化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书院教育是实行社会教化的重要途径。白鹭洲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主要表现在儒释道三兼融、学思行三结合、文教化三统一等方面,对庐陵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儒、释、道三兼融
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方的正统思想,但随着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及东汉末年道教的产生,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了排挤和侵压,引发了儒释道之间的斗争。在历经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动乱,民族大融合之后,儒释道日渐融合,在宋代出现了三教并隆的景象。江万里兴建白鹭洲书院,正是三教融合,理学兴隆之时,白鹭洲书院就是三教融合的产物。
在书院的选址上,白鹭洲书院深受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白鹭洲自古为禅林之所,洲上有僧人修行布道,后为佛教净土庵道场,知吉州江万里见洲上茂林修竹,清幽雅静,是办学佳地,便劝导寺僧让出大片空地,在庵旁创建书院。理学家修建校舍,常选择环境优雅的风景名胜地,以为这种幽静的环境能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儒家学说尊崇天人合一的理念,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追求道德与学问相互渗透。书院选址在山林名胜地,有利于排除外界干扰,使人心无旁鹜,沉迷于学问研究和道德磨砺。刘学朱《白鹭洲净土庵记》[18](P145)记载,吉安知府汪可受在修复白鹭洲书院时,应僧人之请,在吉台东侧修复净土庵。理由是御水护台,其书院约禁也说:“江洲无烟火之地,特设净土庵旁守书院。”刘应秋《重修白鹭洲书院记》亦记载:“高称台,倚台而东建庵,曰净土,沙门守之。”[19](P145)千年白鹭洲上,弦诵钟鼓相闻,书香檀烟袅袅,成为儒释同修之地。
白鹭洲书院在学规,教学制度,组织管理等方面,也受到佛道的影响,佛教以清规戒律管理僧徒的诵经、讲学与生活,白鹭洲书院的讲学制度仿效佛教讲经和禅林制度。李梦阳《白鹿洞书院志》说:“书院讲学或者会讲都要有一定的仪式规定,比如行初至礼,讲毕方饮食进茶等。”[20](P145)如白鹭洲书院的开讲仪式和升堂讲说”。《文献通考·书院》记载说:“在寺院里,讲学之前,按照佛典的规定,需要敬礼佛、法、僧三宝”。[21](P145)儒家讲学并无此举,但书院兴盛之后,这类仪式开始形成,即开讲之前,须由山长、副讲等带领学生到大成殿向“先师”神位四拜。然后才能“登讲席、三肃揖、鸣讲鼓”,开始正式的讲课。此类学规、仪礼显然受佛道规戒影响。
白鹭洲书院的儒释道三兼融深刻影响了青原会馆,永丰的恩江书院、泷冈书院,富田的能仁书院等。以永丰恩江书院为例,恩江书院在学宫的西边,原为报恩寺。嘉靖年间,僧徒寥落,寺宇渐废,始议谋建书院于此地。这些书院建设是统治者崇尚文治的表现,也是统治者思想包容的重要举措,儒释道三兼融对庐陵地区的学术风气与社会教化具有深远影响。
(二)学、思、行三结合
学思行三结合是指学习、思考、实践三者的有机统一。学思行三结合是中国儒家传统强调的重要思想,孔子《论语·为政》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里仁》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说主张为学修行,都要必须坚持学、思、行三结合。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学、思、行三结合成为书院办学的重要教育理念。
白鹭洲书院教学的重要特色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欧阳守道高度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主张在学习要认真读书,独立思考,质疑问难,辨察是非,遵从陆九渊“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白鹭洲书院在教学方法上又主张经世致用,要求弟子勤学审思,坚持学思并重的原则,同时践履躬行,参加实践锻炼,将所学所思运用到实践中去。如此学生方能学得真知,教师方能做到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教学与研究共发展。
白鹭洲书院继承朱熹、陆九渊学思并重相结合的思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倡导学思并进的理念。书院主张启发诱导,教学方法不拘一格,采取升堂讲说、读书思考、祭祀展礼、优游山水等多种学习方法和教育手段,尤其是书院生员之间时时相互切磋,师生之间常常质疑问难,成为师生群居的一种日课,学、思、行三结合的教学法,取得了务实求真的学习成效。
学、思、行三结合也是白鹭洲书院师生共同的教学传统,江万里当年执教书院时就曾“勤劳恭谨,以身先之”,据《江万里文集·言行拾遗事录》记载,江万里“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22](P150)而白鹭洲书院生徒的学、思、行三结合,更体现在历代“馆规”“馆例”中。如《罗太守馆规十三则》之七说:“须要晓得心上是书,世上是书,不止纸上是以心、身体认,道理则得之矣。”强调的就是学习过程中学、思、行三结合的重要性。
白鹭洲书院学思行三结合的教育理念,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知行合一的品格,白鹭洲书院的教学法影响了吉安地区的教育,也对庐陵地区的学风民风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文、教、化三统一
庐陵地区历来就有文、教、化三统一的传统,自唐代杜审言、颜真卿贬官吉州庐陵郡后,渐兴文教,至宋代终成“崇文”“重教”风气。宋代的右文国策,助升了庐陵地区的“尊师”“重道”,而由文化人管理村社的结果,形成强大的区域教化功能。宋明理学的形成,“江右王学”在区域内的兴盛,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江万里创建白鹭洲书院,将书院作为理学传播的基地,与庐陵地区注重教民化俗的传统相结合,较好地实施了文、教、化三统一。
在白鹭洲书院影响下,庐陵地区书院相望,文教繁荣,崇文重教蔚成风气。江万里重视办学育才,说:“夫善国者,必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以地方长官兼办书院教育,格外重视教化。特别是劝俗教化,江万里认为“安利之要不在于他,在乎正风俗而已,故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23](P150)认为地方官就是应该尽己所能,推动任职地的社会教化,关注平民疾苦,而随着地方风俗的改善,社会必然出现父诫其子,兄勉其弟,从而达到人心日厚,民俗日淳,争讼日少,刑罚日清的和谐世道。江万里将书院教育作为从政的第一要务,而办教育的宗旨之一就是促教化。为促进教化,他强调经世致用,乱世之中要挺身而出,维护儒家纲常。文天祥《祭欧阳巽斋先生》说道:“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敢以书谢?然弟子于先生,不取其私谢,而取其不负。”“何谓幸?亲见先生而师之是也……沐其教,嗜其学,负之尤不可。 ”[24](P150)
庐陵地区的传统产业,以农耕而养天下,封建统治者为兴邦固本,以利于治民,也会颁布劝农诏,进行劝农教化。江万里在吉州知州任上,注重农事,也做《劝农文》,但他改变一般《劝农文》内容空洞、不切实际的弊病,而是言之有物,其中说道:“州皆有劝农文,父老听来似不闻,只为空言难感动,须将实写殷勤。使君元起自锄犁,田野辛勤事总知,要为尔民除十害,肯容苛政夺三时。”确是一篇有益乡村教化的好文章。
阳明书院的社会教化,深受白鹭洲书院的影响,阳明书院的山长刘绎在创办阳明书院之初,就把兴教化作为首要任务。受白鹭洲书院的影响,刘绎把祭祀圣贤作为一项重要教学活动,亲自撰写祭文。通过祭祀活动,对生徒进行道德、礼仪方面的教育。受白鹭洲书院的影响,刘绎积极推动公益事业,在吉州建立社仓并把在吉州建立社仓的经验加以推广,以造福更多贫寒农户。由此可见,白鹭洲书院的注重社会教化,影响了吉安地区书院的发展,而书院文、教、化三统一的教育制度,促进了庐陵地区的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