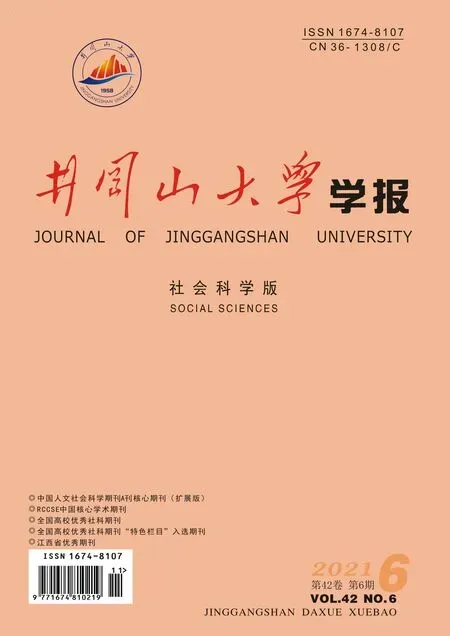论周必大诗歌的禅趣
2021-12-06相明霏
相明霏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作为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周必大为政忠直,官拜左相;为文亦绝,著作等身。有关他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文献整理、生平、家世、交游、文学等方面,较少涉及其思想研究。现存周必大思想研究多围绕其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等身份展开。如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则提到周必大的理学思想,认为周必大在学术思想、政治举措等方面与孝宗时期四大理学宗师互相尊重、彼此支持,同时也对“道学”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1]。而许浩然在《思想与政治——周必大与理学关系考辨》中对余英时的论述提出了异议,认为周必大与理学的关系是一个变动的过程,不能简单将其划归为理学家,其最终的思想立场当归结为北宋儒学治道理念,最终的政治立场归结为官僚派[2]。他的《周必大的历史世界 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士人关系之研究》[3]中也多是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出发去探究周必大的思想内涵。而周必大思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主要有李光生的《周必大研究》[4],其中第四、五章分别讨论了周必大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主要围绕其儒家思想中的知行观和文学思想中的明道、理气等批评展开,认为其思想对南宋文坛甚至后世文坛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王瑞来的《“圣经元自许传疑”——周必大儒学思想例论》[5]则从周必大诗文作品出发对其儒学思想进行了系统地讨论。在学界对周必大各类思想展开研讨之时,却忽略了周必大思想中的佛禅因素。现存有关周必大佛学思想的研究唯王瑞来的《周必大集校证》及刘艳芳的《佛禅对陆游诗歌创作的影响》中稍有提及:前者在前言中提到:“周必大通达世事,还要来自佛教的影响。”[6](P36)后者则将周必大列为“涉佛文士”,从与陆游的诗文互动中分析周必大佛学思想对他的影响[7]。但二者都未能深入探讨其文学创作与佛学思想的关系。本文拟从周必大的诗歌出发,探求周必大的佛禅因缘、佛学思想及其对周必大诗歌创作艺术的影响。
一、周必大的佛学因缘
周必大虽自认“予非学佛者”[6](P591),然其文集中却多有与佛教相关的作品:有参与佛禅活动的《赠崇寿寺僧善修》;有与僧人相交往的《祥符长老智华写余真求赞》;有佛禅思想浓厚的《次韵邹德章监簿官舍芙蓉芭蕉》。此外,《省斋文稿四十》及《平园续稿四十》中亦专门收录其所作的与佛教有关的颂、偈、赞等文章三十多篇。这些情况都表明,周必大思想中含有一定的佛学因素。
周必大接受佛学思想的原因或许有四:一是时代因素。由于宋代统治者的首倡,僧人和儒士的共同努力,三教合一的思想得以进一步深化,士大夫禅悦之风盛行。二是地域因素。周必大自幼长在佛教氛围浓厚的江西,东晋高僧慧远居于庐山,在庐山修禅讲法;唐代高僧青原行思就是庐陵人,在吉州青原山静居寺传法,他们为江西佛教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周必大自然受其影响。三是交游经历。周必大出游时有寺必访,遇僧必交。如《南归录》中载周必大于乾道壬辰二月丙辰至六月庚申南归吉水途中所游所见,他一路访崇先院,与知事净云共菜饭而归;访净慧禅院,为外舅作忌辰;访崇福寺,同主僧共游仔园亭;访灵严山下廨院,与长老共登山……似乎只要有机会就与寺中主僧饮茶聊天、共游共斋。同时,他与陆游、杨万里、朱熹、范成大、葛谦问等具有佛学修养的文人居士相交往,甚至与大师宗杲也有往来。四是学习经历。周必大善于学习先贤,他以陶渊明、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为师,而这些先贤或主动学习佛法,或被动受其影响,周必大在向先贤学习的过程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他们的佛学思想。
然周必大对佛学并不是全盘接受,佛学思想也并没有改变他的基本人生准则,但确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其在经历仕宦沉浮时,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翻阅周必大的诗文作品,可基本勾勒出他对佛学的态度:
首先是“近佛用禅”,以佛学慰藉心灵。与石介、朱熹等宋代著名的排佛者不同的是,周必大对待佛教的态度是理性的,他认为“儒与释异,兹一理也。”[6](P593)周必大主张佛儒相通,特别是在对人生、人性及社会进行思考时,佛儒有着共同之处:如他在《题赵清献公帖》中提出:“儒书释书虽异,而欲人求放心、复本性则同。”[6](P740)是从心性的角度出发看二者的共同点。《袁州宜春台孚惠新祠记》中的:“大而天地,明而为人,寂灭者佛,变化者神。虽曰殊途,然而仁民爱物之性,善善恶恶之情,未尝不均。”[6](P881)则主要是从仁爱的角度出发看二者的相似之处。这种将儒释结合的态度也给在官场沉浮的周必大带去了诸多慰藉。结合周必大的个人经历和诗文创作来看,他一生中创作与佛教相关的诗文较集中于隆兴元年至乾道六年、乾道八年至九年两次贬谪时期以及晚年时,可见佛学对他的主要影响就是借佛学寻求心灵的慰藉,正如他在《跋苏黄门在筠州施楞严標指》中说的:“……十年来渐参悟佛法,经历忧患,真心不乱。今翻覆熟读,乃知诸佛惠我无生法忍,无漏胜果,愿心心护持,勿令失坠。”[6](P768)佛教使他在现实世界中经历苦难忧患时仍能持有乐之精神。
此外,周必大还通过助寺拜佛等方式来为己为人祈福,以达到心之安定。在《赠崇寿寺僧善修》中他吟咏到:“我得九华充法供,亦能禁足老山间。”[6](P52)这是通过捐助寺庙的行为来为自身祈祷。除了助寺之外,也直接去寺庙祈福。如《荐尚氏姊水陆文》是为其亡姐诚心祈祷之作:“消亡者尘尘劫劫之罪愆,释亡者世世生生之冤业。受人天之至乐,慰手足之深悲。”[6](P547)通过为亲人书写疏文以求得生者心安,亡者轮回。周必大自幼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而随着三教合一的推进,佛教也逐渐关注“孝”论,如契嵩就提出了儒家“孝”之外的“大孝”,“是以灵魂不死、三世轮回为前提,孝亲的范围达到‘七世’,并且将人世之孝推广到一切众生。”[8](P211)这就给周必大在儒家之外找到了另一种践行孝悌之道的方式。此外,他笔下的一些祈雨、祈晴文,都是借助佛教,以求风调雨顺、百姓安康,也表现出了他心系天下的热忱。可以看出,周必大近佛一是出于利己的,欲为内心在现实世间寻求一处安顿之所;二是出于利他的,欲使其那颗孝悌友爱、救世爱民之心得以在儒家学说之外借助其他手段继续表达对亲友、社会的关怀。
其次又“远佛逃禅”,不愿经参禅悟道之苦。周必大也在诗文中表现出不愿经参禅悟道之苦的佛教态度。他认为遵守戒律是苦的:在《柴冀秀才著书求跋语》中他明确写到“夫谈禅不必病戒律,用兵不必废行伍。 ”[6](P198)这与苏轼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观点相类似。他认为割断尘俗是苦的:在《寒岩升禅师塔铭》中他写到“迹夫舍父母之养,割妻子之爱,无名利爵禄之念,日夜所求谓苦空寂灭之乐于山巅水涯人迹罕至之处,斯亦难矣。”[6](P594)他难以理解也不能做到僧人断念绝爱之行为,他希望轻松学佛。在《跋此庵记》中他写到:“侍读胡公平生未尝启梵夹,效膜拜……而词理超诣,便得儒释之妙。正使三十年默照坐破蒲团,一万里行脚踏尽草履,恐亦未能到此地位。”[6](P204)他夸赞胡铨不读梵经、不坐蒲团、不行万里仍能达到佛学高深之境界,从侧面反映了他不吃“参禅之苦”而悟得佛法的愿望。《天池观文殊灯》一诗也体现了他欲“偷懒学禅”的想法,诗曰:“一灯别是真知识,不用奔波学善财。”[6](P53)根据《华严经》的记载,善财童子向文殊菩萨学佛法时,文殊菩萨让他参见了五十三位大师、菩萨、波罗门、仙人,最后才得见普贤,终得佛法。周必大这首诗便是说观文殊灯便可获得佛法智慧,无需像善财童子那样奔波劳累。这些都反映出了周必大欲打破传统佛学的修行方式和戒律规定而接受佛学思想的愿望。如此,主张顿悟成佛、宽松戒律仪式的禅宗就成了周必大的首选,他的这种佛学态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最为明显的就是诗歌中蕴含的般若空观。
二、周必大诗歌中的禅趣
禅宗“佛法即是世法”理论让宋代士大夫知晓参禅和生活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既不会让其抛弃儒家思想,亦不会影响其世俗生活。与周必大来往较为密切的著名禅师宗杲就曾说:“佛自有言‘不坏世间相而谈实相’,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往。’”[9](P694)强调佛法不离世间法。如此,禅宗思想逐渐渗入宋代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作为诗文创作主力军的宋代士大夫参禅人数也越来越多,以禅作诗的风气也随之愈加浓厚,周必大的诗文创作也深受此风影响,从他的诗歌中常可寻见具有佛学意趣的内容。
佛教的目的就是普渡众生,帮助个人超越痛苦以达彼岸。而众生的苦厄,有自身生老病死,也有外在的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盛等。众生若深刻了解“五蕴皆空”,破除我执,即可达到通达旷达之境。[10](P70-71)这种思想对周必大产生了诸多影响。周必大的诗歌中不乏借助禅宗思想来抒发自己感情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虽对佛教“诸行无常”有着深切体会,并予以哀吟;但却又能通过“不二法门”,悟得“般若空观”,放下一切,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清直洒脱的性格。具体说来,周必大诗歌中主要有对仕宦沉浮、寿命短暂及亲友分别三方面的感叹。
一是仕宦沉浮之哀叹与般若空观。周必大一生虽位及人臣,但也遭受仕宦的不顺,曾于隆兴元年三月因曾觌、龙大渊事奉辞归乡,其间有“迂儒岂足助维新,日奉威颜谢主臣。”[6](P35)的哀叹,后乾道八年又因张说、王之奇事归乡。此后仕途虽较平顺,但也曾被弹劾、遇党争、遭禁锢。他在《过邬子湖》一诗中他就感叹官场的险恶“从来仕路风波恶,却是江神不世情。”[6](P74)但周必大始终是积极乐观,无论是隆兴元年三月奉祠还乡期间写下的《归庐陵日记》《闲居录》,还是乾道八年二月再次还乡期间写下的《南归录》,都体现了周必大面对官场沉浮时始终怀抱“寸心悬日月,不为去来移。”[6](P25)的通达思想。在从关中到江西这条漫长的道路上,几乎不见他对仕途不顺的哀吟和命运不公的抱怨,反而是抱着随缘的心态去游山玩水。这种随缘心态在他的诗歌中具体体现为参禅坐忘,静心净心。在第一次归乡期间,除了访寺求仙之外,他也自觉参禅,他写下《次韵广东芮漕时闻其部中寇退而湖湘之民方避地来此》,其二曰:
病废壶觞懒废诗,渐参禅悦学希夷。志非鸿鹄宁憎燕,路怯豺狼更畏狸。
节物匆匆愁里度,人情扰扰静中知。已营二顷亲籉笠,何日三间看塈茨。[6](P40)
诗歌明确表达了其在困境中通过“渐参禅悦学希夷”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定,有了归隐之思,思想也更为通达。恐怕正是这期间的参禅活动,让他接受了佛教的般若空观的思想。此外,周必大两次归庐陵期间的诗作中也有部分体现了佛教思想,如《登龟山》写到“注坡缘壁化城中,客愠奴嗔我亦慵。”[6](P51)不仅化用了“化城”之典,还写出了作者自身闲适慵懒、不愠不火的状态,似乎佛教已经助他忘却了对仕宦的执着,达到了随缘任运的状态。
二是人生短暂之无奈与般若空观。除了有仕宦沉浮的漂泊之感外,人之生老病死的幻灭无常也时常困扰周必大。他有生命无常的感叹“多才多艺无多寿,此理凭谁问大钧?”[6](P88)在不得不面对人生无多寿的现实之后,又有时间飞逝的感叹“年华飞电过,耆德晓星稀。”[6](P102)但他的《柬达上座颂一首枕上补作》一诗却化解了他自己的困扰:“剑峰有时折,瀑水有时竭。我性等虚空,今古无生灭。”[6](P589)将人之生灭与山峰之折、瀑水之竭相较,明确表达了“性空”的思想,整首诗歌与般若空观的意旨十分契合。面对人的生老病死之苦,佛教以“五蕴皆空”的要旨来助人得以解脱,帮助凡人认清“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11](P37)的事实,度众生苦厄,卸下心灵的枷锁,获得身心自由,周必大此诗便是在这种般若空思想影响下写成的。周必大对待生命始终拥有乐观的态度,即使是他晚年的诗歌也很少看到生命之叹,反而多是闲适之情,如《游元龄登仕写予真求赞》:“休夸岁岁花相似,莫叹年年貌不同。闲伴长松与龟鹤,免将开落问东风。”[6](P670)此时76岁高龄的周必大,或许已经忘却了时光的流逝,仍持与松鹤比寿的闲心乐趣,享受当下的生活,通达洒脱。又如《法华院僧祖月写余真戏赞》“老子七十七,到处遮人壁。住世更十年,化身千百亿。”[6](P676)就算面对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也仍能以诙谐幽默的态度待之。这些人生态度都反映了他深受般若空观思想影响。
三是亲友分别之苦痛与般若空观。离别是古人常吟咏的话题,在周必大的诗歌中也常见其对离别之苦的哀吟,如“自酹黄花酒,心酸苦泪零。常时爱鸣雁,从此不堪听。”[6](P20)是与兄弟生死离别的悲叹;“莫攀杨柳涛江岸,莫唱阳关动凄断。”[6](P21)是与好友两地分别的不舍。“爱别离”是人生八苦之一,但佛教认为“诸法无常,诸相非相,动静来去,都是无常幻影。不但大小相状为空,就连微尘世界里的众生七情六欲也都是空的。”[12]既如此,离别也是空的,也当“无住生心”,随缘自适。受到般若空观影响的周必大,在与人分别时便有了“行行但祝加餐饭。”[6](P21)的祝福,有了“人生有聚散,安所非游宦。”[6](P24)的豁达,有了“不惮客从南去再,要陪驿召北来双。”[6](P26)的乐观。尽管是在生死离别,他也能在分别之时,暂且忘了离别之苦,不见苦吟,但见达观,在给予亲友祝福的同时,不让自己为受别离苦所累。
三、佛禅对周必大诗歌创作的影响
禅宗对周必大诗歌创作的影响还体现在他诗歌的艺术中。他的一些诗歌,或使用佛言禅语,以禅入诗;或借用佛禅意象,以禅构境。他诗中的艺术形象寓托着禅宗思想,而禅宗思想也给他的诗歌创作增添了许多趣味。
(一)佛禅意象
周必大的诗歌中运用佛禅意象不在少数,整体看来,他常运用的佛禅意象主要有自然意象和实物意象两类:
一是佛禅中的自然意象。在宋代这样一个文化繁荣、生活富足的时代,广大文人热爱生活、亲近自然,踏春赏花、饮酒品茶,这种亲近自然的风尚与佛教的自然观十分契合,“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是佛与儒的共同追求。从周必大的诗歌中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花、云、水等事物皆能启发他获得一些禅悟。“花”的开落是最能展现自然生灭律动的,周必大诗中写“花”的共约48次,其中不乏观花悟禅的例子,如前文提到的《次韵芮国器正字馆中木樨三首》其一,看到桂花便促使他联想到佛与桂的典事,将整首诗歌写得颇有禅意。而他的《次韵邹德章监簿官舍芙蓉芭蕉》一诗更具代表性:
……从渠草木荣与枯,只有此心常自如。水边比色宁见素,隍中覆鹿初何据。似耶非耶谁与论,彼梦我梦随所住。大篇字字皆披沙,清晨走送惊邻家。钝根也复发深省,世间何物非空花。[6](P26)
依题目看这当是一首普通书写官舍芙蓉芭蕉的小诗,或可蕴藏着作者对二者的喜爱之情。但周必大围绕“钝根也复发深省”一句,从芙蓉芭蕉的佛性入手写自己看到二者后的感触,颇具佛理。莲花以其出淤泥而不染、花果叶能并存等特色被佛教视为圣花;而据《维摩经·方便品》“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11](P36)及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考印度禅学,其观身之法,往往比人身于芭蕉等易于解剥之植物,以说明阴蕴俱空,肉体可厌之意。”[13]可知佛教以芭蕉喻人生之脆弱不实,周必大此诗是观花后联系自身的人生体验,借莲花与芭蕉来吟咏人生无常虚空,极具禅意。
除了这些直接展现禅意的诗歌之外,周必大一些写花的诗则隐含着众生平等,生命之美的意蕴,如写莲花之洁净“污沟浊水叶田田,又见新载京府莲。玉井谩传青壁外,雪肤如在射山前。”[6](P8)写牡丹之灵性“翠叶迎风牵荇带,红绡浴日湿宫衣。”[6](P609)都是用拟人手法将大自然与人融为一体,颇具特色。
除了花意象以外山水意象也能激起周必大的禅悟。如前文提到的《柬达上座颂一首枕上补作》一诗,观雄壮的瀑水使他获得了“虚空”之禅悟。而《寄题高仲一殿撰识山堂长韵》中的“不识山面目,只缘在山中。”和“山形不动体,山色含真空。”[6](P618)两句均借山来阐述佛理,前句是化用苏轼之诗,体悟“不立文字”的禅意之难解;后句则是借山色的瞬息万变来表达万物皆空的佛禅意蕴。而“坐观林谷升初日,吟到云山合暮烟。”[6](P55)则是通过日、云、山的结和,传达出了自然闲适的禅意。
二是佛禅中的实物意象。禅宗在传道授业之时十分喜欢运用日常事物做喻,为启众生根钝,为传艰深佛法。这些比喻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逐渐进入到士大夫的诗文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意象。周必大的诗中有也偶有使用这类意象群。如“灯”意象。灯是智慧与佛法的象征,它能破除一切的黑暗,破除一切的愚痴,是照亮众生心灵和万千世界的利器。《华严经》说:“譬如一灯入于暗室,百千年暗悉能破尽。”[14](P218)《坛经》中也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15](P55)周必大的《次韵子中兄相迎诗中有奠松楸之语追念别后叔母子柔下世故卒章及之》“春来怪底鸟乌乐,归去喜同灯烛光。”[6](P35)及前文提到的《天池观文殊灯》一诗,都使用了“灯”意象。前者是借“灯”来祝福追念去世的兄弟,后者是取佛教中"灯"代表智慧之意,说自己观文殊灯后便已悟得佛法真谛。
又如“金篦”意象。该意象出自《涅槃经·如来品性》中的“金篦刮目”之喻,曰“如百盲人为治目故,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篦决其眼膜。”[16](P42)是用以喻去除外界之障蔽而得见本心本性,体悟佛法大意,在诗歌中使用此意象较早者是杜甫。周必大的《刘仙才仲子俊示其父醉庵诗集索鄙句》中的“蹇步媻珊到竹溪,病眸眩瞀乱金篦。 ”[6](P627)及《病中次务观通判韵》中的“开门得新诗,刮膜如释负。”[6](P41)也都用了此意象。前者是周必大晚年不问世事后的作品,借“金篦”来表达自己见到竹溪之景时的豁然开朗之感,表达对栖居山水的喜爱和享受。后者则是借“金篦”表达周必大病后受到陆游诗的欣喜之情。
(二)以禅入诗
周必大有不少直接运用佛禅语写成的诗歌,如“三年一蒲团,近者坐欲朽。”[6](P41)“天怜寓客混缁徒,十日无烟香积厨”[6](P29)“迩来一念了世缘,蝉冕照人头未雪。”[6](P100)这些诗虽禅意不浓,其中的禅语并不能构成诗歌的主要内容,但因借用了佛言佛语,使得诗歌语言或浅俗活泼,或生动灵活,别有一番风味。具体说来,周必大诗中的以禅入诗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善于将禅语与日常生活结合。周必大热爱生活,追求闲适,他的诗歌创作也常取材于生活,这与佛教所主张的“平常心是道”和“随缘任运”的心态是相通的。佛法存在于一切事物当中,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大珠慧海认为饥餐困眠便是禅悟,宋代慧开也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7](P236)此外,诸多禅宗大师都喜用日常生活的点滴助僧徒真正体悟佛法大意。如此,周必大在描写日常生活时,也常喜用佛语。如他的《次韵王少府送焦坑茶》一诗“昏然午枕困漳滨,醒以清风赖子真。初似参禅逢硬语,久如味谏得端人……”[6](P38)本是记录收到焦坑茶的日常小诗,但其特别之处在于“初似参禅逢硬语,久如味谏得端人”一句,以参禅之感喻焦坑茶之味,刚入口时仿若参禅时的枯燥乏味,随后便是如嚼橄榄般的苦尽甘来,十分之生动。又如《次韵芮国器正字馆中木樨三首》“有生定自为黄卷,一念无如鱼蠹何。今度金身散金粟,芸香从此不须多。”[6](P23)一首书写生活中桂花的诗歌,运用了“黄卷”“一念”“金身”等佛语,写出了桂花的色鲜与味香。实际上,自魏晋始,桂花就因其香味淡雅,有花有果等特点被普遍种植于佛寺之中,桂花便与佛教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如王维著名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18](P637)就是以桂花的独自开落,建构了空寂的禅意禅境。宋代著名禅师晦堂大师更是借用简单的“闻木犀香否”一句话点醒黄庭坚,参悟禅机。周必大此诗以佛语写桂花,极具特色,也正说明了周必大心中有佛。
二是善用佛禅事典。周必大学法江西诗社,他的诗作善用典故便是继承江西诗“无一字无来处”的主张,而在典故使用中也常化用佛禅之典,这些典故多来自《维摩经》《法华经》《大般涅槃经》等大乘佛教经典中。以《次韵程泰之正字奉祠惠照院咏雪五首·其一》为例:
“天女飞花现化城,禅房深处想神清。斋心正使无低唱,拥鼻何妨效洛生。”[6](P20)
诗歌通过《维摩经》中的“天女散花”之典和《法华经》中法华七喻之一的“化城”之典描写在雪日禅房,作者参禅悟道以达到“天女飞花”之无杂念的境界。诗歌虽为咏雪,却无一雪字,反是用佛教之典来映衬出雪日中的宁静与祥和,读来颇有趣味。
此外,他的《青原祖灯监寺屡问予久不入山写真戏题》中“欲作青原挂搭僧,传闻米价逐时增。绕腰三篾非难事,空腹何能念葛藤。”[6](P674)和《慧海大师日智索诗》中“三篾绕身尤未解,斋厨已报炊无烟。”[6](P23)都化用了佛教中的“肚束三篾”典故。而前诗中的“欲作青原挂搭僧,传闻米价逐时增。”一句与《同子中兄游龙须吉祥善生诸寺归至柞树渡大风》中的“事业如斯官给廪,庐陵米贵有人饥。”[6](P38)又都是运用了青原行思的“庐陵米价”公案。从周必大诗中灵活用佛典的情况可以看出,一方面周必大对佛教典籍了熟于心,另一方面他所了解的佛经内容不宽,常反复使用,且多游戏之作,并非借这些佛典来抒情说理。
三是学习禅宗语言之浅近。“不立文字”的禅宗为了不“过分抛弃佛经原典”[19](P5),同时又需“更适合向平民僧众传法”[19](P29),便使用更具中国化的、直观通俗的佛学语言,即是所谓“农禅话语系统”,是一种既根植于中华本土文化土壤,又流行于平民大众生活的语言形态。[19](P32-33)禅宗的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特点对诗歌产生的影响就是大量使用口语、俗语入诗。周必大在诗歌中喜用叠字,使得诗歌朗朗上口、浅近易懂,如“小松风飕飕,长松风冽冽。 ”[6](P641)“奇奇怪怪无非洞,下下高高总可亭。”[6](P51)其中的“飕飕”“冽冽”“奇奇怪怪”“下下高高”等词语通俗地写出了作者的所见所感。他还有一些诗歌语言浅易,冲口而出,如“老子七十七,到处遮人壁。 ”[6](P676)“老夫只学龟藏六,未羡梢头首面新。”[6](P58)“五年未续梦中梦,得得来追三伏凉。”[6](P61)“老子”“老夫”等自称的使用和数字的使用,使得诗歌浅白,更具口语化,读来似与作者直接对话。研究周必大的学者常将其这种语言特点的形成“归功于”学白居易,却忽视了周必大受到佛禅语言影响的事实。
综上,周必大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或许不如王安石、黄庭坚、张商英等人那样参禅注经,对佛禅没有如此深入的研究,但在日常生活中,周必大常游寺访僧,为己为民祈福;在文学创作中,周必大能援佛入诗,以佛禅语来表情达思。对于佛教他始终持有接纳、欣赏、亲近的态度,将禅宗看作儒家思想之外的补充。这一方面能够助益他以通达的思想观察社会,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世俗;另一方面能够助力他建构起沟通心灵与宗教的桥梁,得以为去世者祈祷,为在世者祈福。除诗歌创作外,周必大的散文创作中也透露出了佛学思想,有关周必大与佛教的话题仍可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