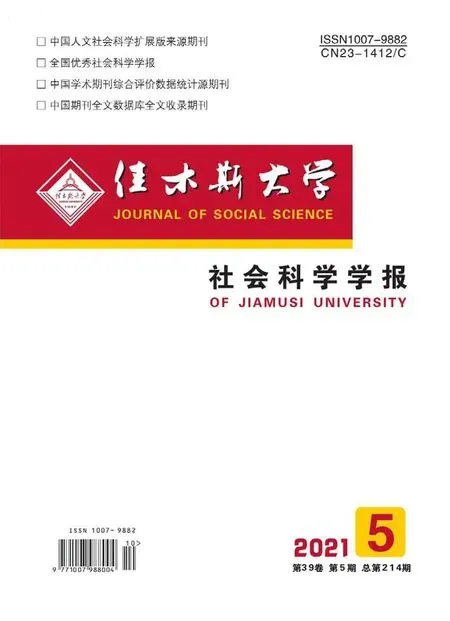东北地区语言接触类型与演化机制研究 *
2021-12-06贾秀春
贾秀春
(佳木斯大学 人文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一、东北地区语言接触概况
“东北”按行政建制来说,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按地理划分或者从方言归属角度来说,“东北”还包括内蒙古东部和河北东北部,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所形成的经济、文化区。本文是指后者。所谓语言接触,通常意义下指某区域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接触或者方言之间的接触,涉及的理论非常复杂,主要有“语言接触”“语言联盟”“语言竞争”“母语干扰”“接触机制”“语言借贷”“语言转用”等,我们先来看一下东北地区语言接触概况。
(一)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以及与汉语之间的接触
我国东北地区地域辽阔,独特的山系水系和平原地理环境,使得长期以来在东北生活和居住着众多的以渔猎和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包括满族、锡伯族、鄂伦春、鄂温克、蒙古族、达幹尔、赫哲族、回族、俄罗斯族等。语言学界绝大多数观点认为,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除了回族语言外,都属于阿尔泰语系(回族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属于内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下的不同语族不同语支。其中满语、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族语属于满—通古斯语族,满语属满语支,鄂伦春、鄂温克属于鄂温克语支,赫哲语属于赫哲语支;达幹尔、蒙古语属于蒙古语族—蒙古语支[1]。汉族和柯尔克孜族、朝鲜族在东北居住的历史要短很多,是后迁移到东北的民族,分别使用汉语、俄罗斯语和朝鲜语。以上这些民族在东北长期的居住交往中,语言接触十分频繁。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蒙古语与满语曾在元明之际,有过密切的接触。元朝时,蒙语占主导地位,到了清朝前期,蒙语与满语的交流十分频繁,有了相互交融的趋势。学堂设立了满蒙双语教学。清朝中期开始,蒙语、满语、汉语共存发展,在人们的交际交往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但是满蒙语言融合的趋势渐渐弱化,汉语的优势突显,到了清朝末期,汉语成了主要的交际语言,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共时的角度来看,满语蒙古语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汉语与各少数民族语言都有过密切的接触。
(二)移民和“流人”使用的方言与东北方言的接触
谈及移民与东北汉语的接触,最晚应从辽宋时期说起。宋朝时,辽多次对中原作战,掠夺了大量汉族人口进入东北,特别是燕京地区的汉族人,被大量地迁移至东北。后来元、明、清历代,都有移民因战乱或者开荒等原因进入东北,这些移民多来自华北、山东一带,所以使用的语言以幽燕地区的方言为主,还有极少数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使用的是中原汉语。所以东北地区,移民的涌入,各民族的接触融合,使得语言使用状况也较为复杂,移民所使用的以幽燕为主的方言与东北方言、与当地原著少数民族的语言都有广泛接触交融。
东北地区的语言构成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历代流放到东北地区的汉人所使用的语言。众所周知,古代东北地区是著名的“流放地”,很多“关外”及中原地区的人们被朝廷流放至此用以“惩戒”或“守边”,其中以清代的“流人”为最多。这些被流放的人,使用的方言与东北汉族人所使用的方言有很大不同,对东北方言的特点和形成都有重要的影响[2]。
二、东北地区语言接触类型
语言的接触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从语言接触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有深度、中度和浅度接触,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东北少数民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两个不同语系语言之间的接触没有同源关系,算不上“语言联盟”或者使语言发生质变,只是产生了语言的借用、兼用现象,所以其接触也只能算浅层接触。移民或“流人”使用的语言与东北汉语同属一个汉藏语系下的不同方言,这两种语言接触的结果主要是源语(移民或“流人”使用的语言)对受语(东北方言)在语音和词汇、语法方面的借入,没有使受语(东北方言)发生质变,所以可以算作中度接触。从接触的方式来看,有文化交流性接触、教育治化性接触和地缘接壤性接触[3]。下面我们分别谈这三种接触类型在东北语言接触中的体现和特点。
(一)文化交流性接触
同少数民族文化相比,汉族文化发展相对来说程度较高,所以,在民族文化交流中,东北各少数民族吸收了大量的汉族的先进文化,来发展本民族文化。同时,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如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狩猎文化,满族、赫哲族的渔猎文化等也各有其特点,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营养也被汉族人所吸收和发扬光大。这种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直接导致了语言接触和影响的加剧。另外,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书面交流时都使用汉文,学校学堂的授课也多用汉文,教材多用汉语来书写,所以汉语通过文字这一书面语的形式,加大了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成为语言接触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
另一方面,历朝历代以来,被流放到东北地区的“流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也带来了中原雅音,虽然到了东北后,多数情况下是学习当地人的语言,但是也保留了自己原来的语言习惯。特别是清朝以来,由于大兴“文字狱”,大批的知识分子被贬到东北。东北人非常崇尚先进文化思想,以文人为尊,所以这些“流人”在东北不仅受平民百姓的尊敬,也深受一些满族官员的喜欢,往往被减免一些差役,使得他们有更多时间钻研学问,教书和传播文化。这些“流人”传播诗词歌赋和佛教文化的同时,将各地的方言融入了东北方言之中。
文化交流性语言接触中,文化传播的方向可以决定语言传播的方向,如果文化是单向传播的,语言传播也是单向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语言传播也是双向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是相互的,所以语言的传播也是双向的,互有借用。移民和“流人”带来了中原的一些文化,对东北来说属于单向输入文化,所以语言传播也是单向的。
(二)治化教育性接触
出于政治教化的目的使语言相互接触是语言接触的一种常见类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东北地区以少数民族政权为主,辽金、元朝、清朝等少数民族创立的政权都在东北有过长时期的统治,当时的语言也以少数民族的语言为通用语。但是蒙古族和满族等统治阶级越来越意识到要想巩固政权,加强对人们的治化教育,语言的沟通交流是必要的。除了开设教授蒙古语、满语的学堂外,还从各种官方渠道开设学习汉语的学堂,科举考试时,优先录取精通满汉两种语言的举人,鼓励人们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特别是鼓励满族人学习汉语,很多满族小孩从小就开始学习汉语。同时,还制定各种政策允许汉族人入职为官,鼓励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杂居等等,这些举措一方面加强了民族的融合,一方面巩固了统治,促进了语言的接触融合。
东北地区治化教育性语言接触同其他的治化教育性语言接触有所不同,国内一些地区的治化教育性接触基本上都是汉语做为“优势语言”,其他民族语言作为“劣势语言”,人们自觉或被迫放弃母语而学习接受汉语。而东北,因历史上满蒙等少数民族政权占有统治地位,因而语言上也曾占有优势,后来随着满蒙政权的衰落,汉族人口的增加,再加之满蒙等统治阶级为了达到巩固自己政权的目的鼓励人们学习汉语,才使得汉语逐渐成为了“优势语言”。
(三)地缘性接触
交错杂居是地缘性语言接触的最典型情形。东北各土著少数民族既有居住在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大中城市的,如满族和回族等。又有分布在偏远牧区和县市的,如蒙古族、鄂温克等。还有跨中国、俄罗斯居住的跨界民族鄂温克族。汉族人口则是由于战乱、灾荒、移民政策等原因,由中原和河北、山东等地迁到东北的。汉族移民进入东北后,与各少数民族杂居相处,除了城镇等人口流动较快的大城市外,各偏远地区也有汉人的分布。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多,东北地区己从原来少数民族聚居地,演变为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而且汉族人口已经超过其他民族,成为这里的主体民族。这样,东北地区各民族杂居相处的分布特点,形成了语言接触上的地缘性接触。
东北地区地缘性接触,历史上曾以少数民族语言为“优势语言”,汉族人口处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包围之中,语言也处于劣势,从清末开始,汉语变成了“强势语言”,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人杂居相处时,语言处于劣势,正不同程度地被汉语“同化”。
以上这几种接触类型的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语言接触演变机制。
三、东北地区语言接触演化机制
不同的语言接触,其语言要素之间影响的方式、干扰的方向、接触演变的结果等都有所不同。当前,关于语言接触演变机制的理论主要有陈保亚的“母语干扰”和“语言转换”,托马森的“借用”和“转用引发的干扰”,以及江荻的“语言感染”、吴福祥的“构式拷贝”等[4]。从语言谱系树的角度来看,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东北少数民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这两种语系的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演变不会像亲属关系的语言那样,发生强烈的“感染”,即词汇上的大量借用,语音和语法系统也因相互借用特征而变得趋于一致。但是,语言学家陈保亚认为,支配语言接触的除了结构因素之外,还有社会因素,东北地区的社会因素决定了语言接触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语言干扰的方向,即产生了语言的借用和语言的转用现象[5]。
(一)语言的借用
“借用”是一种语言(源语)的特征迁移到另一种语言(受语)上,是常见的语言接触演变机制。陈保亚的“无界有阶性”语言接触理论指出,具备了合适的社会条件,例如足够的接触时间以及强度,语言使用者积极的语言态度和广泛的双语制,那么语言中所有特征,包括语音、语序、屈折形态语法范畴和派生词缀等,都可以被借用[6]。从汉语与东北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看,我们可以认为,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借用,是一种“双向借用”。各自的语言当中,都借用了对方的一些语言特征,特别是词汇方面。
1.汉语和满语的相互借用
满汉上百年来的语言接触,使得在各自的语言中,都有对方的借词存在。这些借词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分属不同层次,既有基本词汇的借用,同时也涉及到了一般词汇的借用。 如东北很多地名,就借自满语。“哈尔滨”借自满语,意思是“晒渔网的场子”;“齐齐哈尔”借自满语,意思是“天然牧场”;“吉林”则是满语“沿江”的意思;“完达山”的“完达”是满语音译,“梯”的意思。还有一些表示日常生活中常见事物和现象的词汇也借自满语,往往非常生动形象,有独特的表现力。如“嘎拉哈”指猪、羊等动物的腿骨节,也是妇女和儿童的一种玩具;“波罗盖”指“膝盖”;“嘎叽窝”指“腋下”;“哈了巴”指肩脚骨。“兀突”指“水不热也不凉”。也包括动词借用,如“瘆”指“吓”“使人惊恐害怕”等等。满语中也有很多汉语借词,如“福晋”借自汉语,是“夫人”的意思,“章京”是“将军”的意思[7]。满语中的汉语借词,只有极少数词完全按照汉语的发音,多数按照满语的发音习惯增加了音节,便于满族人的理解和接受。
2.汉语和蒙古语的相互借用
汉语从蒙古语中也借用了一些词汇来丰富自己的语言,如 “站”,约从南宋时起蒙语的“站”被借入汉语中。“喳”在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里写成“札”“者”或“嗻”。蒙语中“喳”是中性词,无褒贬义,也无身份限制[7]。 借用到汉语中指仆役对主人的应诺声,有了身份区分。还有“胡同”“褡裢”“歹”“蘑菇”等词汇也来自蒙古语[8]。语言上的借用,也包括语法上的借用。这种借用可以做宽泛的理解,既包括直接引进某种语法构造、语法形式,也包括只引进某种语法范畴,形式是自己民族语言创造的。如包括式和排除式用法的对立,是从阿尔泰语系中引入的,用到汉语中表示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和“咱们”上,就有了现代汉语中“咱们”同“我们”“俺们”表复数时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9]。汉语属于分析性语言,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是语序和虚词,缺乏形态变化,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属于粘着性语言,有着明显的形态变化和词形标志。汉语中表示复数的词缀“们”就是受阿尔泰语系语言影响产生的[10]。受阿尔泰语系影响,汉语曾增加过一些新的语法特征或者语法手段。如受阿尔泰语系中蒙古语的影响,汉语产生了“X+似+NP/VP”这样与先秦唐宋不同的新的比拟句式[11];再如,汉语定语的复杂化,也是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在元代以前,汉语中“的”字句,多是由单个词或简单短语加“的”构成的,后来在元代汉语和蒙古语书籍对译过程中,受蒙古语影响有了多层定语和复杂短语作定语的形式,使得汉语增加了新的产生语法句式的手段[12]。
(二)语言的转用
语言转用也叫作语言替换,是指一种语言的使用人群放弃自己的母语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是不同语言深度且不平衡接触的结果。在多种语言共存的地区,总是有“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之分。东北地区各种语言通过历时和共时的接触演变,逐渐由少数民族语言为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化。历史上蒙古语、满语等分别做为使用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语言通行一时,元明两代,语言以蒙古语为主,蒙古语是“强势语言”。清初,满族人掌握政权以后,满语成了社会中的主要使用语言,满语有自己的文字,清朝统治者为了推广满语还发行了满语教科书,满语成了“强势语言”。汉语只在汉族人居住地区通行。鄂伦春、鄂温克、达幹尔、赫哲、回族等少数民族则大多居住在相对偏远的地区,维系着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状态,所以多使用自己民族的母语。
清朝中期以来,随着汉族人口的不断移入东北,汉族与满族等各少数民族杂居相处,到了清朝末年,汉族人口大大超过了其他各民族,再加上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发生了转换,各少数民族人都认识到了学习汉语的重要性,特别是满族的统治阶级以各种方式,积极推行汉语。所以在清末民初,满语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汉语在使用人口和通行地域上,已超过满语成了“强势语言”。新中国成立之后,满族人更是纷纷地放弃了母语,公开场合只用汉语进行交流,绝大多数满族人逐渐地由双语使用者转变为只会汉语这一种语言。其他各少数民族也为了改善生活状态和交际需要,以积极的语言态度学习汉语,由最初的母语和汉语兼用,到逐渐地放弃母语转用汉语。
现如今,东北地区会说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只有牧区和林区,以及同江、抚远等偏远地区的一些年岁比较大的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能使用母语进行交流,城市中会使用自己母语的少数人,都转用了汉语。
四、结语
以上我们从语言接触类型与演化机制的角度,对东北地区语言生活状况加以研究和探索,指出语言接触的不同类型以及语言接触演化机制下语言的走向。我们可以了解到,东北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的地位是相互转化的,不同语言接触演化的机制是成系统的,表现最明显的是语言的借用和转用。满蒙等少数民族语言由历史上的“强势语言”逐渐变为“弱势语言”,使用人数越来越少,交际功能逐渐丧失。但语言接触过程中,满蒙等语言也给汉语以反作用,满蒙语言在向汉语的转用过程中,将一些基本词汇留在了东北方言中,成为了低层词汇,使得东北方言保留了很多满蒙等语言中的词汇,具有独到的语言表现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