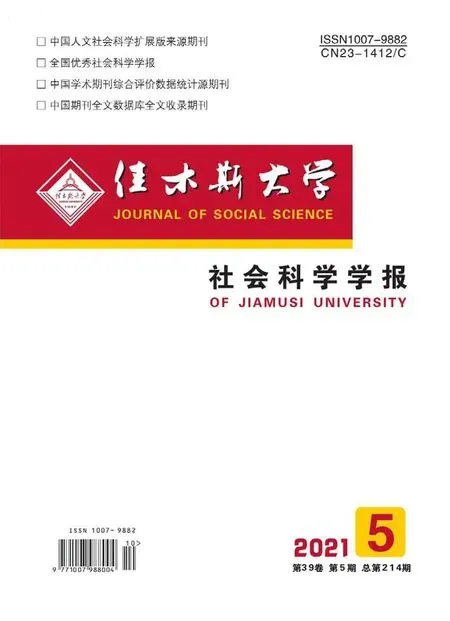创伤的表达与疗愈 *——《远山淡影》中的积极想象
2021-12-06柯智
柯 智
(福建农林大学 金山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一、引言
石黑一雄的开山之作《远山淡影》以二战期间遭受原爆的长崎为创伤场域,通过第一人称叙述重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命运突转和精神重创。作家并未采用“幸存者文学”或“见证文学”的手法,而是从非战争参与者的视角再现集体经历、探寻后战争时代普通民众的命运突转和精神创伤。主人公的叙述表面看似平静克制,实则暗藏巨大的情感力量,在平凡的生活下酝酿着“巨大的骚乱”[1]245,在平静的叙述下隐藏着“过于猛烈而不能直接面对的伤痛”[2]58-88。
创伤足以导致“记忆、知识和情绪之间的正常联结遭到阻隔”[3]31,因而创伤记忆违背传统的叙述模式,打破传统叙事时间的线性结构、叙述内容的可靠性和完整性,呈现非线性、碎片化以及偏离性等特征。面对碎裂的叙述,如何转化叙事困境,同时实现创伤的表达和疗愈是作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先行研究中,有关该作品的创伤研究有周颖[4]、汪筱玲,梁虹[5]175-180、梅丽[6]197-202、盛春来,朱宾忠[7]92-98等学者围绕《远山淡影》的战争创伤主题进行专门讨论,研究对象集中在家庭关系、身份焦虑、及自我欺骗等话题,然而大部分仍停滞在叙述者的“受创”层面 ,而较少涉及“疗愈”层面。
作为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方法,积极想象超越传统心理学中意识和无意识的二元对立,提出二者积极沟通交流的心理活动,即“以意识思维及感受、体验为主体,以无意识内容为为对象的精神活动”[8]238-240近年来,随着理论的发展,积极想象已不仅是一个特定的表达技术,更是不可或缺的疗愈方式。一些心理分析家发展了积极想象技术的运用方式,用更为丰富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如写诗、音乐、和沙盘游戏等。本文将立足文本的叙事分析,借用荣格(Carl Gustav Jung)积极想象的相关概念,考察作家如何突破创伤情境下的叙事困境,实现想象叙事的表达和疗愈的双重功能,并由此追寻作家对人类精神福祉的伦理关怀。
二、作为表达创伤的积极想象
消除无意识与意识分离的第一步便是想象对无意识内容的自然展现,即荣格所提出的“让它(无意识内容)发生(Gescheheulassen)”[9]141-142。《远山淡影》中积极想象的表达功能,在于通过显现和赋形被压抑、被排斥、被否定的无意识内容来呈现主人公的受创经历。
(一)空间
创伤学家库尔克认为,“创伤的实质在于创伤经历只能停留在感官和图像阶段,而无法到达语言阶段。”[10]158-182相对于创伤阴影下模糊化和碎片化的语言叙述,叙事空间是叙事话语中更具象、更生动的叙事表征,是语言叙述的有效助益,有利于读者拼凑出更具象、更完整的创伤经历。
小说呈现的空间主要包括被叙述者佐知子母女的小木屋、内叙述者悦子的混凝土公寓楼、以及外叙述者悦子的英格兰乡村房子。三个空间呈现由纯日式风格(榻榻米、推门、茶壶)到东西混合风格(榻榻米地板、棋盘、西式的浴室和厨房),再到英式风格(咖啡、沙发、壁炉)的转变。建筑风格的趋变重现了悦子艰难的移民历程:破木屋里的佐知子(悦子)为寻找母女的出路而终日在外疲于奔命;混凝土公寓楼里悦子仍然希望“有一天我们会搬到更好的房子里去”[11]9,而与之前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最终生活在英式房子里的悦子在空间需求上出现了折返,她向女儿提出“这房子太大了”[11]278“想换一所更小的房子”[11]279。
相对于三个空间在物质条件上的变化,那些被用来描绘主人公精神生活的空间意象却呈现出相似性,从一开始,封闭、潮湿、肮脏的视觉意象便被用来描绘小木屋的外部环境:“公寓楼和小河之间是一片好几英亩废弃不用的空地,尽是污泥和臭水沟。”[11]9潮湿和黑暗的意象同样出现在小木屋内:“屋里很整洁,但是很破旧。屋顶的木梁看上去很旧、不牢固,到处都有一股霉味。”[11]18木屋的破败和阴暗不仅预示了母女的艰难处境,还表明了亲子关系的岌岌可危。此外,屋子的“整洁”和“破旧”构成强烈的对比,这正与后文出现的陶瓷茶具相互对应:“精美的茶居与破旧的屋子和走廊下方泥泞的土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11]23。悦子在如此破败的房子里仍然努力维持着尊严和体面,突出了其作为没落贵族的阶级属性以及对贵族身份的固着,以及战争为其带来的境遇改变和心理落差。
在英格兰乡村,景子将自己的房间视为“极小心守护的私人领域”[11]75,最终走出这座房子在异乡自杀身亡。景子的死为大宅子带来了同样的黑暗与安静。值得注意的是,佐知子(悦子)最初为了逃离伯父家而投身异国,然而,最终悦子和妮基在大房子里喋喋不休抱怨的“安静”[11]5与伯父房子的“安静得让他想到坟墓”[11]243出现了重合。
叙事空间的“变”与“不变”的反差充斥着幻灭感和悲剧感,生动地构建出主人公充满痛苦和自责的精神画面。当悦子拼劲全力达到梦想的彼岸时,彼岸却与出发地发生了重合,不得不说空间的走向呈现出悦子西西弗斯式的悲剧人生。生活境遇的好转,最终并没有使悦子母女之间的关系走向缓和,反而使其在悦子曾经以为的梦想之地走向另一个极端。
(二)时间
受到创伤威胁的叙事结构集中体现在“历史或时间的中断”[12]13。第一人称叙述声音的频繁地介入将故事时间悬置、凝结,使读者感受到令人窒息的阻滞感,展示出叙述者的精神困顿,如“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神秘的咒语把我们定住了。天越来越暗,我们呆呆地站在原地……”[9]55
重复性的叙事也大大减缓了叙事节奏,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创伤造成意想不到的情感上的冲击,这种冲击会导致个体为充分理解震撼、恐惧和忧虑的感受而不断重复上演同一事件。”[13]15重复的意象(象征景子自杀场景的绳子、柳树枝、秋千)、重复的场景(潮湿黑暗的环境,阴暗的角落,肮脏的水沟泥地)、重复的情节(万里子出走-悦子寻找-万里子受伤)以及重复的自责和自我辩护均展现出破碎的亲子关系以及悦子的精神痛苦。
此外,通过对比两个事件的叙述时距,我们发现,悦子对佐知子母女的叙述占据了小说大部分篇幅,而有关移民后再婚成家这些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事件仅存片言只语。如今悦子漠然对待移民后生活的态度,与之前佐知子为获得移民身份心力交瘁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展示了悦子被压抑的内疚、懊悔、自责等无意识内容。
三、作为疗愈创伤的积极想象
积极想象最关键的一步是意识与无意识的良性沟通,即荣格所提出的“去思考、去孕育(Betrachten)”和“正视自己(Sichauseinandersetzen)”[9]141-142。《远山淡影》中想象叙事的疗愈功能,在于叙事主体通过修复和整合无意识来建构更健康、更完善的人格,并将其运用到现实经验中去。
(一)叙述者的积极干预
叙述者的积极干预主要体现在叙述者通过与“影子人物”之间的对话对无意识内容进行积极的反思和修正。小说中悦子和佐知子的第一次对话便展示了叙事主体现在和过去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态度:
“你想他们还在打吗?”她继续往山上走。
……
佐知子没有回答,继续往山上走[11]13。
佐知子只顾一心“往前走”“往山上走”,对万里子的成长问题却漠然视之,这个失职母亲的形象折射出悦子正为之后悔的过去。在亲情与梦想的角逐之间,佐知子孤注一掷地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我优先考虑的”[11]128,却忽视了孩子爱与归属的需要。更具悲剧性的是,佐知子所秉持的亲情伦理表面上是“为她好”,实则将自己未遂的人生愿望凌驾于万里子,导致母女亲情变质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霸权。沉浸在懊悔与自责中,悦子通过想象叙事补偿性地构建起理想人格:当佐知子在外忙碌时,悦子构建的理想自我总是穿过漫长泥泞的小路去小木屋陪伴看护万里子;当佐知子不近人情地认为稻佐山的游戏是“浪费钱”时,她却毫不犹豫地递给万里子硬币;当佐知子对万里子严厉斥责时,她总是细心呵护耐心沟通。
更重要的是,悦子还通过积极想象将反思和修正的结果构建更加健康的自我人格并将其融合到当下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当叙事角度转向二女儿妮基时,悦子对待“往前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妮基走得很快,每走一步,窄窄的皮靴子都咯咯响……妮基,我认为,应懂得走路本身的快乐。”[11]65
与之前剑拨弩张的母女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悦子和妮基构建了更加良性、正面、和谐的亲子关系。尽管与妮基在价值观、生活习惯和个人喜好上依旧存在分歧,悦子努力给予妮基尊重和宽容,而妮基也在最大程度上给与母亲安慰和陪伴。在妮基的支持与帮助下,悦子努力实现精神世界的重建:
“接着她走近几步,开始小心翼翼地把腾弄直起来。她扶起几根完全倒下去的藤,然后蹲了下来……把我放在地上、用来赶走偷吃的鸟儿的网弄正。”[11]137
连续几个动词“弄直、扶起、弄正”隐喻着妮基的关心和陪伴为悦子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力量与秩序。在此家庭亲情被作者赋予重要意义,良好的亲子关系不仅是人类精神家园建设的基础,还是受创者精神重建的寓所。
(二)被叙述者的积极干预
被叙述者的积极干预体现在叙述者在想象中有意识地与被叙述者进行良性的沟通和互动,实现对无意识的积极反思和修正。先行研究集中关注两个“自我”之间的对话意义,却忽视了其他人物的干预作用。实际上,叙事自我和经验自我之间的交流代表主体与自我(内心世界)进行的对话,而经验自我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对话则代表主体与他者(外部世界)进行的对话,二者即荣格所说的“内心体验”和“外部事件”[14]6。
作为被叙述者,藤原太太和绪方先生对悦子的人格修复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两个人物代表着人间的脉脉温情,在很大程度上为悦子提供了心灵寓所和精神寄托。绪方先生小心翼翼地鼓励悦子;而藤原太太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给悦子起了积极示范的作用。于是,在稻佐山之行中悦子满怀希望地对佐知子宣告重建家园的信心:“我以后一定要过得幸福。藤原太太一直对我说往前看是多么重要。”[11]163悦子还为过去未能传递曾经自己从父辈获得的温暖和善意而感到惋惜,因而通过想象对之前的态度进行修正,佐知子对藤原太太充满不屑与鄙夷,称“我的印象是你的朋友已经一无所有了”,而悦子则作出纠正:“她有一家店……还有她的儿子”[11]181-182;最后,悦子将代表着温情的日历传递到妮基手中,希望女儿也可以接受经过修正和反思重获的精神力量,而在这充满温暖的传递中,悦子的精神世界重获秩序:“我走进房间。透过窗子,我可以看见下面的果园和一排排整齐的小树。我手里的日历原本每一月份都有一张照片,如今只剩下最后一张。”[11]272
四、结语
正如小说名“远山淡影”所暗喻的含义一样,人类的创伤记忆遥远而模糊,却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刻上深重的烙印,深深地影响着精神家园的重建。然而,正如石黑一雄所言,“现实世界并不完美,但作家能够通过创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与现实抗衡,或找到与之妥协的办法……。”[15]36石黑一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人文关怀,并不止于创伤的展演,更在于进一步为精神主体的创伤疗愈指明了方向:只有积极纠正和修复自我内在的意识内容、坚守人性的温暖,人类才能构建出和谐、有序、平衡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