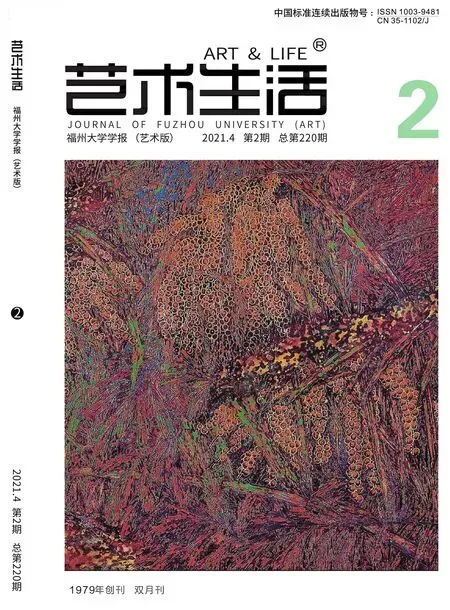傅雷古典审美理想的文化渊源
2021-12-06王茜
王 茜
(安徽工程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傅雷作为法语汉译大家声名远播,掩盖了他作为艺术理论家的功绩和贡献。傅雷一生不光译著等身,还写下大量精彩的艺术批评类文章,以一生的文化活动守望自己的古典审美理想—东方化的 “希腊精神” —以纯洁的心灵追求健全的感官享受[1]84-87,傅雷的整个艺术理论也植根于此,在美术[2]36-40、音乐[3]24-27、文学[4]74-77三个领域均有影响广泛的艺术批评实践。
傅雷古典审美理想的文化渊源脉络清晰:
一、文化血缘: “东方的根”
1.东方的文化血缘在傅雷身上留下的是儒家的烙印。
傅雷受传统文化浸染很深,他的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风流高标,他自己也说自己 “始终是中国儒家的门徒”[5]374。傅雷4岁即由母亲请账房陆先生教认字,7岁正式在家延请老贡生斗南公课读四书五经。东方的儒家文化深入其心始自幼年,与运命遭际一起塑造了傅雷刚烈的性格。傅雷字怒安,语出《孟子·梁惠王下》: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他自印的稿纸上,署 “疾风迅雨楼” 。不论 “雷” “怒” ,还是 “疾风” “迅雨” ,都鲜明地体现了他刚烈的秉性。傅雷的 “刚烈” ,在好友们的回忆文章中多有提及。施蜇存在他的文章《纪念傅雷》中写道: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直还近于狂妄。所以孔子说:‘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傅雷从昆明回来以后,在艺术的涵养、知识学问的累积之后,他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难得见到的,连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刚者。’”[6]48-49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讲: “刚、毅、木、讷近仁。” “刚者” 有着很高的道德水准。傅雷的 “刚” 是宁折不弯。 “疾风迅雨楼” 贴合傅雷的风格,但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道德经》第23章),一语成谶。
傅雷懂 “无欲则刚” 的道理,懂得修身克己,也常以此警戒二子。他还不惮其烦再三再四教导傅聪 “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5]492。集品格与艺术为一身,他本身就是一个榜样。在谈论艺术的时候,他总是强调艺人的品格要高尚,否则终是缺陷, “五代的冯延巳也极多佳句,但因人品关系,我不免对他有些成见”[5]P340。中国文化是一种 “德性文化” ,讲求由自身道德修养形成的自我道德约束。而西方知识分子从宗教观念到法与国家的拘禁无不是外在的 “他力” 。傅雷谈艺把 “德” 放在第一位,道德人格的建立是一切的基础。他的这种信条也显示了他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观念。品格完善是对任何一个艺术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要求—先 “立身” ,后 “立言” 。
2.东方的文化血缘是傅雷能够欣然吸收 “希腊精神” 的文化基础。
傅敏在一次访谈中[6]74说他对父亲总的印象就是一个 “真” 字, “真” 是父亲最大的特点, “心如水晶一般透明” 。这颗 “如水晶一般透明” 的真心就是傅雷爱讲的 “赤子之心” 。 “赤子之心” ,语出《孟子·离娄下》: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 ,就是婴儿的天真纯朴的心,就是纯洁的心灵[5]371;就是普遍的人间爱;是真诚, “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5]421。这与老子说的 “婴儿之性” ,李贽说的 “童心说” 相似。傅雷1933年9月以 “自己出版社” 名义自费出版所译《夏洛外传》,之所以选译这本书,就是因为 “夏洛是一个现世仅有的天真未凿,童心犹在的真人”[7]244。傅雷认为,讲求心地的真诚纯洁是一个人的 “立身” 之本,也是对一个艺者最基本的要求,只有心灵的纯洁才能保证艺术的纯洁,纯洁是中西古典精神的共有理想。孔子的审美理想是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且 “中国哲学的理想,佛教的理想,都是要能控制感情,而不是让感情控制”[5[363。以此为标准,傅雷喜欢讲陶潜、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认为 “中庸有度” ,才 “是浪漫底克兼有古典美的绝妙典型”[5]342。儒家肯定具有自然基础的正常人的一般情感,没有原罪观念和禁欲意识;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又讲求中庸有度,它也就避免了舍弃或轻视现实人生的悲观主义和宗教出世观念,避免了不受节制的刺激感官。傅雷认为: “比起近代的西方人来,我们中华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腊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我们的哲学、文学即使是悲观的部分也不是基督教式的一味投降,或者用现代语说,一味的‘失败主义’;而是人类一般对生老病死,春花秋月的慨叹,如古乐府及我们全部诗词中提到人生如朝露一类的作品;或者是愤激与反抗的表现,如老子的《道德经》。”[5]499-500以 “赤子之心” 咂摸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与以纯洁的心灵追求健全的感官享受的 “希腊精神” 是相通的,东方的文化血缘是傅雷能够欣然吸收 “希腊精神” 的文化基础[1]。
二、时代机缘: “五四的一代”
1. “五四精神” 是 “五四的一代” 一生的思想底色、精神徽记。
傅雷在家书中曾感叹自己 “侥幸的是青壮年时代还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没有消亡,而另一种更进步的力量正在兴起的时期”[5]591,作为精神现象的 “五四” 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思想遗产当是 “五四精神” —个性解放、人道、独立、自由。五四精神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是通过新文学、新音乐表现出来的,是通过胡适、鲁迅、老舍、巴金、曹禺等作家的作品和赵元任、黄自、聂耳、冼星海、贺绿汀、刘雪庵、林声翕等音乐家的歌曲所体现出来的。没有 “五四精神” 就没有中国20世纪的新文化,没有中国20世纪的新文化就难以产生新文学、新音乐(即欧化中国音乐)。
2. “五四时期” 吐故纳新的大时代是傅雷开眼望世界的机缘。
傅雷的母亲有远见,她认识到傅雷成长的时代风云际会,已非传统私塾教育可以适应,于是在请师父课读四书五经之时,又另请英文及算术教师讲课,而后干脆送傅雷入西式学校读书,从周浦镇到上海,从上海到法国。1927年12月31日,傅雷赴法自费留学。五四前后的留学潮给了广大学子出洋看世界的机会,而众多的热血青年确实是想从外面寻一眼清泉,来涤荡老大古国的旧创。傅雷当时就立志要献身文艺,唤醒祖国这头东方睡狮,准备 “此次乘长风破万里浪,到达彼岸,埋首数年,然后一棹归舟,重来故土”[7]21,结束数年来追求人生的烦闷,充实自己的头脑,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敷复病弱的祖国, “竭力肩起这肩不起的担子”[7]40。如果要向西方的文化、艺术有所借鉴,首先必须立足于理解。这充分体现了作为儒家文化背景之下的新时代知识分子以复兴华夏文化为己任,欲将滞后于时代的民族文化引向复兴之路。无疑,沟通中西艺术是艺术探索可选择的最佳切入点。
三、接受因缘:游学艺术之都
1.在法攻读艺术理论期间对 “古典精神” ( “希腊精神” )的接触直接促成了傅雷古典审美理想的形成。
傅雷抵法以后考入巴黎大学文科,专攻文艺理论,主要是读艺术欣赏与剖析(包括文学、绘画、音乐等各方面)。同时去卢佛美术史学校与索邦艺术讲座听讲。在学习中,全面接触了法国当时最新的文艺思潮,后来写下了《现代法国文艺思潮》(1931)、《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1932)、《世界艺坛情报》(1932)等多篇论文,传播新知、探讨理论,较早将 “立体主义” “现代文学” (即 “现代主义文学” )、 “文学史研究” “比较文学” 及其 “影响研究” 、 “俄国形式主义” 等新鲜话题介绍进来,及时传递了世界艺坛的新讯息。傅雷的译名之盛,多少遮蔽了他先前留法所学习从事的专业。其实,于傅雷而言,法语只是语言工具。钱钟书曾注意到傅雷名片上写的是 “美术批评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晗想留傅雷在清华大学教法语,但傅雷只愿教美术史,后终因当时不开这门课而作罢[6]16。
傅雷一生翻译生涯近40年,译作30多部,但只翻译过两部艺术理论作品,一部是广为留传的《艺术哲学》(1958-1959),一部是生前未曾正式发表的罗丹《艺术论》(1931)。
丹纳的《艺术哲学》是丹纳应巴黎美术学校之聘,担任美术史讲座的讲稿。傅雷在1929年9月于巴黎开始翻译第一编第一章,定名为《艺术论》,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傅雷在《〈艺术论〉译者弁言》里讲了他的翻译动机: “我之介绍此书,正着眼在其缺点上面,因这种极端的科学精神,正是我们现代的中国最需要的治学方法。” 傅雷要用实证主义救 “艺术常识极端贫乏的中国学术界” ,因为 “中国学术之所以落后,所以紊乱也就因为我们一般祖先只知道高唱其玄妙的神韵气味,而不知此神韵气味之由来。于是我们眼里所见的‘国学’只有空疏,只有紊乱,只有玄妙” ![7]241近30年后傅雷又于1958年6月始译丹纳的《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事隔30年的一次节译,一次全译,可见丹纳的《艺术哲学》对傅雷的影响贯串一生。傅雷在《〈世界美术名著二十讲〉序》(1934)中讲: “夫一国艺术之产生,必时代、环境、传统演化,迫之产生,犹一国动植物之生长,必土质、气候、温度、雨量,使其成长。”[8]9他在写《世界美术名著二十讲》(1934)的时候就自觉运用了丹纳关于艺术产生受 “种族、时代、环境” 三因素影响的学说。丹纳说过,所谓的古典精神,第一要点是健康,不是无病呻吟,换言之,是生意盎然而毫不夸张的。而傅雷晚年犹为重视的《艺术哲学》第4编 “希腊的雕塑” ,讲的就是希腊精神,故而对《艺术哲学》的介绍完全可视为是傅雷自觉地对其古典审美理想的守望和传播。
傅雷在《现代法国文艺思潮》(1931)中业已表现出对罗丹的关注。1931年冬他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美术史,翻译出了罗丹《艺术论》,作为教学参考用书,弃用坊间译本重译只为 “自学一遍,方便后生,无意出版”[9]13。值得注意的是,年青的傅雷采用了他译的这本罗丹《艺术论》作为美学讲义。想当年鲁迅也是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作为其任课的文学概论的讲义。文学是生命苦闷的呼号,这是鲁迅接受厨川白村的观点。傅雷用罗丹《艺术论》作讲义, “盖以在未曾涉及纯粹哲学之美学之前,先当对美术之各种实际问题(如形式与精神之论辩等)有一确切之认识与探讨也”[9]15。罗丹奉自然为他惟一的女神,以古希腊艺术为他的艺术范本,米开朗基罗是他崇敬一生的大师。罗丹有关艺术规则的创见无不是对自然的追求,对健全感官享受的追求,而所强调的 “艺术死亡时代” 的艺术更应发挥陶冶教化功能,使人类的心灵和社会大环境都得到净化和升华,实际上就是回归人性的自然本真。[10]9-13罗丹的艺术主张不光与中国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的审美理想相契合,更进一步影响了年青的傅雷。罗丹认为艺人要保持完满的人格、不受政治与经济因素的羁缧,傅雷也正是 “心有戚戚焉” 。罗丹可视为傅雷的审美理想在近世法国的兄长,年青的傅雷采用他译的这本罗丹《艺术论》作为美学讲义,实为 “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 ,守望传播自己的古典审美理想。从批评文本看,傅雷艺术批评中的有些观点明显受到罗丹的影响,例如,在《塞尚》(1930)中他写道: “大凡一件艺术品之成功,有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即要你的人格和自然合一(这所谓自然是广义的,世间种种形态色相都在内),因为艺术品不特要表现外形的真与美,且要表现内心的真与美;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方法,我们决不可认错了。要达到这目的,必要你的全人格,透入宇宙之核心,悟到自然的奥秘;再把你的纯真的视觉,抓住自然之外形,这样的结果,才是内在的真与外在的真的最高表现。”[8]205-206这段话的精魂与罗丹的观点如出一辙。
2.巴黎的古典韵致令傅雷终生魂牵梦萦,对大量高品位的艺术作品的欣赏观摩,造就了傅雷纯正高雅的古典艺术品味。
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它的艺术氛围、浪漫情调、历史胜迹和妩媚景致都深深感染了傅雷,使其眷恋不舍。当年负笈之地的一景一物,在其回国后数十年间,依然念念不忘,心驰神往。国立巴黎大学位于巴黎第五区即拉丁区,分文学、理学、法学、医学四个学院。罗曼·罗兰就是巴黎大学音乐艺术史教授、研究贝多芬的专家,傅雷受其影响从而热爱西洋古典音乐。巴黎大学离罗浮宫,卢森堡公园,先贤祠(名人墓)等地不远,傅雷可以时常前去观摩艺术珍品。30年后傅雷仍对巴黎拉丁区书店、罗浮宫和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远东艺术室津津乐道。罗浮宫收藏丰富,那里面的美术品是按照不同区域和年代分别陈列的,所以边欣赏作品,等于边在读美术史。单靠看复制品是培养不出好的鉴赏力的,复制品不能作为批评原作的根据,黑白印刷看不出原画的好坏,彩色的也与作品大有距离。这种以顶尖级艺术珍品真迹为感性依据的学习欣赏,对于艺术研究者而言是绝佳的熏陶,使傅雷对时代演变、派系特征、作家风格了然于胸,从古代的埃及、希腊,中世纪的欧洲,15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的法兰德斯,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西班牙,直到19世纪的法国,真是一览无遗,为他以后写作《世界美术名著二十讲》这部古典美术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拜访大师,友朋论学,游历诸国,寻访艺术遗迹,扩大文化交往面,提升了傅雷的艺术眼光,开拓了傅雷的艺术眼界。
傅雷留法期间,交游广泛,其中有大学教授、批评家、汉学家、音乐家,还有巴黎美专的校长及其他老年画家。当时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也是精英荟萃:刘海粟、刘抗、汪亚尘、王济远、张弦、庞熏琹、张荔英、陈人浩、滕固等都同时在艺术之都逗留,经常又有研究历史的黎东方、攻研文学的梁宗岱和写法文诗的何如来参加聚会,畅谈中归根究底仍回到文学艺术的话题来。这些留学生回国以后均成长成为文艺领域里的精英。当年在咖啡馆里的高谈阔论,思想交锋,互相启发,切磋技艺,裨益良多。1929年10月傅雷与刘海粟、张弦等在巴黎看以马蒂斯为首的野兽派画展并专程拜访马蒂斯,受到年已六旬的画家热情款待。获知著名雕塑家布尔德尔病逝,即与刘抗、刘海粟前往布尔德尔住处瞻仰遗容。1930年春又与刘抗结伴到比利时旅行,在比国修道院小住,参观独立一百周年纪念博览会以及布鲁塞尔博物馆。比利时是法兰德艺术的老家,能乘此机会以管窥豹,着实快慰。1930年5月底,陪同刘海粟夫妇拜访年逾八旬的著名画家阿尔培·斐娜。刘海粟回国以前,傅雷曾为刘向法国教育部美术司推荐由法国政府购买刘海粟作品一件。1931年春,与刘海粟结伴游历意大利的罗马、那不勒斯,不仅领略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风格,而且深切体会到弥盖朗琪罗艰苦卓绝的创作精神,大大加深对古典艺术的了解。这些文化活动提升了傅雷的艺术眼光,开拓了傅雷的艺术眼界。
傅雷深植传统文化之根,汲取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态度,讲究逻辑性,重视美感经验和艺术感悟,从具体真实的美感出发评文论艺,艺术品味是顶级的,融中西文化、诗词歌赋为一炉,极具艺术借鉴价值。傅雷敏锐的文化意识和深邃的交流理性在当今电子媒介时代仍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