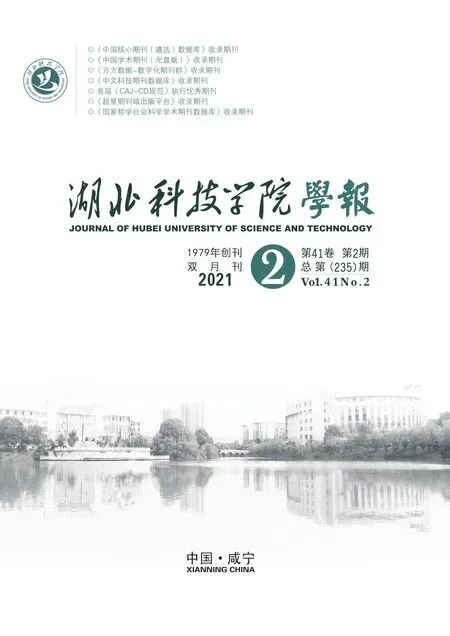言意之辨中的美学品格与美学政治 *
2021-12-06邓安琪
邓安琪
(东南大学 哲学与科学系,江苏 南京 210000)
言意之辨源于汉魏之间名理之学,名理之学源于人伦鉴识、品评人物。如《抱朴子·清鉴篇》曰:“区别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为。自非明并日月,听闻无音者,愿加清澄,以渐进用,不可顿任。”[1](P30);欧阳建《言尽意论》中言:“世之论者一位‘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威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钟、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2](P34)在此人伦鉴识中引起“言意之辨”。
一、析言意之辨
自“言意之辨”争论形成以来,儒释道三家皆十分热衷于谈论:《周易·系辞传》就有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直指语言文字不能够表象出意犹不尽之处;而最有名的“言意之辨”数王弼之“忘象忘言”,即“得意在忘象,得意在忘言”,这是王弼对于象数之末的扫尽与对“道”的体察。此外,有些论著虽未及“言”与“意”,但却在“尽”与“不尽”上亦有讨论。如《周易·说卦传》又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孟子曰“尽心知性知天、尽其才”,荀子也曰“圣人尽伦,王者尽制”;《中庸》又曰“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以至参天地赞化育”。
综观各家之言,所谈“名言”之措辞不尽相同,但都直入质料与本体、有形与神理、迹象与本体、具体与抽象、形下与形上、有限与无限、名言与意会的争论[3](P33);或言,名言与尽意的争辩,涵盖了中国哲学命题中一切符号系统与意义的争辩。
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先秦儒家从正面言“尽”;道家老子只言“可道”与“不可道”,庄子只言“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玄学家中王弼高唱“得意忘言”,而欧阳建却直言“言尽意”。各家似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依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论稿》,各家虽对“名言能否尽意”各执一词,然而纾解其中问题还需落到一个“尽”的理解上来[3](P42)。如荀子《劝学篇》“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其中虽反复强调“全之尽之”,但其穷尽之对象乃是诵经、读礼等言象①,而对于如何“为学”、如何“为圣人”等,则是无尽的。同样,对于《系辞传》中所强调的“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言,变通以尽利,鼓舞以尽神”,汤用彤先生同样认为其所尽者为象,而意、利、情伪、神则是“尽而不尽”的。
因此,在对“名言能否尽意”的回答中,依稀可见其中暗含调和儒道的旨趣:或言儒家圣人体无,从圣人无言处探求,以天道虚无为圣人真性,由末反本回归老庄;或唱至道超象,所谈者象外,依此而崇道卑儒。然而,不论采用哪一条进路,对现象界的停留皆是暂时的,对言外、象外、迹外、方外的求索皆是永恒的。正如《兰亭集序》中所言:“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案此,各家从不同进路回答了“言意之辨”中“意”的胜出;“得意忘言”也以其会通三教之精神而成为根本的思想方法。②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一窥“得意忘言”对于中国美学建构的助力。
二、言意之辨中的美学品格
若论中国美学的品格,大抵可从书画等具象的艺术门类来看其对“言”的刻意遗忘与对“意”的外化。例如,对于画论来说,以形写神、瞻形得神的人物画理念是言意之辨与绘画理论的第一次结合。顾恺之③曾在《论画》中描述了这样的情境:“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趣失矣。”即讲述画家在构建人物造型时应当以人物之外的情境来表现其神采,否则就有违传神的旨趣。此种以形写神的方法正是画者寄象出意、迁想妙得而来。二者相结合以后,对于人物画气韵的要求更是辐射到其他题材,山水、花鸟无不如此;对“形”“言”的态度也从弱意义上的遗忘推进到了更强的断舍。笔者拟从画论中“写照”“传神”与“畅神”之精神来照见“言”的弃舍与“意”的涌现这一美学历程。
1.从写照到传神
《世说新语》有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用“不点目精”这一典故分明地推出了忘形而传神达意的美学旨趣,乃是对“言意之辨”兴盛时期艺术品格的总结。在此之前,汉人看待人物的方式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相法”(汤用彤先生语),即由外貌推测体内五行的不同;而之后的人伦鉴识则更重“神气”“气韵”等,将对人的审度观测放置在难言的虚无之域。
因而,从具体的艺术门类而言,人物画便讲求“传神”;书法便如董其昌所言“晋尚韵”;音乐便要“声无哀乐”;文学便崇尚隽永,《文心雕龙》推许隐秀,隽永谓“甘美而意深长”“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3]((P36)……言意之辨中的美学品格,在魏晋的年代,完美地反应到了艺术创作上来:艺术家不再追求言内的造型、笔墨、语言等,而是通过对言内之物的刻画与利用,去追求象外的情、神、利、命等审美形态。
2.对“畅神”的追求
当艺术的审美形态从写照过渡到传神,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艺术家们不仅仅止步于“传神”,还意图在言外之地寻求“畅神”。宗炳④曾在《画山水序》中提出:“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宗炳为何会发出“何为哉”的感叹?因为在“峰岫嶤嶷,云林森渺”的无人之野中,他能超越俗尘、与绝代的圣人相映;又能突破空间的壁垒,与万物融于神思中。在峰岫与云林之中,宗炳寄托了自己的怀抱、更解放了自己的精神,实质是庄子意义上的“逍遥无碍”。[4](P224)而这条通往精神解放的路径,正是艺术。艺术将山川之质料摹写成美的趣灵,将自然之天赋变成美的理想,最终生发了“道”。
因此,所谓之“畅神”,其原意是对山水画中自然山水与澄明性情合一的追求。但却带来了更大的影响:要更深层次地拓展言外之地的空间,让游履的山水、驰神的风光皆成为言外之意逍遥的领域。如此,“言外之意”的空间更加明晰,“意”的领域大大拓展,“神”的自觉也空前提升,并真正地与文人艺术、自然山水相结合了。
可以说,正是出于这种对于言传意的不信任,中国美学大大拓展出了“言外之意”的领域,将注意力从言象之内的笔墨造型转移到了方外的“神”上,并拓展了“神驰”的领域,将艺术创作的自由赋予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无限性,最终主导形成了以“气韵”“神妙”等为主导的中国美学审美形态,表现出难以言传、内心顿悟的特征。
三、言意之辨中的美学政治
南齐谢赫⑤在其画论著作《画品》中论有“六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5](P176)这一论述构建了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画论,也将中国哲学中“言外之意”的品格详实地运用在艺术理论与创作中去。其六法之第一法“气韵生动”是在顾恺之的基础上将“气”与“韵”兼举,更加突出了庄学意义上清、虚、玄、远的无尽境界。[4](P175)将对“气韵”的要求定位六法之首,可见源自人物画中传“神”的审美品味已然成为中国画最高的表达目标;而对于“生动”的要求则更明确了画者应当外师造化、与物传神,将自己的咏味投入到无限的精神中去。
除了对画品高下的划分外,谢赫还在《画品》中分出六品,举二十七位画家,对其绘画成就及作品进行了深刻的品鉴。通过如此风格的褒贬、品格的排比,“气韵生动”的精神更能引起文人群体的身份共鸣,使画者在追逐同行的认可与画史的垂青中竞相求索。此种身份政治的参与将“气韵生动”中的艺术批评推向了更高的自觉。案此,笔者拟从谢赫六法之第一法“气韵生动”的美学价值说开去,探讨言意之辨以降“意”如何胜于“言”、又如何在美学争论中掺杂入政治的因素。
1.“气韵生动”的终极价值
与“传神写照”相似的是,“气韵生动”同样来源于人物品藻,“气”与“韵”本用来形容人物外形之外的意蕴。如陈传席所说:“谢赫的‘气’实指人的骨,这‘骨’当然不是孤立的骨头和骨架,而是能显示人体风度气派的骨骼结构”[5](P176),以至于后来有董其昌以“骨韵”代“气韵”;而“韵”,《说文·新附》中有“古与‘均’同”,本就有韵度之意。
“六法”中首贵“气韵生动”,谢赫所举六品二十七位画家中第一品者皆以气韵胜。如陆探微“穷理尽性,事绝言象”(见谢赫《古画品录》,下同);曹不兴“观其风骨,名岂虚成”;卫协“虽不说备形妙,颇得壮气”;张墨、荀勖(曰助)“但取精灵,遗其骨法”……所弃绝者皆为言象、形妙、骨法等象内之物,投射到绘画中表现为具体的用笔、线条、构图等形态、技法;而所珍贵者皆为理、性、风骨、壮气、精灵等言外之意,并“谨依远近,随其品第,裁成序引”,将其塑造成绘画批评中的终极标准。
“气韵说”建构着中国绘画批评的终极价值,后世画论皆宗“气韵说”。如唐朝荆浩强调山水画应当“气韵俱盛”,并延申道“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见唐荆浩《笔法记》);宋代黄庭坚更是构建了以韵为中心的书论画论,强调“凡书画当先观韵”(见宋黄庭坚《山谷文集·论书》);明代董其昌更是提出了千古名论“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散见于董其昌题跋中),更加明确了“韵”的艺术范畴与时代特征。此外,“气韵说”同样影响着其他艺术门类与文学批评,如清人王世祯“神韵说”。
案此,“言外之意”的哲学品格构成了“气韵说”最高的价值,即艺术发展几千年来的艺术自觉。
2.“气韵生动”中的身份政治
依上,“气韵生动”形成了中国美学史上的艺术自觉。然而,这一艺术自觉在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混杂着艺术之外的其他因素;其中,佛家的部派划分、儒家的身份认同都是极重要的因素。例如唐始,李思训、昭道父子以擅长青绿山水闻,南唐赵干、南宋赵伯驹、伯骕兄弟以及马远、夏圭、李唐、刘松年等宫廷院体画家亦重钩斫着色之法,于是被视为“北宗”。依此,明末董其昌提出了著名的“南北宗论”,正式划分了南北二宗:“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有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琮、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见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看似参照了佛教史上的“南顿北渐”之二分,实则将画派与禅宗相杂糅,崇南抑北,将“出韵幽澹”的南宗标榜为正宗、又将王维奉为始祖;而贬斥重钩斫等笔法形象的院体画。董其昌本人虽未言明南北方的清晰划分,只说明了不在地域与籍贯上的南北;但其世交陈继儒于《白石樵真稿》中言:“写画分南北派,南派以王右丞为宗……所谓士夫画也;北派以大李将军为宗……所谓画苑画也,大约出入营丘。文则南,硬则北,不在形似,以笔墨求之。”道明了南北二宗的真相,实则在于“士夫”(文人画)与“画苑”(院体画)之分、“文”与“硬”之分。“文”,陈传席先生解为柔软、悠淡,与“硬”之快猛躁动相对。[6](P419)而文人画之首的王摩诘更是用墨渲淡,在淡然悠远的笔墨之上向往山水中的逍遥与自由。案此,不仅进一步突出了绘画艺术品格中的“言外之意”,更贬斥了追求象内之物的画派,通过对两个画派的对立划分,将“言外之意”推崇至空前的理论高度。
然而,除了理论高度之外,给“南北宗论”注入血液的还有其本身对于宗派的划分、对于身份的认可:南北宗的划分明确了风格,对于南宗的认同寓含了褒贬[7](P30),用这些旗号抓住了士人的心理,以至于后世文人更是对“气韵生动”产生了政治性的认同,能够跻身正宗,也成了其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的努力方向与目的之一。对于这一趣味的认同,范景中先生延续贡布里希的传统,认为并不是所谓“民族精神”的积淀或“时代精神”的辉映;而仅仅是趣味与标准的交替,一种标准取代另一种标准时,影响了艺术家的意志,构成了艺术风格与宗派中的情境逻辑。[7](P10)例如“南北宗”的论说确立起来后,“南宗”的标准成了作为文人的艺术家之圭臬,尔后影响了清初四王画派,他们自诩为董其昌嫡传、属画中正派。
案此,若论“气韵说”在美学史上形成的高度理论自觉,不能单看其理论的变迁,还应同时考虑诸多政治认同、社会文化等因素;甚而言之,艺术家的意志如何形成、艺术史的进程如何发展,皆是应当追问的重大问题。然不在本篇讨论之列,兹不赘述。此处笔者欲强调:士人最高艺术理想的确立、风格与宗派的划分,皆从情境的逻辑中强化了对符号系统、笔墨技巧的超越,以及对言外象外、逍遥之域的向往。
四、结语
言意之辨涵盖了中国哲学命题中一切符号系统与意义的争辩。在各家对于“言”与“意”的争辩中,中国美学的基本形态由此建构起来。正如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所言,中国艺术中蕴含的美学须得从艺术家的心灵意境中寻求。[4](P121)艺术家们禀天地山水而摹写创造,乃是对“形”与“言”的刻画;但更甚一境界,倘若能“游心之所在”而造化自然,则是对心源之虚境的勾勒,也才能表象出具有诗心气韵的中国艺术精神。也就是说,中国美学所认为的最高的精神形式,无不是“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8](P129),无不是在万象情伪中澄观一心、透彻到“言不尽”的无限意境中去。或简言之,求美的理想尽在言之外、意之中,这便是中国美学的基本形态。
明了中国美学的基本形态后,而就具体的艺术门类而言,言意之辨中的美学品格是从言象之内的“写照”转移到了方外的“传神”之上,而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也拓展到了“畅神”的无限领域。自此,中国艺术的审美形态由对“形”的书写与描绘进化到了对“形”的超越与对“神”的追索,在方外之迹、虚无之间追寻天趣。
又就艺术批评而言,言外之意中蕴含的哲学品格主导了“气韵生动”的终极美学理想。后世的艺术理论皆以此为纲,将气韵论推向顶峰,形成了高度的艺术自觉。同时,身份政治参与艺术批评,依据对“意”的褒扬与对“言”的贬抑,中国艺术展开了热烈的宗派划分,通过确立政治性的认同塑造更高的理论自觉。
最后,言意之辨为何能引出如此长久而深刻的美学讨论?盖不过其中蕴含的中国艺术精神之本质。其与中国美学的第一次系统性结合,发生在顾恺之“传神”命题的提出,将人物品藻从有形之质引至了出韵幽澹的操行之具。而澄怀味象、畅神于山水,是言意之辨与中国美学的更进一步结合,将“意”的空间放置在了无限自由的造化之中。最后形成了“气韵生动”的美学理想,并垂青中国艺术的历史。解脱自言象之外、逍遥于意韵之中,言意之辨中的自由与玄远建构着中国美学的本质。
注释:
①汤用彤先生将之总结为“列举的全尽”,见于《魏晋玄学论稿》。
②许抗生语,1994: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研究有几大贡献。首先,汤先生揭示了玄学哲学的本质特点,指出玄学乃为宇宙本体之学;其次,他明确指出“言意之辨”“得意忘言”乃是玄学的根本思想方法;第三,汤先生阐说了魏晋玄学乃是汉末魏初思想演变的必然产物;第四,他探讨了魏晋玄学发展的基本线索;第五,他阐说了佛教玄学化的进程。
③顾恺之(公元348-409年),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今江苏省无锡市)。东晋杰出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时人们亦称其画绝、文绝和痴绝。
④宗炳(公元375-443年),字少文,南阳郡涅阳(今河南邓州)人,南朝宋画家。著有《画山水序》。
⑤谢赫,生卒年不详,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集大成的绘画理论家,提出著名的“六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