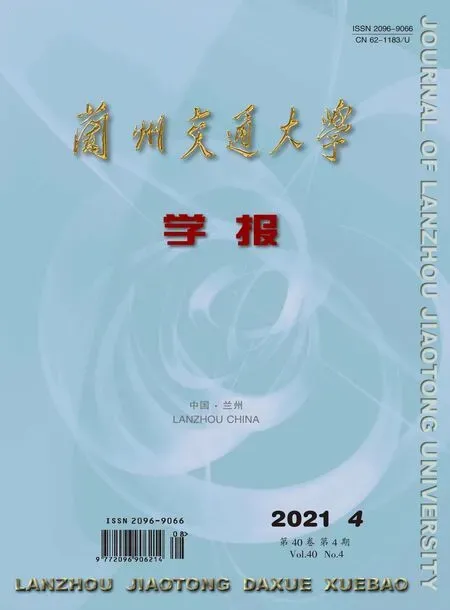再论白银货币化与明代资本主义转型幻象
2021-12-05马应保罗敬达
马应保,罗敬达
(1. 兰州交通大学 教师发展中心,兰州 730070;2.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一、前言——从魏源到贡德·弗兰克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权力是一种资本权力,而货币只有在联系产业资本循环时才具有资本的职能,成为资本的表现形式[1]。由此,明代白银货币化间接成为了资本积累的手段,从表面上看为明代资本主义转型奠定了基础。魏源和贡德·弗兰克皆谈到了白银货币化与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比如,在如何看待晚清经济问题上,魏源为后继的历史学家铺设了一条解释路径。魏源计算了公元1837年的广东进出口商品额,并得出结论:共计外夷岁入中国之货仅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元,而岁运出口之货共值银三千五百又九万三千元,以货易货,岁应补中国银价千四百九十四万五千元。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之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2]。从魏源的结论中,后人可以窥测到三层主要信息:首先,在鸦片未流行晚清社会时,中国仍然是贸易高顺差的国家;其次,鸦片的买卖仅对晚清经济贸易这一项的危害就是不可逆的,这里不计入鸦片对劳动力等其他层面的伤害;最后,从魏源的经济思想中得出一条引论,晚清社会时白银的流入和流出紧密的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
后续史学家不乏以白银的“吞吐量”去作为国家的经济发达与否的标尺,其中贡德·弗兰克就是一名“偏执”的旗手。弗兰克综合前人的数据估算认为,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美洲和日本生产了共三万八千吨白银,最终流入中国的区间大约是7000吨至10000吨。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个份额高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任何地区[3]。据此,弗兰克认为在欧洲卷入世界贸易之前,世界就存在了资本的贸易网络,而这个中心就是中国,当时的欧洲却是这个网络中的“边陲”。实际上,如果以贸易的顺差标志我国的明朝是世界的经济中心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硬伤”。有学者就指出,如果将历史的时间线延伸会发现,唐宋时期的中国贸易逆差很明显,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如何评价中国的“唐宋”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美国如今是世界最大的外贸逆差国,那么又如何评价美国[4]。弗兰克也并没有回避这一问题,他的论证也很清晰和明了:大量白银的涌入应该造成通货膨胀,然而相反的是明朝的经济处于一种通货紧缩的状态;因此,明朝并未将大量流入的白银保存起来,而是将白银再次投入生产之中,简言之白银支撑起了中国的经济生产体系,而明朝时期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网络的中心。
然而,为什么明朝作为昔日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却迟迟不能完成社会的转型?中国为什么不能依靠自身发展走出中世纪,却要被西方轰出中世纪?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弗兰克试图建立的“亚洲中心”论调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它更像是形式逻辑的游戏。历史研究起点是固有真实本质而并非是预设的概念体系,由起点展开的历史画卷也不是顽固的完善自己预设的体系。可以说弗兰克没有准确的切入中国明朝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需要深思的是大量白银涌入明朝是服务于何种的生产关系或制度,而这种生产关系或制度性因素又为何没有促成明朝步入近代化进程。
二、张居正的改革和白银货币化
公元1568年,张居正向明穆宗上了《陈六事疏》,全面阐述了他的治国主张与改革思想,其中包括“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其中与经济相关的义项“固邦本”提出: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此时张居正提出的举措除了“开源节流”之外,并没有像王安石很早就已有完整的财政举措。张居正与在经历与高拱权力斗争胜出之后,率先开启了以“考成法”为核心的吏治方面改革。学者万明(2015)认为考成法的实施,一般称为整肃吏治、提高官僚的行政效率,实际上也可视为张居正改革财政的前奏[5]。樊树志从户科给事中石应岳等的报告推断出考成法的实施颇有成效,不过还是存在官员办事效率低下、处理政务愆期的现象[6]。
赋役的完成度一直是明朝考核官员的核心,明史料记载“天下官员三年六年考满者,俱令赴部给由,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就便铨注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7]又如《明史》记载嘉靖二年的户部议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8]考成法形成了一套以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督察院,六部、督察院稽查巡抚、巡按的层层下压的系统。如果真像学者所认为的考成法是财政改革的前奏,那么层层下压官员促使其完成的是何种任务可想而知。公元1576年,皇帝还要亲自干预使各省官员及时解运税收到京师,考成法实施八年后(公元1581),张居正已经能够奏称,由于强化了财政责任与官员考成的关系,正赋不亏,征解如期[9]。考成法的实施可谓“张弛有度”,在征收赋税包括赋税质量方面,明朝上下严格贯彻考成法;而在官员的廉政方面,朝廷给予了官员的很大“放松”空间。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保定巡抚辛自修虚报税粮,明神宗不仅重责该官员,并对六科稽查部门表示,如果再有此例,严惩不贷。张居正本人对生活的品味就很考究,据明人笔记记载,张居正吃饭时菜肴过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明史》更是记载张居正“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10]。万历时期的户部尚书殷正茂、刑部尚书王崇古都素有性贪之名。黄仁宇指出,张居正的主要目标似乎是防止滥用公共资金中可以说清的项目,而税收则是最容易说清的公共资金项目。
在一条鞭法没有向全国推行前,张居正的财政改革的最重要举措就是撙节政府开支,节流的同时,张居正下一步则瞄准了如何“开源”。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明神宗下令在福建首先清丈粮田。如果按照粮食产量计税,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就势必造成有土地的豪民规避税赋,而有粮无田的贫民则被课税。张居正清丈田粮有积极的意义,这为后续的“一条鞭”赋役改革做了充足的准备。从万历八年到万历十一年(公元1580年~公元1583年),清丈工作在全国陆续完成。然而,层层下压的考成法虽然促进了官员清丈田粮的效率,但官员为了在清丈中确保税粮不致减少,官吏采用“缩弓”、“加田”、“加税”的弄虚作假行为时常有之[11]。但毕竟清丈田粮给王朝带来的利好明显大于弊端,一条鞭法也在此基础上展开。
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初年就已经被明世宗注意到,张居正赋役改革则是将条鞭之法向全国范围推广[12]。黄仁宇在结合学者梁方仲和费正清关于一条鞭法的认识上进一步厘定一条鞭法的概念:
一条鞭法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役被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对于一条鞭法学界多数给予积极的评价,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直接推动了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是社会重要转型标志之一[13]。然而,对于一条鞭法的考察不能仅停留在史书对改革章程的记录上,同时也要查验改革的贯彻过程和实施效果。黄仁宇纵向考察指出了一条鞭法为何是一种“理想状态”,其一,京师的宫廷反对全面的税收改折;其二,里甲涉及了纳税人亲身应役,虽然已经减少,但并没有完全取消。以河南中牟县为例,1584年该县推行一条鞭法,但直到1626年,该县仍然有127种差役。其三,中国北方推行一条鞭法晚于南方,这主要表现在“户银”和“丁银”的各方势力的角逐上。最后一点,一条鞭法只是修改了税收征收方法,而并没有简化税收结构,相反,导致税收结构更为复杂。这几点充分说明,一条鞭法在实施中是混乱的。王家范也对一条鞭法的实施状况做了充分的阐述,他的阐释中更加清晰的指向了明代货币白银化的特殊性。
三、畸变的货币白银化和商品经济
一条鞭法其改革目的是开源以存续明王朝,考成法则以层层下压的方式将赋税革新贯彻到底。王家范指出(2000),明中叶“一条鞭法”实施赋税货币化,固然起到了把农民推向市场的作用,但农民的赋税负担也同时有加重的趋势,境遇更为艰难[14]。白银的大量涌入并非像弗兰克所臆测的那样没有造成通货紧缩,周忱改革时松江府规定一两只能折扣税粮米四石,而到成化年间二石或二石五的粮米只能折银一两[15]。官员催征赋税时,农民急于缴纳,粮商压价,农民就又受一层损失。一条鞭法虽然以将各种杂税项并入,但中央和地方政府总是将旧项杂税恢复。条鞭之法既然没有减轻“税赋”,那么“劳役”也自然没有减轻。1566年,《徽州府志》记载,当一个纳税人估计要交一两白银的劳役任务时,他最后可能要交五、六两白银。除了赋税之外,明朝人们对白银的使用实际保持一种高度警惕。例如《庞氏家训》记载:
柴用耕田稻草,如不足,即于收获时并工割取,用船载回,堆积隔溪树下,如空闲去处,务足一岁之用而后已。若用银买柴,必立见困乏,岂能常给乎[16]。
王家范指出,粮食投入市场形成的商品化不仅是农民应付赋税的重要办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地租的货币化。至于货币地租,傅衣凌认为它不是那时社会上生产、交换诸条件成熟的结果,而是实物地租单纯的折银,这种用货币地租的出现,不仅不能减轻农民的负担,亦不能促进资本经济的发展。顾炎武曾记明末民间不得易银,内地有尤如此。因此犹如学者认为白银货币化标志明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17],其实质是忽略了中国白银使用虽早,但财政的意义重过市场流通交换的作用。
上述分析或许存在一定的争议,如果从明朝的生产、市场和消费整个环节考察,一切皆可洞明。首先从生产方面,明代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确实呈现繁荣景象。同时期相继问世了在工业技术领域影响甚远的著作,如讲述漆器制造技术的《髹饰录》、讲述园林建造理论的《园治》以及有工业百科全书之称的《天工开物》,同一朝代不同类型科学技术著作的问世反映了明代手工业景象的繁荣。从盐、糖、油、酒等生活必须品的制造到船舶、农械器具、采冶器具等规模化扩大再生产工具的制造,再到煤炭资源、石灰技术、硫磺、明矾石等矿物质的运用,都在表明这一时期手工业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空前繁荣。前文已论述农民将农产品投入市场是存有折银赋税的动机。明朝政府也出现了干预农业生产的行为,明初“下令,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伐。”[18]究其原因,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查阅《明实录》发现,明自洪武年间以来,皇室宫廷和军队需要大量棉花,明王朝长期充当了市场棉花消费的大主顾。由此,若商品经济的主要消费群体是特定的少数官僚阶层,那么产品的扩大再生产则受制于少数官僚的需求,市场对商品的调节作用无法发挥最大限度。此时,虽说一条鞭法确实增加了白银的流通货币白银化趋势,但从供需矛盾来看,其对商品经济的繁荣起到的推动作用远不及同时期政治相对宽松的西方市场的推力。
傅衣凌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及明朝涌现出了大量的商人集团,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重要表现,西嶋定生分析认为如果深究这些商人团体,他们其实都是特许商人或者是官商。王家范先生也分条缕析的阐述了整个传统的手工业明显带有“大一统性”、“工艺封闭性”、“劳动密集性”三个基本特性。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国初学天文有历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19],从天文历法研究的限制中可窥见统治阶层对科学研究的禁锢,经验科学向理论科学的转变有助于工业技术的系统化发展,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但对科学研究的束缚间接导致资本扩张的工业技术基础不够牢固。明王朝封建集权的政治体制,政治上的极端控制,人才选用八股取士,导致技术理论发展迟缓,也阻碍了科学技术探究的发展,由此手工业工艺封闭的趋势更加明显,手工业生产多服务于皇室官僚系统的大一统需求和特权阶级,导致市场的价格竞争让位于质量竞争[20]。
最后再以盐商为例,明中叶至乾隆年间是盐商发展的黄金时代,他们一方面锱铢必较,另一方面又穷奢极欲的消费。例如《太函集》记载“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莢者最豪,人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芳华盛丽非不足也”[21]。官场消费、科举消费和购置田产成为盐商花费的主要去向。万历年间,商人吴养春一次就为明王朝捐输三十万两。和盐商有利益往来的官员有时故意让盐商获利,盐商也不得不将巨额利润急公济饷,奉纳朝廷[22]。明朝人民普遍的思想仍然认为土地、房屋是最可靠的东西,因此商人获取大量资财之后往往返乡购买田产和房屋。
四、结语
明代的货币白银化不如贡德·弗兰克所期许的那样锻造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他没有准确的认识到明朝的白银货币化进程主要是服务于当时的财政税收。另一方面,白银被封建中央集权政府投入到一种畸变的生产模式,百姓的市场活动主要也是为了获取白银应付苛捐杂税和地租,明朝的少数权贵阶层是消费主要群体,除此之外的百姓消费空间其实并不大。因此,白银变相的转为一种赋税:农民纳粮折银疲于应付各种税收,中央集权的统治阶级将白银转而进行消费,如此反复最大的获利者必然是少数的统治阶级。正如有历史学家评价“一条鞭法”时指出:一条鞭法主要意义在于简化征收手续,农民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强行征收白银看似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实则往往因此加重了农民的负担[23]。
回溯考成法也可知,张居正的改革目的是提高官吏的办事效率,但是也正是在考成法的加持下,官员提升了催征赋税的效率以完成考核目标。偌大的政权管理一个国家势必会在财政管理上出现混乱,当中央政令到达地方时,为了完成目的,地方官员有很大的裁量权。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记录了大量基层财政管理混乱的案例,中央集权优先于财政管理技术可能是造成财政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就此我们导向另一个问题,如果选择“藏富于民”而非“富国强兵”的经济策略是否可以塑造一个更清晰的财政管理。中央集权的财政系统可以具体的分组交由商业市场调节,最为重要的是“藏富于民”的经济举措更可以解放农民的消费空间进而形成良性的循环。然而,封建中央集权体制终究是铁板一块的僵化了资本主义经济,一切积极和新鲜的因素都将被改造并适应现有体制。
明代的中国错失了向近现代转型是必然的,白银货币化带来的只是虚假和形式上的商品经济的繁荣,明朝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论调也仅是弗兰克意图打破欧洲中心论的偏执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