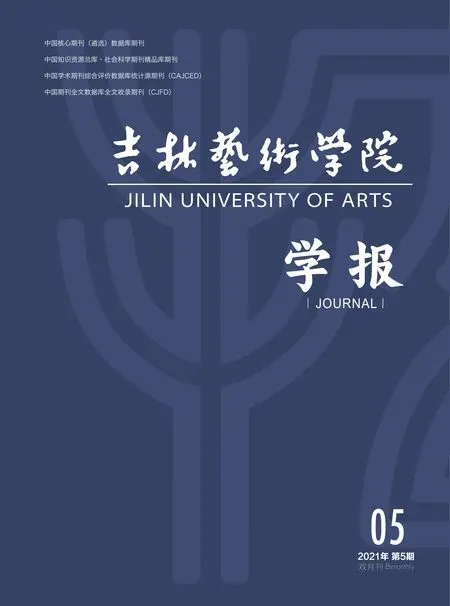刘松年三轴《罗汉图》之风格表现与图像研究
2021-12-05樊珂
樊 珂
(河南科技大学,河南 洛阳 471023)
随着佛教的传入与发展,以罗汉为题材的绘画在佛教绘画中逐渐占据一席之位。自唐、五代之后,形成了以张玄的“世态相罗汉画”和贯休的“野逸体罗汉画”为代表的两大罗汉画之图像系统。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刘松年三轴《罗汉图》隶属于“世态相罗汉画”,通过对这三轴《罗汉图》的图像分析,以表现方式、绘画内容、功能意义等为研究方向,从历史作品图像出发,呈现南宋宫廷罗汉画之样貌,进一步解读刘松年《罗汉图》的艺术风格。
一、刘松年三轴《罗汉图》图绘内容
据《图绘宝鉴》记载:“刘松年,钱塘人,居清波门,俗呼为暗门刘,淳熙画院学生,绍熙年待诏,师张敦礼,工画人物山水,神气精妙,名过于师。宁宗朝进耕织图,称旨,赐金带。院中人绝品也。”[1]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刘松年是集人物、山水、界画于一身的画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刘松年所绘《十六罗汉图》,现存世三幅,每幅款署“开禧丁卯(1207)刘松年画”,立轴,绢本设色,根据其画面内容,分别是《猿猴献果图》《蛮王献宝图》《信士问道图》。
1. 基本图像分析
在《猿猴献果图》中,画一罗汉及其童僧立于树下的场景,树上画有两只黑色的猿猴,树下有两只小鹿。罗汉浓眉高鼻,样貌似印度高僧,身着右袒式袈裟,右胸、肩均裸露在外,双耳挂有两个圈形大耳环,从打扮来看,类似印度僧人。他头上有圆形头光,眉头紧锁,似在思考,双手交叠置于胸前的枝干上。左边画面的前景是一棵枯树,树干呈“S”形,枯树叶已掉光,满身结疸。后面是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直冲画面顶端。两树中间夹着一棵小树,上面结满果实。脚下两只温顺的小鹿相对而昂,头向上仰,左边一鹿似乎在和罗汉对望,右边一鹿似乎在看童僧接果子。树上两只黑色猿猴,一只似正在摘果,另一只正将果子准备扔给童僧,摘果供奉。树下童僧右肩立一长竹杖,直插入树间,抬头仰望,合拢双袖抱于胸前,似去接果。其中,猴谐音“候”,鹿谐音“禄”,似有“封侯进禄”之寓意。
在《蛮王献宝图》中,画一罗汉持长竹杖跣足坐于一石台上,石台上铺有一毯,罗汉头部具有典型的西域特点,嘴巴微张,两耳挂圈形耳环,身着右袒式袈裟。左手肘置于左膝上,呈如意坐。罗汉头后有圆形头光,身后立一楔形石面,石面后方有几丛竹子伸出来,并冲破画面顶端。罗汉前面画一西域之人,双手托一宝盆,盆内放红珊瑚等珍宝,上身微弯向前,头微微仰起,神情谦恭,戴有头饰、臂钏和手镯。
在《信士问道图》中,画一罗汉双手持长杖坐于屏风前面,呈思考状,与前方的仕人相对,仕人手捧经卷,仰首屈身,似在向罗汉请教。罗汉深目高鼻,眉头紧锁,嘴角向下瘪,侧身坐于一圆形藤制椅凳上。罗汉头后有圆形头光,身后有一三折屏风,屏风上绘有山水画,屏风托座为卧鹿,屏风后面画有一丛茂盛的芭蕉直冲画面顶端,开出鲜红色的花朵。
单从这三轴《罗汉图》中罗汉的形貌来看,应表现的是同一人,或为同一时间所收藏。每一个罗汉身后都有圆形头光,三幅作品表现的都是两个人搭配的形式,人物造型上也是一大一小,人物的地位尊卑通过大小比例体现出来,这在早期的人物画中就有所体现。人物的姿态也都是一俯视一仰视,将供养人谦恭的姿态表现得惟妙惟肖。此三幅罗汉图均为单幅,以往关于罗汉的题材大都是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以及五百罗汉。从《宣和画谱》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在刘松年之前曾经画过单体罗汉的有五代的贯休、南唐的王齐翰、五代末宋初的石恪、北宋的孙知微,还有北宋时期其他画家所画的罗汉,但是并未见作品遗存。到了宋代,罗汉题材已非常兴盛,在创作上不是传统的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而是出现了单幅罗汉。南宋时期,刘松年作为宫廷画家,他笔下的罗汉画基本都是单体的,从他的三轴《罗汉图》来看,并不是单一的罗汉画,而是都有背景相称,山水、花鸟等自然景物融于其中,体现出南宋宫廷院体画的特点。
2. 表现手法
(1)构图与空间层次
从刘松年三轴《罗汉图》中可以看出,运用了多种构图的形式。整幅画面都是以罗汉的头部为中心点,采用中轴式构图,位于中轴线上有山石、竹子、娑罗树、屏风、芭蕉等,即使每幅作品各具特色,又使得画面更具稳定性。在佛教绘画中,经常会采用中轴线构图的形式,早期的佛画将佛陀或者主要人物置于画面的中心,其余的人物围绕中心并向四周扩散,这种形式应当是遵循某种规范。另外,为了强调佛画的庄严性,这种中轴式的构图形式也是最为恰当的。此外,刘松年还擅于运用“S”形曲线式构图,使画面呈现出一定的灵动感。如《蛮王献宝图》中的岩石、罗汉、蛮王,《猿猴献果图》中的猿猴、罗汉、小鹿之间相互呼应,也呈现出“S”形构图。
在《蛮王献宝图》中,水面与土坡的交界形成自右下向左上倾斜延伸,把水面和陆地区分开来,罗汉手持的竹杖自左下向右上进行延伸,与水岸形成了交叉视点。延伸的水岸,直达画面顶端的竹子,增加了画面空间上的延伸感。在《猿猴献果图》中,左侧的枯树横生出一枯枝,将画面空间截分为二,形成土坡、双鹿、枯树为主的前景,以罗汉、童僧、树木为主的中景。左边延伸的土坡、罗汉身后的石块、向上延伸的娑罗树,使画面的空间感更强。在《信士问道图》中,屏风呈倾斜方向自左下向右上方摆放,画家用三折式屏风表现画面的深度空间感,罗汉手中的长杖斜向摆放,打破了中轴线中规中矩的形式。左侧延伸的石板与屏风的斜向呈平行,并向画面左右两边延伸。三幅画中长杖的摆放方向都与中轴线形成了交叉视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既打破传统佛画的构图形式,也呈现出空间的深度。虽然三轴《罗汉图》归为道释画的范畴,但是画家把北宋的中轴式构图和南宋的斜角线构图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既体现了道释画的庄严性,同时也表达出了画面的空间感。
(2)疏密、虚实、大小对比
从画面内容的表现上,枝繁叶茂的娑罗树、果树与前景的土坡、野鹿,层叠的岩石、茂密的竹子与水面,屏风、芭蕉与疏朗的人物,形成了疏密对比,从而更能突显画面的人物。从艺术处理的手法上,在三幅画中可以看到,罗汉的头部都画有圆形佛光,画家对圆光进行了巧妙处理,画得很轻薄,似雾似纱,透过朦胧的头光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后面的树枝、岩石、屏风,使得隐在头光后面的景物虚化,这和其他的画面形成极为鲜明的虚实对比,既增加了罗汉的神性,也加强了画面的表现效果。刘松年在画面中大体还是采用满构图的形式,用花草、岩石、动物等充实画面,但是在一边或一角也留有空余,虚实相生。此外,从人物构图的角度来说,每一幅画都是一主一仆的样式,罗汉画得比较大,侍从画得比较小,这种用人物比例的大小来表现地位的高低,在唐代人物画中有诸多体现,在卢棱伽的罗汉画时代也是惯用的手法,凸显主要人物,画面主次分明。
(3)精细、写实、传神的表现技法
在这三轴《罗汉图》中,画家用较为写实的手法,在人物、山石、动物等方面都刻画入微,不论是造型还是笔法上都呈现出精细之姿,风格工整细润,体现出南宋宫廷院画的特点。画中人物面部都刻画得极为精细,罗汉的眉毛、胡子用线勾出,紧皱的眉头、微张开的嘴巴、露出的牙齿、脸上的皱纹、裸露的身体肌肤等都细致地描绘出来。画家在刻画的时候用笔沉着稳健,形神兼备,将人物的表情和内心通过工整细腻的线条传达出来,具有传神性。在《猿猴献果图》中,枯树的结疤,枯树下的竹叶、杂草,猿猴和小鹿身上的毛发,甚至连石榴果上的干疤和娑罗树叶上的虫眼都一一刻画出来。在《信士问道图》中,三折屏风上的木纹,竹制藤椅上的肌理纹饰,屏风上的山水画,侍从靴子上的靴带,经书上的文字等都真实地描绘出来。在《蛮王献宝图》中,蛮王的胡须、头发、发饰和身上的首饰,罗汉服饰的衣纹,座毯、竹杖底端、靴口的纹饰,以及被风微微吹起的衣带等,画家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描绘得十分具体。
刘松年在用笔上也十分严谨,自然而又富有理性,衣纹用线十分流畅,即使看似随意的一笔,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飘起的裙带,走线劲挺有力。在《信士问道图》中,衣纹的转折、起伏流畅,自然而又富于变化,尤其是对持经的信士衣纹的描绘上,用线流畅、精细缜密。在三轴《罗汉图》中的树木和山石,也用写实的手法进行处理,娑罗树、石榴树、枯树、岩石、竹子、杂草、芭蕉……用线都很工整,一丝不苟,细致入微,似乎每一根线条都是经过考量的。特别是对树木和山石的写实,用笔勾勒和皴擦,充分表现出树干的坚硬和山石的体积感。画家的功力深厚,他的线条运用代表了南宋宫廷人物画的水平。在线描上,刘松年采用的是近似李公麟的细润、谨慎的笔法。《庚子销夏记》记载:“今观笔力细密,用心精巧,可谓画中之圣也。”[2]但是和李公麟相比,他的线条更加凝练、严谨,且遵循人物造型的内在结构,取其骨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
二、刘松年三轴《罗汉图》的审美特征
1. 道释画和自然景物相结合
纵观刘松年的三轴《罗汉图》,从画面中可以看出,除了罗汉之外,还有很多配景,如山水、树木、花鸟、屏风、椅凳等,并且所占比例超过罗汉本身。把山水和人物相结合,是隋唐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样式,也是宋代人物画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特征。关于道释画与自然景物结合的问题,在五代贯休的画中已经出现山石、树木的情形,欧阳炯所作的《贯休应梦罗汉画歌》中提出如“怪石安排嵌复枯;倚松根,傍岩缝;崖里老猿斜展臂;芭蕉花里刷轻红;硬筇杖,矮松林……”[3]。从宋代人物画与山水画结合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南宋之后画面中山水布景的比例逐渐多于人物主体,例如,马麟的《静听松风图》、马远的《西园雅集图》,以及一些佚名的《虎溪三笑图》《柳溪闲憩图》等,人物不再是画面的主题,而是置于山水之中。
通过文献记载,我们知道刘松年是兼具山水、人物、界画等多种技法于一身的画家,就现存的资料显示,刘松年的山水人物画远多于道释画。在三轴《罗汉图》中,罗汉、侍从与山石及周边景物的比例已经不似早期的道释画以人物为主,而是极力描绘周边的树、石、山、动物、植物,甚至是屏风等家具都描绘得相当细致,将罗汉彻底融入山水当中。归其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北宋中期山水画崛起,出现了一大批山水画的名家名作,这或许对道释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山水画技法的成熟使得罗汉画进入南宋之后形成了独特的景象。二是南宋的画院中几乎没有专门的道释画家,据清代历鹗《南宋院画录》一书记载,南宋画院的九十多位画家都是专画山水、花鸟、人物或者兼画之。因此,对于罗汉画而言,大多数是由擅长山水人物的画家来创作,因此也就不难解释作为宫廷画家的刘松年在《罗汉图》中将罗汉和山水树石相结合的画法。三是禅宗思想的影响,到了宋代,罗汉画的功能由早期的祭祀、法会逐渐转向“观赏”性。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中说道:“佛教自唐末以后,显、密诸宗渐衰,至五代之世,禅门独存,入宋时禅风益盛。自五代流传之罗汉图及禅僧顶相图,宋时最为发展。神宗以后,专尚此等图像,而供礼拜之诸尊图像渐废,而代以赏玩之道释人物也,乃宗教绘画史上之一大变革。”[4]和现存最早的《十六罗汉图》(日本圣众来迎寺藏)相比较,刘松年的《罗汉画》从室内的场景转移到室外的自然场景,罗汉均置于大自然之中,在山林中修行,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表现方式削弱了罗汉题材的“神性”,增加了“人性”的表现。《潘天寿文集》中谈道:“宋代是禅宗的极盛时期,此间的禅画通行罗汉图及禅宗礼仪的表现,摒弃了从前对诸尊图像的礼拜,取而代之的是以道释人物的绘画,这些作品大都出自兼长山水等画科的画家手中。”[5]
2. 浓郁的世俗气息及文人审美趣味
刘松年的《罗汉图》在罗汉形象的塑造上,不似贯休的“奇状怪貌”,而是更接近世俗生活中睿智的老者,罗汉的衣着也更贴近现实生活中的人,罗汉的姿态从正襟危坐转变为随意的姿态。如《蛮王献宝图》中的罗汉赤足而坐,面露笑容;《猿猴献果图》中的罗汉双手交叉,靠于树干,面部表情轻松愉悦,温驯的小鹿、正在摘果的黑猿猴、茂密的娑罗树等,展现了一派平和的世俗生活场景。在三轴《罗汉图》中,画家在布景时十分巧妙,既表现有体现佛教思想的内容,也有现实生活中的景物,并且加入了一些文人审美趣味的题材。如《猿猴献果图》中的小鹿、猿猴、娑罗树,《信士问道图》中的芭蕉、卧鹿屏风底座等,这些在佛教中都是经常出现的景物。而童僧、仕人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岩石、石榴树、屏风、坐凳等配景也极具生活化。此外,在画面中还出现有松树、竹石、竹杖、屏风中的水墨山水等具有文人审美趣味的题材。苏轼曾在《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中描写这样的情景:“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6]道出了作为文人的苏轼回归自然、通透洒脱之感。
随着唐代禅宗的兴起,佛教早期浓厚的宗教色彩逐渐减弱,而是增加了人情味和亲切感。宋代时期的菩萨形象类同于中下层劳动妇女,罗汉更如同乞丐一般,神性开始淡化,完全进入世俗化的时代,这反映了以前由佛我对立的贵族宗教膜拜体系,向佛我一如的平民宗教膜拜体系转变[7]175。这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价值取向。而罗汉、菩萨则由于更接近人性,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日常信仰。佛性的理想化、佛经对佛的形象规定严格,不可能对佛像进行太多的创造性表现,相反,既有神通法力又兼有人性的罗汉、菩萨,更适合进行个性化的艺术创造,给了文人画家和禅僧画家很大的想象和创作的空间[7]65。佛教艺术不再仅仅是统治阶级用来教化的工具,而是凭借自身的魅力,成为人们表达内心情感、陶冶情操的途径。
3. 南宋院体画的装饰性图案
如果说,从刘松年的三轴《罗汉图》的图绘内容、表现技法、构图等能够窥见南宋院画的艺术风格,那么,通过对《罗汉图》中精美纹饰的研究,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此三轴《罗汉图》或是在统治者的授意下完成的,二是带有典型的宫廷画的艺术元素,或可以被视为南宋宫廷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往的罗汉画在对服饰以及其他配饰的描绘上大多是以简单、素雅为主,但是在刘松年的三轴《罗汉图》中,人物服饰上精美的花纹、座毯上繁缛的图案、藤凳的纹饰等,无一不彰显出华丽之姿,配以浓重的设色,表现出宫廷院画的特点。
在《猿猴献果图》中,罗汉上身着蓝色条纹的僧服,腰间系有墨色绶带,下身着石绿色长裙,足蹬红色芒鞋,整件衣服上布满白色的钱币纹和梅花点。在《蛮王献宝图》中,罗汉坐于石台上,其上铺有一块石绿色的毯子,毯子中间绘有牡丹纹,并露出三只展翅高飞的凤凰穿梭于花卉中,毯子的边缘饰以卷曲的云纹作装饰。罗汉的服饰上布满浅棕色的底纹,并且有大朵盛开的莲花图案,深褐色的条带上也是细密的连续花纹。下身穿绿色条纹状的长裙,裙摆边沿有一条装饰带,上面绘有精美的纹饰,蛮王头戴精美的首饰,胳膊上有臂钏,下身的裙子上也有花纹装饰。
在《信士问道图》中,罗汉的袍服上布满纹饰,深棕色的衣领和袖口上饰有白色的梅花点,罗汉的衣袖上有六瓣团花和点状圆圈组成的图案。浅色外衣上布满白色点状菱格纹,长裙由于坐姿产生了许多褶皱,用层层波纹表现,裙摆处有一宽一窄两条装饰带,上面绘有精细的纹饰。脚穿红色系带芒鞋,芒鞋上还嵌着一颗石绿色宝石。服饰上繁缛华丽的装饰与旁边仕人朴素的服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卢棱伽的罗汉画或贯休的罗汉画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这种极富装饰性和浓烈设色的作品,如果要探究这种表现形式的罗汉画,我们可以从宋代宫廷的肖像画中进行分析[7]274。蒋复璁先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南薰殿画像考》一文中考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典藏的帝后皆出自当时的画家,且大多数供奉于宫廷的神殿内[8]。因此,从《宋仁宗后坐像》和《宋神宗后坐像》中的装饰纹样图式和表现手法,可以看到宋代宫廷画的样式。皇后礼服上的装饰豪华妍丽,衣服上有代表皇后身份的五彩翚雉,以泥金、石黄、石绿、朱砂和墨等五彩绘成,两两相对,整齐排列,形象精确而生动,领口和袖口上装饰有龙纹和祥云纹,身后椅子上也垫有毯子,毯子上饰有繁复精美的花卉纹和龙纹,通过豪华的装饰纹样来显示其高贵出众的身份。在《蛮王进宝图》中,罗汉衣纹上的莲花印纹和座下毯子上的凤凰纹饰采用的是佛教中常用的纹饰,尤其凤凰纹也是宫廷贵族常用的纹饰。三轴《罗汉图》当中的纹饰大多来自宫廷内普遍所认为的富贵或者吉祥的图样,罗汉衣服的花纹多用浓丽的胡彩,施以金碧、朱碧、褐紫等色彩,对比强烈,纹饰细密,富有装饰性。如《信士问道图》中,罗汉衣袖上的六瓣点状花纹和《宋仁宗皇后像》礼服上的六瓣团花外形相似,《宋神宗皇后像》中用白色点状画装饰图案的画法和《罗汉图》中纹饰的表现技法一致。在整幅《罗汉图》中所画服饰的图案都排列有序,不论是花卉还是凤鸟,都表现得一丝不苟,栩栩如生。可见,刘松年在处理罗汉服饰装饰纹样的用心程度上丝毫不亚于宋代的宫廷肖像画。尤其是在《蛮王献宝图》中,罗汉的服饰和毯子的装饰极为华丽,蛮王身上的衣饰和另外两幅图中的供养人相比要复杂繁缛得多,并且罗汉身下有坐毯,其精细的程度更具宫廷院画的特点。
从《罗汉图》的图像来看,不论是袍服、僧服、中衣、长裙还是偏衫,都勾勒得非常详细,纹饰上用众多细小的圆形点状作花纹,排列有六瓣花的图形。设色上多用石青、石绿等较为冷色的色调,不似民间罗汉画的浓艳设色。整个画面在细节处理上十分用心,不论是石榴果上的干疤、枯树上的结疤、毯子、水纹,还是脚上的芒鞋,头上的头饰,等等,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能看出画家的精细。综上所述,三轴《罗汉图》从衣着、装饰纹样以及色彩运用上,和宋代宫廷肖像画的装饰手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加之刘松年作为南宋宫廷画院的画师这一身份,以及南宋时期对罗汉信仰的尊崇,因此可以认为此三轴《罗汉图》应当不是画家随意画之,尤其在《蛮王进宝图》中,所呈现的中轴线构图,罗汉和蛮王服饰上的精美装饰纹样,画有凤凰、牡丹图案的毯子等,如此华丽的装饰、细致的勾线、典雅的设色等,极有可能是在皇家的授意下而完成的,用于赏玩。
三、刘松年三轴《罗汉图》图像的宗教内涵
1. 图像中“罗汉”身份小考
从画作中并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文字介绍图中老者的身份,也没有任何关于罗汉名称的榜题,但是在画面中,老者头后画有淡绿色渐层的圆光,关于圆光,大多数出现在和佛教题材相关的作品中。丁福保的《佛光大辞典》中有“光相”一词,并对该词作如下解释:“光相,又作光明相。指佛、菩萨等诸尊身体发出光明之相,象征佛、菩萨之智慧。绘画、雕刻等所表现之光相多系圆形,故又称圆相、圆光。”[9]2178“头光:(术语)在佛或罗汉顶上之圆光也。又曰背光。亦曰后光”[10]503。《猿猴献果图》和《蛮王献宝图》中老者穿着袒右肩式袈裟,是典型的印度式样,《信士问道图》中的老者身着水田衣、长袖笼的僧袍样式。由此可推断此三轴中的人物为罗汉。如果细观这三轴罗汉的形貌,就不难看出应该为同一罗汉的形象,而不是十六、十八、五百罗汉中的三尊。在刘松年所作《罗汉画》年代相近的罗汉图中,有贯休的《十六罗汉图》、清凉寺本的《十六罗汉图》以及金大受的《十六罗汉图》,每位罗汉样貌各异,从图像中可以清楚地区分开来。由此可以看出,刘松年的三轴《罗汉图》并没有刻意强调罗汉个体的描述,更多的是传达“罗汉”这一宗教题材的内涵。
2. 画面配景里的“宗教元素”
从道释画的角度来看,对三轴《罗汉图》的解读,除了罗汉之外,
还对其他的景、物进行探讨,更有助于对作品本身深层次的理解。在《猿猴献果图》中,画了石榴果、小鹿;在《信士问道图》中,三折屏风下的座托为卧双鹿;在《蛮王进宝图》中,服饰上的莲花纹等,在图像上都有一定的宗教含义。《佛学大辞典》中记载:“石榴(植物)是鬼子母神所持之果物,一切供物果子之中石榴为上。”[10]431“以鹿为转法轮之三昧耶形。两边安鹿,伏跪而住”[10]951。此外,在这三幅画中,其中两幅罗汉手扶长杖,另外一幅中长杖虽然在童僧手里,也应为罗汉之物。《佛光大辞典》又载:“杖,僧伽随身十八物之一。为僧人游行时,若年老力衰、病苦缠身,或为驱遣蛇虫等所必携行之物。”[9]2956虽然刘松年的三轴《罗汉图》从以往的“神界”走向自然界,呈现出一派自然和谐之景,但其中的宗教元素仍然在图像中有所呈现。
3. 供养人的图像表现
纵观三轴《罗汉图》中的人物,除了罗汉之外,在罗汉的右侧皆立有一人,是为供养人。《猿猴献果图》中的供养人应为一童僧,身着汉式袍服,正合袖准备接猿猴摘下的果子。《蛮王献宝图》中的供养人一副西域式样的穿着,双手捧金色的盘子,盘子内放珊瑚、宝石等珍宝,头上、手臂以及手腕上都有复杂的珠宝装饰,从他的服饰上来看,应出自贵族。《信士问道图》中的供养人手捧经卷,似乎在向罗汉请教,身穿圆领袍服,为北宋士大夫阶层平时所穿常服的式样。脚上的芒鞋上也嵌有石绿色珠宝,头上戴有方形桶状的帽子,或为东坡巾,东坡巾即为苏东坡所戴,故而得其名。此巾的式样有四墙,墙外有重墙,比内墙稍窄小,东坡巾为许多士庶所效仿和喜爱[11]。
《法注经》记载:“佛薄伽梵涅槃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并眷属等,令其护持,使不灭没。及敕其身,与诸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12]6“福田”思想的影响,使得罗汉信仰被广泛接受并兴盛起来。另《法注经》记载要供养罗汉,“诸仁者若此世界,一切国王辅相大臣长者居士。若男若女,发殷净心,为四方僧设大师会,或设五年无边师会,或庆寺、庆像、庆经幡等施设大会,或延请僧至所住处设大福会,或诣寺中经行处等安不上妙诸坐卧具、衣药、饮食、奉施僧众,时此十六大阿罗汉及诸眷属,随其所应分散往赴,现种种形,蔽隐圣仪,同常凡众,密受供具,令诸施主得胜果报”[12]6。其中可以看到以制作图像、经幡,奉施卧具、衣药、饮食等是为“财物供养、饮食供养”,而罗汉以种种形式回报供养者,这在佛教的布施中属于“法施”的范畴。《法住记》的主题思想有两个:一是宣示罗汉将承担起佛教护法任务,二是劝慰世人供养罗汉能得大果报[7]39。
在敦煌金刚经的经变壁画中有对财物供养的描写,大多数是一长桌子上放置珠宝物品,桌前有受施者。在《蛮王献宝图》中,有蛮王手中捧的盘中珠宝,有供养者“蛮王”,有受供养者“罗汉”,符合“财物供养”的图像法则。画中蛮王比例较小,且以侧面示人,虽然从服饰上看应属于贵族,但是画家似乎并不是要刻意地强调他的真实身份,主次关系非常鲜明。因此,这幅画突显的应当是罗汉个体以及“财物供养”这一宗教主题。《猿猴献果图》描绘的是猿猴摘果供养的情景,虽然果子是由童僧接的,但是最终要供养的是罗汉。在《信士问道图》中,仕人手持经书,仰望罗汉,似在请教。只是在以往的罗汉画中,一般是罗汉主动为他人说法,但在这幅画中,是仕人主动请教。纵观此三轴《罗汉图》,刘松年在供养人的处理上都采用主动的姿态,猿猴递果、蛮王捧宝、信士持经问道,这或许反映的是让民众主动对罗汉进行供养,以此来获得福报。
四、结语
宋代的罗汉画已经承载了较多的内涵,由宋人的“现世利益”所决定的消灾、除厄、祈雨、修福等感应故事,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大量记载。可见,宋代社会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对于罗汉保国安天下、保家追善的信仰比较普遍,较之唐代,罗汉的地位和对罗汉信仰的深入有了较大的提升[7]278。五代之前,罗汉画主要是以吴道子、卢棱伽等人的风格作为样本,直到五代画僧贯休使罗汉画的风格有了很大的转变,宋代罗汉画继续发展,罗汉画的题材也由神秘、庄重逐渐走向了世俗、自然。刘松年的三轴《罗汉画》是研究南宋画院罗汉画题材的重要图像文本,画家将山石树木等自然景物与人物相结合,进行精心布置和渲染,淡化了作品的宗教氛围。其严谨细腻的装饰手法和色彩应用充分代表了南宋院画的水平,对后来金大受的罗汉画以及明清时期的罗汉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