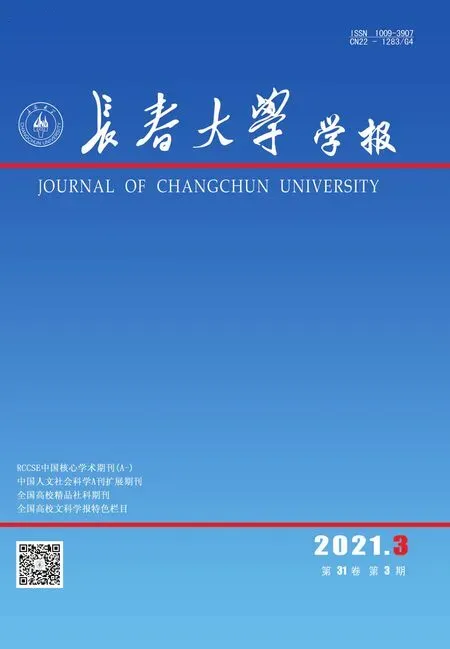论西方音乐肖像作品的创作特征及演变
2021-12-04李云洁
李云洁
(闽南师范大学 艺术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肖像在艺术作品中一般是指对具体的人或集体的描绘。最初,肖像出现在美术作品中,之后发展到文学、音乐以及电影电视艺术中。肖像的创作目的是表达人物的外貌特征,如人物的姿势、手势及面部表情。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露,综合展现出人物复杂的生理与心理特征[1]。我国东晋顾恺之也提出“以形写神”的“形神论”,为我国肖像绘画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在音乐中,肖像一般是指在标题音乐作品中或者在作品的某一乐章中,其主要音乐主题是描写的人物[3]。其创作对象是具体的人。一般外貌特征的表现有姿势、手势、行为及语言特点等,另外还可以表现人物的性格、气质、精神面貌或思想感情,从而达到神似[4]。这些人物形象的所有特征都是通过音乐手段(音乐语言、体裁及风格)重新创造而来,而这些人物形象创作的方法,其历史发展和风格的变化在音乐学中研究还需要更加的系统。所以明确18—19世纪作曲家作品中音乐肖像风格的特征,阐述其基本音乐创作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音乐肖像的诞生——弗朗索瓦·库普兰的作品
肖像从雕塑、素描与色彩的艺术形式延伸至不同的艺术作品领域当中,而肖像出现在音乐作品中已经若干个世纪,且所有的音乐特征都属于新时期的音乐艺术,其艺术观点是“基于对外部和具体事物的关注,以及对人类情感多样性的关注”[5]。最早的音乐肖像出现在17—18世纪英国维它琴和法国大键琴的作品中,以法国作曲家弗朗索瓦·库普兰的作品最为突出,其总共创作了几十个器乐肖像作品。他说:“创作作品时,我始终牢记某个对象:它是由各种不同的情节展现给我。并且,这些作品的标题符合我的意图……当他们在我的手指下演奏时,发现他们很相似。”[6]
(一)题材丰富的库普兰音乐肖像作品
在库普兰的音乐肖像中,有许多不同的典型形象出现,比如贵族形象:献给波旁公爵的年轻女儿的作品《波旁公主》;献给路易十四的女儿,同时也是库普兰的学生的《无与伦比的风度》或《孔蒂公主》;有为纪念路易十五的新娘,波兰斯坦尼斯洛斯一世的女儿《玛利亚公主》;也有纪念摩纳哥一世亲王安东尼·格里马尔迪的小女儿《摩纳哥的缪斯》;还有描绘公爵夫人拉·费特的女儿《拉梅内图》等。
有些肖像作品并不是库普兰专门为人而创作的,只是描绘其对周围人的印象。如描写皇家管风琴家加布里埃尔·加尼尔的妻子《拉加尼尔》;有为纪念作曲家朋友让·巴蒂斯特·马雷的女儿而创作的《拉玛丽列特》;还有对作曲家安托万·福克雷的妻子创作的《华丽的福克雷》等。库普兰还在作品中刻画了自己的家人,如献给作曲家两个女儿中最小的玛格丽塔·安托瓦内特的《拉克鲁伊,或拉库佩里内特》《莫妮卡姐妹》和自己的妻子《拉库普兰》。
有些肖像只以女性名字命名,因此无法确定其原型,如《娜内塔》《咪咪》《马尼翁》《贝比》;有些作品名有明确的人物性格特征,如《美丽温柔的娜内塔》《温柔的芳淑》。
作曲家还在一些作品中忽视人物的内心情感,只展示人物的职业身份。这个特点体现在库普兰的集体肖像作品中,如乐曲《年轻的修女》《朝圣者》《见习修女》《葡萄采集人》等。这些作品并没有刻画单独的人,而是以集体的特征进行展示,具有一种普遍的情感,但这个情感没有明显的人物差别。如展现高贵气度的《哀歌或三个寡妇》,展示内敛与悲伤的《老者》等。
在神话题材的肖像作品中,作曲家同样刻画了单人肖像与集体肖像,如乐曲《戴安娜》《忒耳普西科瑞》《花神芙罗拉》《希尔瓦娜斯》。也有描写具有国家和民族特点的肖像,如作品《佛罗伦萨人》《西班牙女人》《巴斯克人》和《中国人》。但是,这些作品表现人物民族性的程度并没有很高,我们只注意到作品《佛罗伦萨人》的旋律中带有升六级音极具意大利风格;而《玛丽公主》第三部分中带有波兰舞曲的节奏,表明玛丽亚·莱什钦斯基具有波兰人的血统。最有意思的是,作曲家库普兰还创作了一首钢琴小品《中国人》,但作品旋律的色彩较为中性,没有明显的中国民族音乐特点。
(二)弗朗索瓦·库普兰音乐肖像的体裁及创作方式
库普兰的大多数音乐肖像的体裁都属于“小型乐曲”,其标题反映了所描绘的人物原型的鲜明特征。如《胡闹的女人》《危险》《妩媚》《深情》和《丑角》等。库普兰在创作这些作品时,试图通过其特有的情感状态来描绘人的性格。在描写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上,作曲家需要构思作品的体裁、速度、节拍、情绪以及音乐主题和表现手法。这些人物性格特征通常是借助一个或两个细节来体现,如《西尔瓦诺斯》通过跛行的节奏变化,展现他山羊蹄的步态;通过命令式的切分节奏作为动机来展现《女巫》;用大量跳动的旋律来展示《调皮的女孩》;还有通过低音区的多声部来描绘公爵夫人拉·费特的女儿《拉梅内图》。另外,在一些集体肖像作品中,库普兰通过两种调性的运用作为人物情绪的对比(庄重和无忧无虑);或是通过大小调的变化来进行创作,使一个形象同时具有不同色彩,如《年轻的修女》和《双胞胎姐妹》。
库普兰还做了较多的谱面标记,如“温柔”“天真”“优雅”“活泼”“高贵”“庄重”“强调”,有的标记更加细致,如“非常温柔”“稍微温柔”等。这些标记在作品中并没有打算展现角色的内在情感,而只是记录所描绘人物的性格特征。库普兰甚至在作品《贝比》中较为罕见的运用“粗心、懒惰、冷漠”标记,让人印象深刻。
不同的角色性格决定其相应的创作方式,在《娜内塔》中,运用了颤音与倚音来体现天真而朴素的带有r口音的女性形象。作曲家也常常用辅助标题来定义舞曲。如《独一无二》《雄伟辉煌》《忧愁的》萨拉班德舞曲,《勤奋的》阿莱芒德舞曲,《精致的》《阴郁的》《亲密的》的库朗特舞曲等。很多肖像作品常常具有舞蹈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作品风格、节奏形态、和声和曲式,还包括明确的平行乐段结构,也包括对称的带再现乐段的完整结构。特别重要的是库普兰的回旋曲,在作品《查贝公主》和《莫妮卡姐妹》中,短小的主题动机在作品中多次出现,而这种由舞曲发展出来的回旋曲形式,也是展示歌舞音乐的主要特点。
在库普兰的音乐中,刻画的情绪缺乏极端表现,如“快乐”“顽皮”“恶作剧般的”情绪永远不会变得兴奋;而忧郁、悲伤也不会变成沮丧和悲观。如作品《顽皮的女孩》刻画的并非快速与躁动,而是优雅高贵,而作品《忧伤》相对于戏剧性描写,作曲家更注重庄严与肃穆。这一时期的音乐所描绘的人物感情还仅仅出现在谐和的、合理的音乐色彩框架里,反映出库普兰所创作的肖像作品具有宫廷艺术美学思想,是古典主义理性与情感和谐统一的思想特征。
总的来说,在库普兰创作的音乐肖像中,大多数描绘的是女性形象。而且,她们的原型主要是作曲家周围的真实人物。其音乐形象是拟人化的情感、人格化的情绪。每个肖像作品通常是一种情绪,一种情感,而这些情感的描写是通过简单的方式体现,即通过体裁、调性和节奏等手法来体现人物一种或两种性格。库普兰作品另一个特点是标题非常简短,他认为仅借助这些帮助即足够。简短的标题能将听众的感知引导到正确的方向,无须进行详尽的阐述,而所被创作的人物情感、情绪和性格特征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些特征是由作曲家来展示的,而并非是主人公的个人经历。
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期音乐肖像的繁荣
音乐肖像真正的绽放出现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这一时期许多作曲家都创作了大量的音乐肖像作品,其中以舒曼、格里格与穆索尔斯基的作品更为典型。
(一)罗伯特·舒曼浪漫主义音乐肖像的作品特征及创作方式
19世纪最精彩的音乐肖像作品是罗伯特·舒曼的钢琴套曲《狂欢节》。其音乐充满了印象画的特点,类似于人物写生画。作品展现出在舞会的背景下,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各自都有着自己的角色,包含若隐若现的脸庞和片刻交谈的节日场景。作品描绘了一系列的核心人物肖像,有约瑟比乌斯、弗洛里斯坦、基阿琳娜、埃斯特雷拉、肖邦和帕格尼尼。其中第一对夫妇是埃斯比斯和弗洛里斯坦,一个是忧郁的、沉思的,梦幻般的,另一个是活泼的、充满激情和活力的。这两个作品矛盾的性格特征其实是舒曼对于自己“我”的认知。所以在作品《弗洛雷斯坦》和《约瑟比乌斯》中,舒曼明确了自己内心性格的矛盾与对立。根据作者的说法,它们在舒曼的音乐和文学作品中不断地“出现”,是作曲家本人的个性,表达其性格的两个方面。弗洛雷斯坦“冲向天空”的主题体现了浪漫般的热情,对未来的渴望。但他脾气暴躁,有着自相矛盾的思想随意性。作品中有舒曼的表演特征标记“激情的”,表达了他的激情和任性的感受,但其主要音乐形象是急躁的、焦虑和不安的。这不仅体现了人物的内心状态和肢体语言,还展现因激动而感到窒息的语言节奏等。弗洛雷斯坦的叛逆性格通过旋律而迅速上升,并在弱音上静止而展现。这与从作品《蝴蝶》借来的“柔板的”抒情主题形成了鲜明对比。音乐中的张力因不和谐的和声、不稳定的功能以及在突然停顿的节奏中扩张。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弗洛雷斯坦》的结尾打乱了旋律的节奏,将占主导地位的动机进行分裂,并在结束后,毫不停顿地出现作品《妖艳的女子》。这一微妙的细节说明了不知疲倦的渴望是舒曼肖像的本质。
相反,在《约瑟比乌斯》中,节奏的感受几乎不存在,悠扬的旋律,充满了梦幻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这种效果是由“连绵而有呼吸”的旋律来产生。婉转的七连音好像“脱离”了双声部的伴奏,左手透明般的两个声部增加了内心的清澈印象,这个形象通过复调音乐结构逐渐显示出其内心世界的丰富,并且作曲家认为这个作品应该“低声地”演奏。与《弗洛雷斯坦》一样,在《约瑟比乌斯》中,不仅描绘了人物性格,还描绘了人物形象特征:一个梦想家、沉思者;一个有着轻盈的动作、温柔的语调和动作缓慢的人。
作品《帕格尼尼》和《肖邦》的对比方式与《弗洛雷斯坦》和《约瑟比乌斯》非常相似。舒曼模仿了肖邦钢琴作品中歌唱般的旋律,也模仿帕格尼尼高超的小提琴技巧。帕格尼尼的音乐模仿了他著名的《恶魔的拨奏》,在这里,一切都突出了艺术家惊人的技巧和恶魔般的气质:难以置信的跳跃节奏(不匹配左右的声音)和难以置信的左手强弱的动态对比,这种快速的运动正变得越来越大胆和古怪。而作品《肖邦》的形象通过柔和的旋律来表达,透明般的琶音织体背景,仿佛他钢琴作品《夜曲》的抒情风格再现。舒曼精确运用“风格模拟”来反映肖邦旋律创作的一个微妙细节,即在第一个音符之后停顿呼吸,给旋律带来了特别轻盈的空气流动感,如同肖邦的《夜曲Op.9 No.3》。
通过体现作曲家的风格来刻画人物是舒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造性发现,可以称为“舒曼的肖像”,是全新的音乐创作方式。
另外,浪漫的华尔兹《基阿琳娜》和《埃斯特蕾拉》代表了一对反差较大的女性形象——克拉拉·维克和恩尼斯汀·冯·弗里肯的面具。首先是真诚,内心的魅力,其次是热情。克拉拉的本质是“寻找”,她的热情和心态通过“寻找温暖”而展现出来;而后者被深厚的人性和渴望的语调围绕,是一种紧张而虚幻的节奏,抒情的语调被强烈的节奏抑制,并融合成一个扩张的旋律。
《娇艳的女子》的肤浅本性则是通过“轻浮”的语调来刻画,时而活泼,时而狡猾。它们都来自一个听起来像笑声的开场白——银色的铃声和寒冷般的笑声。如果说《弗洛雷斯坦》和《娇艳的女子》倾向于人物内心的独白,那《约瑟比乌斯》和《肖邦》则倾向于展现“歌”或“舞”曲(轻快的抒情短歌或器乐曲)。而在《娇艳的女子》中,我们又清楚地“看”到了舞蹈,作品通过两个小节的引子仿佛展现芭蕾舞的入场,优美的芭蕾女舞者的身影划过舞台,为舞蹈做好站立姿态的准备。
舒曼在《狂欢节》中不仅刻画了人物,还巧妙地结合背景,就像是有画框的绘画作品一样。背景中的舞会场景与华尔兹舞蹈已经成为这个套曲的核心元素,为作品建造了一个完整而动态的舞会背景。这不仅仅是非人格化的戏剧“背景”如《变奏的序言》《高贵的圆舞曲》《德国圆舞曲》,而是渗入了人物的音乐形象:弗洛雷斯坦、基阿丽娜和埃斯特雷拉,成为“圆舞曲—肖像”;《肖邦》的“夜曲肖像”及《娇艳的女子》“圆舞曲—谐谑曲肖像”。与圆舞曲体裁不同的是,他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帕格尼尼的弦乐《练习曲》风格和充满幻想的抒情轻快短小的器乐曲《约瑟比乌斯》。舒曼的音乐肖像作品特点是小型的“音乐人物写生画”,作曲家具备在音乐中探寻对于场景、情绪的生动印象,具备对人物肖像的音乐写生能力。但他并不寻求大篇幅的创作,而是把它们限制在多个“音乐小品”中,并将之组成一个完整的套曲形式。
(二)格里格梦幻般的音乐肖像作品特征及创作方式
格里格的音乐创作对象也较为丰富,且差异较大。其《抒情小品》创作的内容来源于生活所见所闻,但不局限于抒发情感和描述心境[7]。有描写动物的《小鸟》和《蝴蝶》;有描写挪威民间传说中虚构的角色《风之精灵》《精灵之舞》《侏儒进行曲》;也有以作曲家为对象的作品如《海顿》《向肖邦致敬》等。以上所有的音乐作品都属于“钢琴小型曲”。但不同的是,格里格并没有将作品创作为类似《狂欢节》的钢琴套曲形式,而是将所有独立的音乐作品汇编成了曲集,形成《格里格抒情小品集》。
《风之精灵》选自格里格《抒情小品》第七册,它描绘了一个梦幻般的音乐形象。在中世纪的信仰中,它是风元素的精灵,有男女两个性别,具有空气的形态,是具有人格化的神话形象。从外文对这部作品的命名来看,这部作品描绘的是女版的风元素精灵,她叫作希尔菲德。该作品的主题旋律是轻盈的,具有较明显的空间移动感,频繁出现的休止符展现了精灵飞翔时较多的悬空停顿,旋律由较小的动机发展而成,以鲜明的节奏轮廓、优雅的旋律和“神秘不可捉摸”的动作为特点。作品的旋律大部分出现在高音声区,“跳动”的音调和快速的色彩变化营造出轻盈与广阔。作曲家的“轻快的”标记和断奏的演奏方式也印证了这一点,作品中频繁的速度变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创作手法都为创造优美的空中精灵,展示出了令人信服的童话般音乐形象。
格里格另一个神话人物是《抒情小品》第十册中的第三首《精灵之舞》(又称狗头人)。小巨魔的形象以神秘的地下活力为特征,使人感知身影在黑暗光线下迅捷地移动。这部作品基于运动的特征,体现出角色的神秘感,具有极强的压迫感。本曲节奏迅猛,旋律的力量对比强烈(由很弱变为突强),通过和弦的奇妙运用增加了神秘感和不可预测性。在本曲B段,运用和弦组成的乐句具有递进关系,呈现出递增的音乐感受,具有强烈的入侵和危险感。B段末尾在左手的二度下行跑动下,生动地展示出了地下精灵的神秘与诡异。这个乐段是作曲家对于声音与和声运用的经典之一,特别是和弦进行时的突然停顿,类似一种号角。这种创作方式,韦伯与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在有关森林童话的音乐作品中也使用过,为童话人物创造了非常逼真的音乐背景。
除了童话肖像的作品外,格里格也创作了大量的人物系列,这些作品创作的都是真实的人,其作品风格取决于作曲家与挪威民间音乐的深厚渊源。在这些作品中,普通挪威人民的民族性与职业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较为典型的有《抒情小品》第五册作品《牧羊少年》,其旋律让人联想到挪威牧羊人的歌声“洛克”(又被称为“牧牛”),一般是由管乐演奏(长笛或牧羊人的牛角)。作曲家再现了挪威民间音乐的典型特征:小调色彩主题中增IV度的运用,通过“牧牛”本身特有的即兴演奏特征展现短小的三声部旋律。旋律的开端源于简短的民谣,简单易懂,能够引起明确的画面联想。长笛动机通过变奏成了旋律发展的基础,复调在作品的中间部分出现,仿佛听到了牧羊人号角的“呼唤”。最后,“卡农”出现在再现段中,仿佛是对牧羊人的回应。之后旋律进入到低声部,表明牧羊男孩的离去与之后的寂静。
具有极简主义特点的人物形象出现在格里格《抒情小品》的第三组《孤独的流浪者》。一个孤独的旅行者的形象:他表现出对生命的无助与希望的丧失。“叹息”音调以几乎不变的弱起节奏弥漫在整部作品中,给人留下非常疲惫的印象。钢琴中声部感情色彩丰富,悦耳动听的旋律是作品的主要表现因素。旋律以饱满的六度音程构成两个声部,没有宏伟的构造。它以中声部中的持续延长音作为背景,使得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一个孤独的流浪者身上。结尾出现渐慢的主题,更是凸显和强调了叹息与无奈的心理。这是一种表达精神状态的创作技巧,描写了孤独与悲伤的心理,在之后的作品尾声上,旋律稳定结束在小调主音上,又留给了人们一点点幸福的幻想。b小调的调性音色更是加深了流浪者孤独的印象。该流浪者的音乐形象几乎没有描绘出他的外貌特征,只是重现了他的情绪和心情,这样的肖像可以被称为“心理肖像”,只突出人物的内心特征而非外在。
格里格创作的音乐作品中,格里格的绝大多数音乐作品都描绘神话人物,较少涉及真实的人物肖像。而真实的人物肖像出现在《抒情小品》第六册,是以丹麦作曲家的人名来命名的——《加德》。这是一个非常温暖、抒情和浪漫的音乐小品,是专门纪念丹麦小提琴家和作曲家尼尔·加德(格里格的老师)。第二部作品来自格里格钢琴组曲《心情》之练习曲《向肖邦致敬》。
(三)穆索尔斯基人物性格音乐肖像作品及创作方式
在19世纪的俄国,音乐迎来了新的发展。在穆索斯基的钢琴作品中出现了较为典型的肖像作品。作曲家通过参观他的画家朋友维克多·哈尔特曼作品的印象,创作了一系列的音乐肖像作品——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作品以其鲜明而生动的“音乐画像”而著称,在音乐肖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侏儒》描绘的是一个相貌丑陋、内心敏感、具有恶劣态度与警惕目光的侏儒人。这个作品有一些描写外形的音乐元素,但整体是属于描写人物的心理。快速的六连音在低声区跑动,非常突兀的主题动机展示出了人物刻薄的形象,刻画了一个矮小、跳跃、动作笨拙的侏儒形象。其动机也反映了角色破碎的内心世界。作曲家通过音乐的创作手法刻画了一个性格怪异的、行为难测的形象,并确立了角色的性格和行为。作品以八度音阶重复的单音作为旋律,最初出现在低音区中,突然被急剧的八度跳音打断,仿佛瞬间的空间移动(旋律横跨两个八度)。而随后主题出现的非常清晰的连接,短促与延长音的动机显露出侏儒特有的步态——“跛子”,显现了逼真的视觉效果:在这里,他“跳跃—停顿—跳跃”,如此高的运动能力和敏捷的动作给人以特殊的紧张感和原始不安的气质。低音区的颤音增强了音乐的阴郁的特征,类似牙齿在上下抖动,它们似乎模仿了这种非人类痛苦与悲伤的声音,最后以一段非常快速的段落“消失”。
“富裕和贫穷的两个犹太人”——具有社会心理特征的人物场景对话。该作品属于双人肖像,两个角色鲜明而准确的进行对等描绘。富人的主题带有命令式的语调,表达了鄙夷和傲慢的态度。它通过相邻八度的同旋律音的形式呈现,具有人物的权威性。断断续续的语句,没有任何的伴奏,只是独立的叙述角色本身的语言。第二个主题具有哀号的特点,这个穷人的主题是仿佛在向富人恳求某事,其主题是基于抽泣的语调,展现其委屈与讨好的状态。这个穷人着急地提出他的要求,而富人并没有打断他,但也没有仔细聆听他。富有表现力的高音旋律描写了穷人颤抖的内心,“颤抖”主题是一种惊慌的语调,通过较多的三连音与带附点的节奏型与低音背景的音程同步演绎。这里的富人主题与穷人主题交织在一起,直到结尾处出现了穷人的乞求声,但最终被富人粗暴地打断而结束。
穆索尔斯基也创作了童话音乐人物形象——《鸡腿上的小屋》。作品描绘的是俄国童话故事中著名的妖婆,她叫“巴巴亚伽巫婆”。她拥有怪异、狡诈与恶毒的外表,并在木屋里快速地飞行。她的房子也有两只脚,类似某种生物。作曲家利用托卡塔舞曲的韵律、奇怪的音调与参差不齐的重音精准地进行展现。特别在曲目的B段落,右手声部的颤音仿佛巫婆在飞行,低声区类似房子生物的“脚步”,充满了神秘怪异景象。
穆索尔斯基的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所描绘的人物是从真实艺术品中汲取的灵感,这种创作方式较为罕见。但是穆索尔斯基对于人物角色富有感情和表现力的创作,明显比该作品的标题更为惊艳。特别是将哈尔特曼的绘画《鸡腿上的小屋》与穆索尔斯基的创作来进行比较的话,更为明显。哈尔特曼的这个绘画作品展现了俄罗斯的民族内涵:一个像童话小木屋一样的钟表;巴巴亚伽巫婆却不在这里,但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给作品增加了场景的时间与空间,让这个小木屋与巴巴亚伽一起飞行与着陆。
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里的音乐肖像几乎都是属于人物性格的描写,在肖像人物中,被描绘的人或童话形象的性格决定其表现形式,包含性情、行为、运动方式与语言风格。穆索尔斯基擅长精准的通过旋律来刻画角色的语言,而且还能补充角色的社会属性,如《两个犹太人,富人和穷人》《利摩日市场》;有年龄特征的《未孵化出来的小鸡舞蹈》和《杜伊勒里宫花园》。穆索尔斯基创作的人物肖像是对原本形象作了深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展现其性格与精神世界,同时也具有典型的社会和民族特征。
三、结语
18世纪作曲家的肖像作品最初的情感印象是得到更多的关注,而19世纪的音乐肖像作品是为了寻求更深、更全面的人物描写。肖像艺术本质是展现人物的外貌特点,包括姿势、手势、步态与语言方式,更深刻表达人物个性特征,如气质与情绪。因此,用音乐来展现人的综合特征是非常可行的,并不亚于其他艺术形式。但音乐肖像并不是通过某些音乐技术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音乐语言,其中最主要的是富有表现的主题,精准的音色、节奏、风格以及正确的和声色彩来综合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