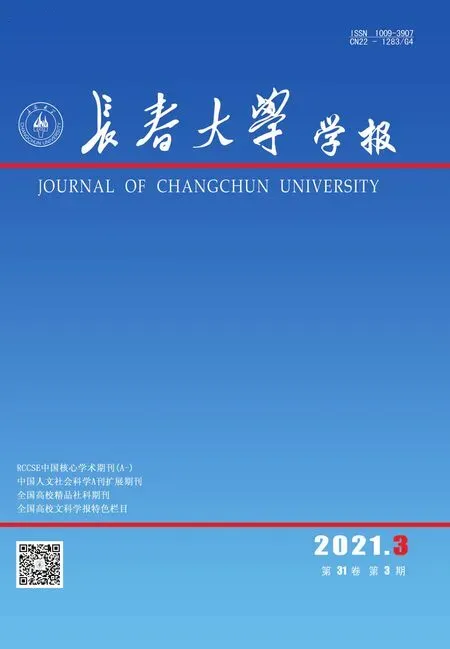戏曲元素在现代民族声乐中的运用
——基于美学视角
2021-12-04赵艳艳
赵艳艳
(安徽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合肥 230000)
传统民族声乐与戏曲艺术关联紧密,民族声乐的发展始终坚持立足传统、发展创新,从传统戏曲中吸收丰富艺术养料,将戏曲艺术中优秀的审美理念、创作方式、演唱技法、文化内涵融入现代声乐艺术之中,有利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实现传统艺术和现代审美的融合,丰富民族声乐作品创作思路,优化现代民族声乐创作和表演方式,使现代民族声乐作品呈现出多元化风格,以符合不同欣赏者的审美需求。
一、基于戏曲元素的现代民族声乐创作手法与创作美学
(一)板腔体结构的借鉴
板腔体是中国戏曲的结构体式,以上下对称的乐句为基本单元,并按照一定规则演变成各种板式,通过板式之间的灵活转换形成戏曲音乐。人们通常称其中的强拍为“板”,弱拍为“眼”,总称“板眼”。戏曲板式跟随音乐节奏而变化,一般以“散板—慢板—中板—快板—散板”的序列进行组合。常见板式类型有四种,分别彰显出不同的音乐表现力。一眼板相当于2/4拍,旋律简单且舒缓,经常用于叙事和抒情。三眼板相当于4/4拍,速度缓慢、旋律婉转,多用于抒情。无眼板相当于1/4拍,速度较快、词句紧凑,多用于表现激烈情绪。散板没有固定的节奏,速度缓慢,适合表现冲突情绪[1]。
各种板式变换能表达出复杂的人物情感,让人物个性更为鲜明。在《洪湖赤卫队》《白毛女》《江姐》的创作中就融合板腔体结构,对作品的节奏、速度进行调整,并融合旋律的紧缩、延伸、加花等,展现出层次分明、细腻深刻的音乐情绪。比如在《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洪湖赤卫队》唱段)中,融合“一眼板”的板式,形式工整、曲调质朴,将角色苦难的生平舒缓委婉地演唱出来,让人不禁潸然泪下。在引入戏曲元素时,通过变化唱腔的旋律和速度,能够演变出多样化的板式,传递复杂的音乐情绪,使民族声乐作品更加立体饱满[2]。
(二)叙唱与唱白互现
戏曲中会采取韵白、念白的手法传情达意,将声音与情感自然融合,清晰呈现人物形象,很多民族声乐作品都借鉴戏曲中叙唱和唱白互现的手法,传递出细腻、质朴、自然的情感。在叙唱性旋律的运用中,以歌词的自然语调为基础,音调变化较小,遵循歌词的朗诵节奏,乐句工整,通常运用四分和八分音符,字句结合基本是一字一音或一字两音,这样的旋律流畅、质朴、自然,符合“依字行腔”的规律。比如《不能尽孝愧对娘》的歌词“那年孩儿我七岁,寒冬腊月降灾难……把儿紧紧搂在身旁”,采取依字行腔的叙唱手法,娓娓诉说母亲含辛茹苦养育儿子的艰辛,用质朴自然的方式表达感人至深的母子深情。
传统戏曲中念白与歌唱相互交融,念白的音调介于说唱之间,配合丰富的节奏变化和人物表情动作,清晰传递作品思想情感,并体现出微妙传神的艺术性。很多现代民族声乐作品也借鉴这样的艺术手法,将质朴的歌词与别致的旋律相融合,彰显民族艺术的新魅力。《十里风雪》中的唱段“喜儿喜儿你睡着了,爹爹叫你不知道,你做梦也没想到你爹我有罪……”就采用唱白的手法,并配合节奏与速度的婉转变化,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杨白劳愧疚、痛苦、悲愤的复杂心情。《思儿》(《野火春风斗古城》选曲)的歌词“昨夜做了一个梦,见他打了胜仗回家乡……门儿外怎么传来脚步声儿响”也借鉴唱白的手法,并在唱白时放缓速度,让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自然流露,质朴简单,却传递出浓浓深情[3]。
(三)“古为今用”的创作美学
戏曲艺术历经八百余年演变,将音乐、美术、舞蹈、文学与表演技艺融为一体,发展出丰富的剧种形式,深刻反映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成为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命脉,在民族声乐史上具有无可撼动的地位。艺术作者必须秉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理念,将传统戏曲的精华运用于现代民族声乐创作中,创新民族艺术发展新思路。
《白毛女》是将戏曲形式和音乐内容相融合的成功范例,继承传统戏曲艺术精髓,借鉴西方艺术元素,践行“古为今用”创作美学,推动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嬗变。随后,人们相继创作出《刘胡兰》《江姐》等优秀歌剧,借鉴戏曲的板腔体结构,融合叙唱和唱白的艺术手法,开辟民族歌剧发展的美好前景。
音乐的创作过程基于对以往经验的借鉴,演唱家和作曲家掌握丰富的戏曲艺术,并深刻理解戏曲艺术与民族声乐之间的时代性关联,就能自由地融合各类艺术元素,创作出兼具艺术性、时代性的民族声乐作品[4]。
二、基于戏曲元素的现代民族声乐演唱方式与情感美学
(一)依字行腔
“依字行腔”是戏曲音乐的基本行腔规律,强调歌词声调与唱腔曲调的协调,实现“字中有声,声中有字”的演唱效果,魏良辅在《曲律》中也有“字清、腔纯,板正”的论述,可见咬字发音是戏曲艺术的重要内容。
1.歌唱的咬字
“喷口”是戏曲演唱的技法,是指将字头迅速有力地演唱出来,多用于表达热烈情感。歌剧《刘胡兰》中的唱段“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后方的事情别挂在心间……也难动我的心半点”,各句字头的发音力度随乐曲情感而变化,首句要轻柔婉约,真挚表达送别的依恋之情。随后是对战士坚定的勉励,咬字必须清晰有力,表达必胜的信念。戏曲艺术注重声音的质感,要求清晰自然地咬字发音,现代民族声乐在引入戏曲的咬字方法时,要注意戏曲细腻传神的唱法,使音乐作品饱含情感。
2.归韵收音
归韵收音在演唱中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必须收好字尾,做到干净利落,将词义清晰、完整地表达出来,确保音乐的韵味。传统民族声乐中总结出“十三辙”的规律,是基本押韵工具,对音乐作品的吐字归韵和情感表达都有借鉴价值。
3.四呼
在戏曲演唱中,口腔内部也随音素而变化,呈现为“开、齐、合、撮”四种口型,简称为“四呼”。各种口型的咬字发音不同,《十五的月亮》的唱段“你孝敬父母任劳任怨……我在保卫国家安全”,歌词中的“怨、全”属于撮口呼,需要嘴唇发力。《珊瑚颂》的歌词“一盏红灯照碧海”,其中的“盏、红、灯”等字属于开口呼。《伏尔加船夫曲》中的“穿过茂盛的白桦林”,“穿、过、桦”都属于合口呼,歌唱时需要张大共鸣腔[5]。
(二)戏曲唱腔
1.唱腔素材
戏曲发展受地方语言的影响,形成丰富的唱腔素材,昆曲唱腔缠绵婉转,注重对声音、节奏的把握,咬字发音讲究韵味;越剧唱腔跌宕婉转、俏丽多变,表演细腻而真切。晋剧的唱腔高亢流畅,念白清晰自然。川剧、豫剧、秦腔等剧种的唱腔都有不同风格,通过继承和发扬戏曲唱腔,现代民族声乐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2.润腔形式
通过对唱腔进行美化、修饰和润色,能增强戏曲情感和神韵,这对现代民族声乐中声腔艺术的创新发展颇具影响。在《杨白劳》《孟姜女》《兰花花》等作品中都掺杂“哭腔”技巧,对音乐情节进行细致刻画,传递出催人泪下的真挚情感。在《牧笛》《芭蕾的春天》中运用到“花腔”,传递出轻快、喜悦的心情。《花木兰》中“不知木兰是女郎”采取“拖腔”技法,将“郎”字的音调延长,配合悠扬婉转的旋律,意味无穷,深刻细腻地表现人物心境。《兰花花》的歌词“五谷里那个田苗子儿”,采取“甩腔”技法演唱其中的“子儿”,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表现陕北民歌豪迈的风格[6]。
3.地方戏曲元素
越剧、昆曲、秦腔等是地方戏曲的典范,丰富多彩的戏曲风格能为民族声乐的发展提供大量素材。歌剧《江姐》借鉴川剧艺术,细致刻画江姐坚强不屈、浩然正气的形象。《故乡是北京》属于“戏歌”,巧妙运用京剧唱腔。《小二黑结婚》大量融合梆子戏的元素,使歌曲传递出质朴、明朗的情感。《洪湖赤卫队》融合西洋的咏叹调,并且引入花鼓戏的元素,成功塑造人物形象。很多著名的艺术家都致力于学习地方戏,李谷一、郭兰英都有深厚的戏曲功底,并在演唱生涯中加以借鉴、发扬。
(三)“气、韵”的借鉴
1.“气”的借鉴
戏曲演唱讲究“气沉丹田”,将气息存于丹田处,经由肌肉收缩调控气息,实现自如发声,并发展出叫板、念白等练声方法,在演唱时体现“字正腔圆”,使声音柔美、明朗、清晰。为使气息更加平稳深沉,需要适时地换气、偷气,自然精巧地运气,灵活吐纳气息,提升唱腔的艺术效果[7]。
现代民族声乐在表演、字音等方面都可以融合戏曲气息技巧,引入“透气、换气”技法,遵守正确的运气规律,达到自然的行腔效果,将声音与情感完美融合,提高声音感染力,自由灵活地传情达意。
2.“韵”的借鉴
“韵”是戏曲演唱中声音、情感、技法等要素融合产生的审美意趣。音乐韵味包括三点:第一,润色修饰唱腔;第二,真切传递音乐情感;第三,美化声音和语言。要根据特定情感变换现代民族声乐的“韵味”,在演唱前须了解作品背景,掌握作品的思想情感与音乐形象,细致理解作品的情感基调,借此把控音乐的韵味。比如,用“气陈声缓”的曲调传递悲伤的心情,如同气息尽竭。在传递爱的心情时,可以体现出“气徐声柔”的韵味,曲调轻软,给人温和之感。而“气满声高”的语调则传递喜悦的心情,“气足声硬”传递出憎恨之情。
戏曲演唱在速度、情感、音调上的变化也能影响音乐的“韵味”,演唱者可以利用这些技巧提高声音的感染力。在歌剧《白毛女》中,雷佳在演唱中融合传统戏曲元素,完美处理真假声和声音色彩,并借鉴戏曲的表演技法,让“喜儿”的形象深入人心。在《故乡是北京》中,李谷一的演唱借鉴京剧的腔调,让歌曲呈现出京剧的韵味,传递出细腻诚挚的情感。
(四)“声情意蕴”融合的美学情感
1.字正腔圆、声情并茂
咬字和音色是歌唱的重要因素,戏曲艺术中有完善的吐字发音规范,并提出“依字行腔”的原则,要求演唱过程达到声音、语言、情感的有机融合,做到“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燕南芝庵的《唱论》曾对此做过详细阐释,强调人声圆润饱满、抑扬顿挫,让情感自然流露,该论述奠定民族声乐的审美基调,将其升华至文化艺术的高度,对民族声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传统音乐美学注重精神层面的内涵,强调音乐在表现思想情感方面的价值,认为人们的情感变化是音乐创作动因,在创作和演唱中要以情感为核心,实现情感与声音的和谐统一,达致“声情并茂、形神合一”的音乐境界[8]。声乐学习者要深刻理解传统民族音乐的审美理念和演唱规则,促进现代民族声乐的创新发展。
2.声音、韵味、风格
声乐表演是一门综合性艺术,演唱者要分析作品的情感色彩,借助丰富经验和技艺把握作品的“声音、韵味、风格”,提升音乐艺术感染力,引发观众共鸣。演唱者需要将嗓音条件与声乐技能相融合,并以良好的艺术和道德修养为依托,清晰表达音乐情绪。在研究歌曲韵味美时,要注重民族性审美理念,根据歌曲风格借鉴相应的戏曲元素,自然呈现民族声乐作品的风格和意境。民族声乐讲究精准的咬字发音和真挚的情感表达,展现丰富的旋律美,这与传统文艺中雅致、高远的意境美相契合,使现代民族声乐艺术在审美理念上立足传统、发扬创新。
三、基于戏曲元素的现代民族声乐表演技巧与现代性美学
(一)形体的借鉴
传统戏曲讲究“唱、念、坐、打”的基本功,强调歌唱艺术与形体动作的有机协调,完整呈现戏曲艺术的魅力。在声乐表演中可以借鉴戏曲的形体艺术,结合音乐情景和人物个性灵活运用手势、步态、眼神,准确塑造人物形象,传递丰富的音乐情感。各种形体动作会传递不同的情感内涵,以手势的姿态为例,手臂张开能营造气势磅礴的氛围,手势合拢时气势减弱,手势动作需与气息、情绪相配合[9]。“眼法”也是重要的戏曲元素,对声乐表演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其中的“看”要求眼神专注而不散漫,“视”类似于轻瞟一眼,蕴含轻视的意味。表演者要恰当地应用戏曲的形体动作,做到端正大方、生动形象,实现视觉审美和听觉审美的统一。
(二)戏曲舞台的运用
传统戏曲注重舞台设计,充分利用有限的舞台空间达致“境生于象外”的艺术效果,将人们对戏剧的感受上升到哲学高度。在歌剧《白毛女》中,演员的步态、转身等动作采用戏曲的写意手法,舞台背景异常简单,将写意和写实相融合,将观众完全带入故事情景。歌剧《红珊瑚》采用戏曲的分场结构,舞台设计呈现虚实结合的效果,渔行的厅堂、大门为实景,其中有大量虚拟空间,随剧情的推进而变化。随着舞台技术的发展,现代化的灯光与音响融入舞台背景,配合演员的新装扮,形成全新的叙事手段,扩展舞台的感染力[10]。在歌剧《运河谣》的舞台背景中,利用多媒体呈现运河景象,主景布置简约大方,只有一河、一桥、一船,随着音乐推进,舞台背景自然变换,在继承传统舞台美学风格基础上融入现代化的审美意趣,实现音乐性和戏剧性的统一。
(三)“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现代性美学
意识形态与文化艺术都具有时代性,现代民族声乐也属于时代产物,这促使民族声乐艺术始终处于发展、创新状态之中,一方面继承传统技法和风格,另一方面融合现代审美特征和表演艺术,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民族声乐艺术始终反映出时代特征,《黄河大合唱》诞生于抗战期间,鼓舞民族士气,激励人民团结一致共抗外敌。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彰显抗战后期坚韧的民族精神。而《木兰诗篇》创作于国富民强的和平年代,在表演形式、舞台设计方面都体现出时代特征。表演者在演绎民族声乐作品时,要分析作品的精神内涵,科学融合传统艺术元素和现代表演技术。
四、结语
传统戏曲包含丰富的文化与艺术底蕴,其完善的创作方式和演唱技法能为现代民族声乐的创新发展提供借鉴,很多经典民族声乐作品都借鉴传统戏曲元素,并将其与现代表演方式相融合,推动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创新,满足并引领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提升我国艺术文化软实力。应加强对戏曲艺术和民族声乐关联性的研究,理性地吸收运用戏曲元素精华,借鉴现代化表演方式,结合现代观众审美心理,创新出更多优秀的现代民族声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