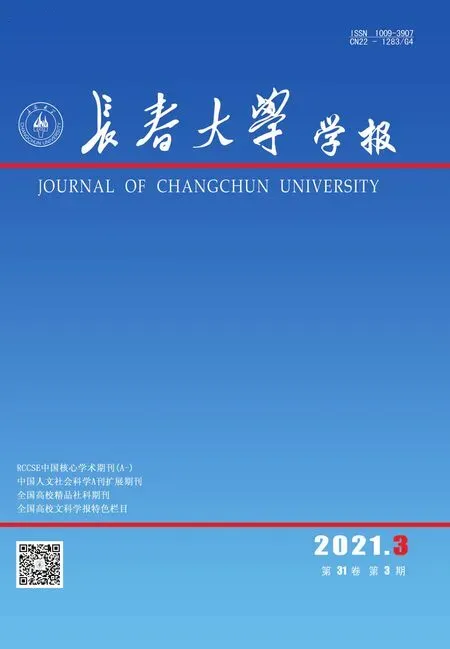试论国际强行法对国家同意原则的冲击
2021-12-04周明园
周明园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200042)
一、国家同意原则概论
与国家制定国内法不同,由于国际社会并不存在超国家的立法机关、司法机构,国际法主要是由国家这一复杂的实体创造并实施的。国际法是国家间的法律,基于国家主权,国家同意原则构成了国家法体系的基石。在国际法理论学说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史中从未停止对国家同意原则的关注和讨论。无论是自然法学派还是实在法学派均肯定了国家同意原则在国际法形成中的重要意义。
传统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建立在理性行为人善良的基础上,自然法是这一规则的总体。自然法因此约束着全体人类,而国际法则是在自然法的基础上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被视为这一学派的代表。格劳秀斯在阐述法律的形成过程时认为,法律源自“为维护我们大致勾勒出来的并且与人类认识水平相一致的社会秩序的需要”,也就是法律自然的渊源。在自然法之外,格劳秀斯认为,还存在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或者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法律的万国法。国际交往中,各国出于其本国利益而行事。只有在达成多数一致时规则方能演进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法律[1]。由此,格劳秀斯将万国法与自然法区分开来,并敏锐地指出国家的同意是万国法存在的前提。继格劳秀斯之后,其他自然法学派在论证国际法的来源时也提到了国家同意的影响。例如,德国学者沃尔夫认为,存在“自愿国际法”,需要依靠一些国家的契约或是准契约所制定的规则使各国统治者听从自然的领导,以此来区别地道的自然状态的必然法[2]。19世纪后期,实在法学派逐渐取代自然法学派成了国际法理论主流学说,国家同意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实在法学派的学者们将法律从道德及自然法的框架中脱离出来,在阐释国际法的形成过程时与自然法学派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认为,法律的基础并非仅仅源自于一种事实,而是一种意愿。也就是说,国家的意愿即是立法的意愿,国家同意是影响法律形成最关键的因素。实在法学派的核心理论在于强调国家主权、国家意志、国家同意的重要性,这一理论在19世纪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对国际法理论学说和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
可以说,无论是自然法学派坚持国际法的主要来源是独立于国家同意而客观存在的天赐规则,或是实在法学派认为国际法基于国家同意而产生,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同意原则在国际法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当前的国际法并不完全是国家意愿的客观体现,但现行的多数国际法规则仍然是建立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的[4]。
进入20世纪早期,国家主权原则的普遍确立再一次重申了国家同意原则在国际法体系中的作用。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核心原则。一方面,国家自治是体现国家主权的客观标准,在广泛的国家实践中,国家强调主权不容侵犯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争取国家的独立和自治。倘若国际法未经国家同意也能够产生普遍的约束力,国家自治几乎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当代许多国家的主权事实上都受到了国际条约的特殊性限制以及国际习惯的一般性限制[5]。国家如何能够在接受国际法约束的同时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则成了国际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围绕国家主权的矛盾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家同意原则是阐释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
国际司法实践特别强调了国家主权原则下国家同意的决定性作用。在1927年的荷花号案(S. S. Lotus Case)中,常设国际法院认为,“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则……源自各自公约所表达的自由意志或通常被视为表达法律原则的惯例”(1)S S Lotus Case (France v. Turkey). Judgment of 7 September 1927,P.C.I.J. Rep. Series A No.10,para.35.;在1970年巴塞罗那电力公司案(Barcelona Traction,Light and Power Company,Limited)中,国际法院认为,“一套规则仅在获得相关同意的基础上才能够形成”(2)Barcelona Traction,Light and Power Company,Ltd (Belgium v. Spain),Judgment of 5 February 1970,Second Phase,I.C.J. Reports 1970,p.3,para. 89.;在1986年美国对尼加拉瓜军事及准军事行动案(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中,国际法院认为,“国际法中并不存在规则,除非这些规则被有关国家通过条约或其他方式接受”(3)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erits,Judgment,I.C.J. Reports 1986,p.14,para.269.。粗略地考察上述司法实践中对国家同意原则的阐述,可以看出,国际法院认为国际法对国家的约束力是国家基于主权做出的选择,具体表现为国家的自由意愿的表达以及对现有国际法规则的接受[6]。尽管也许法院并没有具体回答为什么国际法具有拘束力这一问题,但是却十分务实地阐释了主权国家基于它们可自由行使的同意因而被约束这一观点[7]。国际法院的这一观点明确了国家同意原则在国际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一方面确保国家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民族自决等方面的权利,保障国际法赖以生存的稳定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也明示了自愿受到国际法约束的当事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保证国际法的有效运作[8]。
二、国际强行法对国家同意原则的突破
“法律是因为它能够使那些依据它而行事的人更为有效地追求他们各自目的而逐渐发展起来的。”[9]国际法的发展同样如此。主权国家尽管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是人类社会良好而稳定的秩序,安全而高效的发展是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集体的合作往往比单独的行动更有利于目标的达成,由此便极大地促成了国家间的交往,也促成了国家对国际交往时的必要规则——国际法的自愿服从。一方面,在国家同意原则下,国家间利益的趋同性促进了国际法规则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当追求全体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目标与多数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实相悖时,国际法体系下国家同意原则的局限性便凸显出来。
WTO在近时的困境即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WTO所确立的多边贸易体系本身即是全球法律规则趋同化的代表。正因如此,从WTO成立至今,在促进世界贸易增长或是完善国际贸易法治建设上,WTO取得的辉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此辉煌的成绩并不能够掩盖WTO目前面临的尴尬境遇。2001年,多哈发展回合谈判至今近20年,除了2015年达成的《贸易便利化协定》等少数几项新的协议以外,在其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反倾销、反补贴以及贸易新议题等核心领域几乎毫无建树[10]。以中美贸易战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等问题上的争议对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产生了很大冲击。可以看出,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和成员国数量的不断扩大,WTO在求同存异的道路上已经走得举步维艰,以国家同意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并不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效路径。
如果说解决WTO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赖于如何协调各国经济领域不同的发展水平,国际社会在其他领域所要面临的问题则在更大程度上关乎到人类社会的共同命运,更加需要国际法的调整与制约。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各国之间相互依存性与日俱增: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几乎会影响到国际社会每一个个体的利益;亚洲地区的禁毒政策影响了欧洲和美国的执法立场;任何一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效应都会波及世界其他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武装冲突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因为双方均持有核武器……[11]。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越来越多的问题持有不同的立场和主张,越来越多的问题对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影响,这就使得国际法体系下的国家同意原则变得越来越复杂——国际法尊重主权国家的自主性决策,尽管环境、人权、安全等领域涉及全人类共同的健康发展,但是国家同意原则使得国际法很难就此达成一致,尤显得束手无策。
当前,国际社会对基本核心价值的追求和对人类命运共同发展的夙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对以国家同意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的坚持。国际法正在由国家自治的主权本位逐渐转变为全球一体化发展的社会本位[12]。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践表明,国家同意原则已不再是约束国家行为的唯一标准。国家同意原则之外的国际法规则逐步发展为国际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有学者提出“非合意国际法”这一概念。海法尔(L. R. Helfer)将非合意国际法定义为“在国家没有加入及批准条约或是没有接受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履行相关义务时,仍旧对该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同时,海法尔以跨境恐怖主义、环境保护、人权的领域为视角分析了非合意国际法的相关法律问题[13]。古兹曼(Andrew T. Guzman)在论及非合意国际法时,将习惯国际法和国际强行法同样纳入了非合意国际法的范畴中[11]。日本学者小栗宽史认为,非合意国际法包括国际组织、条约机构等通过多数表决权而具有拘束力的决议,以及国际条约中的参考性法律文件[14]。总结而言,非合意国际法这一概念提出至今,尽管就其范围和分类并未能达成一致性意见,但其对现有法律制度的补充和完善作用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而在这之中,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国际强行法)之于国家同意原则的冲击是最为显著的。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国际强行法)是指被国家组成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和公认为不容克减的规范,此类规范只能由嗣后具有相同性质的一般国际法规范加以变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国际强行法)反映并保护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其等级高于国际法其他规则且普遍适用。国际强行法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国内法上的“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尽管在私领域之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居于非常核心的地位,但当其涉及与社会公共秩序的冲突时,仍然需要退避三舍[15]。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的前身,也即国际法委员会1966年条约法条款草案第50条的评注将“《宪章》中关于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则”列为一个“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国际法规则的显著例子”。 司法实践中,国际法院在1970年巴塞罗那电力公司案第二诉讼阶段中提到了一般国际法的普遍适用性。国际法院认为,有必要对一国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与在外交保护领域对另一国产生的义务作出区分。就其性质而言,前者被所有国家所关注,由于其所涉及权利的重要性,是所有国家均负有的对世界的法律义务。紧接着国际法院举例认为,在当代国际法体系下,这类义务关乎人类基本权利的原则和规则,包括禁止侵略、禁止奴役、禁止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等。最后国际法院指出,这些相应的受保护的权利一则构成普遍的国际法,一则在国际法文件具有普遍性或是准普遍性的特征(4)Case Concerning Barcelona Traction,Light and Power Company,Ltd (Belgium v. Spain),Judgment of 5 February 1970,Second Phase,I.C.J. Reports 1970,p.3,paras. 33-34.。可见,一国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被视为国际法约束国家行为的最低标准,也构成国际强行法规范的基石。与此同时,来自黎巴嫩的Ammoun法官在发表个别意见时认为,“经历了漫长的联合国实践,国际强行法的概念已经获得了较高水平的效力,其作为国际法上的必要规范得到了认可,其原则出现在了《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中”(5)Case Concerning Barcelona Traction,Light and Power Company,Ltd (Belgium v. Spain),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Ammoun,p.304.。可见,尽管在本案中,国际法院并未明确提及国际强行法的概念,但间接地证明了国际强行法的存在。除此之外,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在阐述国际强行法的性质、效力时指出,“由于其所保护的价值观的重要性,这一原则(禁止酷刑)已演变成一种强制性规范或强行法,即在国际等级制度中享有比条约法甚至‘普通’习惯规则更高级别的规范。这一更高级别的最显著后果是,各国不能通过国际条约、地方或特殊习俗,甚至是未被赋予相同规范效力的一般习惯规则减损这一原则”(6)Prosecutor v.Anto Furundzija,Judgment,10 December 1998,Case No. IT-95-17/1,para.153.。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国际强行法)起草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和附件草案》,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国际强行法)相抵触者无效。此种条约的规定无法律效力。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国际强行法)产生时,与该项规范相抵触的任何现行条约即为无效并终止。条约缔约方继续履行条约之义务解除。习惯国际法规则如与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国际强行法)抵触,则停止存在。一贯反对者规则不适用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国际强行法)。国际法委员会还列举了“非详尽无遗的清单”:(1)禁止侵略;(2)禁止灭绝种族;(3)禁止危害人类罪;(4)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规则;(5)禁止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6)禁止奴役;(7)禁止酷刑;(8)自决权。
从国际法委员会对国际强行法的法律效果的评估上可见,无论是条约还是习惯国际法,一旦抵触国际强行法都将导致无效,而条约和习惯国际法都反映了国家同意原则。因此,国际强行法实质上构成了国家同意原则的边界。但是,尚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国际强行法是否能够被国家同意原则所包含呢?又或者说,国家同意原则能否向下兼容国际强行法?此处的关键核心在于国际强行法的约束力是否也是根源于国家同意呢? 这一问题的来源在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中明确提及,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国际强行法)是指被国家组成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和公认为不容克减的规范。这是一项复合要求,“接受和公认”(acceptance and recognition)的要求由其他要素组成,即:(a)“国家组成之国际社会全体”(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States as a whole),(b)“不容克减”(no derogation is permitted)。这些要素描述了《维也纳公约》第53条所述接受和公认的不同方面。它们描述了谁必须接受和公认,什么必须被接受和公认。该条款中的“接受和公认”在某种意义上使得国际强行法成了国家同意原则和非合意国际法的骑墙之作,如何理解“国家组成之国际社会全体”及“接受和公认”就成了破局的关键之所在。
如果我们回溯维也纳会议,根据芬兰、希腊和西班牙的共同提案通过的第53条案文系由起草委员会加插了“全体”二字,“以表明,在确认某一规范为国际强行法方面,没有任何个别国家有否决权”。起草委员会主席进一步解释说,加插“全体”二字是要表明有关规范的强制性质不必“由所有国家接受和公认”,而“只要有很大一部分国家这样做”就足够了。当然,这一观点也并没有得到完全赞同,有部分委员就认为,“全体”一词意味着不是要求各国个别接受和确认,而是要求各国集体接受和公认,指出国际强行法“是各国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国际社会的机关创制的实在法”。
类似的,国际法委员会《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国际强行法)起草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和附件草案》中的结论草案7中也提及:“很大一部分国家(a very large majority of States)接受和承认即足以识别一项规范为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国际强行法);不要求所有国家都接受和承认。”然而,正如中国代表徐宏所指出的,“很大一部分”的标准仍然是不精确的,无论是将其解释为“大多数国家”还是“很大一部分国家”,实践中都很难操作。其他国家支持采取更严格的标准,比如罗马尼亚支持“很大一部分”的标准,称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准一致同意”。俄罗斯代表团则更为严格,表示不同意第2款的规定,即很大一部分国家的承认即足矣,而是需要所有国家予以承认,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承认可能不具积极性:国际强行法规范可在大多数国家积极承认和没有其余国家反对的基础上确定。
到目前为止,国际法委员会起草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和附件草案中的结论草案7,仍然使用的是“很大一部分国家接受和承认即足以识别一项规范为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国际强行法);不要求所有国家都接受和承认”。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虽有争议,但从维也纳会议及国际法委员会的研究成果上看,至少在数量上国际强行法并不要求全体国家的同意,而是呈现多数主权国家的意志。即便少数国家反对某项国际强行法规则,国际强行法仍将对其发生国际法效力。而这种部分国家意志对全体国际社会发生效力的国际法规则,显然跨越了国家同意原则的范畴。
再从法律修辞的角度,厦门理工学院的陈海明教授通过类比的方式阐述了合意与非合意规则的不同法律范式。合同条款的效力是合同双方同意的法律结果,而万有引力规则的客观有效性并非源自于科学家的确认和接受。《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认为强行法系“国家组成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和公认”,这一表述并不表明国际强行法的拘束力是基于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的同意[16]。或者说,国际强行法应当得到国家组成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和公认,但不是由于国家组成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和公认才构成国际强行法的普遍拘束力的。事实上,国际强行法更多的是基于自然法的观念,认为有一种超然于实定法上的不容克减之规范,这种规范的法律拘束力或者说法的效力与传统的条约并不一致。条约与国内法意义上的合同形成了较强的可类比性,系基于主权国家的同意,会随着国家的同意或背弃而形成效力效果,但显然国际强行法的性质与此有显著差异。
总结而言,不以国家合意为前提的国际强行法是国际法体系下的一个重要分支,表现出国际法同样存在某些规范高于国家意志而存在。尽管针对哪些规则能够纳入国际强行法的范围尚存有争议,但这一规则本身即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以国家同意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也是国际法规则走向统一性、规范性的重要表现。
三、结语
国际法形成发展至今,国家同意原则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国际法理论学派对国家同意原则在国际法形成过程中重要作用的阐述,还是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以国家同意原则为基石的国际法体系的确立,抑或是国际法发展过程中习惯国际法乃至国际强行法突破国家同意原则的普遍约束力,以及国际法完善过程中在全球安全、环境、人权保护等领域对非合意国际法效用的呼吁,理论界对国家同意原则基本认识的变化表达了实践层面对国际法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多层需求。总结而言,国家同意原则在国际法体系中的特殊意义体现在其双效性的特点上。一方面,国家同意原则是国际法保障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主权平等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国家对国际社会不同领域的多样化追求使国家同意原则阻碍了国际法发挥更多效用的可能。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生活在一个公担风险、共享利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面对共同的问题,国际社会在不断探索国家同意之外行之有效的规则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除了以国际强行法为代表的非合意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外,国际软法对国际法功能的完善也是这一趋势的重要表现。除此之外,2019年,国际法院在英国政府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发表了对英国与毛里求斯有关查戈斯群岛争议的咨询管辖权。尽管对当事国而言,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本身没有法律拘束力,但作为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司法机构,国际法院的意见无疑会在较广范围内产生指导性的影响[17]。以上种种“类法律规则”符合国际社会普遍的价值追求,是国际社会期待国际法在国家同意原则之外作出更多的直接表达,对完善国际法体系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有必要对国家同意原则之外的国家法规则进行逐步完善。法律本就属于强制性规范,国际法亦然。必须重视以国际强行法为基础的强制性规则的发展从而适当缩小国家同意原则的适用,由此推动国际法的与时俱进,适应国际社会对国际法的要求,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