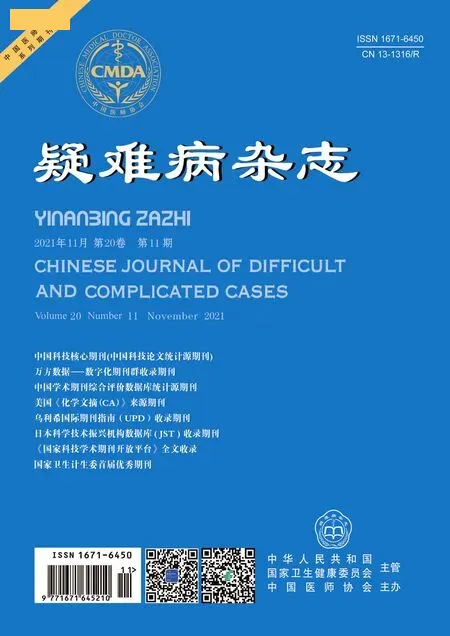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心房颤动的研究现状
2021-12-04刘金鹏综述白梦媛费瑜审校
刘金鹏综述 白梦媛,费瑜审校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一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由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 virus 2, SARS-CoV-2)的S1蛋白与靶宿主细胞上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受体结合进入宿主细胞后以启动感染所致[1-3]。其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在潜伏期即有传染性,发病后5 d内传染性较强。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感染后或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后可获得一定的免疫力,但持续时间尚不明确[4]。在COVID-19救治过程中,学者们发现SARS-CoV-2感染与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AF)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AF的存在是导致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增加的主要心血管因素,早期预测和积极治疗具有高风险特征的患者(如AF)可以改善临床预后[5-6]。目前对于COVID-19合并AF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为此本文对其加以概述。
1 COVID-19并发AF的可能机制
1.1 炎性因子与炎性反应 在以往的研究中,炎性因子与炎性反应不仅可导致心肌细胞凋亡或坏死、心肌纤维化和重构,而且还可引发房内复极和传导障碍,最终导致AF的发生和持续。SARS-CoV-2能使NLRP3炎性小体激活,主要通过以下途径[7]:(1)通过与表达ACE2的心肌细胞结合直接激活NLRP3炎性小体,同时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 Ⅱ,Ang Ⅱ)与血管紧张素1型受体(angiotensin type 1 receptor, AT1 receptor)结合后激活靶细胞中的NLRP3炎性小体;(2)SARS-CoV-2病毒的N蛋白可能以MBL-MASP-2依赖的方式激活补体级联反应(ComC),并裂解ComC的片段(C3a和C5a过敏毒素)及C5b / C9膜攻击复合物(MAC),可能会额外激活细胞中的NLRP3炎性小体。Yao等[8]研究发现,阵发性AF和持续性AF小鼠的心房肌细胞中NLRP3炎性小体的活性增加,且NLRP3的特异性抑制剂MCC950可以减弱心肌细胞特异性敲除小鼠的自发性房性期前收缩和AF的发生。
1.2 ACE2与可溶性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soluble ACE2,sACE 2) 在COVID-19病理生理学中,SARS-CoV-2病毒S1蛋白与靶宿主细胞上的跨膜ACE2受体结合,并与TMPRSS2蛋白酶活性结合,进入宿主细胞以启动感染[3, 9]。ACE2可将AngⅡ转化为七肽血管紧张素1-7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ng1-7),当SARS-CoV-2与ACE2结合后削弱了ACE2的功能,使得Ang Ⅱ水平增加,Ang1-7水平降低,而增加的AngⅡ又可通过去整合素—金属蛋白酶17(ADAM17)将膜结合的ACE2以sACE2的形式释放到循环系统中[10],一些sACE2与病毒结合使得sACE2减少及活性降低,sACE2活性降低会增加AngⅡ的浓度,AngⅡ升高反过来又可以产生sACE2,进而使膜结合ACE2减少,膜结合ACE2的缺失同样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生[11]。研究表明,分别使用生理盐水和AngⅡ处理小鼠心肌细胞后,AngⅡ介导的高血压会增加AF的发生率,还可引起心肌纤维化和心房结构重构,此外AngⅡ还可通过影响心肌细胞离子通道引起心房的电重构,使得AF得以持续[12]。Ang 1-7激活mas受体可以刺激前列腺素释放,增加NO的释放,并通过抑制ACE活性,增加缓激肽代谢作用,抑制平滑肌细胞生长,抑制组织炎性反应及心肌纤维化[13-14],其在AF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主要发挥保护作用。SARS-CoV-2病毒感染抑制了这一作用的发挥,增加了AF形成的风险。
1.3 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 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与AF的触发存在密切关系[15]。COVID-19患者常常伴有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表现在:(1)SARS-CoV-2可能通过局部或全身性炎性反应/免疫刺激影响颈动脉体,随之导致外周动脉化学敏感性和交感神经兴奋的增加[16];(2) AngⅡ可增强ADAM17的活性,ADAM17是下丘脑旁核交感神经元前RAS激活的关键介质,高表达的ADAM17引起交感神经的激活;(3)COVID-19患者症状多可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如咳嗽、心悸、呼吸困难和低血压等。
2 COVID-19并发AF的治疗
2.1 节律控制
2.1.1 胺碘酮:胺碘酮是临床上治疗AF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它不仅能控制节律,而且还能通过抗炎和抗病毒等间接地治疗心律失常。研究表明,胺碘酮潜在的抗病毒可能是因为干扰病毒的内吞和复制,表现在:(1)在常规治疗心律失常的血清药物浓度下,其主要代谢物(单-N-去乙基胺碘酮)可以明显抑制丝状病毒的侵入;(2)它能够阻止SARS 冠状病毒感染在细胞培养物中的传播,而不会改变细胞表面ACE2受体的密度或干扰SARS-CoV-1在细胞上的附着;(3)当SARS-CoV-1直接将其基因组传递到细胞质中,即可绕过内吞途径。基于这些实验,Sanchis-Gomar等[17]认为,或许胺碘酮有望成为治疗COVID-19合并心律失常患者最理想药物之一。
然而对于COVID-19来说,胺碘酮的使用有很大的局限性[17],主要源于胺碘酮一些不良反应,包括缓慢性心律失常、QT间期延长伴扭转性室性心动过速等,并且胺碘酮与部分治疗COVID-19的药物都经肝细胞色素P450(CYP450)酶系代谢,它们经由共同通路,如CYP3A4、CYP2C8和CYP3A5同工酶,这会影响药物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2, 18]。胺碘酮可以延长QT 间期,尽管其致尖端扭转性室性心动过速的可能性很低,但与治疗COVID-19的药物,如洛匹那韦、利托那韦、阿奇霉素、羟氯喹等合用时,可能会进一步延长QT 间期,在停用胺碘酮药物6 d后QT 间期基本恢复正常[2,19],因此,监测血浆胺碘酮浓度使其保持在正常水平(参考值0.21~2.05 mg/ml)非常重要。
2.1.2 电复律:COVID-19大流行期间,由于COVID-19并发AF来势凶猛且常并发血流动力学障碍,加之可避免药物相互影响出现QT 间期延长,所以,电复律(electrical cardioversion,ECV)就成为治疗COVID-19并发AF的主要手段。Schnaubelt等[20]对COVID-19并发AF使用ECV治疗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2 310例COVID-19并发AF患者中有511例采用ECV治疗,认为ECV与AF发生率下降有关。早期应用ECV治疗COVID-19并发AF要比晚期好[21]。ECV治疗COVID-19并发AF不仅快速、安全有效,而且联合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效果更佳。Colon等[22]报道了1例接受ECV的COVID-19合并AF患者在数分钟内恢复窦性心律。Grandinetti等[23]报道12例COVID-19合并AF患者,其中有8例采用ECV治疗,结果均成功恢复窦性心律。
2.2 心率控制
2.2.1 β-受体阻滞剂:β-受体阻滞剂是细胞色素CYP2D6的底物,其中美托洛尔对CYP2D6的依赖性最强,90%的阿替洛尔以原结构发挥作用,不经过肝脏酶代谢,艾司洛尔通过酯酶转化为酸性代谢物(ASL-8123)和甲醇,所以,阿替洛尔或艾司洛尔与治疗COVID-19的药物联合应用时,其血浆水平不变[2],可用于COVID-19患者并发AF的心率控制。
兰地洛尔是一种高度选择的β1受体阻滞剂,它半衰期超短,负性肌力作用较弱,用于AF患者在心脏手术中控制心率或防止室上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在一项包括15例COVID-19合并持续性AF患者的研究中,给予兰地洛尔治疗后患者总体心率降低23%;对整体血流动力学或组织灌注参数无任何负面影响。认为兰地洛尔可控制COVID-19合并AF危重患者的心率,尤其适合于心功能正常或中度降低的患者[24]。Seecheran 等[25]在全面治疗COVID-19的前提下,给予胺碘酮和阿替洛尔治疗COVID-19合并快室率AF患者,随着患者症状逐渐好转和病情的减轻,在48 h后转为窦性心律,说明β1受体阻滞剂可能是COVID-19合并AF的有效治疗手段之一。
2.2.2 地高辛:地高辛和西地兰是强心苷的主要临床代表药物,用于治疗快速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已超过一个世纪。在一项地高辛与所有对照干预措施进行比较的研究中,发现地高辛对急性心率控制(治疗开始后6 h内)优于安慰剂,但低于β受体阻滞剂。急性心率控制较胺碘酮差,地高辛和胺碘酮两者转复的成功率也不一定高[25-26]。以往的研究表明,强心苷不仅阻止了病毒繁衍,包括RNA复制、信使RNA转录、蛋白质的宿主细胞翻译,以及最终新形成的病毒颗粒的出芽,而且还抑制过度炎性反应和细胞因子级联反应[27], 所以认为,当COVID-19合并快速AF需要心率控制时,尤其伴有低血压和心力衰竭共存时,应优先考虑洋地黄和其他的强心苷治疗。
综合上述,对于COVID-19合并AF患者心率控制策略首选β受体阻滞剂,其次为强心苷。
2.3 抗凝治疗 SARS-CoV-2感染可致COVID-19患者有较高血栓并发症的风险,当其合并AF时发生该风险增加。长期以来,CHADS2、CHA2DS2-VASc评分是评估AF患者是否需要抗凝治疗的标准,对于COVID-19患者来说血栓与出血都容易发生,欧洲心脏病学会关于COVID-19大流行期间心血管疾病管理的指南建议抗凝预防AF相关脑卒中或全身栓塞应以CHA2DS2-VASc评分为指导(而不是AF临床类型或当前心律状态)[3]。HAS-BLED是预测出血风险的最佳证据,也适用COVID-19合并AF患者。
华法林适用于机械人工瓣膜置换和透析等患者,它的代谢主要是通过细胞色素P450酶,如CYP1A2、CYP2C19或CYP3A4,当它与治疗COVID-19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阿奇霉素等)联用时,华法林的抗凝作用可能增强,引起出血风险加大,一般来说,发生血栓栓塞事件国际标准化比率(INR)小于2或发生出血事件INR大于3,因此,要监测华法林的血浆浓度和INR。然而,频繁于医疗机构进行INR监测,意味着患者暴露于SARS-CoV-2感染和疾病传播的可能,所以,在COVID-19大流行时期,应避免使用华法林[2, 28]。
由于新型口服抗凝药(new-oral-anticoagulants,NOACs)具有不用经常测定INR的优势,所以用于非瓣膜性AF的抗凝治疗似乎是最简单、安全、可行的。NOACs与治疗COVID-19的药物(如氯喹/羟氯喹、抗病毒药)共用一种酶(CYP34A和G-gp)代谢或运输途径,其合用可增加NOAC血清浓度,引起出血,因此,应避免使用它们预防COVID-19合并AF患者血栓栓塞风险。对于有维生素K拮抗剂或肝素禁忌证的患者,且NOAC治疗是唯一的选择时,使用NOACs药物的剂量应该减少50%[2]。不建议达比加群、阿哌沙班联合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利伐沙班可以合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但不推荐使用。利伐沙班可用于接受阿奇霉素治疗的患者[29]。
普通肝素和依诺肝素增强抗凝血酶Ⅲ活性,没有文献报道它们与COVID-19治疗药物之间有相互作用,此外,肝素及其衍生物的潜在抗炎特性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起到作用[30],因此,COVID-19合并AF患者的抗凝治疗应推荐选择肝素[28]。尽管低分子肝素抗凝可降低严重COVID-19患者的死亡风险,但许多ARDS患者仍会出现严重的血栓性并发症,这或许是由于一些COVID-19感染患者表现出肝素抵抗所致,所以对于重症患者或需要抗凝治疗的患者(即AF患者)需要更高剂量的肝素,为了避免因需要充分的抗凝治疗强度所导致危及生命的出血风险,建议应监测抗Xa水平,以便于调整肝素治疗的剂量。
2.4 上游治疗
2.4.1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ACEI)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 ,ARB)可以逆转心房的电重构和结构重构。不过COVID-19大流行开始阶段,有人担心用ACEIs或ARBs治疗可能会增加COVID-19感染或COVID-19感染后进展成重症的风险。这一担忧源于一个假设,即缘于COVID-19通过细胞表面的ACE2酶结合而侵入细胞[1, 3, 9]。同时在一些动物研究中,ACEI或ARB会增加ACE2表达[31]。但最近一系列回顾性研究表明, 接受ACEI/ARB的患者比未接受ACEI/ARB的患者COVID-19病死率降低[32],Terlecki等[33]对1 729例合并心血管疾病的COVID-19患者住院病死率进行研究,结果显示,ACEIs/ARBs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综合上述,对于COVID-19合并AF患者而言,使用ACEI/ARB治疗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可能从逆转心房重构等方面获得潜在的益处。
2.4.2 他汀类药物:他汀类药物具有抗炎和抗氧化,减少内皮功能障碍和神经激素活化、逆转心房电重构和结构重构的作用,所以,欧洲心脏病学会AF管理指南指出他汀类药物可作为治疗和预防AF的药物[34]。他汀类药物可有效地抑制SARS-CoV-2活性,并能阻断包膜病毒的传染性[35],或许具有治疗COVID-19合并AF患者的作用。在最近一些他汀类药物治疗COVID-19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他汀类药物可降低COVID-19患者病死率,可作为治疗COVID-19患者的辅助药物[36-37]。Terlecki等[33]的研究结果显示,他汀类药物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提示他汀类药物可能降低COVID-19引起AF的风险。对COVID-19患者使用他汀类药物要考虑治疗COVID-19药物相互作用,他汀类药物可通过细胞色素CYP3A4代谢(如辛伐他汀、洛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或CYP2C9(氟伐他汀)[35]。事实上,许多抗病毒药物,如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等抗病毒药物,可明显抑制CYP3A4的生物活性,从而减缓降解他汀类药物,使得血液中药物浓度升高,导致其不良反应风险增加,此外,他汀类药物治疗中不良反应的发生常与个体差异有关,所以,使用他汀类药物治疗COVID-19合并AF患者时,应严格筛查基础疾病,控制用药剂量,避免药物相互作用。
2.5 中医中药治疗
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中,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中医药参与率达到90%以上)已经收到了良好效果。早期研究发现,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能显著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缩短病程,提高临床治愈率,且优于单纯西药治疗[38]。同时有研究表明,参附注射液可抑制肺部炎性反应,降低 IL-1β、IL-6 等细胞因子水平,升高IL-2水平,调节患者抗炎/促炎因子平衡。中医药多靶点、多途径、多层次,作用广泛,治疗优势突出,在面对细胞因子风暴等复杂疾病的防治中体现出了较高的价值[39]。
3 小结与展望
COVID-19疫情还在蔓延中,SARS-CoV-2感染可能会增加患者对AF的易感性,并且其并发AF又可引起血流动力学障碍和血栓栓塞事件,增加COVID-19患者的病死率,然而,目前对COVID-19合并AF的机制还不十分清楚,治疗指南还没有出台,所以对于COVID-19并发AF的治疗及其机制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