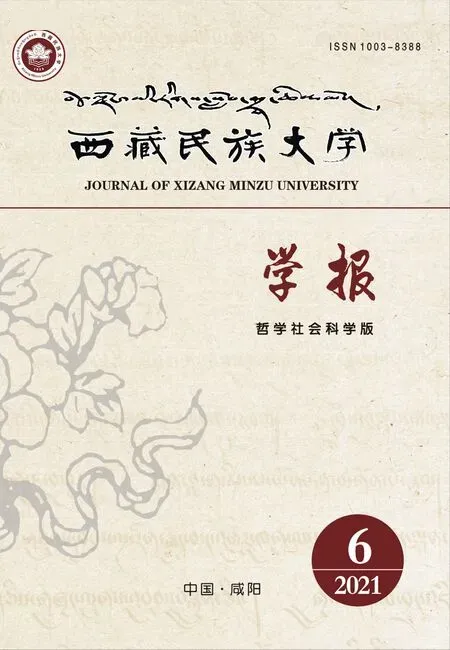十三世达赖从出走到入京觐见相关问题考述
2021-12-04陈鹏辉
陈鹏辉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陕西咸阳 712082)
引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的历史发展,到了晚清时期遭遇了日益严重的外来挑战,在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的背景下,若干历史人物和事件亟需深度论述,准确揭示其历史真实。
光绪三十年(1904)侵藏英军逼近拉萨的危急时刻,十三世达赖离藏出走一事影响时局至深,历来备受史家关注。以往研究的重点是十三世达赖出走库伦有无投俄倾向及其入京觐见相关问题①,近年来始有一些其出走期间的心理活动、在库伦时清廷的宣慰及与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关系等的成果②,但未见从总体上讨论其自1904年出走至1908年入京觐见4年多时间里清政府的应对等相关问题的专题性成果。
就基本史实而言,光绪三十年,侵藏英军进至距离拉萨仅一步之遥的曲水时,十三世达赖于六月十五日(1904年7月27日)后半夜率少数亲随秘密离开拉萨,十月行抵库伦。在库伦逗留一年多时间,清廷不断催令其返藏,至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终按清廷安排,在库伦办事大臣延祉的护送下启程返藏,于次年十月行抵西宁塔尔寺。在塔尔寺停留月余,原定返藏计划改为入京觐见,并于十一月底由塔尔寺启程,次年九月安抵北京,先后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此为十三世达赖从出走到入京觐见4年多时间的大体行止,然而这期间的一些重要细节是不容忽视的。十三世达赖秘密离开拉萨时有无明确目的地?为何前往库伦而不是其他地方?清廷在得知其出走后是如何应对的,原本急切催令其返藏,为何改为准许入京觐见?等等,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必须厘清。本文运用汉藏文史料及俄方档案等资料,拟就此展开探讨。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十三世达赖出走与有泰准奏褫革名号
光绪三十年(1904)侵藏英军逼近拉萨前夕,十三世达赖匆忙委任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为代理摄政,于六月十五日(1904年7月27日)后半夜时分③,“向所依靠和供奉的护法神作嘱托后,带了少量随行人员离开拉萨”[1](P75)。
就客观形势而言,十三世达赖此时离开拉萨实属迫不得已。侵藏英军头目荣赫鹏早在行至江孜时就致函十三世达赖,表示英军将攻进拉萨,他“奉命缔结之条约,一经达赖签字盖印”“即立当退出拉萨”[2](P182),这是赤裸裸地逼迫十三世达赖与其“直接谈判”,继而签订条约以获取侵略利益。而此时清政府对英国的侵略行径一味妥协退让,英军进至曲水后,外务部急忙借用英国驻华公使与侵藏英军之间联系的电报渠道,指示驻藏大臣有泰:“务劝达赖即与英员迅速开议,切弗退避,致误事机”“收到照办”[3](P1188)。有泰不断“开导”十三世达赖与侵藏英军议和,这让十三世达赖对清廷大失所望。然而,西藏地方虽遭英军惨绝人寰的古鲁大屠杀及江孜保卫战的失利,但仍不失斗志,尤其是十三世达赖当时抗英立场坚定,不愿与英方谈判,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侵藏英军行至曲水时,十三世达赖派基巧堪布帕西·阿旺欧珠前去交涉,但荣赫鹏“坚持要到拉萨同达赖喇嘛直接谈判”“达赖喇嘛考虑,如果会见英国军官,谈判时只能屈从于英方的条件,这样本人难以承担由此而给政教大业的现今和未来带来危害的责任。于是产生了出走内地,向皇太后和天子以及内臣面奏佛业遭难的念头”[1](P74)。可见,十三世达赖在侵藏英军开进拉萨前夕秘密出走,确系情势所迫。
十三世达赖出走后七天,六月二十二日(8月3日),荣赫鹏即率侵略军开进拉萨。此时有泰及荣赫鹏均不知其早已出走,外务部则指示有泰“藏人此时当知悔悟,希即相机切实开导,与英员妥为商议”[3](P1190)。有泰对荣赫鹏逼签条约束手无策,方才得知十三世达赖早已出走,但不知去向。七月十一日,有泰上《达赖潜逃乞代奏请旨褫革其名号》一折,指责十三世达赖:“本年战事,该达赖实为罪魁,背旨丧师,拂谏违众,及至事机逼迫,不思挽回,乃复遁迹远扬,弃土地而不顾,致使外人藉口,振振有词”,最后请“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褫革,以肃藩服,而谢邻封。并请旨饬令班禅额尔德尼暂来前招主持黄教,兼办交涉事务”[3](P1190)。七月十六日,清廷下旨:“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著班禅额尔德尼暂摄”[4](P74)。二十日,有泰再上《达赖喇嘛兵败潜逃声名狼藉据实纠参折》,继续指责十三世达赖有“种种劣迹”,强调“若不严行纠参,实无以谢邻封而肃藩服”[3](P1193-1194)。有泰请旨褫革十三世达赖名号后,又大加纠参,全然不顾西藏地方的反应,幻想以此达到“谢邻封而肃藩服”的效果,殊不知此举使局势雪上加霜。同时,有泰一厢情愿邀请九世班禅到拉萨主持事务的计划,也被九世班禅以“若分身前往”“恐有顾此失彼之虞”[3](P1206)为由推辞而落空。英军从拉萨撤走后,有泰称“现在藏中安堵如常,汉番亦尚静谧”。直到十二月,有泰还不知十三世达赖的去向,奏称“数月以来”“踪迹杳然”[3](P1204)。不仅有泰不知十三世达赖的去向,清廷一度也不掌握其动向,更未见对其去往何处作出查明安排。总之,有泰作为驻藏大臣本该对十三世达赖出走负有直接责任,但其以“不遵开导”“兵败潜逃”论处,难免有为自己开脱之意;而清廷在不明十三世达赖去向之时,就采纳有泰的建议,褫革其名号,这让十三世达赖及西藏地方更加对清廷心生不满。应当说,十三世达赖出走后,清廷及有泰的上述应对之策,是欠妥的,至少是没有虑及可能的严重后果。
二、十三世达赖行抵库伦与清廷促其返藏
(一)清廷得知十三世达赖出走及将其“迎护”至库伦
据目前所见史料,十三世达赖出走的主观愿望有两种记载,一是赴京觐见,一是赴俄“求援”。然而清廷起初对此不得而知,直到在得知其一路北走,判断其有可能前往俄国后,才匆忙采取了防止赴俄措施。关于十三世达赖一行的出走路线,据《第十三世达赖年谱》大体为:从拉萨出发往北经那曲,翻越唐古拉山进入青海;然后从玉树过通天河,穿越柴达木盆地行抵甘肃嘉峪关,再经甘新交界进入蒙古境内;最后被清廷“迎护”到库伦。就笔者所见史料,十三世达赖一行进入蒙古之前,清廷一直是不掌握其动向的,也没有重视。直到其一行进入蒙古境内,清廷通过库伦办事大臣德麟的报告方才得知情形,也始意识到其极有可能前往俄国的事态严重性,匆忙采取措施。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四日(11月1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德麟,电悉。达赖喇嘛被难逃出求救,请为代奏等语。著德麟迅即派员迎护到库,优加安抚,以示朝廷德意”[5];同时,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要求传知新授西宁办事大臣延祉⑤,“迅速请训”。二十五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新授西宁办事大臣延祉现在出差库伦,由库伦前赴西宁本任”[6](P180、181);二十六日,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德麟。昨据电奏达赖喇嘛求救,已有旨谕令优加安抚,现派延祉前往库伦迎护,延祉未到任以前,仍著德麟妥为照料”[7](P180、181)。由此可见,清廷为防止十三世达赖赴俄,接连三天的应对之策是要求德麟迅速将其“迎护”至库伦“优加安抚”,再由延祉护送到西宁。九月二十四日的安排是目前史料所见清廷最早采取的措施,清廷是绝不允许十三世达赖赴俄的,应当是在得知其动向后第一时间就即刻做出部署的,因此清廷得知其动向的时间很有可能就是九月二十四日,不会再早太多。
后据乌里雅苏台将军连顺奏称,他“忽于九月二十间,闻蒙人传说达赖有行入喀尔喀地面信息”,遂于十月初一派员前去,“再三请其暂到乌城安歇”,但被婉拒。至十月初十日,连顺才接到库伦办事大臣转来外务部电咨:“无论达赖行抵何处,务即迎护内地,妥为款留,勿任北去”。此时,十三世达赖一行距库伦仅十日路程,连顺随即“密函哲布尊丹巴,以达赖初到库伦,未悉情形,俄人居心叵测,嘱其勿与往来”。又迟至十月二十五日,连顺接到新疆巡抚转来陕甘总督电咨称:“达赖有往赴俄国之意。探明七月二十八日由柴达木赴大库伦,恐其入俄,咨令阻止,劝其返回青海”。连顺表示,驻藏大臣以及青海、甘肃、新疆等地督抚、大臣,“于事前未知防范,岂于事出仍无所闻”“况由藏到库,必经青海、甘、新边界,彼处电信往来,朝夕可通。纵未能就近挽留,亦当早知,各处先事预防,何竟迟之十月下旬,达赖已到库伦,始行转来一咨,亟亟以阻止达赖,勿令入俄为急”。连顺对事后才接到电咨批评:“其谋似忠,其虑似远,而其实竟为事后无祸之空谈”。同时,连顺分析“达赖入俄”的可能性认为:“至云达赖入俄一节,诚为可虑,然由藏而往,固有捷径,自新而入,亦有便途,既因情急外逃,尚知携带印信,其心亦概可想见。总之,入俄一语,可深虑不可明言,恐达赖闻知,反生他志也”[8](P83)。从连顺的奏陈看,青海、甘肃、新疆等地方大员,并未及时掌握十三世达赖的动向。九月二十四日起,经过清廷一番周密安排,十三世达赖一行于十月二十日(11月26日)抵达库伦时,受到了库伦办事大臣、蒙古王公大臣、哲布尊丹巴等僧俗各界的热烈欢迎⑤。
值得注意的是,十三世达赖进入蒙古境内后,距俄国仅一步之遥,为何没有直接前往,而是通过库伦办事大臣德麟主动向清廷发出“求救”?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十三世达赖不管是赴俄还是赴京觐见都没有做好准备。进入蒙古境内后,赴俄虽易,但尚没有得到俄国同意,不可能直接前往;赴京觐见时机更不成熟。而库伦是清代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哲布尊丹巴的驻锡地,也是蒙古藏传佛教的中心,信徒众多,十三世达赖作为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前往库伦不仅会得到很大的精神慰藉,也会有安全感。在此形势下,前往地理位置上既便于赴京觐见,也可为赴俄留有余地的库伦暂住,再根据局势发展进一步抉择,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他们一直是秘密行动,即便决定要去库伦,此时也不能冒然前往,必须充分考虑到清廷得知后的反应。于是他们向清廷发出“求救”,等于是主动报告行踪。此举当是经过精心谋划的,抑或是以此试探清廷有无同意赴京之意;也极有可能是他们分析清廷获悉后必然采取措施防止他们赴俄,而清廷最切实的措施是首先将他们迎护至库伦,这样他们就能顺势到达库伦。结果是,清廷接到德麟的报告后,自然十分担心十三世达赖一行赴俄,急忙采取措施,一面谕令德麟迎护到库伦“妥为照料”;一面让哲布尊丹巴以开展佛事活动为名予以邀请。如此,十三世达赖一行顺利到达了库伦。
十三世达赖到库伦后,因新授库伦办事大臣朴寿尚未到任⑥,清廷以延祉“暂署库伦办事大臣”[9]。十一月初六日,延祉奉懿旨赉交蟒袍料所制皮袍一件、同缎八卷、银六千两。对于清廷的“赏赐多珍”“不独达赖喇嘛感激,即阖藏僧俗莫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3](P1211)。然而对于清廷令延祉“偕同该达赖喇嘛前赴西宁,再令启程,自行回藏”[10]的安排,十三世达赖先后以“建庙”、开展佛事活动、病重等为由拖延了一年半之久。这期间,为防止其赴俄,清廷一面不断电令朴寿、延祉二人督促返藏,一面加强防范。光绪三十一年六月,清廷直接改授延祉为库伦办事大臣,专门负责十三世达赖返藏事宜,要求“遴派廉干妥员沿途护送”“一俟病痊及早启程,毋再延缓”[11]。次年三月,清廷又派御前大臣博迪苏、内阁大学士达寿等人专程赴库伦“宣慰”[12](P1475)。
清廷为防止十三世达赖赴俄百般周折期间,西藏地方对褫革其名号产生了强烈不满,噶厦、三大寺等联名向有泰“再三禀诉,请求开复(名号)”。光绪三十一年五月,有泰奏称西藏地方给他的一道公禀内称:“惟是达赖喇嘛前经被议,咎固难辞,然当离藏之时,亦属迫不得已。第达赖喇嘛为黄教之主,一旦革去名号,恐难号召番众,维系人心。用是联名,务请代恳天恩,开复名号”。有泰转而为十三世达赖“翻案”,奏称其侍从“率多小人,往往不知大体,一味逢迎,于藏印边务情形粉饰多端”,尤其是“箭头寺护法,假托神灵附体,蛊惑达赖,欺诈愚民,而又干预交涉事件。藏印决战失和,实由护法主之。丧师肇乱,实为罪魁。然而怨毒于人,番民恨之不置”。有泰将责任推给箭头寺护法后,为十三世达赖开脱道:“是战争之议,并非出于达赖本心,已有明证”,并称请旨褫革名号“为一时权宜之计”,最后奏请“开复名号以顺番情”[3](P1211)。此时清廷正在积极筹措其返藏事宜,九月初六日下旨:“著俟达赖喇嘛由库伦起程后再降谕旨”[13]。箭头寺护法后被张荫棠查处,其“苛敛横行”等属实,但有泰对十三世达赖“参革在先,回护于后”,前后态度大相径庭,足见其请旨褫革名号是缺乏远见的冒然之举。
(二)德尔智鼓动十三世达赖赴俄阴谋的破灭
关于十三世达赖的赴俄意图,牙含章认为,“根据达赖自拉萨直赴库伦,并带了德尔智的情况推断,达赖原先有由此往俄国的企图”[14](P162)。以下据俄国现已公开的相关档案具体讨论。据当时俄国驻库伦领事吕巴给俄外交部的一份密电,十三世达赖从拉萨出走的“隐秘内情”是,“无疑受到德尔智影响,并对多数谋士[的反对]进行了抵制”[15]。潜伏在十三世达赖身边的俄国间谍德尔智以获取俄国援助抵抗英国蛊惑十三世达赖,但直到他们到库伦也没有取得俄国的同意;并且清廷已于11月1日作出了“迎护”至库伦的部署。11月6日,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给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的密电中表示:“在查明达赖喇嘛来到库伦的后果,或他不会有危险以前,最好切勿采取任何行动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15]。德尔智为争取说服俄国的时间,煽动十三世达赖以“建庙”为由暂居库伦过冬,次年四月启程往西宁。期间俄方对十三世达赖的去向问题意见分歧。俄驻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向拉姆兹多夫建议:“倘能使移居俄国境内一事是出于达赖喇嘛本人决定,则最好促使他移居俄国境内”[15],但以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为代表的一派出于确保俄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坚决反对。12月26日,雷萨尔在给拉姆兹多夫的密电中指出“前往西宁就是流放”,建议“最好推迟一段不长的时间再做最后决定,何况当时情况使我们有可能安排达赖喇嘛前往中国内地,这比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更符合我们的宗旨”[15]。1905年1月28日,雷萨尔根据吕巴的报告,在给拉姆兹多夫的密电中建议让十三世达赖直接返回拉萨,而不必移往西宁。对此意见,沙皇尼古拉二世批示“必须进行讨论”[15]。2月14日,拉姆兹多夫向沙皇上奏讨论结果:“应着重研究下述设想:一、达赖喇嘛留在库伦;二、按中国要求前往西宁;三、移居俄国境内;四、返回西藏”。最后提议:“故从各方面看,最适当的办法是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他本人想返回西藏,当地宗教界也希望他返回西藏;自然,这种情势使他更加坚信,事情能如此解决主要应归功于俄国的关切。显然,中国人不再坚持达赖喇嘛迁居西宁,准备让他返回西藏”[15]。
鉴于俄国不同意赴俄,而清政府规定的起程往西宁时间已经接近,德尔智又急忙煽动十三世达赖以病重为由拒不起程,继续拖延时间以与俄国进一步联系。为争取沙皇同意,德尔智甚至利用俄国外贝加尔地区的佛教徒对达赖喇嘛宗教上的崇拜大做文章。据俄驻库伦领事吕巴向雷萨尔报告:“来此处的布里亚特人散布说,伊罗尔图耶夫奉召到赤塔安排达赖喇嘛俄国之行,且经蒙古人传到了办事大臣那里,他们似乎已经报告北京。达赖喇嘛为此感到不安,务请阁下请[中国]外交部要中国人放心,但他并未放弃去俄国的想法,故请求转告:他对委身沙皇陛下保护充满信心,他欲了解,面对各国俄国能否公开保护西藏抵抗英国和中国人”[15]。雷萨尔指示吕巴:“倘中国人问起俄国似乎已采取措施接纳达赖喇嘛一事,我会让他们放心。另一方面,达赖喇嘛请求保证:俄国面对各国将公开保护西藏抵抗英国和中国人。[我们]根本不可能作这种保证”。从吕巴给雷萨尔的报告看,俄外贝加尔地区的佛教领袖伊罗尔图耶夫“安排达赖喇嘛俄国之行”,仅是信奉藏传佛教的布里亚特人的“散布说”,这可能是布里亚特佛教徒出于对达赖喇嘛宗教上的崇拜,希望促成其到俄国做佛事活动而诱导俄政府同意的一个说辞。而德尔智在给俄外贝加尔省督军霍尔谢夫尼科夫的信中表示:“非常希望根据布里亚特人的请求,正式邀请达赖喇嘛前往外贝加尔地区”[16],可见布里亚特佛教徒希望十三世达赖前往俄国极有可能是德尔智煽动的。无论如何,雷萨尔给吕巴的指示表明,他不仅向清政府否定了此事,同时拒绝了十三世达赖的请求。清政府得知消息后也立即电令驻俄公使胡惟德“俄派佛教人随行一节断难允许”,要求“务向(俄)外务部力阻”[12](P1474)。最终,德尔智以十三世达赖做佛事活动为名前往俄国的阴谋被挫败。
与此同时,十三世达赖的随行人员就是否赴俄问题召开的会议上,“明显分成对立的两派:达赖喇嘛本人相信只有前往俄国才有利,而他周围的多数人,包括有影响的年长堪布均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俄国不可能给予西藏切实帮助”。在此情势下,十三世达赖急需得知俄国政府在面对各国“公开保护西藏抵御英、中两国”[15]这一重要问题上的明确态度。为此,德尔智巧言打破俄国反对派的阻止,带着十三世达赖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亲笔信前往圣彼得堡。此信经拉姆兹多夫转呈给尼古拉二世,其核心内容为:“伟大国君,往日慈悲为怀护佑西藏,今后请勿丢下恭顺的西藏不管”[15]。但沙皇对此并没有做任何批示,这使德尔智未能达到此行的目的。
1906年6月,俄新任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组织俄外交部官员,以及俄皇家地理协会副会长谢苗诺夫、俄前任驻库伦总领事希施马廖夫、俄前任外贝加尔总督纳达罗夫中将等参加的一次会议,专门就十三世达赖是返藏还是移往西宁问题研究制定政策。与会者认为,“俄国在西藏并无直接利益。故在诸多问题中西藏问题是同英国人最容易达成协议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应利用这一问题做可作出的让步,使我们有可能在对我们更为重要的其他问题上从英国那里得到好处”。会议还指出,英国拥有对西藏施加影响的有效手段,而俄国没有,“由此得出结论,俄国应通过同英国政府缔结外交协定竭力保障自己为数不多的利益”。基于此,会议认为俄国随后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是“如何履行对达赖喇嘛承担的道义上的责任,即如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维护他的地位”;而“摆脱困境之唯一办法”“是让达赖喇嘛住在西藏中心附近地区,好处是,即使他不返回拉萨,依然对西藏人和蒙古人有影响,且也不会遭受任何危险”。会上“精通西藏事务的专家们”则明确指出,“青海高原上一座寺院是最方便的驻锡地,它在西藏势力范围内”,这里“俄国与其来往并不特别困难”,而“英国不可能像在拉萨那样轻易对达赖喇嘛全部的行动进行监督”。俄方这次会议实际确立了俄国西藏政策的基本方针,即在英俄“西藏协定”谈判中,以出让其西藏利益给英国,换取英国对其中亚利益的承认;而按此方针,俄国对清政府将十三世达赖迁往西宁不予干涉。6月24日,伊兹沃尔斯基上奏会议意见后,尼古拉二世欣然同意[15]。至此,德尔智鼓动十三世达赖赴俄的阴谋宣告失败。
可见,十三世达赖出走及在库伦时的赴俄动向,都是受德尔智以获取“俄援”为诱饵煽动、蛊惑的;但当时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无力与英国抗衡,加之俄国内革命形势风起云涌,自顾不暇,不可能同意德尔智的请求。对此,十三世达赖早有估计,据1904年8月11日的一则时论分析:“达赖喇嘛近日因闻俄军在辽东之败报,故其信赖俄国之心亦渐薄”⑦,这反映出十三世达赖对赴俄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三)十三世达赖的赴京之意及从库伦起程返藏
俄方档案记十三世达赖有赴俄动向的同时,对其赴京觐见的愿望也有记载。俄恰克图边界委员希特罗沃的《关于达赖喇嘛于1904-1905年留居蒙古的情况报告》中称:“达赖喇嘛起初推断并怀疑英国人和在西藏任职的中国人可能背信弃义要谋害自己而未遂,于是决定远走毗邻俄国的蒙古,即库伦,那里十分安全。他打算通过与中国皇帝的关系,查明自己未来的地位和恢复被英国人践踏的权利,并希望在这方面得到以当地领事为代表的俄国人非公开或公开的支持”[15]。除俄方档案外,更有藏文、汉文史料表明十三世达赖自出走时就有赴京觐见的主观愿望。《第十三世达赖年谱》载,其在出走前“产生了出走内地,向皇太后和天子以及内臣面奏佛业遭难的念头”[1](P74)。李苏·晋美旺秋等人的《西藏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也记,十三世达赖出走之前向西藏地方上层明确表示:“先去蒙古,再赴北京陛见皇太后和光绪皇帝”“拟亲谨大清皇帝全面计议”⑧。张荫棠到拉萨后,代理摄政洛桑坚赞当面向其禀称:“达赖濒行,曾言拟赴北京吁请陛见,面陈西藏情形,恭请圣训,俾得有所遵循”[17](P1330)。总之,十三世达赖出走前就有赴京觐见之意。但当时清廷及驻藏大臣一直对英国侵藏战争妥协退让,且十三世达赖与驻藏大臣矛盾重重,作为政治上已经成熟的他,不可能冒然直接赴京;更为甚者,出走后不久,清廷褫革其名号,无疑加重了其赴京觐见的顾虑。
然而,清廷拒绝承认“拉萨条约”,派唐绍仪等赴印度与英方重订条约,以及承担英国要求的战争赔款、“赏发巨款”犒劳西藏地方在抗英战争中的有功之人等一系列措施,应当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十三世达赖对清廷的一些不满,因此其在库伦时虽受德尔智煽动有赴俄之意,但也是有赴京觐见之意的。《第十三世达赖年谱》载,延祉赶赴库伦后,会同驻库伦满蒙大员会见十三世达赖时,“达赖喇嘛略谈了此次去京向皇帝面奏政教前途一事”[1](P81)。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有泰奏报,“兹据番众禀称,达赖有由库伦到京朝觐之说”[3](P1207)。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注意到这一点,指出:“达赖喇嘛似曾指派他在西藏的摄政向拉萨的驻藏大臣提出请求,希望清朝皇帝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以便他能够向皇帝解释西藏的真实情况”[18](P10)。四月二十八日,有泰在给理藩院的《达赖喇嘛自库伦行将赴京朝觐请沿途照料片》中报告,“现据噶布伦等禀称:达赖喇嘛行将赴京朝觐恩主大皇帝”,因随从乏人,西藏地方也已拣派其兄顿珠多吉公爵⑨,随侍达喇嘛雍和宫札萨克罗桑顿柱以及商上、三大寺代表等,经那曲取道西宁一带前往,“恭送达赖佛爷需用物件,并随侍供差”,恳请发给路照。有泰称:“查该噶布伦来禀所请,系为照料达赖喇嘛起见,词甚恳切,意尚无他,自应照准办理”[3](P1210),“当经善绘路照一张,札发噶布伦等转给,承领启程”;同时有泰将“该差人名、年岁及骑驮、军械、什物等项”清单,向理藩院“抄单咨明”,请求“查照施行”[8](P97-99)。然而关于顿珠多吉一行人的目的,牙含章、恰白·次旦平措等认为是“迎接返藏”⑩,这当是从后来的实际作用为出发点的。当时清廷是坚持返藏的,而十三世达赖有返藏、入京觐见,甚至等待俄国援助几种可能。据《第十三世达赖年谱》载,此一行人于当年十月、十二月先后抵达库伦,但未明记是为入京觐见做准备还是为“迎接返藏”。据1905年1月31日吕巴给俄外交部的密电称:“西藏僧侣、寺院和百姓代表已抵达这里,请求达赖喇嘛返藏”[15];《第十三世达赖年谱》也载,1905年7月2日(六月二日),“接见由拉萨派来迎接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官员孜准旦年·强巴曲桑一行”[1](P85)。就目前所见史料来看,西藏地方派往库伦“迎接返藏”的代表不止一批,顿珠多吉一行人的目的虽不能确知,但西藏地方向有泰禀称是为入京觐见做准备,至少体现出他们的一种意见。总之,十三世达赖在库伦滞留期间,不顾清廷不断催促返藏,一再推迟行程,其中是有赴京觐见之意的。
十三世达赖虽有赴京觐见意愿,但不仅未得到清廷同意,更为俄国所不允许。1906年2月21日,俄外交大臣拉姆兹多夫给俄新任驻华公使璞科第的密电中写道:“据堪布德尔智所接电报,达赖喇嘛拒不前往中国北京,给聚在北京的蒙古王公留下不良印象,他们认为最高教主拒绝来京是您的主意,并指责他过于屈从俄国的影响”“而从德尔智报告可以看出,目前达赖喇嘛健康状况不佳,有充分理由拒绝北京之行,更重要的是……庆亲王对蒙古王公转告他的关于此行的情况作了否定的答复。最好您通过最合适的途径向蒙古王公说明实情”,尼古拉二世明确同意其中意见[15]。这份密电表明俄国是反对十三世达赖赴京觐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就此表态正透漏出他们掌握到十三世达赖是有赴京觐见动向的。可见,德尔智为向俄国表达十三世达赖赴俄的诚意,向俄国称其拒绝前往北京;而十三世达赖则就赴京觐见与清廷是有沟通的,只是沟通是秘密进行的。清廷之所以未即表同意,至少是受俄国干涉。
1906年4月,《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前,十三世达赖通过奉旨前来“宣慰”的御前大臣博迪苏、内阁学士达寿代奏,就开埠等事项表达意见,提出除亚东之外,“英国商人不得任意于江孜、帕里等藏区各地流窜经商”[12](P1474)。此时,他即将按清廷要求启程前往西宁,其请为代奏之事确系因事而奏;但不得不说,此举有试探清廷对他赴京觐见的态度的用意,这是十三世达赖离开库伦之前为赴京觐见所做的最后努力。
在赴俄、赴京觐见都无望,且与哲布尊丹巴产生矛盾,不能再滞留库伦的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只得遵照清廷要求前往西宁。实际上,据《第十三世达赖年谱》载,早在1905年年底,他就给塔尔寺僧俗会议写信[1](P87-88),为前往塔尔寺做准备。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按清廷的安排,十三世达赖在延祉等的护送下启程前往西宁。
以上可见,十三世达赖自出走至行至库伦前,清廷对其出走未予足够重视;而自“迎护”至库伦直到其启程前往西宁期间,清廷的主要应对之策是督促返藏,为此清廷颇费周折。但清廷要求十三世达赖前往西宁,实际只是出于防止其赴俄的权宜之计,其返藏的具体问题仍须进一步筹措。
三、张荫棠促成十三世达赖入京朝觐
九月二十二日,十三世达赖一行即将抵达西宁时,奉旨入藏查办事件的张荫棠接内阁学士达寿以军机处名义发来的电文,通报十三世达赖现已行抵甘肃,下一步将到西宁,计划在西宁休整月余,然后将经由柴达木盆地返藏;同时,询问沿途照应安排情况,但这份电文的重点是“究竟达赖到藏后能否驾驭相安,及番众意向若何”,征询张荫棠的意见,要求“会商有(泰)、联(豫)两大臣,详察妥筹”[17](P1314)。由此,张荫棠开始介入筹措十三世达赖去向问题之中。
张荫棠接到军机处来电时,正由印入藏,行至江孜。实际上,早在印度期间,他在筹谋整顿藏事的整体方案中就已虑及十三世达赖的去向问题,当时虽未明确具体去向,但他所奏呈的整顿藏事方案的重要前提是十三世达赖不在西藏,即暂不返藏。此外,张荫棠还根据与英印陆军司令基钦纳(Hora⁃tio Herbrt Kitchener,张荫棠当时译为吉治纳)的谈话专门向外务部报告:“印陆军总统与棠私言,达赖通俄,我英自有办法。韩税司(韩德森)探称,印政府派前经入藏之提督马顿和日间赴藏勘察进兵路途,似此情形,英人进取之心日决”,他据此建议:“拟请设法阻止达赖,勿令回藏,抑或令其留京,以杜衅端”[17](P1314)。可见,张荫棠尚在印度之时,就根据局势持“勿令回藏”的意见。
此次军机处向张荫棠征询意见的上引电文表明,清廷仍是按返藏进行部署的。九月二十三日,张荫棠结合军机处的通报,对英国加紧拉拢九世班禅、“达赖亲俄”、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矛盾,以及“埠事未妥”、驻春丕英军还未撤走等情势综合分析后,向军机处奏陈意见:“英人现虽无阻止达赖回藏举动,然班禅与达赖仇隙已深,班禅久堕英煽惑术中,难保达赖回藏时不藉端挑衅,而英即乘此坐收渔人之利。昨班禅派扎萨克来见,语次颇有大志,恃英庇不讳。今若以接达赖事会商有(有泰)、联大臣(联豫),黄教自是欢迎。惟现值埠事未妥、春丕兵未撤之时,可否缓接回藏,以免牵动大局。且冬令严寒,应准其在西宁过冬,以示体恤”[17](P1314)。
同时,张荫棠进一步建议“若欲达赖回藏后驾驭相安”,必须予以保护,“乃能收主权而弭隐患”。总体而言,张荫棠的意见是十三世达赖“暂缓回藏”,这一意见为清廷采纳。十月十八日,陕甘总督升允电告有泰:“达赖喇嘛抵甘,弟赴平番接见。现到西宁驻塔尔寺。奉旨款留,暂不回藏”[3](P1235),十三世达赖遂在西宁停留了一年多时间。戈尔斯坦认为,清廷采纳张荫棠“暂缓回藏”的意见,促使其改变策略,开始寻求两条新的行动路线。一是在遭到俄国拒绝后,寻求与清朝中央政府改善关系,最后得以赴京觐见;二是认识到了改善同英国关系的重要性,于是恢复了1903年以亲英罪罢免职务的夏扎·边觉夺吉、雪康·次旦旺秋和羌庆巴·阿旺白桑三位噶伦的权力[18](P10)。戈尔斯坦将十三世达赖转向亲英,完全归咎于清廷采纳张荫棠“暂缓回藏”的意见,是有失偏颇的。
从张荫棠以上奏请“暂缓回藏”时的考虑看,他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防止十三世达赖回藏后被英俄等利用。前述俄国在其西藏政策上已经确立了对英国妥协的方针;而英国此时是有希望其返藏之意的。十三世达赖出走内地后,荣赫鹏等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九世班禅身上,他们诱骗九世班禅赴印的阴谋中是不希望十三世达赖回藏。同时,当看到德尔智蛊惑十三世达赖前往库伦,寻求俄国援助从而对自身不利时,英方希望清政府“应将达赖监禁”[17](P1365)。然而英方诱骗九世班禅赴印阴谋失败后,又反过来加紧拉拢十三世达赖,对其返藏“并无阻止”。然而对张荫棠而言,“暂缓回藏”实际也是权宜之计,他在进一步筹拟方案中不得不警惕英俄的侵略企图。
为抵制英国的侵藏图谋,张荫棠对英方诱骗九世班禅赴印,扬言“以班禅取代达赖,已成独立”的阴谋高度警惕,担心十三世达赖回藏后与九世班禅矛盾激化,而英国得以坐收渔翁之利。同时,为抵制英国拉拢九世班禅的阴谋,张荫棠采取的一个针对性措施是“转劝”九世班禅入京觐见。九世班禅为向清政府澄清赴印并非他的本意,而是被英方“以兵威胁”前往,也有入京觐见之意,于是请张荫棠代奏入京觐见:“开春后拟亲赴北京援案吁请陛见,跪聆圣训,为皇太后皇上虔诵万寿经典。一俟奉到谕旨,即当由北道入都”。然而噶厦得知九世班禅请求入京觐见后,立即向张荫棠提出“令达赖于班禅未到之先速行入觐”。在此情况下,张荫棠认为:“今达赖班禅各争先吁请陛见,想为望恩幸泽起见。倘令联袂同来,获聆圣训,猜嫌互释,永固屏藩,似于藏防不无裨益”[17](P1325)。后来,张荫棠对噶厦主动提出十三世达赖入京觐见的原因奏陈道:“窃惟达赖以桀骜称,班禅以阴鸷著。棠在印度时,亟欲设法致二人于京师羁縻之”“以便我整顿藏事,不至有所牵制”“及棠奉命入藏,道经江孜,班禅差扎萨克来迎。谈次,微露班禅有欲代理达赖之意。棠于是乘机即令转劝班禅呈请来京陛见。及抵拉萨,以前情告知藏王(指代理摄政洛桑坚赞——引者注)。当时噶布伦等颇为惊惶,以为班禅来京后达赖必致失位,是以情急,乃电达赖亦援请陛见。此当时代奏之原委也”[17](P1325)。由此可见,张荫棠起初是通过“转劝”九世班禅入觐以抵制英方对其拉拢,后以此策略性地促成了噶厦请十三世达赖入觐,于是事情发展成了“达赖班禅各争先吁请陛见”。不得不说,在当时“达赖通俄”,而英国一面拉拢九世班禅,一面加紧拉拢十三世达赖,以及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在英俄分别拉拢以致矛盾加深的复杂情势下,力促他们联袂入觐是张荫棠挫败英国俄国侵略目的的一个策略。诚然,这其中是有“以便我整顿藏事,不至有所牵制”的考虑的。
十二月三十日,针对张荫棠奏请的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联袂入觐的意见,清廷下旨:“班禅额尔德尼吁请陛见等语,具见悃忱。著俟藏务大定后听候谕旨,再行来京陛见。达赖喇嘛现在留驻西宁,并著暂缓来京。究竟达赖、班禅等来京是否相宜,著张荫棠体察情形,再行详晰电奏”[19]。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张荫棠向军机处、外务部转呈代理摄政洛桑坚赞请他代奏十三世达赖觐见请求:“达赖现驻西宁,商上等众议,令达赖就近吁恳陛见,乞据情代奏,如蒙俞见,即令由西宁起程赴京”;同时指出:“达赖、班禅自乾隆后久未入觐,致启强邻觊觎,得所藉口。今天诉其衷,先后吁请陛见,则万国观瞻所系,主国名义愈见巩固”。张荫棠也明确指出,达赖、班禅联袂入觐“于地方情形尚无窒碍”[17](P1330),但清廷仍未允准。
同年四月,陕甘总督升允奏称:“达赖喇嘛久驻思归,惟性情贪啬,难资镇摄(慑),应否准回藏,请旨遵行”。清廷批示:“著暂缓回藏,俟藏务大定,再候谕旨”[20]。十三世达赖在库伦时,清廷为防止其“赴俄”,急切地催促返藏;但当其到西宁后,采纳张荫棠“暂缓回藏”的意见,而不同意立即觐见,让其滞留西宁的权宜之计,足见清廷在十三世达赖去向问题上犹豫不决。六月二十七日,张荫棠在藏事改革渐次开启,“藏务大定”后,再次向外务部奏呈入京觐见意见,同时提出:“可否将达赖、班禅请陛见一节宣扬,试探英使及各国声口如何”[17](P1381)。这反映出当时十三世达赖的去向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但张荫棠始终坚持认为入京觐见为妥,此一意见最终为清廷采纳。
对十三世达赖而言,张荫棠严查有泰,有泰受惩以及清廷许诺恢复名号等,应当再次给了他心理抚慰,且寻求俄援的希望当时已经破灭,所以他是乐于觐见的。英国学者兰姆(Alastair Lamb)认为,随着英俄协定的签订,十三世达赖寻求外国援助的想法开始动摇,从而下定了入京觐见的决心[21](P149-150)。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经西宁办事大臣庆恕遵旨“料理”好相关事宜后,十三世达赖于三十日从西宁启程,经兰州、西安、五台山,于次年九月到达北京,先后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
结语
1904年侵藏英军开进拉萨前夕十三世达赖出走至1908年入京觐见4年间,妥善安排其去往何处是清廷处置藏事的一个焦点。清廷从尚不掌握其去向时,就应有泰奏请褫革其名号,到催促其返至塔尔寺的权宜之举,再到最终应张荫棠之请准许入京觐见,百般周折。相比有泰冒然奏请褫革名号,及一味督饬返藏的方案,张荫棠力主的入京觐见,综合了各种因素,是较为稳妥的,体现出在应对上的积极主动性,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就局势而言,十三世达赖入京觐见本可为清廷筹藏的一个绝好契机,但局势并未因此向好,其中教训值得深思。
[注 释]
①集中讨论十三世达赖出走库伦有无投俄倾向的成果主要有郭卫平《清季十三世达赖出走库伦考》(载《西藏研究》1986年第3期)等文,该文认为十三世达赖出走库伦并非想要投靠沙俄,而是爱国忠君的具体体现。集中讨论十三达赖觐见相关问题的成果主要有:陈锵仪《简述十三世达赖入觐》(《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索文清《一九〇八年第十三世达赖晋京朝觐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马林《第十三世达赖进京觐见接待礼仪述略》(《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扎洛《十三世达赖晋京期间的礼仪与奏事权之争新探——民族国家建构视角》(《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等文,这些文章或对觐见的基本事实进行了考察,或从不同角度对觐见礼仪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②详见:史培寅《1904—1909年十三世达赖出走内地时期的心理考察》(高翠莲主编:《民族史研究》第10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婷婷,白·特木尔巴根《清末行纪所见十三世达赖出走喀尔喀蒙古事件— —以<朔漠纪程>和<游蒙日记>为中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赵翔《第十三世达赖出走库伦延祉接送考述》(《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期);王耀科《清末十三世达赖出走库伦与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失和析论》(《西部蒙古论坛》2020年第4期)。
③此时间为《第十三世达赖年谱》所记,有泰奏稿及日记均与之一致;而李苏·晋美旺秋等的《西藏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记:“藏历六月十五日(农历六月十六,公历七月二十八日),天亮前,达赖喇嘛偕少数随员,其中有三大寺的蒙古布热图喇嘛等三十余人,秘密离开了拉萨”(见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内部发行,1985年,第68页)。实际上,《第十三世达赖年谱》及有泰所记的“十五日后半夜”,与李苏·晋美旺秋等所记的“十六日天亮前”,时间是一致的。
④延祉于光绪三十年八月十六日派为西宁办事大臣。见《清实录·德宗实录》卷五三四,光绪三十年八月壬戌。
⑤十三世达赖到达库伦的时间,目前汉文史料仅见延祉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奏称“去岁六月出藏,十月始抵库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16辑),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15页),其中并无确切日期。《第十三世达赖年谱》所记为“十月二十日”(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十三世达赖年谱》,《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80页),此处暂取此说。
⑥朴寿于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派为库伦办事大臣。见《清实录·德宗实录》卷五三四,光绪三十年八月庚午。
⑦《西藏不复信赖俄人》。见《萃新报》(第四期),1904年8月11日(光绪甲辰七月初一日)。
⑧李苏·晋美旺秋,恰宗·其米杰布,德苏·仁钦旺堆,色仲·旺杰:《西藏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二次抗英斗争》。见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内部发行,1985年,第71页。
⑨关于此人的身份,牙含章先生认为是达赖之兄(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年,第163页);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认为是达赖的侄子(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下),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74页)。此处暂取前说。
⑩持“迎接返藏”论者如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牙含章先生等。详见《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下),第974页;《达赖喇嘛传》,第163页。
⑪详见陈鹏辉:《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中的“政教分离”思想及其实践》,《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