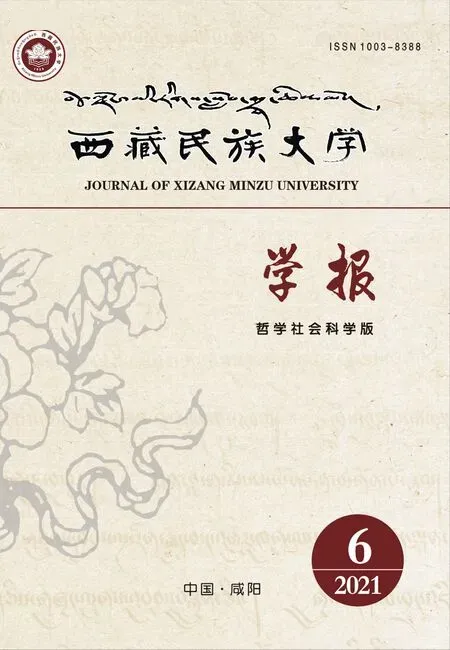用文字拂拭灵魂
——评次仁罗布小说集《强盗酒馆》
2021-12-04徐琴
徐 琴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在当代西藏文学史上,次仁罗布的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次仁罗布和央珍等藏族作家,不仅接续起古典藏族文学的脉络,而且将藏族文学从魔幻的理性探求转到对脚下大地的深刻关怀,“完成了对藏文化的现代传承与书写”[1]。次仁罗布的创作以朴实而又充满感情的语言向我们娓娓讲述了普通人物的命运,既呈现他们世俗的苦乐,又展现了个体的精神追求。他的小说承接着藏族古典文学的美学精神,面对生命中的苦难、痛楚和死亡,他用诗化的、净洁的语言建构了一个充盈丰满的文学世界,“把少数民族的小说作家们所秉承的独特的文化信仰、文学气质和独一无二的想象力、奇妙的感觉,源源不断地输送进了中国文学的肌体里。”[2]
2020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次仁罗布的小说集《强盗酒馆》,收集了次仁罗布自2009年至2018年发表的《强盗酒馆》《红尘慈悲》《兽医罗布》《奔丧》《八廓街》《曲米辛果》《长满虫草的心》《叹息灵魂》等8篇小说,这8篇作品延续了次仁罗布小说创作一贯的叙事指向和精神探求,苦难和死亡、悲悯和温暖这些丰厚的内涵在其作品中多元交融,既展现了藏族人广阔的精神世界,也传达出次仁罗布对灵魂世界的深度探查和在艺术探求上的多元开拓。
一
如学者阎浩岗所论,次仁罗布的创作“既不有意造魅,也不致力祛魅;既不否定普通人的日常幸福,又关注生命个体的精神归宿。”[3]他的创作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时又有超越性的精神探求,在庸俗生活的琐碎和困顿中挖掘人性的温暖和良善之光。
“小说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不得不从看得见的行动世界中掉过头,去关注看不见的内心生活。”[4](P30-31)如何在喧嚣的尘世生活中呈现生活的本质内核,是衡量作家精神维度的重要尺度。芜杂的民间生活样态在次仁罗布笔下得到多元的呈现。小说《强盗酒馆》中的“强盗酒馆”聚集了各色人等,在这里发生着很多有趣的事情:醉酒醒来,脚上的皮鞋变成了一双破球鞋;明明是靠墙醉倒的,醒来却和一个女的和衣躺在一张床铺上;夜幕降临,晃悠悠地走到自行车旁,却发现座椅或轮子早已不在车身上;喝了酒身无分文,然而离开时口袋里却多了一两张百元钞票……在这个葆有世俗魅力的酒馆里,各色人物穿梭其中,次仁罗布以群像式的方式和画龙点睛的方法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在俗世繁杂的生活中映照了人性的良善和美好。拉巴偷走酒馆主人的衣服,大家心知肚明,却不点破,只是在彼此的揶揄中暗示。普穷他们偷走传家银碗,虽然十分心疼,但老板娘央金却不愿告诉警察他们的名字,她认为“肯定是一个生活很窘迫的人偷的,要不他也不敢从佛龛前拿这碗的。”“来这里喝酒的人,都是给我提供生活来源的人。我怎能为了一个银碗,让公安把恩人给抓进去!”[5](P21)作品于轻松诙谐中蕴藏着丰厚的意蕴和蓬勃的力量,从中传达出动人心弦的温暖。虽然单纯地专注于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削弱对人物形象丰富性的塑造和创作可能抵达的思想深度。但不容否认,文学世界其实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次仁罗布在普通世俗的日常生活描写中挖掘隐秘的灵魂,袒露着鲜明的人文情怀,这使他的创作满蕴浓郁的诗情,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人性的超越与升华在次仁罗布笔下得以彰显传达,无不展现着次仁罗布的精神探求。《兽医罗布》中在兽医罗布为抢救牧人的财产死去后,深爱着他的两个女人其米和永青冰释前嫌,相濡以沫。因为这亡魂太重情重义了,亡魂始终到不了中阴界,所以其米和永青相携到拉萨的寺庙,在诸佛前为他祈祷,以让他的魂灵能够早日安心投胎转世。作品在时光转换和穿插叙事中一方面对世人的功利和浅薄给以批判,但另一方面着重展现的是兽医罗布对牧民的大爱,兽医罗布和两个女人之间的爱,在现实和魔幻交叠往复中映照了人间的深沉之爱。“从两个女人的眼神里,我分明能感受到兽医罗布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们,一直生活在她们的周围[5](P150)”,两个女人虽然前往各个寺庙,“在诸佛前祈祷他去投胎,心里却希望夜夜能见到他”[5](P41),这种跨越生死的爱和温情让人动容。在对底层普通小人物世俗生活的描写中,次仁罗布去展现那一点点心灵的颤动,在爱中去辉映那灵魂之光。《奔丧》中,儿子认为姐姐的自杀、母亲精神的一蹶不振、自己成长时期的苦难都是父亲造成的,对父亲心生怨恨,甚至盼望父亲死去,但等到父亲去世,他一路前去奔丧,父亲过往的经历,自己坎坷的爱情婚姻经历,所有的往事层层迭近,面对父亲的遗像,“在哀乐声的催化下,大颗大颗的泪珠滚滚而下,深深地向父亲鞠躬。我在心里告诉他,我原谅了他的过错,我要把心头积攒的怨恨、愤懑都要剔除掉。此时,我仿佛听到父亲的一声长叹,这叹气声从我的灵魂上趟过,拨动起我内心的爱来。我长时间地沉醉在这种酥软、柔绵的爱里,身心得到了净化。”[5](P164)爱和怜悯战胜了仇恨,对父亲的恨和隔膜在死亡面前烟消云散,只剩下对生命逝去的哀怜和叹惋,受伤的灵魂得以宽慰。《红尘慈悲》中的少女阿姆因为对云丹一见倾心,嫁给了贡贡和云丹兄弟,但逐渐长大的云丹却排斥兄弟共妻的旧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村,阿姆像所有的妇女一样生儿育女,像一株草一样默默地生长然后枯萎掉。阿姆的婚姻是不幸的,对云丹的爱也没有得到回应,但她真挚的情感却映照出一颗丰富柔韧的内心。作品中渗透着淡淡的忧伤,岁月的四季轮回里弥漫着对生命消逝的悲哀,然而,冥冥众生,红尘慈悲,小说的结尾,在阿姆那种柔缓、雌性、淡定、深远的眼光中,云丹找到观世音浩瀚的爱和慈悲的柔光。
优秀的文学作品背后是创作者宏阔而高远的精神探求以及对终极命题的执着追问。评论家谢有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这种值得珍重的人世。”[6](P150)而次仁罗布却以其灵魂书写为我们呈现了值得珍重的人世以及这人世的温暖。尘世间有卑微、苦难、死亡,但尘世间更有爱和暖意,次仁罗布的创作沉入到人物最隐幽的灵魂深处,去展现那俗世中令人心动的温暖,闪烁着生命中的纯粹之光。
二
尼采曾说过:“人唯有找到生存的理由,才能承受任何境遇。”广袤的西藏,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物质生活也较为贫瘠,人的生存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面临着各种困境。次仁罗布的创作为我们呈现了藏族生活的全方位图景,朴实无华地展现出底层社会中的芸芸众生相。他的作品有对苦难的描写,对死亡的审视,然而在苦难和死亡的审视中又呈现出生命的坚韧和顽强。《红尘慈悲》中父亲和母亲在觉如那个狭长的谷地里生活,在那间灰色的土坯房里,在日月的轮转中男欢女爱,接连生下了六个孩子。在岁月的四季交替中,两个孩子相继被霜冻掉被干旱掉,两条生命在毫无征兆中被夭折了,他们承受了生命消逝的苦难。在沉重的劳动中,母亲和父亲过早地衰老。然而,在这片贫瘠而又充满深情的土地上,坚韧和顽强在这里生生不息,当云丹让父母跟随自己去拉萨时,父亲朗加诺布说:“我们离不开这里,地里的庄稼已经成熟,该收割了……从我能干农活起,就没有落过一次收割,这块土地真慈悲,它给了我们粮食,才使我们能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5](P41)一代代人在这里播种生命,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苦难没有将人压伏在地,相反在对苦难的描写中映现出一个个超拔的灵魂。
个体的灵魂,在苦难作为底色的岁月中辗转沉浮,却也在跨越生死的爱和永恒的信仰里,得到了慰安、宽宥和成长。《叹息灵魂》中主人公在亲人的死亡和个体的颠沛流离中不是沉沦,而是升腾起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苦难人生的超脱和悲悯之心。在经历过父亲的死亡和哥哥对母亲的不敬,经历过饥饿困苦辗转流离,经历过河边女孩的死亡和自己被人冤枉,经历过为了生活出卖肉体和灵魂,经历过母亲的去世和妻子的难产死去,面对所有的苦难,最后,主人公在跟随天葬师替人天葬的过程中,得以领悟:“仿佛被肢解的是我的身子,让我的灵魂疼痛流血。我想到了我的爸爸妈妈,想到了坠下悬崖的司机,想到了河边死去的女孩,想到了不远的时日里,我也会跟他们一样会来到这个石台上,然后从这尘世中消失掉。”“死亡,让我看到了以往我执着的那些个事情是多么的细小、无聊啊,为了那些我把青春都耗损掉了,我的人生在利益、争斗、愤懑中殆尽。直到死亡,我的灵魂一直要带着更多的怨恨和贪欲,直到无休止地轮回。”[5](P314)怨憎、乖戾在死亡面前随风飘散,在感慨自己苦难之时,也在感慨其他人的苦难,所有的苦难不过是灵魂净化的必要之途,心灵在此刻得以顿悟,由个人的苦难开始升腾起对众生灵魂的悲悯之情,在为自己灵魂叹息的同时,也叹息着所有人的灵魂。
次仁罗布关注尘世的困境,《八廓街》系列中的《威风凛凛》以儿童的眼光呈现了嘎玛的威风凛凛,以及无奈的身体之伤所造成的生命的困境。《岭松少爷》中朗杰俊美的经历,映照出特殊历史时期个体命运的沉浮,呈现出人世难以言明的苍凉和无奈。《梅朵》中对疯癫梅朵不胜唏嘘命运的描写,展现出尘世的悲哀。《长满虫草的心》写物质利益的追逐败坏了人们的良心,因为采掘虫草,有了械斗和杀害。金钱也蒙蔽了亲人的爱心,亲情在物质面前已无藏身之地。他重视对心灵的描写,在令人颤抖的灵魂之伤中展现了生命之痛。他刻画每一个幽微的灵魂,描绘不同的苦难境地,因为对普通人精神质地的深刻洞察,这使他的作品显现了慑人的魅力。他从死亡和离别回看人生,展现小人物命运的坎坷,灵魂的受伤,然而在描写普通人生存的艰难和精神的磨难时,也写出了他们超越苦难走出困境的勇气和坚韧的品性,以及他们的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光辉,灵魂的净化和升华。他对人生饱含着正直的理解,用智慧悲悯之心面对尘世的苦难,“既直面苦难和苦难深处的耻辱、卑微、懦弱,又不轻视苦难所唤醒的那些曾经昏沉的灵魂,这种直逼人心、拷问灵魂的力量促使着读者也经历着一番精神炼狱。”[7]他书写生存的苦难、精神的受难、人性的坚韧,在荒芜中探寻灵魂的安妥之地。“写作是为了唤醒温暖和怜悯”[8],次仁罗布用他笔下的文字传达了他的文学理想,他的创作在面对苦难时,便有了超越性的认知。
三
从精神内蕴上来看,次仁罗布“不仅实现了藏族悲悯文化意识的传承与担当,而且赋予悲悯意识以现代性意义,彰显出对藏族传统悲剧美学的继承与发展,体现出藏民族人性之美,人性之魅。”[1]藏族传统文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书面文学大多受佛教“四圣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的制约和影响。为了宣扬现世唯苦,皈依解脱的思想,一部作品往往前半部分描写的是俗世生活的林林总总,权力的角逐,富贵的享受,情感的漩涡,尘世的美满幸福抑或痛苦焦灼;而后半部分呈现的是人世的无常和幻灭,荣枯相伴,众生皆苦,着眼点在悟道,断绝俗念,认为只有皈依佛法,通过修行才能获得解脱。标志着作家文学开始从文史哲不分的状态和宗教的附庸中脱离出来,具有了文学的审美独立性,走上了纯文学的创作道路的长篇小说《勋努达美》与《郑宛达瓦》在18世纪出现,但这两部作品从中心意旨上来说仍然是宣扬宗教思想,贯穿着因果报应的思想,认为尘世的浮华不过是虚空一场,现世的一切都是苦的,修行佛法是唯一的救赎之路,告诫诸生只有虔诚地皈依佛法,了断尘缘,断除贪念和世间的虚妄,才能修成正果。可以说藏族古典文学是在宗教观指导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宣传宗教思想,对人生唯苦的认识是藏族传统文学的一个基石。正是人生唯苦,使得藏族传统文学对现世的理解有一种天生的悲剧,然而也是因为对终极价值的思考,使得藏族传统文学往往会去关注生死,有着对生命终结性的思考。次仁罗布在宗教氛围极为浓厚的八廓街长大,大学期间进的是藏文系,因此,次仁罗布的文学创作自然而然受传统文学和宗教观念的影响,去关注尘世的苦难和生命的消亡,展现灵魂深处的颤动和不安,他的创作在精神脉络上接续起了藏族古典文学的传统,然而又有着建立在广袤大地上的深刻人性关怀。他的创作不是靠宗教的皈依和救赎去解救人生,而是用温暖和坚韧去化解人生的苦难,具有超越宗教的普世的思考,既显现了藏民族文学的特色,又有着通透人性的魅力,从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从整体创作内蕴上看,次仁罗布的创作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和对民族历史的理性重构,次仁罗布“把藏文化纳入到整个中华文明中加以考察,有效地实现了汉藏文化的对接整合,在人类学和文化学的双重思考中完成被遮蔽文化的正名与价值重现。”[9]其秉持“记述民族心灵,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民族精神”[10]的创作理念,创作力图展现藏民族在时代历史语境中的现实冲突和心灵探求,展现绵绵相传的灵魂之光,从其创作中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从鲁迅开始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在其一系列作品如《红尘慈悲》《强盗酒馆》《兽医罗布》中都有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形象,通过这些形象展现的是对藏地现实生活的理性反思,从中传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凛然大义的担当精神。《强盗酒馆》通过在场的“我”呈现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兽医罗布》中通过兽医罗布死后不被追认为劳模,展现的是城乡二元对立冲突;《红尘慈悲》展现的是现代婚姻制度下对一妻多夫制的反思。作为有着自觉使命感的作家,回望民族的生活,在现代和传统的并辔齐行中,虽然作者的这种理性反思有时是相互纠结并带有一定抵牾的,如《兽医罗布》中“我”更倾向于维护传统的生存方式,目的是展现人性之温馨,但在《红尘慈悲》中却对这种传统的婚恋持摒弃态度,为的是个体的自由与尊严。作者内心的冲突使得其文本显现出驳杂多元的精神指向,蕴涵着民族知识分子在现代化之途中的多元探求和精神质询。他的创作展现粗粝多元的生活,自觉地将其融入中华民族现代化之途的洪流中,展现了民族知识分子的深远探求。
四
作为一名优秀作家,次仁罗布在创作中一直寻求变化和前进的可能,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显现了他在叙事艺术上的努力。《强盗酒馆》中的8篇作品均以第一人称来展开,叙事上精雕细磨,采用了多重的叙事次序,顺叙、倒叙、插叙等多种叙述方式在其文本中变换组接,时间、事件、人物交错反复,通过叙述人物的转换,以及对所叙事件的拆解和重组,打破叙事时间的线性发展顺序,使得故事中断并形成跌宕,有意造成小说阅读的难度,从而使小说不再是平面的单层叙述,而是空间维度的多层呈现。如《兽医罗布》这部作品,虽以第一人称来书写,但中间又以亡魂的角度展开回溯,时间也是交叠繁复,在多层次的书写中展现了丰富的人性,显现了次仁罗布在构建故事上的非凡能力。
此外,次仁罗布的创作关注灵魂,关注生命,很多故事运用佛教中关于中阴、轮回等来展开叙述,传达出独特的文化内蕴。《曲米辛果》以两位昔日朋友对话的方式展开,这两人1904年在“江孜保卫战”中已经战死沙场,对话是在时隔百年后,其中一位已经投胎转世,而另一位是仍未转世的亡魂,通过他们的对话再现了藏族历史上反抗英国侵略的英勇壮观的一幕,在魔幻中传达出对生命的留恋和生生不息的民族英雄情怀。小说在叙述方式上十分独特,运用亡魂叙事,在交错的叙事中从小人物的角度再现了悲壮的战争,在生死轮回中写出了藏族历史上荡气回肠的一幕。《长满虫草的心》也是以亡魂的角度展开叙事,盗挖虫草的“我”被对方摁入冰冷的溪水憋死,魂灵见到了死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并依附同来的伙伴回到县城,接着跟上村里的木匠回到家乡,满蕴不甘和难舍之情的亡魂却遭遇了亲人的冷漠,魂灵再也不能自由飞翔。《兽医罗布》中兽医罗布的亡魂太牵挂尘世,始终不愿投胎,亡魂甚至与“我”一起喝酒对话,亡魂还以回忆的方式讲了和两个女人的感情,以及如何在雪灾中转移牧人和牲畜,最后牺牲的过程。这样一种亡魂叙事的方式可堪比胡安·鲁尔福笔下的《佩德罗·巴拉莫》,意识流、现实、超现实在作者笔下不留痕迹地自由转换,人物丰富的内心得以呈现,在破碎迷离的魔幻氛围中展现灵魂的真实。
在叙事语言方面,次仁罗布具有极强的艺术敏感力和独到的观察能力,他的语言是一种空灵的诗意的语言,温馨而浪漫,在孤独和感伤中还有一种优美之所在。它表达的是对美好易逝的感念,对生死存亡的凝视与哀伤,对世事无常的喟叹,是此在与彼途、自然与人生的契合,弥漫着一种空灵的、浅淡的哀愁,这和他整个作品哀婉、孤独、感伤的基调是一致的。其短篇小说《红尘慈悲》中,环境是恶劣的,生存的困境如影随形,但云丹回忆自己的童年也有很多温馨的记忆:“夜晚满天的星星在头顶的天际窃窃私语,风从隔窗的木板上叫唤我的名字;雪水融化的溪流从山脚滑过,溅出朵朵美丽的浪花;四月的桃花粉嘟嘟地缀满枝头,笨笨鸟麻雀布谷鸟的叫声震碎村子的寂静;一场大雪飘落下来,山上的猴子、獐子、盘羊等跑到村里来觅食,我们隔着几十步相互对望;年迈的西噶老僧跏趺在一块遮阳布下,给我们讲述地球的形成、人类的诞生、神仙的传说等。还有,朗加诺布驱赶骡子,把贫瘠的梯田次第开耕,德西把满载希望的种子撒进土壤里,风把湿土的香味吹进我的鼻孔,再沁入到心脾里。夜晚,村子里的男人们挨家轮转,在油灯微弱的光亮下盘腿就座,诵读祈祷的经文。黑暗中那悠扬的音律荡漾在村子上空,抚慰着全村人的内心。[5](P25-26)他用充满诗意,和灵魂相通的语言将渗入心灵的美好呈现出来,苦难境地中的温馨记忆,更是令人心生感伤,那美好的一切终将逝去,苦难却是永恒,在苦难面前,温馨美好的记忆更是有了一种对比的残缺之美。他的语言是充满情感的心灵化的语言,如在《长满虫草的心》中,“我”在死后,迫切地想回到家乡,“我在众多的房子中,就盯着建在坡地上的我家。我的魂终于回到了家乡,可以伴随家人待到四十多天。我的小孩、我的媳妇,还有开始苍老的爸爸,我会相守到去投胎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对你们满怀爱情,你们对我也是这样的情感。想到这些我快要揉碎掉,我捂着脸嘤嘤地哭泣。”[5](P253)悲凉之雾,痛彻心扉。次仁罗布用文字拂拭灵魂,为我们呈现一个个丰厚敏感的内心。
次仁罗布是一位在灵魂的深度和艺术的创新方面不断在探索的作家,正是这两方面的努力,使得次仁罗布的创作呈现出非同凡响的魅力,而《强盗酒馆》则显现了次仁罗布在这两方面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