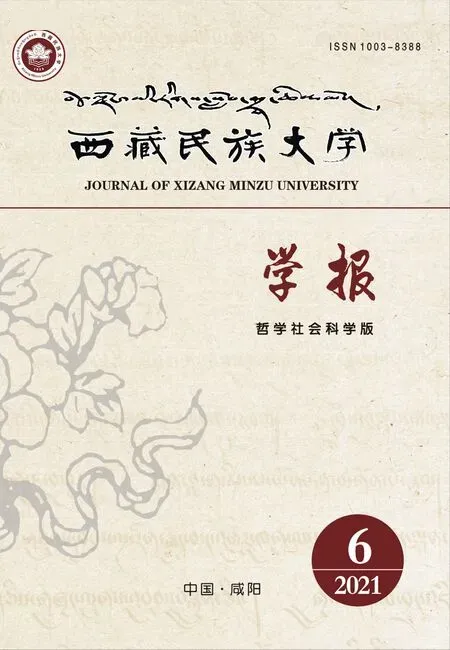清代中尼边境历史文化交流与强边思考
2021-12-04冯智
冯 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为“四件大事”,其中强边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缅甸、不丹等国以及克什米尔地区毗邻,边境线近4000公里。其中,与尼泊尔之间的边境线长约1200公里,定结、定日、聂拉木、吉隆、萨嘎、仲巴、普兰等7个县与尼泊尔交界。中尼之间山水相连,历史关系源远流长。清代,中尼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交往密切,清廷官方和西藏地方记载尼泊尔的史料丰富①,这也说明尼泊尔曾长期处于清朝藩属国的地位。有关成果也较多②,笔者曾到边境一线实地调研③,深感清代中尼边境历史文化遗产是国之财富,迄今对于推动中尼关系发展、中国西藏面向南亚“一带一路”战略和我边境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清代以前的中尼边境区域关系
处于与尼接壤的西藏边境七县中,吉隆、聂拉木、普兰等自古是中国西藏对外的重要通道。吉隆县位于西藏日喀则市西南部,总面积9009平方公里。南和西南面与尼泊尔相邻,边境线长162公里。历史上著名的蕃尼古道、尺尊公主入藏、莲花生进藏、清军驱逐廓尔喀侵藏等重要事件,都与吉隆、聂拉木密切相关。而地处喜马拉雅山中段的阿里地区普兰县位于西藏西部,面积13179平方公里[1](P141),南与尼泊尔、印度接壤,边境线长300多公里。境内有著名的神山冈仁波齐、圣湖玛旁雍错,是我国西藏早期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国内外旅游者和朝圣者的圣地。
(一)西藏早期文明与南亚文明交流之地
考古研究已在吉隆[2](P5-6)和普兰[3]等地发掘旧、新石器文化遗址,证明距今数万年前以迄几千年前,此地就有远古人类活动。吉隆和普兰等地,是中华文化起源之一的西藏早期文明与南亚文明交流交汇的重要通道和区域地带。
吉隆文化,从东南向看,它是古代西藏与尼泊尔、印度等南亚进行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通道[2](P11)。从东西向看,它与古象雄文明有着地域和文化上的天然联系,受其辐射和影响。普兰亦处于象雄范围。象雄是西藏早期文明发源地之一,其部落在吐蕃之前已雄踞于西藏高原,极盛时势力曾囊括西藏的西部、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4]。
(二)清以前对中尼边境区域的管理
历史上,不丹、尼泊尔、锡金、拉达克等地区曾长期受西藏文明的影响。吐蕃聂赤赞普时代,随着雅砻、苏毗等部落势力的兴起,象雄的势力范围逐渐退缩(缩至今阿里和克什米尔地区)。吐蕃王朝兴起后,灭象雄(汉籍作“羊同”),归并其入吐蕃。吐蕃王朝崩溃后,象雄之名亦随之消失,西藏西部代之而起的是史籍中常见的“阿里三围”和古格王国。
吐蕃时期,吉隆宗等地属于吐蕃行政区划之一的茹拉西部[5](P4、57-58)。公元11-17世纪,吐蕃王室沃松的后裔④曾在吉隆宗嘎一带,建立“贡塘王朝世系”(),传承约23代[6](P233-234)。沃松之孙吉德尼玛衮(沃松子贝考赞之次子)移居阿里地区建立王权统治,吉德尼玛衮三子分治阿里,故称“阿里三部”或“阿里三围”[7](P16-17,36,41-44)。元代,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管理,元朝在阿里地区设宣慰司进行管理。
二、清代中尼交通与边境区域管辖
清朝政府对中尼边境进行了有效管理。乾隆时期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全面加强了中尼边境的主权管辖。
(一)清代中尼边界区域历史
1、吉隆:清代的中尼通道关口
2、清代西藏聂拉木、樟木等关口地位
1724年(雍正二年),噶举派八世司徒访问尼泊尔时经后藏抵达定日,再由聂拉木、樟木进入尼泊尔。乾隆年间,清朝在聂拉木和定日驻兵,设检查站,凡尼泊尔人带货物到聂拉木都需检查,到定日时须再次检查。美国学者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研究认为:19世纪或许更早,定日即有两条主商道穿过,一条是从尼泊尔中部至西藏腹心地区的道路;另一条是从东到西,穿过西藏通往拉达克的道路[10](P114-115)。
3、清朝管辖边境贸易
乾隆年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后,划定中尼之间的边界,立“鄂博”⑦为标志。同时在普兰、樟木、吉隆、察隅、绒夏(,今定日县境)、日土等中尼边境地区形成了一些较固定的集市点,这些点也是中尼之间传统的通道所在,清朝在定日、聂拉木等地驻兵管理。清代萨嘎宗(今萨嘎县)头人和尼泊尔之间的商贸规模很大,萨嘎宗南部中尼边界处立有“军人鄂博”,有清兵和定日藏兵守卫。普兰瓦力塘集市,则由尼泊尔等各方商人前来集聚贸易,该山口自11世纪成为印度、尼泊尔与西藏的出入境通道和集市。
(二)清代中尼交通及其扩展
清代,从18世纪以来,尼藏商贸交通主要有:一是从加德满都河谷五天至西藏边境利斯梯和杜阿尔喀,由此进入前藏;二是从加德满都八天至藏尼边境的赖苏瓦(吉隆),这是传统线;三是从加德满都行二十余天到奇纳金,再进入西藏西北部。据《尼泊尔地理》记载,尼泊尔通往西藏的山口有二十个之多,为喜马拉雅山天然山口,形成各种界标和羊肠通道[11](P9-10)。
乾隆年间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乾隆帝派遣福康安大将军率师进藏驱逐廓尔喀。福康安、惠龄、海兰察率清军主力由吉隆一线征剿,深入尼境达七八百里,逼近加德满都;同时成德、岱森保所率另部清军,自聂拉木南下攻取了扎木(今樟木)、铁索桥等地,亦深入尼泊尔境内。致使廓人畏惧,不得不遣人求和。清军深入尼泊尔境内,扩展了中尼交通。福康安从尼泊尔撤兵同时,派穆克登阿勘定了边界,设立了鄂博。西边以“济咙外之热索桥”、东边以“聂拉木外扎木地方之铁锁桥”为界。清军深入尼境致使中尼交通更为扩展[12](P121-129)。
三、清代中尼边境争端解决及其影响
清代,廓尔喀统治者推行领土扩张政策,以贸易纠纷等为借口,先后于1788年和1791年对西藏发动侵略战争,但最终被清军驱逐出境,保卫了边疆,巩固了国防和领土完整。
(一)乾隆年间廓藏战争后的边界形势
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廓藏战争结束,福康安撤兵后查明藏内边界,一一设立鄂博,划定边界。驻藏大臣按四季二人轮流亲往济咙(吉隆)、聂拉木、宗喀等边地稽查⑧。次年,清廷批准了这次划界。廓尔喀表示将“永远遵奉”。同时中国西藏与相邻的锡金(哲孟雄)、不丹(布鲁克巴)自古友好,三方之间的边界长期保持着历史的传统习惯线。1794年,驻藏大臣和琳率游击张志林、噶伦丹津那木吉等,“携带噶厦底册”“率同该处营官”,履勘边地,设立边界鄂博,再次明确标定了西藏与哲孟雄等的边界[13]。如此,西藏的边界西段与廓尔喀相接要隘,福康安已予勘定,西段与廓尔喀、作木朗、洛敏汤(Lamjung)[14](P56-58,161-169)、东段与哲孟雄(锡金)、布噜克巴(不丹)各交界处,亦经和琳、张志林重立界石标志划清[15](P678-684)。同时《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尼泊尔“商人每年准其来藏三次”,事先须“报请驻藏大臣衙门发给印照”,各地官员需“查验印照”。
(二)咸丰年间廓藏战争后边界争端的解决
中尼战争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将侵略魔爪伸向了尼泊尔。1816年英国强迫尼泊尔签订了《塞哥里条约》(The Treaty of Sagauli)。1855年廓尔喀在英国唆使下再次对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西藏地方政府派藏军进行反击。1856年初廓尔喀提出和谈要求,驻藏大臣赫特贺派遣藏军首领与廓军会商,最终双方官员签订了和约(条约十款)。根据条约,廓尔喀退回所占西藏领土,西藏须“年付廓尔喀赎金一万卢比”,规定西藏对尼泊尔商人免税等。通过不平等条约,尼泊尔取得在西藏的治外法权和特殊免税权等各种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该条约在西藏执行近百年(1856-1956),直到中、尼两国于1956年签订新的条约后才被废除⑨。
四、清代中尼边境传统贸易发展
(一)清代中尼贸易传统
清代,中尼边境民间贸易和集市活动很活跃。普兰县西南邻近印度,东南连接尼泊尔,通外山口有7个,其中2个通印度,5个通尼泊尔[16](P204),主要包括丁喀拉()、斜瓦尔()、强拉山口等。17世纪初,普兰边境的主要山口、通道已设有固定的边贸交易点。定日和聂拉木,也有边贸集市。“定日的绒巴和大多数西藏农民一样,……每年到聂拉木两次,赶往尼泊尔直接参加那里的贸易活动。”[10](P117)
(二)清代中尼贸易关系的发展
清初以来,中尼传统贸易持续开展。西藏输往尼泊尔的商品种类很多,并有来自内地的丝绸和茶叶等大宗。尼泊尔输往西藏的商品,以尼泊尔铸造的银币为大宗,其余为大米、铁、铜及染料。克什米尔商人亦在西宁、拉萨、加德满都和巴特那(恒河中游)设有商站。《卫藏通志·贸易》卷十一载尼商在藏有40名、商头3名。同时,在普兰边境,西藏牧民与西邻拉达克人及南邻库马翁人交换日用品。在亚东和帕里,锡金、不丹的商人及边民与西藏商人进行交换。在聂拉木和吉隆两处西藏与尼泊尔之间边境地带设有交易点。1792年福康安曾上奏:西藏“一切日用所需,如布匹、米石、铜铁、纸张、药材、海螺、果品、蔗糖,及藏番戴用之珊瑚、蜜蜡、珠子等物,皆系自阳布(按:加德满都)等处贩运而来。”[17]
中尼战争结束后,福康安等上奏“酌定藏内鼓铸银钱章程”,得到恩准施行。清朝规定禁止廓尔喀银钱在西藏流通,西藏地方政府依照章程先后铸造了“乾隆宝藏”“嘉庆宝藏”“道光宝藏”等,由此改变了以往市场交易的混乱局面,促进了西藏商业贸易的繁荣[18]。聂拉木、济咙(吉隆)和绒峡(今定日县境)成为双方边贸的要点,西藏在此三处设置营官管理。在普兰、樟木、吉隆、察隅、绒夏、日土等边境口岸,双方贸易规模逐渐扩大[19](P248-249)。
(三)英国侵略损害尼中贸易关系
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1893年12月5日签订《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和1904年签订《拉萨条约》,获得在西藏贸易的许多特权。英国为了控制经尼泊尔对西藏的贸易权,另辟通过大吉岭的噶伦堡、从春丕谷到帕里和江孜、从喜马拉雅中部山脉的分支直通藏布河谷等新路线,由此夺走了通过聂拉木、吉隆的贸易。这些行径,严重损害和破坏了中尼之间传统的贸易关系。
五、清代中尼边境的文化及其交流
清代,中尼文化交往密切,留下了许多文化符号和历史遗迹。
(一)边境区域交往密切
尼泊尔境内的佛教圣地,是西藏噶举派高僧、民间朝圣和佛学交流之地,其境内有西藏人居住,他们或是噶举派高僧朝圣时的房东⑥。六世班禅撰写《香巴拉指南》(),书中描述了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古代天竺()的地理、城市和圣境。中尼边境分布着诸多文化遗迹、圣地、神山、神湖,两国信徒具有共同朝拜冈底斯山(冈仁波齐)与玛旁雍错的习俗。清初以来,西藏定日人渐移尼泊尔居住。定日人分散在尼泊尔的索卢、昆布及聂拉木以南许多不同的村落。他们的移居往往受婚姻推动,定日人(几乎均迁自岗嘎)都和尼泊尔人,通常是夏尔巴人结了婚。夏尔巴人的历史表明,他们是通过吸收一批又一批西藏移民而不断发展壮大的。这种情况,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10](P43)。
(二)吉隆县边境区域重要的文化遗迹
中尼边境吉隆县保存有一大批古代寺庙或文化遗址,它们是中尼友好交往的见证,史料和历史价值很高[2](P45-46)。举例有:强准祖布拉康(),为文成公主入藏后,按照“五行算图”修建镇边及重镇神庙之一。吉隆镇帕巴祖布拉康,为楼阁式木塔尼泊尔风格建筑,据传为松赞干布依据尺尊公主的建议所建。宗嘎卓玛拉康,约建于1274年。摩崖题铭《大唐天竺使出铭》,系唐显庆三年(658)所刻,记述了唐使王玄策出使天竺(今印度)途经吉隆的历史。摩崖题铭《招提壁垒》,系清代对石刻所在山峰之称,乾隆年间,为清军反击廓尔喀军时的进军要道。冲堆集市遗址,位于吉隆镇至县城宗嘎公路之右侧,该集市自18至19世纪设立以来,一直是中尼边民互市场所之一[2](P149)。
(三)普兰县边境重要的文化遗迹
普兰边境地区的文化遗址也丰富。主要如:香柏林寺遗址,位于今普兰县国际贸易市场附近的山腰部。遗址约始建于12世纪后半叶,由萨迦派寺庙群和格鲁派寺庙组成,格鲁派寺院为17世纪末统帅甘丹才旺在与拉达克的战争结束后为阵亡将士祈福纪念所建[16](P540)。遗址东部为萨迦派小寺庙废墟[20](P116-119)。贡不日寺,位于县城边马甲藏布河北岸,属直贡噶举派寺庙建筑。相传为藏戏《洛桑王子》中的洛桑王子宫殿所在。科迦寺,位于普兰县科迦村,建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据说为大译师仁钦桑布主持修建[7](P56)。亦为尼泊尔信徒朝拜之地。
(四)清代中尼贸易文化交流
清军驱逐廓尔喀战争期间,尼泊尔音乐和舞蹈传入中国[21](P780)。清代,大批尼泊尔人在西藏定居,多达千人。《东华录》卷一一六(乾隆朝)载:“巴勒布……自康熙年间即在前藏居住……不下数千口……而藏内番民与之婚姻已久。”尼泊尔人侨寓拉萨,并“在孜塘、日喀则、江孜、拉孜,以及工布各地亦有尼泊尔人之足迹”“专业金银铜锡玉石及妇女首饰”[22](P49)。17世纪中叶,西藏从尼泊尔邀请了一大批铸造金、银、铜、铁的工匠来铸造佛像和参与布达拉宫的修建。
尼泊尔是清朝的藩属国,该国遣使来藏,经驻藏大臣等奏,“请赴京进贡谢恩”[23](P38)。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敕谕颇罗鼐选派尼泊尔工匠进京,颇罗鼐奉旨从西藏招募尼泊尔工匠赴京宫廷内务府造办处,参与制作宫廷佛造像。17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纸张经西藏传入尼泊尔,荔枝、马铃薯、花生、金鱼等也逐渐传入尼泊尔[24](P435)。
六、结论和强边思考
上述史实可知,中尼边境除在有限的历史时期发生过冲突之外,大部分历史阶段双方保持着密切友好关系。中尼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历史基础,正因如此,新中国建立后尼泊尔始终坚持对华友好政策。1974年尼泊尔调动皇家军队消灭了盘踞在木斯塘地区的西藏叛匪,恢复了尼中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尼泊尔政局出现剧变时,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尼方仍坚持了以中尼友好大局为重的立场[25](P37、56)。借鉴历史,我们认为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鉴于中尼之间历史和现状之基础,应进一步加强中尼历史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更加巩固中尼边境安全和稳定。同时加强系统收集整理有关汉、藏、外文等史料,弄清楚边境地区印证我主权管辖的古文物、古遗址等史实,加强构成为我主权证据链的重要文物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做好资料和数据储备,为国家涉外交涉和舆论斗争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将中尼边境区域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南亚大通道的重要支点和友好纽带。习近平主席于2019年10月12日至13日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构建中尼发展与繁荣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将造福两国人民,有利于中尼边境和平与安宁。我们须进一步做好对尼泊尔的援建和互联互通等工程。
第三,中尼文化交流具有历史和现实基础,我们须利用历史、文化、情感等各方面的条件,继续加强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我们应加大对尼泊尔的外宣、访学、学术交流和统战工作。在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借助印度和利用“达赖集团”遏制中国的斗争中,形成一定的国际统一战线意义重要。
第四,推动边境基础设施和生态小康村建设,特别是推进“抵边搬迁”战略工程,努力将我西藏4000公里边境线上的600多个村,打造成为守边固边兴边强边的一个个堡垒,使我西南边疆坚如磐石、牢不可破。
第五,夯实涉藏总体国家安全的国土安全底线基础,针对反分裂斗争形势和任务,汲取历史上屡遭外敌入侵教训,加强边防边境一线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国民国土安全教育动员,做好维护国土安全军事斗争。
总之,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和幸福家园的建设者”的指示,不断增强国防教育,运用边民在边境活动的便利条件,参与边境安全建设,形成军地警民共建边境安全和深度融合的守护国防体系。
[注 释]
①《清史稿》《清实录》等官方文献;清代西藏地方档案;噶伦传(如《颇罗鼐传》)、摄政传等地方官员传;历辈达赖传(五世至十三世达赖)、历辈班禅传(四世至九世)、噶举派高僧传(噶玛噶举黑帽系、红帽系、司徒活佛)等教派人物传等官方和民间史料都涉及尼泊尔记载。
②有关成果,早见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方杂志》等刊发文章,例如,《清代西藏与尼泊尔通商概况》朱祖明,《经济汇报》11卷4期,1945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文章见于《人民日报》《西藏日报》《现代佛学》《新华半月刊》等报纸刊物。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成果渐多,例如,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相关问题研究》(日《东方学报》第66册,1994年);骆威《清代抗击廓尔喀侵藏战争背景及意义新探》,《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王海燕《清代在西藏流通剪碎的尼泊尔银币》,《文物》1985年第11期。2000年以来,成果面更广,其中廓尔喀战争是一个热点。例如,孙修身《唐初中尼交通四题》(《中国藏学》2000年第4期)等;冯智《清朝遣藏最高将领福康安治藏建树》,《西藏研究》2005年增刊;田小兰、陈祖军等:《西藏定日县绒辖界碑藏、汉文碑刻简释》,《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藏尼边界纠纷与咸丰朝的廓尔喀之役》,朱昭华、顾梦晓,《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等等。有许多研究西藏历史的著述涉及此领域,其中《西藏通史·清代卷》(邓锐龄、冯智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版)对清代中尼关系的各个方面作了梳理。近年来,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有关成果探讨了中尼关系历史走向,例如,《“一带一路”视域下西藏边境地带安全稳定问题探索》,狄方耀、贾翠霞,《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等等。此外,国外学者有关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文化领域的成果持续被翻译并在国内许多刊物发表。
③笔者在2004年至2013年主持《西藏通史·清代卷》(上)课题期间,曾先后到普兰、定日、樟木、吉隆等边境区域调研;2019年3月又曾到帕里、亚东边境一线调研。
⑤公元7世纪初,尼泊尔尺尊公主由此道进藏。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唐使王玄策由此道出使天竺,吉隆《大唐天竺使出铭》便是其所遗实证。
⑧《钦定廓尔喀纪略》(卷40),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二十七日“谕军机大臣传知福康安等所指各条著详酌妥办”。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3)[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763页。
⑨见1956年9月20日中尼双方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