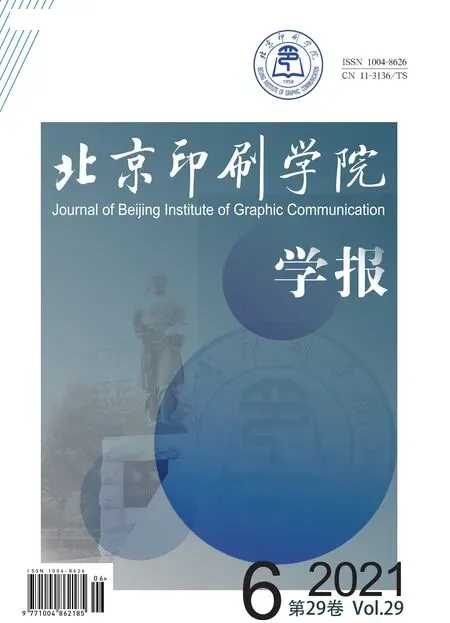接受美学视域下苏词读者接受的三种境界
2021-12-03胡婕
胡 婕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 102600)
苏词的接受史研究者众多,往往提到诸多作家、风格、名篇,将接受具象化成一种创作的延续,但却很少提及接受本身的一种状态。而在接受美学的概念中,接受的本质是作者与读者互动,作品作为桥梁连接了两位主体,相应的,我们在阐释接受情况时就要包含理解与创作两方面。即使中国文学的接受特色主要集中在创造方面,我们依然不能忽视理解的存在,因此在以下的论述中,笔者将在接受美学的视域下注重两个主体、两个方面,探讨苏词接受的三种状态。
一、独到的见解者
韩愈《马说》里开篇第一句话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如同千里马一样的人才,想要能在自己擅长的地方一展抱负,就需要能发现人才的“伯乐”。而在文学领域,一个人的文学作品要想能够被传为经典,除了本身所具备的才华,一位独具慧眼的读者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这点在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中也有提及,“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异采”即作品别具一格的地方,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和风采,而“见异”就是“知音”看见了独属于作品的“异彩”。
那我们在这里会不禁提出一个疑问,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知音”呢?而“知音”在见异时又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以及“见异”本身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改变呢?在这里我们不可避免的要先理解接受美学中的一个概念,那就是读者的期待视野,接受美学的缔造者之一姚斯认为“期待视野就是‘阅读一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现在结构’,‘是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这种期待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界域,此界域圈定了理解之可能的限度。’”
那么根据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在苏词接受里将期待视野界定为对词体这一文体的定向性期待,“词为小道”,一直是北宋主流文体概念,而婉约则一直是词坛的主流风格,因此苏轼以诗为词的写作理念以及清旷豪放的词风在一开始始终不被人看好,即使是作者苏轼自己,也称自己的词是自成一家。但我们要意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往往只有不同中才蕴藏着新的开始,不破不立,如果仍延续着以往的观念和风格,那么也许词体的发展将停滞不前,正是因为“不同”冲击着我们以往的认识,带领我们跨越到新的境界,我们才能认识到词之一体新的美感。这也是接受美学中一直强调的期待视野的改变,对于接受主体(读者)来说,要在作品与原视野的相互作用中改变自己的期待视野,并与作品所代表的作者和传统的视野达到某种程度的“视野融合”这样才能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内蕴,同时文学作品的潜在意义也在读者视野的历史发展中得以连续实现。
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期待视野的改变,首先必须要有眼光独到的“知音”的存在,他们因为“见异”而使得作品与本人之间产生了相互作用,为了真正理解文学作品的内蕴,使代表传统视野的自己通过作品与作者的视野达成了视野的融合。在苏词接受的最初期,我们必须要提到的两个人物,一位是晁补之,一位是黄庭坚。前者,有学界定论:“无咎步武苏轼,开拓词境,以词言志遣怀……在当时词坛上无论笔力、气象都接近于苏”;后者,则是从苏轼交游后词风大变,时有豪迈之气。
《八声甘州·扬州次韵和东坡钱塘作》
宋代:晁补之
谓东坡、未老赋归来。天未遣公归。向西湖两处,秋波一种,飞霭澄辉。又拥竹西歌吹。僧老木兰非。一笑千秋事,浮世危机。
应倚平山栏槛,是醉翁饮处,江雨霏霏。送孤鸿相接,今古眼中稀。念平生、相从江海,任飘蓬、不遣此心违。登临事、更何须惜,吹帽淋衣。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宋代:苏轼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它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晁补之的《八声甘州·扬州次韵和东坡钱塘作》,就是苏轼《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的和作,从意象的使用,到意境的开阔,两首《八声甘州》,不能说不相近,其中晁补之的和作化用苏轼诗句之处不再一一细说。但细论起来,论西湖景色,晁补之写的温婉清丽,苏轼写的荡气回肠;论写时心境,晁补之夹带着对前辈的敬仰,苏
轼则尽抒对好友的怀念;唯独一句“念平生、相从江海,任飘蓬、不遣此心违”,让人不禁在想,晁补之是写苏轼还是在写自己呢?言志遣怀处,才是晁补之创作中与苏轼最相像的地方,主体情性的表达方式,所抒发之心情,以至于心胸抱负,无咎作为独到的见解者,是因为再了解不过苏轼其人,才理解了作品的精妙之处,并模仿创作出自己的作品。中国文学中能“见异”的知音,往往亦是知己,“知人论世”是中国文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这里也是期待视野改变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黄庭坚的《念奴娇·断虹霁雨》,在他自己看来,是“或以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云”(《念奴娇·小序》)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苏轼的词风是极为欣赏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能感觉出他对自己的创作也是满意的。我们说两首作品的相像之处,从词作的具体内容来看,两首词作完全不同,黄庭坚写当下游园聚会之乐,而苏轼则是抒怀古之情,但若从壮阔形象中见傲岸不羁之气这一词风角度来说,两者之间竟突破了内容的限制达到了意境神似的状态。然而,若提及鲁直之前的作品,学界评价则是“未识东坡前,好做艳词,常有游戏笔墨,理俗不减柳永”。从艳词到傲岸的改变,除了与苏轼交游之外,未必没有对其词风之美的独特爱好。黄庭坚曾多次表达对苏轼作品风格的激赏,“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黄庭坚《跋子瞻醉翁操》,《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6)此外,从他对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词的评语:“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殊能至此?”鲁直本身性格耿直,《宋史·黄庭坚传》云:“凡有问,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足可见其性情,因此好做艳词,很有可能只是一直视词为小道,但经苏轼词作所启发,转变了对词体的观念。不过这些归根结底,是鲁直对词作亦能语意高妙、笔下无尘的欣赏与惊叹,有时作品带来的感动,仅仅只是因为作品恰好契合了读者的性格境遇与审美,但却使得读者从原来的视野走进了作者的视野,从此打开了新的创作大门。读者独特的审美爱好,便是期待视野改变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审美偏好的形成原因各种各样,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做详细的论述了。
让我们把眼光拉回笔者在一开始提出的三个问题,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知音”呢?而“知音”在见异时又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以及“见异”本身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改变呢?通过分析晁补之与黄庭坚两位接受者,我们可以发现,要想成为“知音”的人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足够了解作者的性情为人,遵循“知人论世”的作品接受理论,而另一个则是对作品本身充满喜爱欣赏之情,理解并接受作品与主流的不同之处。因此我们可以鲜明地发现,知音若想见异,需得有强烈的主观意愿,无论是对作者的爱屋及乌,还是对作品有独特的审美偏好,都是主观性非常强烈的行为,而正是强烈的主观意愿才使得本身不被主流观点所认同的作品有了生存的机会,也为日后随着时间改变的视野留下发现作品的机遇。最后,所谓“见异”,就是读者从审美脱离到统一的过程,既是见异也是见异彩,不仅是看到作品中独特的地方,也是认同了这些不同的地方有其精彩之处。正是这些见解独到的读者们强烈主观意愿的支持,后来的继承者们才有机会继续了解作品,发掘作品的价值与意义。
二、作者的隐形期待与读者的前理解
在这里作者的隐形期待,指的其实是接受美学中作品的“不定点”,也就是作品所故意留下的空白之处,这些空白之处在自发地召唤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它,在接受美学中这种空白与空缺又被称为召唤结构。
这里的“空白”与“空缺”事实上非常接近我们古代文论中所说的“意境论”,唐代司空图认为诗歌的意境多层次的,提倡虚实相生、含蓄无穷的意境之美。诗家描写景物不宜每言皆实,而要留下一定的艺术空白,为读者阅读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这样才能使作品余蕴深长、韵味无穷。而如果要把握好这种艺术空白,必须要意识到“兴趣”与“诗境”的关系,“兴趣”就是诗人情感自然而然地抒发所产生的审美趣味。“兴趣”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首先,它强调情感的自然抒发,词理意兴的高度融合,以形成浑然无迹的情境或意境。其次,它注重诗的含蓄、蕴藉和朦胧之美,要求诗歌中的境象应像镜花水月一样,既空灵虚幻,又富含无穷的情致韵味。把握好“兴趣”,自然能创造出浑然无迹,朦胧含蓄,空灵虚幻的诗境,也就有了富含无穷情致韵味的空白。
因此诗词作者天然懂得,他们只有通过激活读者的想象,才有可能使读者卷入,并从而实现他本文的种种意象。因此作者写就作品时天然就带有一种强烈的引导意味,但这种引导又因为出自于一种无意识的审美情感抒发,从而浑然天成不露痕迹。
以前文提到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山河壮阔,人物风华,都在这十三个字中。苏轼并未详写这赤壁一草一木,却抓住了赤壁的豪迈之气,并未细述这历史长河中无数英雄面目,却写尽了他们的心胸气概。苏轼在写过往的风华人物,在写自己,亦在写未来的英雄,无数读者卷入他所构造的有关赤壁的时空中,体会他的感动,也是体会自己的感动。
我们前文提到过,接受的本质是作者与读者的双向互动,既然作者在作品中对于读者有强烈的引导意味,那么读者在这种互动中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就成为了值得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前理解”的概念在这里非常重要,“前理解”在这里理解为“读者对每部作品的独特意向”,与我们前文提到的期待视野有相似之处,但是要更加具体,“前理解”将期待视野分割成了更为细致的一个个部分,重点不在于一种总的观念,而是具象化到一类群体或因为特定的社会环境变化而形成的某一种趋势。
而读者不是被动接受文学作品的形象和意义,是根据自己的前理解来选择和取舍形象和意义,从而参与了对作品的形象和意义的创造。读者的这种参与创造活动反映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就是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形象和意义,决定了作品的历史地位、意义和价值。
在这里以南渡词人为例,南渡是宋朝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国家不幸诗家幸”,在国家动荡的时刻,涌现出了一批深受苏词影响的作者们。南渡词人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苏轼的词法、词风,并因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文化气质、艺术趣味、身世遭遇而选择接受苏词中适合自己的因子。按照其接受侧重点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三派:豪壮慷慨派、清超旷达派、清旷颓放派。
豪壮慷慨一派以李纲、李光、赵鼎、胡锉、张元干、张孝祥为代表。他们多半投身疆场或政坛,以自己的文韬武略主持国政和保卫国土;其并非专力写词,而是“业余选手”,在从军、从政之余以词为“陶写之具”,纵意抒情言志。故他们学习苏轼,并非“专意而为之”,而是因言志抒情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接续着东坡“以诗为词”、“豪雄奔放”的词风。清超旷达派因为现实政治的黑暗,抗金事业前途暗淡而易生消极情绪;加之此派文人学士居多,气格较弱。偏取苏轼思想中超然物外、心平气和、随缘自适的一面,作词则力追苏词清旷超逸、通脱自然的主导风格,并将之发展成为南渡时期的一种基本风格。清旷颓放的一派以朱敦儒为代表。他的早期创作就已摆脱北宋晚期“浅斟低唱”风气的影响与束缚,而走上了“以诗为词”的路子。南渡初期,词风大变,一改轻狂之气,而为悲慨苍凉。但政治形势的恶化和“中兴”大业的渺茫,使其词中又开始充溢着清超放旷之情、避世出世之调。朱教儒学习苏词中旷达的一面,但是时代却使他比苏轼走得更远,甚至是消极之路——颓放、寂灭。
三种流派接受情况的描述,展示了接受互动同时包括作者的隐形期待与读者的前理解两个部分,从而强调了文学作品接受的客观性。接受不仅仅需要强烈的主观意愿,作者的隐形期待限制了读者理解的偏差甚至过度解读,而读者的前理解,同样影响了作品在流传与继承中的形象与价值。
三、重构的继承
接受美学的研究者伊赛尔认为,作品和读者的活动不是一个读者单向性的填充文本运动,而是一个双向的交流活动,文本在不断地召唤读者对其加以填充,在此过程中,读者必须充分地展开自己的想象力,让自己的前理解与作品中所包含的内在特征发生持续的相互作用,因此对任何空白的填补都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填补也意味着这样一个接受的过程,那就是从历史到自我,再从自我到历史的这样一个延伸和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因作品和作者而受到启发与感动,同时又将自我的感动融入意境世界中,使得作品与自我的历史不断延绵,这也是中国诗词生生不息的原因。又因为中国文学的接受表现主要集中在创作中,于是这种填补的过程,是继承,更是创造。
(一)内容与形式的继承与创造
提到苏词的接受研究,有两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不能不提及,那就是贺铸与秦观。在自身前理解与苏词作品内在特征的互动中,前者在内容的填补上更加主动,自发地学习苏词用典、寄托等表现手法,融会慷慨激昂之情,呈现出气贯长虹之势,开南宋爱国词的先声;而后者则在形式的填补上有自身独到之处,常常直接运用抒情手段抒写人生的种种体验,“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
在这里要着重解释的是我们在这里提到的空白的填补,不再单指对某一首具体的词作品的填补,而是对苏词整体内容与形式的一种填补,既有对新内容的继承,也有对新形式的运用。下面以贺铸和秦观的作品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六州歌头·少年侠气》
宋代:贺铸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闲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
似黄粱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蓬。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张殿方的《苏词接受史》中说道,贺词学苏最为成功之作是其“大声糙裕”的雄越之歌。这首《六州歌头·少年侠气》,描绘了一位思欲报国而请缨无路的“奇男子”形象,一句“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所用皆为战意极盛的意象,将苏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气运用得淋漓尽致。贺铸接受的不仅仅是苏轼的某一篇豪放派词作,而是继承了苏轼雄越的词风,发掘填补了豪放词作内容的空白。同时,贺铸上承苏轼“以诗为词”的词风,在拓宽词境、提升词格、将体格卑下的应歌之词雅化为文人士大夫之词等方面,开拓出一条有法度技巧可循的词之雅化之路,使苏轼“不可学”的超旷词风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雅化路径。
秦观的《鹊桥仙》延续了晚唐五代词的柔婉,看似与苏轼清旷豪放的词风毫无关联,但实际上秦观对于苏轼的学习是潜性的、有选择的,深度的;重在学其“雅”,词格较高。秦观虽没有继承苏轼豪放式的“新内容”,却以自身的独特的前理解将新形式融入婉约词中,开拓了新的词境。世所公认,秦观在词创作上“独辟蹊径,卓然名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其在男女恋情题材之外,颇多抒写身世感慨和复杂体验之作,突出词的抒情个性,显然是受到苏词重在抒发个人志意的影响。一方面,他直接运用这种抒情手段抒写人生的种种体验,现实生活被他推到前台。另一方面,“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周济《宋四家词选》)在伤情别怨中写尽人生失意之悲慨,一唱三叹,寄托摇深。提炼感情不再泛化,即使一些专咏爱情之作也映射出丰富寓意,正如《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对人生有一种广泛的启发作用。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亦是能轻易唤起读者心中万般感伤,极为动人。
(二)精神的重构
如果说“新内容”与“新形式”是在填补的同时创造独属于自己的风格,那么辛弃疾对苏词的继承就是,站在了与苏轼同等的高度,不再是填补,而是集大成与革新。集前人之力,完成了由苏轼所开启的变伶工之词为士人之词的革新之路,他不仅仅是将苏词的内容与形式化为己用,更是准确把握了苏词的精神,即“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的境界与气魄。使词真正达到与诗文相提并论、成为抒情言志之体的目的。
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曲短词,写尽了诗人忧国家山河之愁绪,欲报国无门之憾恨。事,景,人,情融为一体,仿佛读者能通过这首词作看见亭台上一抹孤寂的背影,体会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可奈何。同时这首《水龙吟》也是最能体现,辛弃疾对苏轼创作理念的继承与创造的,事情的铺陈,景色的烘托,情感的抒发,意志的体现都恰到好处,读一篇词所带来的审美感动并不亚于读一首诗,读一篇文章所感受到的。这种创造性重构的根本原因在于辛弃疾作为读者对作者创作最终目的的深刻理解,他所接受的不仅仅是审美感动,还有感动中所蕴含的人格精神的共鸣,精神的对话使得这种理解超越了内容与形式的表征,达到了创作的终极。
四、结语
笔者将接受的状态分为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个部分强调接受过程中读者作为主体,他的强烈主观意愿对于作品的接受与传播的影响,第二个部分则注重作品解读的客观限制与读者本身的阅读“偏见”对于作品的接受与传播的影响,而在第三部分则是着重讨论了在中国以创作为主要接受方式的特色情况下,阅读与创作的两种互动状态。同时,对于接受美学中“期待视野”“前理解”“隐形期待”“双向性互动”,笔者结合中国文论与诗词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诗词范围内的理论阐释。笔者尝试从微观角度,以具体的例子研究文学接受的具体情况,并且试图寻找古代文论与接受美学理论的契合点,为接受美学中国化做出新的尝试,虽然讨论仍不够细致,但如果能抛砖引玉,便觉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