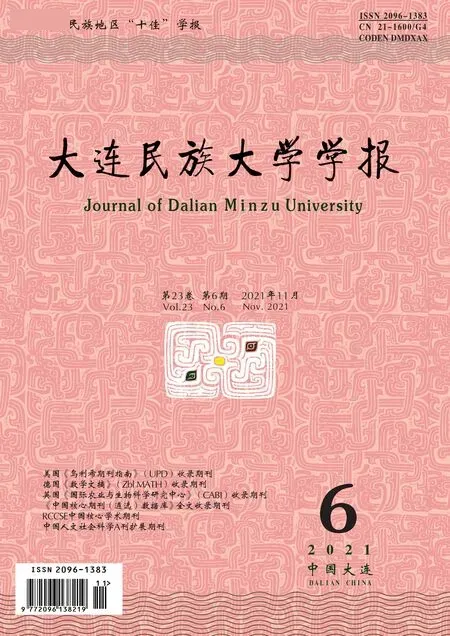符号与象征:庄河正月十五“点属”的仪式解读
2021-12-03张仕洋
张仕洋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正月十五虽是全国共度的传统节日,但不同地区有颇为不同的民俗表现。在辽东半岛东侧南部的庄河,正月十五前后会举行一种名为“点属”的特殊仪式。据传该仪式源于胶东地区,由闯关东移民带入辽东。然而,时过境迁,今日的“点属”仪式已不见于庄河以外的辽东其他地区,事实上已完全成为独具庄河特色的正月十五民俗仪式。本文以笔者对属相灯仪式的亲身经历和观察为基本材料,在符号人类学视角下,试图对该仪式中所使用的符号和象征性行为进行解读。
一、“点属”与人类学仪式研究
所谓“点属”其实是“点燃属相灯”的简称。庄河属相灯本质上是一种面塑形式。其以面为材,塑成主要以各属相为主的不同动物形态,旁边另置小烛碗,上插蜡烛。正月十五前后的晚上点燃蜡烛,即为“点属”。《庄河县志》载:农历正月十五……用豆面或其他泥类制作全家人口属象(应为“相”)和十二月灯,上置灯芯或小蜡烛,于是日晚点燃,谓之“点属”[1]223。
从风俗史的角度观察,点蜡烛一直是中国正月十五的固有仪式,被称为“燃灯”。有说法认为十五燃灯起源于汉武帝正月十五对太一神的祭祀[2]75。但此说法并无直接证据。有学者通过对隋唐类书的梳理得出结论,认为十五燃灯的习俗更多地受到佛教正月十五“观佛舍利”的影响。这一佛教仪式在初唐借由佛教经典的传播和《大唐西域记》的成书而广为流传,并在唐玄宗时完成制度化,其后留存至今。而后世将燃灯习俗追溯至汉武帝祀太一更多的是为了赋予这一习俗悠久的历史[3]。
虽名为“燃灯”,但去除各式外壳,古时的“灯”本质上只是一支蜡烛。庄河的属相灯亦是如此。各种属相形态的面塑实际上等同于属相灯的灯壳,不过蜡烛光源不置于壳内,而暴露其外。因此庄河“点属”可视为全国普遍举行的十五燃灯在地方上的特色表达。
“点属”一类的民俗并非天然被人类学承认为仪式,其可以被仪式化解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学仪式研究的理论流转(1)关于人类学仪式研究的全面分析梳理,可参见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有学者将人类学的仪式研究归纳为两条路径:一是对古典神话和仪式的诠释,二是对仪式的宗教渊源和社会行为的探讨。在两条路径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神话—仪式学派、心理分析学派、结构—功能主义、比较宗教学派、象征学派、实践表演学派等各不相同的研究取向[4]。这些仪式研究学派的理论分野如此之大,以至于埃德蒙·R.利奇认为在对仪式的理解上,人类学家会呈现最显著的差别[5]。
虽然无法得出一个关于仪式的通用定义,但人类学家可以达成一个共识:仪式的定义在不断扩大。以泰勒、弗雷泽为代表的早期仪式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领域,认为仪式就是某种信仰的表达。这种相对狭隘的仪式观在涂尔干那里得到些许放松。涂尔干认为宗教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信仰与仪式。仪式被扩大为“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但这种行为仍要与神圣性相连,“如果仪式不具有一定程度的神圣性,它就不可能存在”[6]。极受涂尔干影响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基本沿袭了他的仪式观点。而待符号人类学兴起后,仪式的神圣性也被逐渐剥离。埃德蒙·R.利奇认为仪式就是属于同一种文化的特殊成员的间或行为,只不过这种行为不能是单纯的“理性—技术”行为[7]。维克多·特纳的定义则更清晰:仪式是指“不运用技术程序,而求助于对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的信仰的场合时的规定性正式行为”[8]23。正是得益于上述仪式定义的扩大,类似于庄河“点属”一类既非宗教亦非神圣的民俗行为才可以被纳入人类学仪式的视角下分析和观察。
关于符号人类学凯瑟琳·贝尔曾精辟地总结道:这一派别的人类学家将符号解释得对仪式如此重要,并非是依据符号与社会组织结构的联系,而是更多地依据符号与一个语言般独立系统的联系。他们的解释并非聚焦于符号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而是聚焦于不同符号在这个系统语境下的含义[9]。换言之,符号人类学将仪式行为视为一种符号体系,即由不同层级的符号联合表达的某种意义系统。而人类学家的工作就是通过观察、询问和分析,探明仪式中各种符号的外在形式、层级归属及象征意义,为外界解读这些符号是如何驱动了整个仪式,又通过仪式表达出怎样的意义。以上种种亦是本文力图完成的对庄河“点属”仪式的解读内容。
二、“点属”仪式的过程观察
“点属”仪式本身并不复杂,整个仪式的总体过程可分为四个部分——制作、放置、点燃和预兆观察。
“点属”仪式的核心是各式的属相灯,而传统上属相灯是在仪式举行之前由各家庭手工制作。属相灯的材质略有特殊。主流的北方面塑以小麦面粉与糯米面粉混合为基本材料,但庄河属相灯以大豆面粉,即豆面为主。其一是由于小麦和糯米并非胶东与辽东盛产,反而大豆更为常见。其二则是生活条件所迫,豆面可从磨豆腐剩余的残渣中获得[10],最大程度节省口粮。但豆面黏性较高,制作属相灯时易附着于手指上,无法成型。因此近年粮食充裕后,大多加入玉米面调和。
属相灯虽以属相为名,但所含内容并不只属相一类。需要制作的属相灯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代表家庭成员的属相灯,即制作的属相灯数量和种类必须与家庭成员的位数和属相类别完全相同。其二是代表牲畜的属相灯,即根据各家庭所豢养的家禽家畜种类,每种制作一盏对应的属相灯。其三是水源属相灯。该种属相灯一般放置在水源附近,有鲤鱼灯和蛤蟆灯两种。此外需要另为每盏属相灯制作一个用以摆放蜡烛的小花盏,或者直接在属相灯上挤压出一个凹槽,插上灯芯。如有凹槽则注入蜡油,放置自然风干;如制作花盏则需另备蜡烛待用。由于凹槽不甚美观,当下庄河的属相灯以配备小花盏为主流形制。
属相灯的摆放位置亦有约定俗成。三种属相灯虽需放置于不同位置,但都依据“就近原则”,即与其所代表的事物相近。家庭成员的属相灯一般放置于生活起居处,比如共同放置在客厅或分别放在各自的卧室中。牲畜属相灯与此类似,放置在各种牲畜被圈养的地方,如鸡窝、猪圈、狗舍等等。水源属相灯依水而置。一般来说,鲤鱼灯放在室内厨房的水缸或水槽处,而蛤蟆灯则放于室外的水井处。
属相灯制作完成和放置妥当后,前期准备工作即告完毕,只待时间一到点燃属相灯即可。但点燃步骤的复杂之处在于“点属”仪式举行的时间并不固定。虽然县志只记载了正月十五当日“点属”,但实际情况却更为多样。一般而言,庄河“点属”仪式的发生时间会有四种不同情况:正月十五一晚;正月十四、正月十五两晚;正月十五、正月十六两晚;正月十四、正月十五、正月十六三晚。其中以第一种和第四种情况最为常见。
庄河“点属”时间的多样性实际来自于历史上正月十五燃灯时间的变动不居。燃灯仪式在唐代兴起之时,举行时间就屡经变化。从正月十五一日,变为二月十五一日,又变为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再变为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日[2]40。此后宋代延长为正月十四至十八共五日,明代甚至延长至十日。清代恢复至五日,但时间为正月十三至十七,其中正月十五为“正灯”[11]。由此可见,历史上对于燃灯时间的制度性规定并不固定。因此作为一种民俗行为,其发生时间亦未达成共识。所以,庄河“点属”的时间除了正月十五当晚为必须外,更多取决于各个家庭不同的节庆习惯。
“点属”仪式最后一步是预兆观察。需要观察的预兆有二:其一是生命预兆,其二是方向预兆。所谓“生命预兆”涉及一个代代相传的观念:属相灯蜡烛燃烧时间的长短代表着生命的长度和命运的顺逆。这种预兆的显现要依靠观察代表家庭成员的属相灯。属相灯一次性点燃,在自然状态下观察蜡烛燃烧时长。观察过程中不能施加人为干预,被风吹灭不能重新燃灯,蜡烛燃尽不能替换蜡烛。蜡烛燃烧时间越长的属相灯则代表该家庭成员的寿命越长。
方向预兆则依赖于对水源属相灯中鲤鱼灯的观察。先将鲤鱼灯置于一个可浮于水面的漂浮物之上,比如水瓢、水舀或小木板。在水缸或水槽内蓄水,将漂浮物浮于水面,以人力转动漂浮物,待漂浮物停止转动时,鱼头所指方向即是新一年中的吉利方向。
从上述对“点属”仪式四个部分的描述中可以发现,预兆观察最是其中最核心的步骤。从属相灯的制作、放置到点燃,最终都是为了确保预兆的顺利显现和准确观察。而两种预兆,即“生命预兆”与“方向预兆”中都暗含了占卜的含义。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这种占卜性来源于人们的知识无法完全控制变化、无法消灭偶然事故、无法预料突发情况,所以人们需要举行某种“更富有实践性、更有确定性、更有局限性”的特殊仪式活动来弥补知识的不足。这种特殊仪式被马林诺夫斯基称为“巫术”[12]。因此,民众举行“点属”仪式是希望从中获得些许来自于超自然力量的指示或安慰,本质上表达了民众在面对生活中诸多力不从心之处时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虽然“点属”仪式有着占卜性的核心,但整个仪式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宗教或神秘色彩,亦没有特别严苛的禁忌和行为规范。整个仪式完全可以由各个家庭独立完成。但仔细分析,仪式的每个环节中都包含了大量的符号和象征性行为。正是这些符号与象征才建构起整个仪式过程。
三、“点属”仪式的象征解读
对仪式中符号与象征的解读可以来自三个方面:仪式的外在形式与特点、普通人的解释和需被挖掘意义的语境[8]。前一节的过程观察正是在完成前两个方面的工作——描述仪式最直接的外在表达、陈述普通人对仪式行为的解释。而此节意在完成解读的第三部分——语境挖掘。在“点属”仪式的语境中,每一个环节都创设和应用了大量隐藏的符号,只有对这些符号做出正确解读,才能理解整个仪式的语境。
“符号”这一术语来自于语言学先驱索绪尔。索绪尔将声音形象称为“能指”,将声音形象所传递的概念称为“所指”,能指与所指共同构成了一个符号[13]。后来这一观点逐渐扩大范围,将声音形象扩展至任何一种表达方式。表达方式与概念的结合是为符号。
属相灯的制作材质即为一个先决符号。如前提及,属相灯以豆面为主要材料,现今多以玉米面混合。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晚近的属相灯出现了更多样的材质,比如石膏制、玻璃制和金属制等等。但非豆面制作的属相灯始终没有流行开来。庄河属相灯“非遗”传承人之一陈东柱在接受采访时曾朴实但一语中的地点明其中原因:人们还是喜欢农民用粮食手工做的(属相灯),说粮食做的“好使”[10]。所谓“好使”即是灵验,即决定了属相灯仪式的预兆观察能否准确。
通过前节对“点属”仪式的观察不难发现,整个仪式中有着浓厚的农业氛围。这与胶东移民闯关东进入东北后的职业取向有着莫大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清代移入东北的山东移民,绝大多数以农为业。这种职业结构直至“九·一八”事变甚至1937年以后才发生向工矿、商业的转变[14-15]。因此,属相灯的豆面材质实际上代表了仪式参与者的生长环境和谋生手段,只有二者的互相匹配才能使接下来的仪式发生应有的效能。豆面的形式背后象征着土地和农民的意义,如此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使得属相灯尚未开始制作之时,符号便已产生。
除了材质,属相灯本身亦是符号。严格来说,可以成为仪式使用物的属相灯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是亲自制作。民间认为,家庭成员们共同参与、亲手制作的过程是为属相灯注入“灵魂”的过程。从仪式理论角度来说,这实际上既是通过提高参与度强化物品的象征性,也是阖家团圆共度佳节的外在表达。其二是外形近似。属相灯样式并非千篇一律或有定式,反而要求因人而异各具特色,即根据属相灯所象征之人的特征制作与之匹配的属相灯。比如在属相灯上配以各种装饰物区分性别、根据个人身材决定属相灯的圆润或纤细,孩子的属相灯比成人偏小等等。以相似外形指代个人本体,正是符号创制的最直接表达。经过这两个过程的属相灯内在拥有个人气息,外在拥有类似外形,它才能由一个普通面塑转化为代表家庭成员或家中牲畜的象征物。
在生命预兆观察中符号的应用亦非常明显。点燃蜡烛以后观察燃烧时长以预测长寿与否。其中蜡烛本身以其物理长度象征了虚拟的生命时间长度,燃烧的火焰和滴落的蜡油象征了生命一点一滴的行进。在此过程中,蜡烛有可能无意中被风吹灭或因蜡油凝固而自然熄灭。无论是风还是蜡油或其他任何可能导致蜡烛熄灭的因素,都象征了生活中的干扰和苦难。而仪式中禁止人为干预的限制则象征着个人不能操纵命运、不能逆天改命的规则与无奈。
方向预兆观察中象征意义大致相同。以鲤鱼灯作为方向预兆的使用物,是由于“鱼”与“余”谐音的缘故。这一简单谐音已经使得鲤鱼灯成为一个象征富足的符号。不仅如此,在方向预兆观察中,鲤鱼灯的旋转象征生活的行进,重力下的旋转自然停止象征命运的安排,而鲤鱼头所指的方向则象征了好运的方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点属”仪式中使用了大量的符号,包括豆面材质、属相灯的“灵魂”与外形、蜡烛、火焰、风甚至是禁止行动的规则、物体的旋转等等。所有符号的运用都是为了完成最后对预兆的观察,为了使参与仪式者能接收到尽可能准确的上天预兆,以此获得当年甚至更久的心理预期和行动指南。在此过程中,各个符号各司其职,联合支撑起“点属”仪式的占卜功能,并且与参与者形成一种互动互惠的关系。这种仪式被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称为“感应性礼仪”[16]。但除了仪式的普遍共性外,庄河“点属”还表现出某些独有的特点。
其一,仪式规则相对灵活。“点属”与其他仪式一般,的确有诸多程序要求,但在某些细节上也表现出大部分仪式没有的宽松。前已提及,首先在仪式举行的时间上每家便各不相同,并不只限于正月十五。其次属相灯的摆放也可各自创造。比如有的家庭会在门口摆放一只狗属相灯和一只鸡属相灯,狗代表看家护院保平安,鸡代表啄食害虫护庄稼。有的家庭会在粮仓放置一只蛇属相灯,称“神虫”,或者只点一支蜡烛。再次,对某些象征的解释也可因地制宜。鲤鱼灯头指示的方向是好运的方向,但好运在各个家庭含义不同。沿海乡镇将其解释为“渔获丰富的方向”,而山区乡镇则解释为“作物兴旺的方向”。
其二,“点属”仪式中所使用的符号全部是肖像符号。斯图尔特·霍尔将符号分为肖像符号与索引符号。肖像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在外形、发音、感受等某个方面有相似联系的符号。而索引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并无明显联系,只是因为约定俗成被成员共同接受的符号[17]。豆面象征农业,是因为大豆本身即是农业产物;属相灯可以象征个人,也是由于二者生肖相符且外形近似;蜡烛象征生命是由于二者都拥有一个线性长度的特征;“鱼”象征“余”则是文字发音相同之故。
其三,“点属”仪式中以属相灯为支配性象征符号。特纳认为一个仪式中的支配性符号应当是“迥然不同的各个所指的统一体”[8]34。属相灯在不同的位置,既可以象征家庭成员,也可以象征家禽家畜,还可以象征水源动物。个人的生肖、动物的外形都可以通过属相灯表达出来,所以在仪式中其代表了不同的所指。更关键的是,属相灯是整个“点属”仪式的核心支撑。没有属相灯对个人和动物的象征,则点燃蜡烛毫无意义,生命与方向预兆则无法进行,那么整个“点属”仪式的意义便荡然无存。可以说,正是因为属相灯这一符号象征意义的独特性,“点属”仪式才被赋予了独特性。
四、余论:移民记忆与象征崩解
虽然民俗学和移民史尚不清楚庄河“点属”仪式的演进过程,亦无法解释为什么该仪式至今只留存于庄河区域内,但“点属”仪式源自于胶东地区则是不争的共识。仔细对比胶东地区正月十五的风俗仍可发现其中与“点属”仪式相联系的蛛丝马迹。庄河的“点属”仪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胶东移民的闯关东记忆。
从清代以来,进入辽东半岛的山东移民就以胶东为主[15]21,主要是今烟台、威海、青岛一带,即旧称登州与莱州区域。在登莱地区的地方志关于正月十五的记载中,可以窥见“点属”的影子。但胶东所点之灯,并非属相灯,而是象征十二个月份的月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登州府志》有载:“上元……作面盏十二,照月序蒸之,以卜水旱。”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福山县志》载:“上元作面盏十二,照月序烝之卜旱涝”。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的《招远县志》载:“又作面灯十二,各照月序烝之,以卜水旱,颇验。”[18]217、226、230
更为晚近的记载则“点属”的痕迹愈发明显。光绪七年(1881年)的《增修登州府志》除了以上表述,又增加有“各家以萝卜燃柱作灯,或以豆面为之”。[18]220此时的做灯材质已与属相灯相同。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莱阳县志》中“以面作蛇形埋于谷仓,或置窗台,谓之‘神虫’”的风俗已可直接见于今日庄河的“点属”仪式中[18]239。
直至今日,胶东地区依然保持着在正月十五点燃十二月灯的习俗,甚至其中还存在点燃全部十二只属相灯的情况,称为“点面灯”[19-20]。但晚清民国的史料中丝毫未见关于胶东属相灯的记载,因此无从判断是胶东风俗的发展还是辽东风俗的反向输入。在某些关于庄河属相灯的文章中,忆及庄河也有在正月十五点燃十二月灯的风俗[21]124。但以笔者的多年经历和多方探问,并未发现十二月灯习俗存在于庄河的证据。虽然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但庄河“点属”由胶东传来乃是事实,今日的“点属”仪式也保留着胶辽悠久联系的移民记忆。
经过多年的传播与沉淀,“点属”已经成为庄河正月十五必不可少的活动。作为一种民俗,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点属”并没有消亡的危险。但作为一种仪式,“点属”却已然到了象征意义崩解的边缘。
其一,属相灯的豆面材质受到冲击。虽然稍早以前的石膏、金属、玻璃材质没能冲击豆面材质的地位。但由于豆面属相灯仍显俗气,近年新引进的树脂、超轻粘土成为属相灯材质的新宠。一旦豆面材质发生改变,则属相灯对土地和耕作的代表无从谈起,民众对粮食属相灯“好使”的信奉也随之消失。所以,属相灯材质的选择只是表面变化,深层却意味着“点属”仪式农业属性的丧失。由此属相灯的象征意义便缺少了先决一环。
其二,属相灯被完全商品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普及,庄河区域内出现数家专事属相灯制作的工坊。其在正月十五之前赶制属相灯,以批发价销售给摊贩,再由摊贩以零售价销售给民众。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家庭已经放弃亲手制作属相灯,转为购买。但属相灯购买而来则无法亲自参与制作,批量生产则无法因人而异。这意味着属相灯转变为象征物的两个过程——注入气息与赋予外形无法完成。属相灯的象征性本需来源于参与,现今只能来源于指定。
其三,城镇化的加速使“点属”仪式的诸多部分无法进行。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移入庄河市区生活,原有“点属”仪式的诸多设计无法与城市相适应,只能被放弃。城市当中没有水井,蛤蟆灯无处放置,笔者在调查之前甚至从不知属相灯当中有蛤蟆灯的存在。城市中没有牲畜饲养、没有粮仓谷仓,完全不需要代表家中牲畜的属相灯或“神虫”。最关键的是,城市楼房相对封闭,蜡烛燃烧的烟尘难以排出。因此很多居民以小电灯代替蜡烛。小电灯没有燃烧时长,电池可以供电一晚而不熄。如此一来则完全失去了“点属”仪式中最重要的生命预兆观察的意义。
由上可见,“点属”仪式中的诸多物品与流程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必然无法完整保留自身的符号与意义。“点属”中的象征性与占卜性被大量消解,因此其作为人类学仪式理解范畴的定位也被危及。如果上述情况继续发展,那么“点属”能否继续被视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则颇存疑虑。
综合上述,庄河“点属”的前身源于胶东,是十五燃灯的全国习俗在地方上独具特色的表达。以符号人类学视角观之,其以属相灯为核心符号,配以蜡烛、火焰、风等辅助符号,通过诸多符号的联合表达形成一种人类学仪式。该仪式包括制作、放置、点燃、预兆观察四个步骤,每一步骤环环相扣,共同达到一种类似于占卜的功能,实际上反映了民众经营生活之时对美好顺遂的祈愿。
“点属”仪式生成于旧时的农业社会,历经时间考验留存至今。作为仪式的“点属”,不仅保留了胶东人海路移民的记忆,更成为见证区域文明发展的链条。随着时代的发展,“点属”的定位与功能不可能一成不变,与时俱进成为必然要求。当代文明下,“点属”仪式的预测功能不会被人们笃信,亦不会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但可以继续以祈福性民俗活动的形式与时代相融合。而作为祈福性民俗活动的“点属”,不仅传承了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满足了地区族群身份识别与认同的需求,更传递了人类文明对生存命题的永恒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