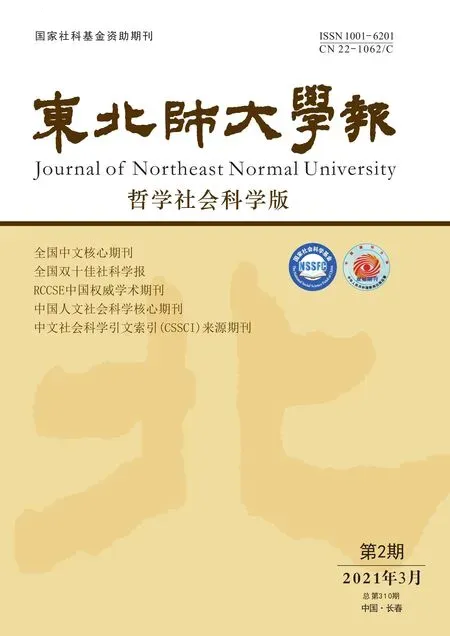话本传统与汪曾祺的文学创作
2021-12-03周哲
周 哲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自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受戒》以来,汪曾祺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这不仅表现在研究者众,还表现在研究成果颇丰。然而,长期以来,对于汪曾祺与话本传统的关系,却较少有人研究,深入研究者更少,即便被提及也往往是一笔带过,没有充分展开和系统论述(1)参见赵勇《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季红真《论汪曾祺散文文体与文章学传统》(《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田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等。。究其因,恐怕主要与汪曾祺对赵树理的“现代评书体小说”的质疑有关。他曾表示:“赵树理是一个农村才子,多才多艺。他在农村集市上能够一个人演一台戏,他唱、演、做身段,并用口拉过门、打锣鼓,非常热闹。他写的小说近似评书。”[1]17“写小说用的语言,文学的语言,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是视觉的语言,不是听觉的语言。……小说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人听的。”[1]101-102他还说:“我并不主张用说评书的语言写小说。”[2]“小小说最好不要有评书气、相声气。”[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对话本传统并不一味拒绝,而是在继承中有探索和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以汪曾祺的小说《皮凤三楦房子》和散文《艺坛逸事》为中心(2)下文所引作品出处:《皮凤三楦房子》(《汪曾祺小说全编·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艺坛逸事》(《汪曾祺散文全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探讨他与话本传统的关系,并阐述他对赵树理话本实践的超越之处。
一
话本小说源于说书人的底本,从开篇到结尾基本保留了说书人独特的讲述方式,这便是对“说书场”的模拟。而汪曾祺对此则既有继承,亦有探索创新。
首先,话本小说中的叙述人经常使用诸如“话说”“单说”“且说”“话分两头”“却说”“不必细说”等套语,来实现情节或话题的开启、转换和结束。关于此,汪曾祺在《皮凤三楦房子》中虽有继承,但使用不多,仅有“如今却说……”“且不说……,单说……”“此是后话”“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常用作章回小说的结尾和评书艺人的收场词)这四处。而这,应是汪曾祺既考虑到要保留“话本笔意”,又要克服“评书气”所做的选择。那么,汪曾祺在基本摒弃了类似的引导词后,又是如何进行起承转合的呢?对此,他多有创新。先看“头回”的开篇“皮凤三是清代评书《清风闸》里的人物”和“正话”的开头“此人名叫高大头。这当然是个外号。他当然是有个大名的。大名也不难查考”,可见,这两者与话本小说的“开门见山”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后者,是对“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和尚……”的“戏仿”,这便使僵化的套路有了新意。再看“‘文化大革命’山呼海啸,席卷全国”,以及“轰轰轰轰,‘文化大革命’过去了”,这两句不仅是情节的转换与结束的标志语,也同样是一种“戏仿”:夸饰词与拟声词的使用暗含了叙述人对“文革”的调侃与反讽,这同样也有新意。另外,用于转换话题、引入新人物的“他现在常在一起谈谈的,只有一个朱雪桥”这一句,也是对上述“且不说……,单说……”这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套路的突破。这样对一些套语的大量摒弃,就令小说少了许多他所谓的“评书气”,而多了鲜活的滋味,且短句的频繁使用也令文风骤然凝练起来。而这,都应与汪曾祺崇尚干净、简洁的文风有极大关联。他在《小说陈言》一文中不仅提到扬州说书人讲究“刀切水洗”——“指的是口齿清楚,同时也包含叙事干净,并不唠叨”,随后他又引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相关片段后总结道:“说书总要有许多枝杈,北方评书艺人称长篇评书为‘蔓子活’,如瓜牵蔓。但无论牵出去多远,最后还能‘找’回来,来龙去脉,清清楚楚。”[1]61如此说来,他对小说叙事的“干净”“简练”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受到话本传统的影响。而在《艺坛逸事》的叙事中,这一点更是得以深化,如汪曾祺完全弃用套语,转以更简洁、精练的单句。在《艺坛逸事·姜妙香》中有这样的句子:“姜先生真是温柔敦厚到了家了”“他从不生气”“姜先生从不争戏”“在上海也遇见过那么一回”“姜先生有一次似乎是生气了”。它们作起承转合用,可谓爽洁、简约之至,极大地维护了散文文体的纯净性。在这一点上,汪曾祺曾谈到鲁迅对他的影响,如他曾说:“鲁迅的教导是非常有益的: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4]378
其次,话本小说的叙述人常会跳出讲述,与读者交流和互动,如用“看官,你看(道)……(?)”此类提示语,或陈述或提问,令读者产生亲切感和现场感,有利于更好地进入故事情境。汪曾祺对此也有继承与创新。由于“看官”这类套语也会产生“评书气”,汪曾祺将其去掉,仅保留问句或设问句(占绝大多数),如《皮凤三楦房子》和《艺坛逸事·姜妙香》中分别有下列句子:“‘文化大革命’怎么会触及他,会把他也拿来挂牌、游街、批斗呢?答曰:因为他是牛鬼蛇神,故在横扫之列”“你猜申四说什么?——‘你凑合着穿吧’”。可见,后者这种“虚拟对话”与前者的“自问自答”比,带来的亲切感和现场感要强得多。而汪曾祺之所以如此,应是考虑到小说和散文的文体特性有别。散文是一种能与读者亲切对语的文体。现代以来,无论是冰心在《寄小读者》中以温柔慈爱的语调向小读者亲密诉说,或是梁实秋、林语堂等人“围炉夜话”般将心中之事娓娓道来,还是巴金在《随想录》中向读者倾诉“回归”后的忧愤与深情,都能说明这一点。而小说则要相对客观些。因此,这种直接向读者(“你”)发问并引起交流互动的“对话”形式,存在于散文中就显得更为融洽和谐。
最后,话本小说的叙述人常在叙述中插入解释说明和议论评价性文字,这以散句为多。若在叙述外进行议论评价,则一般以“正是”“但见”等作为引导词,辅以韵文套语,以偶句较为常见。这种“夹叙夹议”“现场报道”的讲述方式是话本小说的一大特点,是叙述人主观干预的明证。对此,汪曾祺亦有继承、扬弃与创新。在《皮凤三楦房子》中,汪曾祺不仅将上述引导词和韵文套语一并删去,无论解释说明还是议论评价都只用简约、凝练的散句,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评书气”。例如,“高大头怎么办呢?他总得有个家呀。他有老婆,女儿也大了,到了快找对象的时候了,女人总有些女人的事情,不能大敞四开,什么都展览着呀。于是他找了点纤维板,打了半截板壁,把这九平米隔成了两半,两个狭条,各占四米半”。这里的叙述人以论带叙,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也带有一定的现场感。又如,高大头找房产处要房子时与高宗汉对话的场景:“‘你自己盖?你有钱?是你说过:你有八千块钱存款,只要给你一块地皮,盖一所一万块钱的房子,不费事?你说过这话没有?’高大头是曾经夸过这个海口,不知是哪个嘴快的给传到高宗汉耳朵里去了,但他还是赔着笑脸,说:‘那是酒后狂言。’”这与上不同,叙述人借人物对话进行场景描绘的同时,还进行主观干预,这就带有“现场报道”的味道,现场感更强,读之如在目前。
另外,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文中绝大部分解释说明和少量议论评价性文字,是以随文注释的形式出现的,或以“(谨)按:”作为引导词,或无须引导词。体裁上基本为散句。功能上或作为正文的补充材料(说明人物的心理活动、文化程度、生活习惯、居住环境等,解释略叙之原因、特定语汇和历史掌故等),或以表达质疑、发表议论引起关注。从这些随文注释中可分明感受到“文人化”和“书面化”倾向,如“谨按”“前文已表”等文人和书面语汇,以及叙述人对于“文革”的反讽态度,如“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恶作剧都是变态心理学所不得不研究的材料”“‘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好像特别费鞋,因为又要游行,又要开会,又要跳忠字舞”。前者应当是汪曾祺为克服赵树理小说“评书气”所做的进一步努力(在借鉴话本传统时,赵树理过于注重可“听”性,而汪曾祺则更看重可“看”性),而后者则是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余温犹存的政治环境,但又想一抒积郁胸中多年之“块垒”所做的叙事策略的调整。如果说汪曾祺在1980年重写《异秉》意味着“他看似以非政治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实际上却不是‘看透与规避’政治,反倒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它的改造,尽管他对这种改造的效果可能并不自觉”[5],那么随后的《皮凤三楦房子》就已明显表现出他对政治的“巧妙”干预。话说回来,由于散文《艺坛逸事》由四位名伶的逸事趣闻杂录而成,各篇篇幅极精短,十分讲究“见微知著”“简笔传神”,于是这种相对烦琐又意在曲笔微讽的随文注释方式被代之以更简洁、精练的散体文字,自由穿插于叙述中。前者如“‘站住!把身上的钱都拿出来!’——他也不知道里面是谁”(解释说明),后者如“懂得吃而不吃,这是真的节俭”(议论评价)。在此,无论《皮凤三楦房子》还是《艺坛逸事》,都可说是得了话本小说的“神髓”。
二
汪曾祺对话本小说的结构形态亦有所扬弃和创新。先说“入话”。话本小说在“正话”前有引导性成分——“入话”。“入话”一般由“篇首诗词”、相关解释议论性文字和“头回”构成,而汪曾祺无论在小说还是散文中都摈弃了“篇首诗词”及紧随其后的解释性议论文字。为何如此?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自近代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大力推崇小说以来,小说与诗文取得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文人作家大可不必如说书人一般携诗词以自重。而“头回”,其在宋元时期的真正作用是说书人“为了暖场和等待迟到的听众”[6],而在明代文人参与话本小说创作后则基本上用以从“正面或反面来映衬正话,以甲事引出乙事,作为对照”[7]140。在《皮凤三楦房子》中,汪曾祺用清代评书《清风闸》中的人物——皮凤三,来正面引出“正话”的主角——高大头,不仅继承了“头回”的结构性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小说的叙事容量,也发挥了“头回”的“暖场”效用,令小说更能抓住读者眼球,激起阅读兴趣。与小说不同,散文最强调随形赋势、萧散自然,是最自由的文体,倘若加上“头回”则不免显得生硬和累赘,有碍灵动、飘逸。并且,囿于篇幅和容量限制,去掉“头回”直接进入“正话”最为合适。如《艺坛逸事·姜妙香》的开头“姜先生真是温柔敦厚到了家了”,就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接着说“正话”。“正话”就是话本小说的正文部分,集中体现了创作者在情节设计上的匠心独运。为吸引读者,作者必须像说书艺人一样考虑到情节之“奇”。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今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赘矣。”由此看来,他眼中的“奇”应当来源于“耳目之内”的日常生活。而睡乡居士在《二刻拍案惊奇序》中也认为:“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如此说来,话本小说“常中见奇”的情节设计思路,最好遵循“存乎耳目之内”“以无奇为奇”之原则,以免“失真”。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虽是老套的关于青楼女子与嫖客的故事,却又是“旧瓶”装“新酒”:一个卖油郎竟凭借其温柔敦厚、多情善感,让花魁娘子芳心暗许。这便是“无奇中见奇”的例子。在此,汪曾祺在《皮凤三楦房子》中多有继承。小说讲的是一介草民高大头凭借自身智慧,不仅帮好友朱雪桥一同“巧渡”“文革”之“劫”,还让故意“整人”的干部谭凌霄、高宗汉二人纷纷“落马”,最后竟在九平米的地皮上“楦”成一幢三十六平米的房子,因而得了个外号——“皮凤三”。可以说,在“常中见奇”的情节设计思路影响下,整个故事都显得跌宕起伏、妙趣横生。而《艺坛逸事》不同于前者有连贯的故事情节,其碎片化叙述消解了情节,因此“常中见奇”的思路被创造性地用于各个“碎片”,让它们都能妙趣横生、兴味不绝。具体说来,这篇作品分四个部分,各部分相互独立,每部分写一位名优的逸闻趣事。先说萧长华,汪曾祺先写他步行之“奇”,又写他饮食之“奇”,再写他义举之“奇”。后说姜妙香,汪曾祺先写他从不生气,又写他从不争戏,再写他遇到劫道也表现出菩萨心肠。这便将他温柔敦厚的情性之“奇”刻画得淋漓尽致。再说贯盛吉,汪曾祺主要写他“逗”的性格之“奇”。他不仅在生活中“逗”,临死更“逗”。最后说郝寿臣,汪曾祺主要写他“为人老实”之“奇”。他在拿着秘书“捉刀”的讲稿给同学演讲时,说到酣畅竟高举讲稿赞道:“同学们!他说得真对呀!”可以说,这些逸闻趣事都取自寻常生活,存乎“耳目之内”,而这些人则可称为“俗世奇人”。
那么,“奇”在文中究竟如何体现的?罗烨在《醉翁谈录》中认为,“说话人”应在“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广言之,即是说书人讲至高潮处应从细部着眼,方能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才能“久长”。而话本小说作者亦是如此。如《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中写谢小娥全家被强盗杀害的场景,着眼处全在细节,视点转换极快,现场感极强,可谓生动异常,如身临其境。当然,别处也同样需要细节的进入,使情节更加丰满,更有艺术感染力。如写谢小娥得救的场景,既写她溺水后意识模糊的恍惚感受,又写其生理上的表现——吐水,还写她清醒过来后的悲恸表现——放声大哭。这种细节的铺衍无疑令高潮处“热闹”非凡,也让“平淡处”不致冷场。而这种“大场面”的铺陈在汪曾祺的《皮凤三楦房子》中并不少见,最典型如高大头在谭凌霄的乔迁宴上尺量新房的场面,可谓紧张刺激之极。然而,汪曾祺的过人之处并不在此,而在于“小场面”的“简笔传神”,只寥寥数语和不事雕琢而又风流尽得。如写高大头和朱雪桥一同“挨斗”,汪曾祺从“对话”入手,写高大头暗中给朱雪桥递话来安慰他:“你是特务吗?——不是。不是你怕什么?沉住气,没事。光棍不吃眼前亏,注意态度。”将二人的内心活动、脾气秉性写得传神。又如,写二人“挨斗”后的“互通款曲”:“他们有时斗罢归来,分手的时候,还偷偷用手指圈成一个圈,比画一下,表示今天晚上可以喝两盅。”仅仅一个手势就让整个场面活了起来,既揭示了他们面对苦难的超脱心态,又表现了其深厚友谊。《艺坛逸事》篇幅极短、不宜渲染和铺陈,而情节的消解又使汪曾祺更少旁枝斜笔,专注于每一“碎片”的呈现,因此这种“简笔传神”的手法就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在这些“碎片”的呈现中,他也注重借助人物的对话营造情境,间或辅以白描技法摹画人物的神态、表情、动作等细部,有时叙述人还会进行主观干预,以提示说明和显示自己在场。典型如写姜妙香先生两次遭劫的场景。第一次是:“冬天,他坐在洋车里,前面挂着棉布帘。‘站住!把身上的钱都拿出来!’——他也不知道里面的是谁。姜先生不慌不忙地下了车,从左边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从右边又掏出了一沓。‘这是我今儿的戏份儿。这是华乐的,这是长安的。都在这儿,一个不少。您点点’。”(有干预)第二次是:“‘站住,把身浪厢值钿(钱)格物事(东西)才(都)拿出来!’此公把姜先生身上搜刮一空,扬长而去。姜先生在后面喊:‘回来,回来!我这还有一块表哪,您要不要?’”(没有干预)可见,仅此数语,整个场面跃然纸上,人物也栩栩如生,可谓高妙之极。实际上,从源流看,这种注重以语言和细节勾勒人物的“简笔传神”手法无疑脱胎于“史传笔法”。可以说,“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常常有着特殊的精神气质,继承了中国散文传统的一路成就:‘六朝重人物品藻,略略数语, 皆具风神’”[8]。只是在汪曾祺这里,还不时融入话本小说“夹叙夹议”和“现场报道”的讲述方式,这既有传神之妙,又因叙述人的主观干预产生强烈的现场感,尤为引人入胜。
再说“篇尾”。话本小说常以一首诗(多为自撰)作结,或概括,或评价,或劝诫。汪曾祺在《皮凤三楦房子》中以“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作结,既是对评书的借鉴,也是对章回体小说的“戏仿”,颇有新意。之所以说是“戏仿”,是因为故事讲到尾声已阐明高大头为何被称为皮凤三,这就意味着这篇小说是首尾呼应、情节完整、完全独立的。当然,根据该作品的篇幅,而将其看作章回体小说中的某一回看待,也未尝不可——盖因话本小说和章回体小说本出同源,都脱胎于“话本”,即“说话人的底本”(鲁迅)。而在《艺坛逸事》中,汪曾祺则以《汉书》“论赞”的引导词“赞曰”替代话本小说“篇尾诗”的引导词“有诗为证”,再续以两行四句自撰的寓教于乐、寓庄于谐、雅俗共赏、随性自然、朗朗上口的四言韵文作结。如:
(1)萧长华
赞曰:
窝头白菜,寡欲步行,
问心无愧,人间寿星。
(2)姜妙香
赞曰:
温柔敦厚,有何不好?
“文革”英雄,愧对此老。
(3)贯盛吉
赞曰:
拿死开逗,滑稽之雄。
虽东方朔,无此优容。
(4)郝寿臣
赞曰:
人为立言,已不居功。
老老实实,古道可风。
可以说,这既照顾到“篇尾诗”的形制和体例,又兼顾了散文内在的萧散自然的意态;既有说书人的娱众功能,又有文人劝世之妙(洗净“道学气”);既有书面语的文雅凝练,又有口头语的生动活泼,可谓文白交杂、雅俗合流,蔚为奇观;既融个性与情感于褒贬,又言简意赅,堪称点睛之笔[9]。实际上,从源流看,中国古典文学受史传传统影响很深,对“论赞”(“论赞”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史通》,是“史评”的总称)也有继承。散文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以“赞曰”自评,韩愈的《毛颖传》戏仿“太史公曰”作评;白话小说如“三言”“二拍”有“诗曰”“有诗为证”“诗赞云”;文言小说如《聊斋志异》有“异史氏曰”;等等。现代以来,孙犁在小说和随笔中常以“芸斋主人曰”“耕堂曰”作为议论评点,如自传性小说《续弦》有这样的结尾:“芸斋主人曰:婚姻一事,强调结合,讳言交易。然古谚云: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物质实为第一义。人在落魄之时,不只王宝钏彩楼一球为传奇,即金玉奴豆汁一碗,也只能从小说上看到。况当政治左右一切之时乎!固如巫山一片云,阆苑一团雪,皆文士梦幻之词也。”可见,除韵文与散文之别,孙犁更重用典的繁复,更古雅隽秀。他褒贬讽喻、纵横捭阖的杂文气息更为浓郁,可说是“得了‘太史公曰’的真传,而又浸透着‘异史氏曰’的神髓”[9]。而汪曾祺则更重口语的轻逸,更轻灵婉约,散淡随性、幽默闲适的小品风于焉而起。真可谓趣味与韵味并重,情思与妙悟兼得。这无疑是对僵化的“篇尾诗”的一次极好的改造。
三
既然汪曾祺在文学创作中不仅对话本传统有所扬弃,更有创新性发展,那么,这对他所质疑的赵树理的话本实践有何超越之处?首先,最为重要的便是语言品格的提升。宋元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因而带有口语化的特点,而“明人作品,也深受宋元话本的影响,基本上保持口语化的优点。其中较优秀作品的文学语言,是结合着明朝的北方话和江南通用的口语、宋元的某些口语,以及比较浅显的文言,基本上尚能融合一体。其中完全口语化的部分,很接近现代的口语”[7]459。而赵树理和汪曾祺在话本实践中都继承并发扬了这种口语化的特点,但汪曾祺的语言品格是更高的。
赵树理长期生活在北方农村,对农民有深厚的情感,对评书、秧歌等民间文艺形式也十分熟悉和亲近,对新文学在农民之间的隔膜感触颇深[10]61。为创造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赵树理便从身边的评书话本中汲取营养,又考虑到小说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群众之间的传播效果,因而他认为:“写进作品里的语言应该尽量跟口头上的语言一样,口头上说,使群众听得懂,写成文字,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群众看得懂,这样才能达到写作是为人民服务的目的。”[11]为此,他尽量不用生僻字和地域性过强的土语,在语料的选择上兼具地方性与通俗性;竭力避免语言的“欧化”,多用句型结构和句法简单的短句。这当然满足了农民群众对于“听”的需求,也使“他前所未有地将具有地方色彩、原汁原味的方言俗语从纯粹口语提炼成为韵味深长的‘普通话’。在白话文的创造上,胡适主张向传统的白话小说学习,傅斯年主张作欧化的白话文,赵树理则将民间口语提高为文学语言”[12]。不过,过于照顾农民的欣赏感受,会给他的小说语言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啰唆拉杂、不够精炼,僵化呆板、缺少回味;二、文化底蕴有些匮乏。而汪曾祺由于调用其丰富的语言经验,就明显克服了以上不足,极大地提升了语言的品格。
先说前者。赵树理认为:“写文章和说话一样,只是把‘说’变成‘写’;在接受者方面只是把‘听’变成‘读’或‘看’。”[13]并且,“要照着原话写,写出来把不必要的字、词、句尽量删去,不连贯的地方补起来。以说话为基础,把它修理得比说话更准确、鲜明、生动”[14]。这种观点是有一定见地的,但赵树理在具体实践时却有些偏差,例如“她拿出钥匙来,先开了箱子上的锁,又开了首饰匣子上的锁,到她原来放钱的地方放钱……”(《登记》)(3)文中所引《登记》的内容均出自《赵树理小说散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在这里,他显然过于顾及农民听众(读者)的接受效果,不仅重复用字使语言显得有些啰唆拉杂、暗沉无光、不够精练,句型结构也相当单一、缺少变化,甚至有老舍所言“一顺边儿”之“尴尬”,颇为呆板僵化,且缺少回味。实际上,这种“修理”得过于“规整”的文字,除了能准确地向农民群众描述事件的进程之外,几乎很难实现他所说的“鲜明”与“生动”的效果,因为“说话”之“道”远非如此。换言之,现实生活中的人际沟通断然不会诉诸如此之“正”的表达方式,如“到她原来放钱的地方放钱”,这何其啰唆!更何况是文学语言?而受“十七年”文化政策影响的汪曾祺,虽也强调“写小说要像说话一样”,重视语言的准确与生动,但他的理解是更为深入透辟的。他认为:“写小说要像说话,要有语态。说话不可能每一个句子都很规整,主语、谓语、附加语全都齐备,像教科书上的语言。教科书的语言是呆板的语言。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这样语言才明确。平常说话没有说挺老长的句子的。能省略的部分都省掉。我在《异秉》中写陈相公一天的生活,碾药就写‘碾药’。裁纸就写‘裁纸’。这两个字就算一句。因为生活里叙述一件事就是这样叙述的。如果把句子写齐全了,就会成为‘他生活里的另一个项目是碾药’,‘他生活里的又一个项目是裁纸’,那多啰唆!——而且,让人感到你这个人说话像作文章(你和读者的距离立刻就拉远了)。写小说决不能作文章,所用的语言必须是活的,就像聊天说话一样。”[4]378可以感受到,汪曾祺所言似乎就是对赵树理语言观的回应与深化;并且,这也“恰巧”指出了赵树理小说语言的缺憾所在。当然,不仅是理论的阐释,汪曾祺还将其切实地付诸实践。上述《异秉》是如此,《皮凤三楦房子》亦是如此。试看此例:“登了泰山,上了黄山,吃过西湖醋鱼、南京板鸭、苏州的三虾面,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材料虽有,价值不大。”在这里,同样是描述事件的进程,但汪曾祺就完全克服了赵树理小说语言啰唆拉杂、僵化呆板,不够精练、缺少回味的缺憾。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中国文章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从形式上说,汪曾祺创造性地运用了“四六字句”(尤其是四字句)。这主要体现为“四六字句”的口语化。就上例而言,除“乘兴而去,兴尽而归”颇有文言之味,其余如“登了泰山,上了黄山,吃过西湖醋鱼、南京板鸭……材料虽有,价值不大”都是完全口语化的。为何如此?原因其实很简单:既要实践“写小说要像说话”这一观点,又要避免口语化的弊端。他曾说:“中国旧诗用五七言,而文章中多用四六字句。骈体文固然是这样,骈四俪六;就是散文也是这样。尤其是四字句。没有一篇文章找不出大量的四字句。四字句多,几乎成了汉语的一个特色。如果有意避免四字句,便会形成一种非常奇特的拗体,适当地运用一些四字句,可以造成文章的稳定感。”[1]104-105实际上,四字句的穿插或连续使用不仅能强化文章的稳定感,避免啰唆拉杂、不够精练之弊,并突出文字的端庄雅洁之感;且更能摆脱僵化呆板、缺少回味之谬。这就说到语言更为内在的层面。
在赵树理看来,“写文章比说话容易一点。因为话需要接着说,如果每一句话的中间隔五分钟,那任你怎么说得通、说得好也没人听;而写文章就活动得多——写了上一句想不好下一句,隔一天再写也没有关系”[13]。这种说法显然不够合理。说话固然需要连续,但文章之道更讲究气脉贯通,而不仅仅在于表达的准确性。在这种观点之下,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实践自然缺乏“文气”的灌注。如在上例中,赵树理虽准确清晰地描述了事件的具体进程,足够通俗易懂,却没有韵致与回味,为何?因为句与句之间的逻辑联系虽是密切的,但更内在的“文气”不聚,“堆砌”感颇重,于是形神俱散。而汪曾祺是相当重视“文气”的。他认为,“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联系。……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联系的。语言像树、树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摇了百枝摇,它是活的。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中国人说‘行文’,是很好的说法。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4]887-888就上例而言可以深切感受到,同样是描述事件的进程,汪曾祺的文字不但清晰明了,更是“文气”连贯、气韵生动,极富口语的韵味。这是如何产生的?根据汪曾祺对韩愈“气盛言宜”说的阐释,首先应是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实,方能才华横溢、妙语连珠;另外,“文气”与“言之短长”“声之高下”的谐和配比也关系密切[4]887-888。笔者并不知晓作者当时的创作状态,因此仅从语言的技术层面展开讨论。一、整体上说,四字句的穿插会令文字形成长短兼行之态,从而使语言更灵动、更富于节奏感。二、局部而言,四字句的成对使用能形成对仗之势,这不仅“可以摆脱一般语法逻辑的捆绑,能够造成语言上的对比和连续,而且能造成语意上较大的跨度”[4]899,也更能造成平仄相协、抑扬交互的音乐美感,如“登了泰山,上了黄山”。尤其是四字句的多对连用,如“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材料虽有,价值不大”,能于波澜起伏中形成急促铿锵的节奏,有排山倒海、奔涌如流之感。可以说,汪曾祺的文字单拆开看稀松平常、无甚趣味,若是连缀起来,则整体上平仄相协、文白相杂、雅俗相间,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令人回味无穷。而这便是“文气”之美,也是赵树理话本语言所难及之处。
再说后者。赵树理“以评书为正统”[15]的狭隘观念以及过分照顾农民群众的欣赏感受,令他过于强调从民间口语中提炼文学语言,尽管创造了“现代评书体小说”,然鲜活有余而底蕴不足。汪曾祺则不同,他尤为重视“语言的文化积淀”[1]44。在他的话本实践中,他不仅广泛吸纳群众口中和民间文艺里的“活语言”,并予以颇具新意地改造和运用,还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语言中的优良因子的创造性继承;并且,颇值一提的是,他还时时在语言中凸显中国文人生活中的“雅元素”如书画、陶瓷、花鸟、美食等,大有明清小品之遗绪与余韵。这样一来,他的文学语言便更显出雅俗共融之态,文化底蕴深厚。
事实上,中国文学向来有文体上“以尊入卑”的传统,典型如韩愈“以文入小说”(4)参见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苏轼“以诗入词”(5)参见陈师道《后山诗话》。等。而就话本小说而言,诗词韵文的大量使用就是“以诗文入小说”的明证。从源流来看,从宋元话本到明代“三言”“二拍”,再到清代的《无声戏》《十二楼》,由于文人的介入益深,诗词韵文就由单纯僵化的引用如“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罗烨《醉翁谈录》),过渡到新颖独特的创造。现代以来,老舍是尤为关注民间文艺且最早借鉴话本传统的作家,典型如短篇小说《黑白李》和《柳家大院》。另外,他的散文中也偶尔出现“有诗为证”云云,如《一些印象》。不过,这种“以诗入文”是更外在的,颇有“戏仿”之味。在更多的时候,老舍是以其得天独厚的现代北京话作为话本语言之底色,但其“新文艺腔”和“欧化味”还是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16]。老舍之后,赵树理应当是话本传统最有力的践行者,不仅产量颇丰,佳作也不少,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尤其是语言,茅盾、郭沫若、周扬、老舍等一众作家、批评家对他的语言成就有高度评价,如郭沫若盛赞道:“最成功的是言语。不仅每一个人物的口白适如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话,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然而文法确是谨严的,不像旧式的通俗文字,不成章节,而且不容易断句。”[17]然而,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他在话本语言上的探索的确颇显乏力。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以卑为尊”、故步自封,从而放弃了更为广阔的语言探索空间。而汪曾祺,尽管没有赵树理对话本传统的“眷恋”与“痴迷”,但他的语言意识更为自觉、开放和包容,重视“以尊入卑”来主动提升话本实践的语言品格,无论是对说书场的翻新,还是对篇尾诗的改造,都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且以对说书场的模拟为例。赵树理构建说书场的语言也颇为啰唆呆板,且带有浓重的“评书气”。如《登记》中有这样的文字:“诸位朋友: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这个故事题目叫《登记》,要从一个罗汉钱说起”“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照我这么说,性急的朋友们或者要说我不在行:‘……’其实不然:有些事情不到交代的时候,早早交代出来是累赘;到了该交代的时候,想不交代也不行。闲话少说,我还是接着说吧:……”“以前的事已经交代清楚,再回头来接着说今年……”而汪曾祺,如前所述,就很好地克服了这种缺陷。当然,汪曾祺对赵树理话本实践的语言层面上的超越,绝不仅体现在说书场与篇尾诗两处,而是正如前面所论述到的,对整体文字品格的提升。可以说,这便是现代文人介入话本实践的极佳范例。
另外,在话本实践的社会功能层面上,汪曾祺同样对其有所超越。话本一脉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便是娱众,而当文人介入益深后,文字品格虽提高不少,更趋雅化,但娱乐性逐渐丧失,代之以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逐步沦为“文人劝世”的工具,从而就此衰落。而现代以来,老舍为话本小说注入“五四”的“启蒙”意识与“人学”内涵,如《柳家大院》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而《黑白李》注重表现儒家的“仁恕”思想。这虽也有“劝世”之味,但并非以道德说教的方式展现出来,而是诉诸高超的艺术技巧。到了赵树理,他同样肯定并继承了话本小说的“劝人”之用。在他看来,“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18]163。并且,他也重视“劝人”的方式,如他说:“我们写小说的意图虽说在于劝人,可是和光讲道理来劝人的劝法不同——我们是要借着评东家长、西家短来劝人的。”[18]164从而创造了“现代评书体小说”这一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不过,这虽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话本小说的娱众功能,令读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受“劝”,但又因其过分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的创作态度,令作品的政治宣传意味过浓,导致这种“劝”过于生硬和浅露(典型如《登记》的结尾),从而走向“文人劝世”的另一极端。
而汪曾祺则对此有极大的超越。他虽同样强调作家的文学创作“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但他更注重“潜移默化”的效果。如他这样说道:“我觉得文学的作用不是这样直接的。我想一个作品,如果写完了放在自己的抽屉里,那是他个人的事情。如果拿出来发表,就成了一个社会的现实。它总会对人们的思想感情产生这样那样的作用。比如说,可以引起人们对人的关心,让人们感觉到自己应该生活得更好更高尚一些,或者说使人们发现人本身的诗意和美,或者说给人们以希望,尽管这个世界充满了痛苦。但是这个作用是比较间接、缓慢、潜在的。不能像阿司匹林治疗感冒那样有效。中国有句老话叫‘潜移默化’,某些文学作品,我觉得对人们的心灵所起的作用,是一种滋润的作用。”[4]881可以看到,尽管汪曾祺和赵树理的落脚点都在“人”,但赵树理的“劝人”是落在当时的政治框架之内的,具有“时效性”;而汪曾祺的“劝人”,尽管也表现出对政治的干预,但与赵树理的迎合不同,他是站在“抒情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表现出对政治的反思,并“巧妙”地表达出来,最终突出的是“人”而非“政策”,因而更具有“永恒性”。如果我们将《登记》与《皮凤三楦房子》做一对比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在《登记》中,赵树理的叙述逻辑是青年人的自由恋爱受到落后势力的严重阻碍,无论年轻人做出怎样的努力,都难以摆脱这沉重的枷锁,但“婚姻法”的颁布如“天降神兵”一般,即刻扫除一切障碍,几对新人不仅能马上“登记”结婚,连头脑顽固的人都能瞬间转变其态度,进步之“神速”,实在令人瞠目。整个结尾也都显出一派欣欣向荣、花好月圆的景象,可说是将话本小说常用的“大团圆”结局用到极致。而在《皮凤三楦房子》中,汪曾祺始终围绕高大头这一中心人物来结构叙事,并在人物形象的精细雕刻中让读者细细品咂、慢慢感受、久久回味,从而获得心灵的润泽与滋养,而非突兀地将“劝人”的东西“砸”过来,“逼迫”读者咽下去,强调“立即生效”,无论其是否“消化不良”。这既克服了赵树理在话本实践中“重事不重人”[10]63的缺憾,又从根本上消除其浓厚的政治宣传意味,从而只保留了“劝人”的有益成分。并且,通过对说书场的翻新、对话本结构形态的扬弃与创新、对整体语言品格的提升,汪曾祺还大大强化了作品的“可读性”,这便更深层地激活了话本一脉的娱众功能,可谓“寓教于乐”“寓庄于谐”,从而使他的作品有更大的受众面。
总之,汪曾祺文学创作对话本传统的继承、扬弃和创新,既令话本“文脉”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也为现代汉语写作积累了相当宝贵的丰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