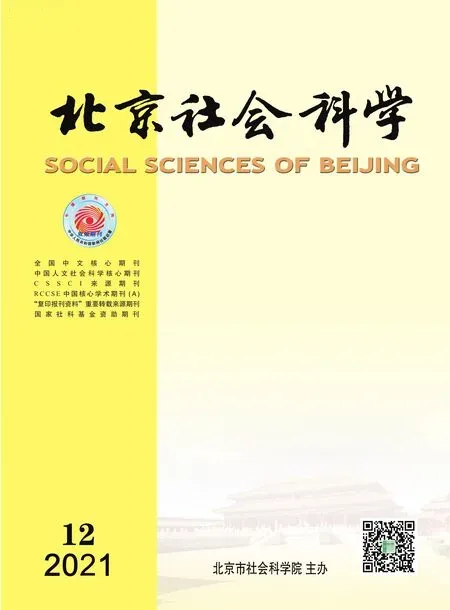宋代书目中文论、史评著作的著录与迁移
2021-12-02翟新明
翟新明
一、引言
文论著作兼具选本与评论的性质,在《七录》与《隋书·经籍志》对集部确立之初,文论著作即附属于总集类;[1]至《古今书录》,开始有意识地将文论著作与总集相区别。[2]在宋代,独立的“文史”类名最早由《三朝国史艺文志》(以下简称“《三朝志》”)确立,文论著作得以与原所附庸的总集类相区别而独立。但在文史类确立之初,文论著作即与史评著作相共存,虽然《崇文总目》将史评著作附于杂史类之末,《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在史部别立史评类、史学类以著录史评著作,但文、史并存仍旧是宋元书目中文史类文献著录的主要标准。
二、“扬榷史法”与“讥评得失”:从文史类到史评类
《三朝志》首次明确设立文史类,且其小序已称“言文章体制……其后述略例者多矣。至于扬榷史法,著为类例者,亦各名家焉”[3],是将文论(言文章体制)与史评(扬榷史法)二类著作均著录于文史类中,对于史评著作,更强调其叙“类例”也就是史法的特点。《崇文总目》的编修曾参考《三朝志》,其集部也设立有文史类,但并未在此类著录史评著作,而是在杂史类之末附录了《史通》《史例》《史通析微》《正史杂论》四部史法著作。《崇文总目》虽接受了“文史”之类名,而仍将此类史评著作著录于杂史类,可见当时编者对于此类著作性质的明确认识,其背后也应该有着对文、史区别的意识。
现存文献中,最早将史评著作附庸于文史类的,是欧阳修所编《新唐书·艺文志》,在文史类“不著录”部分著录了刘知幾《史通》、柳璨《柳氏释史》(即《史通析微》)、刘餗《史例》、田弘正客《沂公史例》与裴杰《史汉异义》五部。从其书名来看,强调的是对史法、史例的考辨,但宋代书目的解题则更强调这些著作的评论性质。如衢本《郡斋读书志》称刘知幾《史通》“乃以前代书史,序其体法,因习废置,掇其得失,述作曲直,分内外篇,著为评议,备载史策之要”[4],《玉海》卷四九引《中兴馆阁书目》称其“评议作史体例,商榷前人,驳难其失”[5],强调对史法的评议。《玉海》卷四九引《中兴馆阁书目》称刘餗《史例》“以前史详略,由于无法,故隠括诸凡,附经为例”[5],则是明确树立史学凡例。至于柳璨《史通析微》,是对刘知幾《史通》的评议,衢本《郡斋读书志》称“因讨论其舛缪”[6],《玉海》卷四九引《中兴馆阁书目》称“随篇评论其失”[5],《直斋书录解题》称“讥评刘氏之失”[7],更接近于对史法评论的批评。与《三朝志》小序中尤其强调类例、史法不同,宋代书目对于史评著作的解题,在类例之外,更强调其评论的性质。《中兴国史艺文志》文史类小序亦称“文史者,讥评文人之得失也”[3],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的对于史评著作性质的不同认识。是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史部别设史评类以著录此类文献。
袁本《郡斋读书志》并未提及史评类设置的缘由。姚应绩重编衢本《郡斋读书志》史评类《刘氏史通》解题称:“前世史部中有史抄类,而集部中有文史类,今世抄节之学不行而论说者为多,故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为史评,附史部,而废史抄云。”[4]此段袁本未载,当为晁公武后来所加,《玉海》《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引均同,可以视为史评类小序,也是对史评类设置的解释。其中“论史”二字,即已确定史评著作之性质。史评类的设置,可以说是对文史类设置不合理的一种修正,表现出文、史分离的著录理念。
所谓“前世史部中有史抄类”,系指宋代的国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称:“隋、唐志史部皆无此门,附在杂史,《宋志》方别立史抄门。”[8]而《宋史·艺文志》之设史抄,实自宋国史艺文志而来,《文献通考·经籍考》列有宋代四部国史艺文志史抄类著录文献的部数与卷数[8],《玉海》卷四七亦引《国史志》:“史抄类:贾昌朝《通纪》八十卷。”[9]知自《三朝志》始已设有史抄一类。再向前追溯,则可至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龙图阁书目》,《玉海》卷五二引《实录》载宋真宗至龙图阁观书,其史传阁已在杂史之外别设史抄一类。[10]知设置史抄类当是宋代官修书目的通例,但《崇文总目》未设,晁公武废史抄而别立史评类,又称“今世抄节之学不行而论说者为多”,考虑的更多是当时的学术背景与文献多寡。
袁本《郡斋读书志》史评类著录文献十四部,为《史记索隐》《唐书直笔》《唐书新例须知》《唐书音训》《唐书辩证》《唐史要论》《西汉发挥》《唐鉴》《注唐纪》《唐史评》《五代史纂误》《三国人物论》《历代史辨志》《刘氏史通》。[11]从书名及晁氏解题来看,既有简单的史书比较(如《唐书新例须知》解题“记《新书》比《旧》增减志传及其总数”),也有对史书的音义注解(如《注唐纪》解题“所注《新书》纪也”)、辨正讹误(如《五代史纂误》解题“皆《五代史》抵捂阙误也”)、议论得失(如《唐书辩证》解题“数《新书》初修之时其失有八类,其舛误二十门”),更有发凡起例(如《刘氏史通》解题“叙其体法”)之作,是“扬榷史法”与“讥评得失”兼备,殊合总称“论史”之义,也符合“史评”类目之名。惟其中《唐鉴》一书,乃范祖禹“为温公《通鉴》局编修官十五年,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著成此书”,实际上是范祖禹新编的编年体唐史,故《直斋书录解题》入于编年类。
赵希弁《读书附志》亦设有史评类,著录《读史管见》《读史明辨》《史说》《史评》《西汉鉴》《两汉博议》《唐史论断》《唐论》等八部。[12]如《读史管见》解题称:“司马文正所述《资治通鉴》,事虽备而立义少,遂用《春秋》经旨,尚论详评。”合乎“扬榷史法”之义,其他各书则史论、史说、史评均有之,其著录亦合“论史”之意,可以视为是对晁公武的步趋。
衢本《郡斋读书志》延续了袁本设立的史评类,共著录文献二十三部,相比袁本而言,增加了《史通析微》《历代史赞论》《唐书音义》《古史》《两汉博闻》《三刘汉书》《东汉刊误》《吕氏前汉论》《晋书指掌》等九部。[13]从所增加的文献来看,在文字音义(如《唐书音义》)、刊误(如《东汉刊误》)、解释评论(如《两汉博闻》《吕氏前汉论》)等著作之外,还加入了如《历代史赞论》之类“纂《史记》迄《五代》史臣赞论”的总集,《古史》之类“始伏羲,讫秦始皇帝,为七本纪、十六世家、三十七列传”的通史,《晋书指掌》之类“以《晋书》事实,以类分六十五门”的类书等其他性质的文献。此类书虽有史名,而实同史抄,晁公武既已废史抄类,而将此类著作移入史评类,无疑扩大了史评类著录的范围。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史评类的设置,使得史评著作得以单独立类,既开创了史部新的类目,也改变了原有的文史类文、史并著的观念,而其著录文献的扩充,也使得史评著作从最早仅“扬榷史法”发展为更广泛的“讥评得失”。史评类的设置影响深远,如尤袤《遂初堂书目》别立史学类、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设有史评史抄类以著录史评著作,且此二目虽仍保留了文史类,但均未收录史评著作。王应麟《玉海·艺文》也设有“论史”,其著录虽多繁杂,但仍可见是以史评著作为主。
史评、史学,强调的都是对于史部文献的评论,由此而形成一批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从其讨论的对象来看,主要集中于正史,如《史记》《汉书》《晋书》《唐书》《五代史》等,既包括对于史书著作的凡例讨论(如《史通》《史例》)、对文字音义的是正刊误(如《东汉刊误》《五代史纂误》)、对史事的注释讨论(如《史记索隐》《唐史要论》),还包括其他各体对于史书的新编汇录(如《唐鉴》《历代史赞论》),以及多部史书的对比探讨(如《唐书新例须知》)。从最初“扬榷史法,著为类例”而依附文史类的史学著作,到南宋以降“讥评文人得失”而得以独立的史评类将史法与议论并著,史评类的著录标准不断变化,著录范围也不断扩大。
从《崇文总目》将史评著作附于杂史类,到《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等别立史评、史学类,史评著作得以从杂史类与文史类中独立出来,而归属于史部单独一类。史评著作的独立是目录学部类发展的趋势,一方面为史部增加了新的类目和文献,扩大了史部的著录范围,反映出史学研究的丰富成果;另一方面也促成了衢本《郡斋读书志》文说类的设立,进一步肃清了文史类原本混淆杂乱的概念,为后世书目中诗文评类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三、“言文章体制”与“讥评得失”:衢本《郡斋读书志》文说类的设立
袁本《郡斋读书志》未设立文史类,其相关文献分置史评类与别集类,赵希弁《读书附志》亦对此步趋,至姚应绩重编衢本《郡斋读书志》,始在集部设立文说类。孙猛曾考证衢本《郡斋读书志》的解题文字多出自晁公武之手,但未曾考证其新设的部类是否同样出于晁氏;[14]郝润华则称:“晁公武还补撰了不少小序,对《郡斋读书志》作了一部分重新编排组织工作,如增设新的类目,调整某些不合理归类和编次等。”[15]但多为推测,并无确证。
姚应绩为晁公武门人,衢本即出自其手编,则此文说类之设立,非晁公武即姚应绩所为。将袁、衢二本对照,衢本在类目设定上最大的创新与突破,即在于将子部天文历算类析为天文、星历二类①,与集部新增文说类。相比袁本,衢本天文类《司天考占星通元宝镜》解题末增“故予所藏书中亦无几,姑裒数种以备数云”[16],孙猛认为“乃天文类、星历类小序”[17]。但此书解题,除衢本所增此句外,袁、衢二本文字基本相同,袁本原作“皇朝兴国中,诏天下知星者诣京师,未几,至者百许人,坐私习[天]文,或诛,配隶海岛,由是星历之学殆绝”[18]。细审此文,是以天文、星历为一,实为对天文星历类的小序,衢本所增,正是延续上文,合而为一,恰恰是衢本对天文星历类完整的小序。也就是说,袁本本有天文星历类的小序,衢本不过是略加补充,所补充的内容亦非重要。如果晁公武将原有的天文历算类析为二类,则其小序当分别重撰,各置本类首书解题之下,而不至于不作大的修改,且仍附在天文类首书解题下。那么,将天文星历析为二类,恐怕不是晁公武而是姚应绩所为。若然,则文说类也当非晁氏所加。
此外,如果是晁公武将天文星历析为二类,那么,对于《郡斋读书志》中最为创新而增设的史评类与文说类,晁氏均应新增小序加以表彰。但衢本仅在史评类首书《刘氏史通》解题之后增加新的内容,可以视为史评类小序,是晁公武对于史评类设置的解释,而文说类则没有任何说明,也值得怀疑。故本文认为文说类并非晁公武所设,而是姚应绩重编时所增。但为免争议,本文仍概称衢本,不作区别。
衢本集部前有总序,其始称“集部其类有三,一曰楚词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19],未及文说类,与袁本相同。按衢本经、史、子三类总序其始作“经之类”“史之类”“子之类”,与此不同,鲍廷博称:“衢本经、史、子小序,与袁本微异,而集部独与袁本同,疑衢本佚集部,传钞者即以袁本补之耳。”[20]当是。从袁本所附衢本目录及文献著录来看,衢本实设有文说一类。
衢本文说类著录文献九部,为《文心雕龙》《修文要诀》《金针诗格》《续金针诗格》《李公诗苑类格》《杜诗刊误》《韩文辨证》《韩柳文章谱》《天厨禁脔》。[21]与袁本相比,系将袁本附于别集之末的《文心雕龙》《修文要诀》《诗苑类格》《韩文辨证》②等四部移置文说类,复增加《金针诗格》《续金针诗格》《杜诗刊误》《韩柳文章谱》《天厨禁脔》五部,而未著录《艺圃折衷》。按郑厚《艺圃折衷》六卷,袁本解题未涉其内容,陶宗仪纂《说郛》收入节本,包括“论君臣”“汤武”“伊周”“扬雄”“孟子”“孔孟”“古今未尝无小人”“神”“须眉发”九条③,并无涉及文章者。张宗祥重编《说郛》将其列在第三十一卷,依据他本增加了“诗”“无声乐”“王介甫”三条,其中“诗”条论列李白、杜甫、陶渊明、鲍照、孟郊、白居易等诗作特点,尚属文章评论。[22]实则此书包含各类讨论,并非专门的文论著作。但《中兴国史艺文志》文史类小序称“《艺苑雌黄》则并子史集之误皆评之”[3],是亦可入于文史类。衢本未著录,或是遗漏所致。④
从衢本解题来看,《文心雕龙》《修文要诀》为文学批评著作,《金针诗格》《续金针诗格》《诗苑类格》《天厨禁脔》为诗格著作,《杜诗刊误》《韩文辨证》为文字刊误著作。惟《韩柳文章谱》解题称:“右皇朝黄大舆撰。大舆之意,以为文章有老壮之异,故取韩愈、柳宗元文章为三谱。其一取其诗文中官次年月可考者次第先后,著其初晚之异也;其一悉取其诗文比叙之;其一列当时君相于上,以见二人之出处。极为详悉。”[23]从此解题来看,所谓三谱,其一、其三可以视为诗文编年,其二是将韩愈、柳宗元文章进行比较。其中只有第二谱有“比叙”之义,但其是否兼有评论,已无可知。衢本将其列入文说类,或以其通过编年与对比来见出其批评性质。事实上,这类著作与史评类中的《唐书新例须知》相似,都是通过两部著作的对比异同来表现出其评论的性质。
衢本《郡斋读书志》对文说类与史评类的设置,建立在其对文史类设置不合理的认识基础上。衢本于《刘氏史通》解题后称“前世史部中有史抄类,而集部中有文史类,今世抄节之学不行而论说者为多,故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为史评,附史部,而废史抄云”[4],强调的是“抄节之学不行而论说者为多”,所以才取消史抄类而设置史评类,其更多是基于现实层面的考虑。由此也可以推测,前志之中集部原有文史类,现在史评著作的部分既已独立,则其文论著作的部分也应加以重新归纳。袁本取消文史类,将文论著作附于别集,只能被视为是晁公武对部类设定考虑未成熟下的权宜之计,衢本有鉴于此而新设立文说类,正是为了汇录文章论说的著作,以与史评类相对应,从而展现出文史类分化为史评与文说两类的发展轨迹。“文说”仅是此类著作的代称,选择“说”而非其他成词,或许正是为了与史“评”相对应。
衢本《郡斋读书志》文说类的设定,是对原有的文史类的修正,但另一方面,文说类的著录标准仍受到前志的影响。宋国史艺文志中列有三种文史类小序,其中《三朝志》小序称“言文章体制”“述略例”,《中兴国史艺文志》小序称“文史者,讥评文人之得失也”,[3]显示出两宋目录学对于文史概念界定的动态变化,从强调体制、略例发展为评论得失。仅从衢本文说类著录的文献来看,正好与史评类形成对应。前文论及衢本所著录史评类文献,既包括史法,也包括评论得失之作,文说类著录的文献与此正相对应,如《文心雕龙》《修文要诀》等是对文章写作之评论,《金针诗格》《续金针诗格》《诗苑类格》《天厨禁脔》是对诗格之评论,均属于“言文章体制”,相当于“文法”的范畴;《杜诗刊误》《韩文辨证》是对文字之考正,而《韩柳文章谱》则是二人著作的编年、对比,更多是“讥评得失”。从这一角度来说,文说正与史评相对应,“说”也就有着“评”的意味。《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著录《文说》一卷,称:“南城包扬显道录朱侍讲论文之语。”[24]“文说”实同“论文”,正与“史评”同于“论史”相应。
前述《崇文总目》虽设文史类,但史评著作附庸杂史类而不入文史类。衢本《郡斋读书志》文说类的设立,其实正延续了《崇文总目》对于文、史分离的思考,这一做法,无疑打破了北宋书目中文史类的著录标准,从而肃清了史部、集部的概念,使得集部重新回到文章范畴。后出书目如《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虽因仍文史类名之旧,但均未在文史类著录史评著作,其性质实同文说类。但细考此类书目著录的文献则会发现,其著录标准已不同于《新唐书·艺文志》等早期书目的文史类,而是重在对其加以修订,著录范围也在扩大,尤其表现在对刊误之作的著录上。
四、刊误与文论的重新界定:校勘学视野下的“讥评得失”
衢本《郡斋读书志》虽设置了文说类,但其著录的文献实际上仍属繁杂,主要体现在《杜诗刊误》《韩文辨证》《韩柳文章谱》等著作上。此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论著作,而是在宋代校勘学发展下的新兴产物,与前述史评著作中对于文字、音义、史事的刊误考辨一样,均可以视为馆阁与个人校勘的产物。李更认为:“在校勘学史上,如余靖《汉书刊误》、刘攽《东汉刊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张淳《仪礼识误》、毛居正《六经正误》、方崧卿《韩集举正》、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等一系列由专书校勘记汇录而成的校勘专著的出现,是宋代校勘趋向于独立的重要体现。”[25]又称:“这种学术传统,在南宋学者的个人治学和书籍校刻当中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出现了如南宋初洪兴祖《离骚楚辞考异》,稍后方崧卿的《韩集举正》、朱熹的《韩文考异》、毛居正的《六经正误》、张淳的《仪礼识误》等一大批校勘专书。”[26]表现出刊误之作从馆阁到个人、从经史到集部的发展过程。李更所举的例证,如《汉书刊误》《东汉刊误》《两汉刊误补遗》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均被著录在史评史抄类下,《韩集举正》《韩文考异》则在赵希弁《读书附志》中附于别集类。从袁、衢二本所附文论著作来看,赵希弁之附录也应被视为文论著作,与袁、衢二本所著录的《杜诗刊误》《韩文辨证》相同。
所谓刊误,实同校勘,刊误之作更是对校勘结果的集中汇总。从这一角度来说,所谓对文字、音义的注释、是正,对史事的辨谬、补正,以及对不同著作的对比,都可以归入刊误之作的大范畴。仔细考察此类著作的性质会发现,其刊误仍然依附于史书、别集而行,与归属于总集类的选本评点相似,均非纯粹的文论著作。李更认为:“校勘脱离章句注疏作为一门单独的学问独立发展,是从馆阁以刊印颁行为目的的史书校勘开始的。”[27]着重强调其与章句注疏的不同及其独立过程,但校勘与章句注疏都需要依附于特定的文本,即使别本单行,也需要参照其原所依附的文本才得以在事实和学理上存在,也才具有其价值。从这一角度来说,刊误之作并未能真正脱离史书、别集而独立存在,其性质仍然需要依附于原书才得以彰显。衢本《郡斋读书志》在史评、文说类中著录刊误之作,可以视为是对此类著作性质的重新审视与认定。
尤袤《遂初堂书目》在史部设立史学类,所著录的文献标准同于衢本《郡斋读书志》,既包括《史通》《史例》之类“扬榷史法”的史学著作,也包括《史记音义》《两汉刊误》之类“讥评得失”的文字刊误著作;其文史类著录,除《文心雕龙》之类“言文章体制”与诗话著作外,还包括《文选同异》《诗史音辨》《诗史总目正异》⑤等与刊误相关的著作,可以视为是对衢本《郡斋读书志》的借鉴。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在史部设史评史抄类,著录衢本《郡斋读书志》史评类与《直斋书录解题》正史、编年等类的相关文献,可以视为是对史评类文献的补充与扩大;其文史类亦同于衢本《郡斋读书志》,著录《杜诗刊误》《韩文辨证》《韩柳文章谱》等刊误之作。从部类划分与文献著录来看,《遂初堂书目》与《文献通考·经籍考》这一做法受到衢本《郡斋读书志》的影响最大。其他如《玉海·艺文》设有论史一类,亦多有校订刊误之作。
但衢本《郡斋读书志》文说、史评二类的设置及其著录刊误之作的标准并未得到目录学界的完全接受,《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未设立史评类。在郑樵《通志·艺文略》中,与刊误相关的著作被附入史部各类,主要集中在正史中;又于正史类另设通史这一三级类目,著录《史通》《史通析微》《正史杂论》《史例》等,于文史类著录《柳氏释史》《史例》《史汉异议》《唐书直笔新例》等史评著作,可以视为对史评著作性质的认识尚未明确,也反映出宋代目录学者对于史评著作著录标准的多种思考与犹疑。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与《通志·艺文略》相同,史评著作也被依照各书性质附入史部各类,如《史记音义》《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三刘汉书标注》《唐书直笔新例》《唐书音训》《唐书纠缪》《五代史纂误》《两汉刊误补遗》等与正史相关者入正史,《通鉴释文》《唐史论断》《唐鉴》《读史管见》等与《通鉴》相关者入编年类,《迁史删改古书异辞》《马班异辞》等入类书类,《史通》《史通析微》《史例》则仍入文史类。凡此之类,《文献通考·经籍考》则均收入史评史抄类。详细考察可知,《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中著录的史评著作,显系效仿《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之著录体例,均为“扬榷史法”之作,刊误之作则被依照其所刊误对象之性质而各归其类。
《通志·艺文略》文类设有文史与诗评两种,除在文史类中著录史评著作外,并未著录与刊误相关的著作,其别集类中也未著录别集刊误著作,或以其不便分类而径删。《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因仍《新唐书·艺文志》之旧,同时著录文论与史评著作,但未著录与刊误相关的著作,而在别集类上著录了黄伯思《校定杜工部集》、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校定韩昌黎集》、葛峤《柳文音释》、郑定《重校添注柳文》、张敦颐《韩柳音辨》等著作,从其解题如“既正其差误,参考岁月,出处异同”,“校其同异”,“凡异同定归于一,多所发明”来看,是亦与刊误相关。[28]此外,别集类尚有陶渊明、韩愈、白居易、李靖、晏殊、欧阳修、三苏、曾巩、张耒、叶梦得、周必大、朱熹、倪思等人,诗集类有苏轼、黄庭坚等人之年谱,亦对传主生平事迹、诗文系年等有所考辨,凡此之类,也略同于衢本《郡斋读书志》“文说”的概念。
《宋史·艺文志》取材于宋四部国史艺文志,其史部未设史评类,与《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相同,史评著作亦各散入史部,如《汉书刊误》《晋书音义》《史记正义》《新唐书纠缪》《五代史纂误》等与正史相关者入正史类,《通鉴释文》等入编年类。其文史类著录,基本为文论、诗话与史评著作,标准同于《直斋书录解题》等,但其末尚附有曾发《选注摘遗》《李善五臣同异》、彭郁《韩文外抄》、赵师懿《柳文笔记》、彭郁《韩文会览》等书。从题名来看,前二部著作是关于《文选》的注释与其异同,《柳文笔记》应当是对柳宗元文章的杂记。《韩文外抄》《韩文会览》均为彭郁所作,《玉海》卷五五载“彭郁《会览》四十卷、《外抄》八卷”[29],欧阳守道《彭石庭〈韩文览〉序》亦称“石庭彭君乃取其先君子大庾君所著《韩文会览》加损益焉”[30],《直斋书录解题》别集上著录《外抄》八卷,解题称:“及葛峤刻柳文,则又以大庾丞韩郁所编注诸本号《外集》者,并考疑误,辑遗事,共为《外抄》刻之。”⑥《文献通考》著录同[31],乃是误“彭”为“韩”。从《直斋书录解题》来看,《外抄》系彭郁对韩文诸本的重新编注,《韩文会览》或亦相同。则此数部文献,都与校注刊误相关。《宋史·艺文志》别集类复著录薛苍舒《杜诗刊误》、祝充《韩文音义》、朱熹《韩文考异》、樊汝霖《谱注韩文》、洪兴祖《韩文年谱》《韩文辨证》、方崧卿《韩集举正》、张敦颐《柳文音辨》、杜田《注杜诗补遗正缪》、薛苍舒《续注杜诗补遗》、洪兴祖《杜诗辨证》等,也均与校注刊误相关,表明《宋史·艺文志》编者以此类著作多附庸别集之下。
《宋史·艺文志》在文史类之末所附的几种刊误著作,似乎自乱其著录体例,这与其汇录宋国史艺文志文献而未作细致整理相关。⑦此数部列在文史类之末,当系来自《中兴国史艺文志》。前引《中兴国史艺文志》文史类小序,对于著录内容的介绍最为驳杂,而《宋史·艺文志》文史类前部分所引的文献来自于《三朝志》《两朝国史艺文志》《四朝国史艺文志》,著录标准相对统一,尚未掺入刊误著作。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宋代四部国史艺文志在文史类著录上的不同标准与体例。
总体来说,对于文史类的文献著录,宋代书目表现出两种趋势,一种以《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为代表,在集部设立文史类,同时著录文论与史评著作,但多局限于体现义例者,也就是文法与史法著作,其他刊误著作则依其所刊误的对象性质而分别归入正史、编年、别集等类,这种著录标准更接近于《三朝志》文史类小序。一种以衢本《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为代表,其将文史类析为文说(或文史)与史评(或史学)二类,文说(或文史)类著录与文法、刊误相关的著作,史评(或史学)类著录与史法、刊误相关的著作,这种著录标准更接近《玉海》所引《国史志》与《中兴国史艺文志》文史类小序。两种分类间的最大区别,除了史评类的独立外,还在于刊误之作的归属。前者以其所刊误对象的性质而附入各类,后者则著录于文说(文史)、史评(史学)类中,似乎更看重其刊误讥评得失的评论特点。
但事实上,后者所采取的归类,也有着自乱著录体例的嫌疑。在宋元各书目中,与史、集二部刊误著作性质相同的经部刊误著作,均各归其类,而未在经部单独设立一类以著录,显示出与史评、文说类不同的著录标准。衢本《郡斋读书志》设立史评、文说类,在于对文史类设置不合理的修正,但这两个类目的著录标准,则从前志中最开始的强调类例著作,转而倾向于同时著录讥评得失的著作。当然,仅从讥评得失的角度来说,刊误著作自然可以被纳入到这两个类目之中,但这一设置本身就使此二类的著录标准变得驳杂。北宋新出的刊误著作与南宋新出的评点一样,都可以被视为具有评论的性质,但后者更强调其对选本的依附性,前者也无法脱离其刊误的文本对象。史评、文说类的设立固然使文、史得以分离,但也造成了文献著录标准的进一步驳杂混乱。
注释:
① 袁本《郡斋读书志》子部总序称“天文历算类”,正文作“天文卜算类”,赵希弁《读书附志》亦作“天文卜算类”,然移置史部;其《后志》录衢本目录作“天文类”“星历类”,正文作“天文历算类”;衢本子部总序称“天文”“星历”,正文作“天文类”“历算类”。疑袁本实当作“天文历算类”,故赵希弁录衢本所增时仍因习未改;正文作“天文卜算”者,疑为赵希弁所改。衢本作“天文类”“星历类”,更符合其小序所言。
② 《诗苑类格》,袁本《郡斋读书志》作《诗菀类格》;《韩文辨证》,袁本《郡斋读书志》作《韩文辩证》。
③ 据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明嘉靖沈瀚抄《说郛》六十九卷本,《艺圃折衷》在该馆所编第二十三册第二卷,原未标卷数;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借树山房原藏抄本(A01507)系节抄沈瀚抄本,《艺圃折衷》在其第一册末,复题“卷五”,未知何据。
④ 根据赵希弁的整理,袁本《郡斋读书志》所载而衢本所遗者有二十九部,见袁本所附《二本四卷考异》。
⑤ 《诗史总目正异》,或作《诗史总目正要》。有关《诗史音辨》《诗史总目正异》的刊误性质,可参见郭绍虞著,蒋凡编.宋诗话考[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93.
⑥ 此节据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直斋书录解题》抄本(06802),“钞”均作“抄”,“考”下无“校”字,从之径改。
⑦ 有关《宋史·艺文志》与宋代国史艺文志的关系及具体文献推原原则,可参见翟新明.从小说到文史——宋代书目中诗话的归属与位置变迁[J].北京社会科学,2019(1):44-54;宋国史艺文志及其集部著录新变考析[C]//.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17-136.又可参见马楠.离析《宋史艺文志》[C]//.唐宋官私目录研究.中西书局,2020:135-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