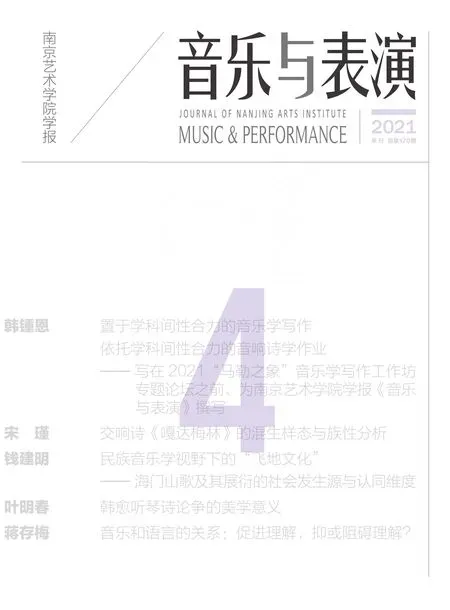“心理描写”构成20世纪舞剧创作的重要支柱 ①
—— 杨少莆舞蹈美学思想述评
2021-12-01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江苏南京210013
于 平(南京艺术学院 舞蹈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杨少莆的舞蹈美学思想,可以说是基于“芭蕾艺术美”的思想。鉴于“芭蕾”并不仅仅指“外开、直立、轻盈、清晰和不言自明”(美国舞蹈美学家塞尔玛・珍妮・科恩语)的“古典舞蹈风格”,自诺维尔之后,它更被视为一种“舞蹈叙事艺术”的舞剧。因此杨少莆的舞蹈美学思想,更体现为基于“芭蕾叙事”的“舞剧艺术观”。杨少莆“写舞”的文字虽未结集出版;但鉴于他用笔甚勤、运思亦深,且笔耕不辍达二十余年(1982—2004),对舞蹈学术界、特别是对中国芭蕾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不可轻忽的影响。
一、从“写意的风格”到“抒情浪漫的格调”
杨少莆第一篇“写舞”的文字,刊发于1982年第1期《舞蹈》杂志。或许那时他已有相当的知识积累和学术思考,但亮相的文字明显让人感到是“出来乍到”的新手,因为文章都没有认真琢磨一个标题(那时还没有现在热衷于抓人眼球的“标题党”),标题就叫《介绍芭蕾舞剧<黛玉之死>》。《黛玉之死》是独幕芭蕾舞剧,由中央芭蕾舞团创演,编导是李承祥和王世琦。作为《红色娘子军》主创之一的李承祥,此时已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他与舞剧《鱼美人》主创之一的王世琦联手创编该剧,引起了舞蹈界极大的关注。这之后更在《黛玉之死》的基础上,创编了大型芭蕾舞剧《林黛玉》。确切地说,《黛玉之死》后来成了《林黛玉》的第四幕。从舞蹈学术界的评价来看,大型的《林黛玉》远不如独幕的《黛玉之死》;而《黛玉之死》的“精彩”是促使杨少莆动笔“写舞”的重要缘由。他在文中写道:“芭蕾舞剧《黛玉之死》的帷幕一拉开,就以强烈的悲剧色彩、感人的艺术形象阐发了舞剧的主题,攫住了观众的心……喜庆的乐曲远远飘来,黛玉又陷入了幻觉,喜堂景象缓缓展开:对对莲花宫灯引出一双新人——木然的宝玉和端庄的宝钗。一段不和谐的双人舞,令人信服地标示出宝玉、宝钗之间理想的差距,游离于婚礼之中的是一股黯然的意味;黛玉抑制不住地奔来,三个人各自的痛苦心境在舞蹈中得以体现……芭蕾舞剧《黛玉之死》以黛玉为主线,捕捉住主人公病危弥留之际的瞬间,展示了幅度宽广的画面——剧中除紫鹃外的全部人物,都在黛玉的想象和幻觉中出现;舞台场景并无变换,人物来去自然,艺术结构浑然一体,笔法简洁而寓意颇深……黛玉的两段独舞是刻画人物的主要段落,编舞设计着重于心理描写;动作虚拟地表达出人物总的情绪,而不追求一举手一投足都说明什么含义,写意的风格贯穿舞剧的结构和舞蹈设计……”[1]
杨少莆高度认同《黛玉之死》的创编理念,一是(除紫鹃外)全部人物都在黛玉的想象和幻觉中出现,这里说的是“结构”;二是“编舞设计着重于心理描写”“动作虚拟地表达出人物总的情绪”,指的是“语言”。杨少莆高度认同的,是“写意的风格贯穿舞剧的结构和舞蹈设计”。那时我们还不用“心理舞剧”这个概念,以“写意的风格”来区别“哑剧的写实”。若干年后,杨少莆参与了芭蕾舞剧《雁南飞》(根据电影《归心似箭》改编)的构思,他在《耕耘与收获——<雁南飞>创作谈》中写道:“从根本上说,《雁南飞》是一部表现心理冲突的戏。摆在主人公面前的‘去与留’的矛盾尽管十分尖锐,却仅仅是人物感情与理念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外部干预的戏剧因素……目前形成于舞台上采用的是传统戏剧芭蕾结构方式,却又不拘泥于顺叙式的时空观念;根据情节所需比较自由地插入倒叙、闪回、化出等手段,将人物情绪、情感、心态表象化……(目前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以‘心理情感’冲突为主线的结构方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抒情浪漫风格,同戏剧情节的铺陈之间存在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我以为要在重新统筹全剧题旨、戏剧主线、人物个性及相互关系的前提下,增设必要的情节,使得人物形象在情节活动中丰满起来,并给予感情主线的渐次推进以足够的铺垫;与此同时,对戏剧情节的处理又要追求舞蹈化、情绪化、虚拟化、写意化,以达到风格统一于全剧抒情浪漫的格调。”[2]通过参与《雁南飞》的构思及该剧演出的反思,杨少莆对舞剧艺术“本体性”的言说方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既要“使得人物形象在情节活动中丰满起来”,又要“追求舞蹈化、情绪化、虚拟化、写意化”的“情节处理”。这时他已不说“写意的风格贯穿舞剧的结构和舞蹈设计”,说的是“统一于全剧抒情浪漫的格调”。
二、舞剧需要能巧妙抵达“主题”的戏剧性
其实,杨少莆对“戏剧芭蕾”经典剧目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也对之取高度认同的态度——这可以从他对《海盗》和《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的分析中看出。他在《<海盗>琐谈》中写道:“《海盗》(1959年我国初演时译为《海侠》——引者)的特色是什么?笔者认为,一是粗犷的艺术线条;二是扣人心弦的戏剧结构;三是多样化的人物形象……《海盗》的剧情惊心动魄,一环扣一环:风暴、沉船、侥幸生还的康拉德面临敌军追捕;见义勇为的米多拉掩护了海盗首领,自己却落入人贩子之手;在奴隶市场上,被拍卖的米多拉,奇迹般被康拉德救走;贪财的比尔邦托叛变后煽动暴乱,又设谋将米多拉抢去;乔装的康拉德深入敌舰侦察为叛徒识破,千钧一发之际海盗偷袭成功,一举歼敌;康拉德与米多拉终于幸福地相会,却又险遭比尔邦托孤注一掷的暗算……真是跌宕起伏、险象丛生。古典芭蕾理论的天才奠基人诺维尔主张,舞剧不能成为舞蹈家单纯技巧表演的手段,他强调能感染观众的‘戏剧性’原则也应该成为舞剧创作的信条。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看:《海盗》的艺术成就就是实践诺维尔理论的一个积极成果。”[3]
稍后,杨少莆又深思熟虑地撰写了《隽永的芭蕾长诗<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这部历来简称为《泪泉》的“戏剧芭蕾”经典,是根据普希金的同名长诗改编的(正如《海盗》由拜伦的长诗改编而来)。杨少莆写道:“这部无论思想的深刻性、艺术的表现力都无愧于原著的舞剧,是长诗在芭蕾舞台的忠实体现。它充满浪漫主义的抒情色调,渗透着深邃而绵密的诗情……舞剧既是一门戏剧,就必须遵循戏剧艺术的构成原则,要求作者精于提炼、巧于构思、善于运筹。《泪泉》的构架就是依据戏剧的基本规律搭起来的,设有尖锐复杂的冲突、渐次展开的情节、错综巧妙的人物关系。全剧含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每一幕乃至每一段舞也如此,舍弃了游离于剧情发展之外的多余的舞蹈和场面;因而结构紧凑、层次清晰,充满诗情画意的舞蹈场面都具有丰富的内涵……舞剧的高潮设在仅有少数人登场的第三幕,更显得别出心裁。在这里不靠热烈的群众场面烘托,没有绝技迭现的精彩舞段,完全依赖于音乐的表现力和表演者浓重的内心体验,造成一种独特的艺术氛围……对‘玛利亚之死’的处理就是产生于这种超乎寻常的运笔……玛利亚在受扎列玛致命一刺时,表现出一种无怨的平静,毫不痛楚地迎接死神的到来,手扶圆柱缓缓地倒了下去……使人感到她那颗破碎的心在欣然一死中得到弥合,也使人理会了死者对凶手的宽宥和怜悯……按理说,玛利亚一死,戏剧矛盾就此完结,可以画句号了。但作者显然认为,悲剧的价值绝非限于哀悼一盏纯洁的生命之光熄灭,而在于她照亮了一个黑暗的灵魂。那么,作者是怎样表现这一题旨呢?反衬的手法!也即用努拉里鼓动起嗜血的征战狂热去刺激统帅的心……果然吉列依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挥舞起战刀冲向前去——努拉里期待的效果发生了!但是,吉列依又突然凝滞了,像被一个声音所呼唤……屠刀从那松软的手臂里跌落在地,预示战神再也不能附着于吉列伊的躯体,永远地!多么巧妙啊!舞蹈就这样融进了舞剧主题!”[4]一个《海盗》,一个《泪泉》,可以说给杨少莆烙下了“何谓‘芭蕾舞剧’”的深深烙印!舞剧需要能感染观众的“戏剧性”,舞剧还需要戏剧性能巧妙地抵达舞剧“主题”!因此,杨少莆虽然为贯穿“写意风格”的《黛玉之死》而首肯,但在面对《雁南飞》时仍然认为要“增设情节”以便“丰满人物形象”!
三、舞剧创作要遵循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理逻辑
1994年是北京舞蹈学院建校四十周年,也是该校在苏联专家古雪夫指导下创编的大型舞剧《鱼美人》问世三十五周年。学院决定以该剧的复排作为校庆的重点项目。杨少莆关心这件事,不仅因为该剧问世之时的1959年他就在学院的前身“北京舞蹈学校” 就读,也不仅因为在该剧问世二十年之际的1979年由中央芭蕾舞团复排了此剧;他由此而想到的是“中国民族舞剧创作”和“芭蕾中国学派”的问题。杨少莆以笔名“邵府”发表了《〈鱼美人〉与中国民族舞剧创作》一文,其中写道:“……抛开《鱼美人》是否仿照《天鹅湖》不谈,说它是依欧洲特别是苏联芭蕾舞剧模式的‘葫芦’,画出的一个贴有中国标签的‘瓢’却不假。《鱼美人》本是一个杜撰的故事,没有文学原著也没有民间传说做依据,这倒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它所设定的内容,是流传于欧洲的那种千篇一律的童话的翻版,是一个脱离于中国人生活逻辑和心理逻辑的产物……但是,《鱼美人》又是一部有着灿烂的表现色彩的舞剧,在中国舞剧发展上也有着独特的贡献。《鱼美人》的艺术创作体现了一次大胆的无拘无束的‘拿来主义’实践,它的创作者敢于拈取各式各样的舞蹈素材,而不以民族或地域为限,在舞台上描绘了一个多彩的舞蹈世界,因此把舞剧创作的想象力推向了一个新境地。在《鱼美人》之前中国已有舞剧诞生,如《宝莲灯》。那是在传统的中国戏曲基础上衍化出来的舞蹈剧,不仅语汇受到戏曲影响,内在结构、叙事方法和表达方式也没有离开母体多远。可以说,《宝莲灯》从内容到形式是完全中国式的。唯其如此,它也受到无形的束缚,没能朝向根本意义上的舞剧化迈出更大的步伐。对比《鱼美人》和《宝莲灯》,看到的似乎是中国民族舞剧的两个侧面——丰富的舞蹈表现却没有深植于民族文化土壤,注重传统文化根基又没有摆脱戏曲舞蹈格式的拘束。是不是可以说,中国民族舞剧的成功之道正在于使二者结合呢?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才面世的《阿诗玛》——它是那样地富于民族特色,又是那样的富于舞蹈特色,称其为‘中国民族舞剧代表作’当不为过……”[5]
在思考“中国民族舞剧”应如何创编的同时,杨少莆其实更关心“中国芭蕾舞剧”的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肯《黛玉之死》、又在20世纪90年代初反思《雁南飞》之后,他认为应当更深入地认识芭蕾舞剧《祝福》的价值。舞剧《祝福》是中央芭蕾舞团纪念鲁迅先生一百周年诞辰(1981年)的创作,是《红色娘子军》主要编导之一的蒋祖慧根据鲁迅先生同名小说而改编。杨少莆以《祥林嫂的人生转折》为题来“回顾舞剧《祝福》兼谈中国芭蕾创作”(副标题)。他写道:“《祝福》是20世纪80年代首先在中国推出的心理描写的一部舞剧。它承续了国际上这一创作趋势,在第二幕的重点舞段——祥林嫂与贺老六的双人舞及各自独舞中,以中国式的情感递进,很细腻很精心地演绎了一段人物性格、理念和情感碰撞的过程。如果用文字简要地标示这段充满心理矛盾的舞蹈,那就是:祥林嫂触桌角以自戕,使得贺老六顿陷尴尬境地——用积攒多年的血汗钱‘娶’来的媳妇,竟是一个为暴力胁迫且性情刚烈的弱女子,于是她的去留便成为摆在贺老六面前的十分艰难的选择。以他的善良是不愿、也不能强使祥林嫂留下来;而从他的苦境与同病相怜的感情出发,他又多么盼望和需要她留下来。同样,苏醒过来的祥林嫂也面临一次人生选择。要么遵从理法观念(这已形成她身上根深蒂固的自觉)宁死不改嫁;要么服从内心的渴求,与一个敦厚善良、对自己体贴理解的男人相依为命。何去何从在二人心中似沸水翻腾,并以舞蹈的形体韵律表达出来。舞台上人物一来一往,都是循‘抉择’而展开的,那便是作者描画的人物之心理轨迹。《祝福》的特色之一便是中国式的表达,即用情感递进、层层剥笋地展示心理变化,如有一条潜线浓浓淡淡、淡淡浓浓地勾画下来,使我们看到体贴、同情、谅解对方在男女主人公情理转折中发生着巨大作用,这是中国的道德观合着东方的含蓄在舞台上泛起的一道雅辉,最终解决了两位主人公的难题……”[6]22《祥林嫂的人生转折》一文发表在《〈鱼美人〉与中国民族舞剧创作》的三年之后,应当包含着对《鱼美人》舞剧创作的反思——杨少莆站在20世纪20世纪90年代“心理舞剧”的创作高度,指出《鱼美人》的要害在于它是一个“脱离了中国人生活逻辑和心理逻辑的产物”,同时更指出是“中国的道德观合着东方的含蓄……最终解决了(《祝福》)两位主人公的难题”。两文透露的主张,对于中国民族舞剧创作以及“芭蕾中国学派”建设已是不言自明的了。
四、“戏剧性朝着人物内心发展”是芭蕾的巨大飞跃
实际上,杨少莆《祥林嫂的人生转折》一文是在国际芭蕾创作的大视野下,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芭蕾舞剧创作趋向的全面审视。如他在文中写道:“……无独有偶,同一时期的中国芭蕾创作,尽管选材、风格、体式、手法有异,但注重心理描写的趋向却不约而同地一致,这一点颇耐人寻味。譬如:同样取材小说《祝福》的舞剧《魂》,追寻祥林嫂的心理历程,亦步亦趋地描绘主人公的精神重负:‘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作者简直是掏出祥林嫂心窝里的死结,亦即桎梏中国妇女的传统道德,血淋淋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林黛玉》首先以其第四幕《黛玉之死》问世,借黛玉弥留的瞬间展示了幅度宽广的画面,所有人物在主人公幻视幻听中出现,意识流手法将主人公殚精竭虑追求爱情的情状描绘得栩栩动人,‘宝黛悲剧’的根由也便揭示出来。《雷雨》将一部底蕴深厚的话剧搬上芭蕾舞台,仅八个登场人物活灵活现地演化了性格的对峙、感情的冲突,因而心理活动成为舞台表演的主要根据;其中尤以繁漪形象最突出——绵密的舞蹈运行,凸显了她的复杂和多层次的内心世界。《家》更是脱开传统戏剧结构和时空艺术观,不在情节上花费笔墨,而采用心理结构方法——即随人物心理和感情流向牵动剧情发展,着意写出人物内心活动,形成性格对比、心境悖逆、命运交错的错综复杂的画面。”[6]22-23
从《祝福》入手,进而分析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包括《魂》《林黛玉》《雷雨》《家》等一批芭蕾舞剧的创作构成,杨少莆特别看重的是这类“心理描写”舞剧产生的时代背景。首先是国内的背景:“正是‘文革’结束不久,整个社会犹如噩梦初醒,沉入了深刻的反思……在舞剧创作领域,一个深刻的变化即是对所谓‘样板戏经验’(内容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题范畴,形式上‘三突出原则’的表现手法)的反叛。‘样板戏’所立下的规矩随着社会畸形变态时期的结束而结束了;《祝福》及其同时代作品的诞生,把舞剧创作触角延伸到了生活更深层的角落,它们是摆脱‘样板戏’阴影的时代产儿……从人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概念出发,刻画人的共同本质,是这些舞剧所表达的新的舞剧观……《祝福》的编导(指蒋祖慧——引者)就谈道:她的创作动机直接来源于苦痛的经历。在干校的漫长日子里,她反复思索,痛感‘盲从’这种现代愚昧对人的精神摧残,不亚于旧礼教对祥林嫂的迫害……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看见了自己及同代人的影子,有种使命感迫切要求将之诉诸舞台。这是深层的悲哀,也是深层的觉醒。《祝福》酝酿构思的过程,就是用当代目光与心灵对一个旧故事的过滤。‘文革’使作者获得一项副产品——多了一层批判的心性,再不像她参加创作《红色娘子军》时那样,充满单纯的理想主义与超然的浪漫主义了。随新时期而来的另一气象,是艺术家们精神振奋,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吸纳能力空前增长……舞剧(芭蕾)演进到20世纪中叶,心理描写的技巧逐渐浸入创作领域,舞台上不再仅仅是戏剧动作或单纯性情绪的舞蹈,而是想方设法用形体——舞蹈艺术唯一和独特的表现手段——表述心理活动。或者换一种说法,舞蹈的肢体运动,变成了明确的心理活动的投影和外延。20世纪60、70年代世界舞坛出现的《奥涅金》《曼侬》《村居一月》《梅雅林》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白斯》,从外部形态的表面化表演,转向人物深层的探索,使得芭蕾美学品格实现了一次飞跃……戏剧性朝着人物内心发展,使选题超越了神话模式的简单贫乏与唯美表现;并且,因题材而突破了形式羁绊,又因突破形式而扩大了选题范围,形成良性循环。可以说,心理描写已构成现代舞剧创作观念的一个支柱。本文论及的中外舞剧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取材于文学名著,这当然不是偶然巧合。正是文学名著沉郁着人文气息、思辨精神、哲理性以及历史穿透力,为创作心像的构成提供了厚度……”[6]23-24在这里,杨少莆深度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初以《祝福》为代表的中国芭蕾创作的巨大飞跃,这个飞跃和本质便是“戏剧性朝着人物内心发展”!
五、“中庸文化”的性格模式与“中国芭蕾学派”
杨少莆《祥林嫂的人生转折》一文,是从舞剧《祝福》来审视中国芭蕾的创作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深层之处,是中国“芭蕾学派”建设的学理问题。舞剧《祝福》问世于1981年,《祥林嫂的人生转折》一文刊发于1997年;而在这之间的1988年杨少莆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即《风格、民族性与文化本源——也谈芭蕾学派》。杨少莆认为:“芭蕾学派的特征最终是透过舞台上演员的表演而得以体现,因而表演风格的差异才是判定学派之标尺。换言之,所谓‘学派’即是表演风格——非个体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群体性表演风格……迄今为止形成的各个芭蕾学派,虽然各异其趣,却是‘异姓同宗’,都建筑在西方‘文化-心理’结构之上……譬如芭蕾的姿态要素,就显示了历史上生活在欧洲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审美选择。自宫廷芭蕾时期就固定下来延续至今的姿态——向上、挺拔、舒张、伸展,代表着当时受到广泛模仿的思想品质;那种举止高雅与自命不凡的气质,体现着文艺复兴后期人的自我解放意识……腾空高跳、延伸至远的arabesque、绷脚及其顺理成章的发展——立起足尖,都是有放射性和憧憬式的特点……我们可以对芭蕾形态的构成做如下解析,即它是追求意念起生和外象表现,也是渴求自由解放和建立起超人业绩的思维模式的物态化或结晶体。”[7]27
将“学派”定义为“非个体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质和群体性表演风格”后,杨少莆想申说“中国芭蕾学派”特质之所在了。他提出:“深入探求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探求其对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塑造和影响,有助于我们在建设中国芭蕾学派的整体工程时更自觉主动而避免盲目性……例如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实用理性构成的性格模式,使中华民族获得并承续了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躁、贵领悟、重含蓄。一旦这种既不同于西方‘罪感文化’,又与印度‘涅槃文化’相异的中国独有的‘中庸文化’,作用于芭蕾演员和表演风格,就会透发出内向、娴静、细腻和更富人情味的艺术特色……提高芭蕾从艺人员的文化素质,在更深层次上开掘、透析无形而强大的文化本源的塑造力,必定能产生我们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展现深刻的民族个性。从厚重的中华文化积淀中跃出的民族之魂,附着于芭蕾艺术之体,这,便是中国芭蕾学派。”[7]28
六、三种演进型态与“中国芭蕾”的完整概念
与指认“中国芭蕾学派”的意涵相关,杨少莆撰写了《“中国芭蕾”什么样》的长文,从历史建构的反思对其美学趋向进行了考量。他指出:“从北京舞蹈学校创建算起,中国大规模引进芭蕾已近半个世纪。但明确的‘中国芭蕾’意识却是近十年才形成的。1950年戴爱莲首创,使芭蕾登上北京舞台——《和平鸽》振羽冲天,第一次用外来形式创作了一个中国式舞剧。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胡蓉蓉为代表)、哈尔滨等地就出现了学习芭蕾的先驱者,但自己创作大型的节目演出,《和平鸽》是第一个。且不说产生《和平鸽》的社会氛围使这部芭蕾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仅就其形态特征而言是套用外来形式,属‘套用型’。当时的社会反映是新鲜却不大被接受,主要是与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不契合——‘大腿满台跑,工农兵受不了’。这个时期当然谈不上‘中国芭蕾’的意识,因此《和平鸽》并未真正开始中国芭蕾的进程。朦胧的‘中国芭蕾’意识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受当时社会生活激扬着一股自力更生豪情的影响,在‘三化’的号召下,芭蕾艺术工作者不仅有了‘走自己路’的设想,而且创作出实现这一设想的具体作品《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红嫂》等。这些舞剧形式上以苏联的戏剧芭蕾为模本,注重根据生活塑造中国式的舞台形象,也注重从中国舞蹈素材‘化’出舞蹈语汇,属于‘糅合型’。此时的‘民族化’是与‘革命化’‘群众化’相联系的,革命化是第一位的衡量标准,而‘民族化’则只是附加值,否则作品不可能产生。《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问世似乎是‘民族化’的具象的答案;然而,在理论上仍然遗留了对芭蕾艺术形态本质的认识、对中西文化结合‘点’的确认以及中国芭蕾的文化价值观的定位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热潮激励中国芭蕾人,使他们目光放远,心胸开阔,有独树一帜的气魄,也有兼收并蓄的雅量,因此这时人们对‘中国芭蕾’的理解超越了旧有的观念。在创作领域,中国理念与文化的渗入及舞蹈表达方式的多样,使得作品不再停留于表面化的拼接——《祝福》《林黛玉》《雷雨》《家》《魂》《阿Q》等即属于这种‘渗入型’……四十多年的实践摸索,中国的芭蕾艺术正一步步踏入意识与操作的成熟期,使得‘以中国人的意识,利用芭蕾的手段,表现新的内容’成为‘中国芭蕾’的某种共识——建立‘中国芭蕾学派’的朦胧目标似乎也明确起来。”[8]
在杨少莆看来,“中国芭蕾尽管年轻,却已成为一种新的不同意义的文化存在……因此,从自己的思维方式出发,把中国历史、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国人的道德标准、中国人的伦理关系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糅进芭蕾,这就是‘中国芭蕾’的‘核’,也是‘中国芭蕾’必然姓‘中’的缘由。”不过,他接下来强调:“中国芭蕾要姓‘中’,是一道复杂却又丢不掉的难题。现在探讨中国芭蕾文化坐标定位的意义在于:走出中国芭蕾发展的盲区,找到建设中国芭蕾的核心所在……那么,‘中国芭蕾’的具体形态是什么样呢?我以为,中国芭蕾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应该是对展现芭蕾艺术美的追求。中国芭蕾作品绝不能抛开‘芭蕾’艺术特征、艺术规律另搞一套……具体地说,中国芭蕾‘语言’必须保持芭蕾艺术特有的纯净……中国芭蕾的完整概念是:以芭蕾艺术的固有规律、特定风格以及严谨、规范和高度发展的技艺来传达中国文化特质,即外来形式与中国文化内涵的结合。这里,最要紧的是以中国文化为魂!其实,中国芭蕾的民族风格并没有一定模式。遵循芭蕾艺术规律,反映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审美品位,从而揭示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就是中国芭蕾的民族风格。以反映作品内容为前提,可以也应该采取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吸收、运用民族民间舞蹈和音乐素材,但这仅仅是外部手段而不是目标,所以不会产生模式。尤其要明确,中国题材的注入不能成为失掉芭蕾风味的理由,而应该将民族风格、民族气质、民族文化内涵与芭蕾固有的规范美结合在一起;其中,学习和运用民族舞蹈语汇与芭蕾的严谨规范并行不悖……与此相反的情形也存在:我国有些芭蕾人士对排演民族芭蕾有成见,认为排中国舞剧‘毁演员’……为寻求芭蕾的纯净规范和高明的表达方式,他们把目光投向外国人。请外国人来创作中国作品也不失为一种尝试,我们从中可以借鉴一些东西;但全心全意地依赖外国人必然陷入另一个误区,因为他们无法深刻理解和真正体现中国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对本民族的浸润是外族人无法企及的。中国编导再不成熟,但在中国文化传统氛围的有形无形影响下,对于中国文化哪怕是不自觉地体现,也会比外国人强一些吧?因此,哪怕是‘芭蕾’这个纯粹欧洲的艺术领域,我们也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9]通过对“中国芭蕾”四十余年创作实践的历史回顾,指出从“套用型”“糅合型”和“渗入型”的三种演进形态,杨少莆提出了“中国芭蕾”的“完整概念”——其中最要紧的就是“以中国文化为魂”。
七、舞剧创作的首要目的是“树立丰满的艺术形象”
到底什么是“以中国文化为魂”?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为魂”?杨少莆不得不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发声。作为中央芭蕾舞团在《祝福》之后近二十年间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中国芭蕾“完整概念”必须评说的实践问题——杨少莆评析该剧文章的标题很醒目,叫作《舞剧创作的目的和意义》。文章从当时媒体的热议切入:“一位电影名导演(指张艺谋——引者)介入舞剧创作,因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我无意于这类话题,但心存期望的是,在发掘舞剧艺术潜力方面,这位导演能够以新的思维予我们以启示。正如所料,这位导演擅长调动多种艺术手段进行综合性处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舞台气氛由于一些‘新招儿’而显得很不一般。譬如第一幕借助灯影戏的效果展开双人舞,尔后双方又数次穿破纸屏逃跑和追逐。同样成功运用布景和道具的例证,还有用一大块红绸遮蔽三太太遭老爷强暴的处理。舞剧最后的‘杖毙’手法尤其高明:舞台后方矗立着一座雪白的影壁,被家丁们轮着抽打,呈现血淋淋的一片;而遭笞刑的三个主人公(三太太、二太太、以及与三太太有情感联系的武生——引者)则在台板上舞动、翻滚。如此简洁、写意又不失强烈与触目惊心,堪称全剧中的大手笔。此外,这部舞剧还采用了一些非传统的手段‘大胆出新’,确实对人的视觉冲击很强烈,但其效果仅仅使人惊讶而非心灵震撼……《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有一些新的舞蹈处理,但整体上由于没有紧紧抓住戏剧主线,没有紧紧围绕主人公的命运展开笔墨,被其他因素分散、干扰了主人公的形象刻画,因此作为一部舞剧是令人失望的……”[10]
对于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失望,杨少莆认为主要还是“戏剧结构和人物塑造”的问题。他说:“归纳舞剧剧本创作有三个要点:一是树立丰满的艺术形象;二是结构合理的戏剧布局;三是给舞蹈表现以足够的空间。《大红灯笼高高挂》恰恰在这三个方面存在较大问题。首先人物没有树立起来。原著小说是以颂莲为主线展开的,写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学生如何堕落成毫无生活信念的姨太太的心理过程;并透过她的眼睛,揭开那个龌龊世界的内幕,揭示出一个个畸形变态的形象及其被扭曲的心灵。因此创作者最予关切的应是三太太这个核心人物的命运,戏剧线索应该紧紧围绕她的性心理的变化而发展。换言之,舞剧应该浓墨重彩描画她的心路历程。譬如:怎样解释她既接受婚姻又没有心理准备,以至新婚之夜遭强暴?按通常逻辑构思,此后应有一段悲怆色彩浓重的独舞(置于第二幕开始),使之排解怨气以及倾诉最终不能不接受现实的无奈。但现在第二幕一开始她就安然坐在老爷身旁看堂会,显然缺乏人物心理变化的呈示。此外,她大胆与情人幽会的过程也缺乏心理彰示,败露后应有的满足和坦然也没有表现。总之,舞剧没有对主人公心理给予足够的篇幅和空间。三太太作为戏剧矛盾的主导还勾连着其他人物——其对立面是老爷,与之情感联系的是武生,自动加入矛盾纠葛的是二太太。前两个人也都没有树立起来。第一男主角武生的形象最差,似乎除了偷情再无其他作为;所以,尽管临终有大段同三太太的情感交流,这个形象依旧苍白。老爷的形象过于简单化,戏剧的转折点往往扣在他身上,但一些关键情节交代不清晰不强烈,匆忙之中使得这个形象缺少了应有的威严感和震慑力……综观全剧,只有二太太的形象较为丰满,甚至超过了三太太。为什么呢?因为给予了她完整的戏剧动作,揭示了由妒忌而告密,幻想得宠却遭遗弃的过程,尤其是表现她的心理落差的一段独舞十分充实(遗憾的是三太太没有哪怕一段这样的内心独白式的舞蹈,使她的偷情缺乏深刻的心理依据,只落得轻佻的印象,与创作者意欲突出爱情和反封建主题的初衷相去甚远)……”[10]虽然杨少莆在文中对“打麻将”“唱京剧”也颇有非议,但他最关心的“舞剧创作的目的和意义”,还是文中提及的“三个要点”——特别是“树立丰满的艺术形象”。杨少莆所坚守的舞剧创作理念,显而易见是受《海盗》《泪泉》等戏剧芭蕾经典的深刻影响。
八、20世纪芭蕾以两个新的因素激动着人们……
其实,在撰写《祥林嫂的人生转折》一文时,杨少莆想强调的就是“戏剧性朝着人物内心发展”的“时代转折”,想强调的就是舞剧创作“心理描写”的时代趋向。他对于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失望,也在于该剧没有紧紧围绕“三太太”这个核心人物的命运、没有浓墨重彩地去描画她的“心路历程”。为此,杨少莆认为要重申自己的舞剧观,用的标题是《20世纪芭蕾发展态势及其启示》(以下简称《态势及其启示》)。这篇文章刊于《舞蹈》2003年第4期,一年之后在该刊2004年第10期发表的《音乐是舞蹈的灵魂》一文,是杨少莆的终笔之作。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态势及其启示》一文可视为杨少莆舞剧观的总结性阐发。杨少莆指出:“20世纪芭蕾的发展进入多元时代,出现了风格多样而互动、流派争妍且融通的态势,图示则呈伞形焦点辐射状。因此20世纪芭蕾的舞台气象万千:现代探索性新作魅力四射;19世纪经典舞剧依旧风光;交响芭蕾与戏剧芭蕾并行不悖;长篇巨著和精致小品相映成趣;各民族文化的注入使得芭蕾愈加异彩纷呈……与上述发展态势并驾齐驱的,是20世纪芭蕾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发生了三个明显变化:一、与现代舞由对立、排斥而相互吸引和交触;二、交响芭蕾的兴起;三、戏剧芭蕾的升华……20世纪芭蕾还以两个新的因素激动着人们:一是交响芭蕾抽象美的舞台空间日益扩大,二是戏剧芭蕾的戏剧性朝着人物内心发展……交响芭蕾的出现,是对古典芭蕾的突破。传统的戏剧芭蕾的构成要素离不开一个核心故事,交响芭蕾把舞蹈同故事剥离开来,变得抽象而愈加音乐化也愈加诗化。交响芭蕾的兴起深刻影响了芭蕾走向,扩展了芭蕾的创作思维;20世纪任何形式、任何风格的芭蕾创作,都不能不参照交响芭蕾的成功系数,追求交响化的体现。”[11]10
在讨论“芭蕾”作为“舞剧艺术”的话语内,杨少莆并非一味地认同“把舞蹈同故事剥离开来”的“交响芭蕾”,他关注的是这一创作思维影响下的“戏剧芭蕾的升华”!如他所言:“由于深化情节、交响处理等现代舞剧观念流行,似乎戏剧芭蕾的生命力已经萎缩。然而20世纪中期,一部部新舞剧如《奥涅金》《曼侬》《村居一月》《梅雅林》等的相继问世,彻底打破了这种悲观的判断——这些舞剧保持纯正的古典风格,却用不同于古典舞剧的格式、结构和编舞手法,成功地把戏剧芭蕾的传统领进现代化剧场,信心十足地面对现代观众大声说:‘请看吧,戏剧依旧是芭蕾的灵魂!’这些崭新的舞剧,既是传统的继续,又是传统的背离;它的叙事结构依然是舞剧的传统,而舞蹈编排却是超越传统的——他们将情感表达与技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舞剧的结构重心最终落到了心理、情感轨迹的描写;舞蹈的肢体运动,变成了明确的心理活动的投影,舞蹈变成了舞剧主人公的心像外延。因此‘心理描写’构成了20世纪现代舞剧创作观念的一个支柱,使得舞剧选题超越了神话模式的简单贫乏与唯美表现……以上所述20世纪芭蕾创作的经验,是我们中国芭蕾应该认真探究学习的。那么20世纪芭蕾给予我们哪些有意义的启示呢?第一,芭蕾艺术所以生命力旺盛,根本在于随时代发展而发展。正如历史所呈示的那样,革新、创造是芭蕾艺术发展的原动力。第二,新事物是从旧事物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对旧事物批判的前提下,扬弃其不合时宜的部分,继承其优良的传统基因……第三,多元互补、融通、共存是当前时代的主题,也是可预见的未来生活的主题。因此,无论是传统风格还是现代风格,都不能替代或掩盖其他艺术风格。尊崇一种风格而贬低、排斥其他风格的狭隘偏见,是违背时代要求的、行不通的。”[11]10-11杨少莆的“两个新的因素”,他认为第一个因素助推了第二个因素。也就是说,“交响芭蕾的兴起”助推了“戏剧芭蕾的升华”!事实上,站在“芭蕾”作为一种“舞剧艺术”的时代立场上,他在其舞剧观中一直申说、并一直主张的,就是:心理描写构成了20世纪舞剧创作观念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