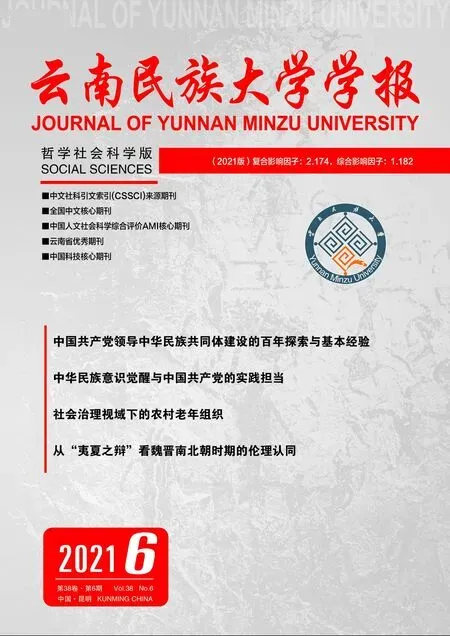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耕耤制度与十八世纪清王朝国家治理的文化策略
2021-12-01王洪兵张松梅
王洪兵,张松梅
(1.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山东 青岛 266100;2.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山东 青岛 266071)
在传统中国,“耕耤”典礼作为一项延续了几千年的重农举措与国家礼制,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广泛认同,在他们看来,农为立国之本,君主需要通过亲耕以为民之表率。耕耤典礼与先民生产劳动中的神话传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炎帝“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1)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1页。,被后人奉为先农神,岁时崇祀,成为后世帝王之道德楷模。源于神话的农耕礼仪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古人以礼仪作为文化传承的媒介,创造出了一种连续不断的、长时段的历史传统,这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在诸多的人类仪式中,农耕仪式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在古代希腊、罗马、印度还是埃及,人们都非常重视“开耕仪式”,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国的耕耤典礼,耕耤典礼有着非凡的社会意义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儒家看来,礼仪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并具备了非凡的象征意义,个人只有遵循相应的礼仪规则,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表明,国家礼仪事关统治秩序的合法性,统治者只有以礼治国,整个社会才能和谐,主持国家礼仪大典是君主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
关于传统中国的耕耤制度,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这些研究或从耕耤礼乐仪式入手,或从耕耤典礼与重农思想之间的关系出发,或关注耕耤制度的文化意义,或考证耕耤典礼的历史演变。(2)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罗莹:《古代的藉田礼和〈藉田赋〉》,载《殷都学刊》2007年第1期;王健:《汉代祈农与籍田仪式及其重农精神》,载《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王美华:《宋代皇帝耕籍礼的演进》,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1期;刘凯:《从“南耕”到“东耕”:“宗周旧制”与“汉家故事”窥管——以周唐间天子/皇帝耤田方位变化为视角》,载《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宁镇疆:《周代“籍礼”补议——兼说商代无“籍田”及“籍礼”》,载《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王洪兵,张松梅:《农耕仪式与文明对话:十八世纪中国耕耤制度在欧洲的传播》,载《东岳论丛》2018年第11期;王洪兵:《耤田礼体现中国古代重农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12日;王洪兵,张松梅:《敬天勤民:耕耤典礼与十八世纪清王朝治国理念的建构》,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上述成果为耕耤制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和思路,开启了良好的开端。然而现有研究对于耕耤制度发展集大成的清代却少有论及,耕耤制度是论证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一项重要国家典礼,十七、十八世纪的清王朝正由一个民族属性突出的满族政权向具有浓厚中华文化传统的农业帝国转向,耕耤制度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十八世纪的清代统治者在不断完善皇帝亲耕制度的同时,将其推广至全国各省府州县,要求地方官实力奉行,乾隆朝时期甚至要求少数民族首领入坛观礼。清代耕耤制度不但宣扬了重农国策,而且诠释了其“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政治纲领,对儒家传统政治经验的认同强化了清代的“国家认同”。
一、耕耤典礼与清王朝的文化认同
古代天子因天时而颁时政,统治者注意通过仪式活动调节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农本”经济的社会大背景将土地与时令、皇帝与臣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耕耤典礼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表达了统治者与上天、祖先建立密切联系的努力。皇帝遵循自然规律,按照时令亲耕,以表率于万民,从而确保全国农事的顺利开展,从此意义上讲,耕耤仪式即是统治者“顺天时”“应天命”的一种政治表态。数千年以来,耕耤典礼作为一项人文主义色彩浓厚的礼俗仪式,成为历代统治者表达德治理想的重要途径,为了稳固在政治、道德、信仰领域的核心地位,皇帝有义务在京城举行耕耤典礼,以为民之表率。中国历代王朝都注重通过耕耤典礼来建构政权的合法性,蒙元政权建立之初,囿于蒙古族固有的游牧特性,忽视农业生产,但是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逐渐意识到中华农业文明的重要性,除颁重农诏书于天下之外,还于大都立籍田,建先农坛,置“籍田署”,“以蒙古胄子代耕籍田”(3)毕沅:《续资治通鉴》(第四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68页。,以示对中华文化的接纳。明初统治者非常重视发挥耕耤礼的示范作用,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认为耕耤礼仪长期废弛,导致“上无以教,下无以劝”,他要求礼部整理耕耤仪注,岁时举行耕耤仪式。(4)《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上,洪武元年十一月癸亥条。明代耤制度的重建,不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而且成为论证明王朝正统合法历史地位的重要文化标签。明朝末年,身处内忧外患的崇祯皇帝仍想重振旗鼓,为了鼓励农耕,同时宣示统治的合法性,崇祯皇帝在1641年正月亲耕耤田后,于二月“再耕耤田”(5)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七九《列传第一百六十七·王锡衮》,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150页。。一年两次亲耕耤田,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先河,显示出崇祯重视耕耤礼,并试图以此为契机扭转统治危机的急迫性。
明清鼎革,满洲统治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但是长期战乱致使民穷财竭,如何吸取明亡教训,克服包括满汉冲突在内各项社会矛盾,缓和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冲突,稳固统治秩序,成为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重要挑战。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根基,像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新兴王朝一样,清初统治者首先面临着合法性的问题。根据传统中国的政治哲学,合法性的关键在于:“皇帝需要履行作为天子应有的仪式和礼仪,这些仪式,例如每年在天坛举行的祭天大典,或者是春天的亲耕大典,均源于儒家经典所描述的典范,它们构成了帝国秩序的道德哲学基础”(6)Nicholas K. Menzies, Forest and Land Management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p.57.。其实,早在入关之初,满洲统治者就注意通过祭祀历代帝王,以及祭祀孔子等仪式,树立“大一统”王朝形象,以此论证其合法性。当然,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不仅是政治体制上的接纳,更为关键的是适应仪式化的中国日常生活,具体而言,在经济上就要接受“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在国家层面的体现就是皇帝要亲耕,皇后要亲蚕。与亲耕相对应,亲蚕仪式的社会意义在于,皇后作为全国妇女的表率,以自己的行为鼓励女性履行相应的社会经济责任,亲蚕与亲耕相伴而行,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帝国运转的基本要素。
顺治作为清王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个皇帝,自从登基以来就开始探索政权的中国化道路。顺治十一年(1654),顺治皇帝亲祭先农坛,行亲耕礼,耕耤制度得以恢复,清代统治者试图通过重建儒家礼仪制度,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得到广大汉人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同。此次耕耤仪式,虽然制度并未完备,但是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表明了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向全国民众宣示了“敬天勤民”的基本国策。亲耕之后,顺治诏告天下:“兹躬耕耤田,劝导农桑,以培邦本……徂夏万物长养,宜沛宽恩,以符天意。”(7)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档号:038175,顺治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顺治诏书。清代统治者通过耕耤典礼表达了“敬天顺时”的基本政治态度和生态观念,由此推演其统治“顺应天命”的合法性。清初耕耤制度的重建对于传达其重农政策、恢复农业生产秩序、缓和民族冲突、强化文化认同、宣示统治合法性、维护政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顺治皇帝在位期间虽仅行亲耕大典一次,但无疑是清王朝在构建中华帝国统治秩序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到康熙年间,耕耤典礼再次被提上康熙君臣之间的议事日程。康熙六年(1667),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疏请行耕耤礼,康熙要求群臣商讨,虽然没有明确的结果,但是在次年树立的孝陵神功圣德碑文中,康熙特别称颂顺治“诣先农坛,躬耕耤田”(8)《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五,康熙七年正月庚戌条。,是其在位时的一大功绩。到康熙十一年(1672),十八岁的康熙举行了康熙朝唯一的一次亲耕礼,“诣先农坛致祭,上亲行耕耤礼,三推毕,登观耕台”(9)《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八,康熙十一年二月丙申条。。虽然康熙皇帝在位期间仅亲行耕耤一次,但是另外开创了丰泽园演耕制度,每年要求皇室子孙参与耕耤仪式,以此培养王朝继承人的政治品质和治国能力。丰泽园演耕之制,“皇帝诣丰泽园演耕。是日,礼部尚书、顺天府府尹各率其属,穿蟒袍补服,于耕所祗候;青箱谷种,照例陈设。皇帝御龙舟至,先诣时应宫拈香毕,至耕所。顺天府府尹进鞭,皇帝扶犁三推,御前大臣侍卫襄事。礼毕,皇子、诸王学习农事,驾回宫,内务府官员终亩”(10)马宗申校注:《授时通考校注》(第三册),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此后,丰泽园演耕被列为皇室家法,历代遵行。雍正朝是清代耕耤典礼完善的关键时期,雍正承续康熙重农国策,并将耕耤仪式进一步制度化,在位十三年间,从雍正二年到十三年连续亲耕十二次,开创了皇帝每年亲耕的惯例。雍正在位期间不仅勤于亲耕,而且将耕耤典礼由中央推行到全国各省、府、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雍正五年(1727),雍正要求全国各地建先农坛,置耤田,各级守土官员将耕耤仪式列为地方常年举办的重要典礼。耕耤典礼不限于在汉人聚居的区域实施,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开展,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雍正七年(1729),全国推行耕耤典礼两年后,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贵州巡抚张广泗、广西巡抚金鉷纷纷进献瑞谷,雍正评价:“朕思古州等处苗蛮界在黔粤之间,自古未通声教,其种类互相仇杀,草菅人命,又常越境扰害邻近之居民,劫夺往来之商客,以致数省通衢行旅阻滞”,社会秩序异常混乱,但是自雍正五年通行耕耤以来,对土司及民众教以礼法,经君臣之间的不懈努力,“俾苗众革面革心,抒诚向化,地方宁谧,和气致祥,感召天和,黔粤二省,岁登大稔。而黔省硗瘠之区,苗彝新辟之地,又蒙天赐瑞谷,显示嘉徵。仰见天心,以经理苗疆为是”(11)胤禛著,魏鉴勋注释:《雍正诗文注解》,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耕耤典礼的普遍推广为推动清王朝的国家治理提供了有益途径,雍正给予高度评价:“如此则官与民联为一体,臣与君又联为一体”(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三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耕耤典礼由中央向地方的普及是雍正皇帝在耕耤制度上的一大创举和突破,乾隆继承了雍正推崇耕耤典礼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乾隆五十年(1785)亲耕之后,乾隆要求后世帝王将耕耤典礼常态化,“凡遇耕耤典礼,若年在六十以内,礼部照例具题,年年躬行”(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一二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86页。。祀先农、亲耕耤虽然仅为清代祭祀体系中的中祀,但逐渐演变成为皇帝例常举行的大典。
历史经验表明,礼仪在儒家思想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它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集中反映,而耕耤典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连绵不断的一项符号象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助于建构文化认同,从而实现政治认同, 清初统治者无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凸显统治的合法性,清初帝王们非常注意继承和完善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以此凸显儒家帝王的形象。到十八世纪,经过长期的冲突与磨合,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认识逐渐加深,因此不断调整国策,推行系统的汉化政策,构筑文化认同成为清初统治者施政的一项重要举措。文化认同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清王朝接受了儒家的礼仪秩序, 儒家的治国理念融入到清代的政治实践,清初对儒家礼仪的接纳,是清代建构其正统王朝合法性的历史性选择。
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国以重视既往传统而著称于世,中国形象的塑造离不开习俗、礼仪和文化传统。文化认同是中国认同的核心,在儒家精英看来,传统礼仪是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清初统治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要成为中国皇帝就必须遵守传统礼仪制度,为显示跟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绪关系,他们不得不重建和恢复中国的文化传统,把祭天、祭孔、耕耤等儒家文化的象征符号纳入到帝国的礼仪核心,把满洲皇帝装扮成中华帝国的当然传承者。在满汉文化交融的过程中,统治者认识到耕耤典礼是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社会记忆,作为满洲出身的中国皇帝,他需要遵守传统道德与礼仪规范,每年垂身示范,第一个扶犁亲耕。正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认同,“蛮夷化为‘中国’”“‘满族人’得以成为天子”(1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为了论证统治的合法性,清王朝统治者除在理论层面解构“华夷之辨”以外,还通过实践儒家礼仪文化来建构“中国认同”,从而重构“大一统”的政治理想。耕耤典礼无疑是实现上述理想的重要手段,清王朝统治者在重建耕耤典礼的过程中,根据时代要求,大力实践并不断改革,通过亲祭先农和亲耕耤田宣示其统治是仰承天命的,以此完善治国经验,调整满汉民族之间的隔阂,实现“中国认同”。在长期的治国实践中,清王朝不断吸收包括满汉在内的各民族的文化和政治智慧,逐渐实现了从民族认同到“中国认同”的转化,其合法性也因“中国认同”的达成而日趋稳固。
二、耕耤典礼与“天人合一”的治国经验
在中国古代,皇帝不但在政治、思想、信仰等领域都扮演着核心角色,而且在国家礼仪方面更要作出表率。遵守儒家礼仪对于新兴的清王朝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魏斐德指出:“新朝代的建立者必须在仪式上特别注意合乎规范,在通往皇权巅峰的道路上,他必须谨遵礼法,才能够获得民心,成就帝业”(15)Frederic Wakeman, Jr.,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p.57.。入关以后的清王朝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逐渐走向“中国化”的道路,“大清”与“中国”的称呼逐渐趋同,大清皇帝也以“中国皇帝”自居。关于清王朝的性质,新清史学者欧立德曾宣称: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16)[美]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刘凤云等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上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第3~15页。这一观点不但违背史实,而且无论是从清王朝治国理论的建构还是国家治理的实践层面来看,都值得商榷。新清史学派将清王朝的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断定清王朝是满洲人的帝国,割裂了清王朝与中国的关系,其观点承袭了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以及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观点,将中国重构为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的“二元结构”,夸大“满洲”元素,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从而分解了中国历史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在讨论清朝国家治理的政策与经验时基本上都脱离了与清以前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关联,否认适应其他文化的能力是满洲人成功的关键,只以满洲中心或内亚性的视角审视中国历史,“这种割裂清与清以前诸王朝之历史联系的内亚观,显然完全不符合中国古代历史之事实”(17)沈卫荣:《大元史与大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17~218页。。清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民族特性,曾试图在政治军事体制、语言文化、国家典礼等方面强化满洲特性,彰显“满洲之道”。乾隆皇帝特别强调满洲“国语骑射”传统,曾经指出:“周家以稼穑开基,我国家以弧矢定天下,又何可一日废武”(18)昭梿:《啸亭杂录·续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但在治国实践中却逐渐意识到,“国语骑射”的国策难以持之以恒。从康熙到雍正、乾隆,为了论证其正统合法性以及获取大多数汉人的支持,不得不通过耕耤典礼这一承载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仪式表演,将自己装扮成符合天命的中华帝国的天子。历史实践表明,清王朝统治的成功并非坚守“满洲之道”的结果,也并非保持了征服民族的特性,其成功之处在于平衡满汉之间的差异与矛盾,统治者能主动接纳中国传统文化,在沿袭传统专制君主官僚制的同时,注入了部分满洲的治国理念。关于清王朝的上述治国特性,常建华先生将其概括为:“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19)常建华:《大清:一个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载《清史研究》2021年第4期。。
耕耤典礼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礼仪,为何饱经岁月洗礼,却从未淡出中国历史舞台?不可否认,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口的急剧增长,十八世纪的中华帝国已经处于“生态极限”,如何处理生态与生计之间的两难困境,成为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考验。耕耤典礼是传统中国天、地、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产物,它顺应自然法则,当然也是统治者施政的基本准则。耕耤典礼充分体现了古人的自然生态观念,与肥田、休耕都被视为农业生态性管理的举措。雍正年间,协助皇帝亲耕的张廷玉深刻剖析了耕耤制度的生态理念,“于时,四野晴和,尘埃不动,百神翼卫,丽景无边。一墢初移,发大地广生之德,三推渐讫,动阳春长养之风”(20)张廷玉:《澄怀园文存》卷七《圣王躬耕耤田诗序》,乾隆间刻澄怀园全集本,第2页。。可见,耕耤制度并非单纯是对农业的重视,统治者的生态观念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只有他们形成了合理科学的环境价值观、自然权利观和人文精神”“整个社会才能真正培养起自觉的生态意识,营造出常态的人类环境,趋向于繁荣健康的生态文化”(21)梅雪芹:《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人”及其活动在环境史中的体现》,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7页。。中国自古就有尊重自然秩序的传统,统治者注意按照时令节律施政,通过颁定历法,以承天时行庶政,从而有效地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耕耤制度反映的生态伦理思想后来一度成为欧洲学习的榜样。
雍正年间,皇帝勤于亲耕,在雍正带动下,全国掀起了一股勤于耕作的重农热潮。有感于此,雍正谕令御用画师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创作《瑞谷图》。雍正五年(1727),在全国各级地方行政衙门推行耕耤典礼后,全国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雍正颁发上谕:“朕念切民依,今岁令各省通行耕耤之礼,为百姓祈求年谷,幸邀上天垂鉴,雨旸时若,中外远近俱获丰登,且各处皆产嘉禾以昭瑞应,而其尤为罕见者则京师耤田之谷,自双穗至于十三穗;御苑之稻,自双穗至于四穗。河南之谷,则多至十有五穗;山西之谷,则长至一尺六七寸有余。又畿辅二十七州县新开稻田共计四千余顷,约收禾稻二百余万石,畅茂颖栗,且有双穗三穗之奇,廷臣佥云:嘉禾为自昔所未有,而水田为北地所创见,屡词陈请宣付史馆。朕惟古者图画豳风于殿壁,所以志重农务本之心。今蒙上天特赐嘉谷,养育万姓,实坚实好,确有明徵。朕祗承之下,感激欢庆,着绘图颁示各省督抚等。朕非夸张以为祥瑞也,朕以诚恪之心,仰蒙天和,所愿自兹以往,观览此图益加儆惕,以修德为事神之本,以勤民为立政之基。将见岁庆丰穰,人歌乐利,则斯图之设未必无裨益云”(22)《瑞谷图》原件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郎世宁《瑞谷图》所绘五枝谷穗,谷穗颗粒饱满,栩栩如生,象征五谷丰登,与雍正上谕合璧,左图右上谕,谕旨末端钤雍正“敬天勤民”宝玺,图文并茂,福瑞叠呈。关于《瑞谷图》可参见聂崇正主编:《郎世宁全集》(上卷),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雍正笃信天人感应之说,将耕耤典礼与自然现象、国家政治紧密结合,雍正五年时值皇帝五旬万寿,其统治地位渐趋稳固,以重农亲民、天人合一为题材的《瑞谷图》正是雍正阐释其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中国形成了一套适应农业生产与环境变迁的农事节律,它将看似杂乱无章的社会生活纳入到结构性的秩序框架,“其他生产与社会活动则均以其为轴心展开进行,并分别依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依次镶嵌于这一轴心之上,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年度时间生活周期”(23)王加华:《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农事节律为整个社会生活设定时间规范,人们相信,农业的繁荣取决于是否遵循节律、顺应天意。在传统中国,“敬授民时”被视为国家的基本职责,统治者注意按照自然节律颁定历法、安排农事。根据历法,京师于每年立春之际举行迎春、进春、鞭春诸仪式,这是一场由皇帝、百官、民众共同参与的春的盛宴,狂欢仪式宣告了农时的来临。随后,按照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在春季一个精心挑选的日子里,皇帝要在百官的陪同下举行亲耕仪式,躬身垂范万民”(24)Lien-sheng Yang, “Schedules of Work and Rest in Imperi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8, No. 3/4 (1955), pp. 301~325.。春天的狂欢仪式已经不是单纯的农业节日,它为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提供了动力。耕耤典礼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调整,有助于调和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确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同时,耕耤典礼也是天人沟通的重要渠道,皇帝通过亲耕仪式的表演,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他与上天、神灵的紧密联系,最终让他们接受君权的合法性不容置疑这一事实。
三、耕耤典礼与清王朝的德治理念
在中国古代,亲耕被视为君主的美德,仪式目的是为了表达对整个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认同,皇帝需要按照儒家传统特别倡导的传统礼仪,象征性举行耕耤礼仪,以此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皇帝是全国臣民的道德典范。
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亲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在耕耤仪式过程中,皇帝通过亲耕表演,呈现给民众的是一幅理想君主的形象,耕耤典礼对于统治者整合政治资源、论证合法性、构筑权威认同等方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域。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农业是国家的第一要务,皇帝每年在先农坛举行亲耕仪式,以此动员全国民众勤于耕作,耕耤仪式充分展现了一个合格君主的应有美德。作为帝制中国的一项合法性信仰,耕耤典礼被视为“有德之君”的重要标识,西晋时潘岳指出:“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勤穑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业至矣哉”(25)陈元龙编辑:《历代赋汇》卷五一《典礼·藉田赋》,康熙四十五年内府刊本。。统治者通过举行这种公共礼仪活动,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从而散发出光辉的政治魅力。
在中国文明漫长的演进过程中,礼超越了仪式的藩篱,升华为道德的规范,中国传统礼仪是一种兼具道德性与宗教性的公共话语。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万民拥戴的理想帝王?福柯认为君主与臣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理论”,“从历史上看来,皇权长期以来远不是一种绝对的治理”,“君主和臣民之间达成协议以便构建一个国家,君主根据协议去做和不去做一些事情”,只有如此,“君主才能成为君主”(26)[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由此可见,皇帝在理论上虽然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实际上其行为要受到各种既定礼俗的约束,礼仪成为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霍尔巴赫颂扬耕耤礼仪是一种帝王美德,他指出:“伟大的中华帝国的皇帝,每年必定要亲自扶犁耕种,让臣民们知晓有益或必要的劳动并不可耻”(27)Baron d’ Holbach, éthocratie: Ou Le Gouvernement Fondé Sur La Morale, Amsterdam: Chez Marc-Michel Rey, 1776,p.67.。如霍尔巴赫所言,清代统治者注意通过耕耤仪式树立道德榜样,在他们看来,为政之道在于“敬天授时”,“敬天”以“事神”,“授时”以“勤民”,而耕耤典礼将两者连结起来,“帝德克勤于民事,天心乃兆以丰年”(28)甘汝来:《甘庄恪公全集》卷四《圣主躬耕藉田赋》,乾隆赐福堂刻本。,统治者借助耕耤典礼昭示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耕耤制度是一项重祀与劝农并举的制度设计,有助于推动统治者完善政治德行,引导民众重农务本。政治合法性离不开政治仪式的建构,在清代统治者看来,耕耤典礼的作用在于:“应天以诚,故志气之动足以格穹苍,勤民有本,故典礼之行足以通众志”(29)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五《颂铭·圣主躬耕耤田颂》,咸丰元年戴钧衡刻本。。仪式连结着人与自然、神圣与世俗,将政治合法性深烙于仪式参与者的记忆中。耕耤典礼因为较为全面地诠释了“敬天勤民”的政治纲领,从而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他们试图利用耕耤典礼来凸显天命意识,据雍正称,“朕每岁躬耕耤田,并非崇尚虚文,实是敬天勤民之至意”(30)《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四七,雍正四年八月丙戌条。,“敬天勤民”“天命有德”“天人感应”成为雍正自我标榜的政治资本。与雍正遥相呼应,臣子高度颂扬皇帝的亲耕行为,称颂雍正为“圣君”“明主”,由此推演其统治合乎天心民意。仪式同时强化了耕耤现场耆老、农夫对皇权的认同,“邑老田父环聚欣睹,莫不协畅,以为圣德洽于上下,大孝格乎天人”(31)陈仪:《陈学士文集》卷一《躬耕耤田颂》,乾隆五年陈氏兰雪斋刻本。。皇权统治的合法性在君、臣、民之间达成共识,仪式消弭了由于认同危机而引发的关于皇权的合法性危机。
将耕耤典礼推向清王朝典礼巅峰的无疑就是乾隆皇帝。耕耤典礼中蕴含着“以德治国”的政治智慧,乾隆将耕耤典礼视为展示帝德、接受儒家民本思想的一种方式,在位期间,除修缮先农坛、观耕台以及加强耤田管理之外,乾隆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亲耕耤田次数最多的纪录。据统计,乾隆在位期间先后28次祭先农、亲耕耤田,并于79岁高龄亲耕之后,手书《邵农纪典》上下两册,收录历年亲耕耤田之后的诗文64首。乾隆如此重视耕耤典礼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培养帝王及其继承人的重本亲民意识,将其自己塑造为国家和后世君主的道德楷模。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这次耕耤典礼,乾隆除自己亲耕之外,还要求5位皇子从耕,其中就包括皇位继承人皇十五子颙琰,耕耤典礼的政治寓意显而易见。耕耤典礼之后,随同皇帝亲耕的军机大臣王杰、吏部尚书刘墉等人为《邵农纪典》题跋,跋文曰:“懿夫劝本先劳昉自姬稷,列代莫不以是数典,至我朝有加重者:辟丰泽以演耕,钦家法也;率皇子以从耕,裕后昆也;秉耒加推,益勤力也;回人列视,扩农功也;撤彩棚之饰,祛华以敦本也;禁蔬圃之艺,昭洁以明敬也”,在总结耕耤典礼对于王朝治理的重要意义之余,王杰等人认为,乾隆亲耕的可贵之处在于坚守初心,“不在耕耤之典,而在乎举是典之一心”,称颂“八旬天子行耤田礼,则史册从来所未见者”(32)王骁主编:《乾隆帝邵农纪典御笔书法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图41。,从而为乾隆树立了光辉的道德榜样。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礼仪所呈现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德治”,国家礼仪成为塑造统治者道德典范的重要手段,通过精心设计的国家礼仪,敬天勤民、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得以在全国推行。
四、结语
在十八世纪,清王朝虽然统一了中国,但是为了维护统治,他们需要遵守历代相沿的儒家礼仪传统。开国伊始,统治者不断探索能够让他们融入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途径,探索的结果是,清王朝承袭了中国的正统,维持了传统礼仪典章。在诸多儒家礼仪规则中,耕耤典礼显得的尤为突出,耕耤典礼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道德至上的中华帝国形象,中国皇帝借助耕耤仪式化身为整个农耕帝国的象征。清代统治者重视调整文化政策,通过尊崇儒学、复兴传统礼仪,树立起共同的社会理想,从而为清王朝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与合法性依据。天命系于政德,皇帝亲耕耤田为民众树立道德楷模,无论是雍正还是乾隆,他们都试图借助耕耤典礼,彰显其“敬天勤民”的政治品格。耕耤仪式不但展现了皇权,而且再造、强化了皇权,作为一项“政治仪式”,构建合法性是其最终目的。权力与合法性隐藏于仪式之中,清代统治者通过耕耤典礼展示了其统治的合法性。清代统治者在礼制建设上曾经徘徊于满洲习俗与儒家传统之间,努力建构符合国家治理需要的礼仪秩序。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儒家礼仪最终占据了整个王朝礼仪的核心,清王朝的命运同儒家礼仪由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此背景下,耕耤典礼作为一项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的象征性资源,被清王朝视为历代遵循的治国策略,统治者以自己的行为诠释着“敬天勤民”的治国理念。十八世纪的清王朝通过践行耕耤典礼,沟通满与汉、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推动农业生产、整合政治资源、完善治理能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