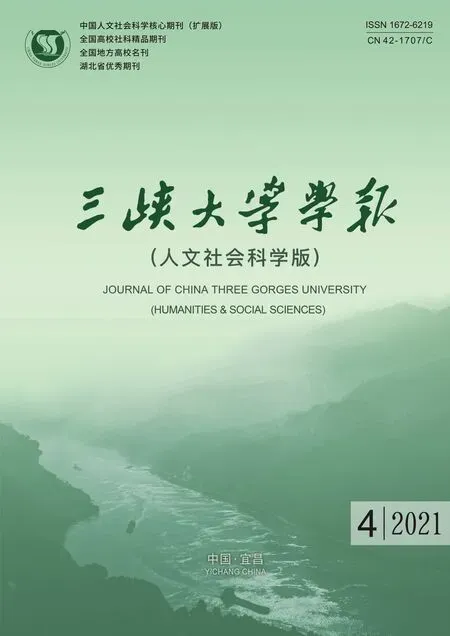如何处理历史
——世纪之交中国诗坛“盘峰论争”的根本分歧
2021-12-01何方丽
何方丽
(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0)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界和思想界在震荡中前行,作为时代敏锐的触角,诗歌的感受更为强烈。90年代的诗歌不再像80年代一呼百应,诗歌真正进入潜沉期,诗坛也因“历史的强行进入”逐渐淡去喧哗之声,波澜不惊、相安无事是这10年间的常态。然而,所谓的安静和无事仅为相较于此前80年代和此后新世纪而言的一个总体表象。表象背后实则暗流涌动,诗坛在等一个炸裂的机会。在1999年4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盘峰诗会”上,日后被划分为“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两派诗人、理论家围绕诗歌资源、语言、诗坛权威等话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由此引发了持续近两年的“盘峰论争”。作为既往美学分野互相抗衡的结果,“盘峰论争”最终让前期积攒的矛盾集中爆发,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20世纪90年代诗坛格局的追认。
一、历史意识与如何处理历史
对于“盘峰论争”,首先需要指出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阵营还是“民间写作”阵营里的诗人、批评家,他们在本质上都是文人知识分子,不过在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科技理性、消费主潮、城镇化浪潮与历史的割裂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宏观来看,90年代不是诗性的年代,也不是一个关注诗人的年代,“一切都物质化、市场化了,商品就是上帝。精英与大众失去了界限,精英文化的荣光不再。对于曾具有独特个人深度和个人魅力,曾属于社会精英、顶尖知识分子的诗人,大众悄然拒绝,至多保持一种疏离、漠视、敬而远之的态度。”[1]8市场意识的生成及文学消费制度的建立让诗歌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和精神氛围,在一个“非诗”的年代,诗歌在沉潜中走向了历史。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朦胧诗除外)疏离历史而具有某种“非历史化”倾向,90年代的诗歌则在反思中表现出了对历史的亲近,“诗歌处理历史的能力被当作检验诗歌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成为评价诗人创造力的一个尺度”[2],“历史意识”成为影响90年代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的重要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有众多集中于“历史意识”这个诗学观念的研究。
在“历史意识”的笼罩下,“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知识分子写作”企图以形而上的“道义”抵达灵魂的安全港湾,故其视线是朝向未来的,这导致其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生活时略显无力,因而秩序和责任被建构成某种道德,并成为“知识分子写作”的重要原则,当然此种姿态的出现与诗人们边缘化的处境也密切相关。90年代多元的价值观和历史观与市场经济时代消费主义的浪潮相伴而生,日常生活或许俗媚、庸常,但也蕴藏着巨大能量。处在“边缘的边缘”的一部分诗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将其作为与“知识分子写作”相抗衡的重要砝码。于是“民间写作”做出的选择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去甚远:直面形而下的日常生活,用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去中和历史的沉滞,抵达生活的本质。其中于坚的《0档案》最具代表性。
指出“民间写作”直面日常生活并非认为“知识分子写作”中没有日常生活的元素。“知识分子写作”也写日常生活,不过在“知识分子写作”的笔下,日常生活要么在历史的视野中被作为审视、批判的对象,要么作为当下生活的公共性场景而被发现,如欧阳江河诗中的广场、肖开愚诗歌中的车站、西川笔下的动物园等等。“民间写作”在处理日常生活时,则是将其作为一种当下性的历史加以书写。在“民间写作”这里,日常生活本身就构成一种正在进行的历史,所以“民间写作”尤其重视对日常生活的瞬时性写作,更善于捕捉瞬间的诗意和灵感。韩东的《甲乙》、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等诗都具备这种瞬时性历史的意味。因此,可以这样理解“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在处理日常生活时的差别,即“知识分子”写作更倾向于有纵向深度的历时性写作,而“民间写作”更倾向于有横向宽度的共时性写作,这也是二者在处理历史时的本质差别。但这种本质上的差别在20世纪90年代并未得到“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阵营双方的重视,尤其是“盘峰论战”期间,双方均以自己的诗歌立场、现实诉求为出发点,缺少了对分歧本身的挖掘和反思。
二、“知识分子写作”的“道义感”
在不断的阐释中“知识分子写作”对历史的处理最终凝结成了写作上的“道义感”,而这种“道义感”一经形成便让“知识分子写作”忽略了其初衷在于解决如何处理历史的问题。“知识分子”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在我国的学术领域,较为著名的西方“知识分子”理论主要有班达的“精英知识分子论”,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和索维尔的“制造观念知识分子论”。具体来看,“精英知识分子论”认为知识分子不追求实践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3]78,班达认为人性、正义、超然和抽象是精英知识分子活动的重要特征;“有机知识分子论”则认为“知识分子是执行着特殊社会职能的人”[4]7;“制造观念知识分子论”将“知识分子”定义为一种职业,核心在于“制造理念”。可见,知识分子群体备受关注,其具体的内涵则众说纷纭,“知识分子”这个命题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意义的生成性。
在中国诗界,“知识分子写作”这个概念最早由西川提出,他认为知识分子“专指那些富有独立精神、怀疑精神、道德动力,以文学为手段,向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群体讲述当代最重大问题的智力超群的人”,因担忧诗歌“被十二亿大众的庸俗无聊的日常生活所吞没”[5]376,遂提出“知识分子写作”。显然“知识分子写作”一经出现就被赋予了与庸俗日常对抗以确保诗歌神圣地位的责任,“智力超群”的诗人成为“当代重大问题”的讲述者,他们面对的读者也特指“受过教育”的普通人。无论是从对读者的指认还是对责任的认领来看,“知识分子写作”被西川构建成精英的而非普通的、承担的而非随性的、神圣的而非世俗的。欧阳江河此后进一步完善了“知识分子写作”概念,并使其内涵基本确立,长文《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身份与知识分子身份》日后成为民间写作者所驳斥的“某些新潮诗歌批评的纲领性文件”[6]280。欧阳江河主要从理论资源、身份指认以及思想和语言资源三个方面展开:“实际上每一个诗人的写作,每一语种的文学史也都包含了其他语种文学史的影子和回声”;“我们当中的不少人本来可以成为游吟诗人……或骑士诗人,但最终坚持下来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知识分子诗人”;“西方理论思潮(主要是法国的和英美的新思潮)的深刻影响……在国内诗歌界已经日益显示出来。这对一个成熟的诗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7]。经由欧阳江河,知识分子诗人具有了“工作的和诗人的”性质以及“典型的边缘人”身份,这就在根本上确定了知识分子诗人的精英地位,证明了其写作中知识优势的合理性,并凭借其严密的逻辑和精准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争取这种优势的合法性。
“民间写作”在世纪末的“揭竿而起”与程光炜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批评阐释有重要关联。1998年程光炜《岁月的遗照》出版,该书旨在重温其个人喜欢的诗篇,他认为独立性的精神要求诗歌成为一种相当独立的个人工作。程光炜并概括性地指出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诗学抱负乃是“秩序和责任”[8]61。此后,根据于坚的“揭露”,臧棣、陈超、陈旭光、谭五昌、唐晓渡以及程光炜等人都对“知识分子写作”取代中国诗歌界的“事实”负有一定责任[6]。
从概念初提到最终形成,“知识分子写作”的核心始终是承担和责任,因此“知识分子写作”尤其看中独立的品质以及批判的精神,这让“知识分子诗人群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谓”[9]69。王家新是一位典型的承担者,其承担意识一方面来源于命运的“恶意嘲笑”[8]165-179,另一方面来自他对俄罗斯诗歌的翻译与追踪,前者使他不得不承担命运之重,后者让他不得不承担时代之重,结果是王家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时代的道义和良知。在《承担者的诗:俄苏诗歌启示》一文中,王家新梳理了其诗歌的精神谱系,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并直言80年代后期以后“正是通过他们我们确定了自己的精神在场”[10]。这些诗人对诗歌和命运的承担正是王家新认同的诗歌精神。王家新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是“承担者”,属于知识分子艺术家类型。诗歌《帕斯捷尔纳克》和《瓦雷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在致敬精神导师的同时抒发了王家新式的责任和承担。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王家新确立了精神坐标,成为程光炜所言的“替时代说话”的诗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人生活和心理层面的波动在王家新这里有深沉的记录:“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在风中燃烧的枫叶/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撇开一切来谈论我自己。”在王家新的诗中,个人、历史、时代因命运这个关键词而盘根错节、互相缠绕,在写作中承担因此成为其人其诗的核心。王家新的俄罗斯情结主要体现在他面对俄罗斯文学时,对其拥有的面向苦难和人民的超越性精神的顶礼膜拜,并在写作中不断去靠近乃至试图超越这些伟大的精神和灵魂。
在“知识分子写作”这里,“知识分子”是“制造观念知识分子论”和“精英知识分子论”的综合。无论“民间写作”诗人如何攻讦“知识分子写作”的“凌空蹈虚”“崇洋媚外”“拾人牙慧”,在对历史与命运的道义和承担上,“知识分子写作”走得确实持重而稳健。毕竟,诗歌不止关乎当前的生活,也关乎历史和命运,“知识分子写作”的初衷就与这份对历史和生命的承担有关,至于“责任和秩序”,则作为一种道德尺度,凝结成了写作的“道义感”并引领“知识分子写作”。
三、“民间写作”的“民间立场”:寻求主流之外的合法性
与知识分子写作一样,“民间写作”也在对自我的叙述中忽略了二者对于如何处理历史的根本分歧,而不断强化“民间立场”与主流的对抗性以确立自身合法性。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封面上,作为年鉴也是“民间写作”根本立场的“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十七个字,黑底红字被安置于页眉,格外醒目。当“民间写作”高调地宣扬其坚守的“民间立场”时,何为“民间立场”以及民间写作诗人此举的真实意图就成了有待探究的重要问题。在年鉴的序言中于坚写到“本世纪最后一年在中国南方出版的这部年鉴,仅仅是要表明,所谓‘好诗’的民间标准”[11]9,于坚在此强调了出版的时间(即“本世纪最后一年”)和空间(即“中国南方”),这也衍生出“盘峰论战”的焦点问题:“民间写作”诗人们首先从时间角度反对“知识分子写作”对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占领,然后从空间角度用南方反对以北京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圈子”和“权威”。
1986年以来随着“第三代”诗歌美学的式微,文化诗、学院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一脉相承,逐渐成为诗坛主流。尤其90年代以后,一方面社会经济体制和诗歌生态对诗歌提出了迥异于“第三代”诗歌的新要求,“知识分子写作”顺势而起;另一方面,因为“文学批评的真正职能在于为读者大众选取样本书”[12]60,所以“新潮诗歌批评”的实践所选取的文本具有样本意义,这使“知识分子写作”的地位被逐渐确立并得以巩固。90年代的诗歌批评既由诗评家承担,也有“诗人批评”参与。在举例诗评家时,洪子诚和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如是排序:“唐晓渡、陈超、程光炜、耿占春、崔卫平、吴思敬……”[13]249排在前三的批评家均对“知识分子写作”青睐有加,并且在“盘峰论争”中曾发表文章声援“知识分子写作”。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写作”的分量在20世纪90年代至少在诗评家这里不轻,基本可以确定“知识分子写作”是90年代诗歌的“主流”。
20世纪末“民间写作”的群起而攻与民间作为诗歌的基本在场不无联系。一方面,无论是新诗草创时期胡适、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还是毛泽东“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都将民间视为文艺(包括诗歌)的重要舞台,因为这里有广阔的生活以及最庞大的劳动、生活及读者主体——人民。另一方面,“民间源源不断地为诗坛输送新的艺术生力军和生长点,开放、吸纳而繁复的存在机制使其成了诗坛的生机和希望所在”[9]54。在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新诗“歌谣化”努力是新诗取法民间的第一次尝试,方言、山歌成为新诗写作的重要资源。“大跃进”时代“新民歌运动”更是将民歌作为与古典相媲美的唯一出路,民歌所代表的民间传统颠覆了“五四”时期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第三代”诗歌运动则是远离政治的真正的民间诗歌运动,“为当代诗歌注入了新的元素,使其获得了主体性意义”[14]。可见,无论政治力量是否参与,对诗歌而言,民间既拥有读者、书写对象,也拥有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在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较早地注意到了新诗的两种不同倾向,即“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由于“人民”的政治性意义,此时“人民的文学”与80年代以来的“民间写作”相去甚远,但二者对语言的要求具有某种一致性,即口语的、平民的语言。进入90年代以后,正如陈思和所言民间文化形态“不过是因为被知识分子的新传统长期排斥,因而处于隐形状态。它不但有自己的话语,也有自己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对知识分子来说不仅仅感到陌生,而且相当反感”[15],这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盘峰论战”最深处的秘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分子写作”的主流地位逐渐确立,具有深远民间传统的“民间写作”渐入隐匿状态,日常和生活之诗不再有“第三代”诗歌的张扬,以至于“民间写作”渐被主流批评界所忽视,来自世纪末的时间焦虑也加强了“民间写作”自我去蔽的需要。在“民间写作”诗人看来,“知识分子写作”对其造成了巨大遮蔽,因此如何在“知识分子写作”的主流之外寻找“民间写作”的合法性成为题中要义,一场声势浩大的诗坛论争将被证明是抵达这种合法性的最佳的选择,“民间”凸显了社会变迁及断裂的意义,“又借助着这类词语在昔日主流表达中的意义,获取着多重合法性的论证”[16]79(戴锦华语)。通过论争,“民间写作”首先以“知识分子写作”这个“庞然大物”作为参照,以与诗坛“主流”相对抗的姿态表明立场,让90年代被遮蔽的“民间写作”得以显形。论争前后,“民间写作”着手理论构建,于坚、韩东、谢有顺、沈奇等人不仅极力为“民间写作”正名,也为其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在指摘“知识分子写作”弊病的同时,对“民间写作”的内涵、宗旨、特点等做了颇有建树的分析和总结。这让此前“民间写作”零散无序的状态有所变化,凝聚力日增,在诗坛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为争取“民间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的合法性,诗人和批评家付出了热情和才情,虽采取的方式有所偏激,但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实为明智。在诗歌被极端边缘化的时代,惟有引人注目的事件才能激发诗坛的活力,让这个有机体再次焕发生机。不少学者认为“盘峰论争”为诗歌带来的热度昙花一现,论战结束后,诗歌依然回归边缘。虽然“盘峰论争”双方忽视了如何处理历史的本质分歧,但论争最动人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再一次看到了诗人们毫无保留的真性情以及对诗歌的热忱,在“民间写作”这里,“盘峰论争”也让90年代的诗歌史无法忽视其真实的存在,对一种写作立场和审美倾向而言,这已足够。
四、身份意识与自我命名的焦虑
“盘峰论战”中,“知识分子写作”强调写作的“道义感”,“民间写作”呼吁“民间立场”,二者本质上的分歧即如何处理历史的分歧却并没有引起论战双方的注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世纪末诗人们身份意识的觉醒以及普遍日重的自我命名焦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诗歌秩序的建构成为诗坛的一大话题。程光炜、陈超、洪子诚、臧棣等批评家开启并引领了对90年代诗歌的讨论与建设,其中程光炜的成果牵涉到“90年代诗歌意义的几个基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8]1;陈超、臧棣对90年代诗歌的转向、趋势、成就等问题进行了论述;除了相关评论文章,丛书出版也是构建90年代诗歌的重要途径。其中包括洪子诚主编的“90年代中国诗歌”丛书、门马主编的“坚守现在书系”、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诗人自选集”、谢冕主编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等,诗歌选集如程光炜选编《岁月的遗照》、小海和杨克选编《他们1986-1996》等。颇有意味的是,除了谢冕主编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和《他们》十年诗选以及《岁月的遗照》中少到仅有象征意味的“民间写作”诗人,丛书和诗选所涵括诗人的并集基本构成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核心阵营,主要有欧阳江河、西川、陈东东、孙文波、肖开愚、王家新、张曙光、西渡、臧棣等诗人,其中前四位诗人“出镜率”尤高。可见无论是在诗歌批评还是诗歌出版方面,“知识分子写作”的优势都显而易见。需要追问的是,“知识分子写作”为何如此密集地发文出书?“民间写作”反击的深层原因何在?
埃斯卡皮认为作家群“也要跟其他人口集团一样,经历老龄化、年轻化、人口过剩、人口减少等相似的变异”,而“一本享有盛誉的文学史里编制的索引”[12]15是对这群人口下定义的方法之一,中国大陆诗人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是文学史的问题。高潮迭起的80年代诗歌已成为文学史上无法抹去的篇章,偏偏90年代诗歌骤然沉寂且走向边缘,加上新世纪就在眼前,“影响的焦虑”再一次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作家、诗人而言,被历史铭记或为普遍愿望。虽然埃斯卡皮认为“只有等作家死后,才能被认定是文学集体中的一员”[12]16,但他忽视了作家生前的活动尤其是自我历史化的活动将或多或少地影响其死后的历史序列,因为作家除了创作,还具有更大的能动性,作家自传、自我作品批评是自我历史化的有效途径。诗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着给诗歌和自我身份命名的双重压力。“从一体化体制内的文化祭祀,到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与‘体制’‘庞然大物’既反抗又共谋共生的文化精英,到90年代以来身份难以指认的松散的一群人”[17]356(周瓒语),诗人们一方面在自己的圈子里孤芳自赏,另一方面又在大众的嘲讽中倍感失意,此外,由于“挥之不去的诗歌崇拜”[13]275,身份成为90年代诗歌批评的“关键词”。周瓒认为,身份认同有两个特征,“一方面,不同出生的、不同职业的个人受制于一时代的强势话语力量(话语权拥有者);另一方面,通过忠诚于自己的精神选择,一个并不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诗人(作家),仍然可以在有限的民主和文化氛围中,寻求自身的精神立场”[16]96,而在确认身份之前,自我命名迫在眉睫。
以于坚、韩东为首的“民间立场”诗人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高举“民间写作”的大旗,与90年代以来主要批评家以及“知识分子写作”诗人否认“第三代”诗歌的诗学成绩有关。在程光炜看来,80年代诗歌与“十七年诗歌”、朦胧诗歌根本的思想逻辑是一致的,即意识形态行使着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权力”,90年代诗歌“多少有点像巴赫金所言的众声喧哗,但与80年代的瞎闹在本质上是截然有别的”,并在于坚、韩东与张曙光的对比中认为于、韩二人的反讽是单纯的讥讽[8]46-64;臧棣则指出技巧的匮乏“损害了第三代诗歌的感染力”[18]。在“知识分子写作”诗人及部分重要批评家看来,“第三代”诗歌的“运动性”意义远大于“美学性”意义。“民间写作”的溯源则从“第三代”诗歌起,到朦胧诗再到中国古典诗歌,以自身的延续性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性,也为其身份的指认提供更为切实的证据。在持“民间立场”的诗人这里,“第三代”诗歌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诗歌运动,“其意义只有胡适们当年的白话诗运动可以相提并论”[11]3,当以“第三代”诗歌为荣的“民间写作”诗人感受到来自“知识分子写作”及“新潮批评家”对“第三代”诗歌的否定,在认同焦虑和“文化英雄”崇拜的影响下,身份指认的形势迫切,毕竟被否决的是“民间写作”的“母胎”,这加重了“民间写作”诗人的不安。
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史属于朦胧诗及“第三代”诗歌,80年代末的“文化诗”虽有一定影响,但为前两座大山所遮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欧阳江河、肖开愚、王家新等人在90年代才逐渐为人所知)。故对“知识分子写作”而言,确立自身在90年代诗歌历史中的地位合情合理,以何种身份入驻则成为关键所在。欧阳江河认为80年代末以来国内诗人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过渡和转变已不可避免。问题是,怎样理解、以什么方式参与诗歌写作的历史转变?”[7]此后“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诗人和推崇这一写作的批评家们通过诗歌作品、批评及选本致力于欧阳江河所言的“历史转变”。无论是欧阳江河对于诗歌“过渡”和“转变”的判断,还是程光炜称之为“非连续性的历史关系”[8]47,都斩断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此前诗歌的联系。“知识分子写作”绕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诗歌成就,直抵五四启蒙时代的诗人们的使命感和诗歌的道义感,在诗歌文本上则回溯40年代的诗学主题:“在艾略特那里是非个人化表现,现实、玄学与象征的综合,在奥登那里是不避俗话俚语的叙事记忆”[8]60。
在“盘峰论争”中,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强调的道义感及独立的思考者身份,还是“民间写作”寻求的合法性和对抗西方文化的本土经验代言人的身份,基本的动力还是在于诗人们沉重的身份意识和自我命名的焦虑,“如何处理历史”这个分歧的起点则未被重视。在身份意识和自我命名的焦虑中,双方迫切地为自身存在提供证明,并试图通过这种证明在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空间中留下痕迹,“天空没有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的从容在“盘峰论争”双方这里,注定只能是一句唯美的“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