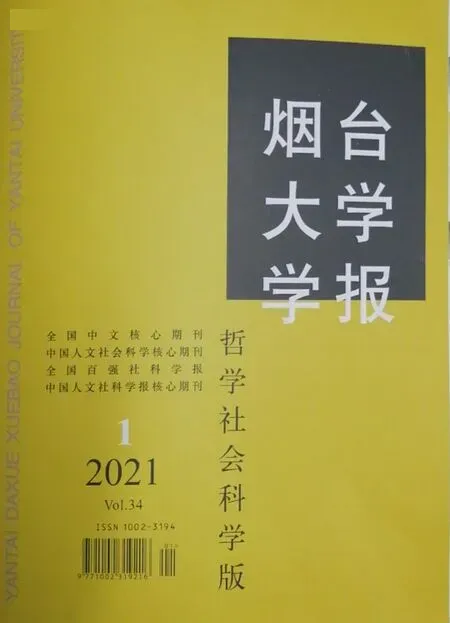先秦“五德终始”说的历史意识和推论
2021-11-30张富祥
张富祥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战国时期由齐国稷下学者驺衍(也写作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是一种著名的历史循环论,阴阳家用此说解释社会历史的运行,比孟子“一治一乱”的命题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
驺衍为地道的齐国人,史称其为稷下先生,生平稍晚于孟子,大约生活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半期,主要当齐湣王、襄王在位的时期(前300—前265)。《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1)《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第7册,第2848-2849页。
这里提到驺衍的著作有《终始》《大圣》两种。《汉书·艺文志》则著录《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合计105篇。疑《大圣》即《邹子》,或出于驺衍后学所编,实为阴阳家学派的著作,因尊驺衍为“大圣”,故又以名书。《大圣》之内容可能与《终始》多同,属于不同的抄本,驺衍本人的著作未必会多至105篇。后人引《终始》亦称《五德终始》或《终始五德》,大约《终始》之名从一开始就只是简称。
载籍所称驺衍的学说主要有两种,一是“五德终始”说,一是“大九州”说。后者以为古代中国所在的大陆为一个大州,包括九个小州,称为“赤县神州”的中国只是九个小州之一;全世界有九个大州,各被“裨海”环绕,九个大州又共被“大瀛海”环绕,于是中国便只当全世界陆地的八十一分之一。这种恢宏阔大的地理观,有类于今日地球陆地的“板块”学说,既出于祖居滨海之齐人的神奇想象,也应有着若干神话传说的依据。例如《山海经》所录诡怪博杂的“人文地理”,过去有不少学者就认为可能出自驺衍学派的编集。《山海经·海外南经》开头说:
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2)《山海经·海经》卷一《海外南经》,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的世界大地理,非普通人所能观睹,是只有“圣人”才能通晓的。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驺衍的著作又名为《大圣》。“大九州”说与“五德终始”说既出于一人,二者应该有联系,即“五德终始”既是纵向时间上的循环,也覆盖“大九州”而作横向空间上的循环。如此则纵横交错,皆往复不已,作为历史观念与政治哲学的“五德”便充满了整个宇宙,且其运行无始无终,有始和有终都只是循环过程中的小段落。
《史记·封禅书》说:“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裴骃《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3)《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4册,第1646-1647页。《孟子荀卿列传》亦谓其“作《主运》”。司马贞《索隐》又引刘向《别录》云:“邹子书有《主运》篇”。(4)《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7册,第2849-2850页。看来,“五德终始”说的原理集中于其书《主运》篇。“运”指气运,实指帝王和国家的气脉、运命及形势等,亦即所谓“五德”之“德”。驺衍的书,包括《主运》篇,都早已失传了,其“五德终始”说的详细论证已不可见。《吕氏春秋·应同》篇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此说的骨架,其文如下: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5)《吕氏春秋》卷十三《应同》,《诸子集成》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6-127页。
这段文字的最后两句话,即“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可能是《吕氏春秋》的作者加上去的,但上面的基本内容应该还是驺衍原书的记录。《吕氏春秋·荡兵》篇还记载:“炎、黄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这也是谈“五德终始”的,可见驺衍原对炎、黄、共工氏及其他“五帝”的“德”也是有排列的,但《吕氏春秋·应同》篇只列举了黄帝与夏、商、周诸朝之间“五德”的转移,又下及即将兴起的秦王朝。
《史记·封禅书》对“五德终始”说有复述: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6)《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4册,第1643页。
此文与《吕氏春秋》一致,唯所记符瑞有个别差异,不是问题。
“五德”在形式上,附会物质化的五行,分指木德、火德、土德、金德、水德。这五种“德”分别与东、南、中、西、北相应,又与服色的青、赤、黄、白、黑相应。以“五德”应用于社会历史,使之各与朝代相应,皆自有始有终,始于朝代建立时的祥瑞,终于朝代灭亡时的灾异,终而复始,循环不止,也就形成所谓“五德终始”说。五行有相生和相克两种循环:相生顺序是木—火—土—金—水,前者生后者,至水而再生木;相克顺序是土—木—金—火—水,后者克前者,至水而再克土,即所谓“胜者用事”。驺衍用的是相克之法,《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引《邹子》曰:“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7)《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诸子集成》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6页。《文选·晋武帝华林园集诗》李善注引《七略》亦云:“邹子有《终始五德》,言土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8)《文选》卷二十《晋武帝华林园集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册,第953页。依此法,从黄帝开始的“五德”即为如下模式:黄帝时有大蚯蚓和大蝼蛄(古人以为是黄龙和土精)之类出现,故黄帝为土德,尚黄色,按土德行事;夏禹时草木秋冬不死,故夏为木德;商汤时水中出金刀(或说山里流出了银矿),故商为金德;周文王时有一群赤色的大鸟,衔着用丹漆书写的玉版,落到了周人的社坛建筑上,故周为火德。这也就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的顺序,再至秦代周则是水克火。若即将建立的秦王朝不知道自己为水德,不按水德行事,那么水德的气数到头时,就会转移到他朝,此即所谓“数备将徙”。这一套附会阴阳五行的学说,内涵相当复杂。顾颉刚先生曾说,驺衍的思想“是讲仁义礼乐的鲁文化和夸诞不经的齐文化的混合物”。(9)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古史辨》第五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243页。这话可能是对的。照《论语·雍也》所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10)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第一册,第128页。,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交融到春秋战国时代已是大趋势。驺衍的“五德终始”说即可说是齐学与鲁学交汇的产物,或说主要是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的混合物。
阴阳五行学说原是在齐国最为盛行的,其开创并不始于驺衍。甲骨文中已有“阴”“阳”二字,金文中则出现了“江汉之阴阳”“以阴以[阳]”及“阳春”等语,(11)分见《殷周金文集成》73-80、428、11324。可见“阴阳”概念起源很早,先秦典籍也广涉阴阳学说。“五行”一词可能较晚起,然《尚书·洪范》已明确以水、火、木、金、土为“五行”,《墨子》《国语》《左传》中亦屡见“五行”字样。阴阳说与五行说的合流,在《管子》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般地说,天地生阴阳,阴阳成四时,四时分为十二个月,这是通行的观念和制度。《管子》的《幼官》《幼官图》和《四时》《五行》《轻重己》诸篇,都是较早的时令文献,其《四时》篇还是按照一年四季的划分谈时令行政的,而《五行》篇已将一年的时间分为5个时段,每段为72天。《幼官》和《幼官图》记载一年有30个节气,每个节气为12天,有两个节气跨季度,实际是以五行说的五时系统和十二月制的四时系统相调和的。《轻重己》篇又有四时八节令的分法,每个时段为46天,已是以天文观测为基础了,并且节气从冬至开始,此亦即西周以后历法常见的岁首设置之起点。《灵枢经》卷十一所记及1977年在安徽阜阳汉墓中出土的九宫式盘,和《轻重己》所记都为同一体制,只是《灵枢经》有两个节气作45天,九宫式盘有三个节气作45天。(12)有关《管子》中的时令文献,可参拙作《〈管子〉书中的“幼官”和有关节气问题》,《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和《礼记·月令》(二者文字相同)是汉代以来最为流行的时令文献,而在“季夏纪”还保存着“中央土”一项,与十二月体制合不拢。《淮南子·时则训》也未去掉这个尾巴,且又有增补。这点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关,因为皇家尚黄,号令四方,所以“月令”中的“中央土”一项也不可去。这类文献都是结合时令谈王者时政的,如《管子·五行》篇所称“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总别列爵,论贤不肖士吏”之类,《吕氏春秋·孟春纪》则称“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等,具体的项目或有不同,而都不脱离阴阳五行。见于《管子》的相关内容当然还只是齐文化的一个侧面,但综观各种载籍可知,阴阳五行学说到春秋战国时代,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齐国则尤为这一流派学术的大本营。驺衍的“五德终始”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他也因此成为阴阳五行家学派的主将。驺衍和鲁文化、鲁学的关系,旧时推论较少,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顾颉刚先生曾说:“我很怀疑驺衍亦儒家。他的学说归本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此其一。《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有驺衍论‘辩’一节,(胡)适之先生以为完全是儒家的口吻,与荀子论辩的话相同,此其二。《史记》以他与孟子、荀卿合传,此其三。西汉儒者如董仲舒、刘向等的学说与他极相像,此其四。”这些都反映出,驺衍的思想与儒家学说是不无相通之处的。顾颉刚先生因此接着指出:“如果这个推论不误,我敢作一假设:《(荀子·)非十二子》中所骂的子思、孟轲即是驺衍的传误,五行说当即驺衍所造。”(13)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古史辨》第五册,第240页。
现在看来,顾颉刚先生推论驺衍为儒家,可存一说;但假设《荀子·非十二子》对思、孟学派的批评乃是针对驺衍的传误,却是有问题的。《荀子》书中对孟子的学说多有批评,其《非十二子》篇更明确抨击思孟学派云: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14)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二册,第59页。
如今学者共知,由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及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五行》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荀子所称思、孟“案往旧造说”的“五行”实为“仁义礼智圣”,盖犹后世所称的“五常”,而并不是指五行家习称的“金木水火土”。(15)有关帛书《五行》与楚简《五行》,可参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陈来:《竹帛〈五行〉篇为子思、孟子所作论——兼论郭店楚简〈五行〉篇出土的历史意义》,《孔子研究》2007年第1期。大概顾先生当时尚以为思、孟之“五行”即《洪范》之“金木水火土”,故谓“五行说当即驺衍所造”。也许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评,主要是针对这一学派以“五行”之名概括儒家德目的“甚僻违而无类”而言的,亦即以为此种比附既有悖常理而又不伦不类,并非是指“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学说“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然则《史记》指称驺衍的学术“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其“始也滥耳”四字,按司马贞《索隐》所说:“滥即滥觞,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滥为初也。谓衍之术言君臣上下六亲之际,行事之所施所始,皆可为后代之宗本,故云滥耳。”(16)《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7册,第2849页。如是,则驺衍的学术宗旨还是务必要归结于仁义和节俭,并且期望在君臣上下和六亲之间推广施行的。司马迁的评述以“仁义”和“节俭”联称,颇值得注意。齐国的风气,自齐桓公称霸以来,就是极为奢侈的,《管子·侈靡》篇还曾倡言趋时兴化“莫善于侈靡”。此种风气流行百余年,至春秋末齐景公时,仍然“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17)《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5册,第1819页。;及晏婴为相,乃力为矫之,“以节俭力行重于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18)《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7册,第2597页。。然下至好大喜功的齐湣王时,奢侈之风也并未改观。《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游说齐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19)《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7册,第2750页。《张仪列传》又载张仪游说齐湣王,“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20)《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7册,第2788页。《战国策·齐策一》也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21)《战国策》卷八《齐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94-195页。这类文字为纵横家言,或略有夸饰,然质诸当时齐国风俗,未必甚过。驺衍处在此种情势之下,或以为神州不过是天下八十一分之一,齐国又是神州之一隅,如此浪费下去,国将不国,所以主张节俭;同时晏婴也曾提倡以礼治国(虽然他不用孔子),所以驺衍也以仁义教化和伦理纲常为治道之本。由此推论言之,驺衍既归本于“仁义节俭”,则其学就必然向儒学靠拢。《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述驺衍的“尚德”观念,以“大雅整之于身”为言,所谓“大雅”实指德劭才高之人,正显示出驺衍对儒家圣贤修齐治平路线的期待。其实,齐文化原本就不排斥儒学,《荀子》之书的治国理念就是隆礼而重法的,《管子·牧民》篇也醒目地记载着“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还记载说:“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22)《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7册,第2851页。这所谓“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也包括驺衍的“五德终始”说在内,则其说本来就是因有为而发的,目的即在耸动人主,归向以儒治国。驺衍没有采取孟子“一治一乱”的论断,但他也许正是受到孟子的启发,又以阴阳家的立场将五行学说移用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才创立了“五德终始”说。五行相克的系统是“数备将徙”的,即每一“德”满一个圆周就将被替代;不过“五德”不是均匀的,人主各据一“德”,治则不满,乱则满。这便把“一治一乱”的经验性说法整齐化了,变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从历史观上看,驺衍把自然界的历史分为两截,即天地剖判以前的混沌状态和天地剖判以来的历史。所谓天地剖判以来的历史,按说还应以人类的起源为分界而划分前后,不过驺衍实用以指称人类社会的历史。这段历史又分为两截,即自有人类以来至黄帝时代以前的历史和黄帝时代以来的历史。这样的区分当然也不仅是驺衍的发明,如《庄子·缮性》篇说: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戏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23)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第三册,第98页。
《缮性》属于《庄子》外篇,其写作不一定是在庄子的时候。庄子学派用“德衰”的观点看待历史,尚质朴而抑文明,所谓“德”即指世道而言,以为世道愈文明而德愈衰。驺衍只讲“德”的转移,潜台词是德衰则转盛,与道家异趣。但《缮性》篇从“混芒(茫)”叙至炎、黄、唐、虞的“治化”,与驺衍的历史叙述相通。这也是战国时代流行的观念,而切实的历史叙述仍普遍始于黄帝,也就是先秦学者所追溯的“五帝”时代以来的华夏史。同时驺衍把华夏史扩大到世界史,这是以往的历史意识所不及的。
按驺衍自定的原理,“五德终始”说是适用于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但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他对黄帝以来的编排,他的原著对前此的历史演变还有无传说或自造的名目,今已不能详。他的历史观的核心还是一个“变”字,表现形式是朝代更迭的“从所不胜”,即“新朝之起必因前朝之德衰,新朝所据之德必为前朝所不胜之德”(24)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古史辨》第五册,第245页。。这样说来,“五德”的转移虽是循环的圆周,实际在每一“德”循环之后,都已不是原有的形态,名同而实异。因为是相克,历史大势便是向前的,不会因为暂时的衰退而总是向后,衰退本身即培育出相克的因素,直到造成“德”的转移。有人称“五德终始”说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此乃以今喻古,难为妥当。然承认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性质,“优胜劣汰”的矛盾和竞争是常态,也不失为一种进化论的见解。从理论上说,循环论也不是要全部剔除进化,而进化也并非都是直线式的。有记载表明,驺衍也是主张治道因时而变的,并非一味讲求循环。《汉书·严安传》载“臣闻邹子曰”:
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25)《汉书》卷六十四下《严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9册,第2809页。
严安是临淄人,所引驺衍的话应是准确的。这话是驺衍思想的精髓,单独来看,并不涉及“五德终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制度措施是为了救弊的,当时有效用,过时则不用,有需要改变的就改变;如果时过境迁,还守着固定的法度和措施不变,那就是不懂得社会治理之道。据此可知,驺衍虽号称“谈天衍”,至于论治道,还是极重实际的,不认为有什么东西可以一成不变。这种反对守经而主张权变的观念,正为齐文化的风格。有意味的是,严安于上引文下接着说:“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示)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无节,则不可赡,民离本而徼末矣。”(26)《汉书》卷六十四下《严安传》,第9册,第2809页。其奏疏首先便抨击奢侈之风,适可与驺衍止乎“仁义节俭”的治学宗旨相对看,从而借以考见“五德终始”说提出的社会现实背景。
“五德终始”说对秦汉政治有重大影响。《史记·封禅书》说:“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27)《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4册,第1646页。采用的结果便是《秦始皇本纪》所说的以本朝为水德,“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2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1册,第306页。之类。这些都是形式上的,秦始皇骨子里头还是“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2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1册,第306页。然其行若不合于水德,从循环程序上说,其他的“德”也都可备选。“五德终始”是讲变的,秦王朝形式上的继承掩盖了“变”的实质,自然也就不顾及驺衍所重视的“仁义节俭”等。显而易见的是,秦始皇称“帝”以“始皇”为名,希望皇权“万世一系”,规定其继任者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这就是一种“不变”的思维。若此,“五德”就长久停滞,无所谓“终始”了。汉朝是水德、土德还是火德,曾引起不尽的争论,也还是表面文章,不关乎政治的根本。汉代思想家用阴阳学说极多,但宗旨各有所主,不过是用驺衍的学术为外在的框架,断不能都划归阴阳家。特别是董仲舒的学术,着力宣扬“天人感应”,看似是驺衍学术的延伸,如果仅仅把他当作驺衍学术的继承者看待,那就无法解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大决策了。
有人认为“五德终始”说是讲天命的,因为它重视符应。实则大凡关于自然界“五行”的扩展说法,都有些迷信的成分,非是科学的推论。“五德终始”说的基本性格是历史的,讲求治乱盛衰的转移,与孟子的“一治一乱”之说并无根本性的差异,现在所知驺衍的论述也不及于天命。孟子曾以“仁义礼智圣”为“五行”,可能属于概念的嫁接;后世统治者以天命附会五行,不能作为原始的五行说指向天命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