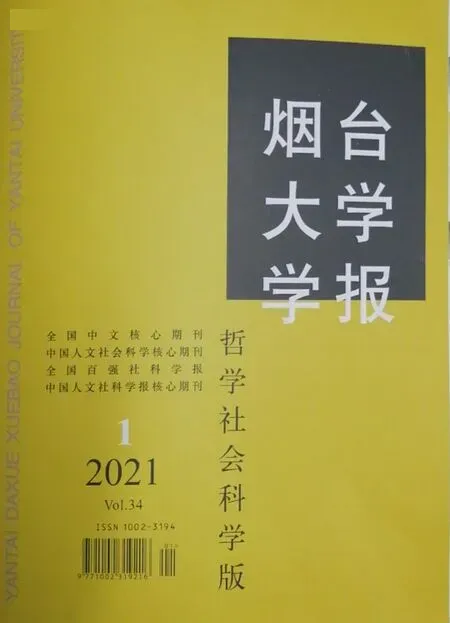从古诗时代到拟古时代
——《文选·杂拟》中的文学史观
2021-11-30郝若辰
郝若辰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一、《文选》中的拟古与拟乐府
现代的中古文学研究,区分出了“古诗”与“乐府”一组相对的概念,进而推衍出“拟古”与“拟乐府”之间的分别。根据后代的标准,“是否入乐”是对乐府最直接的狭义限定。当然,人们通常会采取一个稍稍宽容的标准,将使用乐府古题的篇目也纳入乐府,于是在某种情况下,“拟乐府”作品也属于乐府。因而在一般观念中,“杂拟”基本等同于“拟古”,是与“拟乐府”相对的概念。观察《文选》杂拟类所录篇目,大多数与乐府无关,而是对此前文人诗主题或风格的模拟。
然而,萧统当时所持的是一种不甚精致的乐府观,其中还掺杂着“非今是古”的倾向。《文选》乐府的取舍,基本是以篇名为准,如:XX篇、XX行、XX歌等。除古乐府三首和班婕妤《怨歌行》外,作者都是魏晋文士。另外,在《文选》的乐府观念中,是否入乐也不构成一个关键标准。综合六臣注本,《文选》四十一首“乐府”中只有约三分之一曾经入乐演唱,相反,真正入乐的郊庙祀歌和杂歌都被分别归入其他类别之中。
《文选》中也并非仅凭篇名就一概而论是否属于乐府,例如陆机《君子有所思》归于乐府类,而鲍照《代君子有所思》却归入杂拟类;同样还有南朝宋袁淑《效曹子建乐府白马篇》属于杂拟,然而曹植原作却属于乐府。即便同用乐府诗题,魏晋时期作品可入乐府,而南朝作品却归为杂拟,由此可见,萧统在判断乐府诗时有某种崇古倾向。
另一例证可以通过与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对照发现,这一点胡大雷《文选诗研究》中早已提到:
《文选》诗乐府类共录诗作四十一首,其中入相和歌辞者二十六首,入杂曲歌辞者十四首,入鼓吹曲辞者一首。入相和歌辞者自然是汉魏旧曲或拟汉魏旧曲者;入杂曲歌辞者,其中古辞与汉、魏、西晋所作者自然是旧曲,其中谢灵运与鲍照所作亦是旧曲。谢灵运《会吟行》与鲍照《出自蓟北门行》、《结客少年场行》,即《乐府诗集·杂曲歌辞》解题中所说“复有不见古辞,而后人继有搜述,可以概见其义者”,其中所举就有上述三诗;鲍照《苦热行》、《升天行》,曹植都曾有作,可见也是旧曲。由上可知,从《文选》所录乐府作品来看,萧统是偏向于录汉、魏旧曲的。当日的新兴乐曲是清商曲辞,《文选》一首未录,由此亦可见萧统的传统观念。(2)胡大雷:《文选诗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2页。
值得补充的是,《文选》中对南朝清商曲辞摒弃不录,这与其对典正风格的偏向,以及和同时代的《玉台新咏》分工不同有关。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萧统“是古非今”的乐府观念,这种观念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诗歌发展情况的。较晚的乐府创作,其文人风味与词句的雕琢都更明显,与文人诗之间的差异几乎已经被弥合。可见萧统作为诗人和诗集编纂者,基于对风格的把握,在判断一首作品是否属于乐府时,并非一概以篇题或古今论之。例如《文选》中陆机分别有拟乐府和拟古诗,陈祚明评价:“拟古乐府,稍见萧森;追步《十九首》,便伤平浅。”(3)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 293 页。从类目来看,拟《古诗十九首》属于杂拟,拟乐府十七首皆属乐府,其中《饮马长城窟行》《长歌行》乐府古辞原作同见于《文选》。通过以上对萧统乐府观的讨论,《文选》“杂拟”大致等同于拟古而区别于拟乐府的结论仍可成立,即两晋以来的作者对此前文人经典诗作的模拟。
既然魏晋拟乐府之作皆入乐府,为何却单列“杂拟”一类,而不将其直接归入与其风格内容相近的“杂诗”中?仍以陆机诗为例,其拟乐府十七首在乐府类,而拟《古诗十九首》却不属于《古诗十九首》所在的“杂诗”,而入“杂拟”类。《文选》分类中这种对“模拟”的强调是为了表达何种诗学观念?当时作者模拟的典范作者和主要风格又是哪些?他们所采用的摹拟方式,例如多用组诗形式,全方面关注主题、口吻、风格,为何独见于两晋、南朝文人?
二、杂诗与杂拟概念厘辨
杂诗类目是前人论《文选》编纂系统中溢出条目的主要例子,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提到:“《文选》按文体分为三十九大类,大类之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杂歌’、‘杂诗’、‘杂拟’在诗类最后,盖其内容难以列入‘补亡’、‘述德’、‘祖饯’、‘游仙’等小类也。”(4)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39页。这大致能代表学界对《文选》中这些溢出部分的普遍解读。
如果仔细梳理“杂诗”类下所录篇目,其中一些有较明确的主题,似乎能够归入其他小类之下。例如张协《杂诗十首》其七(此乡非吾地)、其八(述职投边城),依照内容完全可以归入“军戎”一类,保持组诗的完整性当然也是编纂时的重要考虑。同时这也涉及到“杂诗”与组诗间的关联问题。在非组诗作品中,谢灵运的几首诗多可入“游览”类,如《田南树园激流植援》《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迥溪石濑修竹茂林诗》,同样还有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谢朓《观朝雨》等。而谢朓等人的诸多应和之作,也完全可以归入“赠答”类中。另外,文选杂诗类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中为汉魏古诗以及此后题为“杂诗”的作品,而下卷中的诗作都有具体篇名,并非如前人所说:“古人所作,原有题目,撰入《文选》,《文选》失其题目,古人不详,名曰杂诗。”(5)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卢盛江校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50页。因而可以断定,萧统在归类时是以内容而非诗题作为判断依据的。
考察前文所提到的张协、二谢等人作品,除题目所揭示的明显主题之外,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复合性主题的特征。《杂诗》上卷所收无确定题目的作品,主题模糊或多主题正是这些作品没有定题而以杂诗名之的原因。例如苏李诗,便可看作集行旅、军戎、咏怀、赠答主题于一体;谢灵运《斋中读书》,即事之中兼以咏史、咏怀;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赏月起兴,后半首转入行旅和咏怀;谢朓的几首赠答诗,主体内容有极强的游览意味。
前人论杂诗,也曾注意到这种多主题的情况。杨伦《杜诗镜铨》“秦州杂诗二十首”引张溍云:“随意所及,为诗不拘一时,不拘一境,不拘一事,故曰杂诗。”(6)杨伦:《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39页。吴淇《六朝选诗定论》云:“诗不专指一事,亦不必作于一时,称物引类,比兴之义为多,故题名曰杂诗。”(7)吴淇:《六朝选诗定论》,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第113页。
《文选》李善注对杂诗的解释是:“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8)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75页。所谓“遇物即言”,即“能言人同有之情”,抒发汉魏当世文人的普遍悲慨。如陈祚明论《古诗十九首》“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逐臣弃妇与朋友阔绝”。(9)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第80页。仅此二端,其中已有咏怀、哀伤、行旅三意。汉魏离乱,故托军戎;生死阔绝,则有挽歌;别离相思,则有祖饯、赠答;古今同情,则有咏史。仅从人人各具的同有之情,就能推衍出《文选》诗部三分之二的主题。由此来看,杂诗类的作品是抒情主题最为复杂的,同时也是最为纯粹的。古今许多独具慧眼的论者已经发现,《文选》杂诗类正是诗部艺术水准最高的部分之一。
杂诗类作品多主题的另一层涵义是,这一部分作品,以年代最早的五言《古诗十九首》和苏李诗为裘领,代表了诗歌从使用套语集体创作、并无具体主题和诗题的《诗》《骚》之作到后世具名之作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诗题”条:
三百篇之诗人,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国并无一题,雅颂中间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赉》、若《般》,皆庙之乐也。其后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无有也。五言之兴,始自汉魏,而十九首并无题,郊祀歌、铙歌曲各以篇首字为题。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杂诗》,而不必同其义,则亦犹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10)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61页。
吴淇论曹植《杂诗》与《离骚》关系时也说:
《杂诗》六首似皆原本于《离骚》。吾不知其有意摹之欤?抑无心偶合欤?一章“高台多悲风”,即《思美人》。二章“转蓬”,即《悲回风》。三章、四章“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即《经》所谓“蹇修”,乃《离骚》之正托。五章“仆夫早严驾”,即《远游》。末章“咏烈士”,即《九歌》之《国殇》。此诗旧注,以为皆请自试之意,然实非请自试诗也。故诗中不耑指一事,亦不必作于一时。称物引类,比兴之义为多,故题名曰《杂诗》。(11)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第113页。
吴淇将曹植的《杂诗》与《九歌》相关联,这说明他也关注到了《杂诗》六首内部的意脉关联。应当说,《九歌》是最早的感遇抒情组诗,“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12)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5页。除了与《九歌》有直接关联的曹植《杂诗》之外,钟嵘《诗品》中与《楚辞》有源流关系的作者李陵、张协、陶潜、张华,皆有组诗作品见诸《文选》“杂诗”类。
我们无法断定这是对《九歌》的直接效仿,还是这类感发于生命基本母题的作品特别适合以组诗的方式结构。正如方东树所谓“遣兴之作”:“人有兴物生感,而言以遣之。是必有名理、名言、奇情、奇怀、奇句,而后同于著书。不拘一事,不拘一物、一时、一地、一人,悲愉辛苦,杂然而陈。”(13)方东树:《詹昧昭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11页。因而,以《古诗十九首》为裘领的“杂诗”应当被看作是存有古意的特定诗类,而并非《文选》以主题为纲编纂系统中的溢出部分。前文中已讨论过,“杂诗”自有其主题方面的鲜明特征。钱志熙《魏晋“杂诗”》一文也提到,杂诗是“魏晋时期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魏晋诗人凡是创作杂诗者对此都有明确的意识”,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14)钱志熙:《魏晋“杂诗”》,《文史知识》1996年第2期。并且,“从建安诗人如王粲、曹丕、曹植、刘桢诸家到阮籍《咏怀诗》,再到傅玄、张华、张协、左思诸家,最后是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饮酒》二十首,直至影响到后代的《古风》、《感遇》一类诗,都属于‘魏晋杂诗’一脉。”(15)钱志熙:《魏晋“杂诗”》,《文史知识》1996年第2期。就像“唐音宋调”可以代表一种超越时代的风格一样,“魏晋杂诗”也可以不仅指魏晋诗人的这批作品,而且用来指在这一时期开拓形成并由后代诗人不断承续强化的创作风格。它首先是后世五言古诗的典范风格和重要创作流派。在《文选》的诸多小类中,“杂诗”以其最强烈的抒情言志风调自成一格。胡大雷认为,“杂诗”是“咏怀”类的先声。事实上,许多其他小类都能在杂诗中找到母题,因为它展现了诗骚合流的初始阶段,这也是为何《古诗十九首》被陆时雍称作“风余”和“诗母”的原因。
这样来看,“杂诗”不仅是因总集编纂所需而发明的概念,而且是特别关注南朝诗歌发展的一种风格界定。“杂诗”概念此后变得暧昧混沌,是因为《文选》的立类如同墓碑,在给以定论的同时也为其盖棺。后世作者偶以“杂诗”命篇,但已不构成一个统一的诗类。直接以“杂诗”命名的作品,在南朝呈锐减趋势,至有陈一代已无迹可寻。隋唐以来,虽已罕见杂诗,但这类内核为拟古的作品又以“古诗”“古风”“感遇”“咏怀”等诗题重新出现。其中组诗仍占极大比例,即使有了精致的近体诗,新的一代诗人仍旧学着五言先驱们的样子,吟唱着忧生念乱的哀歌。
三、杂拟:对传统的互文与评价
《文选·杂拟》共收入晋代到南朝十位作者的六十三首作品,虽都是对前人作品或古题进行效仿,但模拟方式和限度却不尽相同。前人在研究中已对其进行了详备的分类,例如葛晓音将晋宋之间的拟古诗分为四类,我们大致沿袭此说进行分析,这种分类不但清晰明确,而且能很好地涵盖本文讨论的作品范围。(16)第一类全篇模拟,从题材、主题、内容到情景、句式,基本仿照原诗;第二类不拟体式,但模拟古人的风格口吻;第三类仅拟古诗的传统题材和主题,而篇制结构及表现均不求似;第四类名为拟古,但没有专拟的题材和主题,而是吸取古诗中的某些表现方式以寄托自己的情怀。参见葛晓音:《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文选》刘良注曰:“杂,谓非一类。拟,比也;比古志以明今情。”(17)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第575页。晋宋之间“汉魏古诗”的风格体式已经形成,诗人们在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创作的同时也忧虑,在声律、南朝民歌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新的创作倾向和潮流,最终会冲毁“汉魏古诗”的旧河道,因而以“拟古”的幡麾以招其英魂。
对古题旧作的模拟毫无疑问是古典诗歌与文学传统相互勾连、秘响旁通的渠道之一,中国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中向来强调依循传统、辨章源流。这与西方的互文理论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互文理论常常运用“拼接”或“编织”的隐喻。“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18)茱莉娅·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和小说》,李万祥译,《文化与诗学》2011年第2期。这是互文性理论的一个层面,即在文本中可直接见其底文(热奈特)。而本文讨论的拟古作品则处于更高一个层面,除了第一类全盘模拟的情况之外,底文常常在不着痕迹中被檃栝,体现于题材、语气、风格之中,因而构成热奈特所谓的“超文”。“超文的具体做法包含了对原文的一种转换或模仿,先前的文本并不被直接引用,但多少却被超文引出,仿作就属于这一类型。在仿作的情况中,并没有引用文本,但风格却受到原文的限定。”(19)蒂费娜·萨摩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页。《诗品》奠定的诗歌批评传统往往是单向度的,就像惯用的“源流”的比喻。然而更多时候,面对“超文”我们无法指定某个清晰的上源,因而需要在“互文”的语境下,更多关注于文本如何在其生成时代接受及评估它所面对的传统。
既然谈到“拟古”便涉及到对“古”的定义,并非泛泛的过去最终都能够被称作传统。所谓“拟古”究竟在模拟什么?除了模拟之外还评价、定义了些什么?“一种文化中,‘他者’文本在文本中的在场,它不只是简单地意味着‘影响’,也不仅仅包含特别的指涉或典故,而是在文本性重新界定的部分。”(20)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页。回到《文选》当中,杂拟类虽包含多种不同的模拟方式,但其共同模拟对象便是《古诗十九首》、苏李诗以来奠定的五言诗写作范式。当然,在《文选》编纂的时代,这些又自然而然地被上溯至“诗骚”。然而,新的文本进入历史之后可能形成新的传统,“魏晋古诗”作为被模拟的范式,在《文选》的框架内即是“杂拟”对“杂诗”的模拟。尽管这批典范作品去萧统的时代尚不很远,但此番模拟在历史话语中对它们进行了重新界定。
《文选》杂拟的出现,象征着一个体认与总结传统的时代,其中的作品表达了强烈的文学史意识,既有文人团体、风格流派的归纳,也有对于究竟哪些前人作品能够成为范式文本的探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和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两组。这两组作品之前都有一篇小序,在古典诗学里,诗序向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例如《毛诗序》便是解读《诗经》的第一道符码。而诗人自序则象征作者对其作品的文学自觉。除总序之外,谢灵运一组每首诗下有人物小传(除主人魏太子),以一句话概括被模拟者生平与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例如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陈琳“袁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江淹一组则是捻出一词,作为被拟作者经典主题的概括,例如“李都尉 从军”“魏文帝 游宴”“陈思王 赠友”“刘文学 感遇”等。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曰: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燕,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21)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32页。
序文中可以见到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自身的感往寄兴:“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可与《古诗十九首》 “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或《兰亭集序》等文本对读,这是“杂诗”的共通之义。杂拟中“不专拟,重寄托”一类作品之所以题作“拟古”“效古”,皆因具有此义。
然而仅此尚不足以说明这组限定了时、地、人的拟作的具体作意。这便涉及到序文的第二层表达:感叹文献缺失(“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并同时强调了曹丕首倡的“集”的概念。“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撰其遗文,却为一集。”(22)萧统:《文选》,第1432页。谢灵运的这组拟作,除借古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外,还表现了对文学团体、创作活动和文献整理的观念。
相比较而言,江淹《杂体诗序》中则体现了更少的个人成分,着重表达的是谢序的第二个层面:
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朱成采,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故蛾眉讵同貌,而具动于魄,芳草宁其气,而皆悦于魂,不其然与?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则忌辛,好丹则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乃及公仲宣之论,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评,人立矫抗,况复殊于此者乎?又贵远贱近,人之常情,重耳轻目,俗之恒蔽;是以邯郸托曲于李奇,士季假论于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兴,谅非敻古,但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璧浮沉之殊,仆以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摧云尔。(23)萧统:《文选》,第1432页。
这段话围绕对前代文学的评价问题,并对五言诗的不同写作流派进行辨体,“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然五言之兴,谅非敻古,但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虽然江淹不满于“贵远贱近”,给出了“具美兼善”的折中评价,并强调自己的一组作品不足以“品藻渊流”。事实上,江淹并非没有崇古之意,在模拟的同时也正为后人提供了一批古典范式。除此之外,江淹拟作也有意识地体现此前诸家作品之间的区别,李善注曰:“江之此制,非直学其体,而亦兼用其文。”(24)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第651页。这组模拟将古人创作的方方面面,从代表主题到风格口吻,通通纳入进来,其中自然体现了五言诗形成以来的流变。何焯也评价道:“所拟既众,才力高下,时有不齐。意制体源,罔轶尺寸,爰自椎轮汉京,讫乎大明、泰始。五言之变,旁备无遗矣。”(25)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2-93页。除江淹一组外,“杂拟”中“兼用其文”者还有鲍照《学刘公幹体》,体现对刘桢作品风格主题的归纳和效仿。
《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也关注到了这类作品对于文学传统的总结意义:“有时候,诗人模仿一位早期诗人的‘体’,也即这位诗人的总体风格,而不是他的某一首特定的诗,比如王素的《学阮步兵体》。像这样的诗显示了拟作者对不同诗人的个人风格越来越强烈的认识,以及对文学传统延续性的意识。”(26)宇文所安、孙康宜等:《剑桥中国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62页。
《文选》杂拟中除谢灵运、江淹两组外,还有陆机、刘休玄拟《古诗》,陶渊明《拟古》都以组诗的方式进行架构。前文中讨论过“杂诗”中的组诗现象,既然“杂诗”一脉多有组诗,因而亦见诸对其拟作中。另外,有些拟作着意在史的立场上进行诗学范式的讨论,展示五言诗发展中的“蓝朱成采,杂错之变”或体现文献学中“集”的观念,这类作品更是非组诗无以结构,以组诗论诗的传统一直绵延至杜甫、元好问、赵翼、袁枚等人的论诗组诗中。
四、前夜:古诗时代的失落与拟古时代的来临
前文从《文选》入手,讨论过这一时期“杂诗”类别的确认与“杂拟”的产生与书写,并且认为萧统对《文选》诗的分门设类是有充分的文学史考量的。在萧统的时代之后,“杂诗”与“杂拟”皆产生了新的变化。前文已经提到,南朝陈以后“杂诗”这一名称便极少被使用,然而这一诗类仍在,常名以“古诗”“古风”“古意”“感遇”“咏怀”等。此后的“杂拟”,即学古模拟之作中,“亦步亦趋地模拟”和“学其文兼效其体”两类作品比例大幅减少,而书写古题和广泛拟古的作品增多,并且这部分作品与之前提到的“古诗”“古风”“古意”等界线并不清晰。表面上看来,这似乎体现的是“杂拟”的消退,然而,冠以“古风”“古意”的作品无不是对汉魏古诗风格的模拟与追怀,因而这一现象背后其实是古诗时代的失落。
东晋到南朝时期,是五言古诗发展的极盛和转折时期,虽然此后它始终是最重要的诗体之一,其汉魏以来几乎独尊的地位却永远无法重现。声律意识的萌发决定了这是近体诗出现的前夜,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近体诗的影响下,五言古诗显然无法泾渭分明地守住自己的阵地,并且随着汉语言的发展,逐渐趋向更紧凑密集的表达。并且在政治上,南朝与北朝的分裂意味着诗歌创作必然从悲凉刚健到纤巧清绮,这也预示汉魏音调的暂离,而此时距离重引北朝贞刚入齐梁清新的初唐尚有不短的时间。
也许因为敏感于这一系列已然或未然的重大变革,感受到某些创作传统的消逝倾向,从文学整体发展来讲,这一时期也是自觉与总结的时代。《文选》《玉台新咏》等诗歌总集编纂便体现了这点,讨论谢灵运《拟邺中集》一组时我们也提到从曹丕到谢灵运“集”的观念的确立,同时确立的还有五古创作的传统与范式,模拟与总结的意识也正体现于《文选》“杂拟”。
从时间层面上讲,这也是一个拓展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对过去进行回顾的时期。我们发现很多诗利用了魏晋乐府旧题,还有很多以“拟古”“效古”“依古”“代古”和“古意”为题的诗歌。(27)宇文所安、孙康宜等:《剑桥中国文学史》,第261页。《剑桥中国文学史》将其当作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并试图对相关问题给出更多解释和描摹。其中也提到了以谢氏家族为中心的对文学选集的编纂,以及在这前后出现的诗歌史写作:
伴随着乐府的复兴以及对“古诗”的兴趣,五世纪的作家们发展出对文学史的强烈意识,真正的诗歌史写作于此时诞生。檀道鸾的《续晋阳秋》,五世纪早期的一部作品,讲述了诗歌从建安到西晋直到义熙时期的历史。甚至一直到今天依然构成了通行的文学史叙事。(28)田晓菲:《高楼女子——古诗十九首与隐/显诗学》,《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
该书还认为,诗人们对“古诗”和乐府古题的兴趣起因于刘裕北伐后带到南方的宫廷乐师,所以在诗歌题目中用过“拟”字的东晋诗人,都和能够接触到北方宫廷乐工的人物有关系。当然,这或许只能被看作众多因素中的一种,毕竟拟古写作的源头应当远早于此,并且拟古诗与运用乐府古调也应有所区别。
此外,编写《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一章节的田晓菲,在其另一篇文章《诸子的黄昏》中把这一时期诗歌的代作和模拟与子书的补缺现象相关联,“仲长统作《昌言》未竟而亡,后缪袭撰次之;桓谭《新论》未备而终,班固为其成 《琴道》。”(29)严可均:《全晋文》卷117,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32页。这种观点也可作为一个有力的旁证。
五、技法:近体的殊途
如上文所讨论,南朝时期还面临着另一个诗歌的重大变革:近体诗的兴起。虽然未正式进入近体诗时代,但这一时期在创作的各个层面都已趋于更多雕琢的案头化表达。暂不论错彩镂金的颜延之等人,即使是被誉为“芙蓉出水”的谢灵运,作品中也更偏重层次语意的堆叠铺陈,与魏晋古诗宛然二致。在此并非要判定两种风格之间的优劣,然而需要承认它们代表着一种诗体的不同发展阶段。
《文选》“杂拟”作者在对魏晋古诗的模拟中正强化了他们所理解的古诗的形式特征。
在词汇方面,先秦以来,从单音词占主导到双音词占主导,双音词中从单纯词居多到以合成词为主,是汉语发展的主要趋势。汉代大致已完成双音复合词占主导的转向,从汉大赋的创作中就能体现出来,但是晋宋以来诗人在拟古创作中,还是会有意识地更多使用单纯词,尤其是继承《诗经》到《古诗十九首》的传统,大量运用叠音词,例如:
靡靡江蓠草,熠熠生河侧。皎皎彼姝女,阿那当轩织。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颜色。(陆机《拟青青河畔草》)
平衢修且直,白杨信袅袅;良游匪昼夜,岂云晚与早。(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曹植》)
眇眇陵长道,遥遥行远之。(刘休玄《拟行行重行行》)
苍苍山中桂。团团霜露色。(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刘文学桢感怀》)
在句法结构上,与晋宋的典型作品相比,魏晋古诗更疏宕有致,一唱三叹,当然其反面则是语义重复,层次感不强。即使处于对仗在五言诗中已极具规模、“俳偶渐开”的晋宋时期,拟古作者仍更偏爱最基础的合掌对和流水对,即利用充分互文或叙述性的笔法。例如:
牵牛西北回,织女东南顾(陆机《拟迢迢牵牛星》)
一唱万夫叹,再唱梁尘飞(陆机《拟东城一何高》)
复睹东都辉,重见汉朝则(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陈琳》)
在这样的表达中,上下联间的脉络相对简单,多用平铺直叙的赋法。还有一种情况是两联为一个完整的句法或语义结构,这种形式在《诗经》里曾十分常见,因为四言句式为主的情况,单句信息容纳力更为有限,随着五言产生和成熟,绝大多情况下,一个单句就是一个完整的语法或语义结构。但拟古作者则会有意识地运用两联为一句的表达,使行文更加疏宕。例如:
况值众君子,倾心隆日新。(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魏太子》)
昔隶李将军,十载事西戎。(袁淑《效古》)
远与君别者,乃至雁门关。(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古离别》)
在另外一种情况中,上下两联各自是独立的句法结构,但以问答关系或关联词相结构,问答关系如:
此思亦何思,思君徽与音。(陆机《拟行行重行行》)
人生当几何,譬彼浊水澜。(陆机《拟东城一何高》)
运用关联的词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不怨伫立久,但愿歌者欢。(陆机《拟西北有高楼》)
既作长夜饮,岂顾乘日养。(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王粲》)
且尽一日娱,莫知古来惑。(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陈琳》)
复睹东都辉,重见汉朝则。(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陈琳》)
已免负薪苦,仍游椒兰室。(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徐干》)
既伤蔓草别,方知杕杜情。(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王侍中怀德》)
以上几种,无论是对仗方式、句法结构关系,或关联词的使用,都是在句法层面恢复古诗平实疏宕的表达效果,“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30)谢榛:《四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66-67页。。所谓“家常话”,即顿断多,结构单纯清晰,以关联词强化前后逻辑关系,以设问、反问增加亲切感。
根据汉语音节特征,五言通常被划分为“2/3”结构。当然由于绝大部分情况是单双音节词的相互组合,“2/3”结构会被更加具体地划分为“2/2/1”和“2/1/2”两种,但同时也有少量情况,后三字无法被再次分割,或只能分割成“1/1/1”。当后三字作为名词或形容词组,形成无法分割的整体,诗句的信息容量和表意效率便相对更低。因而,这种情况只在初期的五言诗中较为常见,汉魏以来便大幅减少。《文选》“杂拟”中的诗人们却有意大量采用这类表达,例如:
曷为恒忧苦,守此贫与贱。(陆机《拟今日良宴会》)
故乡一何旷,山川阻且难。高门罗北阙,甲第椒与兰。(陆机《拟青青陵上柏》)
美人何其旷,灼灼在云霄。(陆机《拟兰若生春阳》)
良游匪昼夜,岂云晚与早。(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曹植》)
君在天一涯,妾身长别离。(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古离别》)
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李都尉送别》)
除少数以三字名词结尾的诗句外,整体三字脚都是以一至两字的虚词进行连缀,其中绝大部分是汉代以来五言诗中的惯用表达,因而不将虚词部分单独划分。如“X与X”(守此贫与贱),“X且X”(山川阻且难),这部分可看作“1/1/1”结构。再者是“一何X”(故乡一何旷),“何其X”(美人何其旷),由于“一何”“何其”为虚词,与其后单字形容词结合紧密,故不分割为“2/1”结构。
整体三字脚除了有句义舒朗的古风效果之外,与近体诗的发展也形成了相反的方向。就成型的诗律来看,近体诗强调一句中第二字、第四字异声,然而在后三字是统一整体的情况下,第四字的声律便不显得十分显著。
并且,如果考察《文选》“杂拟”部作品的句子结构,会发现“2/1/2”,“2/2/1”和“2/3”(含“2/1/1”)是根据自然语感交错出现的,不似这些诗人们同时期的一些作品(如谢灵运《登池上楼》等)有意将全篇整齐为“2/1/2”句式。
总之,以上提到词汇与句法的种种方面,都是摹拟者为了增强古意,同时也达到意省言多、平平道出的效果。这是因为古诗和乐府最初关系密切,作为口头文学意象群不能过于密集,不然会影响到听者的接受。同时,为了照顾听者感受,《诗经》以来便有一唱三叹、反复致意的传统,在传统的汉魏古诗中则是大量运用复沓和顶针手法,重复吟咏以期脉络清晰。例如:
此思亦何思,思君徽与音。音徽日夜离,缅缈若飞尘。(陆机《拟行行重行行》)
上山采琼药,穹谷饶芳兰。采采不盈掬,悠悠怀所欢。(陆机《拟涉江采芙蓉》)
苍苍山中桂,团团霜露色。霜露一何紧,桂枝生自直。(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刘文学桢感怀》)
除此之外,以问句或劝讽结尾也是口头文学时代遗留的重要特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以此标明预设听众的在场与出现,文本内部便隐含与听者的互动:吟诵本是一场扮演,疑问或劝讽的结尾宣告扮演的结束。例如:
遨游放情愿,慷慨为谁叹。(陆机《拟青青陵上柏》)
感物恋所欢,采此欲贻谁。(陆机《拟庭中有奇树》)
众宾还城邑,何以慰吾心。(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魏文帝游宴》)
日月方代序,寝兴何时平。(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潘黄门悼亡》)
何言相遇易,此欢信可珍。(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魏太子》)
古诗这两种继承乐府的典型结尾方式,皆昭示着听者的在场与未定。田晓菲论《古诗十九首》说:“‘表演性’(performativity)是理解《古诗十九首》的关键词。关于‘表演性’,我指的并不仅仅是男女两性歌手在观众面前对‘古诗’或其片段的表演, 而且也指听众以及后来的文本传统中的读者参与其中的‘意义创造’(meaning-production)活动。换言之,歌手、听众和读者共同实现了诗歌的叙事之圆满。”(31)田晓菲:《高楼女子——古诗十九首与隐/显诗学》,《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文选》诗人的摹拟中,种种技法上的取舍,无不在回避和抵御着近体诗的浸淫。然而这只是大潮之中微弱的回溯,反顾和摹拟的行为自身也宣告古诗时代的终结与拟古时代的开始。
六、殊途:唐代以来的五言古诗
魏晋杂诗一脉的写作并没有终止,只是以《文选》为分界,从“古诗时代”来到了“拟古时代”,个中区别大致如启功先生所说的“长出来”与“仿出来”。唐代五古虽不似《文选》标举拟古旗帜,也不再冠以“杂诗”之名,但复古风尚仍然存在。
这个蔚为大观的诗歌时代,享受南朝时的总结和摹拟的成果。随着近体确立,各种诗体各居其位,分庭抗礼,五言古诗中也已经形成共识性的典范观念。一方面,受近体诗影响,篇幅、题材上有意与之相区别;另一方面,又试图能直追魏晋,回到最初浑融状态。因而五言古诗自此分流,在唐代形成两派。杨慎说:“五言古诗,汉魏以下,其响声绝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谓之半格。”(3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84页。所谓“半格”,即是指后者中的复古一派。
明人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五古类下列陈子昂、李白为“正宗”。论陈子昂,“初为《感遇》诗,王迪见之曰,是必为海内文宗。 故能掩王卢之靡韵,抑沈宋之新声。继往开来,中流砥柱。”(33)高棅:《唐诗品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1页。对于李白,也大赞“其乐府古调”,并认为“其《古风》两卷皆自陈子昂《感遇》中来。且太白去子昂未远,其高怀慕尚也如此”。(34)高棅:《唐诗品汇》,第133页。可见高棅对“正宗”地位的确认主要在于诗人对某类特定作品的书写,正如我们在文章第二部分讨论过的,这些作品直追汉魏,存有古意,不拘一时一地,多为“悲世藏身二义”的“杂诗”类作品,并且它们大多以组诗形式架构。
王渔洋也说:“夺魏晋之风骨,变齐梁之俳优,陈伯玉之功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感遇》《古风》诸篇,可追嗣宗《咏怀》、景阳《杂诗》。”(35)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93页。其中提及的分别是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张九龄《感遇十二首》、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它们的典范意义在于对更加久远经典的摹拟与追怀。强烈的复古和模拟意识在初唐诗坛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意义,一方面时人以之与齐梁文风相抗衡,另一方面,为在近体时代寻找出路的五言古诗奠定了半壁江山。例如前文提到的陈子昂,在五言诗的创作中已有意区分古体和律体,“打破了宋齐体在声律和体式上难分古诗和齐梁体的混沌状态,为诗坛指出了界分古、律的关键在于上溯于汉魏。”(36)葛晓音:《陈子昂与初唐五言诗古、律体调的界分》,《文史哲》2011年第3期。对于唐代五古,李攀龙曾作出一种颇具争议的论断:“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并且对陈子昂的复古功业也不无微词:“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37)李攀龙:《沧溟集》卷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8 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359 页。结束全篇文章的讨论之时,我们对于李攀龙的观点也稍稍有了同情之理解。“有其古诗”,指唐代五古开创的新方向,即《唐诗品汇》中的“大家”与“正变”一脉;“无五言古诗”,则点破了古诗时代衰落的事实。唐代五古即便以汉魏为正宗,终究已不是汉魏之作,正如翁方纲所说“谓其无《选》体之五言古诗也”(38)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21页。。一旦以《文选》“杂拟”为界进入摹拟的时代,拟作者所追寻的“汉魏古风”也最终宣告失落而不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