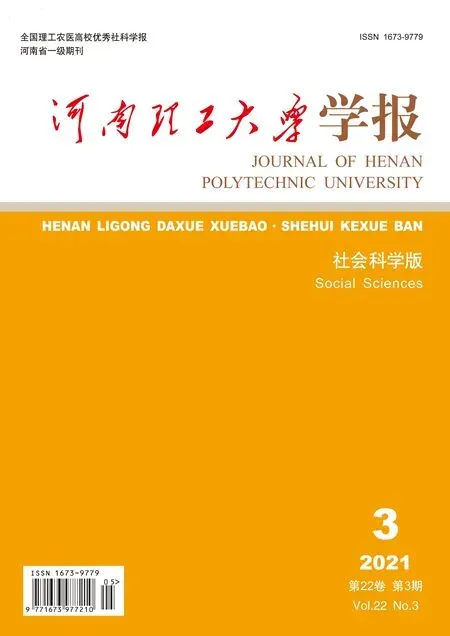论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文学精神
2021-11-30周小东孙新峰
周小东,孙新峰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纵观中国当代文坛,因为特有的文学精神与气质而对读者产生持续影响力的作家为数不多,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称得上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三颗明珠。他们共同组成了陕西文学的总体风貌,成为中国文坛一道靓丽的风景。仔细审视他们三人的创作历程不难看到,厮守乡土的三人共同热爱着文学,信仰着文学,并积极献身文学。他们均将文学(写作)作为主要的价值追求,扎根自己生活的文化板块,用丰富的生活体验进行写作实践,并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展现各色人等在社会转型中的表现,书写生活其间的人的苦难以及他们超越苦难的意识,着力刺探城乡众生被现代文明羁押的尴尬与无奈。虽然在作品中表现的是他们各自的家乡,但共同烛照的却是整个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进程。这样的价值追求着实将文学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作品因而饱含着浓厚的使命感与现实关怀意蕴。同时,作为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作家,他们共同处于三秦大地这个文化大板块,同受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柳青等老一辈作家以及苏俄、拉美文学的浸润,他们在创作观念与创作精神上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如对史诗性格局的追求,作品的乡土情结与现实主义路线,以生命进行写作的意识等。正因为此,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人的文学实践不仅对接了中国文坛,同时也瞭望着世界文坛,对整个人类进行了审美观照。
但若是具体考察他们三人却会发现,由于三人分属三种不同的地理文化板块,独特的人生成长经历与清晰的文化差异促使他们的文学精神在存有共性的同时也呈现出比较大的个性差异,具体表现在:生活于陕北的路遥拥有静思坚守的文学精神,生活于关中的陈忠实则怀有剥离与寻找的文学信仰,而生活于陕南的贾平凹身上则潜藏着探索超越的文学决心。对他们身上所彰显的文学精神的探究,可为我们提供一个透视作家与当代文学层次及境界的崭新视角,对于回答“文学何为”“文学为何神圣”等问题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一、路遥:静思坚守的文学精神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路遥,他的身体里流动着一种于静思姿态下执着坚守“现实主义”规范的伟大文学精神。正是在这种文学信念的感召下,从陕北农村走出的“王卫国”才逐渐成长为中国的路遥、世界的路遥。回顾其短暂却绚烂的创作生涯不难发现,路遥长期以一种不太聪明的沉静姿态“背对着文坛,而面向着大众”。他以生命为献祭,锻造出的百万字现实主义巨著《平凡的世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他的文学精神像土地一样宽厚深沉。
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路遥一直以“疏离”于潮流之外的选择坚守着自己从“人生导师”柳青身上所学习的现实主义文学手法。他立足于黄土地,坚持民生写作,自觉采取底层视角思考中国问题,刺探时代的整体疼痛、精神疼痛。这样的写作选择与人生态度注定使路遥在多种主义、流派、方法异彩纷呈的80年代文坛被扣上一顶“不入流”的帽子。在大部分作家急于摆脱“文革”影响,冲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模式与“十七年”文学话语的禁锢,纷纷改辕易辙,以“反叛”姿态拥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文学潮流之时,相对沉静的路遥却经过反复思索与琢磨,毅然决然地选择“背对文坛”,迈向了平凡的生活。他曾经说过:“社会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民组成的,是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活动,构成了人类一幕幕彩色斑斓的画卷,也使得人类生生不息,向文明进化。作家写他们,他们又给作家以荣誉。这种相互交融的鱼水关系,注定了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作家只能为他们高歌吟唱。”[1]因此,创作中的路遥便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强烈使命感、自觉的文学参与精神和理性追求,将自己与时代、与普通劳苦大众紧密地融为一体,辛勤地为他们记录,为他们创作,“写出了大量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真正‘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学作品”[2]。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中,路遥摒弃了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写作模式“只有控诉的宣泄,但缺少向社会生活深层次的发问”。他选择从自身的经历出发,以“武斗”为题材,具有前瞻性的对“文革”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并以生动的笔触塑造出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马延雄。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显现出独特的性格特质:拥有惊人的意志力,为保护人民利益敢于同黑恶势力作斗争;更重要的是,路遥并没有简单模式化地赋予马延雄这些优秀品质,而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事件里着力突出这个“飞蛾扑火”式的英雄人物,此种写作模式给当时的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到了引人关注的《人生》,作品虽被归为改革文学的代表文本,但路遥却没有仅仅局限于某种文学模式的规约。他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将目光倾注在“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农民身上,塑造出了一位有理想、有信念的典型人物形象高加林,彰显着他在时代大潮中的所有不屈与抗争。《人生》的备受好评使籍籍无名的路遥随即闻名全国。若按常理,此时的路遥完全可以躺在《人生》的功劳簿上享受快意人生。但心系人民、胸怀理想主义、对文学抱有虔诚之心的作家路遥毅然从《人生》的成功中走出,打点行装奔向了新的写作征程。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之时,长篇巨制式的作品似乎已经过时,更不要提被路遥奉为信仰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规范。但平静审视一番的路遥并不为这些外界信息所扰,他果断放弃了热闹的城市生活奔波于陕北、铜川各地,以炙热的现实主义文心触摸真正的生活。一方面,为了真实还原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惧繁琐的路遥全力扎进了瀚如烟海的报纸、杂志等一手材料之中,对其做了细致的分析与甄别,并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生活以及人们由平凡的世界奔向理想世界的艰辛与不易进行了总结。而另一方面,在将前期预备工作安排停当之后,潜心在鸭口煤矿写作的路遥时常在夜里为个人与时代的命运、城乡隔离的状态以及国家、民族的未来选择感到深深地焦虑,以致夜不能寐,只能以抽烟缓解苦闷的迷思。在这种极尽“煎熬”状态的影响下,写作《平凡的世界》之时的作家路遥已经完全将个体的人生经验升华到了时代的高度进行考量。他密切注视着普通民众在社会变迁中的迷惘与选择,思索着他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遭遇与痛苦,这些清晰的反思意识与精神救赎意愿正是《平凡的世界》思想闪光所在。只是长时间超负荷的精神思索与体力消耗早已将疲惫的路遥拖垮,他也在辉煌文学事业未彻底完成之际猝然长逝。对于文学的执念,路遥曾这样回答:“文学创作是勤奋者的一种不潇洒的劳动,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要有一种思想准备,准备去流血,流汗,甚至写得东倒西歪不成人样,别人把你当白痴。如果你越写越年轻,越写越潇洒,头发越写越黑,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1]正是在这种不怕苦不怕难、为文学 “九死其尤未悔”的无畏精神坚强引领下,路遥才一次次获得文学女神的垂青。
长期以思想者姿态观察写作并执着坚守的路遥,他的文学信仰散发出浓浓的哲学韵味。这样的精神使他将文学创作视为自身生命价值的有力体现,哪怕是以肉体为筹码,也要换得生命意义的最大化彰显。他于“平凡的世界”中走出,在“平凡的世界”里追求着自己的 “人生”与社会理想。而他的作品及他的文学精神又恰好似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时代,更照出了人性的是非善恶。路遥乃真正的“黄土之魂”!
二、陈忠实:剥离与寻找的文学信仰
陈忠实的文学精神呈现出不断剥离、不断寻找的动态状态。他于早期师法柳青,被人们称作陕西“小柳青”,至中后期自觉剥离老师傅的影响,积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并最终将对文学的信仰凝聚在了“文学依然神圣”的层次之上。他的辉煌文学成就一方面根源于厚重关中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对文学始终不渝地执着寻找:文学既是陈忠实自我实现的目标,也是他的坚定信仰,是注入血液基于生命又超越生命的本真存在。为了找寻文学的真谛,他不断更新着对于文学的看法,提出了将“生活体验”进化到“生命体验”,“将批判性的文化审视与现代性的文化反思相结合,去探寻民族文化的精魂所在”[3]等诸多具有非凡文学价值的观点。
以耕种者姿态矗立文坛几十年的陈忠实出生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父辈们均是本分的庄稼汉,清贫的生活环境促使陈忠实从小便养成勤劳务实的习惯。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对文学十分倾心的青年陈忠实逐渐明白,从事文学创作不仅可以开拓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出人头地,最重要的还是彻底转变自己农民身份的最优途径。基于此种略带功利性质的心理认知,高考落榜后赋闲务农的陈忠实在农闲之余便开始真正接受文学的熏陶。随着如饥似渴的阅读,陈忠实的人生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在这时期,陕西老一辈作家柳青进入了他的文学视野:柳青生活化的语言风格、时代化的场景设置以及《创业史》的现实主义风格给文学青年陈忠实以巨大的震撼。陈忠实后来坦言:“《创业史》的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还有柳青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都对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4]考察陈忠实早年的文学创作经验便会发现两条清晰效仿柳青的线索。第一条是他对柳青“三个学校”主张的认同,其中最为陈忠实所推崇的是“生活的学校”的观点。有论者便认为“陈忠实小说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等方面都有着柳青文学的影子,甚至把《初夏》与《创业史》进行了相似性的比较”[5]。我们知道,成长于渭河平原的陈忠实对乡村生活与农民大众有着天然的热爱之情,他熟悉身边的人与故乡的事。后来又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与农民群众的频繁接触使得陈忠实对乡土产生了更为深沉的情感。这些生动鲜活的“生活体验”给予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而扎根长安县十几年、自觉贴近农村农民生活的柳青,他的生活轨迹与陈忠实十分相像。《创业史》的完成正是柳青在对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体验与感悟下完成的,这对同样关注农村生活的陈忠实来说,影响可谓深刻。第二,陈忠实出身底层,极负责任心的性格促使他密切注视身边同样清贫的农民兄弟。如何记录他们或喜或悲的生活,在陈忠实初次踏上文学之路时便开始了思索。而一部如实记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无疑给他莫大的精神触动,促使陈忠实开始摸索属于自己的文学写作模式。幸运的是,《创业史》的现实主义风格激发了他思维的火花。此后出现的《夜过流沙河》《康家小院》等作品均可以视为他实践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力作。
虽然柳青某种程度上是陈忠实探索文学之路的拐杖与引路人,但雏鹰总要学会自己飞翔。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过起步阶段的练习与积淀,陈忠实意识到自己应该主动剥离以柳青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文风的影响,寻找属于自己的现实主义。他曾经谈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也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阴影。”[6]“什么时候彻底摆脱了柳青,属于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才可能产生。”[7]面对各类文学思潮的冲击,已对创作局面不再满意的陈忠实便果断对自己的思维模式与文学观念进行了审视:写什么是必须要考虑的。而通过对大量可读性强的小说的阅读与痛苦的剥离思考,陈忠实对怎样写作也有了更多的艺术感悟。他意识到不能简单围绕故乡故土故人故事进行书写、对现实生活做意识形态化的表象呈现,而是应该开启宏大的视野,向人性的深处逼近,向民族历史开掘。这一认识在1985年的小说《蓝袍先生》中便开始逐渐显现。在这部小说中陈忠实彻底抛弃过往的写作模式,着重表现历史带给个体的伤痛,并进一步探索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与连接。同时,他在主人公徐慎行的蜕变过程中更是加入了对时代转折背景之下人物命运沉浮的真切思考。这是陈忠实自觉寻求剥离的结果,更是他在经历历史变迁后感悟到文学对于人及其人性审美艺术建构之奥秘所在。紧随其后创作的《四妹子》可以视为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它的出版标志着陈忠实开始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寻求创作的发力点。这是作家创作观念的又一次剥离与前进,为随后的“垫棺作枕”之作《白鹿原》的成功奠定了扎实的形式技巧实验。关于酝酿《白鹿原》的写作,还有一件小故事:1988年,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在秦岭山中的太白县召开了长篇小说讨论会,陈忠实向一直关心他创作的蒙万夫透露了他写《白鹿原》的情况。蒙万夫对他写《白鹿原》的构想只谈了一个意见:长篇小说要重视结构的艺术。如果没有好的结构,文章就如同缺少骨架,无法站立起来。陈忠实觉得蒙万夫所谈,正好切中了他当时正在困惑并思考着的长篇小说结构问题。为此,他有目的地阅读了王蒙、张炜等人的长篇小说,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最好的结构,只有适合自己小说内容和人物的结构,并且,小说的内容决定结构方式,因此《白鹿原》必须要有自己的结构形式。仔细审视《白鹿原》,其之所以被誉为“民族秘史”,除去作品拥有令人称道的艺术结构,并且在此结构的架设下作家实现了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质变飞跃,认识到“写人,要从多重角度探索人物真实而丰富的心灵历程,要避免重蹈单一的‘剥削压迫,反抗斗争’的老路,要从过去的主要刻画人物性格变换为着重描写‘人的文化心理’”[8]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作品全然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对人物肖像的外在描写,而选择在刻画人物文化心理与精神气质等方面着力倾注笔墨。与柳青的《创业史》相比,陈忠实大胆突破了题材与思想的禁区,从表现物质生活中的个体提升到窥探群体精神的层次,不仅彻底将两性关系撕破,赤裸裸的呈现着“田小娥”“白孝文”等人的疼痛,还窥探着时代对人性的异化与消解,并着重对白嘉轩、鹿子霖、黑娃等人物的心灵溃败史进行了集中的展示,书写了他们由坚强到崩塌、由权威到消解权威的悲惨过程,作品所涉及到的社会矛盾与价值属性因而显得更为深沉、复杂。而以《白鹿原》的诞生为标志,由此作家也进入到一段比较稳定的创作时期,寻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以及“属于自己的句子”。这里的“句子”包涵着他“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的感受,并以生命的形式融进了他的文学”[9]。
从陈忠实的文学创作轨迹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他文学信仰的进化过程。陈忠实从对柳青的忠实学习,到自觉寻求剥离传统现实主义的羁绊,并最终在探索学习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现实主义文风。陈忠实的创作之所以呈现出比较大的跨越,正是在于不断地自我剥离与寻找。陈忠实曾经坦言:“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而先天文学准备不充分的作家却一直将文学写作视为神圣的事业,似痴似愚地刻苦学习,几十年如一日的匍匐在文学的大地上。经过学习与反思、剥离与寻找,一只从平原上奔出的“白鹿”使他的文学事业终于化茧成蝶,完成了一个作为作家的自我。
三、贾平凹:探索超越的文学决心
贾平凹在不断转移与不屈的艺术探索路途中凝聚出他独具个性的文学精神。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贾平凹注定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他于1973年以《一双袜子》登上文坛后便开启了他笔耕不辍的文学生涯。四十余年间,他以一位艺术家、观光者、引领者的姿态,用写诗、作散文的艺术直觉经营着多种文体,出版诗歌、散文、小说近千万字,而这些作品因非凡的艺术风格屡获国内外各项大奖,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文学成就。仔细梳理贾平凹的文学之路,我们在钦佩他天才般存在的同时,不禁会疑问:贾平凹是以怎样的文学决心支持他在文学的园地自由开拓并且长盛不衰?思考这一问题,或许我们能从他答复复旦大学学生提问的回答中获得答案:“写作时间长了以后,一方面,总想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要发泄出来,就像鸡下蛋,你不让下它也憋得慌。另一方面,你一定要有远大的目标,一定要觉得自己还能写,这么不停地给自己提劲。”[10]253-254
与三驾马车里的其余两位作家相比,贾平凹的文学步伐是最善变、最飘忽不定的。他在创作实践中不断进行着话题的探索与文本形式的超越,真乃“山地之灵”也!初登文坛之时,贾平凹以纯净的目光审视世界,肯定生活中人性的美好,笔调显得清新流丽。随着生活经验的增加,他的视角逐渐发生了转变,开始关注人性的复杂,表达思想上的迷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作家对新的文学根据地“商州”的探索,此时他的写作笔触逐渐触及变革时代社会人生的心理状态,并对时代思潮的变化迅速做出了反映。步入20世纪90年代,已不满足于书写商山洛水人与事的贾平凹毅然从他的文学根据地出走,将审视的目光全力聚焦在了他所生活的大都市西安城——《废都》应运而生。这部作品令他毁誉参半,却也使他渐渐建立起新的文学根据地,开始关注都市众生的精神蜕变,探索生命本体存在的价值。2005年以后,《秦腔》《高兴》《古炉》《带灯》《极花》等一系列长篇大作皆以现实主义的目光注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民情、社情、国情,收获了普遍的好评。其中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秦腔》更是独辟蹊径,以大散文的笔调将庸俗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表现,并着力还原了生活的原生情态。此种对生活细节做密实的流年式的全新叙事选择显然对传统的叙事手法进行了颠覆。2018年春,一部涉及秦岭传奇历史的《山本》横空出世。已从商州出走多年的作家重新回到秦岭深处的故乡,将历史还原于文学,以一种独特的哲学观对革命历史进行了书写,展现着自己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反思性思考。《山本》之后,贾平凹在2019年面对媒体的一次采访中真情流露道:“我发现写的东西不行了,想换一个名字来写,不再用贾平凹。”这无疑是一声掷地有声、充满勇气的文学宣言!它昭示着我们的作家已然将过去的自己进行了否定,并谋划走一条新路,蜕变出一个全新的贾平凹。
返观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之路可以发现,他的写作实践及笔下所展示的文学区域一直发生着位移,不断进步,不断“开花结果”。贾平凹对此曾评价道:“创作之所以是创作,作是第二位的,创是第一位的,一切无定式,一切皆 ‘扑腾’。现代文学的核心和灵魂是求变和创新。”[10]36若以1978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满月儿》视为其正式的文学起点的话,那么可以明显的将贾平凹频繁探索的创作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均表现出各异的文学特质。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商州文学”阶段。这个阶段的贾平凹以文学化的商州作为基点所创作的文本显示出他追寻自然、空灵伶俐的艺术风格。而在作品中被着重渲染的村镇乃是一块块神奇的世外桃源,他们虽偏远萧瑟,却不荒凉落后。显然此时期的贾平凹是以一颗明亮的心态面对故土的,他与故乡农民的爱憎情仇几乎完全同步,此时的他仍像是一个进了城的农民。而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山地笔记》《腊月 正月》《商州》《天狗》等也都切合家乡农村的新变化,真实传达着处于变革时代中国农民昂扬向上的生活情绪,但这种情绪的表达在小说《浮躁》中被中断了。贾平凹机警地发现,他应该主动与时代保持适当“距离”,不囿于时代潮流,甚至超越时代进行书写。事实证明,贾平凹的敏锐选择是正确的,而这种选择却正好预示着他创作道路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废都文学”阶段。这一阶段的贾平凹从故乡的乡镇中出走,将探索的笔触聚焦在了大都市,而一部融汇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与贾平凹个人生命骤然裂变”[11]的《废都》成为这时期影响最大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劲风吹拂,趋利浮躁的时代氛围弥漫至社会的角角落落,直接导致了群体精神的“幻灭”,而文学的地位则一降再降,面临着被消解的窘境。作为一名有担当的文化人,贾平凹彼时急迫的心情可想而知,而这种心情在《废都》的叙事中得到了集中的释放。《废都》过后,他于1995年之后创作的《白夜》《土门》《高老庄》等作品大多不迎合于时代潮流,呈现出独立的艺术气魄。而这些作品的风格也与《废都》一脉相承,带有极强的灰暗色彩,充斥着凝重的苦味。第三阶段是近十余年来的“老生文学”阶段。这一时期若从艺术境界与艺术追求等方面审视贾平凹的创作便会发觉,某种程度上他已然将同时代的作家超越,并逐渐形成了“贾平凹式”的文学种类。与同时期进入文坛的其他作家相比,已近花甲的贾平凹却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的创作热情丝毫不减,在为自己设立了“文学的奥林匹克”的远大目标之后,又几乎以三年为一周期不断推出长篇幅小说,超越先前作品所汇聚出的艺术风格,深化自己对世间万物的认知。在作品《古炉》中,贾平凹以 “善人之心”并没有被烧坏清晰地表达着自己的善恶观;到了《极花》,作家对善恶的看法明显发生了改变。作品隐晦地告知读者需辩证看待人性的是非善恶。而以这些作品为代表,作家的艺术品格也随着他生活阅历的增加变得愈发苍茫遒劲。伴随着不断探索的步伐,贾平凹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文学表现手法与审美感受,提出了“在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参照系中,确立自我的意识,寻求立足之地”[10]77的“中西融合”的艺术观点。在这一观点的推动下,作家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文学表现位置,将笔触深入至隐秘的秦岭山深处,创作出《老生》《山本》等诸多作品。以这些文本为依托,贾平凹欲站在商洛看中国,站在中国看世界,俯察人类的未来,对中国的前世今生乃至世界文学的模样进行探寻,作品的艺术境界进一步廓大。
我们说,贾平凹正是这样一位具有丰富性与博大感的作家,而他的文学精神恰似一种创作上的“流寇主义”与超越思维。一方面,他四处探索,多转移也多收获;另一方面,他从不固步自封,勇于超越自我,超越群体,超越时代。这样的文学观念自然源自于他清醒的未雨绸缪式的自我认知。他曾经谦虚的表示:“我开始进入文坛的时候起点很低呀,你不变化,不去否定和修正,不去突围那怎么行呢?文坛的竞争极残酷,新的作家因为创作的环境好,接触外来的东西多,他们起点高,逼得我要不停蜕化。”[12]此言非虚,恰恰是因为贾平凹的不断探索调整,他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时代与文坛的新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目的是为了不落窠臼,找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新看法与独到表现。
四、结 语
不论学界对这三位作家的创作发出过何种争论,但他们的文学追求乃至精神指向始终朝向善与美,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只有紧扣作家的创作路向,才能对这样一个历久弥新、值得不断探索的文学核心要义进行相对准确的把握。基于此,论文以“人文合一”的视角为主旨方法,对这三位作家的文学精神展开了集中探讨。经过研究我们欣喜的发现,拥有信仰的三人并没有“躲进小楼自成一统”,或沉溺于一己之私里;而是前仆后继,以生命为代价进行写作,因此才在探索世间真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让自己的灵魂抵达到社会现实的最内部,抵达到人类最真实的内心!同时,他们的创作一方面为时代立言,为生民立命,表现着自我的胸襟与气度,彰显着自己的道义与担当。正因为此,《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作品才深深影响并打动着社会与读者。而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虽然三位作家的文学精神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若从创作手法方面观之,对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的现实主义文学写作方式的坚守与个性化革新创造却是他们的共同旨归。作为“农裔城籍”的他们,虽早已从故土走出,却仍不舍对农村农民农事的关注、对社会生活变迁的描绘、对个体生存状况与精神诉求的逼真展示。如今,虽然三驾马车只余贾氏一人独挑“陕军”文学之大梁,但其余两人连同贾平凹的巨大影响力却依然陶染着整个陕西文坛,烛照着三秦大地之上崛起的后起之秀们。而时间也必然会向世人证明,他们的文学精神将不仅仅属于陕西文学,更将是整个中国文学乃至中华民族文学的精神气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