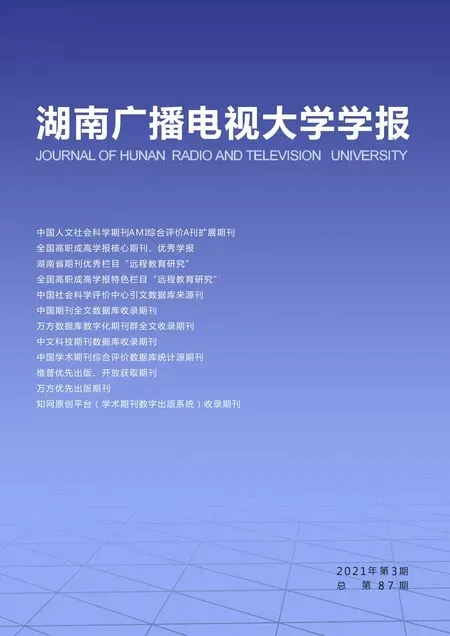衍生态神话的范本——从电影《灯塔》看神话、传说与民间文化的交融
2021-11-30周琳玥
周琳玥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北京 100083)
美国新生代导演罗伯特·艾格斯仅凭两部高度风格化的影片便跻身世界影坛知名导演行列。2015年,他自编自导的处女作《女巫》入围第31届美国圣丹斯电影节,获剧情片导演奖;2019年,他执导的影片《灯塔》入围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获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影片获得的热烈反响使艾格斯在美国独立电影界名声大噪。
作为一个杰出的故事讲述者,艾格斯开创了一套崭新的地域民俗志电影类型。《女巫》的副标题为“新英格兰民间故事”,影片背景设置在17世纪30年代的普利茅斯,讲述了一个遭种植园主驱逐的清教徒家庭定居荒野并在巫术阴影下分崩离析的故事。《灯塔》的背景设置在19世纪90年代的缅因州,讲述了荒岛上两名灯塔看守员逐步走向精神覆灭的际遇。两部影片的片尾均以字幕的方式道出其灵感来源: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法庭记录、故纸堆中的日记等。艾格斯有意用影像探索在地性的民俗文化,他在剧本中大量参引文化材料,汇融了来自新英格兰及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乃至民间野史。
如果说《女巫》是一部带有巫术色彩的宗教民俗志,那么《灯塔》则更接近于一部带有神秘色彩的神话新编。在神话学中,神话通常被划分为四种形态:一是原生态神话,由原始初民创作,内容朴野,反映了人类的原始心态;二是再生态神话,产生于氏族公社时期,在流传过程中因时因地因人而产生各种变异;三是新生态神话,产生于封建社会时期,通常伴随着特定的信仰行为;四是衍生态神话,指上述三类神话在其他领域运用和改编的衍生物,这一类神话起源古老,其母题、形象、情节、观念具有高度的典型性与象征性,因此在许多领域被有意识地加以广泛应用[1]。如今,衍生态神话的表现形式已不再囿于文学作品,而成为一种包含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等在内的综合文化现象。艾格斯在影片《灯塔》中糅合了希腊神话、海洋传说、民间文化的原型要素及象征意蕴,展现了大胆新颖的想象力,从某种程度上可视作现代衍生态神话的跨媒介范本。
一、希腊神话的原型运用
19世纪初,威尔士斯默尔斯灯塔站曾发生过一起两名看守员因暴风雨被困灯塔站的真实事件。艾格斯以此为灵感来源创作了《灯塔》的剧本:在新英格兰的一座荒岛上,年老的灯塔管理员托马斯·维克和年轻的新管理员伊弗列姆·温斯洛将进行为期四周的守塔工作。为营造故事氛围,影片罕见地采用35毫米黑白胶片拍摄,设置1.19∶1的独特画幅,力图还原19世纪的时代感。复古而神秘的影像特质为神话的进驻提供了契机,《灯塔》中古希腊式的神话元素得以展现:盗火的欲求与神祇的阻力、海妖予人的诱惑与迷狂等。
(一)普罗米修斯与普罗透斯的交遇
艾格斯曾在访谈中提到,当故事的框架构建起来时,他便着意寻找能与之吻合的神话。在《灯塔》中,两位主人公的原型取自普罗米修斯和普罗透斯。普罗米修斯和普罗透斯从来没有在希腊神话中一起出现过,不过这似乎就是这个故事里要发生的内容,普罗米修斯可能会呈现出一些他之前没有的特征[2]。换言之,《灯塔》的神话改编践行弗莱的“移位的神话”策略,在置换变形中既保留了神话的原始意义,又充分发挥了现代语境下改编者的创造力。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之名意为“先知先觉者”,他违反宙斯的意志盗取天火给人类,被缚在高加索山上,日复一日被秃鹰啄食肝脏。普罗米修斯盗火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基础神话,从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到弥尔顿、歌德,再到拜伦、雪莱,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在一代代作家笔下嬗变,每次都被赋予新的面相,但其核心意义均在于对高于人的神力的反抗。艾格斯在影片中引入这一神话,他让温斯洛成为普罗米修斯原型的承载者,黑暗中发光的灯塔则俨然是奥林匹斯山上圣火的换喻。在影片中,新人温斯洛只能从事烧锅炉、擦地板、倒夜壶等卑微的工作;而老托马斯作为一个集神权与父权于一体的统治者,独享照料灯塔的特权。对灯塔(圣火)的渴望折磨着温斯洛,他在服从与反抗之间辗转,企图盗取灯塔的钥匙。
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宿醉后的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斗,这时普罗透斯原型附着到托马斯身上:他先是变为温斯洛多年前杀死的伐木工的样子,接着变为温斯洛梦中的欲望对象人鱼,再变为头戴珊瑚冠冕的海神波塞冬。普罗透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早期海神,其名意为“最初”,他只向捉住他的人预言未来;为避免被捉住,他随心所欲改变自己的面貌,于是其名又有“千变万化”之意。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墨涅拉奥斯曾向忒勒玛科斯讲述他捉拿普罗透斯的故事:尽管普罗透斯先后变成了狮子、长蛇、猛豹、野猪甚至流水和大树,但墨涅拉奥斯还是成功捉住他,迫使他透露了奥德修斯的下落[3]。在《灯塔》的剧本创作中,艾格斯充分展现了普罗透斯擅长预言和变形的非凡能力,使普罗透斯化身的托马斯多次充当温斯洛盗火的阻碍力量:他曾变作眼中射出电光的宙斯,牢牢攫住温斯洛;他故意让温斯洛从灯塔跌落,当后者从眩晕中醒来,发现一只海鸟在狠狠啄他的裤管——与普罗米修斯所受惩罚(秃鹰啄食肝脏)形成微妙的互文。
正如变形的普罗透斯一旦被捉住就会失去神力,托马斯被温斯洛打倒后即丧失了他的权威。普罗米修斯式欲望就是对绝对强力的欲望[4]80,对神权/父权的挑战(温斯洛对托马斯的挑战即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挑战)使权力关系发生了倒转:不可一世的托马斯被打倒,温斯洛将他像狗一样牵出屋外,弃于坑中。普罗米修斯式的存在一般以自身为价值核心[4]79,温斯洛弃已然式微的托马斯于不顾,兀自接近圣火,而后者正是在这时发出了“你将受到天谴”的预言。就这样,新神普罗米修斯杀死了旧神普罗透斯,但当温斯洛满身血污地打开通向灯塔顶层的隔板,伸手触摸到光源后,结局则是和普罗米修斯一样陷入永恒的惩罚——跌落楼梯井,裸身于海滩被海鸟啄食。不同之处在于,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集受难者、殉道者和思想者于一身,盗取天火是为济世,他承担了人类从精神到肉体的全部苦难;而影片中的温斯洛则是一个因罪被流放到世界边缘的小人物,在绝对权力的压制下迷失在窥探灯塔秘密的欲求中,并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
普罗米修斯与普罗透斯充满创新性的交遇是艾格斯对神话故事的一次“反弹琵琶”:普罗透斯的含混多义性干扰甚至消解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正义性,使整个故事沦为一个幻觉(托马斯是真实的人物还是仅存在于温斯洛头脑中的人物,观众不得而知)。在这个意义上,《灯塔》可视为一次对古老神话的现代祛魅①。
(二)塞壬与美人鱼的置换变形
除两个男性角色外,《灯塔》中还有一个隐性女性角色,即作为欲望对象的人鱼。温斯洛来到岛上的第一天就在床垫缝隙间发现了一个木制裸体人鱼雕像,他悄悄将其藏起,从此陷入两性欲望中不可自拔。人鱼不断造访温斯洛的梦境,使他克制不住地自渎,幻想与海滩上的人鱼交媾。影片不断进行空间切换:一边是狭小封闭的锅炉房,另一边是雨雾迷茫的旷野,锅炉房刺耳的汽笛与人鱼的尖锐叫声形成奇妙的互文。在二者的交叉剪辑中,具象性地呈现了温斯洛陷入迷狂的过程。
关于《灯塔》中另类的人鱼形象,艾格斯给出的说法是:“从传统意义上讲,美人鱼是黑暗的女性;从男性角度看,她是大海的一部分,是最强大的力量,是大自然母亲;她来引诱男人,把他们拉进无意识的领域。”[5]《灯塔》中人鱼的原型其实是希腊神话中的怪物塞壬。在《奥德赛》中,塞壬是一群人面鸟身的海妖,栖居在海中央的岛屿上,每当船只经过,她们就用动听的歌声诱惑水手。奥德修斯在归程中途经塞壬的海岛,为抵御诱惑,他命同伴用蜡封住耳朵,并将自己绑在桅杆上,从而成功渡过险境,成为唯一一个听过海妖的歌声而又幸存下来的人。塞壬之歌在后来亦演化为“不可抗拒的诱惑”的代名词。
在《灯塔》对神话的改编中,艾格斯从象征主义艺术家让·德维尔、萨沙·施耐德、阿诺德·勃克林等人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将人面鸟身的塞壬与人鱼形象进行了拼贴,人鱼开叉的尾巴更有利于表现与人类男性的相处,这也使得诱惑的重心由歌声转变为性吸引力。正如塞壬诱惑并吞食过往船员,人鱼亦诱惑并逼疯一代代灯塔看守员。托马斯认为其前助手疯了,净说些海妖、人鱼、凶兆之类的胡话。而对于温斯洛来说,人鱼的诱惑固然折磨着他,但由于存在一个更高阶的欲望象征——灯塔,从而能够抵御人鱼的诱惑。当温斯洛从捕虾笼中捞出前任的首级,他自以为发现了托马斯的秘密,叫嚣着:“你用那个小雕像把他逼疯了,但我砸坏了,现在我解脱了,摆脱了你的阴谋!”他天真地以为砸坏雕像即可破除迷狂,却不料被灯塔所散发的更大的诱惑反噬,最终结局仍是毁灭。
如果说在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成功象征着塞壬及其代表的原始自然力的失败,那么在《灯塔》中一代代守塔人的遭遇则象征着人鱼所代表的原始欲望对人类理性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灯塔》又是一次现代神话的复魅②。
二、海洋传说的文本熔铸
在新英格兰,航海神话是其文化中的重要一环。艾格斯在《灯塔》的剧本写作中参考了大量涉及海洋传说的文本,从柯尔律治的《老水手行》、梅尔维尔的《白鲸》、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到缅因州本土作家朱厄特关于航海的短篇怪谈,再到现实中的灯塔管理员日记……艾格斯巧妙熔铸了这些文本,其中最为鲜明的是对《老水手行》和《白鲸》中意象的借用。
(一)《老水手行》——杀死海鸟的诅咒
海鸟作为海域常见的动物出现在各种航海传说中,亦是《灯塔》中一个突出的动物意象。影片中温斯洛与海鸟缠斗的情节直接取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的长诗《老水手行》,其核心情节是老水手在航行途中射杀了一只信天翁,结果造成船上其他人神秘死亡,只剩他一人存活。《灯塔》沿袭了《老水手行》对待海鸟的态度,托马斯多次告诫温斯洛不要招惹海鸟,“杀死海鸟会遭厄运”,“海鸟体内是死去水手的灵魂”。在海洋传说中,海鸟常被视为神鸟,除“水手灵魂”一说外,还具有宗教意义,如柯尔律治诗中的信天翁是带来南风的鸟,甚至被唤作“基督的使徒”。老水手射杀信天翁之举如同人类深层的原罪,其后果必然是遭到天谴与惩罚。在《灯塔》中,温斯洛不听劝告,在水箱边极其血腥地杀死了一只海鸟,马上使得屋顶的风标倒转——风向改变,接着便迎来有如天罚般的暴雨,原本要来接他离岛的船不见踪影。海鸟的诅咒继续发酵,温斯洛的结局不似老水手那般幸运,他没能回到大陆,而是在荒滩上被一群海鸟撕扯吞食。在艾格斯极具创造性的构想中,这一场景与前文所述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相勾连,表现了所谓“天谴”的主旨。
影片中还有一处较为隐晦的呼应,即杀死海鸟的诅咒始终与腐烂意象相联系。在《老水手行》中,老水手射杀信天翁后便陷入可怖的困境,异象开始显现:“连海也腐烂了!……黏滑的爬虫爬进爬出,爬满了黏滑的海面。”[6]34“我看看腐烂发霉的大海,扭头把视线移开;我看看腐烂发霉的船板,船板上堆满尸骸。”[6]46鲍特金曾指出:“对于那种黏糊糊的发光丑物的两重性,柯尔律治似乎从旅行家游记中确实感觉到了,并把它纳入对死寂事物的魔幻般图景的描绘之中。”[7]在《灯塔》中,腐烂与黏性之物的意象十分突出:首先是温斯洛在水箱中发现一只腐烂的、令人作呕的海鸟,它彻底污染了水源;紧接着他又粗暴地摔死了一只海鸟,血污四溅;腐烂黏性之物的意象继续蔓延至室内,体现于从灯塔隔板上滴下的黏液以及鬼魅般的章鱼触手。这些意象围困着温斯洛,不断搅扰他的心智,将他带向覆灭,而他最终的结局亦是周身沾满黏稠的血污,腐烂于海滩之上。
(二)《白鲸》——埃哈伯船长的戏拟
梅尔维尔的《白鲸》被誉为19世纪美国文学的巅峰,亦是航海小说绕不开的源头。《灯塔》的主人公之一托马斯即脱胎于《白鲸》中船长埃哈伯的形象。托马斯曾是一名常年出海的水手(从其表述看还可能是一名船长),因腿伤退役后成为一名灯塔看守员,他像为船掌舵一样牢牢控制着灯塔。早年的海上生活使他敬畏海洋,以致每次喝酒前都必须吟诵一段古老的颂词;酗酒又使他变得性情暴戾,习惯向助手发号施令、肆意咒骂。在一段台词中,托马斯命令温斯洛“把地板擦得像鲸鱼的阴茎一样闪闪发亮”(鲸鱼乃是《白鲸》的核心意象)。两人交恶后,温斯洛反讥道:“我受够了你的鬼话连篇,还有埃哈伯船长那套狗屁,你听起来像在拙劣模仿!”从人物的制服装束到身体特征(瘸腿),再到专制暴戾的性格,托马斯与《白鲸》中的埃哈伯形成明显的对应,甚至可以说,影片就是对埃哈伯船长退役成为灯塔看守员的一次戏拟。
在精神层面,托马斯与埃哈伯有着多方面的契合。首先,他们都将欲望对象阿尼玛投射到一个非人的替代物之上。阿尼玛是荣格提出的重要原型,意指男性心中的女性形象,男性在遇到自己的阿尼玛时,他会体验到极强烈的吸引力。《白鲸》中女性看似缺席,但实质上化作了大海——埃哈伯生命的终极意义就是驰骋于海上,怀着病态的狂热猎杀那头名叫莫比迪克的鲸鱼。在影片《灯塔》中这一原型换成了灯塔。托马斯坦陈:“大海,她才是我的归宿。什么都比不上大海,但我没法再拖着这条老瘸腿到处跑了。如今我是守塔人,这辈子就拴在这灯上了,她可是位温柔、真诚、内敛的妻子,比任何女人都强。”托马斯始终用拟人化的“她”来称呼灯塔,并视之为妻子,是阿尼玛原型的显性表征。其次,二者都服膺于一种神秘的超验力量——圣艾尔摩之火。传说圣艾尔摩是水手的守护者,雷雨中桅杆上的闪光被称为圣艾尔摩之火。《白鲸》第119章详细描述了披谷德号见证圣艾尔摩之火显圣的场景,埃哈伯敬拜这火光,自语:“你哪怕只以你最低级的爱对待我,我也会向你跪拜,吻你。”[8]537在《灯塔》中,托马斯以同样的态度敬拜灯塔。他向温斯洛谈起从前的助手时说:“他坚信灯里有某种魔法,认为圣艾尔摩将他的火焰注入了其中。”这番话实际上更适用于托马斯本人,他将自己赤身裸体地锁在灯塔顶层,周身沐浴在其光亮之中。托马斯和埃哈伯一样,是一个着魔式的人物,他们对超验力量的迷恋影响到周围的人。面对埃哈伯,大副斯塔勃克的感受是:“我的灵魂遇到了比它强大的对手;它被人,被一个疯人控制了! ……把我的理性消灭个精光!”[8]193托马斯的助手则是彻底疯了:“最后体内残存的理智还没他剩的牙多。”所谓超验主义的和谐观点,即超灵论的个人灵魂是宇宙灵魂的一部分,个人身份融入无限之中的说法是蛊惑人心的[9]。最终,埃哈伯对那头“神秘造物”的追捕把全船人带向了毁灭;而温斯洛对灯塔的“朝圣”亦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
三、民间文化的象征意蕴
艾格斯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新罕布什尔州长大,他对新英格兰民间文化的关注在电影中得到了鲜明的呈现。他认为:新英格兰是欧洲白人文化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因此,如果要探索这些古老的故事,那么你就需要一个历史悠久得足以产生鬼魂的地方。这两部电影都是他试图与其所在地区的欧洲非原住民民间文化进行交流[10]。艾格斯在影片筹备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民俗志,有意使《灯塔》的讲述方式接近一个民间故事;同时,他对象征主义的热爱也融入其叙事肌理,使影片充满了丰富的象征意蕴。
(一)阈限人与入会礼
《灯塔》的主体情节可视作一次通过仪式,即个人生活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民俗学家范·杰内普将通过仪式划分为三个阶段:分离、阈限及聚合。作为过渡的阈限阶段最为重要,处于这一过程的仪式主体被称为阈限人。维克多·特纳认为:“阈限或阈限人……的特征不可能是清晰的,因为这种情况和这些人员会从类别……的网状结构中躲避或逃逸出去。阈限的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在法律、习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作为这样的一种存在,他们不清晰、不确定的特点被多种多样的象征手段在众多的社会之中表现了出来。”[11]95
《灯塔》的故事开篇即是轮船送来外来者——曾是北方森林伐木工的温斯洛来到南部荒岛做灯塔看守员。这是典型的分离阶段:主人公从一个空间到另一空间,同时伴随着职业和地位的转变。在接下来的阈限或过渡/考验阶段,阈限人往往被表现成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教导者的命令,还要毫无怨言地接受专断的惩罚”[11]96。常年驻守灯塔的老托马斯扮演了教导者的角色,新人温斯洛处于他的压迫和管束之下。在民间文化中,过渡时期意味着对新人的培育,而传授圣物是阈限问题的核心[12]。圣物在影片中指灯塔,托马斯将灯塔顶层划为一个神圣空间。“神圣空间的观念包含一种想法,即重复将这个地方标志出来、切断它与周围世俗空间联系的原初的神显,从而祝圣这个地方。”[13]358人类只要进入这个空间就能获得力量,与神圣交流。作为教导者,托马斯禁止新人温斯洛涉足顶层,只允许他在底层干活;而后者多次仰观前者赤身步入充满光辉的塔顶。由此,温斯洛对进入神圣空间的欲望不断膨胀,这就顺势引出了入会礼的情节主题。
民间文化中常有崇尚神圣中心的概念。从主人公所处的地域看,作为神圣象征的灯塔位于小岛的中心,而塔顶光亮之所在则是中心的中心,它必将受到严密看守。“要获得它们就相当于一次入会礼,一次对于永生的‘英雄般的’或者‘神秘的’征服。”[13]371-372为使灯塔免受不速之客的侵犯,托马斯扮演了守护者的角色。而当温斯洛打败托马斯,他也就获得了入会礼的资格,这时阈限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倒转,下层的人变成上层的人。温斯洛拿到钥匙后将托马斯杀死,他的通过仪式圆满完成,之后便进入聚合阶段:角色转换,权力复归,他独享灯塔。
温斯洛经历了由分离到阈限再到聚合的过程,可以与神话中从隔离到启蒙再到回归的英雄历险路径相对应。稍有不同的是,影片结局以主人公的死亡跳出了对现实情境的回归,却通过对普罗米修斯受难原型的重复进入一种神圣的、史前的时空,开启了一种新的神话。
(二)双性同体与光的创造
艾格斯在电影中设置了大量象征符号,尤以灯塔最具代表性。艾格斯认为,灯塔以一种神秘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出现在电影中,但它也以一种浪漫而有力的方式存在于电影中[10]。作为影片的核心象征物,灯塔这一意象含混而多义。首先,从形状上看,它是男性性器官的象征。在男性主导的父权制下,越是占据顶端的人越是权力的所有者。托马斯和温斯洛的工作区域分别是塔顶和塔底,与二者的身份地位相对应,隐含要义是权力的划分与更迭。其次,灯塔是男性欲望的投射。守塔人托马斯多次称灯塔为“她”“我的美人”,视其为潜在的性爱对象。托马斯对灯塔的幻想与温斯洛对人鱼的幻想相呼应,构成了一组情欲象征。再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灯塔是双性同体的象征物。艾格斯曾提到,在威廉·达福饰演的托马斯的思维模式中,只将灯塔视为“她”,但灯塔实际上是双性别的,就像是个宇宙蛋[2]。其灵感来源于米尔恰·伊利亚德一篇关于光和种子的论文,即《灵魂、光及种子》[2]。伊利亚德在论文中重点剖析了民俗学中人们对“神圣的光”的体验。他指出,在既有的神话或神学体系中,光被认为是神、灵或圣化了的生命的表现[14]130。他认为所有类型的光的体验都有着共同因素:“它们使一个人脱离其世俗的宇宙或历史的状况,将他投入一个在质上完全不同的宇宙,一个具有根本区别的超越的神圣的世界,……通过与光的交会而被启示出来的宇宙与世俗的宇宙形成对立并超越后者,因为它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换言之,唯有具有灵魂者才能达到它。对光的体检通过揭示灵魂的世界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主体的存在论状况。”[14]129
在民俗学中,光往往被视作原初的种子、太阳的精子,是生殖力的显现。“光依其自身存在形式而成为‘创生宇宙的’。……发光的本源持有生殖的特性强调了神之光的创造性、永不枯竭的显示实在的特性。”[14]153其结果是“光的体验及幻觉的心像都具有性的意义”[14]173。影片中的托马斯和温斯洛都陷入一种对光的出神体验:托马斯将自己关在灯塔顶层,赤身裸体地沐浴在光辉之中;而温斯洛怀着对灯塔的渴望多次在储藏室自渎。光与精子的隐喻再一次对接。
灯塔双性同体的特性又与宇宙蛋相联系。当温斯洛登上塔顶,他看见中央有一个椭圆的、由八面透镜组成的灯芯在缓缓旋转着,就像一个在无尽空间中旋转的蛋。伊利亚德指出:“不管和什么样的仪式范型相联系,蛋从未失去其最初的意义:……蛋确保了重复原初行为,也就是创世行为的可能性。”[13]405影片结尾,当灯芯的窗口似神启一般对温斯洛开启,所散发的超自然的光便直接穿透了体验者的灵魂,被震慑的温斯洛摔下楼梯井,现实时空向神话时空逆转——他重复了原初之神普罗米修斯的受难仪式。
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除了少数民间故事仍然在一些乡间群体中被讲述外,民俗不再作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活生生的特征而存在,且在严格意义上说,民俗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已经僵死的特点[15]。而艾格斯的《灯塔》则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他从民间文化中发掘素材,尝试用影像使观众感受人类曾经的蒙昧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灯塔》为古老民俗志注入了新的生机。
四、结语
神话改编与重述是新时期电影创作的重要路径。罗兰·巴尔特声称,现代神话包含着具有强烈风格化特点的简单修辞,其自辩性不甚明显,其形式难以立刻把握[16]。谢阁兰亦认为,神话不过是一些组合起来的词语,只有拆解神话,从中引出新的碰撞或新的和谐,它才有价值[17]。这表明现代语境中的神话已从单一、明晰的讲述风格和意义结构中挣脱出来,向更加复杂、多元的体系迈进,这无疑对试图驾驭神话的创作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艾格斯的《灯塔》可谓交出了一份独特的答卷:不同于以往以神话为底本的恢宏巨制,反而在小成本独立电影中另辟蹊径地探索了神话再现的新路径。这位文献学家式的导演孜孜矻矻地从神话、传说与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创作策略上放弃了传统神话有机完整的故事结构,转而采用元素拼贴的方式,使得原本不相干的各神话体系在交织中达到混融,乃至产生了奇妙的意义共振。在衍生态神话的大旗下,《灯塔》在有限的时间内展示了杰出的渗透能力,用极具风格的影像将观众从19世纪90年代的新英格兰小岛带往更加久远的蒙昧时代,从希腊神话到海洋传说再到民间文化的象征仪式,在被浓缩的时间经验中构造出一个充满张力的地带,蕴含了可供观众再解读、再创造的无限可能。
注释:
①②祛魅与复魅是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一组概念。祛魅可视为一种现代对前现代或传统的反动,人类意识的不断发展要求祛除对自然、宗教的盲目崇拜;复魅则是现代人意识到正是科学的不断发展使得人类危机更加严重,进而采取的一种基于理性批判要求重新回归原始与自然状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