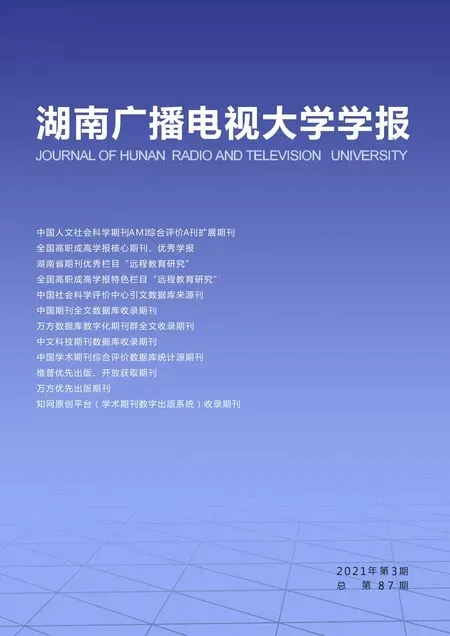视觉引导的知觉综合:论审美通感的发生机制
2021-11-30王婷婷
王婷婷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00)
在日常生活和审美活动中,不同的感官知觉之间经常会出现相互影响和转换的情况。钱钟书较早注意到了文学艺术活动中的这种现象,将其命名为“通感”,并撰《通感》一文,使用大量的资料对文学艺术中的通感现象进行了讨论,但并未对审美通感的发生机制进行解释。之后,国内对于审美通感现象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拓展。就审美通感的发生机制而言,许多研究者都试图从联想这一心理基础出发来进行说明。如金开诚认为,在通感的产生和应用中,联想始终是一个重要环节[1]。陈宪年和陈育德认为,形成通感的心理基础是由神经暂时的联系产生的想象、联想[2]。汪少华认为,通感是以我们概念系统中感官域之间特征相似性的心理联想为基础[3]。相关探讨实际上忽略了审美通感现象发生时知觉的整体性特征,也没有厘清审美通感中各个感官之间的关系。笔者试图从知觉现象学视角对审美通感的发生机制进行研究,以期揭示审美通感发生时知觉的先天综合特性,同时阐明视觉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审美通感的内涵与神经机制
在心理学中,通感又被称作联觉,指一种感觉引起另一种感觉的心理活动[4],但是这个定义仅在广义上对通感进行了界定。在美学领域,我们需要对一般通感和审美通感进行区分,因为二者虽然都具有通感的一般特性,但在发生机制和具体的知觉体验上存在较大差异。
一般通感和审美通感的共性体现在它们的发生都具有自然性和稳定性,自然性体现在主体对于通感知觉的感知通常是不由自主地产生,稳定性体现在主体对于同一刺激物所产生的通感知觉基本上不会改变。二者的差异体现在相比一般通感,审美通感现象的发生更具普遍性。在关于一般通感的研究中存在一种特殊的对通感症患者的研究,患有通感症的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异于常人。美国认知神经科学家葛詹尼加曾描述过一名通感症患者的感知体验:“J.W.和大多数人体验到的世界不一样。他可以‘尝到’词语。例如,单词‘精确的’,尝起来就像酸奶;单词‘接受’,尝起来就像鸡蛋。”[5]171听到不同的单词,J.W.的味觉就感知到了相应的味道,显然,J.W.的听觉与味觉之间存在特定的感知转换。对通感症患者来说,视觉与听觉、听觉与味觉等感官之间的转换是非常强烈的,他们的通感感知都是定向发生,普通人难以理解这种独特的通感体验。但相比这种状况,审美通感则能通过文学艺术大概率地发生在一个并不具有特殊联觉的人的审美活动中。如宋祁在《玉楼春》一诗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句,钱钟书认为用“闹”字“是想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摹成好像有声音,表示他们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6]。在对此句的审美欣赏中,“闹”字所涵盖的对“杏之红”和“花之盛”这两个视觉画面的听觉表达,对于所有的审美主体来说都是开放的。
与日常生活中的一般通感相比,审美通感更为复杂多样。在一般通感里,“视觉—听觉”和“视觉—触觉”的通感知觉现象是最主要也是最常见的:在声音的刺激下,大脑中会自然而然生成相应的视觉图像,如当听觉接收到潺潺的流水声时,视觉上会感知到一幅溪流涌动的画面;在视觉的刺激下,相应的触觉感受也会油然而生,如当人们看到雪亮的刀锋,尽管没有触碰,也会感知到一种锋利的触感。而在审美活动中,通感的发生绝非如此简单,如杜甫的诗句“晨钟云外湿”,叶燮评其“于隔云见钟,声中闻湿,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7]。此诗句用短短五个字便囊括了视觉、听觉、触觉三种不同感知,钟声、云雾、雨后的湿润感共同为读者营造出一个独特的审美情境,读者所体验到的是视觉、听觉、触觉相互交融所带来的别样美学趣味。
审美通感的发生过程伴随着大脑各部分的神经活动,简单来说,审美通感的神经机制可以概括为大脑皮层的一种兴奋泛化。由于大脑皮层的神经活动关联紧密,当某一感官受到对应物体的刺激时,也会对分管其余感官知觉的神经通路和不同区域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认知神经科学家Rauscher与Shaw发现了“莫扎特效应”,莫扎特奏鸣交响乐曲不仅激活了听者的颞叶,同时激活了大脑中枢分管运动以及视觉的神经中枢区域,并且还对具有协调功能的高级思维活动区域产生了影响[8]。除大脑皮层外,审美通感现象的产生也与上丘关系紧密,上丘位于中脑上部,分为浅层和深层:浅层接受来自视网膜、大脑皮层视觉区域和眼球运动中枢的信息投射;深层接受大脑皮层听觉区域以及躯体感受的信息传入;同时浅层与深层能够对传入的各种信息进行整合。这意味着视觉、听觉等感官传输的信息在上丘这一区域有了交换的可能性。已有研究表明:“上丘中单个细胞对联合了视觉、听觉和躯体感觉的刺激的反应要大于这三种刺激分别单独呈现时的反应。”[5]171单独的感官刺激对上丘细胞的激活程度低于多感官刺激,也就是说,上丘中的细胞实际上联合着不同感觉通道的信息,不同的感官知觉在上丘细胞中被统一整合并且能够相互影响。正如葛詹尼加所说:“五种基本的感觉系统,听觉、嗅觉、味觉、躯体感觉以及视觉,……这五种感觉也不是孤立工作的,而是一致行动以构建一个对世界的丰富的解释。”[5]174这一发现使得我们对审美通感现象背后的神经机制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二、审美通感的知觉特征
从对审美通感的内涵和神经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各个感官之间的交融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审美活动中,如果单纯运用分而论之的视角来对审美通感现象进行认知,便走入了审美误区。通过对日常审美经验的考察可以发现,通感现象总是以一种整体的状态被我们察觉。
在关于审美通感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将其发生的心理机制归于联想,但仅仅简单地用联想来解释审美通感中的一系列复杂现象是不充分的。康定斯基在讨论色彩效果时说:“色彩的心理效果究竟如上所述是直接的呢,还是来自联想?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灵魂与肉体浑然一体,心理印象就很可能会通过联想产生一个相应的感觉反应。……但是这样的论断不是普遍适用的。……德累斯顿有一个医生报告说,一个他称为‘感觉异常’的病人一尝到某种酱汁,就尝到了‘蓝色’,也就是见到了‘蓝色’。”[9]康定斯基意在说明,我们面对色彩所产生的一系列不同于视觉的感觉反应并不一定来自联想的作用,而可能是绕开联想更为直接地发生。康定斯基虽然对使用联想来解释审美通感的心理机制持保留意见,但他也止步于此,并未进一步进行说明。梅洛-庞蒂则在他的知觉理论中从现象学的视角对康定斯基所察觉到的审美通感的直接性进行了阐发。
梅洛-庞蒂认为,知觉是以身体为中介朝向世界的存在,身体感官是知觉产生的基石,知觉经由身体获得一种对于世界万物认知的首要地位,因为在知觉中涉及的是关于将物还原为物的原初经验。与此同时,在知觉对物的还原过程中,由于身体这一感知基础的统一性,知觉总是以通感的方式出现。梅洛-庞蒂提出了身体图式这一概念,认为身体的空间性不是一种有关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它不需要根据外部坐标来确定位置。相反,身体面对自身所处的任务处境能够主动地进行明确的自我定位。梅洛-庞蒂认为,人作为主体先天具有的身体图式是一种绝对知识,是主体对自己身体的直接认知。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通过一只内部的眼睛来打量自己的身体,身体不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中存在的实体,而是被纳入现象学的意向性层面。身体不再是一个外部空间中人的各个器官的组合,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是一个完形的结构,也是一个协同发挥作用的系统。他认为身体图式的理论是一种知觉理论。“我们重新学会了感知我们的身体,我们在客观的和与身体相去甚远的知识中重新发现了另一种我们关于身体的知识,……当我们以这种方式重新与身体和世界建立联系时,我们将重新发现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感知,那么身体就是一个自然的我和知觉的主体。”[10]265当我们用现象学的眼光审视身体的概念,图式实际上是一种知觉的表达,我们注意到的将不再是有关身体的客观知识,而是身体作为知觉主体所领会到的感知经验。这种感知经验一方面带来的是主体对于自我身体状态的整体性体悟,即重新发现我们自己。另一方面,如同福柯所言:“‘身体图式’作为‘意义的核心’以自身为‘焦点’向世界展开复杂的关联网络,‘身体—机体’通过一个原初意义的网络与世界相联结,这种原初的意义来自对于事物的知觉……”[11]这种感知经验也使得主体能够在与世界的联结中发现事物的原初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自我身体的重新发现,还是对事物原初意义的还原,诉诸单一的感官知觉是难以实现的,知觉在其中总是以一种综合的方式发生作用,各种感觉体验被知觉集中整合起来。
梅洛-庞蒂提出:“我不用‘视觉语言’来表达‘触觉材料’,或者相反,我不是逐个地把我的身体的各个部分连结在一起的;这种表达和这种连结在我身上是一次完成的:它们就是我的身体本身。”[10]198感官在知觉中建立起相互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不是后天偶然习得,也不是逐个完成,而是在身体完形特征的基础上本身就具有的一种先天性和整体性。知觉存在一种未分化的综合特征,通感就是知觉在这种整体性之下的特殊样态。由此可说,审美活动中审美通感的发生并不是各个感官知觉由分离走向联合的过程,因为知觉本身就具有先天综合特性,审美主体在审美对象的刺激之下所产生的各种感觉总是统一显现,它们不需要翻译就能够相互通达,通感是人类审美活动中自然而然出现的首要的知觉方式。
梅洛-庞蒂还指出:“是因为科学知识转移了经验,是因为要从我们的身体结构和从物理学家想象的世界中推断出我们应该看到、听到和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再会看,不再会听,总之,不再会感觉。”[10]293在这里,他将科学知识与知觉经验区分开,意在说明科学式的认知是难以触及知觉感知的。因为知觉感知指向的是对世界原初意义的揭示,是以要重新找回与世界原初的接触,便不能诉诸科学,此时艺术承担了这一任务。在艺术活动中,审美通感作为首要的知觉方式得到显现,其所涉及的是艺术家在创作表达中所体悟到的关于世界的原初经验。对于艺术家而言,敏锐的审美通感力正是他们能够进行艺术创作的前提条件。艺术家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或者纯粹的精神世界中与对象相遇,而是用感觉去捕捉物的存在及其散发出来的各种信息。梅洛-庞蒂认为塞尚的绘画充满矛盾,他不离开感觉外观来寻找真实,只以直接的自然印象为向导;他不追随物体轮廓,也不按照轮廓来调配颜色,既不用透视也不设计构图,放弃了勾勒,醉心于感觉的迷狂[12]。梅洛-庞蒂认为塞尚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知觉综合状态,即审美通感状态,单个感官之间壁垒的破除使他能够以一种多重感觉交互的迷狂状态来感知整个世界。在这样的状态下,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便得以源源不断地涌出。
三、视觉在审美通感中的特殊地位
虽然不同感官总是以统一的知觉形态出现,但与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知觉相比,视觉在审美活动中具有非同一般的作用。梅洛-庞蒂注意到了视觉的特殊性,他说:“当我说看到一个声音,我指的是我通过我的整个感觉存在,尤其是通过我身上能辨别颜色的这个区域,对声音的振动产生共鸣。”[10]299从梅洛-庞蒂的论述可以看出,主体对于声音的感知是以整体的感觉为基础的,但其中视觉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视觉在通感知觉中如此重要,阿恩海姆将原因归结为视觉本身所具有的思维特性。
阿恩海姆指出:“感性主义哲学家们一直在用强有力的证据提醒我们,在理性所得到的东西中,没有一样不是预先由感官采集,并在感性领域中出现过的。但即使持这种看法的人,也仍然把获取感性材料的活动说成是一种‘粗活’:它们是不可或缺的,但又是低级的,只有创造概念、积累知识、联系、区别和推理等,才是大脑中高级的认识活动。”[13]2知觉和思维的割裂实际上由来已久,即使是重视知觉体验的哲学家们也从狭义上将知觉看作是感官在受到外部刺激时所接收到的感觉经验,认为知觉只是被动地将接收到的信息传送至大脑,在知觉的运作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高级思维活动。阿恩海姆拒绝承认这种知觉和思维的二分,他认为“被称为‘思维’的认识活动并不是那些比知觉更高级的其他心理能力的特权,而是知觉本身的基本构成成分”[13]17。而视觉的运作中就存在积极的理性活动。视觉感官工作的过程并非一个纯粹截取现成图像的过程,即它并不处于一种机械或被动的状态,在面对同一景观时,我们可以将视线投向远处的山峦,也可以将视线转向近旁的树木。正如阿恩海姆所说,视觉活动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活动。“它也许只涉及视觉世界中很小的一部分,也许对准的只是眼前视觉空间的整个构架……从这样一种知觉探索中显现的世界并不是直接产生的,它的某些方面顷刻间就被构造出来,而另一些方面则需慢慢地呈示,但不管是快速形成的部分还是慢慢显示的部分,都要经过不断地证实、重新估计、修改、补充、纠正、加深理解等等。”[13]19视觉不是一个被动的信息接收传递器,其本身具有思维的能力,分析、综合、补充、修正等被认为是高级理性活动所具有的功能其实在视觉活动中就已经发生。
视觉具有选择功能。阿恩海姆提出:“积极的选择是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正如它是任何其他具有理智的东西的基本特征一样。”[13]26视觉在受到外部刺激进行图像捕捉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了自身的思维活动。在将信息传输至大脑之前,视觉能够事先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主动选择与重构,经由视觉整理之后,初步具有结构性的信息一方面能够被大脑更好地掌握和加工,另一方面秩序化的视觉信息也能够协助完善其他知觉感官对于物体的感知。阿恩海姆指出:“视网膜向大脑‘报告’色彩时,不会把无数种色调中的每一种都用一个特殊的信息录制下来,而是仅仅录制少数几种可以由之推衍出其他色彩的最基本的色彩或色彩阈限。”[13]28这一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视觉的选择性倾向,它不是单纯地向大脑“报告”信息,视觉的选择包含了对秩序的追求,在选择中视觉能够首先为我们呈现事物的粗略结构与大概特征,而在对事物一般形式的把握之下,触觉、听觉等知觉体验本身所带有的盲目性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克服。
视觉具有补充功能。在日常生活与审美活动中,一个物体被另一个物体遮挡的情况时有发生。在阿恩海姆看来,视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种重叠现象,能够对只呈现出局部信息的物体进行一种全貌式的把控。他认为:“视觉中的组织活动并不局限于直接呈现于眼前的材料,而是把看不到的那一部分也列入所见物体的真正组成部分。”[13]44如在一幅绘画作品上,一列火车正在经过隧道,列车的一部分车身被隧道掩盖,直接呈现出的是被隧道断开的两节车厢,但对观看者而言这列火车仍然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诸如此类的现象还有很多,由于这种知觉补足功能具有瞬间性,阿恩海姆认为它不是来自记忆经验的协助,而是来自视觉本身,视觉在面对感官刺激物时会主动对刺激物传达出的不完整的结构信息进行协调重组。此外,视觉的补充功能也能对其他感官的知觉活动产生一定影响。视觉概念是立体的,三度视觉概念指“不等同于物体的一个特定方面的概念。……是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之后得到的总印象”[14]。视觉完善了知觉中物体多维度的空间结构,弥补了触觉、嗅觉等感官在感知对象时的片面性和模糊性。视觉的补充功能使得其余感官知觉从朦胧走向清晰,也正由于各感官知觉的明晰化,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得以强化,作为整体出现的审美通感现象也变得更加强烈和明显。
视觉具有媒介功能。阿恩海姆引入感官剥夺实验试图证明视觉思维在不同感官知觉认知中的重要作用。所有的感觉材料都有其自身的丰富性,但如果这些感觉材料都以一种混乱的方式被投入到主体的知觉世界之内,它们所提供的就只是一些不成型的刺激,这将会造成人类感官以及心理机制的紊乱。而当视觉介入其他感官知觉的运作中时,一切就大不相同。阿恩海姆认为:“视觉的一个很大的优点,不仅在于它是一种高度清晰的媒介,而且还在于这一媒介会提供出关于外部世界中的各种物体和事件的无穷无尽的丰富信息。由此看来,视觉乃是思维的一种最基本的工具(或媒介)。”[13]24作为一种带有思维特性的工具,视觉不仅能够主动探索和组织可见或不可见的信息,在其他感官知觉发生之时,视觉也能作为媒介帮助其建立起更为明确的感觉意象。如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珠落玉盘是视觉所见,乐声嘈切是听觉所感,白居易将乐声比作珠落玉盘之声的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珠落玉盘的视觉画面,视觉的介入让此诗所描述的琵琶乐声以一种更明朗的方式得以呈现。此外,伴随着珠落玉盘这一视觉形象出现的,除了更为具象的琵琶乐声,还有珠与盘带来的触觉感知,因为唯有在坚硬而又光滑的表面,珠落玉盘之时才会响起如琵琶弦乐般清脆悦耳的声音。诗中听觉、触觉、视觉和谐交融,读者由此进入审美通感境界,而视觉所扮演的便是推动通感生成并且使其明晰化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