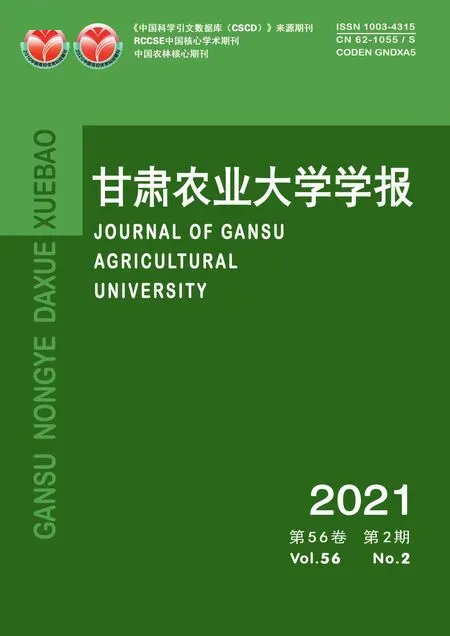高原鼢鼠(Eospalax baileyi)的生态学研究进展
2021-11-30花立民蔡新成
花立民,蔡新成
(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国家林业草原高寒草地鼠害防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70)
高原鼢鼠(Eospalaxbaileyi)是栖息于青藏高原高寒草甸、高寒灌丛草甸的地下啮齿动物.它掘洞造丘和采食牧草,导致地表塌陷、草地生产力下降以及水土流失.当种群密度过高时会严重威胁草地生态安全[1-3].据报道,高原鼢鼠是青藏高原仅次于高原鼠兔(Ochotonacurzoniae)的第二大危害鼠种[4-5].但是,高原鼢鼠也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在能量流通和物质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土壤物质循环和植被群落演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被称为高寒草地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工程师”[6-9].因此,深入开展高原鼢鼠的生态学研究,对于科学防治高原鼢鼠危害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进而维持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动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1 高原鼢鼠的分类地位
高原鼢鼠隶属鼢鼠亚科(Myospalacinae).亚科分类地位变化较大,先后被划入鼠科(Muridae)、瞎鼠科(Spalacidae)和仓鼠科(Circetidae)[10].随着分子系统学的发展,结合形态特征和栖息环境,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同将鼢鼠亚科(Myospalacinae)划分到鼹形鼠科(Spalacidae)中[11-13].目前,我国大部分学者也同意此种分类方式,即高原鼢鼠隶属于鼹形鼠科鼢鼠亚科[14-15].高原鼢鼠属的分类地位争议不多,依据头骨枕部形状归于凸颅属(Eospalax).但是,对于高原鼢鼠种一级分类地位一直颇有争议.主要集中在高原鼢鼠、甘肃鼢鼠(Eospalaxcansus)和中华鼢鼠(Eospalaxfrontanierii)是独立种,还是同种异名的问题上.以往学者在甘肃鼢鼠和高原鼢鼠分类鉴别时多依赖于形态学特征[16-19],并且在不同地理区域的基础上研究种群的形态变异[20].随着分子系统学成为经典分类学的重要补充手段后,利用线粒体DNA的分子系统学方法对鼢鼠的分类地位和系统发育进行了有益探讨[21-22].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甘肃鼢鼠和高原鼢鼠为两个独立种[23-25],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甘肃鼢鼠和高原鼢鼠不能成为独立种,仍为中华鼢鼠的两个亚种[16].国外学者Wilson等[11]认为甘肃鼢鼠和高原鼢鼠是中华鼢鼠的同物异名[11],这就更加剧了这两种鼢鼠的分类地位争议.
2 高原鼢鼠的现实分布范围及气候变化背景下潜在的分布变化
高原鼢鼠是栖息于青藏高原的特有地下啮齿动物,主要分布于高寒草甸和高寒灌丛草甸[9].楚彬[26]通过大尺度调查发现,高原鼢鼠分布与气候、海拔和栖息地植物及土壤理化性状有关,主要分布于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E 100°~103°,N 33°~36°),海拔3 200~3 800 m,年均气温-1~2 ℃,年降水量大于500 mm的高寒草甸区.
高原鼢鼠分布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气候因子中降水可显著影响草地土壤含水量和植物分布,进而影响到高原鼢鼠对栖息地的选择.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预测气候变化背景下高原鼢鼠的潜在分布区变化也将备受业内关注.Su等[27]研究发现,按照当前气候变化的趋势,青藏高原的高原鼢鼠在2050年适宜栖息地会增加6.25%,预计迁移向低海拔的南部区域,迁移距离在1~94 km之间.楚彬[26]利用随机森林模型(RF)预测RCP 2.6、RCP 4.5和RCP 8.5情景下,未来气候变化与高原鼢鼠潜在分布面积变化密切相关.在 RCP 2.6情景下,预测2050s和2070s青藏高原东缘温度会分别上升2.1 ℃和2.0 ℃,相比于当前高原鼢鼠潜在分布面积,2050s高原鼢鼠潜在分布面积将增加2.33%,2070s高原鼢鼠潜在分布面积会减少3.60%;在 RCP4.5情景下,2050s和 2070s青藏高原东缘温度将分别上升2.7 ℃和3.0 ℃,2050s和 2070s高原鼢鼠潜在分布面积相比于当前分布面积会分别增加11.86%和 9.32%;在RCP8.5情景下,2050s和 2070s青藏高原温度将分别上升 3.4 ℃和4.6 ℃,2050s和2070s高原鼢鼠潜的分布面积相比于当前分布面积将分别增加11.74 %和11.60 %.总之,未来在青藏高原气候“暖、湿”化的大背景下,高原鼢鼠的分布范围会呈持续扩张的趋势.
3 高原鼢鼠的栖息环境
栖息环境是野生动物生存和繁殖的基础,明晰高原鼢鼠栖息环境特征有利于掌握高原鼢鼠栖息地选择及利用规律,可为研究其种群生境适应和草地系统健康评价提供科学依据,对高原鼢鼠危害防控和草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研究者对高原鼢鼠栖息环境已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地上环境特征(植被及土壤)和地下洞道环境特征两方面.
3.1 栖息地植被和土壤特征
高原鼢鼠是植食性地下啮齿动物,栖息地植被直接决定着植物性动物的食物来源和质量[28].研究发现,高原鼢鼠栖息地植被主要由禾本科、莎草科和杂类草组成[29-30].多数研究认为高原鼢鼠喜食杂类草[31],因此,其栖息地选择偏向于植物群落中杂类草较多的草地[32-34].但是,高原鼢鼠栖息地选择植物偏向因草地类型而各异.田永亮等[35]研究了祁连山北麓高寒草甸、高寒灌丛草甸和高寒草原上高原鼢鼠栖息地选择特性,结果显示高寒草甸中高原鼢鼠喜选择杂类草较多的草地,而高寒草原中喜欢选择莎草科较多的草地,高寒草原中莎草科类草地主要集中在地下水含量较多的区域.此外,放牧强度对高原鼢鼠栖息地选择也具有重要影响.楚彬等[36]研究了禁牧和放牧条件下高原鼢鼠栖息地植被特征,他发现高原鼢鼠种群密度与杂类草生物量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可食牧草生物量呈负相关关系.禁牧条件下禾本科植物占多数,因此高原鼢鼠种群密度也较低.刘丽等[37]研究了不同放牧强度下高原鼢鼠栖息地植被特征.结果显示高原鼢鼠相对种群密度与地下根系生物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与植物丰富度和地上植被总盖度呈显著正相关,与地上生物量、物种均匀度和多样性呈不显著正相关.在重度放牧条件下,家畜首先采食株高较高的禾本科、莎草科植物,导致匍匐型、莲座型植物增加,而这类植物一般含有大量的块根、鳞茎和轴根,地下生物量和含水量均较高,为高原鼢鼠提供了适宜的食物,因而更偏向栖息于此类草地.
除植物作为食物影响高原鼢鼠对栖息地选择外,土壤也是重要的栖息地选择因素.因为土壤不仅影响到高原鼢鼠挖掘的能量消耗[38],也直接影响植物物种分布和生长.在地理尺度下,楚彬等[39]研究了青藏高原东缘238处高原鼢鼠分布点与土壤因子的关系,发现土壤水分含量、土壤容重、土壤粘粒含量和土壤砂粒含量与高原鼢鼠分布呈单峰响应关系.在微生境尺度下,刘丽等[37]和楚彬等[36]发现高原鼢鼠喜欢选择在土壤紧实度和容重相对较低,而土壤含水量相对较高的区域.相比食物因素,土壤物理性质,主要是土壤紧实度和含水量是影响高原鼢鼠栖息地选择的首选因素.
综合植物和土壤因素,楚彬等[34]利用地统计学方法分析了植物物种、营养、土壤物理性状对高原鼢鼠栖息地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高原鼢鼠喜选择土壤疏松、莎草科丰富度较低、杂类草较多和根系粗脂肪含量较高的地方.
3.2 栖息洞道环境特征
高原鼢鼠常年生活在地下,具有复杂的洞道系统[40-41].洞道环境既为高原鼢鼠采食、繁殖等提供场所,又使其免受天敌和外界不良环境的干扰[42],因此,洞道环境特征对于研究高原鼢鼠地下适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高原鼢鼠生活于封闭、黑暗、高湿的地下洞道中,内部空气几乎无法流通.相比地表环境而言,洞道温度和湿度波动较小,趋于稳定[43].对高原鼢鼠洞道气体研究发现,高原鼢鼠洞道气体含量主要为氧气、二氧化碳和甲烷3种.这3种气体会随季节、土壤类型、降水和洞穴深度不同而发生动态变化,但总体呈现出高二氧化碳、较高甲烷、低氧的特点.高原鼢鼠对氧气浓度尤为敏感,会由于开洞导致洞道氧气浓度变化而发生堵洞行为[44-45].
除气体外,洞道土壤理化性质和微生物也是高原鼢鼠定居后重要的影响对象.姬程鹏等[46]对比分析了高原鼢鼠活动洞道和无鼢鼠扰动的同深度土层土壤(对照)的土壤养分、微生物和土壤酶.研究发现高原鼢鼠活动洞道土壤速效磷和全氮含量均高于无鼢鼠扰动土壤,其中春季和秋季的速效磷达到显著水平.秋季无鼢鼠扰动土壤有机质和真菌的含量显著高于洞道土壤.脲酶、蔗糖酶、碱性磷酸酶活性活动洞道与无鼢鼠扰动土壤间无显著差异.无鼢鼠扰动土壤春季土壤细菌含量显著高于洞道土壤.洞道和无鼢鼠扰动土壤细菌、放线菌、速效磷、全氮和有机质的含量均在夏季达到最大值.田永亮等[47]进一步对洞道上下壁土壤含水量、有机质、全氮和速效氮进行研究,他发现高原鼢鼠活动洞道下壁的有机质、全氮和速效氮含量上升,而上壁的土壤含水量和速效氮含量下降.分析认为高原鼢鼠采食过程中食物掉落和排便行为导致了洞道下壁土壤有机质、氮含量增大,而高原鼢鼠在洞道的来回穿梭而形成“闪急干燥”,使洞壁上层土壤含水量下降和容重增加.
4 高原鼢鼠活动模式与行为
动物活动模式主要受到光照、温度、食物和天敌的综合影响[48-49].高原鼢鼠活动模式受外界环境因素和内在生理机制的共同调节,能反映高原鼢鼠健康状态和行为策略[50-51].高原鼢鼠长期生活在黑暗洞道环境中,似乎其活动节律不受光照影响.但是,现有研究发现高原鼢鼠表现出似昼夜活动节律,以及独特的地表活动行为,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4.1 日活动节律
早期研究认为,高原鼢鼠在夏秋季有2个日活动高峰,一次是15∶00~22∶00,另一次是0∶00~7∶00;春季及入冬前,日活动高峰只有一次,主要集中在下午和前半夜;冬季活动时间段在黄昏前后至初夜[52].随着动物无线电追踪技术的发展,姬程鹏等[53]和张飞宇等[54]利用该技术在高原鼢鼠的非繁殖期和繁殖期对其活动节律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在非繁殖期的6月至10月,高原鼢鼠每日活动均表现出2个高峰时段,其中6月至9月活动高峰期为早上6点和晚20~22点,10月活动高峰在早8点和晚18点[53].在繁殖期,高原鼢鼠日活动有3个高峰期,时间分别为8∶00、14∶00和20∶00.繁殖期活动强度雌雄间存在差异,无论是活动时长还是活动强度,雄性都显著高于雌性,均在14点活动强度达到最大[54].
虽然对高原鼢鼠似昼夜活动节律没有深入研究,但姬程鹏等[53]认为高原鼢鼠地下20 cm的活动洞道土壤温度日出日落期间变化不超过1℃.非繁殖期高原鼢鼠双峰型日活动节律与温度变化无关,而与光照强度变化有关.估计高原鼢鼠的哈氏腺异常发达,可以作为光感受器接收外界光刺激,从而调节昼夜节律活动.
4.2 季节性活动节律
高原鼢鼠一年有求偶、哺乳、储粮和越冬4个阶段的活动期[52],这也使其年活动节律表现出季节性差异.春季是高原鼢鼠的主要繁殖期,在这期间,高原鼢鼠会通过挖掘洞道并利用震动通讯实现求偶定位,从而完成雌雄个体的交配.从高原鼢鼠推出鼠丘的数量可以发现,春季鼠丘数量较多,活动强度在一年间较大.夏季由于食物资源丰富,高原鼢鼠不必通过高强度活动来满足营养需求,其活动总量有所降低.进入秋季,由于高原鼢鼠需要通过大量挖掘采食来储藏越冬食物,日活动量达10 h以上,是高原鼢鼠活动最剧烈的季节.冬季,由于气温过低土层冻结,高原鼢鼠往往连续数天呆在主巢或只在午后外出活动片刻,基本很少活动[51-52,54-55].
4.3 地表活动行为
以往研究认为,高原鼢鼠属于完全营地下生活(year all round)的地下啮齿动物(subterranean rodents),而不是有地表活动行为的穴居动物(fossorial rodents).因而关于高原鼢鼠耐低氧、高二氧化碳的生理适应机制研究都是基于高原鼢鼠完全营地下生活方式.但是,Chu等[56]利用红外相机和无线电追踪技术记录到高原鼢鼠有季节性地表采食行为,集中在夏季的6月和7月的白天,且主要是雌性个体.周文杨等[52]也曾报道过高原鼢鼠在夏秋季有地面活动行为,崔庆虎等[57]也发现在大鵟(Buteohemilasius)和雕鸮(Bubobubo)的食物中高原鼢鼠的贡献率仅次于高原鼠兔.上述研究充分说明,高原鼢鼠并不是完全营地下生活的啮齿动物,具有地表活动的行为特征.Chu等[56]进一步分析了高原鼢鼠地表活动的原因,发现植物地上部分的高脂肪是吸引高原鼢鼠出洞到地表活动的原因,推测可能是6月和7月是高原鼢鼠的泌乳期,雌鼠需要更多的脂肪来哺乳幼仔,权衡风险后到地表采食.
4.4 震动通讯行为
动物通讯是个体识别、竞争、繁殖、躲避天敌以及维持家族联系的基础[58-59],一般包括视觉通讯、听觉通讯、化学通讯、嗅觉通讯和震动通讯等[60-61].高原鼢鼠属于严格独居型地下啮齿动物,非繁殖期雌雄独居于相互隔离的土壤洞道系统.繁殖期雌雄个体间建立求偶通讯联系是其成功交配的关键.进入繁殖期,高原鼢鼠如何实现雌雄间信息交流并定位寻找配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周建伟等[62]利用震动波检测器、无线电追踪以及波信号分析软件,发现高原鼢鼠在洞道内利用吻端敲击洞道前壁产生震动信号,信号由数个连续的脉冲组组成.雌性每个脉冲组包含2~24个脉冲,雄性包含2~13个.雌性单个回合敲击持续时间和敲击次数都显著高于雄性.雌雄个体震动信号都属于低频震动,有利于信号的长距离传递.
5 高原鼢鼠食性
王权业等[63]利用胃内容物镜检法研究了其栖息于高寒草甸和高寒灌丛两种栖息地的高原鼢鼠食性,结果显示高原鼢鼠的食物组成在两种栖息地之间和性别之间均无明显的不同,不同植物出现的频次却有明显的差异.禾本科植物在高原鼢鼠的胃内容物中基本没有发现,对莎草科植物也只取食两个物种,高原鼢鼠所取食的植物主要是杂类草.在两种栖息地中高原鼢鼠喜食度指数最高的 9种植物均为鹅绒委陵菜(Potentillaanserina)、直立梗唐松草(Thalictrumalpinum)、丽江风毛菊(Saussurealikiangensis)、雪白委陵菜(Potentillanivea)、美丽风毛菊(Saussureasuperba)、细叶亚菊(Ajaniatenuifolia)、异叶米口袋(Gueldenstaedtiahimalaica)、磨岭草(Morinachinensis)和棘豆(Oxytropissp.).苏军虎等[64]利用粪便和胃内容物显微组织分析法研究高原鼢鼠食性,结果显示高原鼢鼠主要采食美丽风毛菊、鹅绒委陵菜、蒲公英(Taraxacummongolicum)及垂穗披碱草(Elymusnutans).王志鹏[65]利用稳定性同位素技术研究高原鼢鼠不同季节的食性,他发现高原鼢鼠采食植物地上和地下部分,且不同月份存在差异.9月份地上食物主要是问荆(Equisetumarvense)、矮嵩草(Kobresiahumilis)和赖草(Leymusracemosus),地下食物是线叶嵩草(Kobresiacapillifolia)和早熟禾(Poaannua);8月份地上食物以鹅绒委陵菜和问荆为主,地下食物以鹅绒委陵菜为主;6月份地上食物以鹅绒委陵菜和问荆为主,地下食物以鹅绒委陵菜和矮嵩草为主.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高原鼢鼠主要以采食植物地下根茎为主,对植物地上部分也有所采食.王权业等[63]没有发现高原鼢鼠胃内有禾本科牧草,可能与其捕获高原鼢鼠的时间与采集植物样本的时间不一致有关.
6 高原鼢鼠的种群动态
草地鼠害发生与种群密度波动有关,而种群密度波动与繁殖、死亡、迁移以及外界因素密切相关[66-67].鼠类繁殖力是其种群数量增长的关键[68-69].高原鼢鼠是青藏高原高寒草甸主要危害鼠种之一,其种群数量直接关系到草地生态系统健康[26].因此,研究高原鼢鼠种群动态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于高原鼢鼠危害预警和科学防控意义重大.
6.1 高原鼢鼠的生态寿命
高原鼢鼠寿命多长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的一个难题.多数研究通过体重或牙齿的磨损程度来划分高原鼢鼠的年龄[70-71].楚彬[26]利用电子标签(Pit-Tag)进行标志重捕.通过长达7 a的研究发现,高原鼢鼠雌性个体的平均生态寿命(28.17±9.02)月,高于雄性个体的平均生态寿命(23.20±8.87)月,但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研究区中雄性个体最长寿命为34个月,最短寿命为12个月,大部分雄性个体的寿命在24个月左右.雌性最长寿命为41个月,最短寿命为17个月,大部分雌性个体寿命在22个月左右.
6.2 种群动态月际和年际变化
高原鼢鼠是典型的季节性繁殖动物,因而其种群数量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从当年春季繁殖期开始到秋季植被枯黄期,高原鼢鼠种群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从秋季至翌年春季繁殖期来临期间种群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72].楚彬等[26]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了6 a内高原鼢鼠春季和秋季的种群数量分别与气候和食物因子的关系,结果显示温度对春季和秋季高原鼢鼠种群数量的影响较大,其次是杂类草地下生物量.高原鼢鼠种群数量年际间也存在动态变化,其波动周期约为6~7 a,时间相对较长,分为潜伏期、上升期、高峰期和衰退期4个阶段[73].
高原鼢鼠种群变化受到种群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74],其中种群结构、气候条件和食物资源是影响其种群动态的主要因素[39,73,75].丁连生等[76]对高原鼢鼠的种群消长与其繁殖特性的关系做了研究,结果显示,雌雄性比决定高原鼢鼠怀胎率和繁殖强度,是衡量种群密度及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种群数量的消长.郭强等[75]研究了其高原鼢鼠种群数量与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后发现,高原鼢鼠种群密度与年平均气温、年相对湿度和日照时长紧密相关,气候因子的变化可通过改变高原鼢鼠栖息生境和食物资源来间接影响高原鼢鼠种群动态.周延山等[77]通过6 a的研究发现,高原鼢鼠妊娠率和种群密度与栖息地植被生长状况及气候因子无相关关系,环境因子对高原鼢鼠种群特征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一定种群密度下,高原鼢鼠繁殖特性的变化与地下根可溶性糖含量和土壤水分有关,而繁殖特性与草地植物组成、草地生物量无显著关系[78].这个研究结果说明高原鼢鼠繁殖更多是受其自身生理条件影响,草地植被退化中富含可溶性糖的杂类草比例增加可能会导致其种群数量增加.
6.3 种群扩散
高原鼢鼠是独居型地下啮齿动物,在其幼体长成亚成体或成体后一般会迁移独自生存,实现种群扩散[73].扩散有遗传扩散和生态扩散两种.但无论哪种形式,高原鼢鼠鼠丘空间分布的变化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扩散,这也是导致高原鼢鼠危害面积扩大的原因之一.魏万红等[79]认为,种群密度是引起高原鼢鼠扩散的主要原因.当种群密度达到饱和后,新生个体的出现加剧了其种群内部对生存空间和食物资源的竞争,这迫使处于劣势地位的幼体发生扩散,维持了原有栖息地高原鼢鼠种群密度的稳定.楚彬等[80]采用标志重捕、无线电追踪以及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了时间和空间小尺度高原鼢鼠扩散,高原鼢鼠在不同种群密度下均发生扩散,高密度区扩散个体比例相对较高.高原鼢鼠存在偏雄性扩散,扩散时间一般发生在6~9月[80].
7 高原鼢鼠干扰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高原鼢鼠是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组分,在土壤养分循环、食物网维系和植物群落演替等方面发挥着多重功能.目前,高原鼢鼠对草地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被、土壤和土壤动物等方面.
7.1 对植被的影响
植物是影响高原鼢鼠栖息地选择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栖息时间和种群密度的增加,高原鼢鼠干扰也会影响栖息地植被组成,形成动植物间的协同进化.Niu等[8]以高原鼢鼠鼠丘密度代表干扰强度,研究了其对高寒草甸、高寒灌丛草甸和高寒草原植物多样性的影响.他发现随着鼠丘密度增加,高寒草甸植物多样性呈增长趋势,高寒灌丛草甸植物多样性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而高寒草原植物多样性却呈减少趋势.Chu等[81]研究也发现适度的高原鼢鼠干扰不但不会影响草地生态系统植被生长状况,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植物多样性和丰富度.金樑等[82]研究发现低密度高原鼢鼠通过啃食植物根系可限制鹅绒委陵菜等毒杂草的扩展,从而增加草地禾本科和莎草科等优质牧草的竞争力,优化草地植被群落组分.Niu等[9]进一步研究发现,鼠丘裸地与丘间草地形成的斑块格局对植物群落演替产生重要影响.鼠丘裸地为杂类草和根茎类禾草提供了定植机会,随着群落演替进行,6 a后鼠丘裸地植被群落与丘间草地基本一致.此研究结果说明由于高原鼢鼠鼠丘斑块与丘间草地的耦合,促进了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的更新,是维系草地植物物种共存的驱动力,对于科学理解高原鼢鼠危害具有重要意义[9].
但是,当高原鼢鼠种群密度过高时,草地植被盖度由于鼠丘斑块不断增加而显著降低.优良牧草被鼠丘覆盖致死,大面积鼠丘裸地为毒杂草的入侵和建植提供了便利,之后由于毒杂草在植被群落中竞争力逐渐增强并占据优势地位,造成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和植被生产力严重下降[83-84].此外,高原鼢鼠的重度干扰也促使植物群落出现适应性应答,导致鼠群喜食植物减少,随之被适口性差、耐牧性强的物种代替,迫使高原鼢鼠放弃原有栖息环境,逐渐向周围适应生境转移,扩大危害范围,而被遗弃的洞道由于降水淋溶和风蚀的作用又加剧了黑土滩的形成,使草地退化程度加深[85-86].
7.2 对土壤的影响
土壤是高原鼢鼠掘土造丘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其理化性质不仅影响植物生长,还关系到草地生态系统稳定[87].高原鼢鼠掘土活动还能增加高寒草甸土壤通透性和水分渗透率,促进土壤微生物活性,进而加快土壤养分循环[86,88],为草地植被生长和土壤种子库萌发提供了有利环境[89-90].鼢鼠干扰还使土壤养分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生改变[87],造成鼠丘土壤养分含量和分配的异质性,并在短期内出现养分富集效应[2].
土壤特征是影响高原鼢鼠生存的重要因素,调查发现,高原鼢鼠栖息地通常选择在土壤紧实度、容重相对较低,而土壤含水量相对较高的区域[39,91].同时,高原鼢鼠也能影响草地土壤理化性质.在环境容纳量允许的范围内,随着种群密度的增大,高原鼢鼠栖息地土壤含水量、容重、全氮、全磷和有机碳含量均有增加趋势,而当种群数量过大,高原鼢鼠活动形成的大面积裸地斑块(黑土滩)则会引起土壤水肥流失[88].
7.3 对土壤动物的影响
土壤动物作为陆地生态系统地下分解者和消费者,通过食物网参与了植物-土壤界面的物质循环,对调控生态系统过程和维持系统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高原鼢鼠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重要的生物干扰源之一,对植物-土壤界面的生态学过程具有显著影响,进而可引起土壤动物多样性及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叶国辉等[92]研究发现高原鼢鼠干扰对植食性土壤动物类群组成和空间分布影响较大,但对捕食性类群影响较小.分析认为高原鼢鼠干扰下高寒草甸土壤动物功能类群组成和分布明显受环境因子制约和营养级联效应调控,表现出土壤温度、紧实度以及莎草类地上生物量构成的土壤与植被环境异质性,以及捕食性类群对植食性类群群落调控作用共同影响土壤动物功能群群落组成及分布.
7.4 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据统计,一年内每只高原鼢鼠推丘数可达250个,推土量在1 t左右[93].在高密度高原鼢鼠栖息区,其高效的推土活动严重破环草地土壤表层,形成大量次生裸地,外加风蚀影响,土壤养分逐渐丧失,最终引起草地沙化和水土流失,加剧了草地退化.马素洁等[3]研究发现,高原鼢鼠新生土丘在降雨和风力的影响下,不同地形和不同丘型的新生土丘均会发生中度侵蚀.且在侵蚀作用下,新生土丘表层土壤有机质、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和土壤含水量都显著低于无土丘草地表层土壤,导致土壤营养物质流失.高寒草甸土壤侵蚀现象与草地退化现象密切相关.高原鼢鼠是青藏高原优势物种之一,其造丘形成的次生裸地是高寒草甸退化过程中的主要干扰因素,也是草地退化的重要标志.因此,从水土保持角度出发,应严格控制高原鼢鼠种群密度,防止大量裸露土丘在侵蚀作用下造成土壤及其营养物质的流失.
8 挑战与展望
高原鼢鼠是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地下啮齿动物,也是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由于其分布范围广,对草地的生产和生态功能的影响巨大,因此受到草地管理工作者和科研学者的高度关注.由于高原鼢鼠长期生活在地下洞道,其隐蔽的栖息环境和特有的生活方式,导致高原鼢鼠活动不易直接观察,无疑给高原鼢鼠生态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从目前文献来看,高原鼢鼠在行为、繁殖、种群动态等多个基础生态学领域已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其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还存在很多的推理和猜想未经验证[94-95].Hua等[14]发明了非损伤型鼢鼠活捕器,实现了无线电追踪技术、电子标签标记技术等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高原鼢鼠生态学的发展.但是,对于深居地下1~2 m的高原鼢鼠,研究其巢区温湿度、气体等变化,目前尚存在技术瓶颈.特别是高原鼢鼠在自然状态下的繁殖交配、产仔、哺乳等行为及其时间,还需利用微型成像系统进行细致观察.
高原鼢鼠与草地植被、土壤的互作效应是科学评价其危害、保护物种多样性和理解草地生态系统动态稳定的基础.此类研究需要通过长时间和大空间尺度的研究,才能获得可靠的科学证据.但是,从目前所报道的研究结果来看,许多研究存在研究时间较短、空间尺度较小的不足,高原鼢鼠生态学研究系统性不强.此外,在家畜与高原鼢鼠对草地植被、土壤的影响方面,目前缺少大型控制性试验,导致家畜和高原鼢鼠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差异化影响不能厘清.今后应该设立国家科技专项研发项目,在青藏高原高原鼢鼠重点分布区支持开展不同畜种、不同放牧强度以及不同高原鼢鼠种群密度的组合控制性试验,通过长期定位研究,探究高原鼢鼠在草地生态系统的功能.
研究高原鼢鼠种群动态变化规律是预警和防治其危害的关键.影响高原鼢鼠种群动态变化的因素较多且复杂.目前此类研究由于研究时间短、预测预报模型精度低等问题,导致无法科学指导和防控高原鼢鼠危害.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和高寒草地家畜放牧数量急增的背景下,需通过长期和大范围研究,研发高原鼢鼠种群动态变化驱动力模型.此外,高原鼢鼠种群动态变化中,量化对草地生产和生态功能产生负面影响的鼠密度转折点也是将来研究重点之一.寻找反应高原鼢鼠对草地生产和生态功能影响的科学指标以及量化这些指标的方法是关键.今后此类研究应该整合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知识逐步攻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