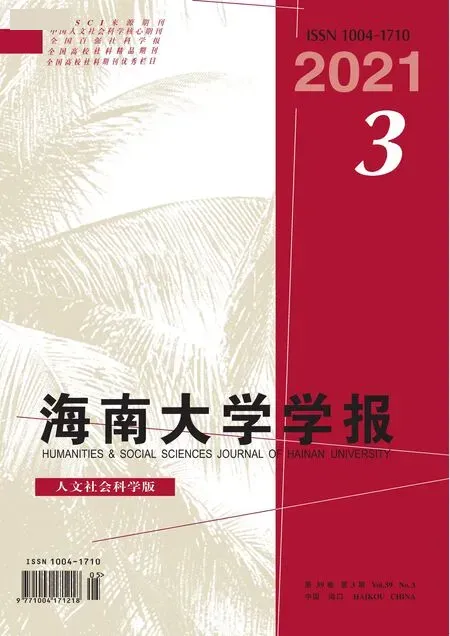论左翼文艺运动初期 “ 革命情绪 ” 的发生与实践
2021-11-30覃昌琦
覃昌琦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左翼文艺运动与左翼文学是近年来受到越来越高关注的研究领域,也呈现出越来越深化的研究格局。总体来看,在延续了史料整理的基础上趋向了多元、立体的学理化研究。一方面,基于长期史料研究,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脉络得以客观镜像式的呈现;另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野的引入,对如何处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提供了广阔视角。可以看到,左翼文学研究在文本阐释、时段分期、历史语境等内外研究中显示出多元化的研究面向。
但是,长期以来对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注重无产阶级理论的客观化研究路径,而对革命知识人思想与情感转折中的主体考察还不够充分。 “ 革命情绪 ” 是左翼文艺运动初期备受关注的问题,革命知识人经由无产阶级理论与 “ 革命文学 ” 论争的语境从而进一步确立自我主体性,并在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将 “ 革命情绪 ” 的话语实践与大众化的问题深入融合。 “ 革命情绪 ” 既是民众情感的组织化,也是革命知识人主体思想和情感改造的社会化实践,它因为理想型革命者人格构造的可能性而具有革命的驱动力。从 “ 革命情绪 ” 与革命知识人主体实践的视角来考察左翼文艺运动初期①文中所论述的 “ 左翼文艺运动初期 ” 概念,采用一般的观点,从时间意义上来说,上以1927年 “ 革命文学 ” 论争为肇始,下迄1930年 “ 左联 ” 成立以及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开展,这也接近张大明的 “ 狭义左翼文学 ” 的观点。值得说明的是,本文的 “ 左翼文艺运动 ” 仍然是建立在 “ 十年左翼 ” 的广义的概念基础上, “ 初期 ” 则是针对这一概念的阶段性划分。参见张大明《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的文艺大众化与革命者人格等问题都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阐释价值。
一、 “ 革命文学 ” 论争时期的无产阶级理论倡导
1927年末,一批留日归来的知识分子首先喊出 “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 的口号。这批 “ 新锐的斗士 ” 抱定 “ 全面批判 ” 的决心和态度,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杂志上发起了 “ 革命文学 ” 的论争,将论战的矛头指向鲁迅、茅盾等人。成仿吾是创造社的元老,经由他发起 “ 革命文学 ” 的论争。成仿吾在论争之初写作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来宣告 “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 新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成仿吾在 “ 革命文学 ” 的理论倡导中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放置在极高的地位,一方面他强调将小资产阶级劣根性 “ 奥伏赫变 ” (德语Aufheben的音译,意即扬弃),知识阶层要进行严厉的自我批判;另一方面,则是要进入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成之中, “ 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工农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 ”①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7年第9期,第6页。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需要与工农大众接触,将工农大众作为无产阶级意识获取的源头,并创作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成仿吾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强调,代表着 “ 革命文学 ” 诉之于阶级理论形态的一股强音,他对知识阶层的自我小资产阶级属性表现出激烈的批判意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强调,成为一般革命的知识阶层驱逐 “ 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Ideologie的音译,意即意识形态) ” ,从而走近并获得无产阶级大众的前提和准备。
那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左翼文艺运动初期是如何与知识人的革命话语发生关联的呢?换句话说,革命知识阶层又是如何获得无产阶级意识的呢?
“ 革命文学 ” 论争之前,郭沫若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文艺创作应该具有阶级立场,站在 “ 第四阶级 ” 说话,而这种立场是与周作人所质疑的阶级意识相对立的,换言之,在郭沫若看来,革命与否,是否跟时代落伍,对于文学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是否具备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那么知识阶层或者说革命文学作家的无产阶级意识从何而来呢?郭沫若认为, “ 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里去,革命的漩涡中去。 ”②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926年第3期,第11页。革命文学作家的无产阶级意识的获取不在其阶级本身,而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之中,社会实践的对象就是工农革命实际,革命文学必然地成为发动和策应工农革命运动的有利 “ 武器 ” ,从而完全告别小资产阶级的 “ 艺术的宫殿 ” , “ 革命文学 ” 从而才能进一步成为无产阶级的 “ 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 ” 在郭沫若这里, “ 革命文学 ” 是摒弃了 “ 艺术宫殿 ” 的全然的个人主义,而被无产阶级意识所取代。在 “ 当一个留声机 ” 的论争中,郭沫若以 “ 接近那种声音 ” 的无产阶级立场来号召一般的知识青年,而在李初梨看来,普罗文学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自身意识和属性的生成过程,因而要 “ 成为那种声音 ”③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第2期,第18页。,无产阶级意识成为了 “ 革命文学 ” 向 “ 普罗文学 ” 转化的必然规定性。
“ 革命文学 ” 的无产阶级理论倡导与李初梨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李初梨进一步阐发了 “ 革命文学 ” 如何经由阶级意识与理论的获取进入到 “ 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 ” 。李初梨首先否定的就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创作出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并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阶层获取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正当性辩护。知识阶层并不因为阶级性的限制而不能创作无产阶级文学,但是他的理论前提仍然是知识阶层迈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途。而这驳斥了郁达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产生于其阶级自身的观点,将 “ 革命文学 ” 创作的主体进一步放大化、自由化。实际上,左翼文艺运动初期的革命文学论争的中心便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主体与对象的问题,针对前者,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则将 “ 有闲 ” 的鲁迅、茅盾等视为应该被 “ 奥伏赫变 ” 的阶层予以批判;而后者,则建立在较为空泛的大众文艺观理论倡导的阶段,知识阶层的大众化实践要到 “ 左联 ” 成立之后才得到进一步深入的展开。
1928年,鲁迅先后发表了《文艺与革命》《 “ 醉眼 ” 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来回击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的 “ 十万两无烟火药 ”④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7年第9期,第5页。。 “ 不革命便是反革命 ” ,革命者/ “ 落伍者 ” 等二元论成为 “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 倡导者发难的主要话语方式。 “ 革命文学 ” 阵营的论战相对于国民政府对新兴左翼文化的压制显得不痛不痒,鲁迅对左翼内部的弊端一直看得清晰,他既有 “ 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 ” ,也有对于革命看得 “ 不胜辽远 ” 的警惕,但是相较于革命文学内部的笔伐论战,鲁迅更为痛斥的则是真实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与利益相对立的国民党统治。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指出 “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之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 ”⑤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二心集》,见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文中揭露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压制,对左翼进步人士的诬蔑、囚禁和杀戮,对左翼文艺的查禁。鲁迅是左翼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尽管他一开始将自己定位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 “ 落伍者 ” ,但是他对 “ 革命文学 ” 的认知并不取旁观者的态度。
梁实秋在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后引起了 “ 革命文学 ” 阶级性争论的又一个小高潮。针对梁实秋的观点,冯乃超率先拾起反驳的利剑,他认为梁实秋是公开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将文学或者说文艺退化到无阶级的谬误中去,进而否定了无产阶级理论与阶级意识的存在合理性。冯乃超将其视为 “ 历史的盲目 ”①冯乃超:《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拓荒者》1930年第2期,第30页。,是对革命文学的反动。冯乃超在无产阶级阶级理论的阐发上显然受到了这一时期党的路线决议的影响,从无产阶级理论的强调延伸到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批判上,阶级观的界限划清固然是无产阶级理论生成与发展的前提,但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 “ 左倾 ” 思想的产生,《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对中国革命的 “ 不间断性 ” 做了重新确定,并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确立为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 “ 左倾 ” 而形成形式化的弊端。而这一 “ 左倾 ” 的路线决议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时得到了系统的纠正。冯乃超将梁实秋划为无产阶级革命向 “ 社会主义革命 ” 跨越时必然要 “ 奥伏赫变 ” 的革命对象,集中凸显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阶级立场。在这之后,鲁迅的《 “ 丧家的 ” “ 资本家的乏走狗 ” 》《 “ 硬译 ” 与 “ 文学的阶级性 ” 》等文章也面世。冯雪峰认为鲁迅 “ 不仅批评了梁实秋的荒谬的理论,并且批判了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文学理论。 ”②冯雪峰:《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1930年,鲁迅在加入 “ 左联 ” 后与冯乃超等人的论争渐趋平息,面对梁实秋的阶级观,鲁迅自觉地站在左翼文化阵线的一端,执起批判的大旗。而这一时期,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强调在左翼文学与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后逐渐内化为知识阶层的革命主体性。
左翼文艺运动初期,无产阶级的理论倡导不仅仅在于阶级意识的论争与理论阐释上,同时也存在于革命知识阶层的宣传与鼓动当中。1928年《文化批判》 “ 新辞源 ” 在译介进西方 “ 宣传propaganda ” 一词时这样阐述, “ 叙与许多非有相当的程度的人,则不能立刻了解的思想的时候,就是‘宣传’,所以宣传多靠著作或杂志等。 ”③“ 新辞源 ” ,《文化批判》1928年第4期,第152页。“ 革命文学 ” 从倡导初期便注重理论化的问题,这和社会革命理论具有着内在一致性。
列宁在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时,特别指出 “ 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 对工农大众的理论引导和宣传作用,在革命斗争中,知识阶层要自觉地 “ 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问题。 ”④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327页。泰东图书局在1927年出版的《革命文学论》在1930年就已经完成了5版的连续再版,由此可见其对 “ 革命文学 ” 理论的宣传作用。除了论著之外, “ 革命文学 ” 大部分的理论阵地则是在于《文化批判》《泰东月刊》《新流月报》《拓荒者》《太阳月刊》等报刊杂志上。报刊杂志的宣传策动效应在左翼文艺运动初期是不可低估的,这一时期应和了 “ 民族主义文学 ” 的《现代文学评论》杂志也不得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已经成为文坛上 “ 最活跃 ” 的潮流了,普罗作家都 “ 走了红运。 ”⑤张季平:《中国普罗文学的总结》,《现代文学评论》1931年第1期,第4-5页。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之间以及对鲁迅、周作人、茅盾等的 “ 革命文学 ” 论争尽管带有宗派主义的弊端,但是正是经过他们的理论的宣传与策动使得无产阶级意识成为了知识阶层的 “ 要获得那种声音 ” 的革命诉求。
1929年,刘剑横在《意识的营垒与革命的智识分子》一文中提出设问, “ 究竟现代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即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无产阶级自身形成的运动呢?还是一部分革命的智识分子的输入品呢? ”⑥刘剑横:《意识的营垒与革命的智识分子》,《泰东月刊》1929年第7期,第38-39页。无产阶级理论在 “ 革命文学 ” 论争中成为了知识阶层较为普遍关注的对象,反思与探询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如何与革命知识阶层发生关联不仅是 “ 革命文学 ” 倡导者所要解答的问题,也是左翼文艺运动兴起,走向20世纪30年代 “ 大众化 ” 问题的讨论与实践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随着左联的成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内化于革命的文艺运动,而从整体的20世纪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来看,从20世纪30年代进入40年代,知识阶层的改造所完成的革命情感与逻辑的合一,在革命史的进程中依然要经受着来自知识人主体实践的考验。
无产阶级意识的论争成为左翼文艺运动初期 “ 革命文学 ” 的切入口,体现了革命的知识阶层对自身主体性话语的关注。经由 “ 革命文学 ” 的论争,左翼文艺运动在理论译介与社会实践中逐渐与苏俄、日本的左翼话语资源发生联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知识人的主体性被激发出来并形构主体自我价值,而 “ 革命情绪 ” 的广泛关注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扩大了影响。随着1930年 “ 左联 ” 的成立,左翼文艺运动在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革命知识人 “ 翻造 ” 与大众化问题凸显出来,如何在知识阶层与民众之间、知识人主体与客体之间寻求突破与发展是左翼文艺必然要面对的现实语境。
二、 “ 民众 ” 的发现与作为革命史考察的 “ 革命情绪 ”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与不断被革命主体化的 “ 民众 ” 及其范畴具有深刻复杂的关联。从 “ 五四 ” 时期的 “ 平民 ” 到 “ 革命文学 ” 中的 “ 民众 ” “ 普罗大众 ” ,再到 “ 左联 ” 成立后的 “ 大众化 ” 运动, “ 民众 ” 这一核心概念的范畴不断发生着文化位移。现代性的启蒙观念所强调的 “ 平民 ” 是现代民族国家的 “ 自由人 ” 复数;而左翼文艺运动由 “ 民众 ” 而 “ 群众 ” 的过程,不仅是政治内涵的强化,也是群体趋向理性人格的编码过程。左翼文艺运动初期,经过了 “ 革命文学 ” “ 普罗文学 ” 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理论倡导,如何从 “ 表同期于无产阶级 ” 到 “ 发出那个阶级的声音 ” 的主体化过程成,为了知识分子不得不去探询的问题。在此背景之下,诸如 “ 平民 ” “ 民间 ” “ 民众 ” “ 大众 ” “ 群众 ” 等概念范畴的名词不断被提及,而 “ 民众 ” 作为一般的中心话语,不但因为其常以官方文件的属性行之于世①20世纪30年代 “ 民众 ” 一词的官方属性,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行政机关设置上:如,国民党中央(各省/市均单独设置下级机构)设置有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民众训练委员会 ” 。机关公文上:如,1930年一则国民党机关文件《决议案: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案》 “ 关于党务者:二、训政时期民众训练方案…… ” 舆论报刊上:冠以 “ 民众 ” 二字的国民党刊物及文章不胜枚举,在此特举一例,1932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红旗周刊》上发表了博古文章《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由此可见,左翼文艺运动初期, “ 民众 ” 已经成为官方话语和社会公共舆论的通用名词。,更是在于这一话语称谓本身所潜在的弥合,因纵向的历史语境差异所造成的话语裂隙的可能性。
“ 民众 ” 的发现在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中并不是新的话题,它更像是因长期客观化的史料实证研究而被遮蔽的一个中心场域。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对 “ 民众 ” 的主体建构实际上被日趋政治化的历史和现实语境所覆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客观化的政治语境中探讨 “ 民众 ” 如何成为革命逻辑生成当中需要大量情感组织工作的对象,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1927年,鲁迅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做演讲时提到平民文学并未真正产生,因为 “ 平民还没开口。 ”②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而已集》,见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页。在国民革命的进程之中,鲁迅是深知动员广大的底层民众投身到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 “ 平民还没开口 ” 的文艺现状与其说是 “ 革命文学 ” 前夜的社会背景,不如说是对国民大革命前途性的一种担忧。而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初期正是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下的思想理论引入,寻找并确立广大民众与知识阶层作为革命 “ 同路人 ” 的 “ 意德沃罗基 ” 。沈泽民1924年便阐述了革命文艺与民众的关系, “ 一个革命的文学者,实是民众情绪生活的组织者。 ”③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1月6日第2版。郭沫若则进一步对革命的知识分子提出参与到民众当中进行锻炼的期望 “ (革命文学家)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 ” , “ 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 ”④郭沫若:《文艺家的觉悟》,《洪水》1926年第16期,第136页。而到了1928年 “ 革命文学 ” 的论争渐趋火热时,如何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与民众动员进行对接成为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问题。沈起予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该与大众情感相联系,并要 “ 能结合大众的感情与思想及意志而加以抬高。 ”⑤沈起予:《艺术运动底根本概念》,《创造月刊》1928年第3期,第7页。实际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回应了鲁迅 “ 平民还没开口 ” 的命题,以及这一命题在进入1928年 “ 革命文学 ” 普遍化的理论语境之中如何释惑的问题。
“ 民众 ” 作为左翼文艺运动初期革命话语的一种发现,既和它自身的社会广泛性分不开,同时也与内化于 “ 民众 ” 之中的深层的情感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常流露出人道主义的关怀,他一方面痛斥资本对人的异化;另一方面又对广大工人阶层投以深切的同情。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 国民经济学提出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国民经济学不考虑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和无产阶级革命初期朴素的民众观具有内在天然的联系。黄药眠在《文艺家应该为谁而战》一文中就对革命文艺家在情感上应该倾向于底层民众的革命理论立场做了具有人道主义的描述, “ 在这一方面是一些终日在工厂里匍匐蠕动、汗流浃背、面目熏黑的工人,一些衣衫褴褛、胼手胝足、终日牛马般在田里工作的农人,和一些僵卧在贫民窟里的草荐上,以拾着残羹冷饭为生的穷汉……假如他(文艺家)都真的还有人的心肠,那么我们就唯有请他到这边来,同工人农人的利害结在一起! ”②黄药眠:《文艺家应该为谁而战》,《流沙》1928年第5期,第24-25页。在普遍的普无产阶级意识的呼求中,黄药眠的这段表述使得普罗大众从 “ 民众 ” 这一结构化的革命策略表述中重新回归到情感动员对象化的路径上,革命理性因 “ 无产阶级的血与泪 ”③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三闲集》,见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的实在而具有了作为革命情感史考察的可能性。
那么, “ 革命情绪 ” 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初期是如何成为革命的内在动力?并如何将 “ 民众 ” 纳入到情感对象化的范畴呢?
裴宜理在讨论20世纪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出 “ 情感工作 ” 这一概念④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观察与交流》2010年第60期,第31页。,他认为恰恰是中共所从事的大量民众动员的情感工作将民主革命的抽象理念落到了实际,广大民众正是从情感工作的受众转而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情感工作的实际内涵。如果说 “ 情感工作 ” 更接近于组织化的政治实践,它的实践基础依靠有力的领导核心和较为成体系的职权机构,那么裴宜理进一步阐发的 “ 情感提升 ” 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初期 “ 革命情绪 ” 的情感实践可能更具有阐释性。
革命的初期,知识阶层逐渐转变为革命者,革命的知识人与民众间逐渐从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转向突破阶层的富有政治激情的互动关系,而 “ 情感提升 ” 往往因革命的目的性、实践性的合一而具有内在的推动力。在 “ 革命文学 ” 倡导时期,冯乃超《人类的与阶级的》一文中把无产阶级文艺的情感组织功能抽象化,认为 “ 经过阶级艺术的过程 ” 是可以达到 “ 没有阶级分裂 ” 的 “ 美好时刻 ” ,进而实现 “ 人类整个‘意识联合起来’ ” ,但是在无产阶级文艺初期, “ 阶级艺术的过程 ” 是必然的一个前提⑤冯乃超:《人类的与阶级的——给向培良先生的〈人类底艺术〉的意见》,《萌芽月刊》1930年第2期,第33-34页。。而蒋光慈则注重从苏俄无产阶级文学批评家波格丹诺夫、波连斯基那里汲取无产阶级文化的理念,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必然地要表现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革命实际以及在革命进程中的情感、观念和意志,革命文学作家应该将自己独特的见解融入到革命争取胜利的斗争当中。这种从 “ 革命火焰 ” 之中突出民众 “ 热情、欲望斗争、危害、愤激、爱情 ”⑥蒋光慈:《无产阶级诗人》,见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4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124页。的左翼文艺,则把抽象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理论注入了 “ 革命情绪 ” 的内涵之中,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推动着民众意志的自觉联合。
1928年,《泰东月刊》上署名香谷的《革命的文学家到民间去》一文就曾指出 “ 革命文学 ” 过于理论化,而革命情绪受到忽略的弊端, “ 现在多少青年到革命文学家,有这么一种现象:他们的思想是很彻底的,他们革命的观点是很正确的,但是不幸所谓革命的情绪,总是一贯的虚飘飘空浮在意识上,很少有突起高涨的可能;所以他很难得有一个机会,从情感方面,建筑起一个完美作品的基础。 ”⑦香谷:《革命的文学家到民间去》,《泰东月刊》1928年第5期,第6页。茅盾在1932年《〈地泉〉读后感》中也清晰地论述诉诸艺术形式的 “ 革命情绪 ” 的重要性,茅盾从辛克莱的 “ 一切文艺都是宣传 ” 中提出文艺作品要 “ 异于标语传单 ” ,所以要运用和开掘艺术的情感表达方式,以文学作品的形象性、感染力去影响读者群体。刘剑横更是立场鲜明地阐述了 “ 革命情绪 ” 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必然性, “ 现代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尚是一种革命生活的表现的文学,而不是一种艺术生活的享受的文学。……它的特点是革命的情绪的扩张和掲露,是革命的意识的宣传煽动,无产阶级的意识的扩张和发挥,而且满含着敌对和煽动的批判性质的文学。 ”⑧刘剑横:《意识的营垒与革命的智识分子》,《泰东月刊》1929年第7期,第39页。刘剑横的论述虽然带有较强烈的 “ 意识营垒 ” 的论战意味,但是所折射出来的 “ 革命情绪 ” 必要性观念是左翼文艺运动初期难以被忽视或遮蔽的内在要素。
“ 革命情绪 ” 成为左翼文艺运动初期论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它对现实主义时代性的强调分不开。香谷和茅盾的 “ 革命情绪 ” 凸显论正是建立在对客观的社会现实充分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前者将 “ 脱离现实 ” 视作革命文学无法突起 “ 革命情绪 ” ,进而不能 “ 构筑起一个完美作品 ” 的主要原因。在香谷那里, “ 革命情绪 ” 的突起应该和现实的、民众的切实利害发生着关联, “ 我们现在应当喊一声口号‘革命的文学家,到民间去!’……不要将自己和普通社会隔得太远了,不要飘飘然逍遥于革命文学的天国,享着特殊的阶级利益,应当到民间去,从事种种活动,这样才可以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文学家。 ”①香谷:《革命的文学家到民间去》,《泰东月刊》1928年第5期,第7页。而茅盾,则更是秉持并发展着现实主义时代性的文学观,他认为普罗文学的问题就在于 “ 缺乏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 ”②茅盾:《〈地泉〉读后感》,见茅盾:《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333页。茅盾对 “ 革命文学 ” 的评价不仅仅停留在对文艺作品如何区别于标语口号而凸显时代的 “ 革命情绪 ” ,而更是把 “ 革命情绪 ” 突起的根本导向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这也再次印证了 “ 革命情绪 ” 在左翼文艺运动中不应是空泛的情感化,而是深刻纠缠于现实社会之中,并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革命实践。
同时, “ 革命情绪 ” 具有革命前途性的内在要求,这是由革命逻辑内部规约性所决定的。革命的出路是左翼文艺运动初期谈论得较为普遍的前途性问题,能否将这一革命远景注入 “ 革命情绪 ” 当中成为论争的重要方面。1928年,芳孤在文章中就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首要职责就是要给人们暗示一条革命的出路,而革命的出路正是内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当中,具备了阶级意识的知识阶层应该自觉地以追寻和表现革命的出路为己任。 “ 这‘暗示的出路’便是革命文学的活力,没有这个活力,便不成其为革命文学。 ”③芳孤:《革命文学与自然主义》,《泰东月刊》1928年第10B期,第14页。实际上,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初期,以 “ 左联 ” 的成立为分界,革命出路问题的指向其实也是不尽相同,它和现实的政治语境变化有关。国民革命失败后,革命知识阶层普遍对看不到出路的现实境况感到苦闷彷徨,诸如这一时期茅盾创作的《幻灭》、阳翰笙的《转换》等。阳翰笙就曾在《〈地泉〉重版自序》中倾吐其写实主义的来由,正是对大革命失败的现实语境与革命知识阶层的苦闷心境的镜像式反映,那种彷徨无边的处境就是 “ 四处找出路而又摸不着出路 ”④阳翰笙:《〈地泉〉重版自序》,见阳翰笙:《地泉》,上海:上海湖风出版社1932年版,第72-74页。的折射。而 “ 革命文学 ” 论争兴起之后,这种没有出路的革命者心态又成为无产阶级文学所批驳的对象。钱杏邨就曾批评茅盾的《蚀》 “ 到处表现了病态 ” , “ 创作的立场是错误的 ”⑤钱杏邨:《〈追求〉:一封信》,《泰东月刊》1928年第4期,第106页。,并指出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摒弃病态的颓废的立场,走向宣传、鼓动的革命奋进之途。1928年,革命出路的问题在成仿吾、钱杏邨与鲁迅、茅盾等的论争之中成为判断 “ 落伍与否 ” 的一个标志。而在 “ 左联 ” 成立后,对革命前途性的强调很快则变成了培育和凸显 “ 革命情绪 ” 的重要面向。
因而可以说,中国左翼文艺初期的 “ 革命情绪 ” ,以现实主义时代性和革命前途性为内在规约,将革命的主体实践由知识分子理论化的强调导向了不断情感对象化的民众,民众被逐渐体系化的 “ 情感工作 ” 组织起来,革命知识人正是在 “ 革命情绪 ” 的倡导中获得主体性,并反过来推动着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向前发展。
三、文艺大众化与革命知识人的主体实践
20世纪30年代作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不断趋向成熟的关键,多元与一体、边缘与中心的张力推动着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如果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 “ 延安文艺 ” 乃至 “ 十七年文学 ” 制定了工农兵文学这一唯一合法的方向,那么左翼文艺运动初期的无产阶级理论强调与文艺大众化、组织化的实践则具有工农兵文学 “ 前史 ” 的考察意义。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作为革命史整体的时空序列,而在于如何理解无产阶级文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对革命与启蒙话语的整合,又是如何走向理论与情感的革命实践;在此基础上知识阶层又是如何践行自我 “ 翻造 ” 并形塑着革命者人格。忽略了这些不同层面的发展演进脉络,将很难把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置放于整体的20世纪观照之中,也将难以理解 “ 总体性 ” 的革命史。
革命与文艺的关系一直是左翼文艺运动的核心论题,对这一论题的阐发在 “ 左联 ” 成立后逐渐转向文艺如何经 “ 革命情绪 ” 组织民众,并进而推进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布哈林的 “ 艺术组织论 ” 对冯乃超、钱杏邨等的革命文学理论都有影响,冯乃超曾指出 “ 艺术是感情社会化的手段,组织感情的方法,某一阶级用它来维持其统治,而某一阶级则用它来求解放。 ”①冯乃超:《人类的与阶级的——给向培良先生的〈人类底艺术〉的意见》,《萌芽月刊》1930年第2期,第35-36页。1932年 “ 左联 ” 的机关刊物《北斗》在关于 “ 文学大众化问题征文 ” 中约请了左翼作家陈望道、杜衡、张天翼、叶沉、沈起予等人就革命文学能否大众化、如何大众化展开讨论。陈望道认为革命文艺能够很好地起到 “ 组织群众的机能 ” ,调动民众的情绪,组织起革命力量,应该成为文艺大众化的目标。叶沉也同样提出 “ 只有大众能了解的文学,只有能组织大众意志和情感的文学才是有艺术价值的文学。 ”②《文学大众化问题征文》,《北斗》1932年第3-4期,第86-90页。沈起予则从革命文学表达的角度提出文艺表达与群众接受的问题,注重革命文学与民众知识水平的契合,而这也成为1935年前后 “ 大众语文学 ” 讨论的一个前兆。
“ 革命情绪 ” 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已经变成了具有实际性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功能的革命实践,已然从 “ 革命文学 ” 论争时期的理论和情感的准备进入了无产阶级文艺中国化的探索之路。这条探索之路贯穿着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并深刻影响着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的革命文艺。1943年艾青在《抗战文艺》表达了对革命文艺的本质认识, “ 作家的工作就是把自己的或他所选择的人物的感觉、情感、思想,凝结成形象的语言,通过这语言,去团结和组织他的民族或阶层的全体。 ”③艾青:《断想》,《抗战文艺》1943年第8卷第4期,第20页。在艾青这里,革命文艺真正成为了作家创作的自然追求,而 “ 革命情绪 ” 也获得了艺术的形象和语言的载体,内化为革命知识人性格和情感的特质。 “ 在他(作家)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于他的情感,因为不这样,他的作品就成了虚伪的,没有生命的。 ”④艾青:《断想》,《抗战文艺》1943年第8卷第4期,第20页。可以看到,革命文艺的大众化、组织化在 “ 延安文艺 ” 中成为了自觉的要求,实际上革命作家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理论和情感的基本素养才能创作出真实的、有生命的作品。
那么,左翼文艺运动初期,在无产阶级意识和 “ 革命情绪 ” 的辩证关系中,革命知识人又是如何从理性的 “ 经济人假设 ”⑤理性人假设,又称经济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西方经济学者指出,所谓 “ 经济人 ” 假设,也称为 “ 合乎理性人 ” 假设,是对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抽象。20世纪50年代, “ 理性人 ” 假设发展到了极至,获得了纯粹工具主义的属性,彻底放弃了任何道德伦理观。转变为兼具革命理性和情感实践的革命知识人主体呢?这一具有主体性的自我 “ 翻造 ” 是否因为 “ 革命情绪 ” 而具备革命者人格形塑的可能性?从 “ 总体性 ” 革命史视角来看,这些问题是值得进行考察的。
“ 革命文学 ” 论争之后,左翼文化阵营中逐渐形成自我批判的倾向和氛围,这对革命知识人的思想和情感也产生了影响。1930年2月16日,包括鲁迅、冯雪峰、郑伯奇等12位在内的左联筹备委员在公啡咖啡馆召开了 “ 上海新文学运动者的讨论会 ” ,和这一时期诸多秘密集会相似,左联的筹备因为有了来自党的指示,加上 “ 革命文学 ” 论争之后国民党舆论管控加强的政治语境,革命文学作家变得空前团结,渴望成立具有行动一致性与组织性的文化团体。而这次会议其实也是左联成立前具有代表性的筹备会议。在左联成立过程中,清算和批评过去革命文学阵营当中的小集团主义、个人主义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或者说任务,尽管筹备委员会中聚集了诸如蒋光慈等曾大力倡导 “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 ,将批判矛头指向鲁迅的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但是,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为促成 “ 新的思想的宣传与新社会的生产 ” ,革命知识阶层必然地要面对新的自我批判与 “ 奥伏赫变 ”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初期之所以能够克服 “ 革命文学 ” 论争时期左倾、小团体主义的弊端,不断推进革命文艺组织活动的深入发展,和左联成立之初即确立起来的自我批判的意识和经验分不开。1930年,潘汉年《左联的意义及其任务》一文在总结左联成立的意义时也单独列出 “ 自我批判的必要 ” 一条,左联的成立是对此前革命知识阶层缺少自我内部批评的组织保障,通过左联的章程与广大盟员的监督,践行自我批评,保持左翼文艺运动的引领作用。在今天看来,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变得日常化,而这也是中共领导的革命与建设留给当下活的思想遗产,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有无认真地批评和自我批评, “ 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这一思想作风的经典化也和革命知识人的情感实践始终关联,1941年,初到延安的萧军曾表达对延安现状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即在给萧军的回复信中以萧军为典型,指出初到延安的左翼作家放弃自我改造的必要性,未能充分认识革命实践的艰苦性与长期性,所以应该要有意识地 “ 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 ”②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毛泽东对革命知识分子进行自我审视与批评是报以期望的,而实际上在 “ 延安文艺 ” 之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就尤为注重自我批判对革命战线的巩固作用,注重自我批判对革命知识人进行思想和情感 “ 翻造 ” 的引导价值。
在左翼文艺运动中,自我批判对革命知识人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思想的 “ 改造 ” ,更是在革命伦理层面上的自我情感的重塑,而这种情感实践是和不断丰富和组织化的 “ 革命情绪 ” 相关联的。1930年5月,田汉发表《我们的自我批判》这一篇长文,文中以 “ 左联 ” 成立为观照,系统回顾和反思了自己主持《南国》杂志时期的思想和文艺实践历程,在自我批判中,田汉对戏剧的社会宣传功能进行了重新审视与定位。革命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已经唤起了民众革命的斗志,民众已然从 “ 五四 ” 时期 “ 文明剧 ” 的观众转变为带有革命意识的观众,他们渴望剧作与演出能够呈现革命时代下的风云突变、反映正在发生的革命实际,因而那种呈现热情与浪漫的都市剧作将要 “ 走向没落之路 ” 。田汉因而发出 “ ‘离开了平民,就失去了平民’,我们应该三复斯言! ”③田汉:《田汉文集》第14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的自我批判之声。文艺大众化以及文艺对 “ 革命情绪 ” 的组织化在 “ 左联 ” 成立后不断深入,田汉正是以对过去阶级意识和情感经验 “ 翻造 ” 的自我批判、清算的态度,走向了以大众戏剧为中心的 “ 革命情绪 ” 组织化之路。田汉在自我清算中将过去的个人主义的戏剧观视为 “ 走向没落之路 ” ,而面向民众的大众戏剧则具有革命的现实性、迫切性和前途性,这一认知过程的转变恰恰是和 “ 革命情绪 ” 对现实主义时代性和革命前途性的内在规约相一致,而左翼文艺运动时期革命知识人的思想 “ 翻造 ”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了值得阐释的革命情感史价值。
蒋光慈在《冲出云围的月亮》中塑造了没落而得以翻造的王曼英这一人物形象,王曼英从 “ 堕入毁灭的深渊到冲出乌云包围 ” 的过程,再现的就是革命者知识人进行自我身心 “ 翻造 ” 的思想和情感实践。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李尚志对王曼英做革命的鼓动,鼓励她从既往的生活中走出来,参加到群众运动当中,从群众生活的体验中重新认识和塑造自己的人格;并将只有革命的阶级才能走向生路的革命情绪作为信条传达给王曼英。
可以说,李尚志作为革命情绪的宣传者,给予了具备知识阶层改造可能性的王曼英以革命的理念与情感动员。这是左翼文艺运动中即将告别了国民革命后期迷惘心理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情感的准备,他们所面对的是普罗列塔利亚阶级意识以及 “ 和群众接近 ” 并坚信这是一条生路的革命情绪。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王曼英作为革命知识人具有主体性的自我身心 “ 翻造 ” 的发生: “ 一切都充满着活泼的生意,仿佛这世界并不是什么黑暗的地狱,而是光明的领地。一切都具着活生生的希望,一切都向着生的道路走去。你看这初升的朝阳…… ”④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见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2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在王曼英这里,身心的双重转变既是革命理念与情感的获得,也是精神爱情对全新人格的重塑。在蒋光慈笔下,她因为参与到群众生活与工人运动中而感受到革命情绪的喷张,同时摒弃了奢靡腐化的生活,成为一个新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化身,这当中既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锻造,也是以理想型革命者人格作为个人主体改造的能动性发生。可以看到的是,革命知识人的自我 “ 翻造 ” 已经从无产阶级理论层面进入了革命运动的实践之中,这一进路中,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自我内心的批判,并尝试改造成革命思想意识和情感伦理高度自觉的革命自由人。在知识人具有主体性的 “ 翻造 ” 过程中, “ 革命情绪 ” 以其对现实时代性和革命前途性的内在规约成为了革命实践活动中有机的情感机制,民众与革命知识人的双向互动,既是革命的要求,也是革命实践对革命者人格的锻造过程。
四、左翼文艺运动与革命者人格
李大钊曾把列宁和孙中山的革命者精神并举,指出革命者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孙中山先生四十年革命生涯永不言弃,经历革命低谷也从不灰心,常为革命党人坚持革命斗争直至胜利鼓与呼;而列宁也是具备了坚韧的革命精神才能领导布尔什维克走向胜利。 “ 列宁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们应该服膺这种精神! ”①李大钊:《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见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1页。在李大钊看来,列宁和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正是革命者人格的彰显。革命者人格是革命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动能,它既有着不断革命直至胜利的信念要求,敢于面对失败的人格力量,也有着不断对革命阵营进行情感提升的领导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者人格对革命前途性的强调和 “ 革命情绪 ” 是内在一体的,实际上,革命者人格正是在不断获取更新的 “ 革命情绪 ” 语境之中实现其前瞻性、现实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汪晖则把革命者人格放在整体的革命史进程中来看待,认为革命者人格之所以具有历史能动性就在于其克服了现实的客观困难,对革命前途性示以强大的感召与远景②汪晖:《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第129页。。
革命者人格是一个历时性的命题,也是一个复杂性的难题。作为一个历时性命题,革命者人格与整体的20世纪革命史深度融汇,并越来越成为理解和重新审视20世纪革命实践的重要视角。但是,革命者人格又是一个复杂性的难题。如何界定和区隔革命历程当中的阶段革命性?革命者人格是否具有绵延的历史持续性?在复杂变动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革命者人格能否成为革命理性和情感伦理的合理参照?这些问题都很难一概而论。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初期,革命知识人将革命者人格的形塑视为自我 “ 翻造 ” 的目标。这一革命经验的发生,与作为革命历史有机组成的革命情感实践密不可分,正是在无产阶级理论倡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发生之初,以 “ 革命情绪 ” 为中心的革命知识人情感论争与实践丰富了革命话语,避免了革命组织理论在走向民众时的抽象、枯燥和失效,成为左翼文艺运动初期重要的革命经验。尽管它并不具备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的强大文化整合能力,也与1943年在解放区大规模开展的 “ 文艺下乡运动 ”③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3月28日第3版。不同,但是它所呈现的知识阶层自我改造的可能性,从无产阶级理论进入到革命主体实践,都为此后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命题提供了可以上溯的阐释资源。
同时也应该看到,左翼文艺运动初期革命知识人对革命者人格的理想型塑造也并不是全然成功。诸如蒋光慈只注重从苏联的 “ 情绪说 ” 出发,一味强调革命情绪的注入,忽视了革命现实与民众动员的实际的复杂性,将知识阶层的自我 “ 翻造 ” 仅仅理解为某种观念的简单摄取,放弃与工人运动、实际的革命斗争的深切互动,从而停留在 “ 只是针对劳动者的情绪表现 ”④李金花:《钱杏邨文学批评的 “ 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2期,第187页。的层面。从而忽视了左翼文艺运动从理论到 “ 革命情绪 ” 实践的转换过程,取消了革命知识人自我 “ 翻造 ” 的现实复杂性与多重可能性,削弱了革命者人格的丰富性。而丁玲写于1930年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则提供了一个趋向现实复杂化的革命者人格形塑的例子。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青年若泉,希望通过好友超生了解到革命现实,但是,这位怀揣革命理论的知识青年却又对革命现实表现出迟疑和不成熟性:
“ 若泉对于这方面极感兴趣,常常希望能从这知识阶级运动跳到工人运动的区域里去,……超生告诉他,他们报纸上有一栏俱乐部,很需要一点文艺的东西,希望若泉去邀几个同志,不过他又表示担忧,说若泉他们艺术不行,工人们看不懂。他要若泉最好写得浅一点,短一点。他还发表了一点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当然他是站在工人立场上的。 ”⑤张炯编:《丁玲全集》第3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
面对革命浪潮的迟疑和不成熟,正是左翼文艺运动初期革命知识人的现实心境,丁玲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革命知识人的自我 “ 翻造 ” 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体现出复杂性和深刻性。文艺大众化是 “ 革命情绪 ” 由论争回落到民众这一革命实践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它所面对的难题既有民众情绪组织的现实困难,也有革命知识人自我思想和情感改造的艰难,二者缺一不可,统一于左翼文艺运动的革命实践之中。革命者人格是一个不尽的历时性话题,它所折射出的现实革命的复杂性与革命知识人的主体实践等诸多问题仍然有较大的阐释空间,并对20世纪 “ 总体性 ” 革命史观照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