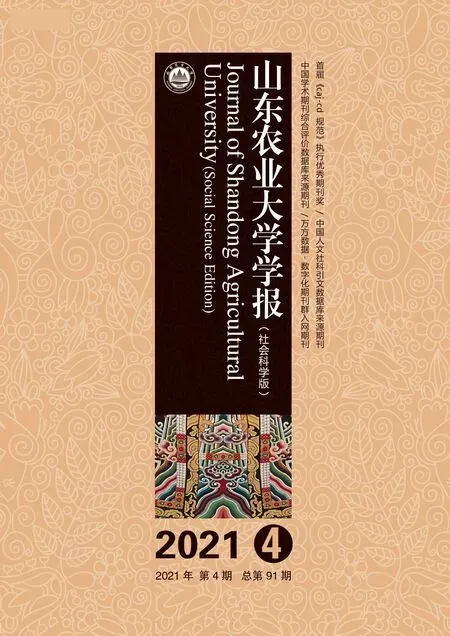东汉龙亢桓氏的家族特征与文学写作
2021-11-30柯镇昌
□柯镇昌
[内容提要]汉魏以来,随着世家大族的大量形成,文化家族也随之出现,龙亢桓氏不仅是汉晋时期重要的世家大族,也是当时重要的文化大族。东汉龙亢桓氏以治儒学起家,但他们在政治上主要是承担润色鸿业的点缀角色。桓氏成员专治儒经的家学和笃行儒教的家风有力地推动了家族的振兴,另一方面又对其家族成员的政治地位起到过一定的限制作用。东汉龙亢桓氏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收获,尤其桓麟、桓彬、桓晔等人作品在当时和后世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不过东汉龙亢桓氏既没有出现文学大家,也没有经典名篇,这又与其世代治儒的家学家风密不可分。
汉魏以来,随着世家大族的大量形成,文化家族也随之出现,龙亢桓氏就是其中重要者之一。《后汉书·桓荣传》称桓荣“沛郡龙亢人也”。[1](P1249)《汉书·地理志上》载沛郡有县三十七,其二为龙亢。[2](P1572)龙亢本为汉县名,位置在今安徽省怀远县龙亢集。据唐林宝《元和姓纂》:“桓,姜姓,齐桓公之后,以谥为姓。”[3](P509)汉刘珍《东观汉记》曰:“荣本齐桓公后。”[4](P619)可知龙亢桓氏的始祖实出姜姓。东汉以前,龙亢桓氏鲜有记载,但从东汉桓荣以后,迅速成为世人瞩目的文化强族。本文试对其家族特征及文学成就作一简要探究。
一、家族特征:儒学起家和政治点缀角色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龙亢桓氏的主要家族成员有五代。《后汉书·桓荣列传》注引《续后汉书》曰:“荣本齐人,迁于龙亢,至荣六叶。”[1](P1249)桓氏由齐地迁往沛郡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按桓荣生活于两汉之际,上推五代,应属汉景帝在位期间或前后不久,但此后数代皆湮灭无考,桓荣是龙亢桓氏有名可考第一人。桓荣字春卿,生于西汉末期,自少于长安随朱普学习《欧阳尚书》。王莽篡逆时,逃匿山林,后复授学于江淮。光武帝建武十九年(43年),桓荣经学生何汤举荐,拜为博士。二十八年(52年)为太子少傅,三十年(54年)为太常。明帝永平二年(59年)拜五更,封关内侯。卒于明帝永平三年(60年)后不久。
第二代人物有桓雍和桓郁。桓雍事迹不详。桓郁(?—93)字仲恩,父卒袭爵,永平十四年(71年)迁侍中、监虎贲中郎将,再迁越骑校尉、屯骑校尉,转侍中奉车都尉。永元四年(92年)任太常,次年病卒。
第三代人物有桓普、桓延、桓鄷、桓焉、桓俊、桓良、桓汎,其中普、延、鄷、俊、汎生平事迹皆无载。桓焉(?—143)字叔元,生年不详。桓焉少以父任为郎,明经笃行,有名称,永初元年入授安帝,后历任侍中步兵校尉、太子少傅、太子太傅、光禄大夫、太常。顺帝即位,拜太傅,录尚书事,入授禁中,封阳平侯,固让不受。又历光禄大夫、大鸿胪,迁太常、太尉,汉顺帝汉安二年卒。桓良,《后汉书》引《东观记》曰“(鸾)父良,龙舒相”,[1](P1259)具体生平事迹不详。
第四代人物有桓衡、桓顺、桓麟、桓鸾,其中衡、顺生平事迹均不详。桓麟(110—150)字元凤,少有才惠,桓帝初为议郎,侍讲禁中,以直道牾左右而出为许令,又因病免。会母病终,麟不胜丧而卒,时年四十一岁。桓鸾(108—184)字始春,少立操行,以世乱而不肯仕,四十余后经太守向苗举为孝廉,迁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即去职奔丧,终三年然后归,淮汝之间高其义”[1](P1259)。后为巳吾、汲二县令,甚有名迹;诸公并荐,复征拜议郎,以病免,中平元年(184年)卒。
第五代人物有桓典、桓晔、桓彬。桓典(?—200)字公雅,少有操行,在颖川教授《尚书》,后举孝廉而为郎,辟司徒袁隗之府,举高第,拜侍御史,为政严明,京师畏惮;后督军破黄巾军,“以牾宦官赏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调”;[1](P1258)后出为郎。灵帝崩,参与大将军何进谋议,三迁羽林中郎将;献帝时拜御史中丞,赐爵关内侯,迁光禄勋,建安六年(200年)卒官。桓晔(又名严)字文林,生卒年不详,曾为郡功曹,举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辟之,皆不受;初平中避乱会稽,为人诬陷,死于合浦狱中。桓彬(133—178)字彦林,少与蔡邕齐名,举孝廉,拜尚书郎,坐刘猛事而忤中常侍曹节,废官。卒后蔡邕等树碑以颂。
东汉时世族发展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凭藉经济上的优势,如《后汉书·黄琬传》载:“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1](P2040)二是外戚、功勋之后凭借政治上的权势,如《后汉书·邓禹传》载:“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1](P619)三是凭依学术上的成就,“因为术业世传,弟子蝟集,遂亦形成一大势力,而变为世族。”[5](P22)龙亢桓氏正是通过经营儒学,逐渐发展成为所谓的“儒学的强宗豪族。”[6](P110)
西汉时地方豪族与学术人家往往不相交叠。东汉伊始,豪强之家与政界显族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士大夫化发展,逐渐注重对家族子弟进行文化学术上的培养。如《后汉书·儒林传序》载本初四年(149年),梁太后下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1](P2547)也就是说,世家大族大多是先由经济或政治上有所发展,然后才于学术上逐渐有所浸淫的。龙亢桓氏则与之不同,这个家族是先在儒学上获得造诣,然后取得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最后在经济方面获得发展。经济条件的改善也是其强宗豪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桓荣本出身低微,“贫窭无资,常客佣以自给”,“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1](P1249)。然自得帝王赏识后,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建武十九年(43年)赐钱十万,不久又特加赏赐。荣病时,太子赐以珍羞、帷帐、奴婢。建武二十八年拜少傅,再赐以辎车、乘马。族人桓元卿叹曰:“岂意学之为利若是哉!”[1](P1252)足见其家此时之富足。明帝即位后,“(荣)数上书乞身,辄加赏赐”[1](P1252),“悉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封关内侯,食邑五千户”[1](P1253)。临终之时,赏赐愈甚。至桓郁时,“恩宠甚笃,赏赐前后数百千万。”[1](P1256)桓焉官居高位,亦曾受赐牛酒。由上可知,龙亢桓氏的经济条件于东汉之初即已相当优越。当然,人丁的增长也是其家族日益兴隆的条件之一。两汉时期与龙亢桓氏一样纯以学术起家的世族实属不多。
桓氏成员虽历任显宦,担任的多是些闲散虚职,极少执掌具有真正实权的官位。汪文学《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指出:“汉朝官僚机构里的成员约可分为儒生和文吏两大群体。儒生、文吏各有所长,儒生是‘知识文化角色’,文吏是‘行政文官角色’;儒生之功在‘轨德立化’,强调推行教化;文吏之功在于‘优理事乱’,强调奉行律令。”[7](P95-96)两汉真正推行的是王、霸政策,儒学高度官方化,并向神学化、经学化发展。封建帝王崇儒,既是治理国家的需要,也是润饰鸿业的需要。在提拔官员时,往往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1](P261)桓氏在汉廷中大多以纯粹儒生身份出现,所任太常、五更、太傅等皆为虚位,如桓荣曾拜五更,而《礼记·文王世子》云:“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郑玄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8](P1410)桓焉曾任太傅,“太傅,上公一人。本注曰:掌以善导,无常职。”[9](P266)桓荣、桓郁、桓焉三代任太常,“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礼仪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常赞天子。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大射、养老、大丧,皆奏其礼仪。每月前晦,察行陵庙。”[9](P274)桓氏最显赫的数位人物,除桓焉曾作过两年太尉,其它所任职务多为虚职。何焯《义门读书记》认为:“侍中窦宪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颇涉经学,上疏皇太后。宪善知郁不为己患,故荐之授经禁中,非德举也。”[10](P376)可谓一语中的。在汉代最高统治者眼中,儒者也有两种,一类是纯儒,只是理论工作的执行者,桓氏属之;一类杂儒,注重实践,杨震等属之。纯儒可敬,却未必能堪大用。在整个东汉王朝,龙亢桓氏几乎都没有进入过国家的政治权利中心,他们所承担的,基本都是在文化上为国家润饰鸿业的政治角色。
二、家学家风:专治儒学和笃信儒教
东汉龙亢桓氏的家学以专治儒经为特色。汉代是经学大盛的时期,通谙经术对于家族的形成与发展意义深远,是以钱穆认为:“自东汉以来,因有累世之经学,而有累世之公卿,于是而有门第之产生。”[11](P164)龙亢桓氏自桓荣开始世代以治经为业:桓荣深谙儒学,“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后以《尚书》授太子,每能辨明经义。桓郁“敦厚笃学,传父业”,其教授《尚书》,门徒常数百,后来也“居中论经书”,[1](P1254)授皇太子刘炟(即汉章帝)经。汉明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曾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桓郁后将其父《章句》精减为十二万言,与父书合称《桓君大小太常章句》,足见他的经学功底。建初三年(78年),“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定五经异同于北宫白虎观。”[1](P1264)和帝即位,复入侍讲,华峤《汉后书》称“议者皆以郁身为名儒,学者之宗”。[12](P545)桓焉也能传承家学,明经笃行,永初元年(107年)入授安帝,弟子“传业者数百人”。[1](P1257)桓鸾综贯《六经》,桓麟也曾入侍讲禁中。桓典亦“以《尚书》教授颖川,门徒数百人。”[1](P1258)桓氏所传家学主要是今文《尚书》。据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考察,原秦博士伏生(胜)传《尚书》与欧阳生,再传至倪宽,至欧阳生子,至欧阳高,至林尊,至平当,至朱普,朱普传桓荣。桓荣弟子有桓郁、丁鸿、鲍骏三家,其中桓郁传桓焉,桓焉分传桓典、黄琼与杨赐。[13](P48)桓氏一门中产生如此多儒学大师,即使在经学发达的东汉也是罕见的。
龙亢桓氏不仅世代传授儒学,同时也能秉承儒家之精神,逐渐形成笃行儒教的家风。这里所说的“儒教”并不涉及其宗教意义,而是对儒行的一种代称。儒学属于学术范畴,儒教则指在思想与行为上遵循儒家学说之精神与提倡,属于思想道德或行为作风之范畴。桓氏笃行的儒教包含以下几点:
首先,安贫守道,轻财重节,家困而晏如。桓荣贫窭无资时,依然在治学上“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1](P1249)《桓典传》注引《华峤书》:“(典)立廉操,不取于人,门生故吏问遗,一无所受”。[1](P1258)桓鸾“少立操行,褞袍糟食,不求盈余”,[1](P1259)本传注引《东观记》称其“推财孤寡,分贿友朋”。[1](P1259)《东观汉记》又载:“礹(即桓晔)到吴郡,扬州刺史刘繇振给谷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4](P629)又《后汉书·列女传》载:
沛刘长卿妻者,同郡桓鸾之女也。鸾已见前传。生一男五岁而长卿卒,妻防远嫌疑,不肯归宁。儿年十五,晚又夭殁。妻虑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妇相与愍之,共谓曰:“若家殊无它意;假令有之,犹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诚,何贵义轻身之甚哉!”对曰:“昔我先君五更,学为儒宗,尊为帝师。五更已来,历代不替,男以忠孝显,女以贞顺称。《诗》云:‘无忝尔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显其门闾,号曰“行义桓釐”,县邑有祀必膰焉。[1](P2797)
桓鸾之女秉承桓氏“男以忠孝显,女以贞顺称”的家教,坚贞高义,充分展示了桓氏子女深受家风熏陶而崇礼重节的美好品质。
其次,尊师礼,重恩情。桓荣在恩师朱普去世时奔丧九江,负土成坟,切实履行弟子的尊师之情。《桓典传》载:“会国相王吉以罪被诛,故人亲戚莫敢至者。典独弃官收敛归葬,服丧三年,负土成坟,为立祠堂,尽礼而去。”[1](P1258)桓鸾经太守向苗推荐,举孝廉,迁为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即去职奔丧,终三年然后归,淮汝之间高其义”,[1](P1259)都是桓氏子弟重恩情、重信义的表现。
再次,忠君事朝,不计私利。“两汉士人,是在儒家正统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君臣之义是他们立身的基本准则。”[14](P10)桓荣不事伪莽新朝,莽篡时便归故里。永平十五年,明帝诏敕太子、诸王各奉贺致礼,“郁数进忠言,多见纳录”。[1](P1254)桓焉为太常,“时废皇太子为济阴王,焉与太仆来历、廷尉张晧谏,不能得,”“顺帝即位……以焉前廷议守正,封阳平侯,固让不受。”[1](P1257)桓典亦“执政无所回避”。[1](P1258)
复次,行事以礼,谦虚谨让。桓荣本传载:“会欧阳博士缺,帝欲用荣。荣叩头让曰:‘臣经术浅薄,不如同门生郎中彭闳,扬州从事皋弘。’帝曰:‘俞,往,女谐。’因拜荣为博士,引闳、弘为议郎。”[1](P1250)又“车驾幸大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赏赐。”“后荣入会庭中,诏赐奇果,受者皆怀之,荣独举手捧之以拜。”[1](P1250)桓荣卒,子郁当袭爵,上书让于兄子汎,明帝称郁“有礼让”;[1](P1254)南朝梁陆倕《为王光禄转太常让表》云:“拜命无辞,受爵不让,况宗卿清重,历选所难,汉晋已降,莫非素范,辞爵则桓郁、张奋,让封则丁鸿、刘恺。”[15]陆倕将桓郁视为辞爵的典型代表,可见其谦让之风深受后人推崇。又,桓晔尤修志介,父卒时,姑贵而不以礼行,晔竟不与其来往,终以笃行礼教而得举孝廉,都属此例。
此外,龙亢桓氏还形成重视教学的家族传统。桓家世代以教习儒经为业,荣、郁、焉等甚至为帝王之师。桓荣终生致力于儒家经学的教授传习,他在九江葬师后,即“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莽败,天下乱。桓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后复客授江淮间。”[1](P1249)桓郁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桓焉“能世传其家学”,“弟子传业者数百人”[1](P1257)桓典“复传其家业,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数百人”。[1](P1258)桓麟曾“入侍讲禁中”。[1](P1260)正是一代代家学相传,桓氏得以成为东汉儒学世家之代表。
桓氏家学家风对其家族振兴起到了重要影响。首先,龙亢桓氏世代致力儒学,辩明经义,符合时代潮流。《后汉书·桓荣传论》曰:“中兴而桓氏尤盛,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1](P1260)赵翼《廿二史札记》云:“计桓氏经学,著于东汉一朝,视孔、伏二家稍逊其久。然一家三代皆以明经为帝王师,且至五帝,则又孔、伏二氏所不及也。”[16](P101)龙亢桓氏自东汉初年桓荣获宠,至汉末桓典受爵,家族显赫时长几乎贯穿整个东汉王朝。其中数人被封侯,几代为帝师,可谓盛极!晋葛玄《抱朴子·内篇·勤求卷》云:
章帝在东宫时,从桓荣以受孝经。及帝即位,以荣为太常上卿。天子幸荣第,令荣东面坐,设几杖。会百官及荣门生生徒数百人,帝亲自持业讲说。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及荣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车,抱卷而趋,如弟子之礼。及荣薨,天子为荣素服。凡此诸君,非能攻城野战,折冲拓境,悬旌效节,祈连方,转元功,骋锐绝域也。徒以一经之业,宣传章句,而见尊重,巍巍如此。[17](P445)
实际上,桓氏五代获汉家帝王青睐,与其以儒经为主的家学和以儒礼为主的家风是分不开的。钱穆指出:“门第起源,与儒家传统有深密不可分之关联。非属因有九品中正制而才有此下之门第。门第即来自士族,血缘本于儒家。”[11](P141)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从此成为汉室提倡的官方学说。《后汉书·儒林列传序》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採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1](P2545)皮锡瑞《经学历史》称自汉元、成至后汉为“经学的极盛时代”,[18](P101)桓荣深谙儒学,得到官方赏识就不足为奇。他后来在朝廷也是通过说解《尚书》、敷奏经书等方式进一步获得赏识与升迁。荣桓曾感叹道:“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1](P1125)桓荣、桓郁、桓焉三代分别为明、章、和、安、顺五帝之师,正是因为“经术成为跃身为世家大族的知识资本”的原因。[19](P145)
其次,桓氏世代重行,即笃行儒教,品行高尚,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以成儒者楷模。东汉时期以察举进仕,德行的好坏往往直接影响其仕途。葛玄《抱朴子·外篇·崇教篇》又云:“其经术如仲舒、桓荣者,强直若龚遂、王吉者,能朝夕讲论忠孝之至道,正色证存亡之轨迹,以洗濯垢涅,闲邪矫枉。宜必抑情遵宪法,入德训者矣。”[20](P124)何耿镛以为:“东汉光武帝提倡经术与西汉有点不同。他鉴于西汉匡衡、张禹、孔光、马宫等虽以经师居显位,但均是持禄保位,于社稷无所匡救之辈,因此主张取士必须经明行修,既重其文,又考其行。”[21](P54)桓氏子弟历代注重品行,如朱普徒众盛多,仅桓荣为之奔丧;王吉亡后无人问,独桓典为之尽礼,自然容易赢得世人的赞赏,猎取声誉,对于他们走向仕途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最后,龙亢桓氏历代从事教学,教授子弟可以为桓氏子弟登攀仕途带来更多的机遇。东汉帝王皆尊师重教,如明帝对桓荣可谓恭敬有加,“乘与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仗,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既罢,悉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其恩礼若此。”[1](P1252)欧阳修《集古录》卷二《后汉孔宙碑阴题名》云:“汉世公卿各自教授常数百人,其亲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22](P1112)龙亢桓氏世代教授,弟子门生众多,既有利于传播声名,也可互为声援和引荐,如桓荣即因弟子推荐而得以仕进。汉人重视师法和家法,桓氏子弟遍及宇内,其中不乏声名显赫者,如丁鸿、朱宠、杨震、杨赐、张辅等均官至显位,如张璠《后汉纪·和帝纪》就记载“张辅事太常桓荣,勤力于学,常在师门,讲诵不殆。每朝会辄敢讲于上前,音动左右。”[12](P682)他们的得势自然会对桓氏家族的发展带来更多的良性帮助。
另一方面,龙亢桓氏的家学家风对其家族成员的政治地位也起到过一定的限制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桓氏成员之所以能获得帝王青睐,所凭依的正是其对儒经的浸淫和对儒教的笃行,由此也决定他们所承担的不过是“润饰鸿业”的政治角色。二是桓氏家族虽于东汉王朝兴盛发达,也并非一条直线,全无风阻。汉明帝、章帝、和帝时桓氏最显赫,桓荣、桓郁、桓焉三代风光更无限,但是到了东汉中后期,家族实际上已显颓势。第四代桓麟、桓鸾为官低微,第五代桓晔流落它乡而被人诬死,桓彬亦被废职,只有桓典稍有起色。然桓典封侯拜官的原因竟然是参与何进欲诛宦官之谋,与先祖以儒学进仕方式迥然不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同当时的政治状况,尤其是东汉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喜爱程度密切相关。前面几代帝王奉崇儒学,然自邓太后称制,学者颇为懈怠。桓帝即位后,“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尽矣。”[1](P2547)此时龙亢桓氏如桓麟、桓晔、桓鸾等依旧死抱家传儒学,不能因时而变,落伍自是必然。桓典乘势而起,参与权谋,才得力保家门不衰。总之,东汉龙亢桓氏家族在政治上的显赫程度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喜爱程度:当帝王们对儒学高度重视时,其家族一跃而成显赫之族;一旦他们对此失去兴趣,其家族在政治上就失去保障而渐呈衰落之势。由此可知,紧扣时代脉搏则上,不合时宜则下,实为东汉龙亢桓氏兴衰的深层原因。
三、文学创作:人才辈出而少有名彦
东汉龙亢桓氏遗留下来的文学作品不多,其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大致概貌如下:
桓荣精通儒学,于诗赋也有较为浓厚的兴趣。《东观汉记》载:“初,桓荣遭仓卒困厄时,尝与族人桓元卿俱捃拾,投闲辄赋诗”。[4](P620)儒学本身与文学即有紧密联系,桓荣在文学上有造诣,自是不难想象,可惜其诗作已经不存。
桓郁把父亲删定的二十三万言之章句,再次进行删定,以成十二万言,与父著合为《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明帝甚至还把自制的《五家要说章句》交给桓郁校定。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删减经典、校定章句自然难以完成。
桓焉自少“明经笃行,有名称”,[1](P1257)桓鸾“学览六经,莫不贯综”,[4](P629)桓礹“邴营气类,经纬士人”,[12](P47)他们对文学亦当有所触及,惜均无作品传世。
东汉龙亢桓氏在文学上成就最高的应属桓麟。皇甫谧《高士传》卷下:“挚恂……渭滨弟子扶风马融,沛国桓麟等,自远方至者十余人。”[23](P103)本传载其“所著碑、诔、赞、说、书凡二十一篇。”注引挚虞《文章志》曰:“麟文见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诔七首,《七说》一首,《沛相郭府君书》一首”。[1](P1260)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诗一首于《汉诗》卷六,严可均辑其《七说》和《太尉刘宽碑》二文于《全后汉文》卷二十七。《答客诗》作于桓麟十二岁时:“邈矣甘罗,超等绝伦,伊彼杨乌,命世称贤,嗟予憃弱,殊才伟年,仰惭二子,俯媿过言。”与同时期作品相比,此诗在艺术上并无突出特点,然用词老练,出自少年之手自然显得有点不同凡响。透过该诗,可以发现桓麟少年时即怀有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抱负。北周滕王宇文迥《庾信集序》赞美庾信早年文采出众时云:“桓驎(麟)十四之岁,答宿客之诗;鲁连十二之年,杜坚离之辨。”[24](P55)可见桓麟年少善文的事迹,颇得后人赞赏。《艺文类聚》卷五十七辑有《七说》残文,已难窥全貌,然其中不乏精彩之句:
王良相其左,造父骖其右,挥沫扬镳,倏忽长驱。轮不暇转,足不及骤,腾虚逾浮,瞥若飚雾,追慌忽,逐无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飞响之应声。超绝壑,逾悬阜,驰猛禽,射劲鸟,骋不失踪,满不空发。弹轻翼于高冥,穷疾足于方外。[25](P1025)
赋中极力渲染和夸赞狩猎时的紧张场面,气势恢宏,节奏紧凑,令人触目惊心。其中对偶的运用,长短句的结合,有利于增添文章的急促感。西晋傅玄《七谟序》称:“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起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26](P1723)可见桓麟《七说》属于随应时风、“枝附影从”之作。但该文的文学水平却不容置疑,傅玄以之与傅毅、崔骃等同列,说明该文于当时已获盛誉。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篇》评价它为:“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27](P148)称赞的是它文辞的优美和华丽。《太尉刘宽碑》序言部分夹述夹议,用词精炼典雅,读来明白晓畅,如见其人。碑文虽尽溢美之词,却也清词丽句,缀采雅泽。
桓彬在文学上也有成就。本传载其“所著《七说》及书凡三篇”,蔡邕等共论序其志,以为彬“学优文丽,至通也”。[1](P1261)严可均辑其文《七设》一篇之残文入《全后汉文》卷二十七。《七设》体制类荀《赋》之谜语体。如其中“新城之秔,雍丘之粱,重穋代熟,既滑且香”,写得音韵优美,清新流畅。桓俨(即桓晔)《遗陈业书》虽仅能见残篇,然其中隐逸之志依然清晰可见。作者曾避地会稽,浮游海上,文中透露出作者不满当时动乱时局,希望深隐遁迹的情怀。
由上可知,东汉龙亢桓氏在文学创作上已有收获,尤其是后辈中桓麟、桓彬、桓晔等人的诗文,在当时就颇得声誉,并在后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不过桓氏在整个东汉时期既没有出现声名卓著的文学大家,也没有出现影响深远的经典名篇,亦是不争的事实。
东汉龙亢桓氏世代治儒的家风对其文学创作影响较大。胡旭《汉魏文学嬗变研究》指出:“经学的最大特征是说教和训诫,那种一本正经的生活理念和行为方式,与文学生动、活泼、浪漫、空灵的那种特征,天然不相合。”[28](P96)桓氏世代好学,遗留作品却不多,恐怕与汉代经师讲求述而不作、限于章句考索的学风有关。儒家诗歌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文学伦理教化之功能,而汉代今古文家说诗“唯从美刺作用出发,不免以意逆志,牵强附会”,[29](P17)这种风气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写作。桓氏文学作品中透露的思想内容与儒家旨归基本一致,在艺术特色上多以平实典雅为主,缺少灵动活泼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其文学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在汉人视野中,文学与经学并无明确分界,但就今人的文学概念来看,当时文学创作对于政治的影响并不明显,远不如经学受重视。西汉武帝、宣帝等少数帝王曾对赋作产生兴趣,但能者如枚皋、东方朔之徒亦不过当作幸臣而蓄养之。后汉灵帝置鸿都门学,“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1](P1991-1992)被蔡邕等评为“才之小者”“效能小善”,以致“士君子皆耻以为列焉”。[9](P164)文学地位的真正提高,应是在曹操父子的大力提倡之后。故钱穆说:“尚文之风,溯源实始曹魏。而门第来历,则远在其前。门第必重儒术,谨礼法,尚文则竞虚华,开轻薄。惟魏晋以下之门第,既不能在政治上有建树,乃转趋于在文辞上作表现。”[11](P173)正是受到当时儒学思潮的影响,龙亢桓氏在文学创作上不多,以致整个东汉王朝,他们在文学上都没有取得特别值得称道的成就。桓氏于诗文方面稍有成就者如桓麟、桓彬、桓晔等皆生活于东汉中晚期。汉末社会动荡,朝政紊乱,不少文人借用诗赋来表达对现实苦闷的哀伤和对内心悲愤的宣泄。桓麟、桓彬和桓晔都性格秉直,不媚于俗,他们在与黑暗的政治势力抗争时,往往采取退避的态度,通过文学创作抒发离尘脱俗的情怀,寻求精神之解脱,以求塑造人格的清高,达到人性的完善。他们在家族政治地位下降的同时,人生路途颇不得意,反而在文学上获得了一定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