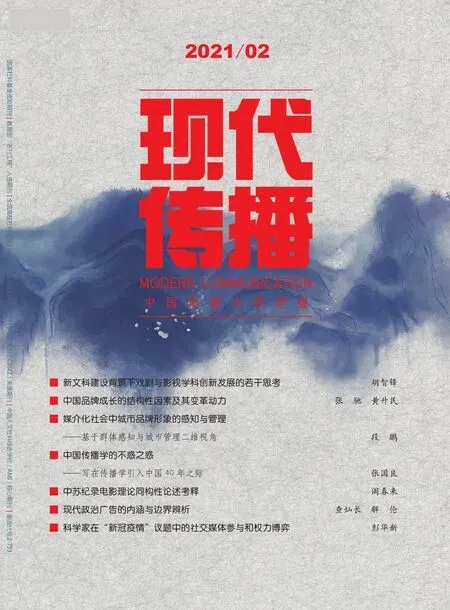论游戏表意的四体演进:一个符号修辞学分析
2021-11-29陆正兰李俊欣
■ 陆正兰 李俊欣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视角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全世界都在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疫情最严峻的4月,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多家游戏公司推出一项名为“Play Apart Together”的活动,旨在提醒人们待在家里,进行适当的游戏娱乐活动,以此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防控疫情的蔓延。游戏作为一种特殊的活动方式,在此刻发挥出它特殊的作用。同样,在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的游戏产业强势增长,据数据统计,2020年1月至3月,移动游戏市场收入达到近550亿,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率超过49%,环比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①由此可见,游戏不只是促进文化经济产业增长的一种有效途径,还是人与世界保持关联的一种独特方式,它触及到社会文化多个方面。
然而,游戏作为一种延续至今的人类活动,在人类文化的版图上,并没有获得一个正式的名分。直到当代,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游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的意义逐渐凸显,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游戏的发展及其在人类世界中的独特作用。
那么,游戏在人类的意义世界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从最早的游戏起源到当代蓬勃发展的各种数字化游戏,其间它的形式意义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游戏行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的意义维度又产生了怎样的异化?它带给我们怎样的反思?本文将借助符号修辞的四体演进模式,回溯游戏意义的演进历史,在寻找其演变规律的同时,分析其意义变迁的动因。
二、理论视角:符号修辞与四体演进
(一)符号修辞
修辞,最早的意思是指加强言辞或文句说服能力的手法。传统的“修辞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领域。随着20世纪“语言学转向”及符号学的发展,修辞学逐渐演变成“新修辞学”,即“符号修辞学”。符号修辞学与传统修辞学的主要区分之一,就是它的研究领域被扩展到各种媒介文本当中,如广告、电影、新闻以及游戏等。其中,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的《图像修辞》最具代表性,且影响深远。巴尔特强调,作为非语言符号的图像,传达意义、获得受众的关注和认同的过程,也是各种修辞手法或技巧的力量显现的过程,图像中的符号组合,彰显的是明喻、隐喻、转喻、反讽等修辞手法所蕴含的媒介文本的深层话语。
因此,明喻、隐喻、转喻、反讽等具体的修辞手段,不只是一种纯粹的表达技巧,还如布斯所说的,是“思想的根本形式”②。所以,当我们讨论游戏的符号修辞,既可以在微观层面上,即具体的游戏文本中展开,以探究其符号修辞效果;也可以从宏观层面上,把游戏修辞看成其文化表意的思想方式,透过这种修辞形式的演变,审视其意义价值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二)四体演进
四体演进的观点,最早出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18世纪初,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神、英雄、凡人、颓废四个时期,并用修辞表意分别描述这四个阶段。他提出,神祇时期将精神赋予万物,以隐喻为主;英雄时期将精神寄予特殊人物,以转喻为主;凡人时期则共享某种精神,将特殊化为一般,以提喻为主;颓废时期则走向谎言,以反讽为主。
实际上早在维柯之前,就有这种将符号修辞的四体演进历时化的思维,宋代学者邵雍在《皇极经世》中,在推演古历史时就已经用到,且更为具体形象,邵雍将中国史分为皇、帝、王、霸四个时期:“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③这种通过意义的否定式关联对人类历史的演进模式进行思考的方式,在现代诺思罗普·弗莱、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乔纳森·卡勒和格雷马斯等人的思想中也有体现。卡勒甚至认为四体演进不仅是“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还是“唯一体系”(the system)④。
由此可见,四体演进是所有符号文本表意方式演化的总趋势,尽管并非所有的符号文本表意方式都整齐划一地分为四步,但总体遵循这样的规律。符号学家赵毅衡对四体演进规律这样解释:“任何一种符号表意方式,不可避免走向自身的否定。形式演化就是文化史,随着程式的过熟,必然走向自我怀疑,自我解构。”⑤为此,他进一步总结了四体演进规律,提出从隐喻开始,符号文本体裁的表意,会形成逐步分解的过程,构成否定式的递进关系,即“隐喻(异之同)>转喻(同之异)>提喻(分之合)>反讽(合之分)”⑥。
参照符号修辞四体演进的规律,回溯游戏形式意义的演进,可以将游戏的表意形式大致分为四个时期:隐喻时期——作为精神世界的纯粹游戏;转喻时期——游戏主体形式的诞生;提喻时期——电子游戏的风靡;反讽时期——游戏异化与电子竞技的出现。
三、隐喻时期:作为一种精神隐喻的游戏
(一)“永恒的活火”:赫拉克利特的游戏隐喻
从古代到近代,游戏经历了漫长的隐喻时期。在这一阶段,游戏一直作为自由精神的象征而存在。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把古希腊神话世界看成是一场游戏,一场宙斯的游戏、一场火的自我游戏。就如尼采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中对赫拉克利特式的世界的描绘:“一种生成和消逝,一种建造和破坏,没有一点儿道德归咎,永远这样无罪,这在这个世界上仅仅属于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如同孩子和艺术家在游戏一样,永恒的活火也游戏着、建造着和破坏着,无罪可言——永恒(der Aeon)和自己玩这游戏。它转化为水和土,堆积着,就像一个孩子在海边堆积又毁坏沙堆;它不断重新开始这游戏”⑦。
赫拉克利特作为“永恒的活火”的游戏,是一种隐喻,它既包含了游戏过程中的竞争性,也呈现出总体上的和谐感,这种竞争与和谐同儿童的游戏及艺术家的创作相一致。儿童与艺术家具有听从“存在之天命”的“自由意志”,因而他们的游戏常被认为是真正的游戏,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时间是孩童的游戏,摆弄着棋子,王权掌握在孩童手中”⑧。实际上,游戏不只是任意的玩耍,同时意味着极为投入的创造,并据此内在地生成秩序。因此,在赫拉克利特思想中,宇宙是以活火为始基的生成与毁灭的游戏,这样的活火游戏流变出万物却又不断生灭;因此,“游戏”就是一个自由、规则和多变的世界的喻象,象征着古希腊神话时期的创造精神,游戏世界呈现的就是神赐予人类有秩序的秘密花园。
(二)“逍遥游”:庄子的游戏境界
在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中,游戏也代表了人性的本真状态。游戏之“游”,是一种绝对自由的“逍遥之游”,无论是“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还是“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庄子·在宥》),“精神世界的解放”总是以“游”字作为象征。庄子强调的“游戏”作为一种人生态度,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精神世界的解放。
在庄子代表的逍遥世界里,“游”包含着游戏、游世以及游心,这三者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庄子的“逍遥游”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和审美上的超越,强调的是人生的绝对自由,因此,庄子的游戏世界实际上是一个超越现实的自由而和谐的理想世界。“庄子所谓游心,乃是对宇宙事物做一种根源性的把握,从而达成一种和谐、恬淡、无限及自然的境界。在庄子看来,游心就是心灵的自由活动,而心灵的自由其实就是通过体道的生活,即体道之自由性、无限性与整体性。”⑨
(三)非功利的审美游戏
进入近代,康德和席勒也将游戏视作绝对自由的象征,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对游戏进行新的阐释,赋予其新的价值。
康德、席勒等人基于各自的哲学立场讨论了游戏在人类意义世界中的地位。康德同样将游戏视作人类精神自由的象征,但他对游戏意义的讨论建立在与劳作的二元对立之上,在他看来,人的“每一种活动不是一种劳作(有目的的活动),就是一种游戏(有意图而无目的的活动)”⑩。劳作具有实践指向的“外在目的”,这种目的受到主客观环境的制约,因而是不自由的;游戏具有意图而无目的,讨论的是游戏的主观“内在目的”,即游戏以自身的娱乐过程为主,包含着幻想与快感体验,不具有实践目的指向,因而是自由的。
从这一层面上看,康德对游戏意义的思考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亚里士多德最早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与《政治学》中讨论了游戏与劳作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眼里,游戏意味着劳作后的休息和消遣,是一种不带目的性的行为活动。康德在游戏与劳作的区隔之上,进一步强调了作为审美活动的游戏,在他看来,艺术和游戏一样,通过与一般性劳作的区别来确立自身的意义。因此,艺术可以分为“自由的艺术”以及“雇佣的艺术”,前者意在获得愉快的情感,而后者在于获得报酬。“我们把前者看作它好像只能作为游戏,即一种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而得出合乎目的的结果(做成功);而后者却是这样,即它能够作为劳动,一种本身并不快适(很辛苦)而只是通过它的结果(如报酬)吸引人的事情,因而强制地加之于人。”因此,游戏和艺术都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并与被迫劳动相对立,是人类精神自由的象征。席勒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游戏理论,他将人的游戏分为了“自然的游戏”与“审美的游戏”,自然的游戏如动物饱腹之后的玩耍,并没有摆脱所有需求,因而是不完全的自由,只有作为“审美的游戏”才能冲破物质的束缚,处于完全的自由状态。“在这些动作中有自由,但不是摆脱了所有需求的自由,而是摆脱了某种外在的需要的自由……就是说,是剩余的生命刺激它行动。”最终,席勒认为游戏和艺术都是人类精力过剩的产物,游戏作为非功利的纯粹审美活动,建立在人的剩余精力之上。
(四)民间游戏的现实隐喻
自古以来,在很多民间文化中,游戏最初的形态,便是隐喻式地仿照幻想而来的现实。在《文化的解释》一书末章,克利福德·格尔茨曾引用边沁的“深层游戏”(deep play)来探讨巴厘岛的文化焦点——斗鸡。边沁用“深层游戏”意指赌注过高的赌博游戏,他认为这种游戏既不理性,也不道德。格尔茨则认为,这种具有赌博性质的游戏镶嵌在巴厘岛的整个社会结构中,是不可或缺的神圣仪式和道德象征。“在有深度的游戏中,投入钱的数量很大,而更为重要的还不是物质性的获取,而是名望、荣誉、尊严、敬重——总之,在巴厘岛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词,也就是‘地位’。”对巴厘岛人而言,雄鸡是人格的隐喻,而斗鸡游戏是社会基体的模拟,关乎他们的存在。但事实上,巴厘岛人的地位并不会因斗鸡而发生变化,而金钱在游戏的参与过程中也不值一提。斗鸡游戏赋予巴厘岛人的只是一种存在的意义、一种地位跃升的假象。因此,在格尔茨看来,“作为一个形象,一种虚构,一个模型和隐喻,斗鸡是一个表达的工具;它的功能既不是缓减社会的激情,也不是增强它们(尽管通过玩火的方式对这两方面都稍有影响),而是以羽毛、血、人群和金钱为媒介来展现它们。”在格尔茨眼里,游戏就是巴厘岛人的一种精神象征的意义形式,它关乎游戏者的存在。
无论是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游戏”还是庄子的“逍遥游”,或是近代审美活动的非功利的游戏状态,亦或是生生不息的各种民间游戏,都是一种精神的隐喻。游戏并不作为独立的形式存在,而是总体上作为一种隐喻,世界如同宙斯的游戏,人生不过是逍遥的游戏,艺术和审美不过是自由的游戏。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话说:“游戏是像迪士尼乐园的一种人为的天堂,或者是一种乌托邦似的幻境,我们借助这种幻境去阐释和补充日常生活的意义。”
四、转喻时期:游戏主体形式的诞生
转喻,并不用直接的喻体来呈现世界,而是通过意义关联的“他者”来认识对象本身。现代以来,游戏进入转喻时期。游戏以一种主体形式诞生,一方面它的意义体现在与艺术、竞赛、法律及战争之间的各种关联中,而另一方面,原先的游戏精神,也与各种文化形式渐行渐远。
在《游戏的人》一书中,赫伊津哈总结了游戏的重要特征:自由、非功利、规则、隔离性。在他看来,“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这种活动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其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游戏以自身为目的而又伴有一种紧张、愉快的情感以及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赫伊津哈的游戏理论是把游戏放在广义的文化形式下,由此推演,在任何人类文化活动中都能够找到游戏的成分,竞赛、音乐、法律甚至战争都具有游戏的形式。
赫伊津哈也认识到,他所讨论的以形式愉悦为主导的游戏精神,在当代文明中日益消减甚至不复存在,“职业化的精神再也不是真正的游戏精神,它丧失了自发性和关心投入(carelessness)”。运动和竞赛早已远离了游戏之域,不再以行动本身为主导,而战争不再是野蛮的竞赛,部落的对抗被可悲的友敌原则所取代。因此赫伊津哈得出的悲观结论也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文化的游戏成分自十八世纪全盛之时以来,就一直处于衰落之中。”
伽达默尔也在讨论“作为文化的游戏”。在他看来,游戏能够通过秩序(Ordnung)来规约游戏者,并且自身带有封闭的结构,这种结构如同赫伊津哈所言的“魔圈”,将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区隔开来。伽达默尔将游戏视作理解艺术经验的重要意象,认为游戏的意义在于游戏自身,“一切游戏活动都是一种被游戏过程(alles Spielen ist ein Gespieltwerden)。游戏的魅力,游戏所表现的迷惑力,正在于游戏超越游戏者而成为主宰”。
和康德、席勒等人不同的是,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应当抛开游戏中人的主观态度和精神,回归到作为自然存在的游戏主体当中。在分析艺术的游戏时,伽达默尔将戏剧视作一种游戏,原因在于戏剧具有自身封闭世界的游戏结构。
因此,伽达默尔和赫伊津哈一样,在肯定游戏以主体形式存在的同时,还认为游戏包含着各种文化形式。赫伊津哈从整体的文化角度讨论游戏,认为竞赛、法律乃至战争都可以是游戏;而伽达默尔的艺术游戏则包含着戏剧、舞蹈和音乐等形式。
从赫伊津哈的“自由、非功利性、隔离性、秩序及规则”到罗杰·卡约瓦归纳的“自由、隔离、无产出、规则掌控、佯信”等游戏特征,从中国学者宗争界定的游戏是“受规则制约,拥有不确定性结局,具有竞争性,虚而非伪的人类活动”,再到白志如总结的游戏具有“虚拟性、自由性、自足性、规则性、竞争性和运动性”六大特征,游戏主体形式的关键特征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对游戏意义的讨论更加强调游戏本身的规则结构和组织特征。
然而,体育、竞赛与游戏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它们是否都被包含在游戏的概念范围内?崔乐泉认为:“游艺的许多内容与体育同源异流,又由于强调以娱乐消遣为主要目的,因而它与强调竞技性的体育又有着差异。而这也同时形成了游艺本身的特点。”同样,赵毅衡在《艺术与游戏在意义世界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艺术和游戏都具有目的论上的无用性以及实践经验上的不透明性。这两者构成了康德所讨论的“内在目的性”,就纯粹以娱乐过程为目的的游戏而言,现代社会的体育和赌博便不再是游戏,虽然体育和竞赛无疑都具有游戏的成分,但“体育实际上是一种对自然‘改造取效’的实践意义活动,它在强健身体的指向上是透明的”。
游戏作为一种转喻,实际上已经逐渐消减了往日的游戏精神,另一方面,文化的游戏成分日益衰退,原本属于游戏范围的体育等文化形式,也不再以娱乐的过程为目的,而是将输赢、收益等视为根本目的,远离了游戏的初衷。
五、提喻时期:电子游戏的风靡
电子游戏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便风靡全球,成为与电影业相竞争的最为获利的娱乐产业。电子游戏的世界不只存在于冰冷的机器界面中,同时也嵌套在日常生活的空间和场景中,游戏参与者在彼此分离却又紧密相连的虚拟域和真实域之间循环。电子游戏的意义既存在于故事情节和规则的内文本当中,也存在于人们的互动过程中。因此,在这个时期,电子游戏作为部分代整体的提喻,代表了一种文化活动形式,代表了一种镶嵌于日常生活的部分场景。一个数据统计可以证明,到2019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308.8亿元,同比增长7.7%;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6.4亿人,同比增长2.5%。
值得注意的是,提喻时期的电子游戏,是伴随着科技而生的文化活动。它最大的影响并不在于创造了商业利润,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游戏的行为方式,甚至颠覆了人们对游戏的认知。
从红白机(Family Computer)到街机(Arcade),从掌上主机(Handheld)到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不同的电子设备创造了不同的游戏场景,而不同的游戏场景又塑造了新的游戏行为。约书亚·梅罗维茨认为“媒介的演化降低了‘亲身参与’对于经历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性”。在电子游戏构建的全新场景中,人机互动取代了人人互动成为游戏的主要形式。人们可以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或者在公交车上玩游戏,只需要盯着显示屏,动动手指便可以体验丰富多彩的游戏世界。
电子游戏对人类行为产生的巨大影响,吸引了全球各地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涌现了一批电子游戏研究的专家,他们来自计算科学、社会学、传播学以及经济学等各个领域。这一时期游戏表意的主要修辞格便是提喻,给出部分对象替代整体,电子游戏成为游戏研究的主流范式。在无特殊语境的情况下,“游戏”一词通常意义上指向的都是电子游戏。
埃根菲尔德-尼尔森等人在《电子游戏概论》(Understanding Video Games:The Essential Introduction)一书中认为电子游戏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叙述学”(Narratology)和“游戏学”(Ludology)两大类,前者借用文学理论将故事情节置于游戏研究的核心,后者则认为游戏的核心意义在于结构和规则。
(一)叙述学:游戏的核心在于情节与故事
叙述学主要运用文学和戏剧模式来描述和理解电子游戏,游戏是否具有叙述能力是讨论游戏叙述学问题的前提。按照赵毅衡的观点,叙述文本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即“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中。此符号文本可以被接受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因此,游戏的叙述必然卷入人物的事态变化,包含情节和故事。那么游戏是否必然包含情节,具有可述性?玛丽-劳尔·瑞安曾在《故事的变身》一书中系统地讨论了游戏的叙述问题,在瑞安看来,有的游戏具有叙述能力,另外一些则没有。因此,瑞安指出:“电脑游戏乃一门在叙事与游戏玩法之间进行妥协的艺术。”宗争则认为,任何游戏活动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叙述文本,原因在于“任何游戏都卷入了人物(玩者) 和情节(玩者动作构成的游戏局面变化)”。
因此,是否所有的游戏类型都具备叙述能力,是一个仍具争议的话题,但游戏媒介本身是具有可述性的。游戏叙述学借用文学理论将游戏中的情节和故事置于游戏的核心,将游戏视作一种新的叙述类型,一种讲故事的互动媒介。布兰达·劳雷尔将电脑视作“类似戏剧的媒介”;亨利·詹金斯认为电子游戏是一种多媒体的讲故事的方式,其叙述方式包括了环境叙述(Environmental storytelling)、嵌入式叙述(Embedded narrative)、微少叙述(Micronarrative)、自生性叙述(Emerngent narrative)等。
(二)游戏学:游戏的核心在于拟真与规则
不同于叙述学对游戏故事和情节的关注,“游戏学”(Ludology)聚焦“游戏的玩法”,强调玩家在游戏的规则框架下的能动性。唤作“游戏学”的游戏理论学派,一开始便主张摆脱文学理论的窠臼,用独立的游戏研究框架取代叙述学路径。在恭扎罗·弗拉斯卡看来,游戏的多变性和故事的叙述性之间存在矛盾,叙述是表征性的,而游戏则主要是拟真(Simulation)。“与传统媒体不同,电子游戏并不是建基于‘再现论’,而是建立在我们熟悉的选择性符号结构——‘拟真’之上。虽然‘拟真’系统叙述学有许多共通的元素,如角色、环境、事件等,但它们的构成在本质上却大相径庭。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提供了不同修辞上的可能类型。”因此,游戏不应是结构性再现的叙述,而是一种“拟真”,它不仅包括事件,还吸收运作规则。埃斯本·埃尔瑟斯也曾指出,“电脑游戏研究需要从叙述主义中解放出来,必须建构该领域的本土理论”。尽管游戏的叙述与玩法并不相斥,两者共同构成了游戏的意义世界,但两者谁才是游戏的第一性问题,是“叙述学”与“游戏学”争论的焦点。总而言之,无论是强调游戏故事性的叙述,还是游戏学聚焦“拟真”基础之上的游戏结构特征,都以游戏文本本身为主,来思考游戏意义的发生机制。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电子游戏的形式愈加多元化,从最早的井字棋游戏(Tic Tac Toe)到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再到最新的VR游戏,游戏的互动性不断提高,游戏场景也愈加逼真。电子游戏时代到来之前,游戏互动基于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在电子游戏时代,这种互动不仅体现为人与机器的互动,同时也包含着“人-机-人”的互动模式。马克·波斯特反思了后人本主义时代人与机器的关系,并将这种双向去中心化交流的时代称为“第二媒介时代”;李沁在波斯特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沉浸传播为特征的“第三媒介时代”,认为“这种状态下的媒介使用者真正享受这个过程、进入到忘我境地,并在此过程中激励自我”。
电子游戏作为新兴的人与机器的关系枢纽,具有强互动性和沉浸感,使得人们可以穿梭于赛博世界和物理空间,在与虚拟或真实主体的互动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愉悦。赛斯·吉丁斯在《游戏世界:虚拟媒介与儿童日常玩耍》一书的结尾描述了这样的游戏场景:“16岁的乔依然可以唱出《精灵宝可梦》电视动画的主题曲,他们俩也会时不时又玩起来,从在线文化中各式各样为大龄儿童和成人设计的游戏,到老练地驾驭新一代《精灵宝可梦》DS游戏机游戏。特别是在假期里,当他们再次聚首,你挨着我,我靠着你一起玩《精灵宝可梦》的时候,兄弟-机器(brother-machine)就被重新连接起来了。”
史蒂芬·克莱恩等人从媒介技术、市场和文化三个角度对电子游戏研究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媒介技术关注电子游戏的设计及其带来的感知重组,政治经济学从产业和市场角度强调电子游戏带来的社会效益以及背后的资本扩张,文化路径则聚焦电子游戏作为媒介文本的表征、叙述以及主体地位(subject-positions),这三种研究路径各自独立又相互交织。吉丁斯所描绘的游戏场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人们可以通过游戏来补充日常生活的意义,但在电子游戏使得世界仿佛变得更美好的同时,“暴力机器”也正在把人们推入深渊。
六、走向反讽:数字监狱与游戏劳工
从最初的“娱乐新天地”到后来的“电子海洛因”,游戏似乎不知不觉进入了反讽时期。随着各种电子游戏高歌猛进,数字时代的游戏是否走向了自由意义的对立面?游戏规则的复杂化、各种程序修辞、多种可能路径,让参与者仿若投身于“数字监狱”,而游戏劳工的出现则强化了这种控制。对于参与者而言,玩游戏看似是一种休闲,实际上是一份工作。
(一)游戏程序与意识形态
伊恩·博格斯特曾将修辞学应用到游戏程序的研究当中,提出了程序修辞(Procedural Rhetoric)这一概念,“程序修辞是游戏程序设计者身份的一个子域(subdomain),其论据的建构并非基于文字或图像,而是通过行为规则或动态模型”。程序修辞即通过计算过程进行说服的实践,游戏设计者或游戏厂商能够将他们的观点和想法隐形地植入到游戏的程序和规则当中,并对游戏玩家产生影响。这意味着,游戏同样也可以是生产意识形态的机器,参与者在其中会受到编码者价值观的影响。正如语言修辞对演说者和听众有效果,书面修辞对作者和读者都有效果,而程序修辞则对程序员和用户、游戏设计者和玩家都有效果。马丁·利斯特等人总结称:“互动媒介中的人类运动不是由‘自由意志’所推动的,而是由作为系统的游戏所唤起的;玩家不需要对他或她的身体负责,因为这个身体‘是作为游戏循环的一部分来决定如何行动的’。玩家被游戏操控——这是充满激情的循环。”因此,游戏的世界并非完全由参与者的自由意志支配,游戏规则的日益复杂化无疑是追求自由的渐进式否定。
(二)游戏玩工:作为劳动的游戏
游戏劳工的出现使得游戏与劳作的区隔日益模糊。朱利安·库克里奇在“数字劳工”的基础上,提出了“游戏劳工”(又译作玩工)(Play-Bour)这一概念。“数字劳工”,按照马里索·桑多瓦尔的定义,指的是“将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包括生产者和使用者”。而游戏劳工指代的则是“通过玩耍的形式,在其闲暇时间内创造价值的用户”,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资本的积累空间从“工厂车间”转向了“社会工厂”,甚至延伸到了人们日常休闲和娱乐的空间。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将休闲活动‘劳动化’的普遍实践标志着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即弹性积累模式,‘玩工’的普遍化与之高度匹配”。不同于游戏行业的工作者,游戏劳工指向的是游戏的用户,是一种无酬的劳动力。游戏劳工的出现,使得工作和游戏的区隔不再明显,游戏的“自由”和规则同样适用于描述这种新的劳动形式。在这一语境下,原本作为自由娱乐活动的游戏被异化为一种劳动生产实践。因此,库克里奇认为“正是自我规训的框架使得人们在信息社会将休闲活动定义为新的劳动形式成为可能,或者说,用‘自由’和‘规则’来描述劳动成为可能。个人玩家便是典型,他们赞同已有的规则仅仅是因为服从规则所获得的乐趣,因此,他们的自由建立在对游戏规则的服从之上”。
(三)电子竞技:职业化与表演式的游戏
游戏的发展推动了游戏形式本身的分化。电子竞技(Electronic Sports)形成于世纪之交,在21世纪10年代席卷全球。自电子竞技诞生以来,围绕“电子竞技是游戏还是体育”的争论从未间断,卢元镇在《体育社会学》一书中认为在从游戏到体育的转变过程中,游戏的特征会发生以下变化:自发娱乐性减少、准备条件更复杂、规则更严格、功利性更明显以及具有高级文化特征。戴焱淼在此基础上,将电子竞技视作一种“后现代体育”,认为“电子竞技先是‘游戏’,再是‘体育’。也可以说,电子竞技是游戏转向体育的一种路径选择,一种安置方式”。
电子竞技作为一种在体育赛事的框架之下开展的游戏活动,因其高度的商业化和职业化,脱离了游戏的本来面目,不再以游戏的娱乐过程为主要目的,而是指向输赢的结果和奖金争夺。电竞从业者也不再是单纯的玩家,他们的游戏过程意味着工作。因此,从这一层面看,电子竞技无疑是对康德“内在目的”游戏观的否定,娱乐和休闲的过程意义不再是电子竞技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职业化和功利化的道路上,电子竞技与以过程为目的的纯粹游戏已经渐行渐远,如赫伊津哈指出的那样:“随着运动不断地系统化和体制化,纯粹游戏品质的某些东西已不可避免地失落了。”如同运动和竞赛那样,电子竞技也从游戏之域中脱离出来,走向了自由意义的对立面。
七、结语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游戏的形式将会愈加多样化。最初的红白机已经成为了电子游戏博物馆的收藏品,而VR游戏正在创造的全新的感官体验向我们迎面扑来。游戏学家们甚至宣称,我们已经进入了“次世代”的游戏时代,高端的游戏引擎、极致的视觉效果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游戏体验,“真实性”与“现场感”成为未来游戏设计与开发的重要标准,数字游戏作为一种越来越活跃的活动,似乎正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乌托邦世界。
然而,胡泳在《未来是湿的》一书的译序中警示:“人们往往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发明互联网,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技术化、更干巴巴。其实正好相反,借由社会性软件,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的人文含义,就是让世界变得湿乎乎的,或很俗地说,让世界充满爱。”在游戏的世界里,如何真正保存“人文含义”而不被技术和其他因素异化?如何保存那种可以滋生人类自由意义的“湿乎乎”的游戏精神?这需要对游戏的未来意义做进一步深思。
注释:
① 伽马数据:《疫情防控期游戏产业调查报告》,https://mp.weixin.qq.com/s/5jfvJxVJHNma-GOe-Cc65A,2020年4月。
② [美]韦恩·C.布斯:《修辞的复兴》,穆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③ 邵雍:《皇极经世》,卷十一,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
④ Jonathan Culler.ThePursuitofSig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65.
⑤⑥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0、214页。
⑦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周国平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9页。
⑧ [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T.M.罗宾森英译、评注,楚荷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⑨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7页。
⑩ 曹俊峰:《康德美学引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