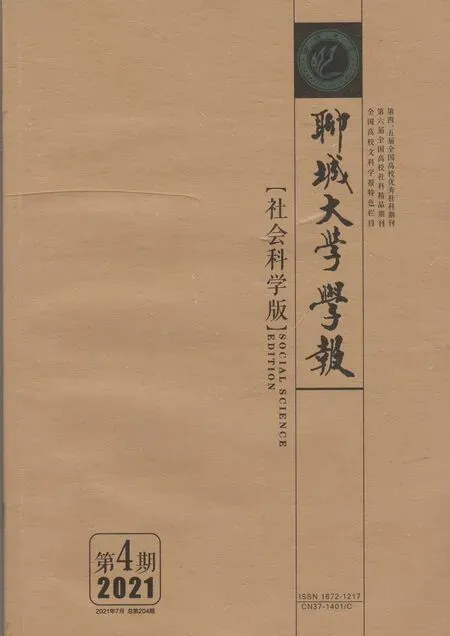庄仲方与桐城文章学
2021-11-29周焕卿
周焕卿
(常州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
张之洞《书目答问》和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都将庄仲方《南宋文范》视为必读书。继南宋吕祖谦《宋文鉴》之后,清代出现了几种南宋文选集。庄仲方《南宋文鉴》、董兆熊《南宋文录》为完帙,吴允嘉《南宋文鉴》为残本,其他选集均已不传①参见周焕卿:《清人选南宋文考佚》,《中国韵文学刊》,2017年第4期,第96-104页。。庄氏《南宋文范》最迟编定于道光八年(1828),最迟嘉庆十三年(1808)即着手编纂②《映雪楼藏书目录》卷十收《南宋文范》谓:“此仲方所编也”,“此编二十余年,阅书凡三百余部,成亦难矣。”(庄仲方:《映雪楼藏书目录》,清稿本)是书卷首有道光八年(1828)吴敬承序。。今传《南宋文范》道光十六年(1836)木活字刻本,是现存最早的南宋文选完帙刻本③是书有道光十六年(1836)木活字刻本、光绪十四年(1888)江苏书局刻本,光绪本卷四十二多出《婺州金华县社仓记》一文,本文据光绪本分析。(庄仲方纂:《南宋文范》,光绪十四年(1888)江苏书局刻本)。。庄仲方,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字兴记,号芝阶,浙江秀水人。师事顾曾,受古文法。卒于咸丰七年(1857)。④禇荣槐:《中书舍人庄芝阶先生传》,闵尔昌辑:《碑传集补》卷十一,民国十二年(1923)刊本。今存《映雪楼杂著》(不分卷)、《映雪楼文偶钞》(不分卷)、《映雪楼藏书目录》十卷、《碧血录》五卷、《南宋文范》七十卷、《金文雅》十六卷。大致在道光八年(1828)至二十一年(1841)间⑤古文选本的编纂,大致在道光八年(1828)至二十一年(1841)。依据有三:其一,庄氏于道光八年编定《映雪楼藏书目录》十卷,是书“总集类”收有《南宋文范》,但并未收任何一部断代文选。其二,庄氏《书〈南宋文读本〉后》载:“惟南宋之文缺如,因相与采辑成书为七十卷,阅书三百部,积二十年而后成。今择其尤者八卷,录为家塾读本。”则知《南宋文读本》必在道光八年《南宋文范》编成后着手择录。其三,庄氏先编定《金文读本》,再于道光二十一年编定《金文雅》。《金文雅》卷首有庄仲方作于是年的序。《书〈金文读本〉后》曰:“录存五卷。他日将广搜精择,以备一代文献之遗,以继《南宋文范》之后云。”(庄仲方:《书〈南宋文读本〉后》《书〈金文读本〉后》,均载《映雪楼杂著》,清抄本;庄仲方纂:《金文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庄氏还辑录了《公羊谷梁传文读本》《国语文读本》《战国策文读本》《周秦诸子文读本》《史记读本》《西汉文读本》《东汉文读本》《三国文读本》《晋文读本》《南北朝文读本》《唐文读本》《北宋文读本》《南宋文读本》《金文读本》《元文读本》《明文读本》《古文练要》。在汉学处于强势而宋学重兴的嘉道年间,正是桐城派崛起之时,庄仲方编纂了上述文选,他与外界有何接触?他的文章学思想如何?与桐城文派有何关系?又有何价值呢?①关于庄氏断代文选的研究成果有郭预衡《南宋诗文的时代特点——〈南宋文范〉校点本序言》、赵大志等《简论〈南宋文范简编〉及其学术价值》、周惠泉《金代文集保存整理述要》等论文,论及《南宋文范》《金文雅》两部文选的体例、特色及价值,但对上述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作出深入的研究。
一
庄氏一生交游广阔,所交以江浙友人居多。其学术、文章,深受师尊顾曾及桐城后学的影响。
顾曾,字骏文,号校经草庐、少卿,江苏长洲人。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曾任博罗书院山长,又主修无锡邑志,课徒为业。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有《校经楼文集》二卷②顾承:《顾少卿先生墓志铭》,顾曾:《校经草庐文集》卷首,道光十九年(1839)蔡氏刻本。。顾曾是顾嗣立的曾孙,“承其家学,发为辞章”,“以文自豪,于历代诸家之作,无所不讨”③张士元:《序》,顾曾:《校经草庐文集》卷首。。时人称顾曾治学“邃于经,尤邃于史,其为文也少好庄周、司马迁”④顾承:《顾少卿先生墓志铭》,顾曾:《校经草庐文集》卷首。,“由欧、曾以上宗昌黎”⑤庄仲方:《映雪楼藏书目录》卷七“校经草庐文集二卷”条,清稿本。。顾氏称赏归有光“其言皆自经出,其理广远,其气沛然有余,以为亦去韩、欧阳也不远”⑥顾曾:《与陈贞白书》,顾曾:《校经草庐文集》卷上。。顾氏的宗法对象有庄子、司马迁、韩愈、曾巩、欧阳修、归有光等。顾氏还注重文以载道、经世致用,提出为文根柢“六经”⑦顾曾:《金文序》,顾曾:《校经草庐文集》卷下。、立言“本于德功”⑧林衍源:《顾少卿先生传》,顾曾:《校经草庐文集》卷首。等主张。庄氏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庆二年(1797)师从顾氏⑨顾廷龙《映雪楼藏书目录跋》称:“庄氏十五岁为乾隆五十七年,余高叔祖知惠州府为乾隆五十五年,岁暮卒于官,则公(顾曾)应庄氏聘当为五十六年。”这一说法有两处疑点。其一,庄仲方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五岁当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不可能为乾隆五十七年。其二,林衍源《顾少卿先生传》谓:“胥园先生(庄肇奎)旋升任广东按察使,君留数年,最契君。嗣因继祖母年高,弟超曾没,决意辞归。”庄肇奎于乾隆六十年(1795)升任广东按察使司。又庄仲方《映雪楼藏书目录》卷七“校经草庐文集二卷”条下载:“(顾曾)游南粤,先君子延课仲方,凡三年。”按顾先生的说法,顾曾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即离去,与林衍源所言不符。故庄肇奎延请顾曾当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顾廷龙:《顾廷龙全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181页)。,自谓由此得识“古文蹊径”⑩庄仲方:《映雪楼藏书目录》卷七“校经草庐文集二卷”条。。顾氏曾编纂南宋文选,并交副本与庄氏[11]顾承:《顾少卿先生墓志铭并序》,顾曾:《校经草庐文集》卷首。。庄氏编纂《南宋文范》时,凡弃取皆与师尊酌定[12]庄仲方纂:《南宋文范》卷首《〈南宋文范〉体例》其九。。
庄氏交往的桐城后学主要是姚门弟子。庄氏曾说:“予所交浙江汪君家禧、赵君坦、陈君善,江南则余师顾少卿先生及顾君承、吴君士模、姚君椿,皆有文章传世”,“最后乃交君(吴德旋)”。[13]庄仲方:《吴君仲伦传》,载《映雪楼文偶抄》(不分卷),清刻本。七人中,陈善、姚椿、吴德旋均与桐城派的枢纽人物姚鼐有或疏或近的关系。乾隆五十四年(1789)后,在钟山皈依姚鼐的生徒就有宜兴吴德旋、娄县姚椿等①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姚椿。庄氏与姚椿相交二十载,姚椿卒于咸丰三年(1853)春,庄仲方为其作《太学生姚君家传》。“余与君(姚椿)交二十年,知君负经世才思,有以自见,而所如不合,大不能用世,小亦不为世用,乃寓意于诗文,尝作樗寮生传,言其性刚多迕,不克得志,比于古之惰民”。两人的认识不晚于道光十三年(1833)。十六年(1836)姚椿为庄氏所编《南宋文范》作序。庄氏称姚椿“其经术文章皆足以匹望溪(方苞)”,对于姚椿尊崇宋学,“遍发濂洛关闽之书读之,悉弃词章训诂两家之言而一志求道”的学术取径也深为赞赏,对其“说经兼通汉宋”“论文必宗桐城”“酌唐之文以准宋之理”等主张,也视为“心平而论公”②庄仲方:《太学生姚君家传》,庄仲方:《映雪楼文偶抄》。。
庄仲方与吴氏族人交往也很密切。除上文庄氏提及的吴士模、吴德旋外,还有吴敬承。德旋是姚鼐弟子。敬承,士模子,师事吴德旋。最初,仲方从族兄宇逵处得见吴士模《泽古斋制义》,称许“荆川、震川之后罕有其俦”,士模感叹“有知己之感”,德旋也因此闻仲方名③吴敬承:《序》,庄仲方:《映雪楼藏书目录》卷首。。道光七年(1827)十一月,德旋应同邑友人程璋之邀到宁波,取道杭州,访仲方,“晨夕相与纵论”,称其学问“出于南宋诸儒,而咨之以宰物成务之方”④吴德旋:《序》,庄仲方:《映雪楼藏书目录》卷首。。前述江浙七名师友中德旋为最后相识者,则仲方与士模订交当在道光七年前。道光八年(1828),庄葆诚选授浙江新城令,聘吴敬承到官署课其子,敬承得便道过钱塘访仲方,数日后,仲方亦来新城回访。敬承说仲方“接其言论温温然,侃侃然,古之儒者洵无以过之”⑤吴敬承:《序》,庄仲方:《映雪楼藏书目录》卷首。。德旋自述“受古文法于张惠言,受经义法于族父士模,受诗法于仁和宋大樽,受书法于钱伯垧,而后以姚姬传为宗”,庄氏称其“先后交姚、张二先生,得其义法,遂自成家,不蹈袭一字一句”⑥庄仲方:《吴君仲伦传》,庄仲方:《映雪楼文偶抄》。。吴氏受业于张惠言、姚鼐,得桐城派古文真传。
庄仲方所交江浙文士陈善,与姚门也有关联。庄氏自述:“余寓居于杭三十年矣,相与励品学,论古文词,得汪君选楼(汪禧)、陈君扶雅(陈善)与君(赵坦)。”⑦庄仲方:《赵征君小传》,庄仲方:《映雪楼文偶抄》。陈善“独与同郡赵君坦、汪君家禧潜研经术,好为古文词。又从常州张皋文编修游,编修通经嗜古,尤精于易礼,著《虞氏消息义》以授君,君读之昼夜研求,尽通其义”。陈善从张惠言游,张氏开创阳湖文派,与桐城派刘大櫆也有师承关系。张卒后,陈善极力筹划其文集的刊刻,“使一千四百年之绝学一旦昌明于世”⑧庄仲方:《扶雅陈君家传》,庄仲方:《映雪楼文偶抄》。,其功至伟。
值得指出的是,顾曾与桐城派学人也有深刻的交谊,其《校经草庐文集》即请张士元、吴德旋作序。张士元,字翰宣,震泽人。工古文辞,师法归有光。与王芑孙、秦瀛、陈用光以学问相切劘,姚鼐见其文,亦拟之震川⑨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71页。。顾与张相识于嘉庆十七年(1812)锡山僧寺。顾出示《校经草庐文集》,求序于张。张氏与姚门弟子陈用光过从甚密。顾曾初识张士元,即邀其作序,自然与其名望、学术背景及取径等有较大的关联。张对顾也奖掖有加,称“其文之规格亦颇近尧峰(汪琬)”⑩张士元:《序》,顾曾:《校经草庐文集》卷首。。顾曾与吴德旋也是文友。顾喜吴文不乖背古人之文,引为知己。因而出示自己的文集,嘱吴作序。吴赞叹顾文之工,也有惺惺相惜之感,谓:“得顾子少卿于吴门”,“惜皋文已逝,不及见少卿相与上下其议论也。然千百载后,必有能知其所志之相合者。”①吴德旋:《序》,顾曾:《校经草庐文集》卷首。吴德旋先后师事张惠言、姚鼐,吴引顾曾为同道。可见顾曾与桐城派思想之契合,庄氏与桐城派可谓渊源有自。
庄氏与桐城后学的订交发生在道光七、八年间,此后结下终生交谊。庄氏断代文选的编纂、成书,也大致发生在此期间。庄氏与姚门弟子共同研讨问学,其文选的编纂自然也会受其影响。
道统观念、文统体系的构建与南宋文的价值,都是嘉道年间文坛的重要话题。庄仲方《南宋文范》及其他断代文选读本的编纂均体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回应,由此即可钩稽庄氏文章学思想与桐城派的离合关系,并对其理论价值作出分析与评估。
二
嘉道年间,面对汉宋之争,庄仲方倾向于宋学。他编纂《南宋文范》,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推崇宋学。
一是大量选录理学名家的文章。
庄书收录文章多于10篇者有24人。胡寅、彭龟年、张守(10),刘克庄(11),陈造、汪应辰、杨时(12),吕祖谦、王十朋(13),程俱、韩元吉、楼钥、文天祥(15),真德秀(16),陈亮(17),胡宏、张栻(18),汪藻(19),杨万里(20),陈傅良(21),李纲、魏了翁(27),叶适(30),陆游(39),朱熹(75)。庄氏兼顾南宋理学各个流派,包括金华学派的吕祖谦、事功学派的陈亮、叶适及陈傅良,不过从作品数量来看,庄氏对程朱理学显然青睐有加。24人中,杨时、胡寅、胡宏、朱熹、张栻、彭龟年、汪应辰、刘克庄、真德秀、魏了翁等人都是著名的道学家。
其中,朱熹文有75篇,为全书之冠。奏议(8)、传状文(3)、碑志文(10)、杂记文(12)、论说文(4)、书牍文(8)、序跋文(26)、哀祭文(2)、颂赞文(2)。8篇奏议大多与儒家伦理、礼制及礼法等相关,如《面奏庙祧札子》《乞进德札子》《乞修三礼札子》《禘袷议》《辛丑延和奏札》《戊申延和奏札》《天申节贺表》等。4篇论说文则旨在阐明理学思想:《仁说》阐发理学“仁”的精义;《观心说》以佛学对照,阐述理学的心性之学;《养生主说》则从“为善求名”切入,辨析道家哲学与理学在价值观及折中思想上的重大分歧;《井田类说》结合历代井田制的发展史,阐述儒家的政治主张。序跋文中也选录多篇与儒家经典论著相关的文章,如《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论语纂训序》《跋古今家祭礼》《家礼序》等。
至于其他道学名家杨时、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也收录了他们大量阐释理学思想的篇章。单以书牍文为例,庄书收杨时书信5篇,其中即有3篇阐发义理。《答陈莹中书》(其一)辨析儒、佛义理之别,以阐述坤复之意;《答陈莹中书》(其二)则发明邵雍理学思想;《答胡康侯书》讲解《春秋》正朔之意。
二是收录与朱子相关的文章。除了大量收录朱子文章外,庄书还选收与朱子有关的文章。例如,奏疏文中,收叶适《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刘光祖《乞留侍讲朱熹札子》;序跋文中,收何镐《书朱元晦杂学辨后》、欧阳守道《书朱文公与赵忠定公帖》;书牍文中,收张栻《答朱元晦秘书书》,陆九渊《与朱元晦书》《又与朱元晦书》(收入外编)。这些文章在《宋文归》《御选古文渊鉴》及其后的选本中均未收录。
三是对于朱陈之辩,只收录朱子文章。朱陈之辩,这场思想史上持续三年的辩论,是事功之学与理学的一次正面交锋,发生在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间。辩论双方陈亮与朱熹均留下与此相关的文献,但庄书有倾向性地收录朱熹的书信,对陈亮却付之阙如。庄书选录朱熹《答陈同甫书》探求义理与利欲之关系。相反,钟惺《宋文归》则收录陈亮《甲辰答朱元晦书》《与朱元晦秘书书》,不收录朱熹与论辩有关的书信。
庄氏对宋学的推崇,还体现在《春秋》三传的读本辑纂中。庄仲方对偏重义理的《公羊传》《谷梁传》情有独钟,辑有《公羊谷梁传文读本》。庄氏承袭宋代《春秋》学家胡安国所论“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之说,指出“其禆益左氏所未及”,对重训诂的《左传》加以贬抑。他认为,就学术角度而论,两者在义例评价上容有轩轾,但从为文角度而言,《公羊》的“隽宕”,《谷梁》的“精奇”已成定谳①庄仲方:《公羊谷梁传文读本序》,庄仲方:《映雪楼杂著》。。
庄氏尊尚宋学有其逻辑依据。他秉承师尊教诲,服膺孔子洙泗之学。其曰:“圣兴东鲁,群贤师之。原本六经,淫词衰熄。迨夫微言既绝,学者各得一偏,于是言议纷驰,至战国而加厉,得洙泗之传者,子舆氏而外,惟屈子、荀卿。”②庄仲方:《书〈周秦诸子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在庄氏看来,孔子学说根柢六经,为儒学正宗。其后,儒家派别分化,唯有孟子、屈原、荀子得孔子真传。至宋代,二程、朱熹发展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创立新学说。由上文可知,庄氏大力推崇宋学,即认为程朱理学传承先秦儒家孔孟之道,为道统之正宗。
庄氏尊尚宋学,但对汉学并不排斥。姚鼐也要求生徒为学兼宗汉宋,择善而从,并以宋学为归③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200页。。庄氏对姚椿秉承师训“汉学兼宗”之论也十分赞同。对清初汉学家胡渭的《大学冀真》给予高度评价,曰:“卷四以下为考定之本,引据精核,诠解亦不与朱子为苟同。”④庄仲方:《映雪楼藏书目录考》卷一“《大学冀真》七卷”条,清稿本。肯定胡渭的考据之功,对其坚持己见的学术勇气也深为赞赏。庄氏尊尚宋学,但不独尊朱子,他反对理学家固守门户之见。元胡炳文独尊朱子,编纂《四书通》,刊削赵顺孙《四书篡疏》与吴真子《四书集成》中与朱子相违的言论,并附以己说,庄氏目为“墨守一家之学者”⑤庄仲方:《映雪楼藏书目录考》卷一“《四书通》二十六卷”条。。足见其观念之开放。
虽然在道统的认同意识方面,庄氏与桐城派大致相近,均汉宋兼宗。但是,二者对道的内涵却有着不同的认识。
顾曾指出:“每谓德、功、言三者并重,立言不本于德、功,言为空言,而不适于用韩、欧阳文。之所以可贵者,盖有在矣。雕虫小技,儒者耻之不为也。”⑥顾曾:《校经草庐文集》卷首,林衍源:《顾少卿先生传》,道光十九年(1839)蔡氏刻本。《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曰:“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⑦杜预《春秋左传正义》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十五,清嘉庆二十年(1815)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在价值评判上,顾曾对德、言、功三者虽然无分轩轾,但强调德功并举,并将其作为立言的根本。即,言必须合乎儒家的伦理道德及有补于现实事功。顾曾对儒家“三不朽”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将以六经为本的儒家理论与匡时济世的现实事功纳入道的内涵。
庄氏秉承师尊经世致用的观点,并以此作为衡量古文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谓诸葛亮“东汉而上之,又非三国人文所能囿”,因其“初膺伊吕之寄,卒行周公之事,发为文章,综事经物”⑧庄仲方:《书〈三国文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称韩愈“真集圣之大成”,因其“气节政治并皆卓绝,发为文章”⑨庄仲方:《书〈唐文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赞赏金元好问、李俊民、麻革,也是因其“寄慨于麦秀黍离,以终完颜之局”⑩庄仲方:《书〈金文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而大力彰显南宋说理文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这些文章反映了南宋抗敌救亡的时代特征,表现出深刻的现实关怀。其实,注重现实,早已是唐宋以来从韩愈到欧阳修所开创的古文传统。
诚然,桐城派在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上都不排斥经世致用。不过,创作经世之文,并非其为文的最高目标。其中,方东树的看法最有代表性。他对古文家之文与经世之文严分畛域,认为二者高下有别。其曰:“(古文家之文)其道足以济天下之用,其词足以媲《坟》《典》之宏,茹古含今,牢笼百氏,与六经并著,与日月常昭”,“(经世家之文)以致用为急,但随时取给,不必以文字为工。二者分立,交相持世。”桐城派有此论调,与其重视文法、写作技巧等外在形式固然分不开,但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即,经世之文反映一时一地具体的现实问题,虽然有一定的实用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失去意义。方氏将其比作“布帛菽粟”,“今日之菽粟,非昨日之菽粟也;已敝之布帛,非改为之布帛”,“此随时取给之文所以不传于后世”①方东树:《〈切问斋文钞〉书后》,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卷六,同治七年(1968)刻本。。吴德旋更是明确表示,“论文必溯源于六经”,认为仅《孟子》七篇能传承六经,荀况、董仲舒、刘向、扬雄、韩愈,其著述“已不能无小疵”,柳宗元、李翱、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轼、辙,“皆不免刻意求工于文,而于古圣人所以自治其身心之理,未尝深求而得之”②吴德旋:《序》,庄仲方纂:《南宋文范》卷首。。他们将六经之道视为唯一真理,也就是将道限制在以六经为本的儒家伦理范畴之内。而文章须根柢六经,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力。基于这样的价值追求,桐城派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崇古倾向。姚鼐以“弥觉古淡之味可爱,殆非今世所有”③姚鼐:《与王铁夫书》,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9页。来评价好文章;吴德旋以“时之为”,即今不及古,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来解释南宋诸家“文不逮乎古”④吴德旋:《序》,庄仲方纂:《南宋文鉴》。的现象;而方东树以“道德泯然绝矣;而去古未远,文章犹盛”⑤方东树:《〈切问斋文钞〉书后》,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卷六。来评骘秦、汉。直至民初,后学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才首次明确提出文学应有“匡时”的作用⑥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卷一,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41页。。而嘉道年间,桐城文派尚固守狭隘的道统观念,未能以历史发展的眼观来看待文章与时代的关系。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桐城派将古文统系的边界置于明代归有光,并对南宋文加以贬抑的举措了。
三
文学流派都有争统序、见体系的做法。有论者指出:“姚鼐所构建的桐城文统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籍贯桐城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三代文士以奖掖、师承为纽带而形成的古文统系,可称为桐城文系;二是以唐宋八家为主轴,上溯先秦、两汉,下联明代归有光的古文统系,可称为古典文系。”⑦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103页。较之桐城派,庄仲方的文统观念更为开放,自上而下构建了从先秦诸子、两汉、唐宋以迄金元明的文统体系。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庄氏以先秦、汉唐、北宋为文章典范。就道统而言,庄氏尊尚孔教,称孔子“原本六经”,又视孟子、屈原及荀况为儒学正宗,但也不排斥法道两家,认为管子应有一席之地,而庄子则传承老子《道德经》的精髓。就文统而论,庄氏也推崇管子的“雄深古劲”、庄子的“恍洋諔诡”、屈原的“哀艳缠绵”及韩非子的“隽杰亷悍”,称四子“弁冕诸子”⑧庄仲方:《书〈公羊谷梁传文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提出“三代以还,文章莫盛于汉唐”⑨庄仲方:《书〈唐文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两汉又以西汉为高,“东都节义,轶于西京,作为文章,未之能逮”⑩庄仲方:《书〈东汉文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将司马迁誉为“文之圣”,“能知尊孔子者惟仲舒及迁耳。董文执圣之经,迁文抉圣之权”①庄仲方:《书〈史记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即强调董仲舒、司马迁为儒学正宗,董仲舒能坚守孔子之经,而司马迁则能极尽其变。认为唐代韩愈“以奥衍宏深之文冠冕一代”,“惟昌黎气节政治并皆卓绝,发为文章,汪汪乎继周孕汉,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真集圣之大成已”②庄仲方:《书〈唐文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庄氏看重韩愈有气节有政治才能,能将文章与教化合二为一。又提出“三代而后,文以汉唐为盛,继之者惟北宋”,对欧阳修、苏轼、苏辙、苏洵、曾巩、王安石六家推崇备至,同时也肯定其他北宋名家,认为他们各有所长。如韩琦、范仲淹、司马光叙事“纯粹”,周敦颐、张载说理“精深”,刘敞“高古奥博”,宋庠、宋祁兄弟“淹雅”,孔平仲、文仲、武仲三兄弟“博洽”,苏舜钦与章淳不相上下,沈括“出入蒙庄”,李觏工“粹于礼学”,陈舜俞“善策时务”③庄仲方:《书〈北宋文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
宗法秦汉与宗法唐宋,是明代以来已有的两种论调。庄氏与桐城派均主张兼取两派,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姚鼐发现吴德旋长期致力于《古文辞类纂》以学习文法,便劝导说:“子之论文主于法,是矣,然此学者之始事也,其终也几且不知有法而未始戾乎法。子其归而求之周、秦诸子及司马子长之书乎!”④吴德旋:《〈七家文钞〉后序》,吴德旋:《初月楼文钞》卷五,光绪九年(1883)刻本。桐城派认为秦汉文为最高境界,但因其“不可绳以篇法”,所以主张“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后可溯流穷源,尽诸家之精蕴”⑤方苞:《古文约选序例》,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4页。。唐宋文,就是学习古文的“津梁”。而庄氏认为“三代以还,文章莫盛于汉唐”“三代而后,文以汉唐为盛,继之者惟北宋”⑥庄仲方:《书〈北宋文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更是将韩愈推为“真集圣之大成”。在庄氏看来,韩愈为古文之集大成者,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文,在总体价值上已超出秦汉文。在文统意识方面,桐城文派同样显示出更为浓厚的尚古意识。
第二,庄氏认为唐宋以还,代有名家,可传承古文文脉。姚鼐则认为能接武唐宋八家的明代作家唯有归有光⑦张士元:《与姚姬传第二书》引姚鼐语,姚椿编:《国朝文录》卷四十二,咸丰元年(1851)张洋河刻本。,而方苞甚至认为古文自唐宋八家后,“失其传者七百年”⑧方苞:《答程夔州书》,方苞:《方苞集》卷六,第166页。。庄氏对南宋及金元明三代名家却不吝赞美之词(庄氏对南宋文的肯定,参见后文)。
庄氏认为金代大定、明昌、承安之间,梁襄、陈规、王若虚等人“足与南宋抗衡”;金代季世,则以元好问、李俊民、麻革为著,抒写亡国之忧;元好问则“雄才巨识,直欲上追龙门,而下启有元一代人文”,“足继八家”⑨庄仲方:《书〈金文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对元好问甚为推崇,称其上承西汉司马迁,下启元代文章。
庄氏对元文评价曰:“有元一代多宗紫阳,故言有范围,词无枝叶”,“若乃体无不备,学无不该,集一代之大成,继八家而无愧,其惟虞道园(虞集)学士乎?”⑩庄仲方:《书〈元文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在庄氏看来,由于元代宗朱熹理学,故合乎纲纪人伦,语言精炼。戴表元、郝经、王约、马端临、元名善、姚燧等各有所长,虞集则是一代翘楚,可与南宋文天祥、金代元好问并驾齐驱,为一代之集大成者,可接武唐宋八家。
庄仲方对明文则以一分为二的方式进行评判。他指出:“明之文才凡三盛,明之文格亦再衰。”首起宋濂、刘基、王祎等,“皆足自成一家,以焜燿于其间”,方孝孺“言以闽中之学,为眉山之文殿于后,譬之皎月中悬,繁星散锦”,此为一盛;李东阳、吴宽、王鏊等接武其后,王守仁“以出类拔萃之才,振兴弘正间,功则再造王国,文亦上继宋,方譬之泰华矗天,群山咸拱”,此亦一盛;嘉靖间,文体分化,赵时春、王慎中、唐顺之等“不为伪体所拔”,归有光“以集大成,譬之汉广江长,朝宗于海”,此又一盛。刘宗周、倪元璐、黄道周、黄淳耀,则“又明夷于末世,以持文运之终”。文格之衰,则发端于李梦阳复古之潮。嘉靖初,李攀龙“复祖其说,实皆剽窃而无心得,由是文体变而之衰”;其后公安三袁“矫前后七子之弊,以轻巧为宗,一新天下耳目。钟、谭继之。公安、竟陵之派肆行,学者恃聪明而不知学问,名为扶衰,其衰益甚,而国祚亦将倾矣。”①庄仲方:《书〈明文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李攀龙的假古董,及公安、竟陵的轻巧粗率,为文格之两衰。
总之,庄氏构建了清以前完整的古典文系。历代散文的发展呈曲线走势,先秦既是高峰又是起点,其后,汉、唐、北宋分别为三个高峰,东汉稍逊西汉,至三国魏晋南北朝为第一个低谷,南宋不及北宋,南宋及金、元呈下降趋势,明有三盛二衰,总体上走向衰败,为第二个低谷。每一个历史时期均有领军人物。先秦时期有管子、庄子、屈原、韩非子;汉代有司马迁、班昭,三国、魏晋南北朝有王羲之、李密、诸葛亮;唐代有韩愈;北宋有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南宋有朱熹、文天祥;元有虞集;金有元好问;明有宋濂、方孝孺、王守仁、归有光为文坛主将。其中,以韩愈为集大成者,“文圣”司马迁次之,韩愈以外的唐宋八家又次之,即以先秦、汉唐、北宋文为典范。可见,庄氏的古典文系边界与桐城姚氏有重叠之处,又有所突破。庄氏强调代有名家,对于南宋、金、元、明的重要作家也予以充分的肯定。
四
南宋诗文总体价值不高,系清人的共识。他们讥刺南宋文有“江湖游士叫嚣狂诞之风”,“讲学诸儒空疏拘腐之习”②纪昀等:《鹤山全集提要》,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391页。,认为“南宋文气冗弱,上不能望汉、唐、北宋,而下亦无以过元、明”③姚椿:《序》,庄仲方纂:《南宋文范》卷首。。当时论者主要就南宋文“文胜”或“理胜”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针对南宋“亡乎道学,其弊由于文胜”的观点,姚椿认为,南宋亡于君主不用道,而非言者不论道,南宋亡,不应归咎于言者。他指出:“以文载道之说,始于韩子,而欧阳子承之,至朱子而其道益光。同时诸贤,莫不质有其文,彬彬乎韩、欧之绪余也”,“道德之言,不专乎文,而亦未始不有其文。”对于南宋文,姚椿仅服膺朱子。至于南宋文选的编纂,他认为,南宋诸贤“才不逮前人,犹将过而存之,以为学者劝”④姚椿:《序》,庄仲方纂:《南宋文范》卷首。。可见,姚椿对南宋诸家的肯定仅在于传承道统方面。其实,也就否定了南宋文文胜于道的说法。
也有论者认为南渡诸家“理胜”,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南宋诸家“理胜而文不逮古”。吴德旋认为“南宋诸家,言理一衷诸孔、孟,然而文卒不逮乎古”。显然,吴氏反对理胜自然文工的观念,强调为文既要以孔孟之道为根柢,“言孔、孟所言之理”,又要讲究一定的写作技巧,“达之以荀况、董仲舒、刘向、扬雄、韩愈氏之笔”。这样,才可以拟制出“旨远辞文”的古文。他希望南宋文选在这个意义上得到借鉴⑤吴德旋:《序》,庄仲方纂:《南宋文范》卷首。。第二种观点主张理胜即“文不蕲工而自工”⑥吴德旋:《序》,庄仲方纂:《南宋文范》卷首。。吴县董兆熊尊崇理学,主张有理即有文,无理则无文。“天下有至文乎?天下之至理而已矣。不明乎理者,不可以言文。六经之书,圣人之文也”。在他看来,北宋文经欧阳修、曾巩后,几乎可并驾于汉唐,但理学并未大显于时。至南宋,朱子为理学之集大成者,“衍程子之传,独造乎孔孟之域,而其文斯超出于诸作者之上,而自为其一大宗。文至斯而极矣”,其他南宋诸家李纲、宗泽、叶适、楼钥、文天祥及郑思肖,其文亦“炳炳可传”⑦董兆熊:《序》,董兆熊纂:《南宋文录》卷首,光绪十七年(1891)苏州书局刻本。。
可见,桐城后学对南宋文评价不高,董氏对南宋文则推崇备至。这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两种看法。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庄氏虽然也认同南宋文“多散漫萎弱”①庄仲方:《〈南宋文范〉体例》其一,庄仲方纂:《南宋文范》卷首。,“深厚雅健,难逮东都”②庄仲方:《书〈南宋文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但他费二十年心力编纂《南宋文范》,即有彰显南宋文价值的深意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庄氏对入选者的时间上限、政治立场,入选作品的体式、特点等方面设定了明确的标准。
第一,限定入选作家的时间上、下限,以连接前后期的断代文选。这显示了操选者鲜明的古文史意识。《南宋文范》上承《北宋文鉴》,所录作家上及宗泽、李纲等北宋名臣,下迄谢翱、汪元量等宋代遗民。这是考虑到“南北宋间人,凡文鉴已选,即不列入。惟如元而不仕者如家铉翁、金履祥诸君子。苏氏虽采入元文类,兹仍选录,从其志也”③庄仲方:《〈南宋文范〉体例》其七,庄仲方纂:《南宋文范》卷首。。庄仲方对南宋文的总体评价,介乎姚门后学与董氏之间,持论不偏不倚,公允通达。他敏感地觉察出南宋各家的风格特征,并予以充分的肯定,魏了翁“撷经膏腴”、真德秀“说理切餍”、陆游“法度严整”、吕祖谦“文词宏富”、陈亮“才辨纵横”、叶适与陈傅良经制之学“可坐而言起而行”、文天祥“雄骏”。这些南宋名家“足以追踪北宋,为学者榘矱”④庄仲方:《书〈南宋文读本〉后》,庄仲方:《映雪楼杂著》。。与董氏重在阐发诸家文章的思想内容不同,庄氏兼重各家的审美特征。各家收文篇数如下:朱熹75、陆游39、叶适30、魏了翁27、陈傅良21、陈亮17、真德秀16、韩元吉15、文天祥15、吕祖谦13、罗愿9、曾丰2。除罗、曾二人外,收文均在10篇以上。庄仲方不持门户之见,将南宋名家纳入到唐宋八家以外的唐宋名家群体中。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有些文章不合其选录标准,但为了存人存事,或兼顾作品的接受程度而纳入外编。“文章虽未合选而或以人存,或以事存,或以人所传诵而存者,别为外编”⑤庄仲方:《〈南宋文范〉体例》其八,庄仲方纂:《南宋文范》卷首。。
第二,追求各体兼备。庄仲方编选是集,既参照以往选本的体例,又针对南宋文的特点有所斟酌,大致上反映了南宋文的整体面貌及价值。是集收录文体有50种,可分为14大类,分别为:1.诏令文(64):册文(1)、敕(4)、诰(1)、缴指挥(1)、批答(3)、赦文(1)、檄(1)、诏(28)、制(24);2.奏议文(328):表(58)、策(9)、策问(42)、对策(2)、笺(2)、启(41)、谥议(3)、议(6)、奏疏(163);3.传状文(19):传(4)、行状(7)、书事(8);4.碑志文(65):碑(6)、墓表(5)、墓碣(2)、墓铭(47)、神道碑(5);5.杂记文(100);6.论说文(124):辨(7)、答问(1)、讲义(2)、解(1)、进故事(11)、论(77)、史断(2)、说(18)、言(4)、义(1);7.书牍文(78);8.序跋文(198):题跋(102)、序(96);9.哀祭文(27):哀词(1)、吊哭文(2)、祭文(23)、送荐文(1);10.箴铭文(15):铭(12)、箴(3);11.颂赞文(25):颂(6)、赞(19);12.劝谕文(4);13.祈谢文(3);14.上梁文(8)。
对于不被其他文选收录的南宋碑志文,庄氏也并非一概否定,“择其雄浑遒洁者,存之以见其概”⑥庄仲方:《〈南宋文范〉体例》其一,庄仲方纂:《南宋文范》卷首。。《南宋文范》中收碑志文65篇,数量上为第6位。如陈亮《谢教授墓志铭》、叶适《故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黄公墓志铭》、陆游《吏部郎中苏君墓志铭》等,要言不烦,颇见遒健之风。
另外,《南宋文范》还收录少量劝谕文、祈谢文及上梁文等应用文体,以求众体兼备。其中,吴儆、刘宰《劝农文》、吴泳《劝士文》,高斯得《谕俗文》等劝谕文,以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恪守本分等生活理念劝导民众,体现了南宋时期理学思想世俗化的倾向。陆游《福州谢雨文》、王安中《大名狄梁公庙祈雨文》及王之道《和州含山县驱狼文》也是公文的一种,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及文化意义。
第三,重视“说理文”。庄仲方认为“南宋说理文最为明达,虽北宋犹未尽及,惟近语录无意为文者,皆不录”⑦庄仲方:《〈南宋文范〉体例》其二,庄仲方纂:《南宋文范》卷首。。庄氏不收“近语录”者,是宋代以来文坛的共识。是集收录的论说文124篇。数量上,仅次于奏议与序跋文。奏议、序跋中论说为主的文章本来就占很大比例。此外,书牍文也有不少议论的成分。其中,奏议类文章,尤重奏疏类,达328篇,为各类文体之冠。南宋的时代特征是抗战救亡,因此,忧国爱民、指陈政治得失,成为南宋诗文的重大主题。以论政、议兵为主要内容的奏疏,毋庸置疑也就成为南宋文中的主体。是编录有宗泽《乞都长安疏》《乞毋割地与金人疏》、李纲《上高宗十议札子》(10)、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刘黻《率太学诸生上书》、辛弃疾《美芹十论》之二《察情》等言之有物、说理明晰、情词并茂的佳作。这些文章继承了唐宋文人关心社会政治,以文辅政的传统,正是南宋文价值之所在。辛弃疾《美芹十论》之二《察情》、李纲《上高宗十议札子》(1),明代钟惺编《宋文归》也有收录。而今人所编《宋文选》收录奏疏类仅有4篇:宗泽《乞毋割地与金人疏》、李纲《上高宗十议札子》(1)、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刘黻《率太学诸生上书》。这些文章均录入《南宋文范》。
在庄氏编纂南宋文选的同一时期,董兆熊也在辑南宋文,但彼此并不知晓其事。《南宋文范》自道光十六年(1836)刊刻,流播应不甚广。江苏书局于光绪十四年(1888)刊刻庄氏《南宋文范》后,始见董书。董氏《南宋文录》成书于道光二十年(1840)。较之董氏《南宋文录》,庄书显然更有影响力。
清末民初,庄书引起较大的反响。成书于同治十三年(1874)的张之洞《书目答问》就收录了庄氏的《南宋文范》。该书自光绪二年(1876)初刻后,多次翻刻重印,流传甚广。坊间对庄氏《南宋文范》的需求大增,光绪十七年(1891)重刊是集。但由于庄书卷轶浩繁,不便于初学者学习。民国七年(1918),杭州张相在庄氏原编的基础上精选优秀作品纂成《南宋文范简编》,并出版。庄启传将姚、吴之论斥为“宗派之见,墨守过深”。他盛赞“朱子理学文章,无可訾议”外,还认为李纲、文天祥二人“卓然成家”,“李纲之奏疏,详密雅健”,文天祥则“著作雄赡”,较之汉唐、北宋名家毫不逊色。除了仲方赞赏的南宋名家叶适、陈亮、吕祖谦外,还补充了王十朋一家。认为南宋诸家虽有不足之处,然瑕不掩瑜,符合曾国藩论文“典显浅”三字,并称《南宋文范简编》“以示初学,取径最宜”①庄启传:《序》,庄仲方原编,张相选评:《南宋文范简编》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18年。。可见,半个世纪之后,姚门弟子贬抑南宋文的观念不再是文坛的主流意识。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发端于桐城派的湘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发展了桐城派的文章理论,论文力主“典显浅”。由于曾氏位高权重,湘乡派在清末影响尤深。南宋文正好符合这一观念,为时人所肯定。其二,以抗战救亡为主要特征的南宋文也适应了晚清的时代需要。因此,作为初学者的入门读物,庄书得到文坛的广泛接受。由此亦可见庄氏观念的超前性。
经晚清名臣的推许,庄书影响越来越来大。民国十二年(1923),胡适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也将庄书列入。庄书光绪本由林邦钧、赵仁硅点校,中华书局于1988年出版。郭预衡先生指出:“在《全宋文》《全宋诗》全部出版之前,当南宋诗文选本亦甚罕见的情况下,《南宋文范》仍是不可多得的一部重要文库。”②郭预衡:《南宋诗文的时代特点——〈南宋文范〉校点本序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12页。其后点校本又收入《中华传世文选》,1998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结论
综上所述,嘉道年间,庄氏的文章学观念与桐城派之间存在有合有离、合中有离的复杂关系。庄氏与桐城派均兼宗汉宋,以宋学为归。但是,由于秉持经世致用的理念,庄氏的道统观念更为开放,不同于桐城派将道统局限在以六经为根本的儒家伦理范畴内,还包括经世济民的现实事功。此外,在文统观念与文章价值观念上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与开放的道统观念相应,庄氏的文统体系也随之扩大,北宋以后的名家均纳入古文统系中,南宋文的价值也得到大力的彰显。桐城派则囿于狭隘的道统观念,自限门户,认为北宋后能传承古文传统的作家仅有归有光一家,对南宋文的价值未能作出公允的评判。庄氏文章学观念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庄氏尊崇宋学,对当时学术风尚的转变有推毂之功。扩大古文统系,一方面突破桐城派的古典文系边界,为彰显南宋文廓清了认识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取径渐广,也为散文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资借鉴的资源。而庄氏最大的贡献,则体现在对南宋文价值的抉发上。
由此可见,庄氏在当时文坛并未引起很大的回响,主要原因在于其理论观点与桐城文派的离合关系。对南宋文价值的肯定、推毂与鼓扬,及其上溯先秦、两汉、唐宋以迄金元明的古文统系,逾越了桐城派文统的藩篱。而桐城后学在嘉庆季执掌文坛,由于庄氏有着更为开放的“道统观念”,持论较为公允,而他本人又未成派别,更兼其学术宗尚的相合、文统边界的部分重叠等,均削弱其理论观点的尖锐性与冲击力。由此即可理解庄氏在嘉道年间不受重视的尴尬处境。但事实上,庄仲方的文章学观念在清代文章学乃至古代文章学史上应有其一席之地。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在考察某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不应囿于古人的观念体系,而应还原当时的历史状态,厘清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对各种理论观点进行价值重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