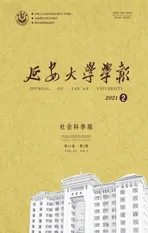论毛泽东的对美方略(1954—1970)
2021-11-29王悦之郭媛媛
王悦之,郭媛媛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毛泽东的美国观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但以往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重心基本都集中于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和1970年代尼克松访华前后。实际上,从1954年以来,美国对新中国深怀敌意,虎视眈眈,如何应对、处理和化解早已形成全球霸权的美国敌意,是中国长期无法回避的艰巨的外交困境和重大的政治课题。1954—1970年毛泽东的对美方略,蕴含着丰富的斗争哲学,对其加以解析,或许不无裨益。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的“破壁外交”
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果之一,是恼羞成怒的美国长期以来的外交方针都意在封锁、孤立和颠覆新中国政权。而中国方面,采取的基本方针则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不断释放善意,尽力缓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外交关系。相对于美国的“封锁外交”,中国的可谓是“破壁外交”。
这首先体现于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在处理中印、中缅关系过程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1954年10月,毛泽东与印度总理尼赫鲁有过四次谈话,同年12月,毛泽东与缅甸总理吴努有过两次谈话,表达的希望均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一个长期的方针,而且应该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针对周边国家比较忧虑的华侨问题,毛泽东也反复做了说明和保证。他甚至几次托付尼赫鲁和吴努传话给泰国,表示“我们是想同它搞好关系的”,[1]168最终推动泰国于1955年派遣了访华代表团。
对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毛泽东也多次明确表达了和缓的意图。1955年4月27日,毛泽东公开对印度尼西亚总理说:“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我想你们是不会反对的。”[1]2101955年10月,毛泽东对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说:“我也想到别的国家去看一看,甚至还想去美国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但现在却没有希望实现。”[1]2231955年12月,他再次对泰国朋友说:“美国同我们的别扭闹得最大,我们都还想同美国做朋友,就是美国它不干。我们想干,它不干,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等吧。”[1]2291956年4月10日,他甚至对丹麦驻华大使表达了学习西方的意旨:“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1]2341956年8月21日,他又对老挝王国首相说:“我们也愿和美国搞好关系。”[1]2441956年8月29日,他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还特意加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2]611
为什么明明感受到了美国那么强烈的敌意,性格倔强的毛泽东仍要面对国内外如此反复表达和缓的意图呢?对其中的原因,毛泽东也是反复明言,毫无避讳:“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战。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归根一句话,不打仗最好。”[1]168“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1]1871964年,毛泽东对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说:“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1]52920世纪前50年,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渐扩大,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希望,因此,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有着对国际和平环境的最真实和极迫切的需求,“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1]160正是这种最真实和迫切的需求,促使中共领导人不断释放善意,期待着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国家都建立友好关系。
二、消解国内人民的“崇美症”和“恐美症”
希望不是现实。表达美好希望的同时还必须面对冰冷的现实。尽管毛泽东面向国内外反复表达过对美和缓的意图,但他并未沉湎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也提醒党内和国内绝不可以“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3]相反,他对满世界(包括中国在内)流行的“崇美症”和“恐美症”,更是坚定而执著地力倡“破除迷信”论。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掌管着主要媒体,话语权笼罩的阴影下,在世界范围内都容易形成根深蒂固的“崇美症”。这种“崇美症”内在包含着两根支柱:一是价值观上的以美国之是非为是非,二是文明等级观中的西方优越论。但毛泽东认为这完全是迷信。在他看来,西方舆论有不少颠倒黑白之处,如美国媒体喜欢渲染中国“好战”和“侵略”,毛泽东常常表示他对此无法理解,“美国在中国周围布满了军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我们没有占领美国的什么岛屿,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1]532相比美国同时渲染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他也明确说:“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它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1]165毛泽东对此虽然无法理解,但他并不因此而怒火攻心,反而常常以一种戏谑的态度,对来访的外国客人开玩笑,自称是一个“侵略者”,比如有一次他就对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说:“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1]165他甚至还写过一首《七律·读报》:“反苏昔忆闹群蛙,今日重看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遍找全球侵略者,仅余中国一孤家。”[4]243这种戏谑的态度蕴含着无穷的嘲讽和蔑视。这是因为毛泽东对美国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2]163事实上,“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1]175
当时一些西方国家不仅抹黑中国,抹黑毛泽东,而且对一切试图反抗西方等级秩序的革命者都要抹黑。抹黑中国和毛泽东本人,他戏谑处之;但抹黑亚非拉地区的抵抗者和革命者,他则义正词严地反驳,“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1]248这是对反抗者和革命者的一种礼敬,是英雄惺惺相惜的一种表达,更是试图超越“霸权/反抗”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而构建一种新的精神谱系。
毛泽东认为:“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进行长期的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1]209针对“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的现实,毛泽东不止一次提醒亚非拉地区来访的客人:“它们喜欢说我们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我看也不见得,我们还干净一点。要有自信心,看不起欧美帝国主义,他们不算数。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5]382因此,他也颠覆了满世界流行的文明论,“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1]339
当然,所谓“破除迷信”并不是看不到差距,更不能等同于盲目排外,毋宁相反,“破除迷信”和“学习西方”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它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它们的设备等。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1]393-394因此,真正的“破除迷信”,并不是否认西方文明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上的先进性,并不是否认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是针对西方文明等级论中的帝国主义和东方主义,是针对亚非拉地区普遍存在的投降主义和奴隶主义。尽管他也深知,“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迷信不容易,它在一些人中根深蒂固”。[1]588但是,毛泽东从来力主,“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5]405
迷信不止一种。迷信不但带来“崇美症”,更加引发“恐美症”,“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1]411“过去我们有恐美病,要去掉它。”[6]386美帝国主义就国力而言自然是最强大的(尤其相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实际国力来看更是如此),因为它有原子弹,“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5]73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了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5]74
二战以后,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东方有韩国、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有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中东有土耳其、伊朗,非洲有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都不止一个基地,比如土耳其二十几个,日本高达八百多个。根据外交部提供的一份材料也可得知,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三千七百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四百五十七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开支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国防部开支在1950年代增加了246%还多,其中美国最大的五十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4]411毛泽东更加坚信美国确实是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必然要吃人的老虎,“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1]388但问题是,“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1]380“他们的处境,好像一个人用双手在桌子上捧起了一万个鸡蛋,顾东顾不了西,不是这个掉了,就是那个掉了”。[4]186故毛泽东的结论是,“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被一条绞索绞住了”。[1]348就此而言,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既是美国侵略性的证明,也是美国作茧自缚的一个困境。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个著名的论断,实际上是对“崇美症”和“恐美症”的双重迷信的大胆破除。断言美国的帝国主义性质,否认美国遍布全球建立军事基地的合法性,指出美国在全球各地进行政治干涉和军事侵略的邪恶性,提醒世界各地(不仅仅是亚非拉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必须关注美国军火工业的疯狂性以及超级霸权的危险性。断言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是大无畏革命精神的一种担当和表现,是对侵略者和剥削者在道义上的一种战略藐视,也是对一切受压迫者和受剥削者敢于反抗强权的一种殷切期待和呼吁。
三、国际统一战线的积极构建
1957年以后,毛泽东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谁怕谁更多一点,他的估计是双方都怕,但帝国主义要怕得更多一点。尽管他明知道美国真正怕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因为中国的实力相比美国差得太远,但是,“被压迫的人民就是要不屈服,就是要有志气”。[1]420在此之前,他曾对美国在中国周边布置了如此之多的军事基地表示过担忧,多次坦言我们怕的就是美国;在此之后,他反而发现,“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1]3741958年8月17日,他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你怕它也打,你不怕它也打,横直是要打,还是跟干部讲清楚,要打就打,叫做横起一条心,打烂了再建设。”[6]412在炮击金门之后,面临美国的核威慑之际,他再一次强调说:“每一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7]390
对于个性倔强的毛泽东而言,在美国尚未转变孤立、封锁和敌对的基本方针之前,他绝不可能通过乞怜的方式来获得美国方面的谅解,而只可能以坚韧的耐力和顽强的意志与美国斗争下去。问题是如何可能在这样一场实力相差悬殊的中美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的方针是,“我们对所有反帝力量都支持,同时他们也支持了我们,这是世界反帝力量最广泛的统一战线”。[1]418
构建国际统一战线的前提是斗争目标和基本原则的确定。值得注意的是,相比那些似乎更易实现的以实际利益为导向的短期目标,毛泽东明显更偏好那种看来有点好高骛远的以精神道义为导向的长期目标,而且从未牺牲后者以换取前者。比如争取美国的承认、与西方国家建交以及获得联合国合法席位等这样的现实利益,他总是表示“慢一点好”,从不迫切追求,以至于1956年来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因诚心期待中国尽早加入联合国而对此深感难以理解。[1]264但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行为,毛泽东则几乎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予以严厉谴责,早在1956年他就认为,“过去的侵略者是日本,现在是美国”。[1]2431960年,他又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1]4141964年,他更坚定地公开断言:“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8]1970年,中美关系已经出现缓和的契机和趋势,但因为美国阴谋发动了一场柬埔寨政变,他宁肯停滞中美关系,仍然义正词严发表了著名的“五二○声明”,表达对西哈努克的支持及对美帝国主义的声讨。[9]其实,早在1964年,他就说过:“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1]525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目标既明确又远大,“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从西太平洋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和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和大洋洲滚出去,从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地方滚出去”![10]就此而言,毛泽东是那个时代最坚定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士,他旗帜鲜明,在道义上获得了最广泛的响应、热爱和推崇,同时也被回报了刻骨铭心的仇恨,“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1]501
由于斗争的主要目标是美帝国主义,根据矛盾论的原理和中间地带理论的说明,毛泽东从未把资本主义集团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伴随形势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判断和应对。实际上,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一个隐秘的趋向,即美国以反共为招牌而加强对中间地带控制的战略意图,“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1]159尽管美国也知道团结的重要性,但美国人的团结是“在美国的控制下,在原子弹下面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缴纳贡物,磕响头称臣”,[7]581这必然引发独立意识和尊严意识比较强的国家的极大不满。事实果如其料,“有的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11]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了只有两句话的建交联合公报,这被视为“外交核爆炸”。[12]369中日两国政府的冷战氛围虽从未消解,但民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却没有中断。遍观毛泽东一生对外国来宾的接见,在资本主义集团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中,当推日本人为最。毛泽东对日本民族其实有相当高的评价,因为日本是亚洲国家中最先也是当时唯一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因此他多次表示了这样一种期待,“日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能让人来占领控制呢?日本必然会完全独立,成为和平的国家”。[1]373他也坚决支持1960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新安保条约》的斗争。他区别了日本垄断资本集团,早知道其中有部分人是不满意美国的,甚至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1961年,他热烈呼应了蒙哥马利将军的“三项原则”(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毛泽东看待问题的独到方式,基本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视野,从未陷入狭隘的民族国家视野或偏激的种族视野。在毛泽东那里,美国并非囫囵一团的庞然大物,而是由不同的阶级力量组合而成,“我们要区别美国人民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人民是好的,坏人就是帝国主义分子”。[1]401“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1]575这就意味着,毛泽东仅仅是美帝国主义的最坚决的敌人,他从来不想成为美国本身的敌人,更加不是美国人民的敌人;相反,他时刻关注着美国人民的动向,殷切期待美国人民的觉醒。1959年,他知道这还只是希望而已,“在美国人中间,虽然有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坏人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好人”。[1]366到了1965年,形势就开始大变了,“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对越南政策的示威发展起来了”。[1]570很快他就注意到,“美国本身也有广大的青年群众起来反对美国政府侵略越南的政策”。[1]574此后,美国人民以青年学生为主体抗议美国政府的越战政策的斗争也日渐呈现烽火燎原之势,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既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不仅如此,到了1960年代,美国国内的黑人运动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日渐密切。毛泽东曾两次发表公开声明对他们予以支持,一次是1963年应黑人罗伯特·威廉的邀请,一次是1968年针对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事件。两次声明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既揭露美帝国主义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又希望明确黑人运动的斗争方向,即不能把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看成是简单的种族斗争,是黑人反白人的斗争,要害在于,“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13]
对于毛泽东来说,那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天下大势,是遍布亚非拉地区而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是毛泽东对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礼赞和颂词。正是这波汹涌澎湃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浪潮,犹如三大洲的政治地震,让毛泽东看到了,“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过去是我们怕帝国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1]400毛泽东充分肯定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公开声言:“全世界任何地方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那里的压迫者的游击战争,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支持。”[1]5431958年古巴革命,他对美国附近的一个弹丸之地在两年时间内就有如此成效赞不绝口;1964年巴拿马运河事件,他马上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声援;1965年多米尼加政变,他大肆讽刺美国的所谓“自由”大旗不过是“江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
毛泽东对此的支持并不止于政治声讨,而且愿意尽己所能给予一定的财政援助。自1958年来访的源于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外宾日渐增多,中国自1958年开始对外援助的经费数额也是逐年增多,1958年2.76亿元,1959年3.50亿元,1960年3.63亿元,1961年5.19亿元,1962年8.54亿元,1963年9.61亿元,1964年则增加到12.16亿元,这一年的援外数已几乎相当于1950—1955年6年外援数的总和了。[14]1960年代,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中国方面多次对美国提出政治警告,毛泽东也明确对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说:“我们两党两国要合作,共同对敌。”[15]事实上,中国派遣30万军队守护北越,帮助越共训练军事人员,并无偿提供军援物资。据不完全统计,1962—1966年,中国援助越南南方各种枪支27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通信器材等;单1964—1969年,中国向越南南方现汇共计1.8亿美元。[12]35尽管1971年以来中美关系明显缓和了,但1971—1973年中国援越却进入了新的高峰期,签订了近9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协定,单军事援助物资就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16]正是这场持续十几年的越南战争,最终促使美国政府无论是在国内抑或国际上均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困境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对外援助,不仅不附带政治条件,一切体现平等互助的精神,有时甚至是无偿提供的。他常常表示:是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帮助了中国,缓解了中国的压力,因此中国有义务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
四、心照不宣的底线
尽管毛泽东从未惧怕过美国,无论是抗美援朝的战争时期,还是台海危机的紧张时期,每次美国企图用原子弹对中国进行核威慑之际,毛泽东反而展示出一种天不怕地不怕誓要决战到底的斗争态势,以致美国的核讹诈每次均落空。但是,通观1954—1970年这段时期,无论是在哪一个时间节点上,毛泽东其实并不希望再与美国发生战争。1960年5月3日,毛泽东接见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及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时,在进行主旨为“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的谈话过程中不露痕迹地夹带了这样一句,“你们别以为我们想和美国开战,我们不想向美国开战”。[1]400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实际上正是毛泽东对美斗争(不是战争,也不是缓和)的基本底线。我们可从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处理和应对上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1958年8月毛泽东决定炮轰金门,本意是“造成一种气势和压力,迫使蒋介石主动放弃金门,从而实现收复全部沿海岛屿的既定军事战略和安全战略”。[17]但这需要避免美国的干涉。实际上,炮轰前两天,叶飞向毛泽东汇报炮轰的准备情况,毛泽东最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当叶飞表示无法避免和不能保证时,他就沉默了。[18]炮轰之后,美国宁肯选择从中东抽身,也要大张旗鼓地调兵干涉。尽管9月3日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军委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规定了“我军陆、海、空不准主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我领海、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6]430但到了9月6日,毛泽东看出前天的杜勒斯声明是雷声大雨点小,他也希望“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6]439第二天,美军护航国民党运输船队,叶飞请示如何处置时,毛泽东的回答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叶飞再问: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泽东明确说:没有命令,不准还击。结果是解放军一炮轰蒋舰,美舰一炮不发,自己竟先逃之夭夭了。毛泽东立刻就明白了,“美国人也害怕跟我们打仗”。[6]452关键就在于这一个“也”字。10月13日,毛泽东在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特意加写了一句,“目前,美国人非常怕打仗,千方百计回避战争。当然,我们也绝不去碰美国人”。[6]464这很快就形成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底线:尽管两国都在战争边缘政策上盘旋,但由于早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交过手了,互相知根知底。因此,不管双方在舆论上的战鼓擂得有多响亮,彼此都不希望再发生直接的战争交锋。
这种心照不宣的底线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也有体现。尽管美国将战争逐步升级,对中国也有过试探,而中国同样把对越南的援助逐步升级,同时在国内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但美国却吸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其陆军从未越过北纬十七度线,而中国军队也就没有公开与美国直接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
五、余论
1954—1970年既不是中美之间的战争时期,也不是中美关系的缓和时期,而是一个特殊的斗争时期。但这并非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原初的和真心的希望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为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创造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然而,客观形势总比主观意愿强大,美国针对中共政权秉持的却是封锁、孤立和颠覆的战略意图。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提醒国内人民对美国要有清醒认识,且在世界范围内力主破除对西方的迷信,特别是要消解“崇美症”和“恐美症”。他以一种“不怕鬼”的斗争精神,坚决树立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大旗,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立分子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美国人民)的抗议,号召、推动和援助遍布亚非拉地区的革命浪潮和民族解放运动,由此构建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但通观1954—1970年这段特殊的斗争时期,中美之间仍然存在若隐若现且心照不宣的底线,即彼此都不希望彻底破裂而走向无可挽回的战争惨境。
毛泽东这种“斗而不破”的对美方略,使得毛泽东的形象在当时就发生了两极分化:一个方面,是毛泽东被刻画成不守规矩、无法无天的“好战分子”和“侵略者”;另一个远为深广的方面,如罗伯特·威廉早在1963年就理解了,“我为什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要求他发表声明,支援我们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因为我感到他深刻了解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最了解美国佬压迫本质的一位世界领袖。因为我感到他是最可能为黑人说话的一位世界领袖。我还感觉到,中国是作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一个新兴领导力量而出现的。我感觉到,这样做将使被压迫的美国黑人和非洲人民同中国人民之间建立起一座团结的桥梁。中国是诚恳关心被残酷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的”。[19]多年后,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之际说:“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20]
正是在后一方面的深远影响下,1971年10月,尽管美国照旧反对,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仍被“亚非拉的穷兄弟们”抬进了联合国。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以前所未有的谦逊姿态,完成了他的访华之旅,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相比于美国方面仅仅需要从越战的泥潭里体面脱身,中国当时面临的却是苏联扬言的核威慑以及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的巨大威胁,即使如此,在双方共同开启和缓大门的整个过程之中,再仔细对比品味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各种表现,我们就会明白,毛泽东不仅仅赢得了承认,还赢得了尊严和道义。这也印证了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时至今日,伴随中国经济体量的日渐庞大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势态,媒体和知识界又开始讨论有关“新冷战”的话题。虽然任何历史经验皆有其限度,因为时间的长河会改变各种主客观条件,所有按图索骥的企图都难免刻舟求剑的尴尬,但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毛泽东那种“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无畏精神和“斗而不破”的对美方略,依然值得我们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