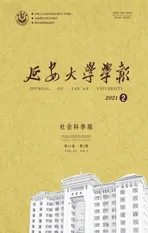未完成的启蒙:中国独立电影的边缘关注
——贾樟柯案例研究
2021-11-29麻菁文
麻菁文
(利兹大学 艺术、艺术史和文化研究学院,英国利兹LS2 9JT)
对阐释和解码的需求,来自于语言符号本身的不可信性。当人们面对意义明确的词语组成的句子时,阻碍他们确信自己已经成为这句话的真实读者的最大障碍就是根本的文化差异。这个差异在后殖民主义者那里被赋予一种对不平等的反抗精神,而在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这种差异又被或积极或消极地定义为大众文化的力量。本文对于中国电影文本的分析将在这样一种暧昧的氛围中展开:一方面,要保持对这些已经无法单一看待的后现代理论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始终与这些诱人的逻辑保持距离。文化研究作为理性学科在西方大学中的确立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其对中国学术领域的影响,发生在一个极其丰富的历史语境中:20世纪90年代中国消费社会的逐渐形成导致的文化沙漠让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对“现代性”的结果和“启蒙”是否在中国生效等问题进行反思,同时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随着全球化和文化交流一同涌入中国。电影的消费、文化和艺术属性决定了它的文本价值:电影语言的特殊性及其本身在文化工业中的显著性给我们提供了讨论空间,而它本身的纪实色彩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民族志来研究。
一、对话的意义:《小武》作为案例的契机
(一)“启蒙”作为文化研究概念的多义性
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看,很容易就能把“未完成的启蒙”与“文化霸权”相关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实际的文化交流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相对宽松开放的态度。一方面,让一大波知识分子感受到西方理性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狂欢化、碎片化的消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国,尤其是沿海发达城市蔓延。这股来自西方的文化氛围在很多方面加速了20世纪80到90年代中国这个历史场域中的话语碰撞。“启蒙”的祛魅在西方理论界已经经历了长久的论争,文明和愚昧的界限逐渐模糊。全球范围内的暴力、歧视和不平等问题并没有随着理性和科学的成熟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中。”[1]“未完成的启蒙”是一种解构性的、历史化了的文化状态。这种状态存在于置身世界民族国家之中的中国,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用西方的知识、文化、技术等等塑造这个国家和人民新面貌的每一次尝试中。这种尝试集中体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自由启蒙之风。之所以是“未完成的”:一方面,启蒙这个概念进入中国始终蒙着一层文化殖民的阴影,它本身的内涵和理论研究已经走向了一个无解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它一边要奋力的从殖民威胁和落后中挣脱出来,一边仍要直面势不可挡的消费挤压和大众文化的冲击。这两个过程在中国从五四以来至今的历史中从来都不是一种平行的历史过程,而是一个不断交织、对话和影响的未完成的话语空间。
(二)“边缘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异质性
本文所聚焦的边缘文化具有独特性。首先,这种边缘文化的主体尽管脱离了后殖民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注解,但仍然带着他们的魂魄。其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政治经济都迈向现代化的时期,边缘人物其实具有非常特殊的普遍性:由于社会制度的剧烈变化,曾经的合理正当变成了法外之境,原来的“大多数”瞬间就被视作社会害虫。这部电影中所呈现的边缘文化,实际上是启蒙意义上的“主流文化”。
中国独立电影或称中国地下电影,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定程度上受到屏蔽,并且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电影消费市场的一批电影创作。这些作品的导演大多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他们的创作方法和实践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西方系统的电影理论的影响。他们的创作风格受到巴赞的纪实主义的影响,强调对现实的艺术还原,常常使用非专业演员和隐藏拍摄来获取更自然真实的画面效果。这种纪实风格看似缺乏艺术感染力,实则更加强烈地展示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人文,也让这一时期的电影文本更加具有文化研究价值。这一批电影人承载着时代和个体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受到西式的精英教育让他们对知识和艺术无比向往;另一方面,他们失落的小城童年和现实中国被经济裹挟的精神荒漠让他们深感前者的不可实现性。实际上,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是永恒存在的,它的普遍性和适用性打破了主体、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只要是包裹在中国快速发展中的这辆列车上的所有文化景观都被深深地打上了这个烙印——差距和失望。(1)参见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页。
关注这部电影的原因是:首先,它反映了发生在中国落后地区的边缘人物的普通生活。其次,它所特有的纪实性,一方面,证实了中国电影人特别是艺术电影人在创作时一定程度的被西方电影理论所影响的事实;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以及结合导演的个人经历后所形成的创作风格让这部作品极具代表性。这种代表性主要体现在电影故事和时代的契合性上,对经济发展和人情淡泊之间矛盾的发掘,对现实琐碎的永恒存在与浪漫梦境的美丽瞬间的反差的呈现。
二、被代表的沉默个体:启蒙的多重悖论
个体沉默在媒体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更加显著。纪实性电影试图让镜头成为接近观众的或者成为大众的眼睛,而非知识分子的眼睛。然而,西西弗斯式的循环仍然存在:个体因为权力、不平等、贫穷、歧视等原因,即使大声呼喊也不会被大众听到。电影也存在于这个权力链条中。因此电影作为本雅明口中“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从诞生起就承载了言说和阐释权力的使命。
(一)边缘个体与时代进步——启蒙的背面
小武在电影中被塑造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他的失败和颓废与整个社会的欣欣向荣形成对比。观影者会把小武与电影中其他人物甚至整个社会对立起来,形成失败成功、边缘主流、善良凶恶等等看似合情合理的二元对立关系。但这种对立叙述是无效的,因为启蒙和现代性本身就处于一个趋向于脱离二元对立的话语中。小武的失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小偷的身份,爱情的发现和失落,友情的抛弃和背叛,亲情的残忍和坍塌。这些失败的个人境遇,实际上都被打上了时代前进的烙印。这句看似矛盾的话实际上是整个电影所要表达的关键:在发展中的现代化民族国家中,启蒙、进步、现代化与个体的命运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悖论?同时,这个悖论是由电影这个技术时代的大众文化产物呈现,它所展示的是被艺术加工过的具有主观性和趋向性的产品,而这个产品是知识分子主动或被动地站在启蒙立场上实践的结果。
“小武”们流窜于新兴城镇和落后乡村之间,游走在规则和法律的边缘地带。面对疾驰而来的改革剧变,他们的游离愈加清晰。这种状态之于社会进步大潮并不是主流,但却成为知识分子们的命题——知识分子具有着逆流而上的眼光和责任。这继承了五四以来形成的知识分子对小人物的关照和讽刺以启发这部分人的心智,例如鲁迅对狂人的书写,沈从文对边城人民的刻画等等。这些创作者本身就具有了启蒙性的话语特权,尤其是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对于农民、市民的刻画无时无刻不隐含着阶级的属性。
贾樟柯作为第六代导演,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鲜明的打上了独立、地下、深刻这样的标签。“贾樟柯的电影无论是拍摄方式、拍摄手法,还是拍摄内容、拍摄理念,都对传统学院式、体制化的电影构成了冲击。”[2]这个印象让他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处在一个极其尴尬的夹缝当中。对内,这种纪实性极强的影片难以通过当时中国电影审查制度上映,这也就客观上阻碍了这部电影即时走进大众的视野。贾樟柯本人朴实真挚的创作风格和严肃深沉的主题,与20世纪90年代高唱经济腾飞的时代风貌格格不入。在小武的接受史中,可以发现,无论是贾樟柯本人,接受电影的部分观众,或电影中的小武和生活中的小武,都处在巨大的沉默的空间中。在这个空间中,每一个集体都被代表着,他们的权力丧失在他们行使权力的瞬间。(2)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Penguin,1991:118.在通往社会进步的光明道路上,被遮蔽的是个体的隐忧和沉默,而这种遮蔽的状态并不是启蒙的意义。在理论的后现代世界中,这种看似混乱无序的状态似乎找到了它的栖息地。但这种短暂的狂热并无法给这个谜题找到更好的谜底。
(二)小武和小勇:现代性的两边-灵晕和权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上了全面现代化的道路。曾经暧昧不清的制度死角开始被匡正,曾经模糊的法律逐步健全规范,曾经拥挤的街道和破旧的房屋逐渐被拆除。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的城市给了小勇们站在镜头前扬眉吐气机会的同时,也让留恋旧时代习惯的小武活得更加艰难。这是一种双重的失衡和颠覆,无论哪种人,他们的人生际遇都深刻的被整个时代的洪流撕扯着。电影全部由非专业演员主演,他们表演时的青涩和自然都让观众对他们彼此的心理纠结感同身受。两人中间没有绝对的善恶、强弱、高低,即使一个是小偷,一个是知名企业家。
1.小勇:时代进步中权力错位的产物
小武的第一个长镜头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大黑框眼镜,叼着一根烟走上了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也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城市的场景。本雅明就曾在对波德莱尔的解读中提到过与陌生人同处一个封闭空间的独特感受。小武借着自己对这个社会的了解,如鱼得水的,甚至是洋洋自得的生活着。镜头切换,一群人围着墙上巨大的海报,然后是带有红色批注的海报的特写,以及伴随着的标准普通话的广播,内容对小武来说可以说是晴天霹雳:政府发布公告治理社会治安。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广播声,小武穿过马路,坐上了朋友的自行车。
而另一边,小勇做慈善被电视台采访,又是新婚,他自信从容地接受采访,与小武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是在广播的声音中仓皇逃走,一个是尽情享受着镜头的光环。两人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和职业经历(小勇曾经也是小偷),但此刻两人眼中的中国却全然不是一个中国了。小勇唯恐自己名誉受损,婚礼没有通知小武,小武通过第三人得知后坚持要按照儿时的约定给小勇“2斤礼钱”。一个沉默的长镜头第一次把小武和小勇纯真的内心展示出来:喧闹欢快的流行音乐衬托着小武单薄的身影,他站在热闹婚礼之外的一间空房里。小勇来后,两人坐下,小武不经意的一句“这是在干什么?”“我明天结婚”。打火机的声音随意的打断着两个人的情绪。他质问小勇隐瞒婚讯,最后一句“你就是忘了”,小勇答道:“就是忘了”。两人几乎要争吵,却怎么也吵不起来的时候,小武拿出自己带来的红包扔到桌上。
两人的表情在烟雾缭绕的灯光下无法辨别,空白占据了一大半。小勇面对小武与面对采访镜头时完全是两个人。电视台镜头下,他姿态优雅、慷慨大方。面对小武,他一口乡音,疲惫不堪。他承认自己忘了,他忘了曾经的自己,那个和小武一样的自己,只沉浸在此刻的成功中。电影对小勇的刻画非常有限,他在电影故事结构中不是主角。在导演的启蒙视角下,小武是不为社会大潮所改变的逆行者。尽管在法律、道德上小武一败涂地,但在质疑这种发展的合理性上,小武却充当了先锋。小勇的角色特征就在于,他没有被塑造成一个彻底被金钱名利所裹挟的反面角色。尽管他因为虚荣没有告诉小武自己的婚礼,但在真正面对小武时,他却还是承认了自己在情感上对小武的亏欠。他也只是一个意外被时代推上舞台的普通人,沉默是他们共同的宿命。他们都无法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语言,一个选择彻底的拒绝改变,一个在取得既得利益后茫然失措。
2.小武:承载灵晕的边缘角色
相比小勇,小武的形象被更加细致的刻画出来了。他虽然偷盗成性,却每次都会通过邮箱归还钱包里的身份证。他记得和儿时好友的约定,即使对方已经彻底忘记了彼此的情谊,也还是固执的坚守承诺。他一个人坐在餐厅里看电视上自己好朋友自信得意的图像。影片中小武不合时宜地坚持是本雅明式的传统艺术品灵晕的变体,复制技术为代表的社会进步不仅会摧毁艺术品的本真,同时也挤压着个体的情感。(3)Benjamin, Walte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photography . Screen, 1972:5-10.
这个镜头里,电视播放着小勇的慈善采访,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小武只能通过电视屏幕来看到对方。技术在某些方面的确改变了人类的情感,它让我们的感情经过了诸如电话、电脑或电视屏幕的过滤,人的声音、面容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电子化”。通过电话线和无线电波传到我耳边的你的声音,绝对不同于我站在你的面前时的感觉,人与人的对话在大多数时候变成了人与物的交流。借由一段点歌的语音,画面再次切到小勇的家,他目不转睛的盯着屏幕上为自己而播放的那首当年红遍中国的流行歌《心雨》,而坐在另一个时空的小武也通过电视分享了这首悲伤又甜蜜的男女对唱情歌。打火机的声音再次响起,打断了整个画面和音乐。这种后现代式的中断和转换,是贾樟柯在创作中先锋一面的尝试,它的先锋性体现在借由音乐对情绪和空间进行转换的尝试。
在这段被时代剧变阻隔的友谊当中,两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彼此的情谊,平淡而真实的感情在贾樟柯沉闷的镜头中缓慢地流淌着。长镜头耐心而迟钝的从人物的身体和他们所处的空间上划过,像纪录片一样平铺直叙的、去艺术化修饰的镜头语言让几十年的感情都融化在他们无法改变的现实生活场景之中。他们对彼此的牵挂和回忆无法改变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赋予他们的角色,所有前所未见的场景和新鲜的挑战都迅速的控制了他们的行动。
(三)纪实性:对启蒙话语的反抗-走向后现代
纪实性的镜头语言体现了导演对加工、改变、代替角色去言说的抗拒,他企图在一种冷静、克制的镜头语言下形成一个让角色自己言说自己生命的空间。“有一种完全不带感情的镜头,那种把客体从那些预先设定的关注方式中剥离出来的镜头。”[3]尽管如此,这个空间仍然是一个艺术空间,在搭建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风貌的过程中,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沉默也甘于沉默的小勇、小武们在这个善恶不分、只谈情谊的美学空间里,说出了仅有的只言片语。“他们拒绝寓言,只关注和讲述‘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同时,在他们的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是一种文化现场式的呈现,而叙事人充当着(或渴望充当)某种目击者的冷静、近于冷酷的影像风格。于是,摄影机作为目击者的替代,以某种自虐与施虐的方式逼近现场。这种令人战栗而又泄露出某种残酷诗意的影像风格成了第六代的共同特征。”[4]413这或许是本片对于20世纪90年代社会最深刻的寄语。在那个集体沉醉的时代,知识分子对五四启蒙精神和“文革”阵痛的回忆愈演愈烈,一场对现代性的重新评估,再次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集中到一个点上。知识分子们对现代性的痴迷大概就源自于对面前飞速运转的一切无法解释、对回忆中疼痛和美好交织的场景的痴迷。
贾樟柯对纪实性的坚持,和对时代生活场景的严苛还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那个时代本雅明式的灵晕的接近。他对人物的刻画不是速写而是水墨画,用详尽甚至冗杂的镜头原原本本的呈现人物在环境中的自然状态。这种方式合理的原因就在于:首先,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普通县城来说,最写实的场景和对话就是最魔幻和生动的戏剧,这是由历史的真实性决定的。其次,在第五代导演为获得国际声誉极力描写边地轶事和改编传统经典的大前提下,贾樟柯意识到这是一条脱离了中国“此刻”和“现状”的路。他的反叛是极具勇气的回归和探索,他的作品依然在国际上获得声誉,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现代性和国民性的冷静思考和呈现依然是具有美学价值和文化研究价值的。
要赋予普通人说话的权利是徒劳的,在所有被书写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中,他们都是被规范、被描写、被塑造的对象。知识分子在优越的启蒙使命下给那些“无意识”“未开化”的普通人戴上了枷锁和面具。他们的痛苦、无助和情感都在一种渴望被阅读的状态下呈现,而他们本身自我的欲望、平庸和真实却无法呈现。(4)参见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就在这种被疯狂挤压,又极度开放的时代空间内,知识分子和他们笔下的人物——现实中的普通人、无形的意识形态氛围,推动着中国社会现代性走向一个未知的后现代场域。这不是自主的选择或主动的迎合,而是历史般的无法拒绝的文化侵染。在一种不可逆的全球化氛围中,所有的文化和他们所处的环境都不由分说的被后现代主义理论归入他们的领域中。“事实上,在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交错映照之中,90年代的中国文化成了一个为纵横交错的目光所穿透的特定空间,它更像是一处镜城。年代在不同的、彼此对立的权力中心的命名与指认之上,在渐趋多元而又彼此叠加的文化空间之中,当代中国文化有如一幅雾中风景。”[4]381在这片迷雾中,一个更加无序的然而又更加集中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在这里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消费主导的文化生活没有留给它的享受者任何喘息的机会,那是一个更加拥挤也更加空白的地带。
三、在个体破碎中重建“新启蒙”
(一)小武们向消费时代的流放
现代性的未完成性体现在对个体欲望的无限压抑之中。在佛洛依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研究中,“自恋是自我意识和自我人格形成的必经之路”,[5]而这种自恋又来源于童年时期对母亲的依恋和对自我形象的认知。对于小武来说,这种自恋的精神是缺乏的,他甚至不能直视自己的脸,极度厌恶听到自己的声音。这是在一种极度扁平化的生活中形成对自我的屏蔽和压迫。这种压迫实际上来自于他的家庭,而家庭又是一个社会单位。
1.家庭的坍塌
小武给露水情人梅梅买的戒指最终转送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却将戒指当着他的面送给了嫂子。小武看到后大吵大闹,最后跟父母闹翻脱离关系,从农村家中离开。贾樟柯对中国农村家庭的刻画是直接而震撼的。梅梅的突然离开让小武想回到家中寻找一点温暖,然而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父母对他并不热情,甚至充满了责备和埋怨。他将失落的爱情本能的移情到母亲的身上,但他的情感却直接被母亲无视,这种失落感让他第一次爆发出了自己的情绪。在与父亲争吵离开家庭最后的庇护之后,他才真正地成为了一个游离在这个社会边缘的无所谓的人。这就是这个时代给予他的一切,这还尚不是法律对一个小偷的审判,而是他的全部童年回忆对他此刻的囚禁。这种精神上绝对的孤独是一种残忍的美感,他和这个漫不经心的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这也代表着他自我的彻底流放。唯一还能将他的肉体包裹的居然是那条充满冷漠眼神的街道,在流行音乐、汽车喧闹声中他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规则的圈套里。
2.身体的困境
最后他企图偷盗被抓获。警察局只有一间屋子,堆满了杂物。年老的警察是他儿时的启蒙老师,深知他内心的善良,在虚张声势的责令他戴上手铐的同时,也不失人情味的帮他打开了电视。电视上播放着广告,他仍在等待梅梅的消息,巨大的广告声逐渐占据整个房间,直到他手机短信铃声响起,老师念出了消息:天气预报,晴转多云。一位叫梅梅的小姐祝你万事顺意。这一刻开始,他差点被唤醒的人格又死去了。他的眼睛里再也没有因为欲望而燃起的活力,他的生命力就在此刻死在了通过现代技术传送的这条消息里。他眼前的自己又一次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躯壳,他为挣脱麻木的束缚而做的全部努力就在此刻功亏一篑。
片尾的小武蹲在一辆车流量很多的路边反省,最后一个镜头中,观众以第三视角,看着来往的人群走走停停观看他的表情和眼神,也可以看到小武自己的神情。这两种神情在表面上看来是有善恶优劣高低之分的,但一个5分钟的长镜头和特写镜头让人们看清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小武的遭遇,被作为罪犯放置在社会最底层的经历在本质上与路过的那些挑选今日食材的路人,与顺着社会发展机遇获得财富和荣耀的小勇并无差别。都是一双双被牵制和被生活挟持的眼睛。他们也和小武一样,刚刚听过港台流行音乐并像梅梅一样快速的迷上了其中最有魅力的一个,但他们从来不敢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们对自己的声音有本能的怀疑和排斥。这种排斥甚至让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音乐是奢侈的,遥远的。
(二)残缺的启蒙-精神恋爱的裸奔
消费社会中,两性关系的商品性质往往与性有关,但在这部电影中,小武与梅梅之间的交往却是一次单方面的误会。这个误会尽管美好,在本质上依然是冷酷的商品交换。这个事实在很多时候被小武忽略了,这也注定了他等待的徒劳。
1.无爱的消费时代
他们的相遇在一首对唱情歌中开始,在王菲空灵的《天空》中达到了精神的高潮,又在最高潮的时候回归开始的陌生。打工妹韩梅梅是拥有歌星梦想的歌厅陪唱女郎,她因为50块钱和小武外出,小武的朴实和木讷以及无意间流露的财力让她误以为这个人可以依靠,于是在50块钱时间结束的时候附赠了他一个吻。这个吻虽然短暂,但对于小武来说却是点燃他生命希望的火种。他从来没有过这种被需要和认可的瞬间。小武的单纯让他义无反顾的对这个刚认识的歌厅女郎付出情感和金钱。为了沟通方便他买了传呼机,整日等待,然而杳无音信。他去歌厅找梅梅时老板娘的一句话道出了两人关系的实质:你才给了多少钱,我又没给你看着她,你把她买了吗?他去看望生病的梅梅这一段以及后面他自己在公共澡堂中的歌唱是整个电影里唯一的理想主义片段。这种理想主义的存在和美化更加凸显了结局查无此人的悲凉和彻底的绝望。
2.告别理想主义:唤醒压抑的欲望
他和梅梅并排坐在床上,对面的墙上贴的是王菲的海报。她说要唱一首《天空》,在飘忽不定却持续不断的尖利歌声中,小武也许在思考为什么自己不能唱歌?为什么自己从来没真正的听到自己的声音。年轻女孩梅梅的梦想是无望的,她只能唱给自己。而这对于小武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拥有关于自己的想象。在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镜像效应”。[6]小武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和心灵中缺少了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恰好是他面前这个女孩拥有的。他在把自我交出去并对他人的强烈欲望感同身受的瞬间领悟到了自己人格的残缺和冷漠。这个过程在他的成长经验中是缺失的,他的家庭没有给他释放“力比多”的机会。(5)Freud,Sigmund,Theinterpretationofdreams.Robertson:Ritchie,1999:18.下一个镜头中,黑暗的公共浴室中赤裸的小武第一次在空旷的浴室中喊出了那首《天空》,这是他压抑许久的首次释放,也是他第一次直面自己的欲望。他的歌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身体空间的扩大,伴随着断断续续的声音,那空旷的浴室充满了他苏醒的自我意识和被压抑的冲动。
导演在这里想打破个体的沉默和僵硬,不顾一切的对着自己喊出一些声音,以感受到自我存在于世界之中的神奇。然而现实是,这种嘶吼对于小武来说只是一次偶尔的尝试,一次意外的冒险,他的意识以及对于生活的反应和对自我的极端否定,仍然是无法改变。他的麻木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但小武的这种麻木比起鲁迅笔下中国人的麻木又有不同。(6)Chow,Rey.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sexuality,ethonography,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56-68.五四时期鲁迅的批判是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以唤起人们对救亡的热情,而小武们并没有这样的忧虑,他们面前摆着的除了自我的人生道路以外没有更多集体的牵绊。同时,在消费社会中,一种跨越阶层的与金钱有关的平等关系让所有人都有一种错觉,这个错觉逐渐麻痹了他们对于自我置身于社会中的位置的真实感,同时也成为他们逃避某种时代潮流的出口。
(三)新的秩序:从小武们的毁灭说开来
小武们在中国现代性被探索的过程中成为主角的原因就在于消费时代让沉迷状态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拜物教、消费热潮让沉默的灵魂既不被自己听到,也很难被他人捕捉,所有人都被包裹进蜜罐中。小武和梅梅之间的错位就在于,梅梅已经彻底被物化了,她不仅将自己的时间明码标价,对于他人的评价也都按金钱来衡量。她的梦想对于她来说是迷幻剂,除了四下无人时轻轻哼起那些喜欢的歌之外,她的行为从来都不为她的梦想所支配,而是一股脑的冲向金钱和稳定。所以当她发现小武其实也没有稳定的工作,无法带领她在这个凭她自己的力量很难活的好的社会里扎根,她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他,甚至连告别也觉得麻烦。而小武从来都对别人的真心抱有一丝幻想,尽管他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仍愿意拿出钱祝福好友,也甘愿给一份虚无缥缈的感情投入自己最大的努力。他的全部行为都与这个时代匆忙的脚步,与高效率法制化的现代生活相矛盾。在与韩梅梅、小勇的对比中,小武彻底的被孤立在这个社会的外面,无论是从道德、情感和法律角度,这个人都失去了地位和做人的基本尊严。当他蹲在路边被迫接受陌生人一双双好奇、反感、同情、冷漠的目光的扫视时,他已经沦为了十足的动物,被限制着自由的同时,被剥夺着自尊。
如果说小武在电影中的沉沦只是启蒙在个体身上受挫并陷入未完成状态的一种方式,那么当作为文化消费者的大众在试图接受或者理解小武的时候,所强加给自己的启蒙地位则更加深刻的预示了这种企图的无意义。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些复制艺术无论多么真实,都潜在的隐藏着技术的加工和以技术为代表的权力的规训。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关于人物和镜头的情绪和感受都不可避免的要与他人分享,而这种分享虽然不一定以公开的形式展出却真实的存在于人们现代生活的日常中。启蒙的无力最终导致了一种开放的文化批判的建立,这种开放氛围在与全球化拥抱的过程中,把世界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只有走向世界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化、世界化。”[7]那些致力于寻找适用于全球的文化方案的理论家们诸如德里达从语音中心主义的偏见中试图探寻新的讨论空间。这个空间让所有的差异和不平等重新以一种多元和无解的方式出现并被讨论。他们仍是在对启蒙的反思中开辟新的方向。(7)Derrida,Jacques.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or,The Prosthesis of Origin,trans. by Mensah,Patrick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1.
个体对自我无形的压迫始终存在,这种压迫既存在于理性的对集体进步的追求中,也体现在无意识的反抗和挑战这种理性的活动中。主流文化所营造的整体气氛并不足以形成个体压抑的本能,更显著的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在关于启蒙和现代性的狂欢中所产生的张力和趋势。特定时期的边缘文化实质上是主流文化。于是,在语言和语音之外,在启蒙的幻想被彻底摧毁随即缓慢建构之时,一种秩序始终存在着,它声称可以到达平等对话的文化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