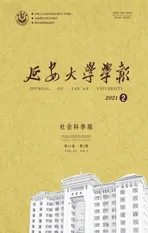从《新儿女英雄传》看延安时期“新英雄传奇”小说的生产
2021-11-29马海娟冉思尧
马海娟,冉思尧
(1.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2.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直接推动了新的文艺政策的确立,也催生和强化了新的主题类型和创作模式的生成。英雄叙事即是其中一例。其代表性长篇小说如《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都集中涌现在这一时期。这种借鉴了民间叙事和古代叙事模式而成的新型叙事类型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壮大于新中国成立后,对当代文学中的英雄叙事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研究者将这种新的小说叙事类型冠之以“革命英雄传奇”“抗日英雄传奇”“新英雄传奇”“革命新传奇”或“革命传奇小说”等。本文援引“新英雄传奇”来指称这一时期这一类型的小说创作。
从广义上而言,“新英雄传奇”属于“革命叙事”的派生物,是后者的拓展或延异。(1)参见王东《传奇叙事与中国现代小说》,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因其自诞生之初就和文艺大众化、建构无产阶级文学等宏大命题相关,深层次上更关涉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生成等命题,而备受批评界关注。20世纪40年代“新英雄传奇”小说兴起后,《解放日报》“书报评介”专栏随即跟进,对这一新兴文学现象迅速作出反应,肯定该小说类型对“旧形式”利用的积极意义和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后50—70年代是研究“新英雄传奇”的热潮期,研究者多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来肯定“新英雄传奇”的现实效用,对封建文艺的批判继承以及所呈现出来的解放区文学活泼、乐观的美学风格。研究方法的真正突破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如陈思和对“民间”的挖掘、董之林等从现代性角度对“新英雄传奇”的再审视,以及唐小兵从文艺生产机制、黄子平等从革命与传统等方面的“新解读”。但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50—70年代的研究成果,还是90年代以来的“再审视”“新解读”,多从宏观角度开掘“新英雄传奇”小说文本隐喻的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忽略了小说作为精神产品的特异性,以及从微观角度对“新英雄”类文学,尤其是“新英雄”小说生产的过程性考察。
如果把延安时期“新英雄传奇”小说的“前史”追溯至1942年毛泽东抄存的《永昌演义》,那么从《洋铁桶的故事》(1944年开始在《群众报》连载)到《吕梁英雄传》(1945年开始在《晋绥大众报》连载)《李勇大摆地雷阵》(1947)再至《新儿女英雄传》(1949),延安时期“新英雄传奇”小说较清晰地呈现了逐步探索“新英雄”叙事的痕迹。《新儿女英雄传》相较于其他作品,在叙事技巧、意义指涉乃至对五四“新文艺”的暗合,既是对“新英雄”叙事的要素进行了整合编码,又为“十七年”文学开创了可资借鉴的写作范式,极具代表性。本文主要以《新儿女英雄传》为研究对象,旁涉其他作品,拟考察作者选择这一叙事方式的动因,作者秉承《讲话》精神探索“新英雄”创作模式时对民间英雄叙事的继承与修正,以及寄托的对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解。须知《新儿女英雄传》对英雄叙事的迷恋并非个案,而是《讲话》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创作的共同倾向。以《新儿女英雄传》为例理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延安文艺的历史作用和跨入新中国后的发展演变。
一、“英雄”与英雄叙事的历史生成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英雄”不是一个陌生词汇。西方对“英雄”概念有清晰定义:
在荷马史诗里,英雄一词指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早期自由人,尤指杰出人物:在战争与惊险中出类拔萃的和珍视勇敢、忠诚等美德的超人。有些英雄的双亲之一是神……此外,英雄业绩不一定仅限于人世,其惊险历程可以引导他进入地府或神界。[1]
古希腊文学中半人半神的“英雄”概念,对西方文学甚至西方文化价值体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自由意志、勇气、力量、抗争精神、悲剧精神(2)对西方文学中的“英雄”的基本要素的归纳研究,参见张岩《英雄·异化·文学——西方文学中的英雄母题及其流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等是构成西方文学中的“英雄”的基本要素。英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卡莱尔在《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中,进一步将“英雄”细化为六大类型:神明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和帝王英雄,并充满激情地声称:“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地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物质的结果,也是他们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2]罗曼·罗兰在前人基础上发展的爱世界、为人类的文化巨人式“英雄”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更是风靡一时。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较早提到“英雄”一词的是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到魏晋时期“英雄”一词已广泛见诸于史书著述,亦有概念界定:“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3]见识、才智、勇气等亦是我国传统“英雄”观的基本组成部分,“英”“雄”兼具或偏“英”偏“雄”型“英雄”是古典小说中常见的文学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剧变,国人保国救世传统信念的影响,以及西学的冲击,人们更急切呼唤着“英雄”的出现。梁启超认为“英雄”和“国民”应当“粉身碎骨,以血染地”,也不愿受“异种人压制”,才有兴国希望。[4]至此,“英雄”增入了新内容——民族性和平民性。前者是从个人与集体的角度谈“英雄”应超越个人利害为国家、民族独立而奋斗,后者是扩大“英雄”范围提出英雄平民化、争做“无名英雄”。[5]23
五四时期,囿于思想文化革命激烈的反传统姿态,以及“平民文学”等新兴文学观念的倡导,“英雄”观及其“英雄”文学形象逐渐式微。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虽有呼吁“新英雄”及写“新人”、反映时代潮流的理论提倡,但创作始终落后于社会实践,亦没有贡献有价值的“新英雄”文学典型。再加之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的文人集团对“民族主义文学”及“英雄崇拜”的异化,也干扰了国人,尤其是文化界对“英雄”共识的达成。
待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亡国灭种的危机乃至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史,都急切呼唤新的时代英雄,以及英雄在符号化过程中彰显的榜样力量。而拯救民族、国民于水火的抗战也确实造就了无数英雄。他们出身平凡却行事传奇,出其不意,打击敌人,因陋就简发明地雷战、地道战、运动战、破袭战,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鼓舞了抗战士气,增强了民族信心。
“新英雄”的出现为文学提供了新的素材,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确立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座谈会后解放区对“穷人乐”方向的推动以及将“‘写真人真事’的理论与实践”“作为一种典范性原则而铺开”,[6]则为作家书写英雄提供了制度规范和理论支撑。周扬直言“真人真事”创作作为座谈会后的一个新现象,“是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工农兵走向文艺的良好捷径”。[7]502延安时期的“新英雄传奇”基本都是对英雄儿女们的真实记录或艺术加工。1944年边区群英会涌现了124位民兵英雄,《晋绥大众报》需报道英雄事迹又限于篇幅,报纸编委会让作者挑选典型材料编成连载故事,就有了《吕梁英雄传》;《李勇大摆地雷阵》也取材于李勇的真实经历,1943年5月11日,李勇在阜平五丈湾布下地雷阵,炸死日寇33人,事后晋察冀军区授予他爆破英雄称号;袁静在《关于〈新儿女英雄传〉的创作》中直言,正是对好友马淑芳革命经历的“同情和兴趣”,才引发了她想塑造这类“妇女典型”的创作愿望。[8]《新儿女英雄传》中杨小梅的原型张惠忠,原籍河北深县辛村乡北小营村人,13岁开始担任党员父亲的秘密通信员,经历七年“青纱帐”游击战。她擅使双枪且枪法精准,引导冀中百姓挖地道多次打退敌人扫荡,也在数次遭遇战里死里逃生。敌人对这位“双枪女八路”又恨又怕,多次试图截杀都以失败告终。(3)参见李红怡《“杨小梅”的昨天与今天——访〈新儿女英雄传〉女主人公生活原型张惠忠》,《民族大家庭》,1998年第6期,第29-31页。
二、“新英雄传奇”对民间英雄叙事的承继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工农兵成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对象。就文艺层面来说,肇始于延安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对民间形式的讨论,大生产运动中提倡推广的“劳模文化”对个人主义与“英雄”伦理冲突的解决,(4)参见田松林《模范文化与延安文学中的英雄叙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68-77页。《解放日报》副刊自1942年开始对“通俗故事”的青睐,(5)参见戴莉《新英雄传奇的发生学考察——以〈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为中心》,《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7-8页。以及轰轰烈烈的文艺下乡等,在解决文艺的创作主题、表现对象、创作风格等难题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导向了民间英雄叙事这一艺术资源。从这一角度而言,袁静和孔厥等作家对英雄叙事的选择,就不再具有偶然性,而是解决文艺大众化、探索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必然之路。
中国古代的民间英雄叙事上承古代神话。无论是远古时代女娲冶石补天保得太平,还是大禹治水终获成功,古代神话叙事模式多为:灾害降临——英雄抗争——消除灾害。凸显的不仅是英雄的事迹和胆识,更是“为了达到某种理想,敢于战斗,勇于牺牲,自强不息,舍己为人的博大坚韧的精神”。[9]对“新英雄”创作有直接影响的还有古代有关英雄叙事的文学作品。远至唐传奇,近至元明清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侠义小说等,种类繁多,流传极广。这些长期流传于民间、经文人加工整理的小说,在英雄叙事上有明显特点,主要表现为英雄群体化、注重故事情节的传奇性。以《水浒传》为例,梁山好汉虽主次有别,但个个都曾声震一方。整部小说以英雄群像为主体。故事情节注重传奇性,情节离奇或者人物行为超越常规。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多智、《水浒传》中宋江受助九天玄女等都在此列。
马烽和西戎从小熟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这直接影响了《吕梁英雄传》的叙事模式。当时有文学批评认为这些英雄们“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来的”,[10]144也有读者反映“老武像孔明一样,尽是耍计策”。[10]108袁静在回顾自己创作之路时也坦承从小喜爱《红楼梦》《水浒传》等经典著作,创作《新儿女英雄传》之前更是反复研读这些古典小说。(6)参见孔厥《下乡和创作》,人民日报,1949年7月13日。因此,《新儿女英雄传》从整体来看有古代神话英雄叙事模式的影子,仍是灾害降临(七七事变爆发,百姓逃难)——英雄抗争(党员发动群众抗日)——消除灾害(日伪敌军被消灭,县城解放),主体依然是借鉴古代小说的英雄叙事模式。
首先,小说塑造的“都是集体的英雄”。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青年农民牛大水和杨小梅的英雄事迹贯穿全书。其他人物叙述虽少,但同样都是英雄儿女。如“大扫荡”中被鬼子活埋的老排长冯国标,追击张金龙牺牲后仍保持射击姿势的赵五更,独闯申家庄深陷重围宁死不降的刘双喜等。他们殊途同归,各以自己的方式完成英雄壮举。当然叙说群体英雄也容易受到民间英雄叙事类型化的影响,有论者已注意到牛大水能从“张金龙,黑老蔡…当中清楚地分别开来”,但放在高屯儿和双喜等人中间就显得模糊,“他们是一个类型。小梅的情形也是一样”。[11]
其次,《新儿女英雄传》情节生动曲折。小说以牛大水和杨小梅的爱情为主线,两人的悲欢离合又和革命潮流紧贴在一起,虽然最后革命的胜利给了爱情完美结局,但中间过程可谓跌宕起伏。就爱情主线而言,牛大水和杨小梅相互有意却擦身而过,一度各自组建家庭,互诉衷肠建立关系后,杨小梅又不幸被捕险些遇难;就革命线索而言,牛大水与杨小梅丈夫张金龙既是爱情冤家,又是革命对头,两人数次交手,牛大水九死一生。惊险曲折的故事自然少不了传奇色彩的渲染。作品描述了大量抗日时期的传奇细节,这既包含对古代小说的借鉴,更有对敌后抗战无数惊险事迹的真实再现。这些传奇元素的加入凸显了英雄们在险峻环境中超凡的智慧和胆识,洋溢着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精神。但过度追求传奇性也使作品存在失真现象。如“大扫荡”中尹大伯掩护牛大水时,以耳聋蒙骗敌人,待其走后大笑,表现过于戏剧化。在动辄烧杀掳掠的“大扫荡”中,每一次敌人的搜查都是游走于生死之间。作者本意可能是想通过这一细节展现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军民鱼水情以及敌人的愚昧,却不符历史真实,损伤了应有的表达效果。
三、“新英雄”叙事模式的探索
延安时期“新英雄传奇”小说脱胎于古代的英雄叙事,但却与其有着很大区别。作家们依据《讲话》精神试图塑造的“新英雄”,是“那些经过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改造,并完成了这一改造过程的工农兵群众的代表人物”。[5]77和传统英雄相比,“新英雄”继承了“见解、才能超群出众或领袖群众”的旧有属性,又增加新内涵,呈现新特点。
第一,“新英雄”的身份。《讲话》确立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要求文艺必须服务于抗战,而抗战必须团结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体的工农大众不再是“启蒙”对象,而是学习榜样和宣传主体,甚至成了“启蒙”的主体。这样,从“五四”新文学延续下来的“启蒙”传统、对底层民众精神奴役创伤的揭示及劣根性的批判就不再适用于延安文学创作。因此塑造“新英雄”时就必须改变传统上“重血统、重师承”的特殊性(如《儿女英雄传》中的“儿女英雄”何玉凤便出身显贵,且有一身绝技),而注重其平民性,尤其注重其无产阶级的身份。因为英雄行事争议、成分复杂,会冲淡、削弱,甚至重新评判英雄斗争(革命)的性质。这是新文艺方针绝对不允许的。酝酿于1943年、成书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铁道游击队》,其作者知侠在了解“英雄”的原型都是“问题英雄”后,就依据自己对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解,对他们进行了大胆改写。
第二,“新英雄”的成长。“新英雄”来自最革命、也是最底层阶级,他们身上有革命的基因,但先进和愚昧并存于一身。“新英雄”的淬炼、成长不再自发自在(如关羽和武松,其成长经历各具特色,不受单一成长模式约束),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克服自身缺点逐步完成转变提升。周扬曾经就说过:“工农兵群众不是没有缺点的,他们身上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所遗留的坏思想和坏习惯。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以及群众的批评帮助之下,许多有缺点的人把缺点克服了,本来是落后分子的,终于克服了自己的落后意识,成为一个新的英雄人物。”[7]516-517《新儿女英雄传》中作者在第二回用了整整三节的篇幅来写牛大水和杨小梅如何受党委派到县上受训。党组织或政委、党代表对正面人物或高屋建瓴点化促其成长,或适时出现指导扭转时局。这一创作模式已超出《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英雄叙事小说,几乎涵盖“十七年”文学所有类型。
第三,“新英雄”的特性。经过主流意识形态改造后的“新英雄”,需要具备两个刚性条件:“一是大公无私,富有牺牲精神;二是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艰苦和困难”。[12]这两个条件虽脱胎于民间英雄旧有类型(如大禹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关羽刮骨疗伤等),但仍有明显区别。一方面,“新英雄”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如果公而忘私却经不住困难考验或有钢铁意志但公私处理失当,都不能称其为英雄;另一方面,“新英雄”的“身体”作为符号的功能被放大,“身体”成为区分敌我性质、衡量革命意志、争夺话语权和道德优势的主战场。肉体磨难是“新英雄”的“成人”仪式。《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杨小梅,《洋铁桶的故事》中的吴贵,《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等,无一不是公私分明、坚贞不屈。
四、“新英雄”创作对民间英雄叙事的修正与超越
陈思和认为,民间文化“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有着自己独立的传统和历史,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精华与糟粕并存”。[13]民间英雄叙事作为民间文化形态的一种,自然具备上述要素特征。但这显然与《讲话》后确立的文艺原则不合拍,因而作者在塑造“新英雄”过程中修正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地方亦在意料之中。
小说对反面人物张金龙的塑造就体现了这种修正。细究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张金龙具备草莽英雄的潜质:他不受约束、不事生产、有自尊心、广交朋友,有一手好枪法,还一度加入革命队伍。后来被开除,和其不愿受约束有很大关系。张金龙表现出的“自由自在”恰是民间文化形态的特性之一。他去县大队受训,“顺着他的劲儿,他就干,不对他的心眼儿,他就闹情绪”,[14]79回乡后带着一个班就拔掉了区小队极为头疼的斜柳村岗楼,却又贪图自在擅自驻扎斜柳村。作者通过塑造这样一位有英雄潜质的民间人物,展示出主流意识形态参照下民间英雄的两面性。在表现其抗争性的同时,更放大了他的危害,以凸显“自由自在的、民间意义上的英雄”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以及成为“新英雄”的必由之路。张金龙一意孤行终落得横尸野外,目的就在于警示英雄成长道路选择的唯一性:必须经过革命的“修正”,方能成为真正的“新英雄”。
隐性的修正则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衍伸出的革命伦理对民间文化形态中的传统伦理的规范。革命伦理以革命旨归为标向,是伦理高度政治化和革命化的结果,它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目的性,不是单纯的革命道德,还包括具体的服务于最终革命目的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等。(7)参见孙红震《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伦理阐释》,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新英雄”的成长过程也是用革命伦理进行自我规范的过程。如牛大水被捕遭受酷刑后,他从刚开始的怨天尤人到从“同志”那里汲取精神力量,咬牙挺了过来。引领其走出精神低谷的并非传统伦理,而是革命伦理。作者还借牛大水之口封堵了从传统伦理那里获得精神动力的可能性:“我刚才想些什么来着?我是个共产党员,我他妈的还不抵个群众啊?”[14]127在作者笔下,牛大水消弭了作为普通人应有的情感和来自传统伦理的影响,身体原初的生命意义、传统伦理的温情被摒弃,完全靠革命伦理唤醒生的意志,进而完成自身的淬炼与成熟。
家庭伦理是推动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当革命伦理与家庭伦理发生冲突时,作者就会毫不客气地让革命伦理消解置换家庭伦理。大水弟弟受了哥哥的影响加入了区小队。小说写到,大水集合队员研究如何打敌人汽船时,弟弟牛小水大呼“哥!我可有个好主意!”大水却“一脸正经地说:‘这是开会,什么哥不哥的!’”[14]71作者用喜剧手法展现了革命伦理与家庭伦理的冲突,以及家庭人伦在试图冲击革命伦理时受到的严厉规范。在两者的冲突中,阶级情谊才是唯一的情感联结纽带。
但若将袁静和孔厥若的“新英雄”写作仅仅理解为模式上的探索,就无法解释《新儿女英雄传》何以成为具有范式意味的写作模式,被新中国成立后的《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等“新英雄传奇”小说广泛借鉴。恰如黄子平指出的,“革命历史小说”以来自西方的“进化史观”取代了传统的“循环史观”,革命历史写作担负着“解释‘善恶堕赎’‘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等宗教性根本困惑的伟大功能”,以灾难或失败开篇“不仅仅是小说的‘话头’,从根本意义上说,更是革命的起点、历史的起点”。[15]《林海雪原》以“血债”开篇、《烈火金钢》从“史更新死而复生 赵连荣舍身成仁”开始等,和《吕梁英雄传》以“日本鬼兴兵作乱 康家寨全村遭劫”开篇、《洋铁桶的故事》从刘家庄被围开始、《新儿女英雄传》以“事变”开头等,就不再是巧合和模仿,而是讲述现代民族国家的起点。《新儿女英雄传》描摹普通人在抗战中从平凡儿女“成长”为英雄,也就不单是对现代革命战争中英雄事迹的艺术再现,而是呈现共产党如何通过“革命”启迪民众对自身主体及其主体性的认知,从而达到“成长”为无产阶级“新人”的目的。英雄叙事“当然不是描写到个人和社会的冲突而是要描写到‘集团’如何创造了‘新的人’,又创造了新的社会;这个写实主义的人物当然不能是个人主义的英雄,而是勇敢的有组织的服从纪律的新英雄”。[16]
《新儿女英雄传》作为《讲话》与“十七年”文学的“中间物”,就艺术层面来讲,在文学史上没有留下太多的亮色。但其开创性作用不可低估,新中国成立后的英雄叙事小说大多沿袭其模式框架。李希凡就曾在直言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儿女英雄传》等作品成就不高的同时,也认为这些作品在革命英雄传奇方面做了启蒙尝试。新中国成立后《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和《敌后武工队》四部长篇,“则更鲜明地展示了它们的特征”。[17]特别是《新儿女英雄传》中展现的“成长主题”和“生活化叙事”,更被广泛借鉴到其他题材的文学创作中。革命英雄主义在“十七年”文学中风行一时,亦可看作《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所掀起的“新英雄”叙事的极致化,以及其表征的美学风格和隐喻的逻辑理念被接纳认可的程度。由此可见《新儿女英雄传》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