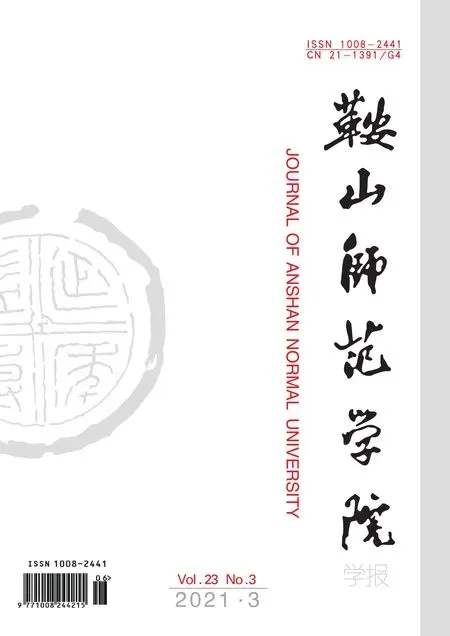《雪国》的音乐叙事艺术与自然色彩解读
2021-11-29邱田
邱 田
(沈阳音乐学院,辽宁 沈阳 110822)
《雪国》作为川端康成的代表作,由日本著名文艺片导演丰田四郎执导,经著名剧作家八住利雄改编,在1957年以黑白电影的形式首次登上了电影世界的舞台。电影本身以其韵律清晰的音乐叙事以及对自然色彩的巧妙把握,在音乐创作与电影艺术之间搭建了互通的桥梁。电影的起始,一列冒着滚滚白烟的列车呼啸而过,钻入漆黑的隧道后,驶进了一片银白的世界。导演用强烈的黑白色彩反差与壮阔的自然景观,将原著开头的场景描写还原得惟妙惟肖,将文学语言通过镜头的转换与对接,在呜呜的火车汽笛鸣响声中完美地转换成了影像语言。这部电影对音乐节奏叙述的把控以及自然景观画面的重视,与原作者川端康成对自然美、音律美的偏爱,以及日本大和民族深刻的文化背景所合流。同时对于影片而言,背景音乐就像含情脉脉的电影语言,在细语呢喃中构成了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细微之处都恰如一道道涓涓细流,通过光与影的交错,点点滴滴地刻在我们的心头。本文以电影《雪国》恰到好处的复调音乐叙事艺术与绚丽多姿的色彩意象解读为基点,展开对其影视音乐实际应用的讨论。
一、东方文化的“风花雪月”——自然和谐的音乐底色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在他的颁奖致辞《我在美丽的日本》中,以“雪月花”这样一个带有明显朦胧美感的词来概括他心中日本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这种评价在凸显了唯美与感伤文学情绪的同时,强调了自然在日本古典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在日本的文学传统中,对自然景致的尊崇与体悟是日式美学发展的基础。从自然风物的生长状态体悟人生的美感与文化意义,将自然景物的枯荣沉淀为具有民族共性的审美意识,这是日本文化宏观层面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文化观念。而从民族文化心理角度思考,川端康成也早已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广袤的大自然是神圣的灵域……凡是高岳、深山、瀑布、泉水、岩石,连老树都是神灵的化身。”[1]这种将自然事物作为神灵崇拜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根据生命欲求的本质而得来的。亲和自然、崇拜自然的传统观念自然内化成为日本大和民族“自然崇拜”的深层文化心理。在电影中,这种对自然的崇拜与热诚同样得到了影像文化的继承与再创造。
在《雪国》中,岛村第一次到访雪国村庄是在盛夏时节,处处都是植物生长发芽的绿意,山顶的积雪变得只有薄薄的一层,大自然在向原住民和旅人散发着温和的善意。就在这个时节,他结识了驹子,在温暖的地炉旁,在驹子娴熟的三弦琴和弦声音中,最终灵肉相交达到了双重欢愉。对于岛村来说,驹子是纯真与自然的化身,正当岛村步入迷途到访雪国、思想深陷在虚无缥缈之中,驹子走了过来,就像带来了热和光。这种冲击,在驹子为岛村弹奏《劝进帐》的曲子时,在艺术对感觉的强化作用下,达到了高潮。岛村当时的反应是:脸颊起了鸡皮疙瘩,一股冷意直透肺腑。在他那空空如也的脑子里充满了三弦琴的音响。与其说他是全然感到意外,不如说是完全被征服了。他被虔诚的心打动,被悔恨的思绪洗刷。他感到已经没有力气,只好愉快地投身到驹子那艺术魅力的激流之中,任凭它漂浮激荡。[2]为什么这一曲能让岛村产生如此大的反应?川端康成给出了解释:“因为驹子总是以大自然的峡谷作为自己的听众,孤独地练习弹奏。久而久之,她的弹拨自然就有力量,这种孤独驱散了哀愁,蕴含着一种豪放的意志。”在这样的场景下,三弦琴悠扬的音色融合了人物的意志与自然的美感,构成了《雪国》以自然和谐为底蕴的音乐基调。
三弦琴作为日本大和民族的传统乐器代表,其声音细腻柔和,其意境悠扬辽远;既适合村民围炉夜话时乐律在笑声间汩汩流淌,也适合舞台开演时的阳春白雪。《雪国》影片背景音乐将三弦琴演奏作为其配乐基调,从文化审美因素上来看,与东方文化体系中自然和谐的价值表达不谋而合。而作为与丰田四郎合作多次的日本三大作曲家之一,团伊玖磨将其音乐艺术追求中对于东方文化美感的强烈喜爱灵活运用于电影配乐中,为《雪国》构筑起了层次多元、感官丰富的音乐疆域。在歌剧艺术与交响乐曲调交相辉映的创作中,团伊玖磨的音乐叙述具有强烈的张力。尤其是经历了多年来的与中国音乐界深度交流,东方文化的和谐美深深地烙印在了团伊玖磨的诸多艺术作品中。通过对三弦琴、日本琵琶等古典日式乐器音长、和弦、频率以及其共鸣模式的调整,团伊玖磨使乐曲作为电影情节起承转合的要素翩然飞舞于电影全程,在自然和谐的琴声中融入了其中正平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这无疑与电影原著作者川端康成所提倡的自然文化美感与东方文化观念形成了同调共鸣,为电影增色颇多。
二、黑白构建的“雪国风姿”——音色共鸣的色彩表达
作为川端康成文学作品影视改编的经典之作,电影《雪国》曾两次登上电影荧幕,一次是1957年由丰田四郎执导的黑白电影,另一次则是1965年由大庭秀雄执导的彩色版本。正如德国电影理论家鲁道夫·爱因汉姆所指出的,黑白电影更能够“使画面形象背离自然,从而有可能利用光影来构成含义深远、格调优美的画面”[3],在黑白之间,才真正弱化了画面光感度与影视特效的影响,凸显了音乐韵律与故事情节对于电影本身的推动作用。基于这一点,本文所讨论的是黑白片为底色的1957年版本。作为20世纪上半叶日本著名的文艺片导演,丰田四郎在几十年间将《夫妇善哉》《地狱变》《恍惚的人》等多部日本经典名著搬上了电影大银幕,在同一时期的日本导演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文学作品的电影化一直是电影世界里的一枝奇葩。文字艺术与光影艺术的结合共生,并不是简单依靠剧本构思与单纯复制就能够达到的,在这一方面丰田四郎始终孜孜不倦地找寻电影文学化文艺化的平衡点,这种尝试与探寻在电影《雪国》中尤为明显,在音乐与色彩的绚丽飞舞间融合一新。
色彩,在光影世界里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视觉特效与虹膜反应,它在剧情的推动、气氛的渲染和情感的表达层面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音乐的融合下,可以起到渲染场景气氛、烘托人物性格、延拓故事发展等重要作用。电影《雪国》的整体色彩布局集中于雪一样纯洁的白色上。从影片开头那段雪山环抱下轰鸣前进的火车让人联想到原著开篇的名句“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赫然一片莹白。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这种无色彩的色彩表现方式,带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白茫茫的雪色。也是由此开始,大片大片的白色积雪贯穿于电影剧情的每一个重要场景。随着主人公感情的增进与浓烈,电影的色调在不断加深,在单一的雪白之外勾勒了浓重的感情色调。在岛村与驹子分别的场景中,镜头定格在飘飘洒洒的飞雪下,身着黑服的岛村与红色外套的驹子在屋檐下回首凝视,三弦琴的透亮音色映衬下主人公炽热的情感宣发得淋漓尽致。黑、白、红三色在近景画框中相交融,自然的柔美、岛村的阴暗与驹子的热情交织在雪中,令观众印象深刻。而驹子为岛村表演的室内,黑色的框分割了整体的室内空间,窗外不远处辽阔的雪山色泽厚重,黑白分明的轮廓延伸到室外,构成了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空间。窗外的夕阳照射在地炉的钩子上,驹子红扑扑的脸庞与暗色的室内象征着情欲与生命力的升起与消退。色彩的迥异与变化引发了观众不同的视觉情绪,在情节舒缓的段落,雪色的纯洁让人感受到山川的静美与爱恋的纯洁;在结尾部分的雪中火灾,镜头从一个雪堆成的拱洞向外推进,明亮的火把与燃烧的光亮映照了整个屏幕,随之而起的急促的琴声与太鼓的精准运用,在音色融合之间使观众能切身地感受到电影情节的紧张与紧迫。
《雪国》作为一部对“美”的颂歌与哀歌,在人性的污点下,人生静美的主题与色彩世界的映衬密不可分。驹子的人物形象在整部影片中是一抹鲜亮的红色,她面部的红晕与服饰的色搭,在原著与影片中都着墨颇多。在对人物色彩的解读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妩媚、纯真、野性而热情的少女形象层层铺开。她虽然沦落风尘成了一个娼妓,但是她仍然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对爱情的美好向往,而与之相称的是热情洋溢的三弦琴音。作为音域广阔的日本传统弦乐代表,三弦琴的变奏与驹子跌宕的人生经历相呼应,在冷暖色调交集之间描绘出了女主人公的别样人生。与此相对应的是始终身着黑衣的岛村,阴暗的色调始终笼罩在他的心灵世界,作为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画家,他是影片中恶的一面的象征,在肉体上的占有之后,欺骗并玩弄了驹子纯洁的感情。岛村出场时低沉的琴鼓声极具传统日本民俗音乐的特色,完美衬托出了男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但岛村身上的黑色是一种虚像映衬,整个影片所要突出表现的是雪白的纯洁与红色的生命,这完整地展现了原著蕴含的对生命的思考、自然的敬畏与唯美的追求,与日本传统文化下富有艺术美感的文化追求所契合。电影《雪国》所勾勒构建的色彩世界并不以颜色的斑斓制胜,而是以色彩的设置为情境切入点,在节奏分明、腔调明朗的音乐融入下,将鲜明的人物性格与明确的思想主题以柔和的方式呈现在观众的视野里。
三、光影世界的“镜像再生”——音乐表述与电影艺术的互通互融
自电影文化诞生以来,文学作品的电影化与再改编就成了影视园地里一支光彩夺目的玫瑰,长盛不谢。然而,在影像艺术和传统文字之间仍然存在着诸多难以逾越的藩篱,在这种具有时代背景的文化困境下,音乐叙事艺术的合理应用作为一条具有创新性质的影视改编要素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密切关注。在音乐与色彩相互融合的勉力加持下,电影《雪国》巧妙而生动地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小说原著的情节场景与文化美感,川端康成的美学理念与文化诉求就像是一面镜子,在摄像头与文本之间穿梭,延展着镜头中不断变幻的景与人。在影片结尾的雪中火这一幕中,静穆的银河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岛村渺小的身影,这面镜子在迥然不同的视角间无暇地切换着,在呜呜咽咽的琴声与箫声中,一瞬之间是旺火燃烧下的雪村凄美炽热的场景,一瞬之间是苍茫大地上驹子向前奔跑的小小身影,在音韵交错、光影变换之间,让人联想到群星闪烁的荧荧银河与星光闪耀下的殷红裙摆。弦乐的交织,颜色的对比,透出简洁流畅、凄美哀婉的美学风格,通过视觉感受传递给观众以精神世界的慰藉。这与川端康成在创作方法上所提倡的重视感官感觉的意识流创作手法接轨并合流。
在电影《雪国》中,无论是对朦胧恋情的美好向往,还是对逝者思念的婉转表达,都能够通过音律转承的叙事节奏来进行完美演绎。三弦琴音色悠扬,琴弦的音色含情,表现力丰富,能较好地反映人的情感。太鼓的增强与共振使发音明亮与暗底兼备,干净圆润,光彩柔和。配乐的时机、时长和强度则通过剪辑,对电影的 “传情”与节奏的推进起了决定性作用。电影中多次在没有对白的空旷场景中,借音乐表现环境、氛围和人物的内心,以色彩传递无声的价值表述。一方面来看,感性的声音传达了丰富的情感,使抽象的感情如同音乐美感一样呈现出具象化表达,使整部电影都沉浸在导演有意营造的氛围中,让观众不由自主地形成情感共鸣;另一方面,音符在表意方面也给观众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去感受和想象,在有限的语言表述之外给观影者以无限的文化想象[4]。
音乐的细腻表述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抒发文学作品原作者的艺术理念与文化诉求。在影视作品光影结合的“镜像再生”世界中,音乐转换对于影片叙事的艺术价值不可替代,尤其是对于《雪国》这类故事情节相对松散的作品而言,背景音乐的合理运用从根本上组织起了全篇的叙事结构。电影的原著《雪国》是川端康成自称以“随心所欲发表法”洋洋洒洒成篇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的整体创作践行了他所提倡的“新感觉派”的艺术特质,将意识的流动和光影的浮动作为作品架构的基点,重视感觉与情绪的抒发表达。《雪国》讲述的故事以《暮景之镜》为缘起,以《雪中火灾》一部单章作为结尾,在1934年末直至1948年末长达14年的创作周期内,分散发表刊载在多家杂志社上,这在川端康成本人的创作史上是很罕见的。从故事情节的角度来看,整部作品结构松散,舒缓平淡,散文化的不固定的结构为本作的电影改编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针对作品的文学特性,镜像思维的渗透与音乐色彩的有机组合,为影片的叙事角度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切入点。影片开头在拍摄火车越过隧道运动的镜头时,有意识地采用电影“叠画”处理手法,采用定格化画面的摄影手法,将每一个停顿的瞬间从连续的时间轴内抽取出来,强调了视觉“穿越”意义。同时导演将电影中有流动感的、悠缓的时间推移及与之伴随的音韵辗转变换,以连续的镜头构建影片的时空结构,保持了原著松散情节下故事的流动性和艺术性。这种改编强调了重视影像文化中视觉与听觉的优先级,最大程度上还原并再创了原著情节场景的流动感与美感。
川端康成的创作始终带有明显的日本传统美学文化印记。在此基础上,他吸收了西方现代美学的表现手法,以注重感官表征的文学表达,鲜明的色彩对比以及崇尚自然的美学体验对日本本土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贡献。而电影《雪国》在最大程度上秉承了原著作者川端康成的美学思想,以和谐婉转的音乐叙事与相辅相成的色彩解构,歌颂了生命的壮丽与人性的静美。在文学史意义上,为文学名著的电影化和再改编提供了参考,为音乐曲调在文化领域内的灵活运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优秀范例,同时在电影艺术史上也形成了持久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