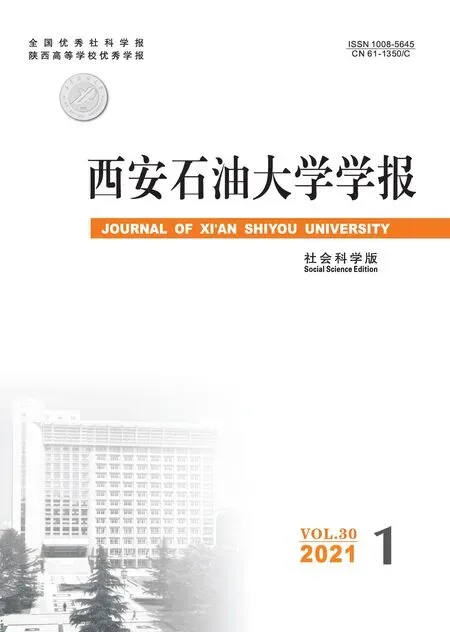李达与毛泽东交谊考论
2021-11-29史佩岚
史佩岚
(西安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0 引 言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与作为理论家、教育家、宣传家的李达,不仅是湖南同乡,也是相知相惜的挚友。他们相识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革命战争年代在思想交往方面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李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宣传工作,直到1966年去世,才结束了二人长达四十余年的交谊。在交往过程中,二人不仅对彼此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还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推动者和贡献者。
1 李达与毛泽东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历程
李达与毛泽东的交谊渊源颇深,源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并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笔者通过对资料的梳理,将李达与毛泽东的交往历程集中划分为三个阶段:建党初期、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
1.1 建党初期
在中共“一大”上,李达与毛泽东作为“一大”代表初次谋面,自此二人便展开了长久的互动交往。其实早在1921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到了李达主编的《共产党》刊物:“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1]4可见,在素未谋面之时,李达就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2年5月,李达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一职,主要宣传、讲授马列主义相关课程。1923年4月,李达与毛泽东共同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并担任主编。[2]28然而不久后,学校在军阀赵恒惕的强令下被迫关闭。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主张发动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农民运动,李达应邀给农讲所学员讲授“社会科学概论”[2]51,同期参加授课的还有瞿秋白、李汉俊、方志敏等人。在李达看来,革命斗争离不开理论研究,而自己擅长的正是理论研究。自此,李达便开始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著译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并在大学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而毛泽东则领导工农群众开展革命,站在了革命运动的前沿。
1.2 革命战争年代
李达与毛泽东相知于革命战争年代,即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易礼容的信中提到了李达夫妇:“李鹤鸣(1)李鹤鸣即李达。李达,字永锡,号鹤鸣,使用过的笔名还有“立达”“李平凡”“江春”“白鸽”等。、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3]47毛泽东还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对李达所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第三、四版作了摘要和批注。9月22日,毛泽东致信蔡元培探讨抗日救国,信末致敬多位社会爱国人士、党国故人、学术师友和社会朋旧,其中提及李鹤鸣先生。[1]445可见,即便在抗日局势艰难、动荡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李达,并设法与其取得联系。1938年1月至3月,毛泽东在延安收到李达寄来的《社会学大纲》一书,并对其非常重视,认真阅读、详细批注了该书的第一篇《唯物辩证法》,并在读书日记中记录了阅读每一篇的具体日期。同年,根据武纡生的回忆,他曾见过毛泽东从延安写给李达的亲笔信,信中主要表达了毛泽东对李达及夫人的关怀之意,邀请李达有空偕家人去延安做客,并表示已将《社会学大纲》读了三遍。[4]16毛泽东还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了该书,并称赞其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5]16。1941年9月,毛泽东致信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建议同志们在研究时应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而理论方面则需关注研究思想方法论,并提议阅读学习四项材料,其中之一便是李达所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论法与形式论理学”。[3]1891948年春,根据陈立新与李梅彬的回忆,毛泽东曾经多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到解放区。11月9日,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教书的李达接到了毛泽东这样一封信:“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2)此信内容见于《李达全集》(第一卷)卷首彩印图片。接到这个消息,李达激动不已。1949年4月,李达由地下党安排,从长沙辗转到达北京。12月,李达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在这之后,李达检讨了自己早年脱党的重大错误,并向毛泽东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请求。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李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领域的成就,表示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李达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以及各种艰难条件下所做出的贡献。不久后,李达终于如愿,由刘少奇介绍,在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三人的见证下,被批准重新入党,无候补期。[5]20已年近花甲的李达激动得热泪盈眶,并表示愿意继续在高校从事理论工作。从那一刻起,李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付出一切,鞠躬尽瘁。毛泽东召唤李达“归队”的那封信,至今陈列在李达纪念馆里,不仅体现了两位伟人坚定的革命信仰,也是二人情感上相知相惜的一种见证。
1.3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先后担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哲学会会长等多职,日常繁重的工作使得已到花甲之年的李达常感身体不支,但他仍然把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3)《〈实践论〉解说》与《〈矛盾论〉解说》分别收录于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十六卷、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就是李达在解放初期的重要哲学著作。这两本《解说》作为独立的研究成果,精准深刻且通俗易懂。此后,李达还发表了大量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论著和讲演,例如:《〈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怎样学习〈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三十周年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两周年而作》《读毛泽东同志在1926年—1929年的四篇文章》《读〈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帮助学习党史的几篇重要著作》《读〈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一批文章(4)李达以上七篇文章均收录于汪信砚主编:《李达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其中,《读毛泽东同志在1926年—1929年的四篇文章》影响力较大,文章中李达从阐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意义入手,结合中国革命的历程和问题,分析了毛泽东这四篇文章的背景、内容和贡献,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逐年发表的著作是学习党史的最好教科书。”李达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文章,为当时广大人民群众与青年学子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加快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1954年12月,李达将自己的两篇文章《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寄给毛泽东交流探讨,毛泽东在回信中肯定了李达的文章,特别提到了政治思想一篇通俗易懂,对读者帮助很大,并建议李达在今后写文章时“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3]4871956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到武汉,与李达会面。毛泽东待李达十分亲切,要其以“润之”称呼,回忆往事二人相谈甚欢。在毛泽东看来,李达从五四时期就传播马克思主义直到全国解放,还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和著述,翻译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堪称是“理论界的鲁迅”,甚至在中国革命的艰难时期,虽身在党外,思想上却从未离开共产主义事业,不畏惧国统区的高压,冒着巨大的风险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黑旋风李逵”。[6]18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武汉大学实习学生在街上看到了一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口号,回校告诉了李达。之后,在武汉东湖客舍李达同毛泽东为这个口号发生了分歧和争论。李达很生气,认为这样唯心主义的口号不该有,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5)白小梅:《毛泽东同李达争论:毛承认错了》,载《春秋》1988年第1期。由于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二人最终不欢而散。[6]181961年,李达与毛泽东在庐山会面,毛泽东再次肯定了李达《社会学大纲》的价值,并鼓励他修改再版。自此,李达开始潜心投入到《社会学大纲》的再版工作中,并主编了《唯物辩证法大纲》,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李达被诬陷为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头目”而遭受错误批斗,开除党籍,身心饱受摧残。7月,在艰难的情形下,李达向毛主席发出了最后一封信,也是危难关头的求救信,毛主席收到后作了批示,等批示转到武汉,却已经来不及了。8月,李达病故,结束了与毛泽东近半个世纪的交往。1974年1月,中共中央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2 李达与毛泽东的学术讨论
2.1 毛泽东盛赞李达的《社会学大纲》
《社会学大纲》是一部47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是李达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第一篇是唯物辩证法,第二篇至第五篇是历史唯物论。该书是李达1930年任教北平大学商学院时讲授社会学的讲义,1935年首次印行,补充修改后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之后,李达辗转寄给了在延安的毛泽东一本。毛泽东非常重视,一页不落地看了一遍,在其读书日记中记录了阅读该书的详细时间进程,并详细批注了该书的第一篇《唯物辩证法》(6)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05-283页。。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回忆,毛泽东称自己已将《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7)郭化若:《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段——纪念毛主席八十五诞辰》,《解放军报》1978年12月28日。,并向延安哲学研究会与抗日军政大学推荐了该书,并盛赞其为“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都来阅读学习这本书。[5]16甚至在20多年后,毛泽东与李达庐山会面时,还又一次谈到了这本书的影响和意义,建议李达再次修改出版,足见毛泽东对李达《社会学大纲》的赞赏与认同。更重要的是,在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出版之前,毛泽东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通过研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两本书。然而,这两本书是专门针对苏联情况而编的,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相较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不是马列著作的一般复述,也不是照搬外国经验,而是侧重系统准确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以及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哲学思想,论述客观,体系严密。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新的内容,丰富了毛泽东的哲学底蕴,对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实践论》与《矛盾论》的问世。
2.2 李达对毛泽东《实践论》与《矛盾论》的解说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和1951年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两论”是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长期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一经发表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李达非常欣赏这两篇文章,并对“两论”进行了细致入微、逐字逐句的解说,力求较为精粹准确地阐释毛泽东思想。同时期,在阐释“两论”的诸多著作中,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在看完《〈实践论〉解说》第一、二部分后,毛泽东在1951年3月给李达的回信中,对部分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8)详细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54页。,并高度评价:“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7]1541952年9月,毛泽东对《矛盾论》第四章的小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提醒李达在写解说时,要多加注意(9)详细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445页。。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揭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与意义起了很大的作用,揭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使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和平与统一,并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两本《解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意义重大。
2.3 毛泽东提议李达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
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是他生平最后一部专著,而李达晚年编撰《唯物辩证法大纲》的重要动因,便是毛泽东的极力推荐。1961年8月,李达与毛泽东在庐山会面时,毛泽东表示自己对苏联哲学教科书有很多不满之处,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哲学教科书,并于时隔二十多年后又一次高度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书,认为该书意义重大,应该修改再版。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仍长时间使用苏联教材,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早在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就曾提到,“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8]109在中苏关系破裂后,马克思主义教学与宣传工作形势严峻之际,毛泽东的话给了李达巨大的信心与启发,他决定接受毛主席的提议,重新编写一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李达计划分上下卷完成这本书,上卷论述唯物辩证法,下卷论述唯物史观。经过四年努力,在1965年下半年完成上卷《唯物辩证法大纲》的编写后,李达立即寄给毛泽东和中央有关负责人审阅,广泛听取学术界的意见,并开始指导编写下册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大纲》在着重总结当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全面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1978年,人民出版社请陶德麟根据李达生前意见对上卷送审本进行必要修改后,《唯物辩证法大纲》正式出版。李达人生最后一部著作,在他逝世12年后终于问世。这部汇集了他人生最后几年心血的重要著作,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3 李达与毛泽东交往的价值意蕴
3.1 有助于保持理论与实践的凝聚力,合力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李达与毛泽东,一个是理论家、思想家,一个是政治家、革命家。提到这两者,大多数人往往容易受主观看法的影响而产生误会,片面地认为理论学者就代表思想真理,领袖人物则代表政治权势。其实,真理是辩证的,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没有天然的真理,也没有天生的学者,学者不能代表真理,不能将学者简单地同真理划等号,尤其是个体学者,更不能保证其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与全面性,学者从事理论研究离不开在社会大环境的锤炼,所以不能拿理论或个体学者的思想来片面否定社会实践。同时,领袖人物不仅是政治家,还是国家发展的领航人,往往在实践方面对国情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感悟。从李达与毛泽东的交往历程,可以看出二者的交流、碰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进理论研究实现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避免学者在理论研究时纸上谈兵、回避现实问题,使理论研究沦为一种纯粹“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东西。[9]431李达在解放后发表的大量文章,就是建立在为革命斗争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现实帮助的基础上而写的。同样,政治权力也不是鲁莽和专断,不重视理论研究的政治决策是空洞的、盲目的、没有根基的。一般来说,从信息到决策的角度,国家领袖需要理论学者针对社会现实问题,通过发表思想观点或形成理论研究成果的方式,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参考与建议。从理论服务现实的角度,学者无法回避政治运行与领袖人物的意志去研究,理论研究不是为了片面地研究某个词句、内容,而是要运用研究的方法与成果,来具体地分析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理论研究的最终旨归是为现实提供思想资源。[10]19因此,从李达与毛泽东的交谊互动中可以看出,保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凝聚力,使二者不被分离,能够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在交流与碰撞中迸发活力,从而合力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达到高效整合利用一切社会资源,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3.2 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在李达与毛泽东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中,始终紧紧联系着二人关系的重要纽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交流与探讨,二人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推动者与贡献者。李达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坚持著译马列主义理论著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与传播。其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社会进化史》等著作,对毛泽东的影响尤为深刻,为其开始从客观地、全面地思考中国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前提,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侧面助力了战争局势的转变。同样,毛泽东关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群众、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相结合等思想,一定程度上对李达转换学术研究的思路影响重大。在李达看来,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的判断与思考,是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必要理论基础,并且,解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难以取得突破,是缘于部分学者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下,较少将学术研究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相联系。因此,李达在高校开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强调“研究马列主义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随时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理论不至于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具体实践分离脱节,变成抽象的、空洞的东西”[11]46。同时,李达还在毛泽东的启发下鼓励学界专家大胆突破局限,主动深入乡村基层,向人民群众学习,打破理论研究的常规,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道路。可见,李达与毛泽东交往,源于两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的交往对彼此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4 结 语
李达与毛泽东的交往,经历了革命战争时代的艰难考验与和平年代的思想神交,最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的思想交流,加快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梳理研究李达与毛泽东的交往历程以及价值意蕴,对于更深入地了解两位伟人的友谊以及二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中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