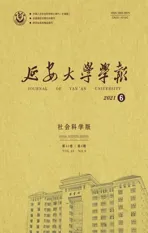“他者视域”下中共领导形象塑造及当代启示
——以《西行漫记》为中心
2021-11-29郭冰茹
李 萍,郭冰茹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西行漫记》以一个域外闯入者的视角,首次向国内外全方位展示了一个充满视觉真实与历史感的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整体形象。英文本初版在伦敦出版一个月内重印3次,此后又陆续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文字,畅销全世界。(1)参见张注洪《论〈西行漫记〉的国际影响》,《国际政治研究》1990年第3期,第88页。伴随其广泛传播,延安革命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符号性和文本性内涵逐步生成。有学者指出,《西行漫记》是“确立‘世界的延安观’的第一部作品”,[1]158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有关《西行漫记》的研究目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作家主体性为切入点,关注作家斯诺的跨族际和跨国际身份,重点分析延安革命文化和中共历史建构;二是以传播学视角为切入点,中心在于分析红军整体形象,仅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形象塑造作为其中一个叙述维度,并未曾全面系统阐释这一形象的核心价值。
事实上,“他者”叙述区别于中共主体的自我建构,具有重要的历史旁证意义。“他者”视域非自我观照,是带有隔阂和审视意味的域外异己观察者视角或立场。作者斯诺来自美国,是独立于当时国内历史政治局势的域外异己者。由于国民党严禁一切记者进入陕甘宁边区、放任中共和红军妖魔化形象的传播,斯诺之前从西安到陕甘宁边区的路径甚至是秘密,故当时中共未曾与社会达成公开、广泛的信息交流。在《西行漫记》中,中共领导人形象塑造不失为其叙述亮点,同时,斯诺的他者叙述对中共和中国革命具有空前的历史旁证意义和持久有力的传播效果。
一、“他者”视域下中共领导形象塑造的特点
《西行漫记》具体描写的中共领导人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海东、刘志丹。斯诺基本都介绍了他们的籍贯、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军政职位和革命实践经历等,关于毛泽东的篇幅最大,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徐海东四人都有专属章节标题介绍,其余人则杂糅在斯诺对边区的采访行程中。不同于当时国内外媒体的谣言讹传,在斯诺极具视觉效果和清新自然的语言文字中,中共领导人形象重新得到有力整合和正面突显,同时,领导身份原本的神秘色彩,也被其真实的个性张力和充溢的情感内涵特点所取代。
(一)形象个体被真实呈现
秉承着客观、公正的新闻态度和不畏艰险、认真的职业精神,斯诺突破重重关卡来到陕甘宁边区,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展开了对中共和边区的采访。斯诺的西北之行,缘于“毛泽东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真相”,[2]出于中共领导人原本的主观意愿;不过,斯诺的采访并未受到中共领导人的干涉,纯粹是自由,同时,又被历史证实的“他者”言说。中共领导人不曾查看斯诺的采访稿件,丝毫没有表现出试图隐藏事实、甚至威胁和修改其采访结果之意。而且斯诺在采访毛泽东时重点补充道:“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3]78可见,他者视域下斯诺的采访报道内容是客观、真实的。
中国古代君主往往宣扬其“天命神授”血统,刻意规定特殊条文以维护其至高无上的领导身份。斯诺笔下的中共领导人毫无神秘或高贵特点,而是真实的时代血肉个体。斯诺言证:中共领导人在参加革命之前,就是那个内忧外患时代下痛苦和疑虑着的普通青年人;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民和工人家庭,参加革命的动机不是感知到了自己的非凡命格或是为了个人一统江山的雄心壮志。斯诺提到了民间流传着许多中共领导人的神奇传说,如朱德能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甚至死而复生,刘志丹在西北同样是“刀枪不入”。这对应的是中国古代帝王式的夸张宣传,如刘邦头顶“天子气”,刘备可以跃马过檀溪。但斯诺有力地指出中共领导人并非拥有非同寻常的过人之处,像周恩来、朱德等甚至身材不高,而当时的毛泽东在斯诺看来,他仍然保留着看似粗鄙的农民习惯。这些描述都在塑造中共领导人的质朴真实形象,淡化了领导身份的“荣光”,是来自斯诺对中共领导人的平民化的真实书写。
总之,中共领导人并非天生异人。斯诺具体介绍了中共领导人接受教育、展开社会实践和在边区生活的内容。他们得以指挥军队和指导边区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人,不关乎神圣的天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切社会条件发展和成熟的结果,中共领导人走上历史的舞台也得益于个人的求学、实践探索等不懈追求和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
(二)形象情感充溢饱满
有学者指出,延安革命文化的精神性内核是对中国传统“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的借鉴与改造成果,(2)参见王鑫《跨际观察与史性阐述——域外作家的延安叙述》,《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4期,第210页。而斯诺塑造的中共领导人形象正充分表现了这种内核精神。如在描述中共领导人外貌时,斯诺几次重点提及他们的眼睛:毛泽东双眼炯炯有神,周恩来又大又深的眼睛富有热情,朱德眼光非常和蔼等。眼神中自然流露出了情感,让人体会到他们对信仰的坚定、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而这些“都是斯诺作品中所着意渲染的”。[1]161在斯诺笔下,中共领导人的形象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用理性”态度和“乐感文化”精神。
一是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之情。共产主义不等于宗教信仰。中共领导人领导中国武装革命斗争不单纯凭一腔热血,相反,他们热衷学习、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不被眼前的现象所遮蔽,依据实用理性的辩证逻辑,这是一种非常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思想。斯诺笔下的中共领导人基本都接受过文化和军事教育,如周恩来、朱德等拥有国外留学经历,毛泽东给斯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毛泽东十三岁离开小学堂后,尽管白天需要做劳力活,晚上还要替父亲记账,学习时间有限,还是“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3]121中共领导人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也始于阅读《共产主义入门》《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书籍。这部分的内容表现了中共领导人对于真理和知识的渴求之情,中共领导人从来不是媒体所讹传的“无知土匪”与“强盗”。
二是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之情。在斯诺笔下,边区生活之所以令人向往,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领导人都表现出由衷地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在条件相对艰苦的边区,处处洋溢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与“乐感文化”。中共领导人尤其表现出超物质性的情感追求,珍惜浮现在边区的种种来之不易的美,认真地感知生活。斯诺在与周恩来漫步乡间田埂时,周恩来“充满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3]53顿时让人感受到了周恩来的豁达和纯真的孩子气。斯诺还指出,他常常见到彭德怀和两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认真地向他们讲政治和他们的个人问题。当毛泽东和斯诺一起去参加群众大会,毛泽东也毫不起眼的坐在观众中间谈得很高兴,乐于参与到大众文化活动中,共同感受边区生活的喜悦。中共领导人不是单纯的政治符号,斯诺言证他们还活跃在边区生活的各个角落,以自身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感染着边区的人民群众。
三是对革命同志和普通民众的关切之情。中共领导人始终与普通战士和民众在一起,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体现了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根本动力。斯诺在书中写到一个细节,毛泽东在讲述一位与他一起革命的同志死于暴动时,眼睛里不自觉地含满了泪花。朱德在军政事务之余,还帮助农民种庄稼,在长征途中,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可见,中国共产党没有所谓的阶级贵贱区分,因此中共领导人才受到民众发自内心的爱戴和尊敬。斯诺言证:“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念叨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词,但是,我却也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每个人都这样叫他。”[3]72这是中国古代君主和当时的国民党领导都未曾感受的,中共领导人从不吹捧自己的政治地位,扎扎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却真正走进了人民心中。
二、“他者”视域下中共领导形象塑造策略
(一)设置问题引起注意,以第三人物视角展开叙述
在展开中共领导人的介绍时,斯诺先提出了一些外界媒体和民间传说关于他们的讨论,引发人们的好奇心,又带着这些问题从记者的角度去寻找真相。例如,斯诺在采访毛泽东时首先指出,虽然“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3]70毛泽东被宣称患有严重肺病,甚至几次被国民党宣布死讯;这无疑让在边区亲眼见到毛泽东,而且听到医生宣布毛泽东身体非常健康的斯诺,产生巨大的反差感,谣言讹传也不攻自破。
对于采访报道,斯诺坚守住了新闻作品的客观性。一方面,斯诺实地观察了中共领导人的住所,尽力与之多方面接触,基本保留了与中共领导人采访时的原话;另一方面,斯诺又通过采访边区百姓和战士收集中共领导人平时的为人处世信息,让读者不受他的影响而是身临其境般地去认识真实的中共领导人。对于没有亲眼见到的中共领导人,如关于贺龙的介绍,斯诺借用了奉国民党之命去争取他过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时任红军指挥员的李长林的话;此外还有朱德,则是保留了第二个见到红军领袖的外国人韦尔斯女士关于朱德妻子康克清介绍朱德性格的采访信息,保证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此外,斯诺有意识地运用对比手法,突出中共领导人的正面形象。具体表现在:一是边区内外对比,如南京以高额价钱悬赏中共领导人的首级,甚至派飞机到边区散发悬赏通告,但这被烘托出的紧张感和危机感却被消解在中共领导人的泰然处之中。如斯诺言证彭德怀甚至下令保存这些悬赏传单,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二是表现在中共领导人与国民党领导之间的对比,突出中共领导人优越的领导能力,例如朱德统帅红军长征,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竟然保全了一支军队,斯诺指出国民党军队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成功效仿朱德,他在军事战略以及战术处理上在中国是无人能及的。
(二)以中共领导人的经历映衬党的发展历史,突出形象个性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克服了“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问题,突出中共领导人形象的立体化和可亲可信性。一方面,斯诺介绍了中共领导人的成长经历,即其性格来源的历史环境,使其性格有据可循;另一方面,斯诺着重通过中共领导人的语言表达、行为举止和居住环境等构建他们的基本形象,最终形成他们各自的外在与内在统一的个性。
斯诺深入介绍中共领导人物时采取新闻通讯的写作手法,交代了其籍贯、家庭背景和求学实践等生活经历,其中重点突出了他们的童年生活。在整个叙述的过程中,也把领导人物的性格形成因素展现出来。如,因为家庭浓厚文化的熏陶和个人留学经历的影响,周恩来态度温和、英语表达准确,显得非常儒雅。
从中共领导人的成长经历中,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和壮大的历程,在此,斯诺也基本完成了对中共和边区的整体展现。中共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他们各自负责的工作共同串联起了整个中国共产党和边区的运转。斯诺认为毛泽东生平的历史即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3]70通过采访,他获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建过程、红军的成长历程及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在和周恩来交谈时引出了他组织工人起义和南昌起义的经历,即红军武装力量的来源;此外,采访林彪时又展现了红军大学的真实模样等等。斯诺指出:“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3]165中共领导人既是真实的人,又是与历史具体进程紧密结合的人。
斯诺采访时还注意到中共领导人采取了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如毛泽东利用“执政党”和“反对党”等政治名词来介绍他少年时的家庭生活,周恩来则使用英语以温和文雅的口气跟斯诺交谈,彭德怀在回答斯诺关于“红色游击战术的原则”这一问题时则非常专业且精准地列举了十条内容,这些表达都非常契合他们各自的领导身份,突出了其政治意识、外交态度和军事能力等。
(三)以中共领导人对于时局和政策的言论引起导向,提供判断参考
斯诺对于中共领导人的采访报道做到了新闻性和宣传性的平衡。通过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斯诺整理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政策和政治态度等内容。在当时的实际环境下有利于宣传党的路线、推进党的事业发展。毛泽东认为:“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4]因此,对于中共领导人而言,斯诺到边区采访也是他们对外宣传难得的历史契机。
《西行漫记》中,斯诺为“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专列了一个章节,就此问题与毛泽东进行了十几次的谈话。采访涉及中国的外交问题、日军侵华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等,访问记录长达两万字。毛泽东也由此得以向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争取国际援助的愿望。毛泽东谈到,中国人民今天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友好各国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积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3]85字里行间透露出中共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烈愿望。结合当时国内外局势,关于中共军事政策和政治态度的采访无疑是重中之重。
斯诺采访彭德怀时要求其归纳“红色游击战术”原则,而彭德怀在归纳了十条具体的原则后,指出游击队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认为“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3]286这旁证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也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决心。由此,斯诺对中共领导人的这部分采访不断深入,最终有力地传递出了中共关于抗日救亡、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声音。
三、《西行漫记》的传播效果及其当代启示
《西行漫记》将中共领导人形象紧紧地融合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整体形象中,在斯诺“他者”眼光的观照下,中共领导人的主体叙述得到了实质性的正名,中共形象的对外宣传终于获得了空前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并在政治与历史的层面被注入了全新的意义,这具有启发当代思考的重要价值。
(一)《西行漫记》的传播效果
一是打破新闻封锁,拓宽了中共的对外宣传渠道。《西行漫记》的出现,大大提升了各国对边区的关注度。斯诺西北之行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为外国记者开拓了采访红色中国报道中国革命的途径”,[5]斯诺本人也为之后来到边区采访的外国记者提供了有效帮助。在斯诺的影响下,一些域外记者为寻求可靠的政策来源,纷纷专意来采访作为中共和边区政策的制定者和代言人的中共领导人。同时,他们将在边区的所见所闻撰写成书或文章发表,使得边区之外的国内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统治的根据地形成客观的整体了解。如1937年4月,海伦·斯诺到延安访问了斯诺未及访问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见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性变迁,并撰写了《续西行漫记》和《延安采访录》。同年6月,美国学者托马斯·彼森访问延安,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及国共合作等问题,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交谈。(3)参见汪湘,袁武振《国际友人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活动及其贡献》,《理论导刊》2004年第10期,第79页。这些为中共的对外宣传提供有利帮助,边区不再是被封锁和孤立的“赤匪之地”。
二是提高了中共的整体声望与评价,增强了革命圣地的吸引力。《西行漫记》既描写了中共领导人在领导国民革命和边区建设中的优秀事迹,又在观察中共领导人实际生活中的个人魅力。由此,中共领导人再不是被妖魔化的形象,民众借此了解中共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最终大白于天下。这既显现了边区生活的朴实美好,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向和领导政策的可取性和优越性,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声誉正名。原上海地下党委书记肖英回忆说:“读这本书使我从理论上进到形象上,具体清晰地见到了共产党人,如临其境,见到了让人尊敬、依赖、热爱的共产党人、革命领袖和无数革命战士、英雄们,他们所作的一切是多么艰难而又伟大的事业,要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党。”[6]据统计,1938年5月至8月仅三个月时间,就有2288名知识青年经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全国有1万多人在此获得去往延安的批准,直至1939年年底,抗大共招收了16144名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知识青年。(4)参见卢毅,罗平汉,齐小林合著的《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80页。在当时,对于进步青年而言,延安之行甚至具有人格自由独立的象征意义。
三是为中共争取国际援助和舆论支持提供了有效支撑。1937年《西行漫记》出版后陆续传播到德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西行漫记》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对于当时急需为中国革命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争取国际援助的中国共产党起到了非常有效的支撑作用。斯诺到边区采访时是1936年,正值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时期,蒋介石执着于“攘外必先安内”,不顾民众经受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的痛苦。为争取民族独立、救亡图存,中共领导人借助来延记者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基本政策。1938年《西行漫记》在美国发行,这不仅有助于美国各阶层人士了解中国,也帮助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来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西行漫记》向世界宣扬了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斯诺所转述的中共领导人言谈,也不是背诵教条的留声机唱片,而是适于中国国情、可据此组织抗日的精辟主张。(5)参见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序,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对于此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起到了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二)当代启示
国家领导人的公共形象是民主社会重要的符号语言,是国家形象和声望的重要组成部分。斯诺笔下中共领导人形象之所以值得重视,即是斯诺克服了自我本位主义思想,不仅客观真实地表现了其形象,还揭示了中共领导形象的本质内容。中共领导人是历史上最特殊的一类领导人,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代君主,也区别于当时国民党领导和西方世界的君主,斯诺的描写为中共领导人形象的正面塑造和优势性宣传提供了有力的“他者”辅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时期国家领导人形象塑造与宣传同样具有战略需求,《西行漫记》中对于中共领导人的形象塑造及其策略仍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及参照价值。
一是借鉴从现象到本质的客观、深入塑造方法。前文重点分析了斯诺在采访此前从未谋面且众说纷纭的中共领导人时,采取从疑问、现象到本质,层层深入、点面结合的策略,历时四个多月尽可能地与之熟悉、交谈,表达自己真实所见所闻的同时,又引用和中共领导人朝夕相处的战士、民众的评论,既多角度、立体化地塑造了中共领导形象,又表达了中共的政策和主张。
当前存在一种“关心政治”的现象,这得益于社交媒介的便捷,普通民众也有机会在媒介平台上,在不需要借助专业知识和实践调查的情况下公开谈论与品评国内外党政领导人,党政领导人形象在虚拟空间被刻意塑造和宣传,以更加多面化、轻松化,甚至平民化的形象出现。例如,周恩来青年时期的影像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以欣赏美貌为主题的视频和文章中,其面容俊秀的特点被着重强调;习近平同志的“习大大”这一陕西方言中意为叔叔伯伯的称谓被广大网友亲切地呼唤着;而普京勇武、威猛的形象也借助其“骑着狗熊”、抚摸猎豹等图片得以传播。在这种热闹的宣传氛围下,这些党政领导人的形象容易给人造成单一甚至刻板的印象,有失偏颇,甚至被过度娱乐化。
对于新时代语境下的普通民众而言,科技工具和媒介社交平台为人们创造了消解政治严肃性的空间。以消除距离感、增加趣味性为主要特征的领导人物形象在社交媒介上广泛传播,在增强亲近感的同时,也给民众造成了戏谑的空间。若深究其利弊,按照现象学的观点,其中需要警惕的是:存在利用这种热闹氛围下所塑造的领导人物形象来遮蔽政治和历史本质的宣传手段,虽然可以迎合公众的消遣心理,却无法启发人们对真正有价值的内容进行思索,而仅仅留下了娱乐心情之余的极端或刻板印象。
二是利用“他者”视角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有力旁证。虽然《西行漫记》使用第一人称书写,但在战争环境下,斯诺作为来自美国第一个访问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中共领导人的域外记者,依然能坚守客观公正的职业精神,不受谣言讹传影响。在《西行漫记》中,斯诺的存在,基本上属于中共和边区真实情况的一个“零度”叙述的见证者,他并未以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国际偏见来过多地影响读者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斯诺在塑造中共领导人形象的过程中,实现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宣传性的平衡,既从客观角度表现了中共领导人的真实情况,又突出了其正面形象,为当时中共和边区的对外宣传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当下,塑造具有积极正面导向的国家领导人形象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之一。对国家领导人形象内涵的积极传播以及民众对其积极正面价值的理解和接受,有助于增强国家和民族自信的内在动力。首先,国家宣传部门要以中国的方式进行自我型构。其次,域外他者视角的叙述也是重要的旁证和补充。例如,从《西行漫记》可以看到,中共早期领导人自小就热爱学习、崇尚真理,斯诺指出其中蕴含不可征服的精神和热情,这既是有力的“他者”旁证,也是当下社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动力,值得对这部分内涵进行深挖和借鉴。同时,讲好中国故事,不能仅仅是自说自话,这样极易陷入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深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为了一家独大,而是不可避免地要与世界对话;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脚步从来没有被族际、国际束缚,未来中国故事也同样欢迎全世界人民来共同参与和见证。
三是宣传形式适当利用现代科技工具取长补短。斯诺在采访时,除了利用文字记载,还用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借助这些照片保存住中共领导的真实外貌形象,不再局限于口耳相传和文字传递的形式,而显得更加鲜明直观。当前,现代科技工具的发展,如网络虚拟技术,更使得人们得以全身心“参与”和“感受”现场。同时,在教材和宣传册之外更多新史料被发现,一些历史影像也由现代修复技术被展示出来,人们得以听到来自历史的真实声音,对历史领导人物理解也更加立体化。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正面塑造国家政党领导形象的过程中,有效借助这些技术工具调整宣传形式,可以获得更加积极、全面的宣传效果。
当然,这些都不能以掩盖积极导向性内容和无端强化民族中心主义为代价,兼听则明,取长补短才是有利于民族进步、国家发展要求的应有态度。新时代语境下,有必要汲取斯诺这种“他者视域下”的精神态度和方法策略,并运用到实际条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