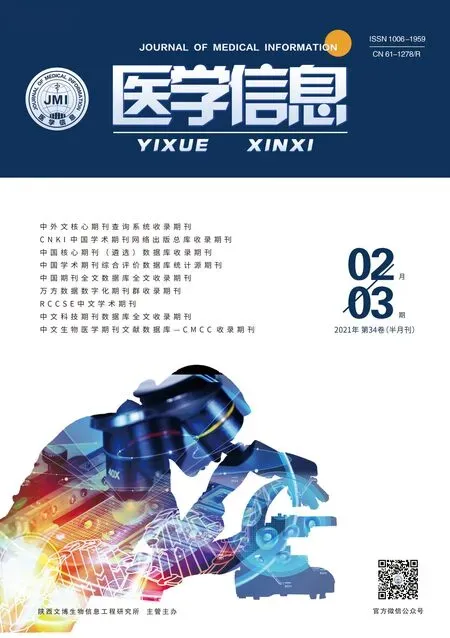浅谈温病理论辨治中风探析
2021-11-29
(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1)
目前,西医治疗缺血性卒中主要有静脉溶栓、血管内治疗、抗血小板、抗凝、降纤、扩容、他汀和神经保护等[5];出血性卒中主要包括止血、清除血肿的外科治疗等[6]。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超时间窗溶栓可能导致安全性低且获益少[7],另抗血小板药物治疗仍有不良反应率高及血栓复发的风险[8],神经保护药物疗效不明确[9],止血药物有可能无法改善其功能结局,外科治疗时机与方式不好掌握[6]。中医作为中国特色治疗方式,针对中风意识障碍、言语不利、肢体偏瘫、口角斜、吞咽障碍等突出表现具良好效果,能减缓疾病进展,减少并发症以及改善后遗症等[10]。多项研究表明[11],中西医结合治疗中风较单纯西医治疗效果更佳。温病理论作为中医理论重要的学术思想,其理法方药兼备,利用温病理论对中风进行辨证施治,值得进一步探讨。
1 以温病理论论治中风的理论基础
1.1 病因病机 中风病本虚标实,其中本以“阴虚”为主,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认为中风的病机是“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变动”,肝肾阴虚,肾水亏虚,无法滋养肝阳,肝阳化风,上越损液灼筋,蒙蔽清窍,导致猝然昏仆、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等各种中风症状的发生,如《临证指南医案》中所述“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内风时起”。同时,阴虚也是温病易感发病的病理基础,《素问·金匮真言论》云“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与此相反,不藏精者春易病温。另《温病条辨》言“温病之人,下焦精气久已不固”,指的是温病易感之人,其素体肝肾亏虚。由此可见,温病及中风的病机皆与肝肾阴虚有关。
1.2 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理论与中风的联系
1.2.1 中风与卫气营血的相关性 根据证候来说,中风病向来病情进展急骤,变化迅速,符合“风”的特性,并有“数变”的特点。临床上发现大多数中风前都有外感症状,如发热、恶寒、恶风等卫分证表现。因此,中风的“风证”可与温病的卫分证相联系。中风病中常见证候有痰热互结,腑气不通,常常伴有头痛眩晕、面赤口干、舌红苔黄、脉弦滑而数等临床症状。温病气分证有热结腑实的表现,见于病程极期,临床常见患者壮热汗多、口渴喜饮、尿赤、大便秘结不通、舌红苔黄、脉滑数有力,与中风之痰热腑实证有类似之处,可相互借鉴。《温热论》提到“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心神不安”,“若脉数舌绛,邪在营分……或夜有谵语,已入血分矣”,热邪入心营证,见躁扰烦乱、神昏谵语、舌红绛、脉细数等。而中风病之痰火瘀闭证见于急性期,证见突然昏仆、不省人事、面赤身热、牙关紧闭、舌红绛等,与温病之热入心营之营分证相似。血瘀证是中风的基本证候之一,缺血性中风被认为是气血运行不畅,血液于脑中血脉停滞而瘀;出血性中风是指虽是离经之血,但溢于脉外,无以入络入脉往复循环,弥散于脑中实质,亦是瘀血,可导致脑脉瘀阻,脑神失养,出现半身不遂、饮水呛咳、吞咽困难、偏身麻木等症状。温病邪热深入血分,煎灼阴血成瘀,致使血行不畅,脏腑功能失调,也可出现神昏谵语、舌深绛、脉细数等险恶的临床表现,由此可看出温病血分证与中风血瘀证两者间的相似之处。
1.2.2 中风与三焦辨证的关系 三焦辨证是温病中可以用来指导定位病所、总结证候、描述温病病情进展轻重的辨证思想纲领。三焦的生理功能有通调气机,主司元气运行以及是升降出入的通道。“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因气能生血、行血、摄血,若三焦气机失调,气机阻滞或原气生成减少、运化无权,则无力推动血的运行,可导致脑脉闭塞引起中风。上焦有心肺,肺主呼吸,为后天清气输送全身之关键。研究表明[12],肺脏的功能与中风发作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如肺失肃降与中风气机逆乱、肺合大肠与中风痰热腑实等。心主神明,而脑为元神之府,两者又有血脉相通,心血不足,则不能充养于脑,髓海失养而见头昏、记忆减退,甚至神志异常,更有研究表明心与中风在生理机制上关系密切[13]。中焦有脾胃、肝胆,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化生水谷精微之气,若脾胃受损,则水谷精微之气无以化生,同样无力推动血液运行而致瘀;湿热易从中焦而生,湿热困脾,上扰清阳,蒙蔽脑窍,继而发病。另外肝风内动是属中焦,肝阳上亢,灼筋熬络,发为中风。下焦有肾,肾为封藏之本、生气之根,若肾气亏虚,则无以温煦上中二焦推动气血运行,下焦之肾又与脑髓关系密切。有研究表明[14],采用补肾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神经细胞的凋亡,并能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
2 以温病治法辨治中风
2.1 开窍法 开窍法在温病治法中占有重要地位。临床上可见部分处于病情危重期中风患者,因肝阳化风生热,痰热内陷心包,出现身热面赤、燥扰不安、神昏不语等症状,与温病中邪热内陷心包的临床病机和证候有许多相似之处。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有云“邪入心包,舌蹇肢厥,牛黄丸主之,紫雪丹亦主之”,“湿毒神昏谵语者,先与安宫牛黄丸,紫雪丹之属”。故在治疗上两者可以相互借鉴,常用“凉开三宝”,如安宫牛黄丸清热解毒、豁痰开窍。
2.2 通腑法 通腑法是温病学中常见的治法之一,属于温病理论中的“下法”。温病大家吴鞠通创造性地提出牛黄承气汤治疗热入心包兼有腑实,增液承气汤治疗腑实兼有阴亏,宣白承气汤治疗痰热阻肺兼热结腑实,导赤承气汤治疗腑实兼有小肠热结等5个承气汤治疗方剂。中风“总属阴阳失调,气血逆乱”,邪实充斥三焦,阻滞中腑,藴而发热,为中风痰热腑实之证,此时证实标急,治疗上当急则治其标,理应泻下通腑、宣通三焦。因此治疗中风应运用温病通腑法,通畅腑气,祛瘀达络,使邪有去路,胃肠积滞得以消除,不致上扰神明。临床上可辨证论治,予承气汤进行加减,有利于中风的尽早恢复。
2.3 凉血散血法“凉血散血”语出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叶天士的名著《温热论》第2 条,其言“入血就恐耗血,直须凉血散血”,这是温热病热入血分的治疗原则,但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发病机制为“瘀热互结”的缺血性中风,也提倡用凉血散血法治疗。肝肾阴亏、脏腑功能失调是导致瘀热互结的病理基础。肝肾阴虚导致血液浓黏,运行不利;瘀血日久,壅结化热,热瘀互结,血行更易瘀滞,导致循环障碍而诱发中风。治疗中风的凉血散血方以叶天士犀角地黄汤进行加减,有清热解毒、凉血散血之功。
2.4 滋阴生津法 滋阴生津为温病学基本治法之一,温病理论中向来强调“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中风病的病机虽然复杂,然究其本当属阴液不足,治疗时多选用养阴及培补滋肾之品,如枸杞、白芍、石斛、天冬、玄参、生地黄等药物,既可柔润调和缓肝之急,又可涵养肾阴之亏。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更加明确了养阴在于滋养津液和防止汗泄过度,在治疗上用甘寒濡润之品养胃阴,用辛凉甘润配甘寒之品以救肺阴,用咸寒柔润配甘寒之品以滋肾液[15]。
2.5 分消走泄法 痰湿,不仅为致病因素,也是病理产物,随着现代人饮食结构的改变,多有过食肥甘厚腻,或恣意生冷,由此损伤脾胃,脾伤则运化失职,水湿内停,酿生痰湿,郁久化热,痰热互结,壅滞经络,上蒙清窍,或随肝之风阳窜扰痉挛,均可发为中风。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也提出“半身不遂,大率多痰”的理论。分消走泄法其名首见于叶天士《温热论》第七条“再论气病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寒中少阳病,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随证变法,如近时杏朴苓等类,或如温胆汤之走泄”,“以杏仁开上,厚朴宣中,茯苓导下”,具体而言,就是通过通调三焦气机,开郁行滞,使湿热或痰热邪气从上中下三部得以消除。因此,在中风之脾胃失和、痰湿较重的情况下,应该运用分消走泄法进行治疗,如运用温胆汤加减,往往可以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16]。
3 总结
通过温病卫气营血理论辨治中风,在中风合并外感,有卫分证时可根据“在卫汗之可也”,采用宣透之法,如银翘散加减以驱散外感之邪;中风痰热腑实证,与气分证之热炽阳明、热结肠腑相似,可结合通腑法,应清热开窍、攻下腑实,如用牛黄承气汤加减;中风痰蒙脑窍同温病营分证,应结合开窍法,治以清热解毒、醒脑开窍,方以安宫牛黄丸加减;中风热瘀互结同温病之血分证时,可结合凉血散血法,治以清热凉血、解毒散血,方以犀角地黄汤加减。利用温病三焦辨证探究中风,需宣通三焦气机,结合分消走泄法,涤痰祛湿、开郁行滞,方用温胆汤加减。又因“肝肾阴虚”的这一病因病机,在运用相关治法时不能忘本,可结合滋阴生津法,增水行血、消散凝聚,如运用芦根、生地、元参、麦冬、桑葚子、知母等养阴生津之品,起到滋阴润燥、补充阴液不足的作用。虽然温病理论主要治疗外感热病,但其丰富的内涵绝不仅仅止于此,在中风病这个内伤杂病的辨证论治中,温病理论同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中风的诊疗提供了开阔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