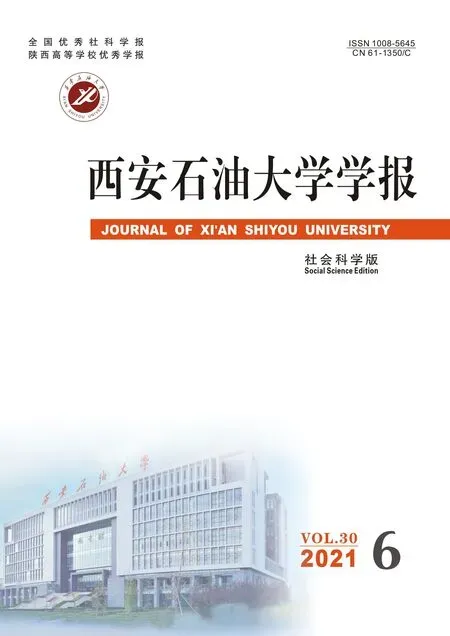张承志小说的“诗意清洁”
——“以洁为美”的濯净审美世界的筑造
2021-11-29黄思颖
黄思颖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110)
0 引 言
阅读张承志的小说,总会产生一种读散文的错觉,不论是草原、天山、黄土高原还是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淳朴的人们,在张承志的笔下,都充满了一种“诗性”的气质,那是一种属于景物的空灵的美,一种对于生命状态的大彻大悟。可以说,在张承志整个的文学景观中,最突出的特色就是这种“诗性”的“美文”表达。诗化与散文化的风格形成了他小说的“诗意清洁”,表达在文本中,就是他濯净的审美世界的构造,这也是张承志对于当下文风“不洁”,俗文学、口头文学泛滥以及文学中粗俗的性欲描写的一种反抗。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尝试从“自然”民间的诗意栖息地、诗性言说与主体灵犀的融通、唯我独尊的孤独审美行者等三个向度,审视张承志小说的“诗意清洁”。
1 “自然”民间的诗意栖息地
自然作为人类的母亲,从人类诞生之初就用自己的身躯与血脉滋润着人类成长。从远古到现代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由敬畏到亲近再到征服的过程。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自然在人类面前的境遇,都市生活的便利让人类渐渐远离了神秘与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然而,在便利的同时,喧嚣嘈杂与拥挤却也充斥着都市人的生命现场,对于名利与金钱的追逐压抑了人类生命自由的本性。张承志厌倦了这种异化的生活模式,便只身远离繁忙的都市场景,以决然的姿态拥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在整个人生长旅中,他走过了三块民间大陆,广阔的内蒙草原、雄伟的新疆天山以及静穆的黄土高原,而它们则分别代表了优美、壮美和静谧的美,张承志在草原的优美中发现了青春的活力,在天山的壮美中发现了英雄的气概,在高原的静谧中发现了无言的信仰与忠诚的圣徒。可以说,自然在张承志这里从来都不是作为背景出现的,而是真正的小说主角,自然的美成为张承志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表达主题,而对于自然的美的叙述也成为其小说“诗意清洁”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在自然与主人公一同的呼吸中,得到拓展美的空间,自然内置着张承志的生命情感和愿望,它已然化为作家的精神主体。
从清华附中毕业以后张承志就去了他心神向往的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成为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并且在那里生活了四年。历史的“玩笑”促使了个人生命历程的改变,草原的生活成为他青年时期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面貌。他自己也说过:“草原是我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甚至该说,草原是养育了我一切特征的一种母亲。”[1]84带着这样的情感,张承志将草原上的一草一木以及那里淳朴的人淳朴的事都带进自己的书写中,用诗意的叙述诉说着草原上的美,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文学世界。之所以选择“草原”作为打开文学大门的钥匙,除却其个人经历外,更多的是“草原”上独特的浪漫气氛和净化气质与其文学追求不谋而合。青青的草地、飞奔的骏马、湍流的河水、初升的太阳以及皑皑的白雪,都成为诱发张承志“诗意”的“温床”,在他眼里它们都是美的存在。可以说,正是草原的滋养引发了张承志对于“美文”的追求,他高唱着“美则生,失美则死”,高唱着“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只有诗一般美的表达才能写尽草原的生生不息与生存法则。而同时,张承志也用“美文”的诉说升华了草原的“美”。
《黑骏马》中随处可见的草原景物描写构造了诗意的世界,故事的叙述在景物的描摹中舒缓了脚步。张承志绝不止单纯地描写草原景色,而是将草原景物变迁与主人公的心绪变化联系在一起,使得自然获得了与小说主体同样的厚度,自然的美在张承志的笔下呼之欲出。《晚潮》中,草原景物的表达更加淋漓尽致,全篇几乎没有任何对话,而是用“他”的思绪贯穿全文,情节性的叙述转为了抽象性的人生体验。同样地,在《阿勒泰足球》《绿夜》《金牧场》等小说中,草原的美也充斥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信手拈来的景致成为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们已经获得了同小说主人公同样的重量。甚至如果褪去这些草原景物的表达,他的小说也就不算完整。可以说,草原在张承志的笔下成为了“优美”的存在,构成草原的景致单纯、和谐而富有生命力,主体生活于草原之中感受到的是宁静与平和,甚至生离死别这样大喜大悲的情绪震动也被融化在草原的静穆中。草原以其独有的浪漫气质诱发了张承志的“诗思”,又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容纳了张承志的生命情怀。与此同时,张承志也在对草原的追忆中创造了更加富有“诗性”的草原,那是融入作家主观情感的灵性的草原。
草原见证了张承志青春的成长,成熟后的他又以学者的身份在天山腹地游历长达十年之久,在他的眼中,新疆是“至死不渝的恋人”,因而又怎能不珍惜和这恋人浪漫深挚的爱情。他骑马走过天山腹地中每一条深邃的古道,赶驴踏遍火焰山的每一条沟谷;他跨过险峻的大坂,到达醉人的顶峰;他穿过荒凉的戈壁沙漠,只身来到凝固着火焰色的山脉。新疆用异域的美,天山用巍峨的力量指引着张承志不断向前,于是,在这样的旅途中,生命与这恋人融为一体,精神也在自然的引领下得到净化。天山在张承志的笔下具有崇高的美的力量。在康德看来,崇高的特征就是无形式,即对象形式的无规律和无限制性,具体表现为体积数量的无比庞大和力量的无比强大。由此观照张承志以天山腹地为背景的小说,便会发现张承志眼中的天山的美与康德的崇高完成了一次汇合。《顶峰》与《大坂》显示了审美对象力量的强大性,在对“顶峰”与“大坂”进行刻画时,张承志的书写语言已经由草原上的平和变得激扬,然而不变的仍旧是美文的表达。主人公的攀登行为是小说的主要内容,可是攀登的对象却也是不能忽视的小说主体,张承志用艺术化的手法刻画了这些巍峨高山的雄伟面目,让它们拥有崇高力量的同时也拥有了难以言状的美。不能忽视的还有新疆戈壁的美,《凝固火焰》《九座宫殿》中的沙漠显示的是与神山同样的崇高的力量。探索者面对广袤的沙漠时感受到的是体积数量的无比庞大,探索的过程之中,在与自然对抗时实现了主体生命的开拓与升华,升华的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审美的愉悦感由此诞生。沙漠本是一片无垠的荒原,在张承志的笔下却成为了美的形象,这美就体现在小说主人公一次又一次深入征服并最终体悟沙漠的旅途中,体现在诗一般的刻画和描绘中。
如果说草原展示的是充满活力的绿色,天山道出的是灵动耀眼的白色,那么西海固则写出了干枯黄色背后的辛酸与坚韧。踏遍北方大陆的张承志在这里找到了灵魂的归宿,找到了自我的终极信仰,于是将其所有的感情倾诉在这神秘深邃的高原中。铺天盖地的黄土掩埋了色彩缤纷的大地,这时他的小说中再也难以寻觅到草原景物中的跳跃和活力以及天山腹地上的磅礴与激情,字里行间充斥的是深沉静穆的美,是神圣庄严的美。那是一个穷得让人窒息的地方,荒凉与贫瘠,干枯与粗粝,无不挑战着生活在西海固一代代人民的生命。而张承志却发现了潜藏在这穷苦背后的难以言状的美,荒芜的黄土高原在他的笔下变成了有生命的活物。《残月》中夜色的描写与杨三老汉的思绪构造了全篇,黑色的夜空有助于杨三老汉思维的飘荡,而飘荡的思绪也有助于认真观赏这夜空,景与情的相互交融使小说的表达拓展了深度。同样的景物串联出现在《黄泥小屋》中,一望无际的贫瘠的黄土在张承志笔下变成了拥有生命灵气的广阔大海,充满了属于自然的生生不息的气质,这是一种动人心魄的美。人们在黄土中坚守着信仰,坚定努力地过活,黄土因此而守护民众,完成生命的长旅。在这些小说中,人物已经作为元素,被张承志嵌入自然的画廊中。于是,小说就在人与自然相互依靠的关系层面上开拓了深度,人物性格已经不再重要。甚至可以说,这种相偎相依的关系所包含的意义空间已经凌驾在故事情节的构筑以及人物性格的塑造之上,并且使作品笼罩着一股神秘的精神氛围。因此,人物的内心世界不用作家的刻意点染,在自然的描述下,人物心灵便呼之欲出,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
由此,三块大陆的不同面貌在张承志的小说中完成了融合,对于自然的描写成为其小说的中坚力量,而张承志对于“美文”的推崇也在自然景物的描摹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自然寄托了作家的人生理想,它变成了承载价值的符号和隐喻,不论是草地、天山还是黄土高原,它们在张承志这里已然变成一种意义的世界,是张承志内在价值和心灵自由的选择。自然成为小说的主角,成为“诗意的栖息地”,供人们“诗意地栖息”。张承志的“清洁”叙说理想也在这自然之美的表达中显示出了色彩。
2 诗性言说与主体灵犀的融通
张承志小说因“自然”空间的拓展而出现了“唯美”言说的感觉,其开篇通常都是大段的景物描写以及意境构造,接着小说主人公才缓缓走入读者的视线。在小说线索展开的同时,景物的描绘与主观情感的抒发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推动小说的情节发展,甚至成为小说的主体部分。这种纯粹的美的表达与诗性的言说直接形成了他“诗化小说”的风格。
“诗化小说”最早在西方出现,法国象征派诗人古尔蒙曾提出“小说是一首诗篇,不是诗歌的小说并不存在”。[2]37J·弗里德曼也曾指出:“新小说不像它的前辈们那样注重按顺序讲故事和从生到死单刀直入地刻画人物;它更愿意分解叙述,把经验切割成小块的事件,通过重复出现的意象和象征,而不是通过事件来把这些零碎的经验连接起来。”[3]423张承志小说的诗化风格,除了西方象征主义传入中国的这种影响之外,更与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作家特有的气质分不开关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与考古学者的身份使张承志常年“流浪”于民间,他在自然的大地上汲取了浪漫的气质,因而与文学团体内部的作家天然地区分开来。再加上异域血缘与本土民族相融而生的生存状态铸造了回民沉默寡言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驱使张承志产生了“倾诉”愿望,他希望能够自由而尽情地挥洒自己的语言,而不是被压抑的沉默,这种主观抒情的“诗化小说”能更好地贴近他的理想。另外,严格的教门制度与宗教礼仪也培养了张承志的“净化”思想,那么小说表达的“净化”倾向也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说最开始写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青年还在努力寻找小说的事件,力图从中构造出高潮和结局,那么到《黑骏马》时期,已经明显可以看出作家心态的改变:用古老的蒙古歌谣贯穿全文,主人公的一生则演绎了平凡歌谣的伟大意蕴,只是这时,情感的抒发仍然直接大胆,事件的贯穿也是清晰展现。到了作家创作的第二阶段,那远方高高挂起的“残月”,以及大漠深处的“九座宫殿”,还有那理想的“黄泥小屋”,已经成为作品的终极意义,没有特别的情节和人物,作家已经将这些化为神圣的目标,可以说,它们的存在就是作品的目的。而后,面对商品经济的不断冲击,张承志再也不能仅限于动情就好,他开始宣泄,开始呐喊,于是就有了富于激情宣泄的《胡涂乱抹》,而接下来创作的《金牧场》更是恣意挥发,“红卫兵”与“知识青年”两条结构交叉并行,每一条结构中又穿插着回忆,打破行文逻辑和顺序,完全像写诗一样自由前进。
张承志看尽了文学创作的“不洁”模式,他想要寻找心中最纯净的净土,而小说带有虚构和故事的模式阻碍了他的发挥,所以他将小说写得像诗,故事和人物并非重点,而在故事背后所渗透的哲思才是作者要表达的真正内容。可以说,诗性的小说一直是张承志的追求,他曾经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无论小说、散文、随笔、剧本,只要达到诗的境界就是上品。”[4]220他的小说是荡漾着激烈的感觉色彩的,张承志不止一次地在散文中表示过钟爱“纯诗”这种形式,而他自己也创作出了《错开的花》《海骚》《黑山羊谣》等诗体小说,便于情感更加恣意地流露,后来更是拒绝小说,专心散文这种创作模式。从意象的营造到感觉空间的叙写,从时空顺序的倒置到完全心理层面的挥洒,张承志使自己的诗化小说完成了它的发展和成熟轨迹,也在“诗化小说”中实践着自己“清洁”的文学理想。
与“诗化小说”理想相通的,便是小说中主体情绪的渲染。诗性的言说在客体与主体无限的沟通中显示了意义。叙述的“主体性体验”的强调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效果而淡化了情节性和客观性,抒情主体的主观生命体验傲然凌驾于一切之上。因此,在张承志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把握到作家的主体精神,获得诗性的享受。由此观照《北方的河》《大坂》《凝固火焰》《顶峰》《金牧场》《终旅》等小说,构成其情节的因素都很简单:永不放弃的追随者克服千辛万苦,奔赴自己理想的“圣地”。如此单一的情节线索,张承志却写出这么多的篇章,并且读之感觉不到千篇一律,这是因为作家在每一篇中都赋予了主体不一样的情绪表达。《北方的河》和《顶峰》作为青春的反叛姿态出场,在主人公激扬的自信背后是作家给予的生命强力,而《大坂》《凝固火焰》等所展示的则是挑战生命极限的超越人格力量与自然不可战胜的神秘魔力。这种追随到了《金牧场》《终旅》中就成了为了信仰九死不悔的追逐勇气。另外,《黑骏马》《绿夜》《老桥》《废墟》等小说构成了“青春回归”的篇章,在这些小说的背后都有作家自我的声音,是张承志对于知识青年过往的独特回忆。大量的抒情独白与景色渲染中断了作品戏剧性的同时也宣告了作家主体对于青春岁月的难舍情感。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张承志对于《金牧场》的重写。两条交叉并进的结构以及在叙述中穿插的回忆线索展示了《金牧场》承载的巨大历史容量,可是张承志对它并不满意,不仅永远停止了对于《金牧场》的再版,并且将近三十万字的《金牧场》删改成仅有十六万字的《金草地》。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就是:“放弃三十万字造作的辽阔牧场,为自己保留一片心灵的草地。”[4]169在《金草地》中,他将此前小说中关于日本文化的描写、理想主义的设计以及虚构的小说人物和古文献空议论全部删除,只留下了蒙古草原和红卫兵长征的部分,而且具体的生活情节也不见了,留下更多的是自我的心灵独白与倾诉。这样,在《金草地》中,之前那种混乱焦灼的历史情绪不见了,代之以浓郁的抒情气氛。可以说,《金草地》成为张承志主体情绪渲染的更加深入的表达,也更符合张承志主观抒情理想的表达。
诗意化的表达与主体情绪的渲染使张承志的小说拥有了一种朦胧的意境美感。“意境”在中国文学这里从来都不是新鲜的话语,可以说,张承志小说的主体抒情式表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思与境偕”的境界特征,在审美创造中达到了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思想与形象的融合。在诗意的言说中拥有了一种“蓝田日暖,良玉生烟”的朦胧美,这种朦胧美,就体现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境构造中,在似虚而实的空间中,达到自然与主体灵犀的融通。象征意蕴的存在扩大了其小说文本表达的空间范围,“黄泥小屋”“金牧场”“九座宫殿”式的理想家园创造了一个虚幻的艺术空间。张承志在文本塑造中,以这些“理想”的牵引构造故事,却从未对它们进行实际具体的描写和刻画,而是作为想象出现,指引着一个远方的画面。主人公在此情境中追逐“上路”,这是可感知的实景描写,可是文本显然意在更广阔的天地:在苏尕三一次又一次看见的那座小泥屋、在额吉心驰神往的黄金牧地、在蓬头发与韩三十八都向往过的“特古思·沙莱”古城。想象空间的家园成为小说的终极目标,那空间美好而富于灵气,在这种虚实结合的描写中,使文本表达出了一种若有若无的朦胧感。同时,“老桥”“黑骏马”式的见证意象连接了过去与未来,青春的记忆与淡漠的过去都在老桥和骏马的呼唤下喷涌而出,文本空间由现时转化为过去,同时也指引了未来。不论是在现实之光的打击下不堪一击的约定,还是在世俗世界冲刷下脆弱不堪的浪漫,是温情美好的爱恋过往,还是青春年少的无知姿态,都因为实体景象的存在而被唤醒了颜色,回忆伸向远方的时空,曾经的故事悉数登场,为小说创造了另一种虚幻的空间,这是实际经历与回忆想象共同加工出的“象外之象”。
由是,张承志带着自己诗人般的气质行走在自然民间,用诗性的言说以及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宣泄着主体内心澎涌而出的情感,在写意化抒情和象征化叙述中创造出了文本独特的意境之美,似是而非,虚实相生,在朦胧的空间中,构造出一幅意蕴广阔的深层画面。
3 唯我独尊的孤独审美行者
中国现当代文坛上,张承志的存在是特殊的,他举起“清洁”的旗帜,在文学中“规避”了许多在他看来“不清洁”的内容。关于艺术,他有两个独特的观点,那便是“规避”和“倾诉”,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对于“美”的表达也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不同于当代的审美泛化、世俗化、娱乐化,以俗为美,以性欲的抒发为精神的突破口,张承志小说中善良的人性、美好的生命才是他极力赞颂的东西,可以说他小说中的人物都透露出一种超越的人格理想,世俗的话语被张承志全部遮蔽在了草原、高山中。而审美也不是康德标榜的那种较高层次的形而上的活动,它就存在于生活中,苦难的人生也具有审美的力量。
“倾诉”的愿望指引张承志走向创作的道路,他曾经用一个蒙古式的民间故事来形容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方式:放羊的小孩忍受不住内心的冲动而向神秘的铁门掷出了自己手中的羊鞭。“忍受不住的内心冲动”成了“倾诉”的动力,而“倾诉”也成了张承志关于艺术的看法。在《错开的花自序》中,他说道:“我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也弄不清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散文。只是,多少年来,我渐渐明白了有些人需要倾诉;我努力从五花八门的倾诉中寻求甄别,我模糊地感到应该有一种高贵的、正义的、美的倾诉。”[5]233张承志进行文学创作完全是由于内心喷涌而出的情感需要找到适当的宣泄方式,他的小说几乎都是自我内心情感的真情流动,因而规避了许多政治历史的题材,呈现出“清洁”的模式,以至于最后当他发现小说不能很好地承载他的激情的时候,开始转而创作长诗和散文。
另外,张承志很推崇日本摇滚歌手冈林信康。唱歌对于冈林信康来说是一种宣泄行为,这对张承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而更影响张承志的则是冈林信康歌曲对政治的全面规避。他用“规避”的歌唱坚守自我内心的纯洁,甚至“只要剥去疯痴的摇滚或古调,都仅仅剩下一股纯美的男性爱。”[6]187因而张承志将他的歌曲当作自己的一个“重大参照物”,确认了自己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观点:“艺术即规避;在一种真正的角落里,艺术在不断新生着。我深信这一点,他证实过,我也正在证实。”[6]188可以说,“规避”一直是张承志创作的一个准则,也是他小说“清洁叙事”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带着这种思想进行创作,张承志首先“规避”了艺术中的政治、重大历史话语与文学潮流等因素。他在散文《江山不幸诗人幸》中指出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作家中出现的两种潮流,第一种就是“干预生活”触及政治与社会背景的作家,还有一种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开创文学的新形式和新语言的现代派作家。可见,张承志对这两种文学潮流都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他信奉的是“艺术即规避,选择文学就意味着选择了比政治更原初、更私人、更永恒的道路。”[6]166他的小说是心灵语言自由的表现,没有任何关于“政治”与“历史”的话语面貌。政治与历史都成为遥远的背景,被作家熔铸入自然的描摹中,“草原”“天山”“黄土高原”更像是作家逃离历史现场后的“世外桃源”,他在这里发现了异样的美的天地。此外,张承志也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金牧场》那种两条并行结构以及《晚潮》《三岔戈壁》《胡涂乱抹》等小说的意识流构架不能不说是现代派影响的产物。但是,张承志并没有完全受到那些理论的牵引,模仿结构的长篇小说阻碍了他心灵情感的抒发,于是他大肆删改,将“牧场”变为“心灵的草地”;他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意识流动也不仅仅是表达心灵思绪的篇章,而是将这种内心情感的飘飞都内置在坚守与信仰中,在心绪流动的同时始终有一条由信仰牵引着的线,因而与“意识流小说”区分开来,拥有了作家自我的书写面貌。
同时,张承志也在小说中“规避”了肤浅、直白、粗俗的文学表达。在身体写作、欲望书写大肆流行的当下时代,张承志却依然能够握紧自己手中的笔,保持着“清洁”的面貌,在文学浊流中开辟出一股清流。他在评价法国作家梅里美时这样说道:“对爱情和性的写法高人一等。不作官能的描述,但给人以更大的空间和静态的磁力,使人难以忘怀,因此也更具魅力。”[7]209他在自己的文本中也这样实践着,人民的语言被放置在了祖国边疆的土地上,除却了口语可能出现的“粗陋”;对于“性”的描写也只是浅尝辄止,《黄泥小屋》《终旅》中都有“爱情”的篇章,可是张承志更主要表达的是爱情背后的苦涩与无奈,男人面对女人看到的不是身体而是心灵,背负着“炼狱”也好,准备“赴死”也好,终究只能舍弃女子才能保全她们的生活,这是只有纯粹信仰的人才会有的举动,由此小说便开拓了更深一层的空间,而不是浮于表面的爱情。
带着“倾诉”与“规避”的观点进行创作,行文中流露出的美感便也与众不同。张承志以一种卓尔不群的姿态行走在文学的天地里,成为“唯我独尊”的审美行者,在诗一般的“倾诉”中“规避”了政治历史话语,“规避”了粗俗浅显的文本,使其文学世界呈现出一种不一样的审美感觉。可以说,张承志所号召的一直是一种纯粹生命意义上的审美,是一种真诚与善良,也是一种超越的人格理想。不论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额吉对于知识青年的关心爱护,还是《金牧场》中额吉从容端茶击退“恶”的势力,亦或是《黑山羊谣》中额吉对于秃子辱骂的原谅,它们都展示出了额吉的爱、宽容与大智慧,使其拥有了“善良”的美感。此外,边地上那些纯真的少女在张承志笔下也成为了“美”的存在。《绿夜》中的“他”在惜别草原后再次回归,在奥云娜的“阿哈”声中获得了真诚的感动,带着美的体味走向城市;《婀依努尔,我的月光》中,“我”在婀依努尔的身上看见了过去的生活,在她灵动的舞姿中,“我”终于收获了久违的“美感”,并将之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红花蕾》中的美是热爱知识青年老师的小女孩的单纯的心,那一片片羊毛中凝聚着世间最美好的爱与真……张承志将所有的美好人格全部赋予在草原额吉身上,赋予在纯真的少女身上,一方面是借这些单纯善良的女性表达自己对于“美”的追认,另一方面也是对都市文化躁乱不堪的“美”的一种反抗。
曹文轩在评价当代文学时表现了对于现时文学的激烈批判,他认为追求文学的“深刻性”指引着作家们走向了一条“不归路”:“‘深刻’这条狗追撵得人们撒丫子奔跑,往阴暗里去,往恶毒里去,往垃圾上去,往乱伦上去,往自虐、嗜血、暴力、兽奸、窥视、舔脚丫子等诸多变态行为上去。因为这里才有深刻,才有写作的资源和无边无际的风景……”[8]7作家们已然忘却,文学并不是将人撕裂开来赤裸裸地描述,更不是袒胸露怀以示思想的深刻。文学的作用,就是要写出那些哪怕生活已经不堪入目,却还要倔强生活的人;哪怕知道前方难行,却依然坚守信念的人。如同西绪弗斯的大石头,人们大都只能看见他推动的那颗巨石,却见不到拼尽全力推动它的人。解剖石头并不是美的本真,透过石头,见到支撑它的人才是文学要展示的“美”。由此观照张承志的文学世界,会寻找到那“石头下支撑的人”,她们便是拥有真诚和善良美好品质的额吉和少女们。审美在张承志这里回归到了古希腊那种真、善、美合一的理想,审美不是装饰品,而是文明的必需,美就是生命,就是文明与善良,是追求理想人格、实现幸福生活的途径。
由此,张承志在对“真”与“善”的赞颂与表达中,表现了自己对于美的追随,它就存在于作家走过的北方大陆中,存在于那些默默生活的坚韧的底层人民之间。在他们身上,张承志发现了真诚与善良,发现了一种与世俗的蝇营狗苟不同的久违的美。于是,作家将这些在文学作品中用“倾诉”的口吻,用“规避”的笔调不遗余力地展现出来,形成了不一样的美学风格。
4 结 语
不论是自然的美、文本意境的美还是生命人性的美,张承志笔下的文学世界,都是涤荡心灵的濯净的审美世界,其“诗意清洁”也在这世界中诞生了。“美文”的表现是其“清洁”理想最好的载体,面对嘈杂的文学艺术世界,张承志始终能够保持着自我内心的纯洁并且构造出不一样的美学天地,在“清洁”中,“清洁”地书写,创造出当代文坛中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