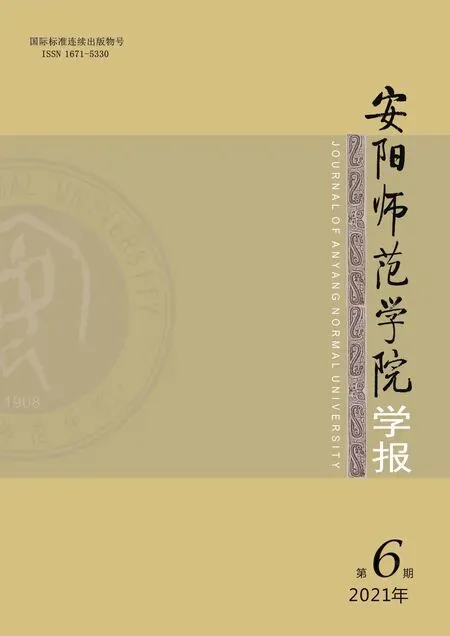《南非华人成长录》中的中国形象
2021-11-28代学田
代学田
(天津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所,天津 300204)
《南非华人成长录》(Paper Sons and Daughters:Growing up Chinese in South Africa,a Memoire)的作者,是南非知名华裔作家、记者何菲黛(Ufrieda Ho)。她曾于2007年获得安东尼·桑普森基金会(Anthony Sampson Foundation)记者奖。《南非华人成长录》的出版,使她成为继“南非第一位华人作家”(1)据Melanie Yap和Dianne Leong Man的考据,南非华裔Aubrey Wong On常被说成是“南非第一位华人作家”(‘South Africa’s first Chinese writer')。详见YAP Melanie,LEONG MAN Dianne.Colour,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M].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6:310.之后用英语写作回忆录文学的第一位华裔女作家。该回忆录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自己家人及其他华人在移民南非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坦诚地叙述了自己眼中的第二代移民同第一代移民对中国之情感、认知等方面的不同,讲述了自己的身份选择和情感归属。行文中,作者也以自己身边同中国有关的日常器物、食物、药物等,“在想象中……拼贴出”自己故土、故国的形象,展示了她眼中的中国形象。[1](P23)
在回忆录创作和研究两个领域都颇有造诣的巴林顿曾说,进行回忆录创作时,不需要作者“给读者扔出一堆细节——比如某个人外貌上的细节”,而是要“选择代表了那个人精髓的那一小部分细节”。[2](P97)因为“通常是具体的感官细节……为作者和读者同时展现出藏身在表面描写之下的意义。”[2](P102)故此,笔者在勾勒《南非华人成长录》中的中国形象时,准备爬梳检视一下其中展示的同中国有关的生活细节:日常器物、食物与药物。
一、器物中的中国形象
谈到生活中具体的器物,不少人习惯以“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传统目之。[3](P85)似乎,器物只不过是人类生活中那些实用性、功能性的有形外体。加之人们常见的上下分别之心,器物常被看成末物。其实不然,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4](P1)一旦器物同人发生联系,尤其是当器物通过神与物游的作者之笔而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其便可“用以折射社会风貌、文化环境,映射人的精神世界、道德高度、文化修养以及社会身份,甚至用以暗喻人的情感和立场”,具有“丰富的抽象概念、象征性和符号含义”。[5](P59)此时,文学作品中的器物,也就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作者某些创作意图的桥梁,比如其身份建构、形象塑造等的切入点。
在回忆录“遥远的来路”一章中,何菲黛集中描述了自己母亲和外祖母来南非之前,也即是她们在中国的生活情景。从外祖母的痛苦回忆中,何菲黛看到了一个落后的中国形象。比如:与现代价值观中之性别平等的追求格格不入,但已浸入旧时代中国人骨髓的重男轻女观念;现代科学观熏陶下的理性人无法理解,但在中国旧传统中普遍存在的冥婚习俗等。家人叙述的前文本背景,再加上何菲黛自己的想象和解读,一个落后且停滞不前的中国形象逐渐显现。
何菲黛将中国建构为落后、停滞不前国家形象的倾向,在回忆录第二章那些关于中国日常器物的描述中有着鲜明体现。她说:
现在,那里就算是乡下也有了现代化的生活设备。但是……现代性依然不得不向旧习俗低头:电视机和DVD播放机虽然一闪一闪地显示着数字化的待机时间,可它们上面却不得不顶着一块厚厚的印满花朵图案的塑料布。墙上挂的照片,从其椭圆形的边框或者发红发棕的色调,就能一眼看出它是专业摄影室的作品。可是,照片周围……贴满了传统的祈福求祥的挥春贴(2)挥春,原文为fai cheun,应为春联、门联、福贴等在粤语中的叫法。。
年轻人穿的可能是牛仔裤和名牌休闲衣,可村庄里上岁数的妇女每天穿的依然是传统的衣裤。……上衣款式常常还保留着满清时期的“y”形斜襟儿领口。没人给这些妇女们染发、修眉。她们不断加速的老朽,只不过是那些透骨寒风中、灼人高温里无尽而艰辛的农田生活之见证。[1](P22)
上述两段引文中有关中国人生活中的器物、服饰等日常细节的描写,应该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情形。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正处于努力学习现代化、实现中国全面发展的阶段。对正在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来说,这一阶段是传统和现代相互角力、彼此催生的一个发展阶段。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也是旧貌换新颜的甦生者。但是,在何菲黛的描述中,这些来自西方、代表现代性的mod cons(现代化生活设备),依然被中国落后但强大的旧势力所包围、压制,就像此部分第二段引文中的中国乡村妇女,只有风霜摧残下加速的老朽,却没有苦难后的新生。即使周围出现了牛仔裤等新的、现代化的形象和因素,它们也不过是作者眼中反衬中国之停滞不前的有力证据而已。面对过渡性或者说富有矛盾性的同一事物,到底“见仁”还是“见智”,最能体现“见者”的立场和取向。何菲黛如此强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器物中的落后和停滞,更是体现了她眼中落后中国的国家形象。
作为鲜明的对比,我们可以看看当南非生活中的旧器物被新器物代替时,作者是又怎样的认知: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记着妈妈教我的蒸米教程。只是,现在我用来蒸米饭的锅是一个由电脑芯片控制的多功能锅。这个电脑锅没了锅盖在锅沿上上下跳动的撞击声,也不再有小窗口去看锅内的米粒慢慢吸收咕咕嘟嘟的水泡。可它完备地配上了多彩的灯光和警示音。这新锅真是一次高品质的升级。[1](P18)
同样是电器上的灯光,出现在南非的日常器物上时,它是多姿多彩的“高品质的升级”(fancy upgrade),而出现在中国的日常器物上时,它却不得不承受厚厚的塑料布的重压,成为“向旧习俗低头”的牺牲品;前者的器物上有了灯光是完备的,而后者只不过是西方/欧美现代性同中国落后传统相割裂却又无能为力的目击者。同是现代科技产物的电器灯光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不同的特征,都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国家形象不同。
为了证明自己文字/想象中建构的落后中国的形象并不是无中生有,作者还与回过中国的亲戚们所拍摄的照片做了对比:
不过,有些亲戚前往这个旧国旅游去了。回来时,他们用数码相机拍摄了这些边野乡村的高清照片。我在照片上看到,时代的转变并未能掩饰住他们生活的简陋。如今的时代是一个资本消费不断增长的时代,可那里的生活依然贫乏。这些照片印证了我脑海中的形象。[1](P21)
数字不会撒谎,照片来自真实。数字与影像相结合的“数码相机”所拍摄的“高清照片”因而也具备了双倍的证明力量。而借着数码照片具有的双重说服力及其“客观性”,何菲黛向南非/西方读者表明,她在回忆录中建构的落后中国的国家形象是真实而客观的。
二、食物中的中国形象
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必备物资,普遍存在于各个文化的日常生活中。因此,食物也成为了最为常见的文化符号。由于历史、现实等原因,亚洲移民,尤其是华人移民同食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从职业上说,“在华人移民社会,餐饮业是华人经济中分布区域最广的行业,几乎遍及全球每一个角落。”[6](P167)从文化上来说,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饮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到治国之道,小到人际往来,举凡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军事学、医学以致艺术理论、文学批评,无不向饮食学、烹饪学认同,从那里借用概念、词汇,甚至获得灵感。”[7](P2)或许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华人移民创作的文学中有关食物的叙述常常不绝于目。这种描写食物的现象在华裔作品中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同为华裔作家的赵健秀(Frank Chin)极为反感,在自己的作品中借人物之口,说阅读刘裔昌(Pardee Low)、黄玉雪(Jade Snow Wong)等人的作品就像是“打开菜谱”,里面充斥着:
关于调味品和蒸煮的胡言乱语;唐人街米饭的秘密;伸向食物的手;食物简直爬满了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还活着的肉类食品,把进餐变成了一次远征这个神秘国度和探索血淋淋的仪式的探险。食物色情文学。[8](P95)
虽然沉溺于描写华人饮食的某些作品的确有“食物色情文学”的售奇嫌疑,但食物作为一种“族裔符号”,的确起到了“界定族群之外延和身份,将族人和非族人区分开……为族群仪式的举行提供语境”的作用。[9](P65)也正是因为食物有如此作用,法国比较文学形象学重镇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说,在研究异域形象时,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中所描绘的“……居所、客栈(la venta)、饮食这些东西构成了形象的重要成分”。[10](P170)
复盘《南非华人成长录》中所建构的中国形象时,笔者之所以将聚光镜对准其中的食物描写,也正是因为何菲黛在作品中叙述有关饮食的内容时,非常清楚食物的文化编码、族裔符号等功能,有意识地对食物进行文化、族裔等层面地阐释。比如,在说到自己家的饮食特征时,何菲黛就说:
我们何家的饮食是一种大杂烩:既有竹筷和炒锅,也有烧烤钳和烤面包箱。两个世界在我们位于勃特伦斯的家里合而为一。[1](P20)
这里,作者正是将食物制作的工具:竹筷和炒锅,烧烤钳和烤面包箱,分别看成了中国、南非/欧美世界的形象象征,才会认为同时使用这两类四种食物制作工具的何家融合“两个世界”。这段引文之后,何菲黛更是在作品中直接用中国食物“煎堆”(3)原文为jeeng dui,对应的应该就是“麻团”在粤语中的叫法“煎堆”。来比喻何家的形象特征。也就是说,在作者眼中,食物或器物都可以同文化形象建立连接并彼此互证形象。
那么,在《南非华人成长录》中有关中国食物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窥见怎样的中国形象呢?
在“龙的传人在南非”这一集中展示“龙的传人”之生活特征的章节中,有几段这样描写中国人与食物的内容:
很多时候,我们吃的食物对大多数人的胃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小时候,吃鱼时我父亲最爱和我们分享的是鱼眼睛。大大的鱼眼还在盘子上瞪向外边时,我父亲开始照顾我们吃鱼眼了:他先把筷子扎入眼眶,然后就把这个黏嗒嗒、脏兮兮的鱼眼扔在了我碗里的米饭上。最后,这个黏黏的胶球,慢慢化得只剩下那个又小又硬的珠子在我舌头上滚来滚去。[1](P19)
这些鸽子可不是宠物。养它们是为了杀它们……我感觉自己从没喜欢上那个笼子。因为我知道,这些鸽子的脖子早晚会被割开;然后,它们软下来的身体就被扔进沸腾的水中……之后,它们就被精心炸成我父亲特别爱吃的焦脆可口的美味。[1](P13)
终其一生,我都不记得父亲试着培养任何一种真正得体的爱好。消磨时光的形式……有时候就是变身大厨,给我们做焦脆的炸乳鸽,或是做姜蒜螃蟹。父亲回来拿它们大展身手之前,它们都还活着,心惊胆战地在打着小孔的盒子里,或是盛着一点水的桶中乱抓。[1](P8)
阅读上面这些有关食物描写的引文之后,最后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不是食物之美味,而是场景之残酷:无辜的动物被中国饮食制作者残杀:动物的大眼睛正在向外张望,却忽地被一个中国人扎穿,然后眼珠被夹出来扔给另一个中国人,成为其舌上骨骸;在西方人眼中温顺到可做宠物的鸽子,并没有被中国人温柔对待,而是被先割喉、再煮尸、后炸肉。这些被冠以中国食物的加工过程,对在肉类加工工业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西方人来说,是非常不人道、非常残酷的行为。这是因为,一方面肉类加工的工业化,使得吃肉的现代西方人不用再目睹血淋淋的屠宰过程;另一方面,肉类饲养企业和肉类食品加工企业在广告中刻意营造的人性化环境之宣传,更使现代西方肉类消费者觉得他们享受的只是美味,和血腥、残酷的动物宰杀没有关系。故此,一旦在文字中或是其他场景中目睹到详细的屠宰过程时,很多现代肉食者便会不自觉地将这种行为和执行这一行为的人贴上“实在野蛮、非我族类”的标签,并同之拉开距离,以保证自己在享受来自动物身体的食物时不必感觉愧疚。
有了上述关于现代西方人对肉类食物之反应的背景后,我们再阅读引文中如下两句话时就感到它们颇有意味:何菲黛说,“我们的食物对很多人的胃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又说,“终其一生,我都不记得父亲培养过任何一种真正得体的爱好”。显然,这里的“我们的食物”,指的应该是“中国人的食物”,所谓“很多人的胃”,指的应该是“非中国饮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西方人的胃”。而这样说的原因,正是中国食物在西方人看来是野蛮残酷的,是他们难以接受的。而所谓“真正得体的爱好”(proper hobby),更是值得探究:“得体”的标准是什么?爱烹饪做饭就算不得爱好么?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再阅读以下三段有关饮食的文字一并思考。
第一段,是何菲黛有关西方饮食的一段描写:
不过,我们最喜欢的还是沙拉吧台。在这里,你可以从精心摆放在灯光之下的各种大深碗里随便夹选各种蔬菜,堆满自己的盘子后再在上面浇上各种油品和佐料;你也可以把各种蔬菜和其它小零食盛到盘中,然后拌上滑爽的粉色酱料。这样的吃法在我们眼中着实迷人而富有异国情调。[1](P140)
第二段,是伍慧明(Ng Fae Myenne)的《一件红毛衣》(A Red Sweater)中有关西方饮食的描写:
西餐的风味并不算优秀,优秀的是西餐厅的环境。三把带齿的叉子。粉色的桌布。鲜花。可爱的服务生。(4)转引自:WONG,Sau-ling Cynthia.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72.
第三段,是《红楼梦》中刘姥姥的一段话。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在大观园坐席的过程中看到李纨和王熙凤端庄地对坐着吃饭,便忍不住说道:
“别的罢了,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说‘礼出大家’。”[11](P537)
理解了这三段文字中人物态度背后可能的心理动机,也就理解了何菲黛为何在前文中觉得父亲烹饪中国食物的行为算不得“真正得体的爱好”,认为中国食物是一种挑战,进而也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何菲黛在此过程中所建构的中国形象。
为了理解三个人物羡慕不同于自己日常饮食习惯的心理动机,此处不妨引入黄秀玲提出的“正确饮食”(right eating)这一概念。在讨论美国亚裔文学中的有关食物描写的内容时,黄秀玲曾颇为贴切地引用过林德赛·塔克(Lindsey Tucker)的一个观点,即:饮食代表“一种阐释世界并将自我融入世界的方式”,[9](P71)进而提出了美国亚裔文学中存在追求所谓“正确饮食”(right eating)的现象,即:亚裔美国人渴望通过在饮食方面符合美国主流文化,或者说白人饮食文化的标准,从而使自己“不再受到痛苦的局外/局内、外国/本土、他者/自我的辩证法的困扰”之现象。[8](P104)
从“正确饮食”这一角度思考,包括何菲黛在内的三个人物之所以非常向往沙拉吧台、西餐厅和荣府宴席,很有可能是因为它们都代表了一种高出其族群或阶层的身份和地位——所谓“礼出大家”——因而令人向往。“正确饮食”,比如从各种大碗中取菜然后浇上沙拉酱,或者在摆着鲜花和粉色桌布的餐桌上就餐,或者像李纨和凤姐那样端庄地小口用餐,而非“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11](P536)代表了正确地阐释世界并将自我融入世界的方式。而只有正确地将自我融入周围的世界之中,个体才能感觉到同周围世界之间的和谐,才能消解格格不入的乡愁和痛苦。因此,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在美国,都可以说是“非主流”的华裔族群,特别想通过模仿实践、消化吸收主流饮食文化而成为主流/白人族群的一员。这种心理作用下,主流白人的爱好、饮食,自然也就成为了何菲黛的标准和向往。相辅相成地,中国的饮食文化,比如其中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肉食加工过程,自然常常就成了反面教材。而“野蛮”的中国式肉食加工所折射的中国形象,被读者有意无意地简化为“野蛮”国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何菲黛在文中所描写的中国食物加工过程并非虚构,而是中国传统饮食中常见的情形。但这些加工过程中种种血腥的真实细节,加上作者如此带有情感批判和价值判断的描述,定然会造成读者评判其文化起源国的形象时以“野蛮国度”视之,这并非夸大其词。
三、药物中的中国形象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医药在保护国人健康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和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在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就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12](P8)据《2015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的数据,中医被认定为最能代表中国形象的元素,选择比例达50%。[13](P1)如果加上排名第二但“与中医密不可分的武术”,其在中国形象建构因素中的比例更是“远超书法、戏曲、饮食等元素”,[14](P34)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形象皇冠上的明珠。
但是,因为“医学文化的产生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所以中医药背后的中医文化表现出的“直观综合、注重整体的模糊性思维,与追求确定性、精确性、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西医思维相悖”。以“实证”为特征的西方近现代医学比以“思辨”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医学在理论上更有说服力;再加上“国内外中医药医疗市场良莠不齐的现状,以及西方政府及媒体对负面事件的过度宣传”,[15](P542)西方世界极易曲解甚至是刻意丑化中医,尤其是中医药。(5)据法国巴黎十三大学达芬奇医学院中医部王永洲的观察,中医的针灸东学西渐却给我们带来另外的思考,针灸在海外的传播,尤其向西方强势文化渗透,完全是一种自发状态下产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逆流”。王永洲.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复兴[J].环球中医药,2012,5(1):52-55.
在《南非华人成长录》中,作者“爸爸妈妈存放的那些来自遥远东方的药剂、药方”,即中国医药就常常以负面形象作为西药的对立面出现,在作者长大成人、明白事理的过程中,日益散发出一股令作者越来越“无法忍受的浓烈味道”。在何菲黛眼中,中医药物代表了一种“让人日益感觉愚蠢、落后”的文化形象。[1](P95)
为了证明自己有关中国医药“愚蠢、落后”的认知是对的,作者在回忆录中曾泛举过如下一些场景:
还有不少捏造的药方、制剂。它们要么是老妇人才信的迷信,要么来自日常体验或者灵机一动。被蜜蜂蛰了,我母亲会说:把水和糖搅拌好粘在蛰伤的地方,蜂毒就会被吸出来。有一次,我在亲戚家的花园时不小心跌入玫瑰丛里,我的膝盖就被抹上了一层黄油。要是肚子疼了,我母亲便会用布包住一个剥了壳的煮鸡蛋和一枚银币……在我们腹部滚动。很可能是鸡蛋的温度抚慰了我们痉挛的肚肚,让我们不再疼痛。可是,我母亲却认为这是因为毒素由硬币传到鸡蛋里了。因为现在这枚硬币由白色变成了黑灰色。现在鸡蛋成了病鸡蛋,得把它扔掉了。[1](P95)
不可否认,糖水、黄油、硬币鸡蛋包做解毒治病药物,大有“来自日常体验或者灵机一动”而与“老妇人才信的迷信(old wives’tales)”无异。作者这里列举的药方、制剂,即使在中医体系内,它们往往也只能被看成是偏方。虽然现在人们常常将偏方归于中医,甚至等同于中医,但其实二者的关系并非如此。据于业礼的观点,所谓的“偏方”,指的是“类似于单验方,(6)所谓“单验方”是指:“单方”为中医名词,是指以单味或两三味药组成的医方,用于疾病治疗时,往往能因用药单纯而直中病机,而起到预想不到的效果。中医另外还有一个名词是“验方”,“验”的意思是效验或经验,即某一味药或几味药组合起来,对于特定的疾病有较好的效果。单方和验方,两者在概念上多有重合,故往往合称为“单验方”。详见:于业礼.偏方”锅”,中医不背[N].上海中医药报,2020-08-07(12).又不是单验方。似乎可以用中医理论进行解释,但又无法说得清楚”的那些方剂。[16](P12)而且,根据于业礼的分类,这三种偏方还是偏方当中应该摒弃的一类。如此看来,单就作者罗列的这些具体药方制剂来说,认为它们是“捏造的(made-up)药方、制剂”,似乎并无不妥。
但是,作者眼中认为“愚蠢、落后”的,并非只是吸蜂毒的糖水、治跌伤的黄油以及医肚疼的硬币鸡蛋包,而是还有整个中医。在讲述这些生动可感但也令人瞠目的中医药物使用场景之前,何菲黛还讲述了另外一个有关传统中医的故事:传统中医的治疗,令外婆年幼的儿子夭折了。在解释她的舅舅之所以不幸夭折时,何菲黛外婆说:
“要是当初你祖父去找新式医生给他看病的话,他现在就能活着了。我就知道该找新式医生,我就知道该找新式医生……”外婆常常这样说。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可外婆还是忍不住这样跟人分辨。[1](P29)
从回忆录中的叙述语境可以得知,这里所谓的“新式医生”(modern doctors),就是区别于中医大夫的西医医生。而要找新式医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会像过时的中医那样只会用“毫不可信只靠运气的小作坊式的汤汤水水”。[1](P29)
至此,读者既看到了细节尽显因而其荒唐可笑也更为深入人心的“捏造”的药物,也看到了一笔带过但其直击人心的影响同样深入的“中医大夫”群像图。如此点面结合,再经作者不时点出其“愚蠢、落后”的性质之后,一个愚昧的中医及中国形象,在读者脑海中也就呼之欲出了。
四、结语
人们总是更容易只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进而根据自己看见的这些信息建构自己和他者的世界。由于历史、现实以及个人经历等原因,《南非华人成长录》中折射的中国形象难以做到全面、客观。作品描述的同中国有关的器物、食物和药物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有着极强的文学性和经验性想象。正如詹乔所言,“有些华裔作家在无从知晓现实的情况下”所建构中国形象,往往是凭借头脑里存留的“上辈传下来的菲薄的家族史”[17](P181)而打磨出来的有限视角之形象。对此,读者需要有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