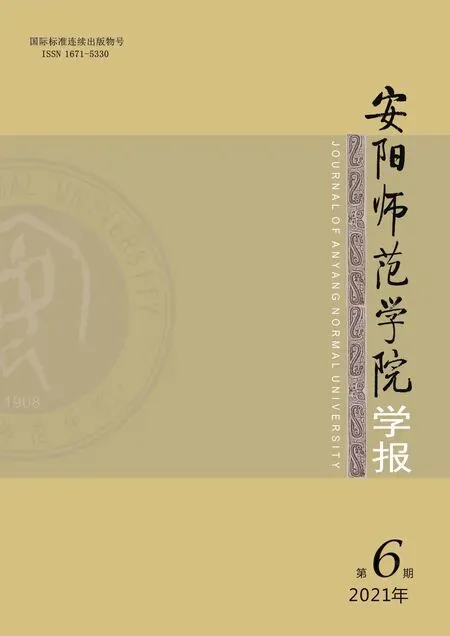论女性诗学关键词“姐妹情谊”
2021-11-28赵思奇
赵思奇,牛 露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姐妹情谊”(sisterhood)作为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的关键词,由著名黑人女性批评家贝尔胡克斯提出并发展。在此之前白人女性批评家波伏娃、肖瓦尔特等人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胡克斯在《从边缘到中心:女权主义理论》中详细地论述了“姐妹情谊”的内涵、特质与模塑过程,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成果。具体而言,当前国外学界对“姐妹情谊”的研究,重心多集中在将“姐妹情谊”作为一种视角,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阐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国内学界对于“姐妹情谊”的研究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侧重对文学作品中的“姐妹情谊”主题进行分析,例如苏亚楠的《庐隐笔下的女性身体与姐妹情谊》、冯慧敏的《王安忆<天香>中的姐妹情谊》等,把研究对象放置在某个作家作品所描绘的女性关系上,表现出女性在书写传统中自觉展露的姐妹意识,以及对男性统治秩序的反抗和消解。其二是对“姐妹情谊”进行理论建构。例如高小弘的《亲和与悖离——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姐妹情谊”》,将目光聚集于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下的姐妹书写,对女性关系中所展现的不同向度做出解释和分析。或者是对“姐妹情谊”的现实可能性进行探讨,比如郝琳的《难以构筑的“姐妹情谊”》,从内忧和外患两个方面对“姐妹情谊”产生质疑和解构,增添其悲剧性色彩。也有用多种文学批评方法阐释“姐妹情谊”,例如蒋艳丽的《多重文化视域下的“姐妹情谊”》,从社会分析、精神分析、文本分析等多重视野解读“姐妹情谊”和中国女性文学的整体发展以及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架构出多维度的历史观。但总的来说,当前研究鲜少涉及从宏观理论层面对不同群体“姐妹情谊”进行比较研究,“姐妹情谊”作为女性诗学关键词,关涉到女性运动的历史和现实,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不仅可以深入探究关键词的内涵,亦可以丰富中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
一、白人女性:对立下的反抗
“姐妹情谊”作为建立在女性共同性别经验和情感认同基础之上的同盟关系,其历史使命不仅在于消解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更在于在女性群体内部产生一种认同和团结,从而为女性传统的构建提供内在动力。20世纪中期,白人女性批评家对历史上女性的生存形态进行回溯,发现由于生理条件的制约和社会分工的不合理,导致女性长期囿于家庭之中,在社会上几乎处于缺席状态,她们也因此难以收获自己的情谊,可见,历史中女性之间的平行交流是不被鼓励的。正如波伏娃所说,“被封闭、被隔绝开的女人,不了解友情的快乐”[1](P376)。而且“在年轻女人和她的家庭之间往往不再有真正的亲密关系”[1](P376)。作为性别关系中的“他者”,女性被规定了亲密关系的对象只能指向男性,她的一切包括自己的情感都应当属于男性。但以往由男性建构的文学传统更是鲜少涉及对女性情谊的描述,伍尔夫直言,“在我看过的书里没有两个女人是很好的朋友,所有小说、戏剧里的伟大的女人不但是仅仅由男人眼里写出来,而且仅因他们和男人的关系而写出来”[2](P116)。因此,男性话语体系关涉女性的书写是主体之外的客体,缺乏言说的空间和权力,更无妄想能成为不平等的性别结构的批判者,而女性关系也面临被挤压、歪曲乃至妖魔化的宿命。
当女性试图塑造姐妹之间的关系时,被认为是对现存秩序的破坏和威胁而遭到阻扰甚至攻击,“男性批评家们把女性之间的关系看作是邪恶的和不自然的……即女人的团结威胁着男性统治和男性特征”[3](P55),这恰恰是女性构建“姐妹情谊”的初衷,也反证了这一行为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波伏娃认为,“女人由于封闭在自身共同的命运当中,通过一种内在的共谋联结在一起”[1](P376)。“共同的命运”是指女性在生理经验和社会身份上所共同构成的性别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正如朱迪·劳斯顿(Jodie M.Lawston)所言:“建构‘姐妹情谊’的框架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女性所遭受的性别压迫,这是令人压抑的;另一部分是聚焦于女性作为照顾者的经验,而这是压抑和欢愉并存的”[4](P649)。也就是说,“姐妹情谊”得以建构的基础包含了女性历史和生理特征两方面。首先,女性在历史中所遭受的性别压迫被看作女性联盟的现实基础;其次,女性经验的特殊性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女性独特的生理特征,赋予女性相似的情感体验,她们通过怀孕、分娩、抚养小孩等过程,分享自己作为母亲、妻子的角色经验,也分享孕育生命带来的神圣感,这正是她们能够团结在一起的纽带,也是“姐妹情谊”内在的情感基础。由此可见,“内在共谋”为女性的反抗和言说提供了平台,客观上为女性寻找主体性提供了契机。
如果说波伏娃提出的“反抗”是建立女性同盟关系的契机,那么肖瓦尔特便是从文学传统入手践行“姐妹情谊”。肖瓦尔特认为并非不存在女性文学传统,只是被刻意抹掉了,因此,她从文学史的重构开始,将历史中被掩盖的女性书写重新挖掘出来,不只是伟大的山峰,还包括那些不出名、被忽视的沟壑,最终形成一条脉络清晰完整的女性文学谱系,并在社会中发展出“女性亚文化群体”,而在这个过程中,“姐妹情谊”是重要的粘和力。肖瓦尔特试图用女作家之间的联合对以往的男性文学传统进行消解,并摆脱传统出版业内的“父权商业控制”[5](P27),让女作家得以进入到正式的文学生产活动中。因此,她提出“女权主义者彼此间极为忠实,她们需要与其他女性结成紧密的充满感情的友谊,当然也需要女性听众怀着爱心的奉承”[5](P25)。女作家之间相互支持的力量,女性前辈在精神和传统上给后辈的滋养,女作家与读者之间情感上的双向交流,不仅满足了女性文学传统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是“姐妹情谊”模塑的必然过程。
和波伏娃相同的是,肖瓦尔特也质疑了“姐妹情谊”的牢固性,她不止一次提到女小说家之间尤其女性作家和女性读者之间的竞争和敌对情绪,最严厉的指责往往来自同性之间。女性的性别经验可以成为结盟的成因,但并非是坚不可摧。首先,在男性主导的性别结构中,被动的“他者”角色使得女性不具备完整的主体性,这也成为一直以来女性被诟病具有“永恒的女性气质”的重要原因。其次,女性作为呈现在家庭单元中的个体,“从来没有以‘群体’的身份实现充分的自我表现,几千年来,她们分散存在于每一个‘他的’家庭中,其人格与个性,也具体地融化在对‘这一个’男人的依附中”[6](P53)。家庭成为女人行使权力和成就自己的唯一场所,她们被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囚困于一座座孤岛当中。并且随着女性年龄、身份的变化,她们逐渐靠近封建家庭的权力核心,成为男性家长的傀儡和延伸,正如肖瓦尔特所说,“妇女一般被视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变色龙’,所体现的是其男性亲属的阶级、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5](P8),而在这个过程中女人是需要通过不断竞争的方式来维持自身的地位,因此这带走了女性之间建立情谊的可能性。
在女权运动早期,女性关系之于女性解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泰勒强调“如果没有团结,女性运动也将不复存在”[7](P282),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从女性作为被压迫群体的社会现实入手,将构建同盟关系视为反性别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白人女性认同“姐妹情谊”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但将建构的关注点局限于白人范畴内,忽略了少数族裔女性群体,受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的质疑,她们认为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将自己的经验等同于女性普遍的经验,忽视了差异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姐妹情谊”,会造成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化。
二、黑人女性:差异中的平等
白人女性强调性别压迫是女性联盟的基础,正是从反对单一的“性别压迫”入手,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开始了对“姐妹情谊”的深层发掘。胡克斯指出,“过分自信、自我肯定的妇女常常在女权运动中没有一席之地”[8](P54),缺席感促使她们对女性主义运动产生误解和排斥情绪,客观上造成女性群体内部的分歧。同时,白人女性错误地将黑人女性在生活中展示出来的强大力量等同为她们已经不属于“受压迫者”的范围,因此认为“黑人妇女已经得到了解放”[8](P55),她们不需要借助“姐妹情谊”的力量,无形中将黑人女性排除出同盟阵线。将女性置于“受害者”的角色,一方面是女性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也是在无形中建立了一种反向的强有力的控制手段,不断地固化传统的霸权结构,这正是黑人女性批评家的担忧和质疑。同时,胡克斯发现,正是这些“最渴望被视为受害者的、最强调受害者角色的妇女却要比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妇女更加有特权,更加有力”[8](P54),揭示出隐藏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特权背景下的种族压迫和阶级分化。如果说白人女性的“姐妹情谊”是从两性关系的二元对立出发,以共同创伤作为依据来构建女性同盟,那么黑人女性则更注重从女性群体内部出发,以多层面差异作为立足点,寻找姐妹情谊的现实可能性。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一书中,胡克斯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概念:“支持”。她强调,“支持”是跨越了阶级、种族、意识形态差异的团结,具有更强的包容性。黑人女性认为白人女性提出的“团结”预先设定了其对象在社会地位、成长环境以及心愿诉求方面具有一致性和相似性,并不符合当下女性群体四分五裂的现实情况,“支持”则更强调在无法轻易消除矛盾的情况下,承认矛盾,并用一种更大的善意超越分歧。
爱丽丝·沃克关注黑人女性祖先和后辈间的血缘关系,她说“我在故事里搜集我的祖先们生活的历史和精神线索,在创作过程中我感到一种快乐和力量,体味到我自己的延续”[9](P53)。这是对天然的女性谱系的确认和感悟,女人从中寻找到了可以依附和归属的力量。而胡克斯从黑人女性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将女性之间的联系视为必不可少的部分,描绘出更丰富的女性谱系。“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关系,可以作为我们团结的基础的是以结束性压迫为目的的女权运动的政治职责,而不是共同牺牲或者对一个共同敌人的错觉的反应。”[8](P56)这既是对白人女性霸权主义的质疑,更是对具有包容性的女性同盟的寻找,“妇女们需要在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形势下走到一起”[8](P76),在差异中建构统一,无疑是基于当前女性现实所提供的方法论指导。黑人女性批评家对女性谱系的重视是源自于对女性传统的渴望。女性传统关乎女人的身份界定,尤其对应于那些生活在美国的非裔黑人女性因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难以追溯自身的历史,然而她们可以在某些特定的传统中寻找到身份认同,例如:吟唱布鲁斯音乐、缝制百纳被、坚持口述文学等等。这些极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一方面是黑人女性日常生活经验的高度凝结,另一方面也为女性间的联合提供了支持和鼓励,让“姐妹情谊”成为建构女性传统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女性之间的对立冲突是建构姐妹情谊的最大障碍。造成冲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性别问题,性别歧视不止存在于两性之间,在女性群体内部也同样明显。“性别歧视教妇女们成为男性的性客体,那些对此提出批评的妇女们轻视那些没有对此提出批评的妇女,觉得自己比她们优越”[8](P56),这会进一步加剧女性群体内部的不平等现象。种族也是重要原因,西方哲学传统带有深刻的“进化论”思想,“白人至上”的特权意识影响了白人女性的思维,她们试图让自己成为姐妹关系、甚至女性运动中的领导者,促使姐妹情谊掉入霸权主义的陷阱中。阶级问题也不容忽视,在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制约下,黑人女性经济、社会地位层面受到挤压,客观上阻碍了和白人女性结盟的渠道。托尼·莫里森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讲述了贫穷的黑人女孩佩科拉、弗里达和克劳迪亚之间真诚的友谊,而当她们试图和富足的浅肤色女孩莫丽恩交朋友时却受到了戏弄和拒绝。种族、性别和阶级这些现实的鸿沟,使得“姐妹情谊”往往呈现出解体的局面。
针对上述现状,自我定义成了黑人女性的有效应对策略。非裔美国女性在以白人为主的学术机构(PWIS)中,应对充斥着种族和性别刻板印象的“扭曲房间”(crooked room concept),是她们重要的学术使命。研究人员发现,在PWIS环境中,一个人可能通过将自己与已经“扭曲”的房间对齐,仍报告说自己是完全笔直的”[10](P57)。在这种环境中,保持自己的背景或种族特征,不至于迷失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规范和习俗的世界里,定义自我尤为重要。具体而言,在已有的社会身份和保持“直立”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不必频繁地启动应对机制,以在白人主流文化空间中穿行,又可以将非裔美国女性的社会动态带进上述空间中,有效互动和融合,为姐妹情谊的构建创造包容空间。
三、“姐妹情谊”在中国
在西方女性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女性诗学从五四时期始呈现快速而又自觉的发展状态。女作家们致力于对自身性别身份的阐释,将原本被隐匿的女性经验展现在时代面前,“姐妹情谊”作为不可回避的主题,引起了重视,她们将“姐妹情谊”和女性的自我意识、自由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个体生存中窥探出集体的命运走向,从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现象,并随着中国女性诗学的整体变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20世纪早期,在启蒙思潮影响下,反对封建父权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姐妹情谊”故而作为一种反抗的手段呈现在女性文学之中,这与西方女性反对性别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本质上都是对女性失落地位进行申诉和抵抗,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有所不同。在本土,女作家们试图用女子间的联盟,消解传统父权体制下的社会秩序,不过她们的力量还尚显单薄。在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中,学生云罗和影曼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时,产生了介乎于同性与异性之间的暧昧感情,作者故意使用这样一种模糊不清的方式来对抗传统父权制文化中的核心观念,即异性恋的价值取向。但这种欲说还休的关系最终随着一位女子的结婚戛然而止。庐隐的《海滨故人》中,五个姐妹在年少时结识下了深厚情谊,但最终她们或者走入婚姻,或者孤独终老,昔日的乐园不复存在,徒留感伤与怀念。因此,这个时期的姐妹书写正如女性主义的发展道路一样,刚刚兴起还显得青涩稚嫩。尽管这些女孩子们怀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姐妹关系当中,却只是构筑起了一个个空虚且脆弱的女儿国,敌不过封建秩序的强压,很快便烟消云散。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人道主义的呼声,“姐妹情谊”的内涵也更加深入,从外在反抗转为对内在的寻找,具体表现为对女性对自我意识、自我欲望的发现和肯定。张洁在《方舟》中刻画了三位中年女性,于婚姻、家庭、事业中经历了种种不幸,面对外界的困扰和伤害,她们在物质、精神上陪伴支持对方,“姐妹情谊”最终成了她们的寄身之所。王安忆的《弟兄们》同样也是讲述了三个女人之间的“姐妹情谊”,但作者巧妙地将故事情节置于身份、时空的多重变化之中,借由她们之间的关系表达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主题,使其产生了复杂的张力关系。在此,姐妹关系充当了女性成长过程中的自我启蒙的角色,是姐妹之间的交流和指引让她们完成了从“人”到“女人”的蜕变。随着西方女性诗学身体写作的引入,女作家们倾向于将女性欲望融入姐妹情谊的叙述中,女性的身体从男人的凝视中走向女人自己的欣赏。陈染的《与往事干杯》中,肖濛作为言说的主体,大胆地向乔琳讲述自己的性经历、性欲望以及深藏在心底的负罪感,这既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分享和共情,也是一个女人内心深处的独白。而在林白的《致命的飞翔》中,女性的欲望和身体被表达地更加直接,无论是李莴还是北诺都对女性身体有着痴迷般的沉醉,她们会对镜自赏,毫不掩饰自身的性欲望。这两人之间虽然并没有过多的交流,但李莴将北诺当作一个幻想的膜拜对象,是自我意识的折射,她把自己对于身体、欲望和性的美好幻想都寄托在对方身上,“姐妹情谊”承载了女性身体解放的体认。由此看来,对姐妹情谊主题的深入也伴随着对女性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入,这不仅仅是偶然的个体行为,更是社会时代下女性的集体意愿,与女性解放事业、社会革命和民主化进程紧密相连。
当然,女作家们秉承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描绘出完整的女性关系,尤其是缠绕在“姐妹情谊”身上的多重矛盾。在《弟兄们》中,姐妹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老三毕业之后选择回归家庭,时空环境发生了转变,再加上男性关系的介入,这些外部条件迫使“姐妹情谊”最终解体。如果继续深究不难发现,“姐妹情谊”自身也存在着难解的悖论。“姐妹情谊”建立的前提,是在女性性别经验和情感认同基础上形成团结关系,这种集体性势必与女性个体之间产生对立,维护集体性就意味着个体的牺牲,凸显个体性又会面临“姐妹情谊”的牺牲,正如魏天真所言,“这也许就是女性关系的悲剧性所在”[11](P60)。姐妹情谊能否兼顾个体价值和群体利益,很大程度决定了其现实可行性。此外,复杂的外部环境也会影响女性社会身份的建构,把她们隔离成不同的单元,多重身份的割裂,将女性置于难以平衡的矛盾关系中,阻碍了女性主体性转变。女性的自我意识呈现出一种非统一性特征,也就是说,女人在不断成长、建构自我的过程中是矛盾的。她们在青年时渴望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中年时希望成为合格的母亲、温柔的妻子,但很多时候导致她们的各种身份无法兼容,因此,女性的自我建构始终是非一致性的,每当她们试图寻找真实的自我个性时,她们就会重新回到姐妹身边,获得肯定和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在毕业多年之后,老大和老二之间仍然存有能唤醒对方自由意志的力量,但当她们被妻性和母性所占据的时候,“姐妹情谊”很快就会面临着破裂的危险。上述众多的矛盾对立关系,让女性对“姐妹情谊”产生了复杂的认知,她们既希望收获认同,又不可避免地对姐妹关系产生质疑。
总之,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性诉求,本土“姐妹情谊”主要聚焦于文学批评领域,彰显在外部环境影响下,女性个体之间、女性个体与女性群体之间的矛盾关系,既可以是温情脉脉的,也可以是冷漠疏离的,在流动的时间线索中见证女性的成长变化,探索女性发展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引人思索“姐妹情谊”是存在于文学叙事中的乌托邦书写,还是现实的真实再现。
四、结语
“姐妹情谊”作为呈现女性关系、建构女性传统的关键词,是一个不断发展、持续变化的理论话题。无论是白人女性主义者首先提出“姐妹情谊”的可能性,在两性关系的对立范畴中确认其价值和意义,从共同压迫的历史中建立“同盟”关系;还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性别、种族、阶级平等的基础上得出来的相互理解、尊重差异的支持关系;亦或是中国女性诗学用作品来阐释理论,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一幅幅真实的“姐妹情谊”图景,都可以看作是不同女性群体为延续姐妹情谊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这充分表征了“姐妹情谊”作为女性诗学关键词的发展前景,映射着女性群体结盟关系的重要价值。而姐妹情谊又不仅只局限于女性关系的内部发展,同时还作为两性关系的窗口,为实现健康友好的性别环境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