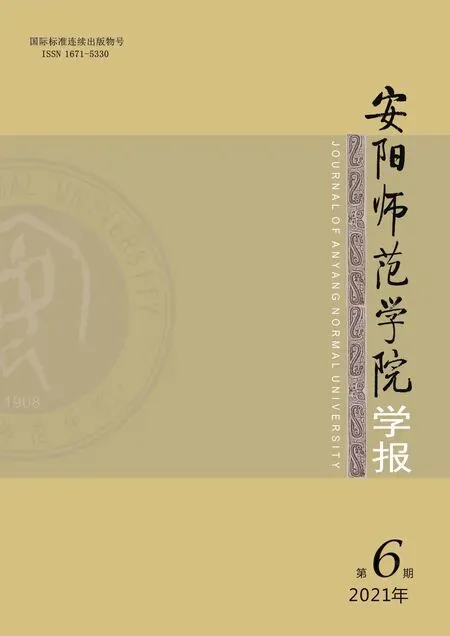“二辰丸”事件中的日本外交策略
2021-11-28陈珍
陈 珍
(1.常州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2.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积极推行大陆政策,加强了对中国、朝鲜等近邻的侵略。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在亚洲的地位发生逆转,日本成为亚洲强国。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强敌沙俄,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地位,同时也刺激了侵略野心。日本在华的扩张侵害了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在与列强的竞争中,日本意识到仅靠本国国力,力有未逮,因此调整策略,改善外交环境,并加以利用。“二辰丸”事件的解决即是日本积极运用有利的外交环境,加强对中国侵略的典型案例。
目前,学界对“二辰丸”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葡海权之争、“二辰丸”事件与抵制日货运动的关系等,从外交策略角度考察“二辰丸”事件的研究成果不多。现有研究多是从清政府的角度出发,认为清政府的软弱和日本的强硬态度造成了中国外交上的失败。例如,有学者认为清政府在“二辰丸”事件交涉中虽然一度持强硬态度,但是这种强硬态度不过是昙花一现[1](P57);有学者认为日本的强硬外交政策才是造成清政府外交失败的原因[2](P29)。清政府的软弱和日本强硬的外交政策固然是造成“二辰丸”事件交涉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日本灵活的外交策略也不容忽视。文章拟考察日本在解决“二辰丸”事件中的外交策略,揭示其侵略中国的手段。
一、“二辰丸”事件始末
1908年2月7日(正月初六日),两广总督张人骏上奏“二辰丸”事件的经过:
日商船第二辰丸装有枪二千余支,码四万,初四日已刻到九洲洋中国海面卸货,经会商拱北关员见证上船查验,并无中国军火护照,该船主无可置辩,已将船械暂扣,请示办理前来。査洋商私载军火及一切违禁货物,既经拿获,按约应将船货入官,系照通商条约第三款并统共章程办理,历经总署咨行有案,自应按照遵办。迭饬将船货一并带回黄埔,以凭照章充公按办(罚办充公,原文注)[3](P3757)。
张人骏认为,日轮没有中国军火护照,属私运军火,故将日轮扣留,准备将船上军火没收充公,并建议外务部将事件经过及处理结果告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日本在中国领海走私军火,事实清楚,且日轮船主也直认不讳,在此情况下,中国官员扣船、没收军火的处理本无不妥,但是日本领事却撺掇船主照峰翻供,并倒打一耙,反咬中国官兵非法拘留日本船只[4](P175)。
日本国内,以日本船主同盟会为代表的民间力量极力声援“二辰丸”,认为该船并无违法行为,要求立即释放。日本政府也对“二辰丸”事件持强硬态度,认为如果清政府一味推诿,不肯赔偿,则日本政府将采取断然措施。[5]日本外务臣林董放言:“二辰丸”停泊之处,属于葡萄牙海界。“二辰丸”所运货物,已经获得官方批准,并未违背何款条约。日本政府已预备实行既定方略,坚持让清政府赔偿损失。[6]
2月14日,林权助就扣留“二辰丸”一事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态度强硬至极。声称“二辰丸”是因为风浪太大,才暂时在九洲洋一带躲避,并指责中国官员暴力执法,强行将日轮上的日本国旗换成中国国旗。主张该船军械是运往澳门之物,已经得到葡萄牙官员的允准,不属于走私;向清政府提出“放船”“还旗”“惩办官员”等要求。林权助的电文中涉及日方认定的事实,特别是针对日轮所停位置的海权所属提出了质疑,企图引起中葡海权之争,以便从中渔利。电文内容如下:
据驻广东本国领事电称:本国商船第二辰丸装载货物,由本国开往澳门,于本月五日,即华历正月初四日上午抵该口附近。适是日海面浪大,潮水不顺,未能进口,不得已在九洲洋方面东经一百十三度三十八分二十秒、北纬二十二度九分四十五秒地点暂为下锚,等待潮水浪顺。……查第二辰丸下锚地点是否在中国领海内,如重行精测,自可显然[3](3757-P3758)。
面对日方的狡辩和无理要求,清政府唯恐张人骏所奏内容出现差池,予日方以口实,在外交上陷入被动。2月15日,外务部致电张人骏,要求核查日轮停泊位置,弄清撤换日旗经过等。2月17日,张人骏复电外务部,认为当地官员对该案件的处理并无不当,主张日轮是否释放或者充公,必须经过会同查询才能决断。2月18日,张人骏再次致电外务部,确定日轮所停位置确系中国领海,解释撤换日旗是为了避免引起葡萄牙船干涉,并且在葡船离开后立刻将龙旗收回;指出日本领事言辞强硬是因为害怕查明真相后,清政府会扣留“二辰丸”,给日商造成损失。为了妥善解决该事件,张人骏致电驻日公使李家驹,要求其与日本外务省据理交涉,同时建议“坚持会讯办法,免堕狡计”,请外务部“妥商日使,转饬日领,照章会讯”[3](P3759)。
3月1日,驻日公使李家驹转述日本外务大臣林董的意见书。在意见书中,林董否认日轮走私军火、日轮所停地点为中国领海、日方船长答应起卸船上军火等事实,指责清政府无理取闹,擅自扣留日本船只,违反国际法。并指出撤换日本国旗,是对日本政府的侮辱,要求清政府立刻释放被扣船只、赔偿损失、惩办相关官员。并且恫吓清政府,如果此事处理不当,将引起两国纠纷[3](P3765)。日本政府颠倒黑白,将责任全部推到清政府身上。在与清政府的交涉过程中,言辞强硬,以武力相威胁,企图逼迫清政府屈服。
张人骏有理有据地对日方的狡辩予以驳斥,但在外务部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先行释放被扣日轮,只扣留军火。张人骏深知日人无信,提醒外务部日本人狡诈,即使释放船只,满足日本人的要求,也难保日本人不节外生枝,提出更过分的要求[3](P3765)。
事实证明张人骏并非杞人忧天,日方果然得寸进尺,在释放船只之后,不准中国起卸船上的军火,并于三年后旧事重提,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损失。日方提出将船上军火高价卖给中国,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慨、不满,终于点燃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的经济受到巨大打击。
3月4日下午,林权助与翻译高尾享一起来到那桐家里,与那桐、袁世凯、联芳等人协商“二辰丸”事件的解决方法。日方认为军火不同于鸦片,没有明文规定必须取得海关允准。针对中国提出的请英国提督公断的建议,则以日轮所停位置未判明海权所属为名予以拒绝。威胁说,假使中日两国请英国提督公断,则必须弄清该处海域的归属。如此一来,必将牵涉葡萄牙政府,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清政府害怕扩大事端,提出三条解决办法:先将第二辰丸释放,另行具结候査;军火先行扣存,俟查明后另行核办;下旗一节,俟査明究系何人错误,酌量办理,以表歉忧。
面对清政府的让步,林权助坚持“具结释放是决办不到,扣存军火亦不能允,”要求必须追究下旗军官的责任。借口清政府扣船是违约之举,日本政府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进一步向清政府施压,赤裸裸地进行武力威胁。同时又表示如果事件顺利解决,日本政府愿意制定军火出口章程,协助清政府稳定社会治安。对那桐等人又打又拉,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
3月5日,外务部迫于压力,致电张人骏,指示就换旗一事进行道歉,并惩办相关官员。6日,张人骏复电外务部,认为“放船”“道歉”“惩员”等貌似小事,但是事关重大。“二辰丸”事件如果交涉失败,“则条约、关章均成废纸。查缉济匪军火之令立须收回,即不收回,亦同虚设。”张人骏认为“二辰丸”船上的军火必定是卖给盗匪之物,如果不能没收充公,最后会落入盗匪之手,危害治安。因此,极力向清政府澄清利害关系:“査察两粤匪情,澳门接济匪械之路不断,盗匪必无清日,揭竿蜂起,仓猝可成。虽有善者,不知其可。且本案失败,我国从此于各国商轮私运军火无敢过问,国权浸失,桀黠生心,滋蔓将及于沿海各省,如大局何?”[3](P3771-3772)
同日,林权助在给清政府的照会中污蔑广东水师之行为实近海盗,以强硬态度向外务部提出四条要求:立即将第二辰丸及所载货物尽行释放;侮辱日本国旗一事,清政府必须依适当之方法,向日本政府表明歉意;清政府必须严罚所有有关官员;赔偿一切损失。在该照会中,虽然再次提到日轮所停地点归属不明,但是日方也深知所停位置确是中国领海,唯恐海权所属确定后对日本不利,因此蛮不讲理地补充说明道:船舶所停位置即使属于中国,日本政府依然认定中国官兵所作所为皆是违法行为,从而将按照日方的意愿采取行动[3](P3777-3778)。可见,日方提出所谓“二辰丸”停泊位置归属不明,只是为了挑起中葡两国的纠纷,以增加清政府的外交压力的手段。林权助威胁清政府尽快答应日本政府提出的所有要求,否则日本政府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向清政府下达最后通牒。至此,日本政府威逼清政府的外交态度已经暴露无遗。
为了促使清政府能够早日下定决心,日本政府又抛出诱饵,承诺不会将军火卖给党匪,并表示日本政府愿意协助清政府防范外国军火走私。3月13日,林权助向外务部提出和平解决“二辰丸”事件的条件:中国政府派兵舰升炮,对撤换国旗一事表示道歉;惩办相关官兵;立即无条件释放“二辰丸”;清政府赔偿所有损失;清政府以“二万一千四百元”的超高价格购买船上的军火。并指出日本政府虽然答应协助清政府防范外国走私军火,但是与本案件不相牵连。
清政府在日本强硬外交政策的威逼下,态度愈加软化,又得日本答应不将军火卖与“匪党”,消除了心中的最大担忧,无心再与日方纠缠,答应了日方的要求。时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之所以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全是因为日本人承诺严禁日商将军火贩卖给中国人的缘故[7](P13)。“二辰丸”事件发生的时候,正值清政府面临内忧外困之际。日本外交人员及日本政府抓住时机,对清政府威逼利诱,迫使清政府答应日本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日本政府对“二辰丸”事件的处理结果“甚为满足”[3](P3792)。
二、“二辰丸”事件的外交背景
1894年7月16日,日本利用英俄矛盾,签订《日英新约》。《日英新约》的签订,使日本政府找到了靠山,有了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的底气[8](P65)。英外相金伯理在签订日英条约时公然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大军还远为有利”[9](P62)。7月25日,日本海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中日甲午战争。1902年1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澜斯登(Lansdowne)与日本驻英公使林董签订盟约,第一次日英同盟成立。日英同盟的成立,使日本获得了与俄国作战的勇气。清政府对于英日同盟感到“宽慰、羞辱和恐惧”,对在西方拥有最强海军的英国与在东方拥有最强陆军的日本结盟普遍感到绝望,因为清政府对日本有可能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无能为力[10](P162-163)。这种恐惧、绝望的情绪使清政府与清朝官员在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时,更加畏首畏尾。
日俄战争即将结束时,日本为了提高对俄媾和的地位,应对将来俄国的报复,于1905年8月12日与英国签订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为侵略中国东北、吞并朝鲜铺好了道路。日俄战争后,日本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广泛寻求西方列强作为盟国。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曾经说过:以帝国之国力,很难在军备上超过欧美列强中任何两三国的同盟联合,因此在外交上必须一方面加深与同盟各国的交流,一方面极力防止与帝国利害不一的国际间的联合[11](P707)。
1907年6月10日,日法两国为了保障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签订了《日法协定》及附属宣言,并为日俄关系的缓和与《日俄协定》的签订打下了基础。1907年7月30日,《日俄协定》签订,日俄双方由冲突变为合作,由争夺变为瓜分在中国的权益。《日俄协定》为日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外交环境,日本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1907年是日本外交大丰收的一年,“其纵横捭阖之结果,远东形势一变,欧洲大局亦因之转移”[9](P49)。外交上的成功让日本摆脱了来自列强威胁的同时,又加大了外交上的筹码,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日俄协定》签订后,日本改变外交策略,在处理吉林间岛问题、“二辰丸”事件时,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12](P4)。
日英同盟对日本来说是最重要的外交胜利,英国在“二辰丸”事件中也尽职尽责地扮演了盟友的角色。“二辰丸”案件交涉陷入僵局后,外务部向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教解决问题的方法,赫德给出17条建议。主要内容是:澳门既居洋界地位,则澳门前列之海面即为通行之海,并非中国之水面;“二辰丸”上装有运往澳门之货物,则此货无论何物,及如何由船运至澳岸,所挂之日本国旗,及指运之澳门洋界,均得保护所运物品。中国海关在日轮起运货物时,不能有任何干涉,中国官员没有权利扣留日轮及船上货物。总之,现所查悉之各情事,都足以表明日本没有过错。建议外务部释还船只,鸣炮致歉、进行赔偿,并认为这样也无损清政府体面[3](P3762)。外务部出于对赫德的信任,将建议转达给张人骏,希望按照建议办理。
3月5日,张人骏针认为赫德的建议是在“事出追揣,于细情或未尽悉”的情况下做出的,对赫德的意见逐一反驳,指出中国官员的做法并无不当之处,中国官员之所以扣留日方轮船,“全因驻粤日领不肯照办之故,中国可不任咎”[3](P3768-3769)。
赫德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张人骏的“电文所列各节,甚为详细”,感到“不胜钦佩”。但是依然坚持“惟所论虽为有理,然似凭情形可疑而著此论断,窃恐不足折服彼造之心”。并进一步为日本辩护,“由日本装载军火运送葡国,亦非不应为之事。船身甚大,水浅不能进口,停于口外,亦属常情。且至被拿以前,该船并无何项举动。现该船被获,若未经日本官员认系罪有应得,则此面即不能竟行充公。至所论会讯一节,原系善法,惟系因两造各执一词,可由会讯判断。今闻日本官员并不认该船有违犯章程之事,是彼面不允会讯,则谈判亦无由可开”[3](P3782)。赫德虽然声明没有袒护日船之意,但是他久居中国,深谙清政府处世之道。一句“恐不足折服彼造之心”,可谓抓住了清政府的“七寸”。赫德的“好心建议”提升了日本政府对清政府威逼策略的效果。
清政府一直以为赫德是自己人,本想请赫德主持公道,但是赫德却建议清政府“释放船只”“鸣炮道歉”,向日方赔偿。更重要的是,赫德认为“澳门前列之海面即为通行之海,并非中国之水面”,这大大损害了中国的领海主权。赫德不仅没有如清政府所愿,提出对中方有利的建议,反而完全站在日方的立场。对于自己的行为,赫德解释道:“我从一个去中国为女王陛下服务的英国外交官成为这个国家的政府大臣,这件事竟然如此神奇地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禁为命运深深折服,但我仍然在为女王陛下服务,我永远是她和大英帝国的忠实臣民,当然我也在为中国服务。……英国不能失去中国,不能失去中国海关!中国对我们太重要了,有了它,英国在全世界的贸易和统治才是完整的。”[13](P61-62)
赫德作为一名英国人,在处理事情时不可能不考虑英国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身为中国的总税务司,却要偏袒英国的盟国——日本的原因。赫德的继任者安格联也完全赞同赫德处理“二辰丸”事件的立场,并将它作为海关处理各种案件的准则。[14](P128-129)
英国外务部虽然声明“二辰丸”事件不在英日盟约范围之内,英国没有理由干涉,但是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朱尔典却“忠告”中国外务部:解决“二辰丸”案件最妥善的办法,是答允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同时请相关各国会同议商,严加监督私运军火之事。日本必定会协助清政府加强取缔私贩军火案件。英国的“忠告”正好与日本的做法不谋而合。1908年3月15日,《新闻报》转载了日本《时事新闻》刊登的朱尔典请英国外务部训示,以便调停“二辰丸”一案的消息。[5]“二辰丸”事件交涉结束之后,《时事新闻》大赞朱尔典相助之功。
“二辰丸”事件发生后不久,林权助以日轮所停位置归属不明为该船的非法行为开脱,同时利用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挑拨葡萄牙殖民者与中国争夺领海主权。葡萄牙殖民者为了领土野心,与日本一起共同向清政府施压。1908年2月18日,葡萄牙驻华使馆致电外务部,提出“查该船系装载枪支,运卸澳门。该船被拿,有违葡国所领沿海权,并有碍葡国主权,阻害澳门商务,本署大臣甚为驳斥。”[3](P3759)对此,有研究认为,日本政府之所以如此嚣张地欺压中国政府,其罪魁祸首就是不顾事实、恶意诬证的澳葡[15](P687),实则葡萄牙政府只不过是日本“以夷制华”外交策略的棋子,其目的是借助葡萄牙政府的力量,向清政府施压。
日本为了达到“以夷制华”的目的,还充分利用舆论宣传,在国际上制造有利于本国的消息,使各国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二辰丸交涉问题,孰是孰非,两言而决。拘获之地……惟果在何国领海,言人人殊。或曰中国领海,或曰葡国领海,或曰公海。”但是已有外国公使认定为在公海。尤其是英国舆论,在处理“二辰丸”一事上非常袒护盟国日本。[6]对于日本利用西文报纸取得外交优势的情况,国人早有察觉,故建议清政府“广设西报”以抵制日本的外交宣传。[6]
1908年4月18日,刘式训致电外务部,报告法国关于“二辰丸”事件的舆论已经被日本所左右,“此案争执之时,各报所登,或云在澳门水面,或云虐待日船水手,或云澳门官用军火,凡此皆系日本消息。”受此影响,法国既有《日法协定》,两国又有共同利益,并且法国人觉得中日相争,有利可图,出现了“法国银市以日本不惮寻衅为财力充足之据,又逆料战事结束可十倍取偿于中国,因此旬日间日本国债票异常腾涨,迨此案商结,仍复落回原价”的局面[3](P3802-3803)。
日英同盟的成立,《日法协定》《日俄协定》的先后签署,使清政府对日本更加忌惮,惧怕日本与诸列强联合起来对付自己。3月11日,外务部因“近闻日已将此案传告各国”,特意致电驻俄的萨萌图,命其待“彼中官绅、各驻使谈及此事,希将原委申明,以免误会。公论如何,随时电复,并照转英、法、德、比、荷、意、奥、美各使照办。”[3](P3786)清政府虽然意识到需要将案件原委告知各国,但与日本相比,实属后知后觉。一步落后,处处受制于人,不得不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正如《申报》评论的那样:“自四国协约成,而我国之外交界,已无容喙之地……盖弱国本无外交也。”[5]
三、结语
“二辰丸”事件中的外交失败,再一次表明清政府一贯坚持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已经连治标的效果都达不到了。日本政府在长期交涉的过程中,已经摸清了清政府的外交风格,“认为只要‘坚守地位’‘勿躁’。以‘忍耐渐进手段’即可获得最后的胜利”[6]。日本政府利用强权对清政府进行威逼的同时,还抓住清政府害怕革命党得到军火的心理,以协助防范外国军火走私为条件进行利诱;借助葡萄牙政府的力量向清政府施压的同时,注意舆论宣传,利用英日同盟、《日法协定》、《日俄协定》带来的外交优势,运用“以夷制华”的策略,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