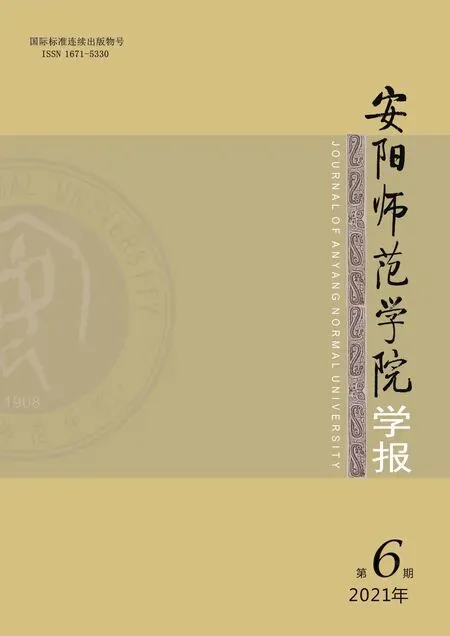民国城市生活中的政治视野
2021-11-28高路
高 路
(江汉大学 城市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56)
一般认为,充满浓厚世俗色彩的市民文化兴起,是现代文化兴起的重要特征。世俗性的市民文化追求个人幸福、欲望的满足,冲破前现代的禁欲主义、宗教迷信、礼教伦常的束缚,成为资产阶级发展的精神动力。有学者认为,现代性表现为三个分离,其中两个分离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经济与(非功利主义)道德的分离。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结果是经济被视为独立于政治的领域,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经济与道德分离的结果是实利主义的经济观取代了道德观。[1]但是,在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政治与世俗在城市文化的建构中并不是那么截然分立的。自中国城市化运动起步以后,以世俗化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市民文化得到了迅猛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在如上海这样的沿海口岸城市,吸收西方城市文明得天独厚,十里洋场、霓虹摩登、轻歌曼舞成为城市文化的标志符号。可是,尽管在市民生活的层面,不可阻遏地呈现出世俗化特征,在引领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和城市执政者的视野里,却一直都在将城市文化纳入政治的范畴里。哈贝马斯认为,欧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前身是文学公共领域,随后才从文学问题转向政治问题,形成政治的公共领域。而近代中国的各种有识之士则不同,从一开始所关注的就是政治问题,“其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公共的文学艺术问题,而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传统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2]
一
早在晚清时期,一些地方的城市改良活动已经具有道德标准至上的政治味道。根据王笛的介绍,在20世纪初的成都戏曲改良中,城市改良者们对城市文化进行改良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符合他们心中文明标准的新型文化,却并没有在意底层大众的利益需求,因此出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3]这已经说明一批城市精英在进行城市改革伊始,就树立了一种政治的框框。到了国民党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以后,政治对于城市文化的影响就更加浓厚。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尤其是随着中日之间战争的逼近,学者和政治家们对市民文化的评判标准往往是政治标准至上,政治的需要取代美学的情调,民族主义思想压倒市民的个体主义意识。论者常常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去评判城市文化,并力图构建一种以民族主义为指导的新城市文化。
著名市政学家殷体扬在20世纪30年代对北平文化兴起的摩登时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号称有钱阶级之摩登男女,烫发、露胸、赤腿、高跟、口必红、眉必翠,终日流荡于跳舞场、电影院、各剧场、各公园,女云诱惑,男曰追求,憧憧往来,如鬼如蜮,此复成何世界?此岂国难期间所应有之现象?故吾甚愿侨居豪绅右族、游闲青年,毋恃势力以自大,毋溺淫僻以自废也。”[4]对于那些满是大腿、肩膀的商业片,许多人认为这是败坏了民族精神,呼吁负责人应该取缔这种不良的、不合时代的片子,而“易以教育的、国耻的爱国的片子,来教育儿童,警惕儿童,激励儿童,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沸腾他们的爱国情绪,养成他们的牺牲精神,为国家、为民族”[5]。他们从一开始就很强调文化艺术的政治功能。不仅学者如此,不少普通市民也甚为反感低俗文化充斥城市生活的现象。抗战结束后有读者写信反映上海广播电台每天播送的节目,“尽是一些陈旧的唱片淫糜的歌曲,以及低级趣味的滑稽,至于富有教育意义的各种讲座,则除英文而外,其他如历史、地理、科学常识等等,就绝无仅有了。”他指出,大多数的电台似乎都以盈利为目的,各种广告的节目,占了一大半时间,其语絮絮,闹人厌烦,不但得不到什么愉快,反且叫人讨厌。希望有关当局及各电台主人“不要专在利上面材算,让我们多听一些有意义高尚的音乐、常识和有价值的东西。”[6]
妇女的解放程度是一国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妇女的生活时尚会表现出醒目的变化。但是民国时期的不少知名市政学家对于这种时尚并没有太多好感,如著名市政学家刘郁樱就站在救亡的高度表达了对重庆市民的“女性审美期待”的反感:
女人们已是称为新时代的女性了,而社会上所崇尚的美的根本精神,仍然是优秀、柔弱一派,意识反映在女人们的身上来,便成为病态的人为的瘦而美的姿态体格、装束,这样瘦下去、美下去,弱柳迎风,落花依草,诚然是一件病的美术品。但是国难有些深了!抗争的事实,将不可避免。社会上需要壮美的体格,与激昂的情绪,更为迫切。人谁能以蒲柳之资,荏弱无力,而取得预备奴隶之地位?瘦而美的重庆女人,请你们强壮起来罢!自然男人们也应该发愤自强。[7]
如果说,刘郁樱的观点还是针对中国男人以柔弱为女性美的传统审美观而发,另一位著名市政学家殷体扬则对当时的妇女摩登时尚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取缔城市妇女的奇装异服。他阐述道:
将来民族之复兴,妇女也负了一半责任,如不及时觉悟,共同前进,国家前途是很暗淡的。大家知道苏俄妇女,人人工作,以及刻苦耐劳的精神,都应取法,至于取缔奇装异服,不过是促进妇女生活向上的一种至低限度的举动,还要妇女界自动起来革除过去的错误,人人都努力朝着创造路上进行,那才不愧新时代的妇女。[8]
这两位市政学家虽然批判的时尚略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希望妇女要由柔弱变为刚强。在刘郁樱的批评文字里,我们会发现,这位民国市政学者将女性美的形象定位于“壮美的体格、激昂的情绪”,这在今天的许多美学家看来,估计属于将“女性男性化”,等于抺杀了女性的个性。后来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女性形象与之极为类似,也遭到了不少当代人的批评。殷体扬的想法和后来的“妇女能顶半边天”“飒爽英姿五尺枪”等宣传何其相似!他们都是给予了妇女不亚于男性的能力期待,赋予妇女极强的政治使命,鼓励她们去承担国家、社会的改造责任,参与到社会的建设工作中去。如果我们从构建国民政治主体性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种将“女性男性化”的文化构建在于唤醒妇女的社会主人翁意识。并且,“妇女”在这里还有一种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它是弱者的象征,是整个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都处于柔弱、病态的形象的一个意象符号。唤醒妇女的自强意识,就是在唤醒整个民族的主体意识。所以,刘郁樱才要呼吁:“男人们也应该发愤自强。”
汪晖教授认为,在晚清以降的文化运动中,中国产生的真正新生事物,就是主权国家的政治形式,是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科学技术及其世界观的革命性力量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有机互动,是以现代教育和都市文化为中心展开的知识谱系与新的国家认同的关系,是一种能够将个人从家庭、地方性和其他集体认同机制中抽离出来并直接组织到国家认同之中的认同方式以及由此产生出的义务和权利的新概念,是在上述条件之下民族主体本身的更新。[9]将处于与政治隔膜状态中的妇女和市民们从声色享乐或家务劳动中脱离出来,促使他们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联系,使他们具有了国家、民族、国民的概念,政治主体性在这些实践中得以觉醒,这难道不是建立现代国家、构建现代国民必须具有的一个重要步骤吗?近代的市政建设也是为这样一个目标服务的。我们也可以说,从构建国民主体性的意义上说,新中国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工作和部分民国市政学者的“市民想象”存在着一定的延续性。
那么,随着市政活动的政治化,在官方和市政界那里,市政实际上也是一种运动群众的途径。一边通过市政建设构建起一种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政治空间,一边通过市政训导市民的日常规范。在市民对市政的参与活动中,市民被统治阶级塑造成“政治化”的市民。不过由于当权者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殊性,他们总是在政治化建设中将自己的特殊政治利益烙印其上,最有代表性的是国民党当局开展的新生活运动。当然,官方也承认市民有“正当娱乐”的权利,比如20世纪30年代沙市修建中山公园,民国官员阐述修公园的理由是沙市“在过去未有一个正当娱乐的场所,以致一般人在公余之睱,没有方法寻求正当娱乐,所以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惯。”[10]不过所谓“正当娱乐”这个概念本来就是政治性的。“正当”即意味着一件事取得了当时政治上的合法性,不合乎这种政治的娱乐就被视为“不正当娱乐”。“其实所讲的个人娱乐,无非是一些不正当的娱乐。”[11](P3)提倡“正当娱乐”就是在将娱乐“政治化”,排斥“世俗化”。在塑造提供“正当娱乐”的公共空间时,政府始终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烙印在这个空间中传播给市民。之所以将纪念堂建筑在中山公园内,当局承认“其用意是在使市民们在公余之睱到公园里去游览,随时看到中山纪念堂,随时就可以想到总理一生伟大的事业和人格,使我们时时刻刻去效法总理,同时努力实行总理的遗教,以图复兴民族,复兴国家。”[12]并说“在现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时候,本不应娱乐,不过娱乐在使身心获得健全,我们要想救国必须身体强健……希望大家,娱乐不忘救国,娱乐不忘事业,以成就伟大精神和伟大事业。”[11](P3)所以,娱乐也是为了救国救亡,无益于救国的娱乐自然是不正当娱乐。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加深,催动着人们强调用统一、集中的要求来塑造城市文化,规范市民人格。有人认为对所谓“现代文化”必须一分为二,“思想定要现代化的”,至于生活,在这民穷财困的时候,“却不必一定现代化,只来个‘纪律化’,已经足用了。”按照这个思路,论者以为生活上还是应当继续沿用传统生活方式,拒绝西式文明。“你们仍要用那价廉工省,连汤带菜的‘羊肉泡馍’,甚至‘白水泡馍’,万不必垂涎西餐馆里的‘英法大菜’呀!”[13]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仇家恨纷至沓来,如何将全体人民动员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更是成了时代的主题,也成了市政教育的主题。不少人对于当时市民文化的世俗色彩冲淡了政治追求的现状忧心忡忡:“现在是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群众时代,大多数人对于事理物情如不大了解,没有切肤之痛,怎么能够自动的集中意志和力量,怎么能够知道死有重于泰山去慷慨赴难呢?”[14](P8)“这个加强的工作,最适宜的还是由市政府来主动发起。”[14](P8)在这个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如怒涛排壑一般汇成汹涌澎湃之势的年代,市政教育比之前更加具有鲜明的为国家、民族服务的政治目的,个人主义的理念都要让步。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战时重庆新市政极其强调生活之“严整”“秩序”“整洁”“健康”为市民战时生活之准则。“重庆之美是重庆市民‘人格化’的表现,都市‘人格化’的美,表现是人类生活于有机的都市的一种共同意志、共同道德,与共同的精神。”[15]但是事实上,抗战时期的重庆仍然弥漫着一股奢靡享乐之风,而且这股风气就是那些官宦富豪带动的。有人描述:“我国打了四年仗,有钱的人,要吃什么就有什么,重庆有五六百家饭馆,每天收买山珍海味以待大贾高官。”[16]
二
如果以现代的眼光看去,既然市民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世俗性,政治家和学者们所批判的这种城市文化潮流体现的内容似乎就具有世俗化的“现代性”特征。中国城市由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向近代工商业功能转型,以追求世俗享乐、消费为主要目的,具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市民文化兴起具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他们所批判的这些文化现象,似乎正预示着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世俗领域在发展之中,但正是这些引起了许多政界和市政界人士的不快,亟欲将其纳入政治的规范中。这种思想是否是“反现代性”的呢?
追溯缘由,中国近代的城市执政者和学者对世俗文化至少在形式上呈如此反感态度,其直接原因是消费文化在当时确实对城市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因为中国城市生产能力一直较低,近代工业化尚在起步阶段,过分的消费倾向在现实里往往和发展城市经济、振兴城市工业的理想发生冲突。有志于“实业救国”之士常以此痛惜不已:“国货之代替不多,而价格则有时反较外货为昂,于是爱国心所驱使,终不敌事实上消费之选择,夫如是,工商业之振兴宁能有望?”[17]
如果从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为生产而生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资本发展的规律是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也就是说,新形成的资本愈来愈多地转入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经济部门。因此,这一部门必然比制造消费品的那个部门增长得快......因此,个人消费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总额中所占的地位日益缩小。”[18]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大大超过消费品的生产,如是形成资本积累,在这种生产方式统治下的城市必然是生产性远远强于其消费性。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西方中世纪以后的城市是随着生产功能的发展而出现消费文化和世俗化的市民生活,其“世俗性”或“消费性”不是对“生产性”的反动,反而是为其生产性服务的。相反,中国自宋明以来,虽然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市民文化的繁荣,仿佛具有了“现代性”特点,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其商业生产基本上是为满足城市里的官宦富豪们的奢侈生活需要而兴起的消费型商业,由此带动了崇尚奢靡的世俗文化风尚。这种通过上流社会的权贵们的奢靡享乐来带动社会风尚世俗化的文化发展模式在民国城市生活里也延续了下来,传统城市重消费轻生产的功能特点也继续得到了强化。一方面是生产功能薄弱,另一方面却是过于世俗性的市民文化,这种消费文化催生出了发达的商业资本。可这种消费商业和消费文化却既没有催生出现代工业,也没有催生出工业资本主义,这就使得城市长期停留在了消费型商业城市的层面。这种城市既缺乏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也缺乏生产精神产品的能力,只能消费外来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所以与其说这种“世俗文化”体现了“现代性”,还不如说它类似于一种“伪现代性”或“伪资本主义化”,结果是既阻碍了城市功能的现代转型,也阻碍了现代中国的形成。
因此,民国市政界对于那些文化时尚的反感,实质是对城市始终停留在消费型城市的反感。他们力图用政治手段和意识形态来建构一种“政治性”的城市文化,对“世俗性”的消费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以催动城市生产功能的勃发,具体做法是通过弘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来医治这种畸形的消费文化,提升城市文化的层次,这种想法在逻辑上存在着一定合理性。“为什么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特别重要,并且始终有新的意识形态产生,原因正在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建设需要依靠政治的力量进行信仰重塑与组织重建。”[19]当时的中国正是一个需要“政治性”的时期,并且在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也是长期用 “政治性”的视野来构建城市文化的,这其中确实有历史的内在要求。
但是事实上,民国时期以构建政治文化推动的城市转型并不成功。整个近代时期,中国城市经济始终没有跳出三大缺陷:(一)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大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分,占主要经济地位的是几千年来支持和构成城市经济主体的地主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如北平、苏州;(二)商业经济大大超过工业经济。据估计,1933年全国商业人员约1171万人,是当时工厂职工人数的24倍,商业资本约为工业资本的10倍。[20]1936年全国民族资本中工业净产值为11.7亿元,同年商业营业额达30亿元,高出工业产值近3倍。抗战前中国的商业资本约占工商业全部资本的70%。[21](P10)到1948年,中国商业资本所占比重已达90%,工业资本仅占10%左右。[21](P10)(三)消费活动大于生产活动,城市经济的消耗多于生产。城市消费的来源是依靠封建势力对农村的榨取、官僚豪门对民间的搜刮,以及商业资本对农民与一般小市民的剥削而得,还有一部分消费是以农产品和金银外汇的方式,流向国外而换得。由此可见,城市的工业生产功能始终十分薄弱,支撑城市经济的仍是消费性商业,民国时期对城市文化的构建理想并未实现。